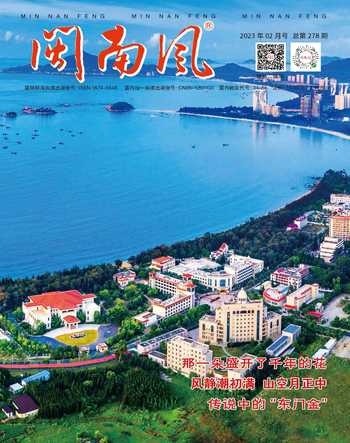古韻婺源
伍啟梅

初冬的婺源,并無寒意。身著秋裝,我首次來到了這座皖贛交界的小城。古韻盎然的城鎮,徽派建筑群鱗次櫛比。白墻黛瓦,高翹的馬頭墻,昂揚聳立在屋頂上,黑白分明,簡潔大方。這里街巷干凈,市井繁榮。星羅棋布的古村落,有小橋流水、進士村莊。幽谷聽泉聲,池塘見鴨歡。綠色的茶園,希望的田野,仿佛身在桃花源。晨起,賞石城云霧繚繞,炊煙裊裊;晌午,觀篁嶺曬秋、云梯人家;暮歸,品雨前茗眉、皇菊佳飲。星江河畔有朱子故里,鳳凰山下文人輩出,書香四溢。
嚴田村距紫陽鎮38公里,這個城郊小村莊自宋代到清末,共出過27位進士,其中有父子、兄弟、叔侄同登科。前輩的輝煌激勵后人,“山間茅屋書聲響,放下扁擔考一場”的民謠,折射出嚴田村耕讀文化底蘊之深厚。“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的家訓,鞭策嚴田人“讀未曉則思,思未曉則讀”的求學理念,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中產生出莘莘學子。書聲朗朗蔚然成風,世代相傳。
清道光二十一年,嚴田人朱錫珍考取進士,官至戶部云南司主事。家道貧寒的他,自幼勤奮好學,少年時在縣庠里求學,困了就打個盹。一次其父在他臨行時,將菜桶藏于被褥中讓他帶去,他則半月未打開被褥取出食用,足見他廢寑忘食攻讀之刻苦。他博學多才,深得當朝皇帝賞識,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這是進士中的頂級,為皇帝近臣,負責起草詔書等。他為官多年謙虛謹慎,廉潔奉公。著有《日新齋集》《讀史管見》《忍字輯略》等著作流傳于世。
走出進士堂,在村口千年古樟樹下,有一對年過八旬的夫婦,在篩選山茶籽。我好奇地過去打招呼,問“老伯伯,這么多山茶籽有啥用?”老伯母含笑道:“可以榨油,一斤60元,很便宜喲!”我又說:“你們進士村,真了不起呀!”他們驕傲地回答:“嚴田人自古愛讀書,若是三代不讀書,不如一窩豬。”聽罷,我十分震撼,耕讀文化已深入人心,普及婦孺,真不愧為進士村。閑聊中他們還說:“1977年恢復高考時,回鄉知青的兒子考上大學,畢業后在南昌工作,前些年省城的孫子也從名牌大學畢業,如今在上海成家立業,曾孫都是小學生了。”
望著滿臉自豪、雙手粗糙的一對老人,我油然生起一股敬意,向他們買了一瓶兩斤重的山茶油。
次日黎明前,我來到了山勢陡峭的石城村,只見旭日從遠處連綿起伏的山巒里冉冉升起。萬道霞光下,宛如仙境的村落在云霧繚繞中若隱若現,畫家架好寫生夾,正對景描繪。“長槍短炮”的攝影機不斷調整焦距、按下快門。我從如潮游人中擠出,站在山坡上,也用手機爭分奪秒搶拍晨曦中云蒸霞蔚的美景。還有那炊煙、云霧交織,變幻出奇異景色下的楓林、村舍、梯田、茶園。人們為難得的奇遇而驚喜,在人流涌動中各自尋找最佳的拍攝位置。這如夢如幻的人間仙境,只持續了一個時辰,當太陽高照時,就煙消云散了。
石城遠離縣城達50公里,偏僻的鄉村坐落在四面是峰巒的山洼里。這里不僅有變幻奇異的晨霧,還有800余年的香榧,枝繁葉茂。有600年之久的楓林,此時正值紅葉掛滿枝頭,一片一片紅得嬌美,艷得俏麗,恰似唐代詩人杜牧筆下“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的意境。
聽聞南宋民族英雄岳飛,在紹興元年領兵征討李成的時候,曾路過此地,并在石壁上用槍尖留下“石城”兩個鐵畫銀鉤的大字。“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真是拳拳愛國之心,滿腔豪情壯志。這里還保留著“十面埋伏”“韓信點兵”等楚漢相爭的典故遺跡。人文歷史在這個山勢險峻之地,留下了一段段深刻的印記。
晌午,我坐攬車登上了有著500多年歷史的篁嶺村。放眼望去,山高路遠的篁嶺梯田疊翠鋪綠,茶園嫩葉鵝黃;民居圍繞水口呈扇形梯狀,錯落有致,古香古色。這個有著186戶村民的村莊,自古被譽為云梯人家。
徒步越過一片原始森林,耳旁鳥語花香,腳下幽谷泉響。踩在落英繽紛的古驛道上,樹葉松軟舒適,一種久違的鄉愁油然而生,讓我想起了當年知青歲月走過的羊腸小道。那時,我十七八歲,在一個鄉村任民辦教師,時常要走山路往返于知青點和大隊、公社之間,起初非常膽怯,經過兩個學年的鍛煉,能輕松翻越5華里的山間小路。當我還沉浸在往日的思緒中,眼前豁然開朗,迎面而來的是一個熱鬧非凡、人來人往的古村落。
篁嶺村依山勢而建,從民宅、官邸、祠堂到牌坊,均蘊藏著數百年徽風皖韻的“徽三雕”圖案。在木雕、磚雕、石雕中,磚雕是徽派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素有“無宅不雕花”之說。抬頭仰望,這里的門樓、門罩、門楣都是取上好木材,鑲嵌在上面的花鳥禽獸,精雕細琢,栩栩如生,其工藝之考究,無不彰顯出徽派古韻,端莊典雅。這里的房屋是用白石灰粉刷外墻,用小青瓦蓋坡屋頂。高出屋頂的墻體,似馬頭昂起,壯志凌云。它既有防火的功能,也顯示造型上的美觀。
自古篁嶺村,地無三尺平。屋頂曬架,就成了秋收冬藏晾曬農作物的場所。聰明的農家人,順應自然地形,在自家屋頂搭起曬架,把從田間地頭采摘的新鮮蔬菜、瓜果,放入竹編的簸箕里晾曬。陽光燦爛時,只見各家各戶的曬架上,紅的辣椒,黃的玉米,金色的稻谷,綠色的茶葉,菊花,藥材,五顏六色,光彩奪目。隨著篁嶺旅游業的興起,這里吸引了海內外游客絡繹不絕前來觀光,篁嶺農家的植物晾曬,便成了聞名遐邇的篁嶺曬秋。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早在學生時代,我就背誦過這首家喻戶曉的古詩,如今來到作者的故里,怎能錯過瞻仰。

懷著對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的敬意,我來到了位于婺源城北的朱家莊,這里曾是朱熹二世祖、三世祖居住的地方,朱熹曾兩次到過此地祭祖、訪親。2013年冬,政府重新修繕后稱其為“熹園”,對公眾開放。
仰望石牌坊中的“文公闕里”四字,觀者無不贊嘆其石雕工藝精湛,字跡遒勁大方。門楣門樓,厚重古樸。沿著整潔的青石板路,我走進了熹園。寬闊敞亮的庭院,古樹掩映,花紅竹翠。石拱橋下荷塘水碧,木廊坊上雕梁畫棟。倘佯在亭臺樓閣,曲徑通幽中,倍感其優雅恬靜。園林地處星江河畔,面水依山,環境優美,風景秀麗。
款款步入“修齊堂”,這是朱家莊僅存的一幢徽式官邸。門罩上磚雕圖案的簡單,與室內木雕梁板的精美,產生反差,顯示婺源文人深受朱子文化影響而形成的收斂、含蓄、睿智的人性特征。而建于清末的“善慶堂”,是一座典型的徽派民居,整幢房屋中規中矩,巧妙地揉進了當時較為先進的玻璃飾材。房子呈兩進一天井,每進三間二房,表現出以天井為核心,左右對稱平衡的格局。“朱熹生平紀念館”是一布局小巧精致的家祠,天井開闊,明堂寬敞,體現明末清初徽派建筑天人合一的構思。
紫陽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時期最著名的書院之一。“紫陽”是朱熹的號,而婺源的紫陽書院更是以祭祀朱子、宣揚朱熹理學思想為宗旨,是讀朱子之書、傳文公之教,延續程朱學之脈的場所。走進“瑞云樓”,只見門枋上雕刻著朱熹《觀書有感》《春日》等詩文的意境圖。里側三根主梁上,鐫刻著囊螢夜讀、山中鄒魯、溫公警枕的典故畫面。來到“講堂”,這是讀書聽課、宣傳弘揚理學思想的學堂。明堂上懸掛著“圣學昌明”四個大字,十分醒目。兩邊是康熙帝賜的楹聯:“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進一定之規。”瞧,皇帝對朱老夫子給予多高的評價呀!正堂左右懸掛的是“忠孝廉潔”四字,是朱熹當年為岳麓書院題寫的四字教規。從此,“忠孝廉潔”之訓遍及天下書院,也成了官臣、子民做事做人的準則。步入“三賢祠”,我肅然起敬,明堂正中懸掛著程顥、程頤、朱熹三個人的畫像,大堂左右兩邊則擺放著編鐘、祭器、樂器,莊嚴中散發出一股濃濃的書香墨韻。我情不自禁地仰望他們,從他們那慈祥、睿智的目光中,我讀到了“心傳之奧”和“忠孝廉潔”。他們是“洛學”的創始人,是“理學”的傳承者,是華夏兒女的楷模,更是民族的驕傲!

北宋洛陽的程顥、程頤兩兄弟,是理學文化的創始人,而南宋的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他們的學說,成為一代理學大家。二程學說的核心觀是“存天理,去人欲”,后來被朱熹所繼承、發展、弘揚,世稱“程朱學派”。
依依不舍地走出三賢祠,越過古老的“引桂橋”,沿石階而上,便來到了“尊經閣”。這是一座兩層的閣樓,是朱家莊最高的建筑物。它與引桂橋、紫陽書院同在一條中軸線上,是朱家莊的藏書樓。用名貴木料打造的門窗,上面有精美的雕花,旋轉式樓梯直達頂樓,頂端有一個銀色的葫蘆,陽光下大放異彩。“為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先于讀書”,尊經閣上的對聯,多有哲理呀!古人云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人生,怎能不讀書呢?“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從古至今,在人們心中已形成共識,詩書傳家,以德育人。朱熹的理學思想,深深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婺源之美,不僅有她山光水色的天然美,更有她千百年來,人們用智慧和耕讀文化創造的美。美得就像一首詩,一幅畫,令人流連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