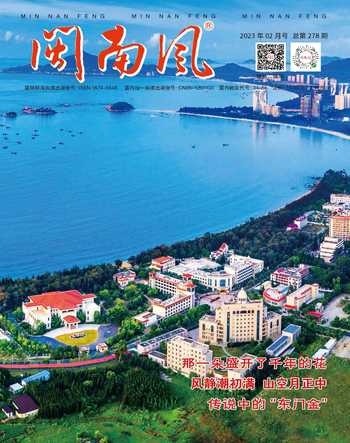尋找平衡
于燕青
老舍在小說《離婚》中有一段這樣的描寫:“張大哥的全身整個兒是顯微鏡兼天平。在顯微鏡下發現了一位姑娘,臉上有幾個麻子;他立刻就會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說話有點結巴,或是眼睛有點近視。在天平上,麻子與近視眼恰好兩相抵銷,上等婚姻。近視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麻小姐當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鏡,馬上進行雙方——假如有必要——交換相片,只許成功,不準失敗。”看了忍俊不止,按現今的話說,這位張大哥很現實,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很佩服老舍的神來之筆。現實中,看到有妙齡靚女嫁老翁的,在婚姻的天平上,青春美貌所對峙的另一邊要么是金錢,要么是名利地位,籌碼相當,達成平衡,仿佛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會憑空產生,也不會憑空消失,它只會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或者從一個物體轉移到其它物體,而能量的總量保持不變。”飲食男女的婚姻就是一種平衡。誰看到博士自愿嫁娶文盲?特定歷史環境另當別論。超現實主義繪畫大師達利,在學堂上被要求畫圣母時卻無厘頭地畫了一架天平,也許在他眼里圣母就是公平公義的化身?我不得而知。平衡,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公平、公正、不偷斤減兩、不傾斜。反正我就是一個在生命中不斷尋找平衡的人。
我跌倒多次。那一年的夏日,我再次跌倒了。我被抬上120救護車的那一刻,肉體難耐的疼痛以及心底的恐慌比車笛更凄厲。我知道這個世界每天都有人遭遇不幸,病了幾個人或死了幾個人,地球照樣轉,太陽照樣升起。那一夜,繁華的街市照樣車水馬龍,燈照樣紅酒照樣綠,就好像沒有災難發生過。可我的世界已然不同了,我的世界傾斜了。我一再地被問,你怎么又跌倒了?我無以回答,我若有答案我愿意像祥林嫂那樣一遍遍地回答他們,可我沒有答案。我只能一遍遍地咀嚼這句話。這句話將我引向兩個歧途,一個是身體的,一個是命運的。多數朋友認為我的身體出了毛病,而命運的那條路似乎有更強大的引力,讓我想到一些玄奧的,超出以往認知經驗的東西。我有限的思維都朝著這個方向傾下去、傾下去,我找不到平衡,我在人生的平衡木上舉步維艱。那時我開始脫發,一枕一地的落發紛紛嘆息著,嘆息我人生的坎坷,不平衡。
那個夏日我在醫院的骨科病房住了一段時間,我飽含汁液地綻放成一朵夏日災花。我從不知道我可以這般肥沃,疼痛在我的身體歡樂筑巢。我也因此結識了很多病友,殘弱病痛讓我們惺惺相惜,這是怎樣的緣分?一對夫婦下坡時摩托車車輪飛了,兩人摔成熊貓臉,男的表情凄慘,女的還能笑,雖有些勉強,她嘆了一口氣,說她去年同樣也作了骨科手術。我知道了,她笑是因為她在尋找平衡。另一女子,手指被機器軋斷,也是一副坦然的樣子,正當欽佩油然升起,并羞愧于自己的脆弱時,那女子忽然一個低頭便抽泣起來,我的心也疼了起來,我把面巾紙悄悄塞給她,她驚愕地抬頭說了很大聲的“謝謝!”嚇了我一跳。這是個知道感恩的人。隔壁病房有個要開腦的病人,據說他茫然的眼睛總是看向窗外,大家擔憂他的精神要出問題。從病房看出去,窗外,是同一個天空,天空下卻是不同的人。每個不幸的人都有各自的不幸,都要經歷一段痛苦的心路才能尋找到一種平衡,才能接受現狀,也許永遠都找不到平衡。這里的痛苦刺著我的眼球,這里聽不到為賦新詩強說愁。
到了夜晚,月亮似乎總是低懸的、幽暗的、詭異的,不再是“一鉤新月天如水”,月亮成了病人蒼白枯槁的映照。我特別想回到跌倒之前的日子,可惜生活沒有還原鍵。病房里的電視是打破夜空、打破孤寂的利器,我在電視里看到了本市第N屆飲食文化節開幕,打廣告的人白天已經竄進病房送來街頭小報,里面還有醫藥廣告,也有某影星的緋聞等等,某些健康到無聊的人正在弄出極大的動靜,這使我們的內心更加不堪。我躺在病床上翻開蘇珊·桑塔格的《床上的愛麗斯》,第一幕:暗場。(愛麗斯的臥室)護士的聲音:你當然起得來。愛麗斯的聲音:我起不來。護士:是不想起。愛麗斯:是起不來。護士:不想起。愛麗斯:起不來。哦。好吧。護士:想起。你想起。愛麗斯:先把燈掌上。
我那時也需要一盞燈,一盞能引領我走人生平衡木的燈,我是個平衡能力很差的人。文森特·梵高也是一個不會走平衡木的人。他渴望找到一家咖啡館展出他自己的作品,他起初信心滿滿,可是,在生活的磨難中他也沒能把持住,他沒有經濟來源,他的畫得不到世人的認可,感情屢屢受挫,經濟又拮據,成為弟弟的負擔,他一直在掙扎,他的天平一再失衡,以至于他沒能看見整個世界都成了他的咖啡館。就連我們這個小城也有一處以他命名的地方“梵高小鎮”。他的畫像和他的《星夜》印在墻上很大幅,他的畫有種攝人心魄的美,色彩凌厲的艷,他真的很會配色,他就是一個天才,只是天平失衡了。喬·麥克唐納說:“偉大往往是各種對立品質自然平衡。” 從梵高的自畫像看,雖然他眼神堅定,但整個面部表情依然落魄、狂躁、憤怒、憂郁。才氣、自信與頹廢、絕望在天平上較量著,天平在雙方的籌碼中搖擺不定,此起彼伏。他不知道,一旦天才成了天平的一端,另一端可能就是各種苦難,或是無邊暗黑的寂寞。天才,稍有不慎就能把人碾得粉身碎骨。他并不具備抵御這一切的能量。尤其高更的離去,仿佛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梵高畫了《高更的椅子》,那把有著紅漆的老式座椅成了他刺眼的寂寞。那《星夜》整個天空暗黑幽藍,那些充斥在星月之間的旋渦很暴力,他是在畫中釋放自己,終于,他沒能扛得住,他向著憂郁、憤怒的方向一路狂奔,天平徹底傾斜了。他最后的畫《麥田昏鴉》,整個畫面線條粗硬,那些黑黢黢的烏鴉仿佛是死亡的預告,梵高最終精神崩潰,自殺身亡。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的苦難也太普通了,甚至,普通得不足掛齒。可是,什么樣的苦難,都不能被虛拋、被荒廢,苦難應該開出花來,這也是一種平衡。可是我的苦難像干癟的種子,不能生根發芽開花,我配不上我的苦難。我沒有與苦難抗衡的東西,也就是說,我沒有任何籌碼可以平衡苦難這個大籌碼。我是多么的不甘,但我也曾經找到過平衡。那是我被雨后路面上的乳膠漆滑倒之后的事。我躺臥家中。高高翹起的腿,像一桿失去平衡的稱。那條腿腫得有兩條腿粗,青紫色發亮的皮膚像要漲破,大拇指甲脫落,血跡斑斑。恰逢鐘點工來做衛生,她見到我這個樣子立馬閉上眼不忍目睹,嘴里不住地感嘆:“水人沒水命!水人沒水命!”閩南語“水”就是漂亮的意思。她的話和她為我發出命運不公的嘆息,安慰了我,溫暖了我,幾乎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就像一桿破敗的稱終于找到了平衡點,我的眼淚流了下來。并非我真的自以為“水”,我知道那只是她對我的偏愛。我只是從“水”得到了啟示,看到那盤命運的葡萄,不全是青葡萄,也有紫葡萄。我開始數算我生命里的恩典,一個兩個三個……我數算不完,我空手來到這個人間,我已經得到很多。況且,苦難也給了我益處。這就是我尋找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