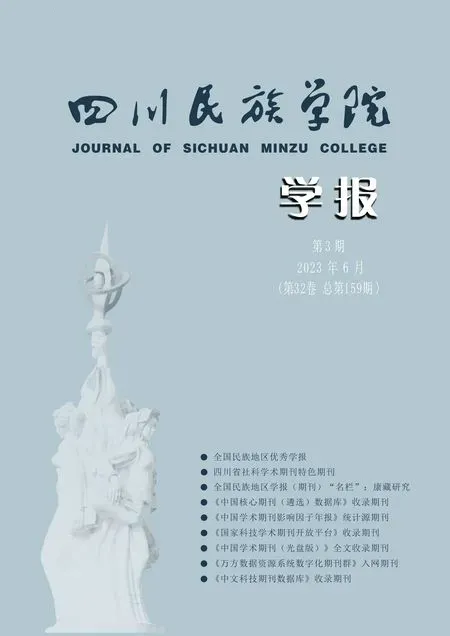“大一統”思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三重邏輯
吳宇晴 吳秀云
(安徽醫科大學,安徽 合肥 230032)
習近平總書記基于新時代我國民族工作的新特點,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1]39。走中國式民族問題解決的“正確道路”,離不開對中國傳統國家治理理念的歷史承繼。其中,“從歷史傳統看,‘大一統’始終是中華各民族的價值追求和最高目標”[2],“大一統”思想蘊涵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治智慧。近年來,國內學者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圍繞多方面、多維度展開,既從本體視角出發探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在發展,也從歷史維度深入研究其生成邏輯,并著眼于當前民族工作實踐進行實踐維度與價值維度的探析[3],但較少學者從“大一統”思想出發,進一步探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邏輯。因此,通過揭示“大一統”思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邏輯,進而明確其價值邏輯、推進其實踐邏輯,有助于深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新時代多民族“大一統”的政治格局。
一、“大一統”思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邏輯
“大一統”思想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淀,是我國傳統國家治理經驗的思想精華,蘊含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傳統。因此,從歷史源頭、內生動力、情感旨歸三個層面揭示“大一統”思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邏輯,有助于厘清“大一統”思想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源流關系,深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大一統”思想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源頭
中國歷史是一部各民族追求“大一統”理想的歷史,“大一統”始終是主流,分裂才是異態[4]。在我國歷史上,“大一統”格局最初見于周王朝,《詩經·北山》有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5]但“大一統”一詞最初見于戰國晚期儒學經典《公羊傳· 隱公元年》的首篇《春秋》:“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6]其中,將“王正月”釋為“大一統”,但西周式“大一統”在春秋時期早已難尋蹤跡。隨著西漢政局穩固、儒學復興,大儒董仲舒強調:“《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7]認為“大一統”合乎天地之道、遵循古今之法。在隋唐時期,統治階級變革了傳統官僚體制,創建了科舉制、三省六部制,以及相對成熟的文官制,這些制度在宋朝進一步完善,為維系我國傳統“大一統”格局輸送了大批政治人才。到了明清時期,統治階級則重視邊區管理與民族規治,形成了各民族“大一統”的融合格局,進而緩和了中原同外族的民族矛盾。在中國各大王朝的時代更迭中,“大一統”思想雖發生了歷史流變,但其追崇統一、崇尚整體的價值內核已逐漸為中華民族所內化,生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大一統”思想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生動力
縱觀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演進,能夠明確“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實現統一為己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視為中華正統,統一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分裂從來不得人心”[2]。“大一統”思想萌發于西周“大一統”的倫理基礎、穩固于秦漢“大一統”的政治體制、完善于隋唐宋“大一統”的官僚機制、發展于明清“大一統”的民族融合,已內化為各民族的政治信仰與社會共識,生長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生動力。“大一統”思想作為團結各民族的情感紐帶,雖歷經千年卻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感召力,一方面“大一統”思想的包容性激發了其生命力,“大一統”思想能夠與現代多民族國家治理體系相融合,并以符合各民族利益、貼合各民族文化、融合各民族特色的治理方式加深其內在的思想聯結,進一步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另一方面“大一統”思想的認同感強化了其感召力,能夠增強各民族的自覺意識,使各民族自覺進行心理聯結,進而形塑各民族的政治品格,深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三)“大一統”思想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情感旨歸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國各民族共同締造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集體民族認同,核心內容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8],這種“認同”從屬于對“大一統”格局的認同,其本質仍是服務新時代“大一統”格局的穩步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源于“大一統”思想,并汲取了“大一統”思想的情感內核,“大一統”思想之“一統”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共同”具有內在的情感聯系。其中,“大一統”思想之“一統”主要強調客觀層面的“一統”,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共同”則是吸收了“大一統”思想的核心意蘊所延伸出的情感共識,更加強調心理層面的“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大一統”思想的當代詮釋,既豐富了“大一統”思想的時代內涵,又依托其強大的認同力進一步鞏固了新時代多民族“大一統”的政治格局。總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求服務于新時代“大一統”格局的思想建設,回歸于“大一統”思想的情感系統。
二、“大一統”思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價值邏輯
“大一統”思想具有價值導向性,其中“天下一統”的疆域觀、“王權一統”的政治觀、“儒家一統”的文化觀、“華夷一統”的族群觀[9]作為“大一統”思想的歷史意蘊,從國家、政權、文化、民族四個層面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出了價值指向,要求強化各民族的國家認同、政治認同、文化認同以及民族認同,進而鞏固新時代多民族“大一統”格局。
(一)從“天下一統”的疆域觀到對偉大祖國的強烈歸屬
“天下一統”的疆域觀意指我國地理疆域的完整性及治理狀態的統一性。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繼承“天下一統”理念的歷史基礎上,更加注重從國民心理層面,提升中華民族對偉大祖國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主要體現在國家認同上。當前,以國家認同為心理基礎建構國家合法性是深化我國“大一統”格局的必然舉措,而“只有那些共享的價值觀、象征符號以及彼此接受的法律——政治秩序,才能夠提供必要的、廣泛流行的合法性”[10]。國家“政治秩序”或稱國家治理秩序作為穩固我國“大一統”格局的堅實地基,不僅是新時代強化國家合法性的制度設計,還是維系各民族國家認同的制度安排。但全球化的發展雖帶來工業化加速與城鎮化推進,但也引發了資本化擴張,極大地影響了鞏固中國傳統“大一統”格局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使部分民族群體出現身份認同的不協調,以及部分民族地區的歷史、文化、信念等地域傳統的包容性弱化。因此,為改變為這種局面,要求不能僅僅局限于“天下一統”理念所強調的客觀層面的國家統一,而應深入到各民族的心理層面,不斷強化中華民族對偉大祖國的歸屬感。
(二)從“王權一統”的政治觀到堅持黨領導的強大共識
“王權一統”的政治觀意指我國歷代中央王朝政治形態的穩定性及政治權力的集中性。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演化于“王權一統”的政治格局,汲取了“王權一統”理念的積極內容,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局限于客觀層面政局與政權的穩定集中,而是更加強調心理層面的政治信仰與政治認同。在中國政權更迭的歷史演進中,我國政權最終實現了從“王權”到“民權”的歷史轉向,“民權”即公民的政治權利,最初在現代意義上對“民權”進行系統闡述的是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即政治革命,但由于中國歷史與中國人民的堅定選擇,最終將徹底實現“民權”這一偉大的政治使命落于中國共產黨肩上,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族進行英勇斗爭,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在中國真正意義上形成了多民族“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使中華民族的政治信仰更加堅定乃至凝結為堅持黨領導的強大共識。在新時代新起點上,這種政治共識必將匯聚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族共創歷史新成就的磅礴力量,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三)從“儒家一統”的文化觀到對中華文化的深切認同
“儒家一統”的文化觀意指我國思想意識的凝聚性以及文化傳統的整合性。“儒家一統”理念將儒家文化置于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使儒家文化烙上政治色彩,因此自漢代以來儒家文化便承擔起政治教化的重要任務,但居于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高位”并非真正能夠使各民族在心理層面達到深切認同與真正接受,因此儒家文化經中國千百年的歷史“揚棄”,其思想精華最終熔鑄于各民族“共同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11]。中華文化在中華各族人民傳承創新的歷史實踐中“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價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12],沉淀著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深切認同。這種“共同的”文化認同意味著各民族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真正接受,既充分詮釋了“大一統”思想的文化導向,又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力量。現今,面對文化虛無主義引發的多重認同危機,應高度重視中華文化的時代價值,促進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深切認同,為構筑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注入文化力量,進而深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四)從“華夷一統”的族群觀到團結各民族的堅定信念
“華夷一統”的族群觀意指我國民族關系的和諧性以及少數民族的團結性。“華夷一統”理念為清朝所倡導,但其形成演進卻歷經多朝更迭,如先秦時期所萌生的“華夷之辨”觀念、漢代所強調的“華夷首足論”、魏晉南北朝時期所盛行的“華夷”皆正統之論調、宋代所形成的“禮別華夷”之觀等,在這漫長的歷史演化中,最終于清朝完成了從“華夷之辨”到“華夷一統”的時代轉向。同時,“華夷一統”理念作為古代統治階級提出的民族治理理念,更多地強調各民族在客觀層面上的和諧團結如沒有戰火紛爭、民族矛盾等,往往缺乏從心理層面強化各民族情感聯結的思想意識。因此,為鞏固多民族國家、處理多民族問題、發展多民族關系,要求不斷增強團結各民族的堅定信念,習近平總書記將“民族團結視為各族人民的生命線”[13],民族團結以“生命線”的天然形態聯結著各族人民的社會交往,極大地拉近了各族人民的心靈距離,這種堅定信念也將轉化為各民族間牢固的“生命聯結”,深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時代應通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4],從而真正實現以民族團結促民族進步,以共同奮斗促共同富裕,最終以民族團結為戰略基點鞏固多民族“大一統”的政治格局。
三、“大一統”思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邏輯
在中華民族千百年的歷史實踐中,“大一統”思想以國家發展與民族進步為基準不斷調適,在中國歷史上創造了輝煌成就。面對新時代的偉大實踐,應加快國家治理創新進程、堅持完善黨的領導制度、弘揚中華優秀治理傳統、提升民族區域治理效能,不斷凝聚、引領、深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而鞏固多民族“大一統”的新時代國家治理秩序。
(一)加快國家治理創新進程、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大一統”思想蘊涵著樸素的國家治理觀,要求通過制度治理鏈接法律、技術、人民、全球等多主體治理,進一步創新國家治理體系,提升國家治理效能,從根本上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大一統”思想強調制度的完善性是古代“圣王”的治理追求。1980年鄧小平在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失誤教訓時,指明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15],中國制度作為國家治理的頂層設計,是鞏固多民族“大一統”格局、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保障,因此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模式,其根本就在于堅持制度治理。其中,依法治國作為制度治理的組成部分,是實現國家治理制度化、法治化、現代化的基本方略,新時代堅持走依法治國道路,必須以“良法”促“善治”,在法治軌道上堅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國家的效能,最終實現國家治理的法治化與現代化[16]。在數字時代,數字治理已成為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當前將數字技術賦能國家治理,以數字化服務、數字化管理為主線提升數字治理能力,進而打造數字政府已成為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一項長期發展戰略。但數字治理本質上仍是人民治理,以人為主而非以技術為主,人民借助數字工具不斷強化國家治理效能,有助于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進而提升我國全球治理效能,增強我國全球治理話語權,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參與全球治理的“入場券”,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國家治理模式的轉型升級提供了發展平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導著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實現良性互動,進而極大地凝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堅持完善黨的領導制度、引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大一統”思想強調“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17],“堅持黨的領導”作為我黨百年奮斗經驗的第一條,要求堅持完善黨的領導制度,發揮制度優勢、推進制度創新、提升制度自信,不斷引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國共產黨是先鋒型政黨、群眾型政黨、使命型政黨的辯證統一[18],我國通過制度設計,將“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政治共識上升到制度層面,確立了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歷史經驗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17]。一方面,要求深化制度優勢推進制度創新。以黨的自我革命精神完善黨的領導制度,堅持戰略思維與底線思維相結合,重點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全面落實黨的組織安排、系統深化黨的統籌規劃,堅持從制度設計層面加強黨的政治領導,從制度執行層面強化黨的戰略決策,從制度反饋層面優化黨的政策落實,結合新時代的偉大實踐創新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不斷完善黨的監督體制、健全黨的反腐機制、深化黨的斗爭意識,進而形成科學的制度安排、完備的制度結構、有效的制度耦合[18],真正在制度層面做到“兩個維護”。另一方面,要求在制度創新中提升制度自信。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在實踐創新中將其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通過創新黨的領導制度執行機制、提高黨的領導制度執行力度、強化黨的領導制度執行效能,實現治理效能的社會積淀、力量勃發與真實反饋,進一步將其效能優勢轉化為制度自信,同時當制度自信作用于社會主體,能夠自動對外輸出政治認同,使各民族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有助于引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新時代多民族“大一統”的政治格局。
(三)弘揚中華優秀治理傳統、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大一統”思想扎根于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文化土壤,是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橋梁,必須堅持以科學理念為指導探索科學方法,在教育實踐中實現歷史傳承,在“兩個結合”中推動創新發展,在數字時代加快跨域傳播,持續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文化興則國運興,中華優秀治理傳統承續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必須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好”[17]。首先,新時代推動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傳承與創新,必須強化其“辯證意識”“價值意識”“體系意識”“功能意識”以及“融合意識”[19]等科學理念,堅持以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為指導思想,提煉提純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多重價值,充分發揮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多元功能,科學完善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傳承創新體系,不斷推進中華優秀治理傳統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其次,在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歷史傳承中,應不斷優化中華優秀治理傳統教育體系,打造專業化教師團隊,將中華優秀治理傳統融入大中小幼的思政教育中,助推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入腦入心,實現“三全育人”。再次,在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時代創新中,既要將中華優秀治理傳統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加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也要將中華優秀治理傳統同時代精神相結合,實現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時代創新。最后,在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跨域傳播中,應充分發揮新媒體的新優勢,拓寬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傳播空間,重塑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話語體系,培育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傳播人才,不斷提升中華優秀治理傳統的傳播效率。
(四)提升民族區域治理效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大一統”思想蘊涵著豐富的民族區域治理智慧,最終會沉淀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情感內核,新時代必須堅持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融入多民族治理,進一步團結各民族力量、提升民族區域治理效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結構形式和民族問題處理模式的偉大創造。”[20]當前,堅持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已成為新時代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現實要求。其一,在面對全球化、信息化、城鎮化的多重沖擊時,應結合各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探索其個性化民族自治模式,進而提升民族區域治理效能。其二,應高度重視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始終堅持以《憲法》為根本指導,以《民族區域自治法》為主軸,與時俱進地完善民族區域自治的各項法律法規。其三,為更好地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應建立健全民族自治權力監督體系,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的權力體制,提升民族自治機關的治理能力與權利意識,破除民族區域自治的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優化民族自治地方的干部結構,打造覺悟高、能力強的少數民族干部隊伍,進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新時代多民族“大一統”格局。其四,應在弘揚社會主旋律的現實前提下充分吸收各民族特色,創造出為各民族所喜聞樂見的精神產品,借助精神產品生成情感鏈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五,應從思想意識層面深化各民族的認同感,不斷“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充分發揮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制度優勢,并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民族區域治理效能,以治理效能的強化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
四、結語
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既是千百年來人民群眾的殷切希望,更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大一統”思想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緊密的邏輯關聯,能夠以其歷史邏輯明確價值邏輯、以其價值邏輯推進實踐邏輯。新時代以“大一統”思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高度重視“大一統”思想的時代價值,注重從客觀層面的“一統”深入到心理層面的“認同”,不斷完善多民族“大一統”格局的治理體系,進一步深化中華民族的國家認同、政治認同、文化認同以及民族認同,助推新時代多民族“大一統”格局的系統優化,進而為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1]58奠定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