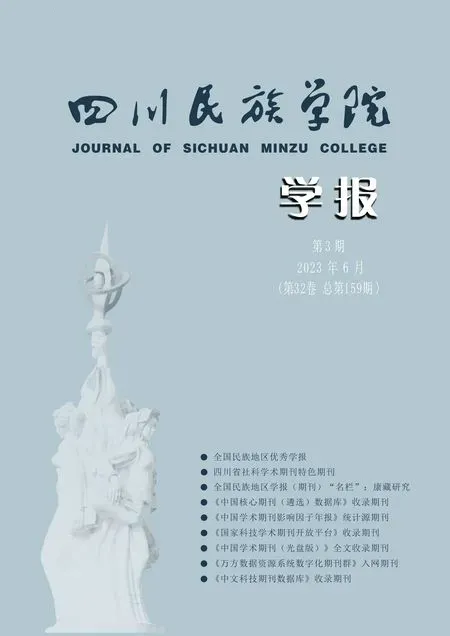四川羌族舞蹈作品創(chuàng)作研究
王利橋
(四川音樂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0021)
羌族,中國西部的一個古老民族,又稱“云朵上的民族”。羌族舞蹈以其獨特的動律特征、體態(tài)特征、審美特征及藝術(shù)魅力,并以身體為文化符號來記錄、反映羌民族的生產(chǎn)生活與精神品質(zhì),其始終伴隨著羌民族的成長與發(fā)展。
一、羌族舞蹈作品創(chuàng)作發(fā)展歷程概述
羌族舞蹈歷史悠久,但其作為舞臺劇場化藝術(shù)舞蹈的形式呈現(xiàn)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據(jù)現(xiàn)有史料記載,1946年,在重慶舉辦的“邊疆音樂舞蹈大會”上,由彭松先生主導(dǎo)創(chuàng)作、表演的羌族舞蹈作品《端公驅(qū)鬼》驚艷亮相。其“以該地羌族端公跳鬼時所用羊皮鼓舞及用于做法趕鬼的三色棍舞加工改編。舞蹈寓驅(qū)逐邪惡,迎來吉祥之意。”[1]
在此之后,羌族舞蹈以藝術(shù)表演的形式搬上舞臺是在十余年之后的1957年了。據(jù)《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藝術(shù)志》史料資料記載:“1957年,登珠編排出《一瓦白學(xué)》,古萍玉編排出《搶帕子》。”[2]自1946年由彭松先生創(chuàng)作并表演的首個羌族舞蹈作品起,羌族舞蹈以舞臺表演的形式出現(xiàn)在大眾視野之中的七十余年里,其表演團體在川內(nèi)以專業(yè)舞蹈院校和專業(yè)舞蹈院團為主導(dǎo),尤其是川內(nèi)地方院團(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團、茂縣羌族歌舞團),院校(西南民族大學(xué)、四川音樂學(xué)院、阿壩師范學(xué)院)。而川外地區(qū)創(chuàng)作、表演團體以專業(yè)舞蹈院校為主。
自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團1950年建團以來,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羌族舞蹈作品。繼1957年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團創(chuàng)作了《一瓦白學(xué)》《搶帕子》之后,在60年代又創(chuàng)作了《扳玉麥》《摘蘋果》《火盆花兒獻北京》等作品,并于70年代又創(chuàng)作演出了《喜迎鐵牛上羌寨》《噴灌好》《鈴鼓聲聲慶豐收》《毛選五卷到羌寨》等一批具有濃厚時代氣息的作品。從這些羌族舞蹈作品中我們能夠感受到當年全國人民熱火朝天抓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場景,以及羌族民眾對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的熱切擁戴之情。但由于地理位置較為閉塞,加之當時信息的傳播力度等原因,其僅在四川地區(qū)有一定的影響力,并未被全國廣大人民所熟知。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影響力,羌族舞蹈也得到了更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1980年,在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藝會演中,由蔣亞雄創(chuàng)作的女子獨舞《羊角花開》和馬壽年創(chuàng)作的群舞《鎧甲舞》得到全國舞蹈界的極大關(guān)注,羌族舞蹈因此被國內(nèi)更多舞蹈人所熟知和喜愛。而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羌族舞蹈的創(chuàng)作和表演團體主要集中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1982年,四川省歌舞團編導(dǎo)潘琪、呂波創(chuàng)作的作品《百合花》誕生,標志著羌族舞蹈作為藝術(shù)作品的樣態(tài)在四川省范圍內(nèi)得到廣泛傳播。隨著更多專業(yè)創(chuàng)作、演出人才的加入,羌族舞蹈作品的題材與表現(xiàn)領(lǐng)域也逐步擴大,其影響力也隨之增強。而后又有編導(dǎo)梅永剛先后創(chuàng)作出了《腰帶舞》《爾瑪姑娘》《依娜麥達》等羌族舞蹈佳作。
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以后,受到汶川大地震事件的影響,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保護和傳承民族傳統(tǒng)文化。這為羌族舞蹈帶來了良好的發(fā)展機遇。在此期間,羌族舞蹈作品相比以前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并呈現(xiàn)出良性發(fā)展態(tài)勢。首先,涌現(xiàn)出了一批大型的舞蹈作品,例如《羌魂》這樣的原生態(tài)歌舞以及《云朵·薩朗姐》這樣的羌族情景詩畫樂舞。雖然《震撼》舞蹈詩、大型音樂舞蹈詩劇《5.12不能忘卻的記憶》以及大型史詩《大北川》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羌族民間舞蹈,但編導(dǎo)們?nèi)匀煌ㄟ^現(xiàn)代舞的表現(xiàn)形式成功傳達了羌族民眾在汶川大地震中堅強不屈、不屈不撓的精神內(nèi)涵。其次,不論是在全國專業(yè)舞蹈比賽中獲獎的作品,如《羌》《春到百合開》《羌繡》《跳羌紅》,還是在“大學(xué)生藝術(shù)節(jié)”上展示的作品,如《羌寨歡歌》《星火》,以及在“中小學(xué)生藝術(shù)節(jié)”上獲獎的作品,如《羌山羊趣》,甚至是在業(yè)余群眾舞蹈比賽中出現(xiàn)的作品,例如四川省第八屆少數(shù)民族藝術(shù)節(jié)舞臺藝術(shù)精品大賽業(yè)余組比賽獲獎作品《繡春》,以及藍天老年大學(xué)民族舞班創(chuàng)演的《太陽里走出來的羊角花》等等,我們都可以看到羌族藝術(shù)舞蹈作品的身影。這些作品也充分展示了羌族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表演,以多層次、多方位、全視角的方式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
二、羌族舞蹈作品創(chuàng)作與政治經(jīng)濟的關(guān)聯(lián)
(一)羌族舞蹈作品創(chuàng)作與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
回望過去,羌族舞蹈作品的創(chuàng)作和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可謂息息相關(guān)。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從羌族舞蹈作品的創(chuàng)作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伴隨著國民經(jīng)濟的發(fā)展,國家層面專門組建了專業(yè)的藝術(shù)院團,用以發(fā)展文化藝術(shù)事業(yè)。因此,羌族舞蹈作品《一瓦白學(xué)》《搶帕子》等才得以在舞臺上展現(xiàn)。尤其是在2008年經(jīng)歷汶川大地震后,羌族文化受到極大的破壞,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來進行羌族文化藝術(shù)的搶救和保護工作。因此,羌族舞蹈也迎來了一個良好的發(fā)展機遇,涌現(xiàn)出了一批羌族大型舞作。例如,大型原生態(tài)歌舞《羌魂》、羌族情景詩畫樂舞《云朵·薩朗姐》以及大型史詩《大北川》等作品。隨著國家經(jīng)濟的發(fā)展,社會的進步,尤其是近些年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精神層面需求也極大提高,我們發(fā)現(xiàn),羌族舞蹈由于其獨特的動作律動、柔美的舞姿,不論是在舞蹈作品的創(chuàng)作演出中,還是在業(yè)余群眾的健身訓(xùn)練中,都有其身影。從綿陽市文化館、綿陽市老齡辦藝術(shù)團參加四川省第八屆少數(shù)民族藝術(shù)節(jié)舞臺藝術(shù)精品大賽業(yè)余組中獲獎節(jié)目《繡春》和藍天老年大學(xué)民族舞班參加“我和我的祖國”文藝匯演的節(jié)目《太陽里走出來的羊角花》中,以及代表中國赴俄羅斯進行民間交流演出的羊角花藝術(shù)團所演出的《珙桐千姿花沐春》里,我們都能切身感受到羌族舞蹈的全民參與和推廣。
(二)羌族舞蹈作品創(chuàng)作與國家政治緊密相連
羌族舞蹈作品的創(chuàng)作不僅與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與國家政治也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羌族舞蹈作品的創(chuàng)作始終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長。正是由于國家專業(yè)院團政策制度的建立,才使得有專門的人員從事舞蹈的創(chuàng)演活動,這也勢必會促進舞蹈作品的產(chǎn)生發(fā)展。由于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特定社會環(huán)境,中國文藝的發(fā)展深受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的影響,特別是藝術(shù)社會學(xué)理論的影響,即“高度重視和主要著眼于藝術(shù)對現(xiàn)實生活和革命斗爭的實際效用,從而強調(diào)藝術(shù)對現(xiàn)實生活的某種模寫、反映、認識”[3],羌族舞蹈創(chuàng)作也正是這樣。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受到“雙百”方針文藝政策的影響及關(guān)于民族民間舞蹈保護與利用的一系列政策出臺,明確要求文藝工作者要不遺余力地向民間學(xué)習(xí),取其精華,舞臺藝術(shù)創(chuàng)作、羌族舞蹈作品亦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chǎn)生的。受其影響,涌現(xiàn)出了一批由專業(yè)舞蹈工作者改編傳統(tǒng)民間舞蹈而成的舞蹈作品。編導(dǎo)們以原生態(tài)民間舞蹈為素材,借鑒并發(fā)展了民族民間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手法,使之能夠反應(yīng)社會嶄新的生活和當代人的感情。因此,創(chuàng)作了《一瓦白學(xué)》《搶帕子》《羌寨的春天》等作品。
20世紀60—70年,因國家政治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舞蹈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也進行了一系列貼近時代的改良,廣大舞蹈工作者積極響應(yīng)黨的號召,以飽滿的熱情點燃了激情四溢的創(chuàng)作熱潮,其作品和演出發(fā)揮著極大的鼓舞士氣與推動社會發(fā)展的作用,同時也自然且有力地推動了羌族舞蹈作品的創(chuàng)作發(fā)展。我們可以從《扳玉麥》《摘蘋果》《火盆花兒獻北京》《喜迎鐵牛上羌寨》《噴灌好》《毛選五卷到羌寨》這些作品中得以明晰。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隨著保護羌族文化國家政策的出臺,一系列大型舞作得以面世,可見羌族舞蹈作品的創(chuàng)作與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
三、羌族舞蹈作品創(chuàng)作與社會生活的關(guān)聯(lián)
(一)作品表現(xiàn)內(nèi)容源于社會生活
任何藝術(shù)都是對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因此社會生活是舞蹈創(chuàng)作的源泉和基礎(chǔ)。羌族舞蹈作品以羌族民眾的社會生活為“根基”,并在此基礎(chǔ)上產(chǎn)生了大量優(yōu)秀作品。從以往作品的歷史軌跡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不僅有塑造勤勞樸實、熱愛生活的羌民形象的舞蹈《鈴鼓聲聲慶豐收》《噠板》;有敘述羌族青年男女愛情的舞蹈《依娜麥達》《羌寨里的年輕人》《坐花夜》;有描繪羌年祭山會場面的《跳羌紅》;更有表達抒發(fā)羌族民眾迎接新生活的幸福與喜悅之情的《鴿子花開》《羌繡》等等,可謂碩果累累。這些作品不僅流露出濃郁的傳統(tǒng)風格與民族特色,同時也具有現(xiàn)實性與時代性,堪稱佳作。
羌族民眾在婚嫁、喪葬、豐收等重要的社會活動中,通常都會舉行各種群眾性的舞蹈活動。編導(dǎo)即以此為內(nèi)容,創(chuàng)作出了大量的舞蹈作品。例如:群舞《鈴鼓聲聲慶豐收》——以羌族羊皮鼓和鈴鐺為道具,通過敲擊羊皮鼓、搖響鈴鐺等動作描寫了羌寨糧食豐收的歡樂場面并表達羌族民眾豐收后的喜悅心情。舞者們通過變幻的隊形和活潑生動的舞姿,展現(xiàn)了羌族男女充滿喜悅的心情,同時表現(xiàn)出了羌族民眾在喜慶豐收時的獨特習(xí)俗。尤其是男子獨舞《噠板》,舞者將勞動工具“噠板”帶到舞臺,通過擊打帶有聲響的“噠板”,模擬了羌族民眾在豐收時刻的喜悅景象。這一表演不僅反應(yīng)了當代羌族民眾內(nèi)心的喜悅,還展現(xiàn)了他們勤勞淳樸的民族氣質(zhì)。勤勞勇敢的羌族民眾用“噠板”既不斷敲出了自我內(nèi)心的喜悅,亦敲出了羌族民眾新時代下幸福美好的生活態(tài)度。群舞《羌寨里的年輕人》以羌族喜事鍋莊為主要元素,描述羌寨里的青年男女談情說愛的場景,以舞蹈的方式表達了羌族青年男女對愛情的憧憬和追求。群舞《依娜麥達》以濃郁的羌族傳統(tǒng)舞蹈形態(tài)為依托,加之幽默詼諧的情節(jié),形象生動地展現(xiàn)了羌族青年男女樂觀豁達的生活狀態(tài)。女子群舞《坐花夜》則以羌族古老的婚俗“花夜”為創(chuàng)作背景,將羌族姑娘們靈巧優(yōu)美的舞姿與羌族婉轉(zhuǎn)動聽的民歌聲及民族器樂聲融為一體,隨著歡快的歌聲,羌族姑娘們將羌鈴串成一圈圈美麗的弧線,將羌寨姑娘出嫁前載歌載舞過“花夜”的情景藝術(shù)化地呈現(xiàn)于舞臺之上,極具民族特色。而男子群舞《跳羌紅》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急需保護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項目《羌年》與羌族古老的“轉(zhuǎn)山會”為創(chuàng)作背景,通過羌族傳統(tǒng)動作的重組與創(chuàng)新以及道具——紅色長綢的運用,極力展現(xiàn)羌族的生命顏色與狀態(tài),同時也讓觀眾感受到羌民族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社會生活場景。
(二)作品風格特征源于社會生活
在眾多羌族藝術(shù)作品中,舞蹈動作風格鮮明,動作形態(tài)主要表現(xiàn)為“一順邊”“出腳頂胯”“拐腿”和“胯部的軸向轉(zhuǎn)動”。究其緣由,與其民族地域和歷史文化有著極大的關(guān)系。在舞蹈時,羌族民眾會做出同手同腳和出腳頂跨的動作,這種動作的形成符合羌族民眾的生活習(xí)慣。羌族民眾在狹窄的山路中負重前行時,同手同腳地進行運動是相對省力和安全的行為。這一行為在體現(xiàn)羌族民眾勞作過程中生活智慧的同時,也形成了羌族舞蹈所特有的韻律。呈現(xiàn)出的舞蹈動作不僅有較好的藝術(shù)觀賞性,也體現(xiàn)出羌民族獨特的民族特色。由于淳樸的原始生殖崇拜及審美觀念等因素影響,羌族舞蹈胯部動作顯得極具特色,進而影響到羌族舞蹈特征、體態(tài)特征、審美特征的形成。
在羌族舞蹈作品中,不管是《腰帶舞》《春到百合開》《坐花夜》,還是《羌繡》《一川春露》《瓦爾俄足》等作品,都在“一順邊”“出腳頂胯”“拐腿”和“胯部的軸向轉(zhuǎn)動”的動態(tài)特征上顯得尤為突出。例如:女子群舞《春到百合開》突出地運用了羌族舞蹈中“胯部動律”,包含了“頂胯”“擺胯”“轉(zhuǎn)胯”“晃胯”“篩胯”等多種胯部姿態(tài),姿態(tài)構(gòu)圖和隊形變換融合在一起,羌族姑娘的青春氣息、美麗氣質(zhì)一覽無遺。女子群舞《坐花夜》則是在舞蹈語匯的呈現(xiàn)和表達上、在羌族極具特點的“S”形運動路線上做足了功夫,將其與“出胯”“拐腿”等動作姿態(tài)巧妙地有機結(jié)合,不僅突出了女性的俏皮活潑,更展現(xiàn)了女性之間深厚的情誼。女子群舞《羌繡》將羌繡的勞作過程藝術(shù)化地提取和展現(xiàn),將“甩線軸、繞線軸”等羌繡勞作過程與“出胯”“拐腿”等羌族舞蹈動態(tài)巧妙結(jié)合,舞蹈就是勞作,勞作好似舞蹈,二者完美融合,取得了精妙的藝術(shù)效果。女子獨舞《一川春露》通過“一邊順”和“頂胯”的動作,表達了人們在“下雨了”這個場景中的欣喜之情。[4]150并通過雙膝跪地,伸展雙臂懷抱大地的動作,表達著勞動人民對土地最真實的熱愛,讓觀眾仿佛也能聞到春露中羌山泥土與花草的清香,也能品嘗到羌山春露帶來的甘甜,充分感受到羌族民眾迎接春露時的欣喜之情以及對大自然的熱愛。尤其是女子群舞《瓦爾俄足》,該作品以胯的軸向轉(zhuǎn)動為主要舞蹈語匯,從細小的擺胯到帶動全身的胯部轉(zhuǎn)動,進行了較為大膽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用女性極致的美感呈現(xiàn)出生命力的無限延續(xù),也充分彰顯出編導(dǎo)獨特的審美追求。
四、羌族舞蹈作品與創(chuàng)作人才的關(guān)聯(lián)
(一)舞蹈編導(dǎo)對作品的發(fā)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在羌族舞蹈作品創(chuàng)作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舞蹈編導(dǎo)深入生活,對羌民族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及舞蹈語匯進行充分了解和認識,再結(jié)合自身積累的生活經(jīng)驗和對藝術(shù)審美的思考、提煉、加工,進而創(chuàng)作出反映羌族民眾情感生活的舞蹈佳作。在作品創(chuàng)作時,編導(dǎo)們除了選擇羌族薩朗舞、羊皮鼓舞、鎧甲舞等與生活緊密相關(guān)的題材作品外,還有部分編導(dǎo)并不局限于既定的民間風格與形式,而在文化與審美追求上尋求新的突破。例如《腰帶舞》《爾瑪姑娘》《瓦爾俄足》《羌》等作品。
在女子群舞《腰帶舞》中,編導(dǎo)梅永剛將系在羌族姑娘腰胯上的“腰帶”作為身體動律延展的重要道具,隨著身體舞動,飄蕩的“腰帶”便開始發(fā)揮它的功效,逐步展現(xiàn)著羌族女性不同的動態(tài)情狀。通過系在羌族姑娘腰胯上的腰帶和“S”型的胯部動律——側(cè)身頂胯、身體呈“S”狀的體態(tài)舞姿,觀眾享受到一場美輪美奐的視覺盛宴,羌族特有的舞蹈服飾、羌族女性獨特的氣質(zhì)以及民族的性格都得到了藝術(shù)的升華。女子群舞《爾瑪姑娘》則主要采用了肩部和胯部細碎、重復(fù)地抖動甚至晃動,加以“重復(fù)”技法,將這種肩部、胯部細碎的動態(tài)運用到極致,從而表現(xiàn)出少女由內(nèi)而外歡快的心情。女子群舞《瓦爾俄足》在保持“S”型的體態(tài)動律下,恰到好處地運用了胯部動律和肩部動律,并在此基礎(chǔ)上不斷地發(fā)展變化。從細小的擺胯到帶動全身的胯部轉(zhuǎn)動,從肩部微微而節(jié)奏平緩地轉(zhuǎn)動到大幅度且起伏不平地變化轉(zhuǎn)動,在不斷變化中呈現(xiàn)出生命力的真實狀態(tài)。群舞《羌》以“5.12”汶川特大地震為創(chuàng)作背景,創(chuàng)新性地將帶有羌族舞蹈元素的動作與當代舞表現(xiàn)方式相結(jié)合,[4]130于差異中見和諧,展現(xiàn)了羌族民眾堅韌不拔、眾志成城、戰(zhàn)勝災(zāi)害,涅槃重生、撥云見日之景象。在作品的動態(tài)設(shè)置中,將傳統(tǒng)舞蹈中手臂呈彎曲上撩的姿態(tài)發(fā)展為手臂貼身快速上揚的動作,將動作進行了“質(zhì)”的改變,使舞蹈更加切合作品所表達的奮進、向上地精神內(nèi)涵。另外,對身體軸向轉(zhuǎn)動的節(jié)奏處理和對屈膝時下顫頓挫的風格處理貫穿作品始終,舞蹈動作顯得沉穩(wěn)有力,充滿了韌勁,又不失彈性,更好地展現(xiàn)出羌族民眾自強不息、奮發(fā)向上的精神狀態(tài)。
從以上作品中,不難看出當代編導(dǎo)個性化的藝術(shù)探索與獨特的審美追求。這些作品不僅表達了羌族民眾對美好未來的追求與對生命的熱愛,同時也對羌族民眾堅韌不拔的品質(zhì)與陽光般的生活態(tài)度進行了謳歌與贊美。這些作品中顯現(xiàn)出的藝術(shù)性與個性特征,不僅融入了編導(dǎo)們審美情感,更是編導(dǎo)們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勞動結(jié)晶。
(二)舞蹈編導(dǎo)對作品的創(chuàng)新起到了推動作用
當然,除了編導(dǎo)們對舞蹈作品審美情感的滲入、姿態(tài)動律的提煉發(fā)展外,好的作品還飽含了編導(dǎo)在專業(yè)技巧、形式表達上的創(chuàng)新。尤其是羌族肩鈴舞的創(chuàng)新運用,值得我們探討和借鑒學(xué)習(xí)。
據(jù)舞蹈家馬壽年(原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團團長、編導(dǎo))和舞蹈家奪科(原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團舞蹈隊隊長)口述,編導(dǎo)蔣亞雄從羌族鎧甲舞服裝上掉落的鈴鐺而得到創(chuàng)作靈感,嘗試將掉落在半空中的鈴鐺,進行了不同動作的探索,進而創(chuàng)作出獨具特色的羌族“肩鈴舞”,同時完成了舞蹈作品《羊角花開》的創(chuàng)作。作品中編導(dǎo)把姑娘比作盛開的羊角花,通過一系列美麗如花般的舞姿,展現(xiàn)羌族姑娘靈動如花的氣質(zhì)。女演員在表演時,通過連續(xù)的繞肩使鈴鐺形成回環(huán)飛舞的舞動形態(tài),鈴鐺以肩為軸甩動的動作,不僅展現(xiàn)出高超技藝,更是將“羊角花”盛開的形狀構(gòu)成一幅幅流動的雕塑,以全新的動態(tài)形式展現(xiàn)在觀眾眼前,人花相映,趣意盎然,將羌族姑娘靈動活潑的氣質(zhì)展現(xiàn)得恰到好處,整個作品散發(fā)出濃厚的民族特色和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因此,該作品在1980年參加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藝會演時,大放異彩,可謂是為羌族舞蹈作品的發(fā)展賦予了嶄新的形式美。1982年,潘琪、呂波創(chuàng)作的女子群舞《百合花》在肩鈴舞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發(fā)展創(chuàng)作,兩位編導(dǎo)將“肩鈴”塑造成百合花朵的形狀,通過舞者隊形的變化,構(gòu)成百合花的空間意象,在空間中通過高低對比、層次劃分,舞者們變作一朵朵潔白的百合花,舞者的舞姿也猶如一片片百合花瓣在空間中綻放,輕盈又富于詩意。該作品之所以能取得較大的成功,百合花朵翻飛中帶出“肩鈴”的運用絕對功不可沒。這一作品的問世使得肩鈴舞的運用又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女子群舞《鴿子花開的時候》越加成熟地以羌族舞蹈的動律、姿態(tài)、肩鈴技巧表現(xiàn)為依托,通過將象征生命美好的鴿子花在肩部甩動、軸轉(zhuǎn)而形成大圓甩動,使肩鈴技巧與身體律動巧妙融合在一起,再加之羌族舞蹈別致的動態(tài)和韻律,從而彰顯出羌族舞蹈的獨特之美,表現(xiàn)出羌族民眾在災(zāi)難之后依然充滿著對生命及美好生活的希望和向往。該作品獲得第九屆全軍文藝會演創(chuàng)作一等獎、表演二等獎;第五屆CCTV電視舞蹈大賽銀獎;第八屆全國舞蹈比賽表演二等獎的殊榮。
如今,經(jīng)過常藝、呂品、毛軍豪等一批批年輕舞蹈編導(dǎo)的匠心獨運,肩鈴舞技術(shù)更加成熟,形式豐富多樣、運用更加廣泛。例如在全國舞蹈比賽的舞臺上大放異彩的《羌繡》,由單肩羌鈴技術(shù)發(fā)展而來的《孜姆蘭巴》,榮獲第四屆“荷花少年”全國校園舞蹈展演金獎的《贊姆·噌噌》等。編導(dǎo)們不斷創(chuàng)新,使羌族舞蹈的表演形式更為豐富多彩、引人入勝。這種創(chuàng)新性的肩鈴舞動運用,亦被族群、觀眾、業(yè)界所接受和認同,認為是美且有特色的,并且肩鈴舞動已成為羌族舞蹈典型風格性語言特征。
五、結(jié)語
縱觀70年來羌族舞蹈作品創(chuàng)作,可謂是碩果累累。羌族舞蹈正以其濃郁的民族特征和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guān)注與喜愛。從羌族舞蹈作品的發(fā)展經(jīng)歷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一門藝術(shù)的發(fā)展規(guī)律,即一門藝術(shù)能夠永葆青春,與杰出人才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有著密切關(guān)系。羌族舞蹈作品創(chuàng)作,始終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和人才的貢獻。正是有了蔣亞雄、馬壽年、登珠、王志富、李楠、梅永剛、蘇冬梅、楊莉等眾多編導(dǎo)的努力創(chuàng)作付出,才會有一個個經(jīng)典的舞蹈力作得以產(chǎn)生;正是有了陳紅、秀花、梅永剛、易辛這樣的好演員,才使編導(dǎo)的絕妙想法得以精彩呈現(xiàn)。加之各個院團的各項保障、齊心協(xié)作以及政府提供的各個展示平臺,才使羌族舞蹈更好地以藝術(shù)作品的形式展現(xiàn)在舞臺上。這些作品不僅僅將羌民族的生活狀態(tài)活靈活現(xiàn)地展現(xiàn)出來,并有著嶄新的時代內(nèi)涵。同時,也推動了羌民族文化的多元發(fā)展和舞蹈的繁榮大發(fā)展,使羌民族的文化與風采得以更好呈現(xiàn),有助于幫助更多民眾了解羌族文化,羌族舞蹈與文化齊飛,優(yōu)秀作品與民族特質(zhì)共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