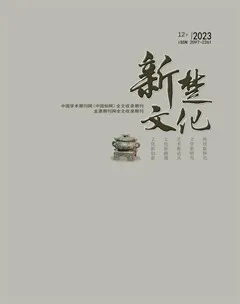許淵沖翻譯理論的創(chuàng)新性分析
【摘要】許淵沖是文學翻譯領域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實踐家和理論家。許氏譯論在繼承中外傳統譯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開拓性和創(chuàng)新性的翻譯思想,頗具學術價值和研究意義。通過深入探析許氏譯論,本文認為許淵沖翻譯理論創(chuàng)新性主要體現在四方面:推動“文學翻譯”轉變?yōu)椤胺g文學”;重視翻譯的“文化交流”功能;主張譯作對讀者的關照以及強調譯者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關鍵詞】許淵沖;翻譯理論;創(chuàng)新性
【中圖分類號】H159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36-0053-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3.36.016
在我國現代翻譯史上,許淵沖是少有的結合自身豐富的翻譯實踐,構建獨樹一幟翻譯理論的翻譯大家。許淵沖將中國古典詩詞外譯,同時將一些重要的英法文著作漢譯,他是英語、法語、漢語三語互譯的一座豐碑。他的《西廂記》英譯本受到高度評價,英國智慧女神出版社認為它“可與莎士比亞媲美”[1];企鵝出版社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聯合推出了許淵沖英譯的《不朽之歌》,這也是企鵝文學經典叢書第一次選用中國本土譯者的中詩外譯作品。“書銷中外百余本,詩譯英法唯一人”[2]這就是許淵沖和他的譯作成果的一幅生動的畫。在吸收中西方傳統翻譯理論精華并結合自身豐富翻譯實踐的基礎上,許淵沖針對文學翻譯理論進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最終構建了獨樹一幟的許氏文學翻譯理論——“美化之藝術,創(chuàng)優(yōu)似競賽”[3]。譯論從本體論、知識論、目的論和方法論等方面對文學翻譯進行了研究。“建構翻譯學科的華語邏輯體系,探討雙向文學翻譯問題”[4]。有學者認為“許淵沖翻譯理論體系的提出和形成,標志著中國傳統翻譯理論的終結”[5]。然而,相較于許先生翻譯作品的大量出版和廣受贊譽,其翻譯理論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也有學者對其翻譯理論存在誤解;因而本文擬從以下四個方面對許淵沖翻譯理論的創(chuàng)新性進行分析和探討。
一、推動“文學翻譯”轉變?yōu)椤胺g文學”
何謂文學翻譯?何謂翻譯文學?學界對兩者概念的界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嚴格來說,“文學翻譯”定性于原著的性質,是“對外國文學的翻譯”;而“翻譯文學”定性于譯著的質地和水準,指“翻譯成本國語的文學”[6];宋學智指出翻譯文學“不可以忽略譯者,或者說少了譯者就很欠缺”[7]。許淵沖作為極有遠見的翻譯理論家,在建構翻譯理論時,曾多次提到將文學翻譯轉化為翻譯文學。許淵沖認為“文學翻譯的最高目標是成為翻譯文學,也就是說,翻譯作品本身要是文學作品。”[8]什么樣的文學翻譯可以稱其為翻譯文學?許先生認為“外國文學經過翻譯成為中國文學的,英國作品有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法國作品有傅雷譯的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可由此可以看出,許淵沖在文學翻譯上是何等的苛求。而譯者如何能使自己的翻譯作品成為翻譯文學呢?許先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傅譯和朱譯所以能成為文學作品,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我看就是他們發(fā)揮了譯文語言的優(yōu)勢”[9]。
“發(fā)揮譯語優(yōu)勢”是許淵沖在《翻譯的標準》一文中首次提出。文章指出“譯文首先要忠實準確,其次要求通順流暢,最后要發(fā)揚譯文語言的優(yōu)勢”。在隨后談及翻譯的文章中,許先生對于“發(fā)揮譯語優(yōu)勢”的內在涵義這樣解釋:“在中文里,我說的是‘在譯文中發(fā)揮優(yōu)勢,但是在英文里,我不會用先進或者優(yōu)越的語言,而是用完全使用來表達好的語言,翻譯成中文,就變成了最好的譯文。其實“發(fā)揮”就是“最大限度地運用”,“優(yōu)勢”則是“良好的表現形式”。譯者主觀能動性的發(fā)揮關系重大,決定著譯文語言是否地道,以及譯作質量的好壞。與此同時,許淵沖認為西方之間的文字較接近,翻譯時要盡可能做到“形神兼?zhèn)洹保欢形鞣轿淖植罹啻笥指饔袃?yōu)勢,“亦步亦趨”的翻譯只會淪為平庸甚至災難,因此優(yōu)秀的譯文必須發(fā)揮譯語的優(yōu)勢,發(fā)揮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具體來說,即“當原文本比譯文本高時,應盡量保持其內容與形式,充分利用其語言上的長處;當翻譯水平比原作更高時,我們還可以利用自己的長處,揚長避短。”許淵沖本著提高文學翻譯質量的目標,著眼于解決中西兩種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從非常具體實用的角度,主張發(fā)揮譯者的能動性和創(chuàng)新精神,發(fā)揮譯語優(yōu)勢,譯文可以勝過原文,文學翻譯不再是對原文亦步亦趨的復制,而是在東道國獲得新生,成為翻譯文學。只有譯文成為翻譯文學,才能產生真正的文學性,有了文學性的翻譯作品才能獲得長久的生命力。從翻譯實踐角度來看,譯文超越原文成為翻譯文學經典的例子絕非個案。文學翻譯只有成為翻譯文學才能真正擁有長久的生命力,不被時代和讀者所淘汰。許淵沖對于翻譯文學的重視,體現了他作為一位具有歷史使命感的翻譯家對中國文學翻譯事業(yè)的深刻思考和終極關懷。
二、重視翻譯的“文化交流”功能
翻譯是一項跨文化的交流活動。20世紀后期,翻譯被放在社會和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建構,隨后“文化轉向”主張的提出使翻譯研究從語言層面轉向文化層面,本文認為,翻譯不僅是跨語言交際,還是跨文化交際行為。許淵沖歷來強調中西方文化雙向交流的重要意義,并且認為譯者和翻譯可以在中西雙方交流過程中發(fā)揮巨大的作用。早在1982年,許淵沖就提出“我們中國的文學譯者,有義務向中國文化中注入一種外來文化的血脈,并注入中國的一部分,這樣,世界上的文化就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輝煌。”許淵沖更是身先士卒、孜孜不倦地將《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西廂記》、《牡丹亭》等英譯、法譯,又將莎士比亞作品、《紅與黑》等西方經典著作漢譯。許淵沖是名副其實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為中西方文化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
同時,許淵沖又道“我覺得,我們應該互相幫助,共同創(chuàng)造一個全新的文明。”“二十一世紀,中國翻譯理論要走向國際,就算不能一統天下,也要在新的世紀里,與西方并駕齊驅,建立一個全球性的文化體系。”因此,許淵沖立足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主張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走出去”,將西方優(yōu)秀的文學著作“引進來”;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是“東西并立”,從對方的優(yōu)秀著作中汲取養(yǎng)分,取長補短,共同繁榮,“建立新的世界文化”。當今的世界正面處在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局當中,中國面臨新的時代機遇,因而我們應以大國的姿態(tài)將蘊含中華民族傳統與智慧的作品傳遞出去,講好中國故事,傳遞真實的中國聲音,樹立可親、可敬、可愛的中國形象,彰顯中國文化的價值。許淵沖的英文翻譯和法文翻譯作品得到國外的認可,對中國文化目前面臨的困難,“走出去”具有良好的借鑒意義。我國優(yōu)秀文學作品“走出去”的過程中,翻譯的質量決定著譯作是否能夠得到譯語讀者的認可,也是中國文化能否真正“走出去”的關鍵。“翻譯的地位不應該在創(chuàng)作之下,翻譯的質量也不應該低于創(chuàng)作的質量。”許淵沖提出必須用“再創(chuàng)作”的翻譯提高文學翻譯的質量。“再創(chuàng)作”指的是原文的“再創(chuàng)作”,它可以在譯文中重現原文的聲音、意義和形式之美,讓人有一種閱讀原文的感覺。得到愉悅的感受。許淵沖站在民族、文化、世界的高度看待翻譯的功能與作用,強調翻譯在文化交流中起到的重要意義,并以自身實際行動助力中國文化走向異國的千家萬戶,用“再創(chuàng)作”的翻譯搭建起一座跨文化交際的堅實橋梁,使中西方的讀者通過翻譯作品就能了解對方不同的文化、別樣的風景,加深了東西方對彼此的了解,加快了中西雙方文化交融的步伐,其觀點的創(chuàng)新性和實際行動的有效性不言自喻。
三、主張譯作對讀者的關照
傳統譯論認為原文和作者是“主”,譯者是“仆”,要求譯作對原作絕對忠誠;近代譯論提出翻譯是理解、闡釋和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譯者是原作的闡釋者,翻譯須重視譯者的主體性和主觀能動性;近期在翻譯界盛行的接受美學理論和讀者反應理論則特別關注讀者,主張通過研究和分析讀者的反應,來評判譯作質量。譯者在翻譯時應考慮到讀者的閱讀感受,優(yōu)秀的譯作能夠帶給讀者愉悅的閱讀體驗。譯者應把自己放在讀者的位置上,充分考慮讀者的興趣、心理、文化等情況,在忠實傳達原作的意義的基礎上,得到讀者的理解和認可。
許淵沖在多篇文章中談及“翻譯目的論”即“三之論”。許淵沖這樣闡述:“孔子在《論語·雍也篇》中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我認為這也適用于翻譯。也就是說,忠實的譯文只能使讀者‘知之,忠實而通順的譯文才能使讀者‘好之,只有忠實、流暢、充分發(fā)揮其長處的翻譯,才能打動讀者……‘樂之它代表著翻譯的至高水平,代表著讀者對其的最高贊譽,也是翻譯領域的皇冠。”文學作品如何為讀者所譯“知之、好之、樂之”呢?許淵沖并沒有泛泛而談,他提出了具體的解決辦法:“概括地說,可以采用‘深化、等化、淺化三種方法,這就是翻譯哲學的方法論。”“三之論”強化了讀者的重要性,并且有切實可行的“方法論”確保其實現,這樣許淵沖將讀者因素納入翻譯理論體系。許淵沖的讀者中有自己的老師、同學,外國的編輯、教授,更有自己的學生,不論是誰都給了他的作品很高的評價,這也正是因為許淵沖在翻譯實踐中強調譯作對讀者的關照,始終致力于使讀者“知之、好之、樂之”,他的翻譯作品才能夠在國內外擁有大批讀者,在譯評界得到充分肯定和廣泛贊譽。許淵沖打破了傳統譯論只重視原作和作者,而將讀者次要化和邊緣化的局面,從理論上強調關照讀者的重要性,將讀者作為譯者和譯作服務的目標,是對我國傳統譯論的一次推動和革新。
四、強調譯者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文化自覺”一詞由費孝通于20世紀90年代首先提出,他認為,文化意識是“生存于某一特定文化之中的人們,對于自己所擁有的文化的自覺”[10]。在當下翻譯研究文化轉向和中國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文化自覺要求譯者“既要有‘自知之明,還要有‘他知之明,即對本國文化和他國文化都要有‘知之明。要有一種正確的文化態(tài)度。一是不要有文化自卑感,不敢向外宣傳自己國家的文化;我們不能因為自己的文化而驕傲,將所有的東西都排除在外。”[11]
許淵沖作為學貫中西的翻譯家,一方面扎根東方傳統文化,具有很高的中國古典文化素養(yǎng),另一方面極力鉆研西方文化,對西方的文學文化知之甚詳,他對于東西方文化都有極清醒的認識。
許淵沖指出中國文化重宏觀,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被當成藝術;西方文化重微觀,翻譯被當成科學。體現在翻譯理論上,我國譯學家提出“信達雅”“神似”“化境”;西方則提出“等值”“等效”等理論。正是基于對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的準確把握,許淵沖認為西方翻譯理論只能解決西方語文的翻譯,而中西方的文學翻譯需要我國的譯者提出能夠解決中西方翻譯實踐的翻譯理論。
由此,許淵沖的“三美論”“三化論”“爭勝論”“創(chuàng)譯論”等,都是他在文學翻譯中的重要地位。他將嚴復的“信達雅”發(fā)展為“信達優(yōu)”,而“優(yōu)”即發(fā)揮譯語的優(yōu)勢來解決翻譯時中西方語言和文化的差異。高度的文化自覺促使許淵沖構建了富有中國特色的許氏翻譯理論體系,以堅持不懈的努力和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翻譯,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和西方文化“引進來”不斷作出新的貢獻。
許淵沖不僅擁有充分的文化自覺,他還是一位有文化底氣和文化自信的翻譯家。在20世紀末,許先生便提出譯者要克服自卑心理,“譯學要敢為天下先”。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中國人出版過中英互譯的作品,而能解決中西互譯實踐問題的翻譯理論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這并非許先生的自我陶醉,而是他積累六十年文學翻譯實踐經驗,潛心鉆研中國傳統翻譯理論之后,發(fā)出的有信心、有底氣的心聲。
一百多年以來,我國學術界向來以西方為師,截取西方理論的片言只字分析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這往往會涉及西方理論在我國的適應性問題。然而沒有信心,談何創(chuàng)新?我國譯者只有滿懷自信心,在總結中國傳統譯論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出適合當今時代和國情的新譯論,同時新譯論必須從實踐中來并接受實踐的修正和檢驗。充分的文化自覺和高度的文化自信是促使許淵沖幾十年如一日進行翻譯實踐的動力,也是他不斷提出創(chuàng)新的翻譯理論的思想源泉。在當下盲目迷信西方理論,缺乏創(chuàng)新精神的譯學界,許先生“敢為天下先”的譯論顯得尤為可愛和彌足珍貴。
五、結語
許淵沖是我國當代杰出的翻譯家,其翻譯作品遠銷海內外,贏得東西方讀者的稱贊。先生為中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提高中國文學在世界范圍的地位作出了突出貢獻。許淵沖的譯論是“革新了翻譯美學理念,開創(chuàng)了翻譯美學新理念的先驅,為中國文學翻譯提供了方向。”[12]我們認為許淵沖翻譯理論的創(chuàng)新性主要體現在四方面:推動“文學翻譯”轉變?yōu)椤胺g文學”;重視翻譯的“文化交流”功能;主張譯作對讀者的關照;強調譯者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盡管學界對他的翻譯理論仍有不同看法,但在當今世界翻譯研究發(fā)展的文化背景之下,其翻譯理論的研究意義和學術價值顯得越來越重要。“在眾多學者的努力下,我堅信,許淵沖的翻譯思想必將像一輪朝陽般冉冉升起,照耀在文藝理論與實踐的星空中。伴隨著這輪“紅日”的升起,中國甚至全世界的傳統譯論都會煥發(fā)出新的生機,從而進入許淵沖的文學譯論時代。”[13]
參考文獻:
[1]許淵沖.詩書人生[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
[2]張智中.誤幾回天際識歸舟——論國內許淵沖翻譯研究的誤區(qū)與不足[J].中國化研究,2017(03):140-153.
[3]許淵沖.文學與翻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4]賈洪偉.許淵沖翻譯觀之本質論——兼論中國翻譯觀之變異[J].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02):22-25.
[5]張智中.許淵沖文學翻譯理論的美學特征[J].時代文學(上半月),2008(01):144-146.
[6]張德明.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J].人文雜志,2004(02):114-119.
[7]宋學智.翻譯文學經典的影響與接受[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8]許淵沖:翻譯的標準[J].中國翻譯,1981(01):1-4.
[9]許淵沖.翻譯的藝術[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
[10]費孝通.反思·對話·文化自覺[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03):15-22.
[11]許明武、葛瑞紅.翻譯與文化自覺[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04):102-105.
[12]鄭海凌.解讀“優(yōu)勢競賽論”[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08):42-45.
[13]黨爭勝.對許淵沖文學翻譯理論的幾點認識和思考[J].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02):16-21.
作者簡介:
李丹丹(1988.6-),女,江蘇,南京人,碩士研究生,南京師范大學中北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法語翻譯學、法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