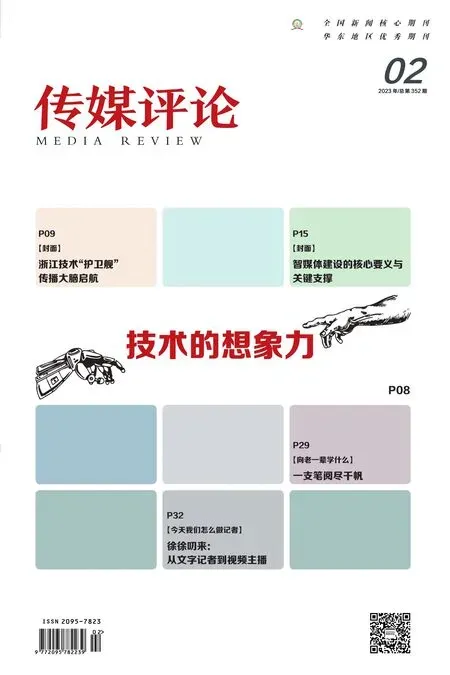構建傳統文化類電視節目的敘事新范式
——以《典籍里的中國》為例
文_范康文
傳統文化類電視節目作為表現與傳播我國優秀文化的有效載體,通過挖掘、弘揚傳統文化,在助力文化強國建設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年來,以中央電視臺為主推出的一系列傳統文化類電視節目,將傳統文化精神進行現代性轉化,形成具有時代特征的敘事新范式,不僅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給予精準的闡釋,而且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本文以《典籍里的中國》為主要案例,分析當下傳統文化類節目所呈現出的敘事內容與敘事方式,探討傳統文化類電視節目敘事新范式的構建路徑。
一、傳統文化精神的現代性轉化
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破題的關鍵是傳承與創新。傳承,首先要文化尋根,回歸經典,知曉民族文化精神在傳統文化語境中的含義。《典籍里的中國》節目以“典籍”為媒,以“穿越”為手段,開拓出鏈接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通道,有效地幫助觀眾理解今日中國文化體系之源。創新,意味著傳統文化要進行現代性轉化。只有經過現代性轉化,傳統文化的精神才能被當代人所理解與接受,進而指向未來。以下以《典籍里的中國》為例,探尋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現代性轉化路徑。
(一)重農固本——保障糧食安全的底線思維
作為一個人口大國、農業大國,“國無農不穩,農以種為先”一直是我們國家的治國之要。《典籍里的中國》節目通過介紹《天工開物》致敬“古有《天工開物》,今人繼往開來”的傳統文化精神。典籍作者宋應星把多年走訪大江南北了解到的生產方式和工農技術記載下來,最后寫出《天工開物》。其中有一句話,“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意思是一天得不到它,饑寒就產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把五谷看得很貴重,而把金玉看得很輕賤。這正體現出了我國“重農固本”思想的淵源。《典籍里的中國·天工開物》節目,在稻香飄逸的原野上,袁隆平與他的前輩宋應星跨時空握手相逢,這一剎那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新一代農業科學家身上的傳承。所謂“悠悠萬事,吃飯為大”。糧之安全,國之大者,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到的“國之大者”,提出保障糧食安全的底線思維,也正是典籍中“重農固本”傳統文化精神的現代性表達。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貴五谷而賤金玉”的傳統文化精神,從未改變。

(二)以和為貴——中國一貫的外交理念
和合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以和為貴”思想成為中國人的一種價值觀念,無形中影響著人們的思維與行為方式。當撒貝寧帶領“孫武”看到《孫子兵法》在后世流傳下來時,眼神流露出了欣慰、高興和釋懷之情。這深厚的思想精髓至今仍在指引著我們的行動決策,當下國際形勢動蕩不安,“以和為貴”的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已成為中國政府處理國際關系的價值觀,從將“和平共處”作為我國對外關系的基本準則,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中國外交始終秉承著“以和為貴”的理念,時刻彰顯著大國的責任與擔當。
中華典籍中所蘊含的重農固本、以和為貴、求知探索、自強不息等傳統文化精神從炎黃時代到今天現代化建設階段,始終滋養著中國人民的成長和社會進步,是我們實現民族復興的精神指南。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精神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使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得到持續豐富和發展,實現自身的現代性轉化。
二、傳統文化內涵的故事化表達
文化價值是傳統文化類節目相較于其他類型節目所獨具的優勢。但是,也存在“輸出內容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節目趣味性低、受眾黏性不強”等問題。《典籍里的中國》揚長避短,創新傳統文化內涵的表達方式,以年輕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故事化表達增強節目吸引力,使觀眾層次和規模逐漸穩固。
(一)故事化演繹使傳統文化符碼更受歡迎
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為電視節目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資源。但是如何使傳統文化“晦澀難懂”轉變為“平易近人”,是創作者長久以來面臨的一大難題。柏拉圖說:“誰會講故事,誰就擁有世界。”聽故事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而講故事就成為一種重要的交流策略和技術。內容表現的“故事化”是指根據故事本身的特點和元素重新編織事件。更確切地說,“故事化”是依附于故事而存在,通過某種方式讓事件的本身具有其故事性。
傳統文化類節目采用的敘事范式之一是將傳統文化精神以講故事方式進行編碼創作,最終以富含故事性的內容呈現給大眾,增強傳統文化的感召力。《典籍里的中國》節目以“中國典籍”為抓手,打造“典籍IP”,選擇《尚書》《論語》《道德經》等經典書籍,將典籍中的亮點內涵以故事的形式表達出來。通過當代讀書人撒貝寧與古代圣賢的“古今對話”情景敘事,以及主持人和圖書解說員的解讀對話,來實現傳統文化內涵的故事化呈現。兩條敘事線有機組合,在敘事、表情、達意上更加順暢,使受眾更容易理解。
(二)影視化視聽使故事講述生動立體
《典籍里的中國》節目不僅設立了戲劇執行導演,而且還特別設立了影視化執行導演,用影視化的聲畫語言表現戲劇故事。內容設計上,將典籍、歷史、文化內涵、戲劇按照影視創作思維進行了重組;表現形式上,靈活運用影視視聽語言、新媒體技術,用虛實結合的方式充分調動觀眾的感官。融入影視創作思維的戲劇故事更加契合電視節目視聽接受特征,有效提升受眾的觀影感受。
節目借助影視化的創作手法彌補了戲劇藝術時空自由度缺乏、景別變換少、視角單一等缺陷。以視聽語言等影視化設計為故事表達錦上添花,使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故事化呈現兼具了趣味性和時代性。例如在演出之前,演員站在鏡子前,鏡子中出現飾演角色的身影,同時鏡頭不斷變換著視角,時而帶入現場觀眾的全知視角,時而又以推鏡頭、積累蒙太奇等手法將我們置于角色的情感世界,每一次鏡頭機位的變化都是在引導觀眾如何觀看。這種鏡頭分切帶來的體驗是節目對傳統文化內涵故事化表達的一種強化,可以讓觀眾最大程度地接受甚至體會傳統文化的魅力,獲得更加沉浸的體驗,同時觀眾對傳統文化內涵的理解過程也從“他者觀看接受”變成了“自我精神觀念建構”。
三、傳統文化記憶的視聽化呈現
揚·阿斯曼曾提出“文化意義”的概念,即共同的價值、經驗、期望和理解,在達到了一定積累后,進而構造出一個社會的“象征體系”和“世界觀”。在共同擁有的文化意義循環中促生的“共識”,就是“文化認同”。當人們認同集體的共同文化之后,就會接受這種文化內涵的影響,運用共同的文化象征并采用共同的文化符號,遵循某種文化觀念。
(一)穿越歷史的在場感和親歷感
存在于典籍中的文化記憶雖然都是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但未曾經歷過的我們會對典籍中記載的歷史記憶有疏離感,所以節目需要將無數代炎黃子孫的記憶“真實化”。李普曼曾指出媒介具有構建“擬態環境”的作用,當前的媒介傳播更加注重運用沉浸式傳播,構建特定媒介空間,以實現預期傳播效果。《典籍里的中國》在將人們的傳統文化記憶視聽化的過程中,首先運用舞臺藝術、特效藝術將“時間河流”這一意象化存在真真切切地打造出來。通過新興技術進行情景再現,讓當代讀書人穿越回過去時空里。通過“穿越”,我們可以與前人進行跨時空的溝通,我們可以和那些不可能見面的先賢們進行“真正的對話”,此外,在現代人和先賢會面合集中,利用鏡子做穿越媒介,配合演員表演與服裝造型變化,節目還利用音樂、肢體表演、3D投影、全包圍式舞臺等媒介,仿佛先賢們真切地來到了我們身邊一般,從而給觀眾提供了虛擬的在場感。
(二)強化傳統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
鑒于記憶的不穩定性和時間的不可逆性,為了保證傳統文化記憶能夠歷久彌新,我們必須對喚醒的傳統文化記憶物態化。《典籍里的中國》節目延伸記憶的時空維度,以節目為載體實現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共享,在記憶場域中實現同頻共振,由此培養共同的文化身份和歸屬感。比如節目將典籍影視化,利用情景再現和人物扮演等方式來還原記憶內容,在表現徐霞客的這一期中,節目重現了徐霞客與其母親的對話場景,讓我們了解徐霞客建功立業的背后離不開母親的默默支持。臺詞中的那句“母親,我想您了”,喚醒了刻在中國人骨子里的“孝道文化”記憶。其目的是聯結個體記憶和傳統文化記憶,讓現代觀眾與傳統文化實現跨越時空的聯結,從而增強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與此同時,以《典籍里的中國》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類節目在流媒體平臺廣泛傳播,利用“朋友圈效應”和“帶貨”頻上熱搜,讓節目積攢了良好的口碑,讓傳統文化好風憑借力,成功打破了常規的流通圈層,拓展了“記憶擴散”的渠道,也幫助觀眾完成了對于自我身份的確認和文化歸屬,比如彈幕中“請受炎黃子孫一拜”就是很好的案例。
四、結語
在短視頻、甜寵劇、爽文、無腦短劇刷屏的泛娛樂化傳播環境中,厚重端莊、大氣磅礴的傳統文化類電視節目無疑是一股清流。《詩詞大會》《中國成語大會》《國家寶藏》《經典詠流傳》《典籍里的中國》……這些節目不光“逆流而上”,還做得華麗大方、光彩四溢、好看易讀,一改以往文化類節目照本宣科式的文化介紹和平鋪直敘的表現方式,為傳統文化類電視節目構建了敘事新范式。概括起來,首先內容以傳統文化內涵為根基進行創造性轉化;以故事化影視化為節目表現形式穩固觀眾群體;以增強文化歸屬感為訴求,促進文化記憶的分享和傳承。因此,在泛娛樂化日漸受到摒棄的傳播環境中,創作者只要堅持正確的文化導向,強化文化自覺,創新敘事方式,構建全媒體傳播渠道,相信傳統文化類節目會有更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