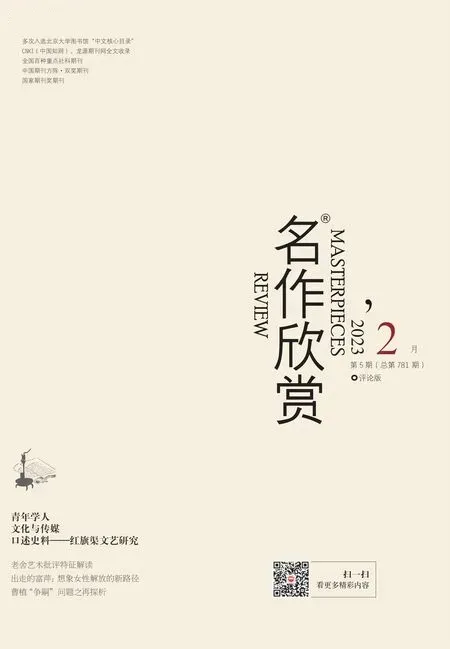多重視域下的大學書寫
——讀阿袁的《師母》
⊙萬麗君 [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江西 南昌 330031]
學院派作家阿袁以古典俏皮的敘事語言和譏誚反諷的敘事策略將敘事目光放在大學的各色男女身上,擅長從人與人的關系中折射出知識分子群體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面貌,形成其獨特的大學敘事風格。阿袁認為:“寫作者要熱愛生活,到樸實的生活中去練就眼力,從最熟悉的題材入手,鍛煉處理素材的能力,以拓荒者的精神尋找全新的角度,在題材選擇時代入人物關系、性別關系,學習經典作品的寫作技巧。”①作為大學教授,阿袁對“師母”這個群體再熟悉不過,選擇從“師母”這一視角切入大學教授們的生活,既刁鉆又貼切。“師母”是大學校園中具有獨特身份象征的女性群體。成為“師母”之前,她們有自己的生命歷程;成為“師母”之后,又與“教授群”的生活息息相關。“之前”與“之后”暗藏的敘事張力使得《師母》與阿袁以往的“去知識分子化”敘事不同。《師母》不僅將敘事的焦點放在知識分子的家事和情事上,而且也輻射到大學的學情和人事上,蘊含著作者“對大學體制、精神、文化的反思與重構”②。因此,對《師母》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敘事視角的研究為了解阿袁的大學敘事提供了可能。
一、物化下的他者生存之道
鄢雉始終以一種外鄉人看物的眼光打量自己的家鄉。幼時,她就認為家鄉的房子、街乃至狗都是庸俗的,即使白里帶紫的辛夷花開滿全鎮,她眼里也只有破舊寒酸的房子。這種看物的視角隱含著一種對家鄉的冷漠、疏離甚至厭棄,也意味著自我處于失根的狀態。高考落榜的鄢雉毅然接受了陳良生編織的旁聽生之夢,離開了她厭棄的家鄉。離家逐夢看似為失根的自我尋找扎根之地,實則走向了“他者化”。事實上,陳良生誘惑鄢雉來大學只是為了“躬行”私欲,從一開始便將她置于“他者”位置。首先,從他將鄢雉安置在素有“紅燈區”的西區,而不是有良好學風的北區便可見一斑。租住的半地下室房間隱喻著鄢雉的灰色身份,雙人床則鮮明地指向鄢雉對大學的美好向往在陳良生處心積慮的引導下走向不可控的境地,最終從尋找自我的“強者”淪為“守在半地下室”的“他者”。其次,是鄢雉的自我垮塌于看清大學上課機制之后的選擇。她不是選擇離去,而是選擇寄生于陳良生對她的“愛”,自我逐漸被陳良生大學生的身份所蠶食,委頓在陳良生為她安排好的“他者”位置上。最終,委頓至極的鄢雉爆發生命之火,離開了陳良生,走向書屋,從“他者”的泥濘中拔出腳,卻又迷失在孟一桴的馬桶上,滿足于“師母”身份的她再次陷入“他者”的境地。從表面上看,她以“師母”的身份留在心中的美麗之地,像一株終于長在自己夢想國的植物,怡然自得地扮演著女性主內的角色。實質上,她的自我卻是蜷縮的,她像擦拭精美瓷器般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她的“師母”生活,羞于沒有文憑和工作的金牙,戰戰兢兢地生活著。小北的“歸來”,陳良生的再次出現,這“兩只蚤子”將她平靜的生活攪得晃晃悠悠。身體、身份與精神的博弈將其拉入“他者”的深淵。
阿袁曾說:“女人從來沒有真正解放過,總有另一個女人,像雷峰塔一樣,囚禁女人一輩子。”③這也是她寫《師母》鄢紅的初衷。縱觀鄢雉到鄢紅的過程,可以看出其“他者化”的本質正是在于另一個女人的存在。這個女人潛藏在“鄢雉”和“鄢紅”的內心深處,成為不自覺的參照物,牽引著她的一舉一動。在她還是鄢雉的時候,她心里的另外那個女人有兩個。從兩性關系看,她希望成為顧艷麗一樣有女性魅力的女人,這一點從她跟朱周分享的愛情經歷都是剽竊顧艷麗的可以佐證。從身份地位來看,她希望成為像蘇小扇一樣統招的女大學生。她清楚地意識到她與這兩者存在天塹般的鴻溝,當她無意中走進孟一桴家時,她找到了一條捷徑——通過婚姻便可獲得比兩者都更高的身份象征。如愿成為“師母”的她改名為“鄢紅”,勢要跟以往庸俗的“鄢雉”揮別,但她潛意識里覺得自己不配“師母”之位,內心惶恐不安。這種惶恐幻化成為兩個另外的女人,其中一個是朱周。朱周在“鄢紅”心目中是一個具有先天優越性的師母,她不僅生于師大這個美麗之地,而且冠有“外語系系花”的美名,女性魅力遠超顧艷麗且滌蕩了顧艷麗的庸俗。這無不讓“鄢紅”仰望著她,成為她影子一般的人物。另一個則是莊瑾瑜。莊瑾瑜有著“鄢紅”難以企及的高學歷和高職位。盡管“鄢紅”平時與朱周站在同一戰線譏諷莊瑾瑜,但在關鍵時刻,比如決心再見陳良生,還給他傳言里的“師母”形象,她選擇了和莊瑾瑜一樣的黑色套裝,下意識覺得“大學女教授”的形象能夠讓她碾壓舊情人,挽回她“不良的”師母形象。這種潛意識的認知讓她面對莊瑾瑜處于被動“他者”的位置。
面對“他者化”的境地,鄢紅以愛物代替愛人扎根于美麗之地。從傳統婚戀角度來看,愛是婚姻的基礎,而在鄢雉眼里,對孟一桴家物件的愛才是她婚姻的基礎。這種愛持續了六年,她依舊小心呵護著孟一桴家里的物件。可見,愛物比愛人更有穩定性,“人”的動態性為婚姻帶來很多不確定因素,而物的靜態性則具有恒定性。她傾注在物上的情感與孟一桴心目中母親對父親的愛重疊,孟一桴漸漸愛上了這個“有愛”的女人。這無不具有反諷意味,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鄢紅惶恐不安的同時她以對物的愛扎根于她“師母”的位置,也隱喻著在這個快消費時代愛物比愛人更容易得到反饋,而這種物欲得到滿足后的平靜生活狀態是否是生命的意義未可知。
二、不可靠敘事下的高知女性形象
《師母》全篇并沒有按正常的時間順序推進故事發展,而是隨著人物的意識流穿梭在現在與過去,敘事視角也從第三人稱和人物視角來回切換。申丹認為,無論是在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敘述,人物的眼光均可導致敘述話語的不可靠,而這種“不可靠敘述”又可對塑造人物起到重要作用。④不可靠敘事在《師母》 中則集中在對莊瑾瑜和小北這兩個高知女性的塑造上。
莊瑾瑜作為具有高學歷和高職位雙金牙的職業女性,她本應該是被高光所籠罩,但是在朱周和鄢紅的視角下,她炫耀上海讀博經歷、炫耀教授工作、炫耀夫妻恩愛。但事實上朱周只是一個以饕餮為榮、以隨性為傲的享樂主義者,并沒有看到她的努力在何處。而鄢紅更是以計謀獲得“師母”位置,以對孟一桴家的愛維持著自己“偷來的生活”。她們兩者的視角本身帶有主觀的感情色彩,并不是客觀事實的陳述。作為第三人稱敘述,《師母》所隱含的作者明顯帶著傳統的眼光來評判作品中的女性。朱周因其美貌率性不需努力便獲得老公的疼愛,甚至連莊瑾瑜的老公也對她心生愛慕,而鄢紅則因對孟一桴家的愛誤打誤撞呈現出賢良特質,因此而獲得了孟一桴的愛。從這兩個人物身上可以看出:學歷、工作都不是評判女性的標準,而美貌或賢良才是女性幸福的秘訣,這明顯是傳統評判女性的標準。反觀莊瑾瑜,全篇皆以諷刺的旁觀者眼光斜視著她。她出身農村,不夠美麗,但足夠努力,從大專生一步步成為博士,再成為高校教研室主任;她極盡所能隱忍和順從丈夫,扮演一位高校副主任的妻子,但最終她還是不得不忍受生活的“蚤子”,扭曲成為一個看著他人被“蚤子”噬咬才能緩解心中難耐的畸形人物。事實上,在現代社會,這樣高知高薪女性難道就沒有第二條路走嗎?很顯然,莊瑾瑜這個人物只是在不可信敘述下的產物,其人物本身的價值被其他人物的不可靠敘事和隱含作者的有意設置所遮蔽。
身為“前師母”的小北,僅出現在孟一桴、沈岱山、朱周以及樓棟其他鄰居的敘述里。這些敘事者無不以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打量她。沈岱山和朱周直言,他們不喜歡小北,覺得鄢紅與孟一桴更合適。同樓棟的師母則感嘆,幾年下來連小北長什么樣都沒看清,只看清了她腳上的紅耐克鞋像哪吒的風火輪。孟一桴則羞于承認,“他后來對小北的感情傾向,有輕微的憎厭”⑤。這些敘事者的口吻不無夾雜著對小北追求速度、我行我素的不認同,暗含著社會對高知女性的評判。小北僅有的一次出場,也是以孟一桴的視角展示小北瘦得暴筋的手,以及覆住孟一桴的手傳遞出有意復合的信號,暗示小北追求速度的人生觀觸礁了。但孟一桴暗想,“見過了現在的小北,他就不想聽沈岱宗再說小北什么了”⑥,這種上位者的同情將小北釘在了弱者的十字架上。可見,這些都只是旁觀者的眼光,僅是一種不可靠的敘述。小北自己的體驗如何不得而知,從另一個角度看,她何嘗不是一個獨立、勇敢的女性?
無論是莊瑾瑜還是小北,都具有雙重身份,一重是師母,一重是高知女教授。在第三人稱敘事的視角下,她們做了兩種不同的選擇。莊瑾瑜選擇平衡兩種身份,最后被生活的“蚤子”噬咬著,時刻擔心心中隱藏的粗暴的另一個女人會現形。小北則選擇拋棄師母身份,奔赴高知女教授的職場,最后卻以瘦骨嶙峋的身軀黯淡謝幕。作者以旁觀者的視角打造出一個滿含對高知女性評判的社會圈,揭露了現代高知女性的生存困境。
三、多重視域下的大學百態
“大學敘事對大學人物、體制、精神、文化的呈現與反思,既彰顯了創作者對現實社會的批判精神,也表達了對大學精神和知識分子品格的理想訴求。”⑦《師母》里面的大學敘事是由家長里短、流言蜚語和人物聲音匯成的多聲部敘事。這些聲音是在“旁聽生”“注冊生”“師母”和“教師”等多種敘事視角觀照下匯集而成的,反映了當代高校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面貌,折射出當前大學存在的問題。
旁聽生與注冊生的視角交錯,投射到大學校園的各個角落。作為旁聽生,鄢雉只能旁聽大課和選修課,她一方面目睹了在這些課堂上大學生們睡覺、戴耳機聽音樂、談戀愛,描繪出一群混沌蒙昧、毫無學院氣息的大學生群像。但另一方面,當她在上一些專業課時,卻感覺格格不入,展示了大學精英教育的一面,也促使她認識到旁聽生與注冊生的不同。除了課堂,作為旁聽生的鄢雉待得最多的地方便是西區,這里潛藏著大學生活放縱物欲的一面,以及校園與都市交錯的一面。鄢雉與陳良生的人生交集將視角由旁聽生轉向注冊生。作為來自農村的大學生,陳良生一方面為了私欲,花言巧語將鄢雉騙來做旁聽生;一方面,他將與蘇小扇的兩性關系解讀為“為稻粱謀而努力”,將靠裙帶關系美化成“終南捷徑”,徹底發揚“底層男人忍辱負重的品質”,但他身上也確實具有底層男人的拼勁,從中學教師拼搏至博士在讀。這些都折射出當前部分來自底層的大學生在物欲熏心下矛盾而扭曲的心理。
“師母”視角下的大學則是由各種家長里短所織成。其中教師的私生活,教師與教師之間的博弈以及學校的各種流言蜚語,穿插成象牙塔世俗的一面。“師母”視角下的女大學生都是被剔除了學生特征,變成對老師存在潛在誘惑的“女性符號”。鄢紅對馬驪從顧忌到不屑再到同情,莊瑾瑜對呂小黛則從關愛有加到暗中挑撥再到無可奈何。馬驪對孟一桴僅僅是單方面的思慕,隨著畢業與工作,逐漸明晰與孟老師的距離。呂小黛則是從小享受到美貌帶來的好處,深知自己似洛麗塔般對比她大的男人有著天然的誘惑,并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獲益。無論馬驪還是呂小黛,都只是女大學生中的極少數,卻刺激著“師母們”的神經,側面反映了傳統女主內男主外的婚姻模式下女性的被動與無奈。
教師視角下的大學則各不相同。沈岱山視角下呈現的是新式老師的境遇。沈岱山堅持按學生的需求授課,而不是一板一眼進行流水線生產,盡管上課深受學生歡迎,卻三番五次被督導查出問題,被罰去當資料員,折射出大學教師的身不由己。孟一桴視角下呈現的則是傳統老夫子式的教育堅守。孟一桴是一位深受學生喜愛的老師,但他只對做學問感興趣,“對學而優則仕”避之唯恐不及,最終成為胡豐登夫妻不愿交往的大學邊緣人物。胡豐登視角下的大學則是名利角斗場。胡豐登身為大學教授和副主任,一心鉆營的卻是如何討好領導升為主任。事業上的失意會引起他喉嚨腫痛,甚至成了他對妻子燕婉冷暖的晴雨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無心教學的他卻獲得了“十佳優秀”教師,可見,無論是新式還是傳統的教師都面臨著生存困境,僅有一心鉆營人事的教師左右逢源。大學教師該何去何從的迷茫,在開放式的結尾設置中成為讀者想撓而又撓不著的癢處,牽扯著讀者的神經,引發讀者關注和深思。
四、結語
阿袁的《師母》以鄢雉到鄢紅的轉變為明線,以人物的意識流動為暗線,從旁聽生的視角展示了大學的精神面貌,從“師母”的視角聚焦了高知群體的婚戀狀態,從“教師”的視角揭示了大學教師的職業困境,表現出作者對當下高知群體的人文關懷。在第三人稱敘事視角下,高知“師母”成為社會評判的對象,家庭與事業的平衡將其擠壓變形,其生存空間愈漸逼仄。全職“師母”則在將愛寄于“物”上尋找到生活的突破口,由惴惴不安的“他者”變成扎根“師母”之位的魅力人物。這種反差無不告誡著人們,面對種種誘惑及刺激,我們應始終保持初心,成為理想中的自己。
①阿袁:《關于經典小說中的性別關系研究——以毛姆創作為例》,2021-9-27,https://www.sohu.com/a/492475135_121124762.
② 李洪華:《20世紀以來中國大學敘事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21年版,第1頁。
③ 阿袁:《如果愛,如果不愛》,河南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57頁。
④ 申丹:《敘事、文體與潛文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5頁。
⑤⑥ 阿袁:《師母》,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34頁,第237頁。
⑦ 李洪華:《革命救亡語境中的大學想象:論抗戰時期的大學敘事》,《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第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