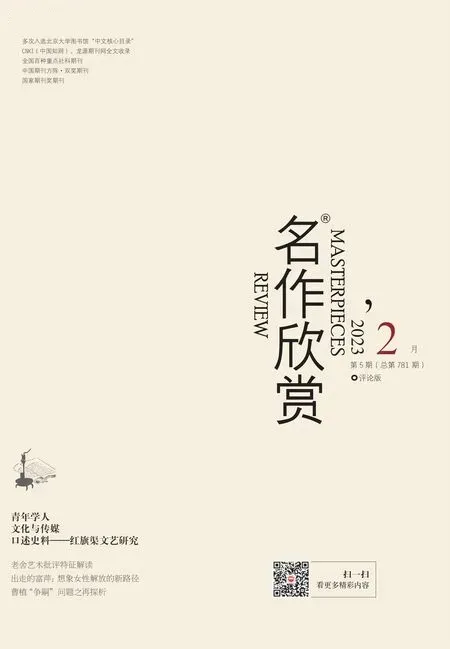論遲子建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傷懷之美
⊙孫丁凡 [西北民族大學,蘭州 730124]
遲子建是當代中國文壇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女作家之一。1986 年,她在《人民文學》發表了成名作《北極村童話》,小說講述的是一個七歲小女孩燈子被寄養在北極村姥姥家的童年故事,以兒童視角追憶東北漠河村奇異而神秘的北極生活。小說寫得澄澈而唯美,蘇童認為:“大約沒有一個作家會像遲子建一樣歷經20 多年的創作而容顏不改,始終保持著一種均勻的創作節奏,一種穩定的美學追求,一種晶瑩透亮的文字品格。”①確實,遲子建的小說總是以她的故鄉大興安嶺一帶為背景,聚焦于平凡庸常的人生,有著充沛的溫情與溫潤的柔軟。遲子建在書寫人生和生活浪漫詩性與溫情的同時,也對人生之痛有著深切的體驗,這使得她的小說呈現出一種蒼涼的美感,“傷懷之美”由此成為遲子建小說的徽記。在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以對原始自然風景的眷戀、對萬物有靈論的敬仰、對人生情態“痛感”的表達和對鄂溫克人古老生活方式變遷的感傷成就了小說的“傷懷之美”。
一、何謂“傷懷之美”
“文學風格主要指作家和作品的風格,既是作家獨特的藝術創造力穩定的標志,又是其語言和文體成熟的體現,通常被譽為作家的徽記或指紋。”②“傷懷之美”一詞源自遲子建的散文《傷懷之美》,在散文中遲子建以抒情的筆觸描繪自己與美好大自然、往昔的情境不期而遇時產生的感動傷懷以及由此產生的圣潔之感,也嘆惋人們被世俗的利益與喧囂鈍化、物化,失去了敏感、空靈的心靈。可以說,遲子建的“傷懷之美”就是當人處于物質社會中對原始自然事物的逝去感到眷戀與惋惜的一種感情。
首先,“傷懷之美”是遲子建對逝去事物飽含深情的回望,它蘊含著遲子建對原始自然事物的惋惜和悲憫的人生情懷。謝有順評價遲子建的作品:“憂傷而不絕望。”③遲子建說:“‘憂傷’可以說是我作品彌漫著的一種氣息,這種‘憂傷’表現在對生之掙扎的憂傷,對幸福的獲得滿含辛酸的憂傷,對蒼茫世事變幻無常的憂傷。‘不絕望’可以理解為對生之憂傷中溫情亮色的感動,對能照亮人生的一縷人性之光的向往,這些,是人活下去的巨大動力。”④可見,遲子建的“傷懷之美”雖然充滿著憂傷,但是并沒有對生活充滿絕望,而是用一種溫情的目光飽含希望地對未來充滿向往。其次,“傷懷之美”體現為一種具有情懷的美感力量。遲子建在《傷懷之美》中寫道:“我相信每一個富有情懷的人都遇見過傷懷之美,而且我也深信那會是人一生中為數不多的幾次珍貴片段,能成為人永久回憶的美。”⑤當生活在城市混沌的煙云之中歷經生活的種種考驗之后,我們唯有內心富有情懷對未來發出無盡的憧憬與神往,以敏感而細膩的心靈看待與體悟世界,立足于塵世生活去探索一種超越性的精神追求,才會讓“傷懷之美”與我們不期而遇。
回顧遲子建的創作經歷,我們不難發現:從最早創作的《北極村童話》中燈子那清純憂傷的生命到《逝川》中對于青春與美的挽歌,從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鄂溫克人在現代文明擠壓下求生存的無奈,再到《候鳥的勇敢》中候鳥遷徙反映的嚴峻社會現實以及長篇小說新作《煙火漫卷》更是通過聚焦于哈爾濱城市人們的日常書寫,把人間煙火之中每個人生命之中的收獲與失意、歡笑與痛苦、生活之苦與歲月之甜,在不疾不徐的講述中伸展開來,不得不說,遲子建的每部作品,其憂傷的氣息都是氤氳而出的。而在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從自身的感悟之中所體味到的“傷懷之美”,或是生發出對于原始文明的眷戀,或是對于萬物有靈論的敬仰,或是對于人生情態“痛感”書寫所生發出的感傷,或是對于鄂溫克人古老生活方式變遷的感傷……這幾種感官體驗之下所生發出的情緒表達,體現了遲子建對于“傷懷之美”所理解的獨到之處。
二、《額爾古納河右岸》中“傷懷之美”的表征
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通過對原始古樸文明的眷戀與緬懷以及對人生情態的“痛感”書寫,使“傷懷之美”以更為厚重的形式表現出來。在作品中,遲子建以其敏感而細膩的心靈看待與體悟世界,充滿了對原始自然風景的眷戀、對民族文化的憂慮,蘊含著她感傷的自然情懷和悲憫的人生情懷,呈現出濃郁的“傷懷之美”。
首先,通過對原始自然風景的書寫,表現對大自然的眷戀之情。遲子建是一位將根深植于大自然的作家,故鄉大興安嶺地區的自然景物給予她審美的靈性感知和思考深度。在《傷懷之美》中遲子建寫道:“那種人、情、景相融為一體的傷懷之美似乎逃之夭夭了。或者說傷懷之美正在某個角落因為蒙難而掩面哭泣。”⑥那種人、情、景融為一體的故鄉原始自然風景,成為遲子建“傷懷之美”的支撐點,這一支撐點的存在,使得遲子建對那些已經消逝的原始古樸文明有著眷戀與緬懷。自古以來,人類與大自然都是和諧共生,共同成長。遲子建在作品之中所觀照到的大自然的消逝與鄂溫克人的死亡情態同樣都是有著不可逆的結果,而這二者不可逆的結果之下,都需要我們用“傷懷之美”去進行感悟。
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作者用大量的筆墨書寫原始自然風景,表現遲子建對這片土地深沉的熱愛。在小說中,奇特的白晝、無際的雪野、神秘的大山、自由自在的馴鹿們等一個個美好的自然之物,給我們帶來的是或濃墨重彩或沖淡平和的東北邊地的特有風情。比如,遲子建在作品中書寫拉穆湖的景色:
勒拿河是一條藍色的河流,傳說它寬闊得連啄木鳥都不能飛過去。在勒拿河的上游,有一個拉穆湖,也就是貝加爾湖。有八條大河注入湖中,湖水也是碧藍的。拉穆湖中生長著許多碧綠的水草,太陽離湖水很近,湖面上終年漂浮著陽光以及粉的和白的荷花。拉穆湖周圍,是挺拔的高山,我們的祖先,一個梳著長辮子的鄂溫克人,就居住在那里。⑦
但是,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鄂溫克族人的生活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額爾古納河右岸》的下部《黃昏》體現了這種信號: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雖然鹿鈴聲聽起來越清脆了。我抬頭看了看月亮,覺得它就像朝我們跑來的白色馴鹿;而我再看那只離我們越來越近的馴鹿時,覺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輪淡白的月亮。⑧
鄂溫克人對于現代文明的發展感到無可奈何,最后營地里只有“我”和安草兒。讀到這里,感傷情緒油然而生。
現代文明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它的到來促使人類社會向前發展,但同時也使人類自己走向窮途末路。正如遲子建所說:“我痛心的是,現代文明的進程,正在靜悄悄地扼殺著原始之美,粗獷之美。”⑨現代社會的加速發展使得我們離原始之美愈來愈遠,留給我們的只有深深的眷戀與緬懷。在這樣一種悵然若失感傷情緒的基礎之上,“傷懷之美”也就不由得慢慢沁入我們的心扉。
其次,對萬物有靈論的敬仰。在“萬物有靈”“對自然界生物的敬畏和尊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等原始生存信仰中,尋找人與宇宙關系的合理內核,使其成為環境惡化、重建自然宇宙觀和生態文化秩序的參照系。⑩遲子建就是在這樣一種對人與自然界關系的深邃思考之上,以足夠的智慧和能量讓我們關注到她和鄂溫克族同樣所信奉的“萬物有靈論”。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自然萬物,都是一個個自由自在的獨立個體。同時,富有神奇色彩的原始文化濡染使遲子建的“傷懷之美”被賦予了神性的光輝,使她筆下的一草一木有了靈性。作品的開篇這樣敘述:“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歲了。”?這位年屆九旬的老人把大自然當作親密的友人進行平等友善的相處,雨和雪與人一樣擁有生命的尊嚴;部落中的馴鹿被賦予了神性的光輝,是絕對可以和人類進行平等交流的生物;作品中的列娜病重,尼都薩滿用一頭灰色馴鹿幼崽去交換列娜的“烏麥”;鄂溫克族進山打獵,一定要在一顆山神樹下,對神樹進行磕頭膜拜……
鄂溫克族的大山和河流同樣也被神性的光輝籠罩著,每一座大山和每一條河流都被賦予名字,和人一樣擁有尊嚴。鄂溫克人會根據山的特點給山進行命名,比如哪座山苔蘚多并且馴鹿喜歡在那兒流連,就把那座山命名為“莫霍夫卡山”,即生有苔蘚的山之意。再比如額爾古納河的支流得爾布爾河、塔里亞河等,也都是由鄂溫克人依據其特點進行命名的。對“萬物有靈論”的敬仰是“傷懷之美”的焦點,因為相信萬物有靈,遲子建筆下的一草一木有了靈性,遲子建的“傷懷之美”才具有了靈魂。正因為對于“萬物有靈論”的敬仰,當人類作為萬物之中一員的時候,作品之中的鄂溫克人對于自然界中人類的生死與存亡也就同樣含有了一顆敬重之心。在這種厚重氛圍的渲染之下,遲子建的“傷懷之美”得以增加了一些感傷的情緒化色彩。
再次,遲子建對人生情態的“痛感”書寫,使她的小說藝術地表達了蘊藏于內心的感傷情緒。作品中遲子建對鄂溫克人死亡情態的感動和對古老生活方式變遷的感傷,使得“傷懷之美”以一種更為厚重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對于鄂溫克人死亡情態的感動,其實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這種情懷主要體現在遲子建小說中對鄂溫克人死亡情態的感動。例如,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妮浩會對死去的人唱起神歌,這些神歌像一首首抒情詩,在死亡的憂傷中營造了一種詩意的氛圍。把“死亡”詩化,有一種圣潔之感,描繪出一種令人神往的“傷懷之美”。鄂溫克人的死亡充滿著憂傷的氣息,小說中男性的生命往往是在人生中最旺盛的時候戛然而止的。鄂溫克人因為長期生活在山林中,導致他們死亡的形式多樣,遭遇雷電、凍死在途中、遇到熊害、酗酒而死……但是他們不會因為死亡而過分悲哀,也不會因為世事無常而感到絕望,而是在心中種下希望。因為信仰“萬物有靈論”,鄂溫克人才有著獨特的生死觀,才對于人生情態的“痛感”并不是一味地悲傷,這體現出他們面對死亡時坦然處之的人生態度。
再比如,在作品中作為薩滿的尼都薩滿和妮浩,每次跳神都可以拯救瀕死的人,但是隨之付出的代價就是會失去一位自己的至親。妮浩為了救人,前后就有四個孩子夭折。妮浩說因為她是薩滿,所以不能見死不救,即使是以失去自己的孩子為代價。聽起來似乎有些荒唐,一個人怎么可以通過跳神去挽救一個跟自己無關的生命?又怎么可以以自己的孩子為代價而救活別人?作為薩滿的尼都薩滿和妮浩,因為在救助他人時有著悲天憫人的情懷,才可以坦然地去面對生活中的苦難。遲子建對鄂溫克人死亡情態的感動使作品充滿著一股憂傷的情調,同時鄂溫克人獨有的生死觀又讓遲子建對他們肅然起敬,這種獨特的生死觀是鄂溫克人看待與體悟世界的方式。
最后,《額爾古納河右岸》中所體現的“傷懷之美”,也同樣表現為對古老生活方式變遷的感傷。隨著現代文明的入侵,鄂溫克人不得不改變之前古老的生活方式,只能在現代文明的擠壓下求生存。
《額爾古納河右岸》四個部分的標題依次為:清晨、正午、黃昏、半個月亮,是時間順序的推移,更是鄂溫克族部落生活方式的變遷。從中部《正午》開始,現代文明逐漸進入鄂溫克族,打破了他們往日平淡的生活,并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作品中的許財發走后不久,一名鄂溫克獵民便帶領了一個叫吉田的日本人和一個叫王錄的日本人翻譯到部落中。在此之后,鄂溫克族的生活方式開始逐漸發生變化:鄂溫克族的男人們去山下充軍受訓,部落里只剩下女人們和馴鹿。
其實,鄂溫克人生活變遷的寫照就是外面世界世事變化的一個縮影。自此以后,他們住的不再是可以自由呼吸、到晚上抬頭就能看到星空的希楞柱,而是住在讓人感到壓抑的房屋。他們也不能像之前在部落里時頓頓可以吃到自己喜愛的生肉,而是吃著他們不愛吃的蔬菜與熟食。他們也不再以狩獵為生,而是為了生計在激流鄉尋找工作。不只是鄂溫克人,就連具有靈性的馴鹿也都被圈養起來,吃著不愛吃的草料和豆餅。
遲子建以抒情的筆觸寫出了鄂溫克人對于改變自己生活方式的無奈與感傷,以其敏感而細膩的心靈去看待與體悟鄂溫克族。
三、遲子建“傷懷之美”的形成原因
一種文學風格的形成是漸進的過程,需要作家全身心地投入和精神成長。總體來說,一個作家文學風格的形成,需要外在的社會因素和內在的個人因素共同作用。
其一,傳統文化的熏陶。毫無疑問,作家的文學創作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必然的,我國的文人大家也都是如此。遲子建“傷懷之美”文學風格的形成就受到了傳統文化中“憂郁之美”的影響。傷春悲秋是中國古典詩詞當中的文學傳統,詩人們常常因季節、景物的變化而產生悲傷的情緒。陸機在《文賦》中提到:“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以此來說明氣候、景物的變化與文學情感之間發生的關系。從屈原《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開始,古典詩詞中感傷的色彩就越來越重,到了《全唐詩》,帶有感傷色彩的詩更是不勝枚舉。遲子建受到了古典詩詞中“憂郁之美”的影響,偏愛讀書與學習,尤其喜歡屈原、辛棄疾等帶有“憂郁之美”的文學大家,而她最喜歡的經典著作是《紅樓夢》。由此可見,古典文學作品中的“憂郁之美”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遲子建的文學創作。
其二,“黑土地文化”的影響。遲子建自小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也同樣自小就生活在嚴寒的東北地區,濃郁的傳統文化的影響與獨特的地理位置生長環境,二者相互作用,使她的“傷懷之美”文學風格逐漸形成。遲子建作為地地道道的黑龍江人,她的絕大多數作品都以故鄉大興安嶺一帶為背景,表現著她濃厚的“戀鄉情懷”,她的作品也因為這片天然寒冷的土地而帶有憂傷的氣息。大興安嶺人煙稀少,四時景色不同,她感受到最多的便是家鄉寒冷的雪、綿綿的秋雨和那片黑土地的泥濘。換句話說,她心靈深處的憂傷其實是家鄉那片無垠寒冷的土地所給予的。
《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鄂溫克人因為信仰“萬物有靈論”,一草一木才被賦予了神性的光輝,由此有效地保護了自然。“萬物有靈論”使得遲子建的憂傷帶有了溫情的力量,從而使得這股憂傷不絕望,“傷懷之美”由此在遲子建的筆下油然而生。
其三,作家敏感、沉穩的個性。傳統文化的熏陶和“黑土地文化”的影響,是遲子建“傷懷之美”風格形成的外在原因,形成“傷懷之美”的內在原因是遲子建本人的個性特征。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中談道:“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各師成心,其異如面。”?意思是說,“情性”或“成心”是內心的精神氣質和思想感情決定的語言的格調風格,因為取法于內在的“情性”和“成心”,作品風貌也就各具特色。遲子建內在的“情性”和“成心”是感傷和憂郁的。她天生就是一個不愛說話的人,從不沉湎于社交媒體,而是專心于自己的文學創作。作家畢淑敏這樣描述遲子建:“假如天氣好,就會在飯廳旁的藤蘿架下,看到一個女孩依著清冷的石凳,慢慢地吃她的飯。她吃得很仔細,吃得很寂寞,一任涼風揚起她悠長的發絲。”?遲子建個性敏感、沉靜,喜歡安靜。因而,她的文風才沉靜婉約,描寫細膩生動,精妙的語言中透著一種晶瑩明亮的文字品格。
遲子建敏感沉靜的個性與她的個人經歷有關。她是在死亡的哀傷氣息中長大的,祖父和父親的去世給她的童年帶來哀傷,結婚之后,丈夫車禍去世,更對她的生活給予沉重的打擊。成長的經歷使遲子建骨子里的哀傷之感愈來愈重,她筆下的文章也就越發呈現出蒼涼的感覺,顯現出一種殘缺之美。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以其敏感而細膩的心靈去看待與體悟逝去的鄂溫克族,表現出對鄂溫克人死亡情態的感動和對古老生活方式變遷的感傷,使其帶有著一股蒼涼的美感。
《額爾古納河右岸》中對原始古樸文明的眷戀與緬懷,對人生情態的“痛感”書寫,賦予小說感傷的意味。“傷懷之美”是一種飽含深情的審美體驗,也是遲子建以其敏感而細膩的心靈看待與體悟世界的獨有方式,它充滿了對原始自然風景的惋惜、對歲月流逝的悵惘、對故土文明的眷戀、對民族文化的憂慮,它蘊含著感傷的自然情懷、悲憫的人生情懷。可以說,遲子建“傷懷之美”是在主張萬物有靈論的基礎上,立足于塵世生活的一種超越性精神追求。如今,我們生活在阡陌交通的城市之中,穿梭在星羅棋布的高樓大廈之間,更多體會到的是城市混沌的煙云。我們似乎離夢想越來越近,但是顯然已經離遲子建式的“傷懷之美”越來越遠,每天面對更多的是無休無止的工作與充滿壓力的生活,人已經逐漸變得麻木,不能敏銳地感受到“傷懷之美”。我們只有內心真正富有情懷,以敏感而細膩的心靈去看待與感受世界,才可以與“傷懷之美”不期而遇。
①胡忠偉:《遲子建:如水一樣透明》,《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年11月30日第10版。
② 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修訂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頁。
③謝有順:《憂傷而不絕望的寫作——我讀遲子建的小說》,《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第1期,第66頁。
④ 魏蘭:《擠過縫隙的魂靈 60年代女作家小說印象》,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148頁。
⑤⑥ 遲子建:《傷懷之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頁,第2頁。
⑦ ⑧? 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5年版,第11頁,第191頁,第3頁。
⑨ 遲子建,郭力:《遲子建與新時期文學——現代文明的傷懷者》,《南方文壇》2008年第1期,第60頁。
⑩ 郭淑梅:《女性文學景觀與文本批評》,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頁。
? 杜占明:《中國古訓辭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386頁。
? 趙志遠,劉華明:《中華辭海(第3冊)》,印刷工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6頁。
? 童慶炳:《文學理論新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44頁。
? 畢淑敏:《背窗而立》,《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第1期,第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