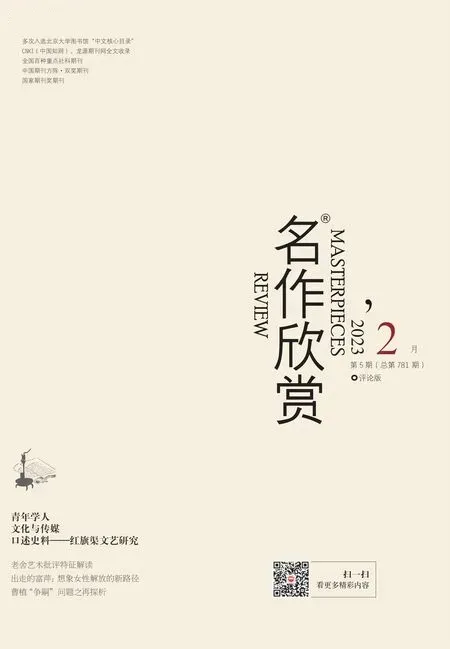數罪、贖罪與恕罪:論《煙火漫卷》的原罪觀與救贖論
⊙胡偉婧[西南大學,重慶 400715]
“罪與救贖”一直是文學創作中的不朽主題,無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還是伊恩·麥克尤恩的《贖罪》,都是對這一主題的延伸與回應。在此基礎上,為人物寄予期冀的作者,有時會在這一模式中加入“恕罪”的成分,與前二者相結合,形成“數罪、贖罪與恕罪”三位一體的新模式。遲子建的《煙火漫卷》就是這樣一部踐行了三體式“罪論”新模式并取得成功的作品。除開城市傳記性質的特色書寫與作品中歷史語境下人物的表達與對話,《煙火漫卷》對原罪觀與救贖論的書寫也是一個十分值得挖掘、但往往被我們所忽視的視角。
《煙火漫卷》自劉建國、黃娥等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出發,從小著筆、由微入手,以其作為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膩筆觸,串聯起哈爾濱這座城市數十年來的風云變幻與人心遷易。令讀者在復雜的人生故事里,觀賞到如同煙火般一時絢麗而復歸塵埃的一段人生,也窺見了這人生如煙塵般的飄蕩無依。“恕罪”成分的加入,讓作者的寬恕之情得以全程滲透,讓作品呈現出儒家人文關懷下中國文學所特有的溫情與魅力,使哈爾濱紛繁絢爛的文化在作品中深化,折射出哲學的光輝,罪罰主題也由此完整呈現出來。
通過個體的小故事,哈爾濱,黑龍江乃至當今社會的個別現狀折射在其中。世人來來往往,總是在善良中掙扎著擺脫罪愆,在惡念里逃避說不清、道不明的惶然。在遲子建的筆下,人人承受著負罪之苦,在悔罪之中,他們或爭取救贖以獲得精神解脫,或自我折磨以心安理得。在找尋自我的路上,這些人物在世間掙扎前行,如同煙火隨風漫卷,消逝在風中。
一、數罪:原罪觀與罪論意識
原罪概念源于《圣經·創世紀》,作為最初之人的亞當、夏娃未能抵擋住蛇的誘惑,偷食了禁忌之果,獲得智慧。上帝因而將其逐出伊甸園,人類由此開始背負原罪,不再被庇佑,要承受痛苦與災難。同時,在原罪論的敘事中,認為罪有傳承性:一是祖先罪責影響后代的因性原罪;二是從襁褓中帶來的果性原罪——當前社會大眾所背負的,更傾向于后者的果性原罪。在原罪論的視野下,又區分出了作家筆下更常見的、人物親手鑄就的后世罪行。
遲子建在書中揭露了罪的普遍性,即人人都有罪,所謂的道德歸罪只不過是神義論和人義論的成功結合。在眾人皆獲有原罪的前提下,個人各自的后世罪惡則是由于自身各種原因所造成的罪惡,這是具有個體性的。作品中除劉建國因特殊身世與血脈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原罪外,其余的人物角色則是更多地以后世個人原因的罪惡來呈現。這樣多層次的情節設計與布局規劃,使得作品中罪論的演繹更加多元全面,在精心構建中呈現出層次豐盈的美感。對于作品中“數罪”部分的呈現,是通過劉建國的身世原罪與其失子和猥褻的后世罪以及黃娥誤殺夫等罪行所展開的。這種數罪最終通過作者論述與人物自我領悟共同達成。
數罪觀能如此自然地融入作品,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煙火漫卷》中的城市選擇與歷史限定。因其中俄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殖民年代的歷史痕跡,使這座城市擁有了獨有的歷史語境;與此同時,遲子建所加入的特殊人物:謝普蓮娜、伊格納維奇等也從側面印證了該城市的社會狀態。此外,哈爾濱與俄羅斯的地緣關系,令它飽含多元的文化印記,而這都可以從其文化建筑的設計描繪中窺見,或是浮雕圓木的音樂廳,或是巴洛克風格的榆櫻院,又或是隨處可見的宏偉教堂,這些元素的融入,讓作品中的“罪、救贖與寬恕”擁有了堅實的落腳點。
二、贖罪:自我救贖的艱難之路
贖罪是在認罪的前提下進行的,而當人處于罪惡的深淵,與墜落僅咫尺之距時,此時的拯救又該由誰來執行?遲子建認為,人應該自我救贖。這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點不謀而合,陀氏認為人必須為自己的存在賦予意義,必須自己確立自己的終極價值。他將自我完善和自我拯救作為理想人格的目標,一句話:“自我救贖”才是真正的救贖之道。同時,人必先達成某種程度上的自救——這也就與“苦海無涯,唯有自渡”擁有了相近的意義。
在小說的敘事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作者的立場。丟失“銅錘”后的劉建國無比悔恨,自責不已,即使謝普蓮娜至死都沒有埋怨過他一句話,即使于大衛也與母親一樣,將傷痛埋在心底,甚至說出“建國,只要你不是因為銅錘有猶太血統而嫌棄他,故意把他弄丟,未來找不找到孩子,我都能接受”這樣令人哀憐、催人淚下的話來。盡管一切都體現出外界并未因他的罪孽對其進行裁決,甚至要為他洗凈這份罪責,但是劉建國仍一直處于自責的寒冬。直到他得知翁子安就是“銅錘”時,他才真正從內心得到救贖,將自己從牢籠中解救出來,解開了那自我束縛于心中的、任他人誰都解不開的繩。從始至終,在遲子建心中,能夠解開罪的繩結的只有背負罪孽之人自己。
(一)劉建國:數罪負身的“原罪之子”
劉建國作為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故事由其開端,亦由其終結。作者以插敘手法交代了劉建國當前“開愛心救護車”的工作,也開啟了對于這個故事的講述。在一次意外中,劉建國丟失了朋友托付給他照顧的孩子,為了尋找“銅錘”,他放棄了自己的生活,而選擇了這樣一個“流動性大,接觸人多”的工作,就是為了在拯救生命的過程中,拓寬交際圈來尋找孩子。在這一點上,他與麥克尤恩的《贖罪》中那個選擇護士職業的布里奧妮有異曲同工之處,他們都試圖以“拯救生命”這樣最直接、最實際的方式為自己贖罪,壓抑心中的自責,獲得心中的安寧。就在這復年復日的生活中,作者將在某一時刻以其筆端撥動命運之線,給予劉建國最終解脫的機會。與翁子安命運的交錯,是對這個花甲老人一生善意最大的回報,也是從作者層面證實了“贖罪方能恕罪”的真理。
除去失子之罪,劉建國還因與張依婷失戀的打擊對男孩武鳴犯下了猥褻的罪行。與前者不同,這一罪行更加不能被世俗所接受,更不會有人為其開解,這攀附在罪惡之上的第二層罪惡,雖然程度遠不及失子,但其性質更加不能為世人所容。兩者如附骨之疽般一直纏繞折磨著劉建國,這使得最終結束了尋子之途的他,毅然決定返回那個地方,用自己的后半生陪伴這個可憐的孩子,以求第二次的贖罪。
構成其第三層罪孽的,是作者為其賦予的、據身世被揭發出的罪。作為日本遺孤,他還對世人背負著一項無法改變的原罪。從父親劉鼎初的保護,到于大衛的隱瞞,都展現出這層罪孽的深重與頑固。從宿命論的角度而言,背負罪孽成了劉建國與生俱來的宿命——即使作者與他都認為其是無辜且無奈的。而他之所以擁有身世原罪,更需依賴的是特定城市——哈爾濱之罪與侵華戰爭之罪結合之后的成果。在原罪和后世罪的探討中,在這樣的歷史與空間中形成了一種原罪語境,更貼切地呈現出在城市空間構架中疊加的歷史與敘述的文化。針對劉建國的原罪,相較于《圣經》中提出的果性原罪,奧古斯丁的“奧氏原罪”更易理解并使人信服。他認為“不是因為犯了罪才成為罪人,而是因為我們是罪人,才會犯罪”。這與荀子的“人性本惡”論不謀而合,也是在事實論證后更貼近我們所面對的真實的一種解釋,在這樣的理解中回望劉建國的一生,一切都明朗起來。
(二)黃娥:積極贖罪的“東方阿佛洛狄忒”
作為一個坦然面對肉體情欲的自由女性角色,黃娥曾多次與客人偷情而未受懲罰,但最終卻因被丈夫誤解撒謊而背上了弒夫的罪名。在痛苦掙扎中,她最終沒有逃避現實一走了之,而是選擇在一條無比煎熬的道路上踽踽而行。她以丈夫出走為由,想要將兒子雜拌兒托付給一個值得信任的人,在此期間,她再次無奈撒謊,以謊言使謊言圓滿,乃至分發傳單作為掩飾。在將雜拌兒托付給疼愛他的人——謝楚薇手中之后,她將自己繪制的哈爾濱地圖與“哈爾濱記事”留給雜拌兒,并帶他去拜訪了哈爾濱城內眾多神靈。她這樣的行為與舉動是她決心告別與啟發贖罪的開始,這樣的托付就是試圖在祈求中感化神明,拜托他們代替自己庇佑雜拌兒。在這一過程中,在為兒子未來祈禱的同時,也是黃娥對自己的罪惡做出的虔誠懺悔。因而在她決然返回鷹谷,要以死殉夫之時,翁子安的出現,為她的罪帶來了寬恕與諒解,這也是作者對黃娥的外力拯救。
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人性惡中首當其沖的便是性本能,在陀氏的眼中,這種原始的欲望幾乎可以與罪惡畫等號,它不受理智、道德、羞恥和倫理的控制,蠻橫地沖破人類社會的樊籬,肆無忌憚地毀滅一切。但不論是低賤的瑪麗昂,還是快活的卡吉婭;不論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中自由女神般的薩賓娜,還是《白鹿原》中“妖孽”一樣的田小娥,這些女人都擁有一種不加掩飾、不媚俗作態的自然姿態——在她們的身上,欲望的本能如太陽一般不可遮掩,女性的美與真赤裸裸地展現出來。她們是性欲女神阿佛洛狄忒的現實化身,其肉欲的罪孽是對傳統道德束縛的強力反叛,是對自我欲望的不窘、容納與內化。即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論之下,包括黃娥在內的她們背負著罪孽,但是在所謂毀滅的背后,與自由主義的旗幟鮮明飄揚,這份罪的背后更體現著純粹的生命力。黃娥在不斷祈求和禱告的過程中慢慢贖罪,反而在馬車災難中印證了“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句話,似《西游記》的最終一難,此后便是重生與解脫的開始。翁子安的出現,成為盧木頭對妻子的憐憫與最終原諒。至此,黃娥的贖罪畫上句號。
(三)劉驕華:自毀中再生的“獄之守護神”
相較于黃娥的自信與堅強,劉驕華則是一個心理極度脆弱的女人,她因懷疑而想要懲罰丈夫,于是去尋找情夫、自輕自賤。幸而一絲理智仍存,讓她在最后一步的防線被攻破前終止了行動。劉驕華的試罪行為,更像是一種自我懲罰,在罪惡感中尋求愉悅,在雙重的痛苦中獲得自我滿足。這種行為成功的前提是踐行者需要處于喪失理智與倫理觀念的狀態,然而劉矯華只是一個被懷疑折磨、在道德懸崖邊徘徊的可憐女性。因此她在毀滅的邊界前停止了腳步,在將要邁出最后一步之時,是她自己的清醒也是作者給予她的一束希望之光,才使她不至于墮落無境。
后來劉驕華將全部身心投入對出獄犯人的幫助中,經營“徳至”小吃攤幫助他們自給自足,以幫助他人來麻痹自己,試圖以“大家”忘“小家”,這也是某種程度上的贖罪。她最終在助人中收獲到家的愛與關懷。保持清醒未被罪孽所污染的是她自己和作者,而將她從罪之邊界拉出來的,何嘗不是那些她以家人之愛幫助的犯人呢?
(四)翁子安舅舅:同情難責的“始作俑者”
《煙火漫卷》由許多條敘事線索構成,其中的主線情節就是劉建國失子尋子。從這一角度來說,翁子安的舅舅才是使這一切得以發生的始作俑者。這個高個子的男人在車站偷走銅錘,引發了之后的故事。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他毀了兩個家庭的幸福也毫不為過——因他之罪,于大衛和謝楚薇的家庭從此失去生機,劉建國的一生也在贖罪和懺悔中度過,不愿也不敢追求幸福;劉建國失戀猥褻的行為中失子的因素更是不可忽視的原因。在故事結尾,翁子安舅舅為了贖罪將工廠股份賠償給劉建國,這又怎么足夠?他最后贖罪成功的原因并不在此,而在于他對銅錘——翁子安的真心愛護和他對姐姐的誠摯親情。遲子建有意提及他內心的無比煎熬與懺悔,這也是作者為使讀者寬恕其罪責所做的最大努力。
三、恕罪:反饋機制下的究極重生
林季杉教授曾在其文章中寫道:“利科說過,‘罪與其說是一種轉向,不如說是一種無能’,這與使徒保羅所說的‘罪是向善的無力’有同樣的意義價值。”在最初的數罪與贖罪之后,人物或多或少都能暫時獲得一定程度的解脫,但最終使得恕罪完全實現的,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行為與付出,更具決定性的是旁觀者與評判者的接受和認同。在自我救贖的背后,隱含著對寬恕者的需要,罪人往往需要通過一定的反饋機制,使自己的罪真正在客觀層面被洗凈。簡而言之,在贖罪中,他人只是一種助力,而贖罪的施行者與評判者都是自己;而在恕罪中,自己只是施予者,其裁決權在他人手中。這種角度與身份的變化,需要“罪人”保有清晰的自我認知與審慎的考量,隨時對自身行為進行調整和校準。唯此,贖罪才能向恕罪轉變,讓罪人獲得新生,在此過程中擔任恕罪裁決者的是不同維度的“作者”形象。
(一)直接敘述者:最直接的話語體系表征
米蘭·昆德拉提出,文學應該秉持“人義論”的追求,使文學尤其是小說達到人義論的“最高精神綜合”,即通過描述人的道德可能性,讓人在不確定的人生中尋找可能的幸福。這就要求作者在文本文學性之外的倫理思考中,開始探索個人面對模糊道德處境時的不確定性。同樣,作者遲子建在自己的話語體系與語言書寫中,總是有意無意地表現出其特有的道德意愿:真誠的贖罪應該被接受,進而在被認可中完成恕罪,最終與過去的罪達成和解,轉而獲得面對未來的信心。她讓翁子安平安無事,讓武鳴沒有放棄生命,使二人得以與劉建國再次重逢;她讓黃娥死中求生,為翁子安所救贖……遲子建在第零作者潛移默化地影響下,以第一作者的權柄為作品操舵,給予了贖罪者們恕罪的機會,賦予他們希望與重生。
(二)最終接受者:讀者感悟后的回饋反響
作為接受者的讀者決定了作品的最終呈現。之所以將其稱之為第二作者,是因為在“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語境下,讀者擁有對作品內涵進行重寫與轉譯的權利。最終呈現在讀者內心的作品,是其在第一作者的原稿基礎上進行個人化闡釋的唯一版本。因此,無論是前期的“原罪”思想,還是作者的苦心設計、細致安排,都是為了使讀者接受與融入文本語境,達成最后一步的進擊。
本作所渴求的讀者群體,是懷有中國特有的悲天憫人情懷的一群人,要在儒家“仁”之范疇之下,拓展更廣闊的包容度。在這樣的倫理基礎上,作者所進行的一系列引導才能使讀者的重新書寫落腳到“恕罪”,在讀者層面實現其謀劃。讀者在這樣的道德暗示之下,才會順理成章地接受寬容的精神,與作者共同完成作品的敘事設計,才能使作品中的人物真正在作品、作者、讀者三個層面獲得恕罪,實現自身的解脫,達成最終救贖。
四、結語
借這樣一個煙火世界的人潮涌動,遲子建為人生幸福摹畫出了自己的理想方向。她認為人應該有意識數自我之罪,并在數罪后能夠有勇氣贖罪,并努力付出獲得恕罪的反饋。這就是“罪與救贖”,是自我新生所必達的條件。
《煙火漫卷》中的蕓蕓眾生,他們在人間萬般煙火中迷失,不斷追尋自我,努力找到自我。“萬物有靈,靈擇附罪”,每個人都是有罪的,應該且需要通過“數罪、贖罪與恕罪”的過程,從內心認識到自己存在的罪惡,以思想意志推動行動以贖罪,進而在他人寬恕與自我寬恕中完成恕罪,最終獲得自我救贖與解脫。這樣的過程,是殘缺自我尋求圓滿自我的過程,也是為“我是誰”的疑問作出回答的過程,人與人就在這樣的交流碰撞中相互尋找,掀起漫卷的煙火與人世的雜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