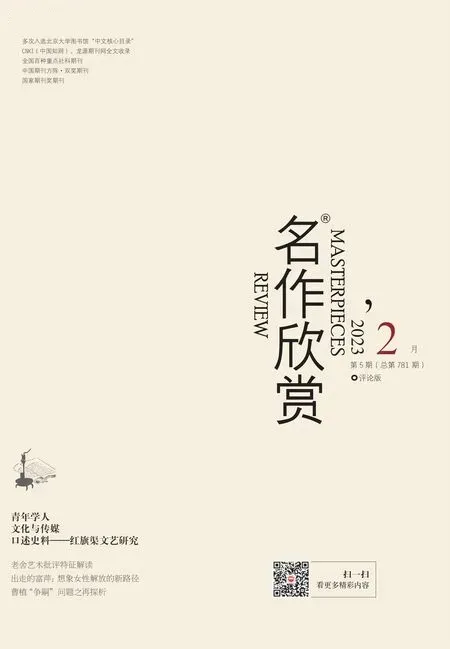淺析卡夫卡小說《變形記》中的甲蟲意象
⊙胡俊才[井岡山大學,江西 吉安 343009]
在20 世紀的西方文學領域中,后現代主義文學占據著不可撼動的主導地位,其中,魔幻現實主義和荒誕派是備受矚目的重要流派,憑借著“天馬行空”的想象、“荒誕不經”的情節、“映射現實”的寓意、“充滿批評性”的哲理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卡夫卡創作的《變形記》就是經典代表作,作者以“甲蟲”的視角及經歷刻畫了在現代社會中充滿扭曲的人性及無意識的主觀感受,表達了創作者關于人性的見解。解析被作者寄予了深刻寓意的“甲蟲”,深入挖掘其所凝聚的豐富內涵,對讀者拓展思維、增長見聞、升華情感等大有裨益。
一、卡夫卡及《變形記》的概述
(一)卡夫卡——無家可歸的異鄉人
卡夫卡生前好友馬克斯·勃羅德稱他是一個“無家可歸的異鄉人”。他在短暫的人生中,沒能很好地融入社會,融入家庭,融入生活。他從來沒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和歸屬感,實際上,在具體的生活中,他成了一個無法確定自己身份的孤獨的精神漂泊者。弗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 年7 月3 日—1924 年6 月3 日),是生活于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捷克德語小說家,本職為保險業職員,熱愛文學與創作,主要作品有小說《審判》《城堡》《變形記》等,被評選為20 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德語小說家。
卡夫卡出生在一個猶太商人家庭,自幼愛好文學、戲劇,18 歲進入布拉格大學,初習化學、文學,后習法律,獲博士學位。畢業后,在保險公司任職。多次與人訂婚又多次退婚,終生未娶,41 歲時死于肺癆。他的父親粗暴、專制,對兒子的學習、生活不聞不問,只是偶爾指手畫腳地訓斥一通,一心想把兒子培養成性格堅強而又能干的人,但結果適得其反,卡夫卡內心一直對父親存有無法消除的畏懼,由此形成了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憂郁的氣質,正是這種性格特征對其后期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變形記》——人的異化的寓言
《變形記》中,主人公格里高爾是一個旅行推銷員,也是家里的“頂梁柱”,需要照顧父母和幼小的妹妹,承擔著非常重的壓力。在某個清晨,格里高爾從床上醒來后發現,自己變成了甲蟲,雖然它的身形是“甲蟲”狀,也擁有了蟲的特性,比如爬行,喜食腐壞變質的食物,但是依舊保留著人的“思維”,也具有人的“心理動態”。在變為甲蟲之后,他遭受到家人的冷眼與虐待,最終不堪病痛折磨及饑餓而死去。
卡夫卡以“甲蟲”為意象承載體,向讀者揭示了小人物在西方社會中的悲慘命運,以寫實的手法展示了人們在承受家庭、社會等多重壓力下艱難的生存狀況,這種將人異化為“甲蟲”的創作手法帶有強烈的象征寓意。這篇小說不僅對西方超現實主義、荒誕派、魔幻現實主義、黑色幽默等文學流派影響極大,而且被認為是一則關于西方社會中人的異化的寓言。無論從科學法則上還是經驗邏輯上來說,人都不可能變為甲蟲。蟲化之荒誕性,隱喻的是西方人真實的悲慘的生存狀態,是西方現代人自我價值、自由意志和個性的喪失。
二、小說《變形記》中甲蟲的多重意象
(一)甲蟲的“情感”意象:作者與父親之間的情感糾葛
在《變形記》中,卡夫卡將格里高爾變化為一只身形巨大、細腿繁多但整體較為虛弱的甲蟲并不是偶然,也不是隨意選擇,而是在深度融合個人生命體驗之后做出的理智選擇。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父子沖突是常見的主題。《變形記》中,從心理層面來講,卡夫卡之所以將甲蟲作為意象,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和父親之間不平等、不溫馨、不和諧的親子關系。作者的父親是一個粗暴、專制且受教育程度比較低的商人,缺乏溫情,也不懂得照顧他人的情緒。他對卡夫卡從小就非常嚴厲,并不只是單純的嚴厲,而是毫無溫情的嚴厲,在卡夫卡的認知里,他的父親喜怒無常、專橫霸道,他害怕與父親見面,更害怕遭受父親的責備與呵斥,而這種野蠻粗暴的親子關系給卡夫卡幼小的心靈造成了嚴重陰影。縱然成年后,卡夫卡也依舊受到父親的“野蠻”管制,就連他交朋友這種再平常不過的事情都會受到父親的干預和阻攔。卡夫卡年滿18 歲之后,偶然之下結識了名為“略韋”的人,他是一個劇團的導演,同時也是劇團的演員,他才華出眾,性格開朗,卡夫卡與略韋相處時感到非常快樂。但是卡夫卡的父親了解到此事之后表現得非常粗暴憤怒,不僅嚴聲呵斥卡夫卡,并且還對其表現出一副輕蔑的態度,令卡夫卡感到非常難受。這件事對卡夫卡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在其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來,卡夫卡在《致父親》這封信中,明確指出:“只需對我一個人有一點興趣,你就會毫不考慮我的感情、毫不尊重我的評價地對這個人破口大罵、誣陷、丑化。比如像意第緒語演員略韋這樣的天真無辜的人就遭到這樣的命運。你還從未見過他,就用一種可怕的方式把他同蟲相比。”通過此信能夠看出,卡夫卡不僅對其父親感到畏懼,并且也流露出嚴重的不滿,他一直在父親的陰影下生活、學習、工作,內心充滿了孤寂。于是,他將這種情緒、體會融入《變形記》中,將主人公格里高爾異化為一只甲蟲,描述其父親無情野蠻地驅趕異化后的主人公,甚至提到父親將蘋果狠狠地砸向它并深深地陷在它的殼內,隨著蘋果的腐敗變質,它的殼及其脊背也受到很大傷害,最終由于脊背發炎且未得到及時救治而死去。卡夫卡通過“甲蟲”事件,描述了父親的殘暴,也表達了對父親的極度不滿。
卡夫卡自幼在父親的粗暴管制下成長,對其身心健康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他甚至認為,自己是父親的“出氣筒”,是父親的“剝削”對象,長期生活在這種環境下,卡夫卡的心理、精神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問題,他將個人精神世界分為三部分:一是卡夫卡的世界,由于自己比較弱小,無法反抗,所以這是一個被管制、被奴役的奴隸世界;二是父親的世界,由于父親一直以來都嚴厲粗暴、隨心所欲地管制卡夫卡,所以卡夫卡認為這是一個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統治者的世界;三是他人的世界,即正常的、溫馨的、平等的、開心的世界,這也是他所向往的世界。卡夫卡在《致父親》這封信中,直接將其與父親之間的親子關系看作是一場甲蟲的斗爭,指出:“我承認我們在相互斗爭……是甲蟲的斗爭,這甲蟲不僅蜇人,而且還吸血以維持生命。這是真正的職業戰士,這就是你。”完成這封信之后,作者就投入《變形記》的創作之中,主人公雖異化為甲蟲,但是依舊保留著人的“思維”,也具有人的“心理動態”。在他變為甲蟲且被家人知悉后,并未獲得父母的疼惜和關懷,而是被冷漠對待,家人將其視為毫無價值甚至會給家庭帶來負擔的“累贅”;家人的殘暴對待令變為甲蟲的格里高爾變得更加敏感、自卑,逐漸對外界一切事物產生了恐懼感,但是縱然它努力掙扎也無濟于事,最終不堪病痛折磨及饑餓而死去。甲蟲的意象與卡夫卡的經歷、心路高度契合,反映了作者內心深處難以排解的恐懼感和孤寂感。卡夫卡通過描寫甲蟲的生存斗爭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其對父親的敬畏與恐懼,他作為一只弱小的甲蟲,在與父親的斗爭中徹底失敗,最終被父親吸干血,折磨而死。
《變形記》中的格里高爾在一夜之間異化為“甲蟲”與卡夫卡的成長經歷、生命體驗息息相關。格里高爾變形為甲蟲后,父親用暴力對待他,母親默認他的自殺,妹妹最后也無法忍受他。所以,他倍感孤獨,也對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充滿了恐懼。在書中,作者借格里高爾之口道出:“我在自己的家里,在那些最好、最親的人中間,感覺比陌生人還要陌生。”由此可知,甲蟲的象征意蘊是卡夫卡生命中深刻的心靈烙印,與父親之間的情感糾葛成為甲蟲意象的象征之一。
(二)甲蟲的“社會”意象:底層人物在社會中的痛苦掙扎
在《變形記》中,作者并沒有對主人公變形為甲蟲的外在形象進行直接清晰的介紹,不過根據文本內容,可粗略地描繪出甲蟲的形象,即“沒有牙齒,身形巨大,顏色為棕色,長著一對長長的觸角,眼睛略微向外凸起,背部是非常堅硬的殼,穹頂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塊弧形的硬片,有兩排非常細弱的腿”。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講,甲蟲屬于鞘翅目昆蟲一類,是昆蟲綱中最大的一個目,無論是在高山、沼澤,還是在平原、盆地等,都活躍著它們的蹤跡。它們如同身處于資本社會中的普通人一般,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壓力,不僅“弱小”,而且屬于“弱勢”群體。
在《變形記》中,卡夫卡通過人物獨白的形式淋漓盡致地揭示了小人物在殘酷無情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生存的艱辛與悲哀:如果人失去了謀生的能力,就會被家人、被社會嫌棄,繼而遭受被拋棄的命運。在還沒有變形時,格里高爾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小職員,是社會底層人物的一員,整天為全家人的生計勞作。而在偌大的動物世界中,甲蟲也是非常普通的、弱小的。在還沒有變形時,格里高爾的工作是無趣的、艱辛的,也是廉價的,他為了照顧父母和妹妹,不辭辛苦地四處奔波,吃著廉價的食物,與其他人只是“點頭之交”,身邊也沒有知心朋友。對于格里高爾而言,不求生活美滿,只求不會面臨無妄之災。在變形為一只甲蟲之后,格里高爾依舊一心牽掛著父母和妹妹,依舊記著上班的時間,依舊想著上班的內容,并沒有因自己一夜之間變成甲蟲而感到悲哀和無助。無論是格里高爾,還是甲蟲,他們都在艱難的環境下成長繁衍,都處于社會的最底層,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壓力。
在《變形記》中,格里高爾上班、工作、吃飯等有其固定的節奏,這與甲蟲只有晃動、協調細腿才可以獲取食物如出一轍,生動地描述了人們在承受社會高壓時,只能夠通過機械反復的勞動而謀生。卡夫卡將格里高爾異化為甲蟲是為了凸顯其本身弱小且生活艱難的共性,借助“甲蟲”暗喻底層人民、普通人民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的無助與掙扎,從而映射出資本主義統治下,底層人民長年累月四處奔波、忍氣吞聲、唯唯諾諾、戰戰兢兢的生存狀況。
(三)甲蟲的“文化”意象:西歐文化變形文學的產物
在西方文學領域,變形文學占據著一席之位,卡夫卡在《變形記》中采用異化寫實手法其實也深受西方異形文化的影響,格里高爾異化為甲蟲具有“文化”意象,是西歐文化變形文學的產物。換言之,在西方文化體系中,甲蟲始終被賦予深厚的文化內涵,西歐很多國家都保留著用甲蟲揭露人性、反映家庭的“文學創作傳統”,比如在寓言小說、諺語以及電影中,通過甲蟲反映人的某種生存現狀,隱喻家庭和人性,有的充滿褒義色彩,有的則蘊含著貶低的意味,而卡夫卡在《變形記》中,將主人公異化為甲蟲不可不說是受到本土文化影響的結果。
在卡夫卡創作《變形記》之前,已出現了多部以異化寫實手法表達主題的文學作品,比如古羅馬作家阿普列尤斯的《變形記》(又譯《金驢記》)、奧維德的《變形記》等。在阿普列尤斯的《變形記》中,魯巧希望能夠通過魔法變成一只能夠自由自在飛翔的鳥兒,但是事與愿違,他變成一只了被管制、被奴役的驢,在此之后,他一直被安排勞作,一直遭受生活的苦,最終在知錯改錯后恢復人形。這部作品揭示了宗教的懲罰觀念,即魯巧因為貪念而變幻為一只被奴役、被管制的驢,這是上天對他的懲罰,而其在真心悔過之后又變為人形。
在卡夫卡創作的《變形記》中,對于格里高爾來講,變形是一種補償,是為了讓一直承受巨大社會壓力,一直忙于照顧家人的格里高爾暫時以甲蟲的身份來擺脫艱難的生活現狀。不管是從法律層面來講,還是從道德倫理層面而言,格里高爾責任意識強,工作賣命,心地善良,他是沒有任何罪過的。但最大的問題是他處于物欲橫流、信仰缺失的罪惡社會之中,每日奔波于各種世俗事務。進一步來講,格里高爾在照顧家人、奔波工作的過程中逐步喪失了人應有的尊嚴、情感及自我掌握命運的能力,慢慢地淪為無人性、無感情、無思想的機器,沒日沒夜地重復著相同的動作行為,而這就是格里高爾的真實處境,也是格里高爾遭受變形懲罰的主要原因,所以格里高爾在一夜之間變形為甲蟲是必然事件。
由此可知,格里高爾變形并非是因為個人在某方面犯錯、犯罪而受到的懲處,而是源于其對宗教信仰的忽略以及對各種物欲的渴求。在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堅持信仰、沉溺于物欲是西方人的常態,所以,格里高爾的受罰變形其實也預示了現代西方人將面臨的命運,與西方異形文學發展一脈相承。正是這種變形文學,卡夫卡才對現代西方人的困惑進行了尖銳、新穎而深刻的詮釋,因而他成了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杰出大師,也成了現代西方人心目中的“傳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
三、結語
卡夫卡是一個自傳色彩很強的作家,他的創作都是從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切身體驗出發加以升華的。他的《變形記》被認為是一則關于現當代西方社會人的異化的寓言。他的文學作品或多或少地映射著創作者的成長經歷和生命體驗,卡夫卡在《變形記》中,以人物獨白的形式淋漓盡致地揭示了小人物在殘酷無情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生存的艱辛與悲哀,以主人公異形為甲蟲這一藝術寫作方法向讀者講述了人性與家庭的故事,引領讀者在走進甲蟲世界的過程中感受小人物的恐懼、家庭的冷漠以及受社會壓迫的真實狀態,也讓人看到“人變為甲蟲”這一荒誕的狀態,既是小人物悲慘命運的寫照,也是作者卡夫卡對“現代困惑”的真實把握,它深刻地揭示了失去“自我”的現代人具有的孤獨感、災難感以及尋求自我的悲劇感和無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