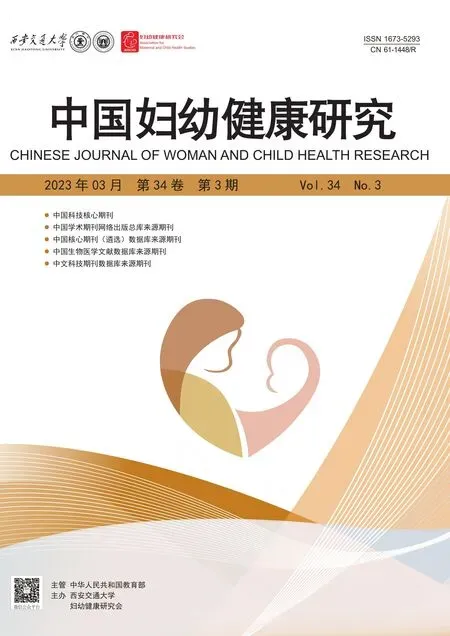兒童超重肥胖與中樞性性早熟關系的病例對照研究
郭金鑫,盧 昱,劉改燕,張學靜,劉 雪,馮偉偉,郝現偉,郭義軍,薛紅妹
(1.河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2.河北省邢臺市第三醫院兒科,河北 邢臺 054000)
中樞性性早熟(central precocious puberty,CPP)是一種生長發育異常的疾病,其特征是由于性腺激素釋放激素(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GnRH)的脈動性分泌過早導致青少年性征提前[1-2]。國內外最新研究表明,歐美發達國家及我國兒童CPP的發生年齡呈提前趨勢[3]。CPP不僅會威脅兒童身心健康,還是許多生殖系統癌癥、胰島素抵抗、成年期肥胖及心腦血管疾病等多種慢性病的重要危險因素[4]。肥胖是多種代謝性疾病的重要危險因素,但肥胖和CPP的關系還有待研究[5]。國內外大多數的橫斷面研究和隊列研究均顯示肥胖女孩青春期啟動年齡較早[6-7]。現有相關研究在評價青春期啟動時只采用乳房發育或月經初潮指標,但乳房發育不等于性早熟,月經初潮是生殖階段較晚階段出現的特征。單純利用兩者評價青春期啟動會造成對肥胖和性早熟關系的錯估。而目前針對男孩開展的研究非常有限,且結論不一。因此,本研究將邢臺市第三醫院CPP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病例對照研究,分析超重肥胖和CPP的關系,為CPP的一級預防提供科學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采用基于醫院1∶1配對的病例對照研究。將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于河北省邢臺市第三醫院就診并被診斷為CPP的234例年齡在6~9歲的患者(38例男童和196例女童)作為病例組。病例組與對照組按1∶1配對,選取同期于我院兒科就診的234例未患CPP的兒童作為對照組。對照組兒童的選取原則是與病例組兒童同性別、年齡相差<0.5歲,兩組患者的年齡、性別、體格特點等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邢臺市第三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號:2020-KY-40),并在實施過程中遵守《赫爾辛基宣言》。
1.2 納入排除標準
病例組納入標準:①CPP符合《中樞性性早熟診斷與治療共識(2015)》中相關標準[8];②監護人同意參加本研究并均已簽署知情同意書。對照組納入標準:①同期在我院兒科就診并經診斷未患CPP的兒童;②未服用過激素相關藥物和患有其他會影響體格的代謝性疾病者。
病例排除標準:①排除診斷CPP之前已是超重或肥胖的患者[8];②服用過激素相關藥物和患有其他會影響體格的代謝性疾病者;③家長不愿意參與、依從性不好的患兒。
1.3 方法
1.3.1 體格測量
患兒在門診就診時,由臨床專業醫師利用身高體重計(DHM-20T)對其身高、體重進行測量。身高精確到0.1cm,體重精確到0.1kg,重復測量兩次后取均值。計算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BMI=體重(kg)/[身高(m)]2。采用學齡期兒童和青少年性別-年齡BMI篩查超重和肥胖閾值來定義兒童超重和肥胖[9]。
1.3.2 CPP診斷標準
CPP的診斷采用2015年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內分泌遺傳代謝組公布的《中樞性性早熟診斷與治療共識(2015)》[8]:男童在9歲前、女童在8歲前出現第二性征;且經過GnRH激發試驗后符合診斷標準的確定為CPP患者。
1.3.3 實驗室檢測
于清晨空腹狀態下,對兩組兒童皮下注射GnRH,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劑量為2.5~3.0μg/kg,最大劑量不超過100μg,分別在藥物注射前、注射后30 min、注射后60min采集靜脈血2mL立即送檢,應用免疫化學發光法檢測血清促黃體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及促卵泡激素(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值。激發峰值LH>3.3~5.0 IU/L是判斷真性發育的界點,同時LH/FSH比值>0.6時可診斷為CPP。
1.3.4 問卷調查
利用自行設計的問卷,由經過專門培訓的調查員在門診對患兒母親進行詢問。調查內容包括兒童的出生日期、出生體重、母乳喂養情況,兒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職業、身高/體重、家庭人均收入,以及母親月經初潮年齡等。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連續性變量用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M(P25,P75)]表示,分類變量用頻數(百分比)表示。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進行組間差異比較;計量資料數據比較采用t檢驗。以CPP為因變量,超重、肥胖分別作為自變量,利用多因素條件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一般人群特征
病例組男童38人、女童196人;男童中位年齡8.2歲(7.5,8.8),女童中位年齡7.0歲(6.2,7.8),男女性別比約為1∶5。對照組與病例組年齡和性別匹配。病例組女童與對照組比較,出生體重較高、6個月純母乳喂養率較低、母親月經初潮年齡較小(P<0.05);在男童中,病例組6個月純母乳喂養率低于對照組(P<0.05),其他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兩組超重肥胖檢出情況
男童中,病例組和對照組超重檢出率分別為21.1%(8/38)、13.2%(5/38),肥胖檢出率分別為13.2%(5/38)、7.9%(3/38),兩組超重率和肥胖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女童中,病例組超重率、肥胖率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超重率:17.9% vs 10.2%,χ2=4.76,P<0.05;肥胖率:12.2% vs 4.6%,χ2=7.45,P<0.05),見表1。

表1 病例組與對照組人群基本特征[n(%)]Table 1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case and control groups[n(%)]
2.3 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調整混雜因素前,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與正常體重兒童相比,女童超重、肥胖可以增加CPP的發病風險(超重:OR=2.1,95%CI=1.2~3.9,P<0.05;肥胖:OR=1.8,95%CI=1.2~2.8,P<0.01)。調整了出生體重、6個月純母乳喂養(是/否)、家庭人均年收入、母親超重、父親超重、母親月經來潮年齡等混雜因素后,女童超重和肥胖仍然與CPP密切相關(超重:OR=2.0,95%CI=1.1~3.7,P<0.05;肥胖:OR=1.8,95%CI=1.2~2.8,P<0.05)。男童中,調整混雜因素前后,超重、肥胖均表現為與CPP無關(P>0.05),見表2。

表2 超重肥胖與CPP的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Table 2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nd CPP
3 討論
3.1 女童超重肥胖和青春期啟動的關系
女童超重肥胖和青春期啟動的關系在國內外被多次研究。如波蘭[10]、美國[11-14]、英國[15]、芬蘭[16]、德國[17-18]、丹麥[19]等國家的研究都證實了同一時期兒童肥胖率的增加可能是導致青春期啟動年齡提前的主要因素,而不是青春期啟動提前引起了體脂肪的增加。我國相關研究也得出類似結論[20-21]。但現有相關研究在評價青春期啟動時只采用乳房發育或月經初潮指標,乳房發育不等于性早熟,月經初潮也是生殖階段較晚出現的特征。如朱銘強等于2013年對全國6個地區的青春發育研究發現,女童8歲以前出現乳房發育的比例為2.9%,經過進一步的GnRH激發試驗等檢查確診為性早熟的有43例,性早熟的實際患病率僅為0.48%。有研究發現女童月經初潮在近幾十年較少出現變化,而乳房發育的年齡卻呈持續提前的趨勢[2]。可見,僅用乳房發育或月經初潮并不能夠全面反映女童青春期啟動的開始和變化,由此可能會引起對肥胖和性早熟的關系的錯估。本研究采用病例對照研究的方法,以經過GnRH激發試驗進行確診的CPP患兒與同年齡對照人群開展研究,回顧性地收集研究對象超重和肥胖狀況,以進一步確定女童超重和肥胖可能是CPP發生發展的危險因素。本研究結果對于正確理解超重肥胖和中樞性早熟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3.2 超重肥胖和男童青春期啟動或性早熟的關系
目前,對超重肥胖和男童青春期啟動或性早熟的關系仍存在爭議。部分研究認為兩者呈正相關[20,22],部分研究認為二者呈負相關[23-25],也有研究并未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聯系。此外,還有研究認為超重和肥胖對男童青春期發育的影響不同,表現為超重的男生青春期發育提前,而肥胖男生青春期發育延遲[26]。本研究未發現男童超重肥胖和性早熟的關系,可能與納入的男童人數較少、采用客觀準確的金標準—GnRH激發試驗判斷是否發生性早熟及混雜因素的控制等密切相關。同時本研究結果也可能與青春期男生體質量增加主要是骨骼和肌肉量增加較多,而不是體脂肪增加有關。
已有研究發現,青春期啟動提前可能和瘦素水平較高、脂聯素水平較低從而刺激性激素分泌有關[27];而且脂肪組織增多或可導致胰島素抵抗,從而降低了性激素結合蛋白的濃度,導致青春期啟動提前發生[28]。超重肥胖對性早熟的影響機制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3.3 CPP和兒童超重肥胖的關系
本研究發現,對于女童來說,超重和肥胖都可能是其發生CPP的危險因素,即超重率和肥胖率越高,其發生CPP的危險性越高。與正常體重女童相比,超重女童和肥胖女童發生CPP的危險性分別增加了101.0%和81.3%。出生體重、母乳喂養情況和母親月經初潮情況等均可能對CPP的發生造成影響。
3.4 小結
本研究采用客觀準確的方法篩選CPP患兒,利用病例對照的方法開展超重肥胖和中樞性早熟的關系研究。研究結果提示實施兒童期超重肥胖預防控制措施可能是降低CPP發生風險的重要途徑。但本研究控制的混雜因素有限,且未進行回顧性研究,研究結果還需要質量較好的前瞻性隊列研究進行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