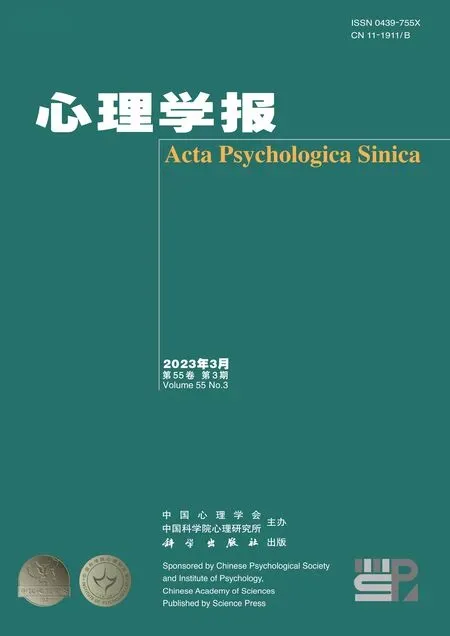“均”與“寡”階段性變動下中國居民公平感的變遷*
王俊秀 劉洋洋
“均”與“寡”階段性變動下中國居民公平感的變遷*
王俊秀1,2劉洋洋3
(1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內蒙古師范大學心理學院, 呼和浩特 011517) (3濱州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山東 濱州 256600)
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和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重復截面數據, 通過年齡?時期?隊列模型對居民公平感的時代變化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公平感在年齡上呈“J”型趨勢; 從時期效應看, 2008年公平感較高, 2010~2013年在低谷徘徊, 2015年以后又開始回升; 從隊列視角看, 建國前出生隊列公平感偏低, 建國后初期的隊列相對較高, “50”后有所下滑, 從“60”后開始公平感持續走低, 到“80”后跌入低谷, 但“90”后又開始升高。從1949年前后“寡且不均”到建國初期階段的“寡且均”, 再到改革開放40年快速經濟增長下“不寡但不均”的社會變遷過程影響了居民的公平感。
公平感, 均貧富, 社會變遷, HAPC模型
習近平在2017和2018年先后講到, “放眼世界, 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當前, 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 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大變局往往意味著重大發展機遇, 同時也面臨重大挑戰。如何贏得機遇實現更好的發展, 如何“化危為機”, 是當下中國必須解決的難題。中華文明是世界唯一以國家形態傳承不中斷的古老文明, 在許多歷史關頭能夠通過不斷的變革而應對危機。近40年來, 改革開放帶來中國快速的發展, 但中國崛起除了遇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竭力遏制, 新冠疫情常態化帶來大量經濟社會問題等外在阻力外, 社會發展也存在內在的制約因素, 其中包括貧富差距加大帶來的社會不公平等問題。這是新發展階段的危機之一, 但這樣的危機與傳染病爆發、空氣污染等風險不同, 是人們社會心態變化帶來的危機, 應對這種危機需要對風險做風險預判。居安思危是中國應對風險的哲學, 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人一次次化解風險, 臨危求變, 以智慧贏得社會發展。千百年來中國人追求富裕的努力從未停止, 同時, 防范主觀風險的意識也沒有放松過。孔子在《論語·季氏》中曾說, “有國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 和無寡, 安無傾”, 這成為后世歷代統治者消除社會不公平的準則, 也成為主觀風險的警示。當前, 在消除絕對貧困后, 貧富差距加大使得社會張力不斷加大, 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消除不公平感危機?應該說共同富裕政策的提出在一定意義上是面對這一危機, 但共同富裕并非“均富”, 貧富差距依然存在, 這一目標除了客觀的社會經濟指標外, 更重要的是主觀的社會心理尺度, 取決于人們對“共同富裕”與“均富”差異的理解。因此, 了解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公平感受及其演變規律就顯得很重要, 成為共同富裕目標實現在社會心理意義上的政策支點。
1 文獻回顧
1.1 公平感及相關概念
社會公平體現了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 是衡量社會進步的重要尺度(李迎生, 2019), 實現公平、正義是民眾的需要, 也是社會治理的目標。公平、正義是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重要議題, 相關的概念還有平等、公正等。平等(equality)指人們享有同等的人格、基礎資源、基本權利、重要能力和社會地位無差別的結果或狀態, 是擁有“社會基本品”的平等。按照羅爾斯的觀點, 公平與正義是不可分割的, 公平(fairness)就是按照相同的原則分配公共權利和社會資源, 將平等的結果和公平的程序完美結合起來的理想狀態便是社會正義(俞可平, 2017)。
社會公平要求確立一套分配資源和權利的客觀標準和程序(俞可平, 2017), 但公平感是民眾對社會公平程度的主觀評價。不同的學者在討論公平感時存在差異, 有的理解為是對公平的感知(sense of fairness) (Messé & Watts, 1983; 劉欣, 胡安寧, 2016; 鄭雄飛, 黃一倬, 2020), 有的理解為是對公正的感知(sense of justice, perceived social justice, 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 justice perceptions) (胡小勇等, 2016; 薛潔, 2007), 有的理解為是對平等的感知(perception of equality) (栗治強, 王毅杰, 2014; 李路路等, 2012)。本文的公平感指的是對社會總體平等狀況的感受(sense of fairness)。
1.2 社會變遷與公平感
社會學家什托姆普卡認為不同的社會過程因其時代、社會事件等不同而表現為不同的社會變遷形態,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可以考察其是否有發展和進步(彼得·什托姆普卡, 1993/2011), 社會進步意味著社會應該表現得更加公平。一些學者認為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沒有帶來相應的社會進步, 是一種“扭曲的發展”, 典型的表現是收入和財富分配嚴重偏斜(詹姆斯·米奇利, 1995/2009), 而經濟不平等被稱為“一種危險且不斷增長的不平等” (沙伊德爾, 2018/2019)。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不同群體之間都存在不平等, 除了通過個人財富外, 教育程度、個人權利等也體現出不平等, 不平等引發了諸多社會和心理健康問題, 消除不平等是全球面臨的難題。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的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擴大, 已經超過了基尼系數的警戒線(葛和平, 吳福象, 2019; 吳忠民, 2005; 孫立平, 2007)。隨社會變遷而來的公平問題是社會治理不得不面對的嚴峻挑戰, “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共同富裕”是新發展階段的目標(王靈桂, 2021), 共同富裕的推進將直接面對這一世界難題。“共同富裕”以經濟、社會的客觀指標來衡量, 更重要的是受國民公平感受的影響。
幾千年中國文化有“均貧富”的平均主義心態(陸震, 1996; 王曉青, 2013), 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獨特的社會正義。傳統的公平觀念被概括為“不患寡而患不均” (張志學, 2006; 周欽等, 2018)。陸震認為“均貧富”是中國歷史傳統中很古老的平均主義思想, “均貧富”并非人人均等, 而是在等級內部的“均貧富”, 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階級差別之上的等級平均主義。何蓉考察了中國歷史上“均”的含義與社會正義觀念的關系, 發現先秦時期“均”是明確的等級秩序, 貴賤高低不同所得惠利、所負義務有所不同(何蓉, 2014)。孔子在《論語﹒季氏》中曾說, “有國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 和無寡, 安無傾”。與孔子的思想類似, 孟子思想中的“均”也并非絕對平均, 而是在既定等級秩序下的整體上的合理、有度。但社會下層中一直存在實現絕對平均主義的愿望, 從唐朝中后期開始, “均”在社會思想和社會運動中變得顯著起來, 農民運動的口號與綱領中出現了均分財富與土地的要求。歷代農民起義中許多是以“均貧富”的絕對平均主義為主張喚起民眾參與的, 如北宋王小波的“吾疾貧富不均, 今為汝均之!”, 明朝李自成起義喊出“等貴賤, 均田免糧”的口號(張宜民, 2020)。“均貧富”觀念與佛教傳入中原有關, 佛教帶來了超出人倫秩序的平等觀念, 促成了唐宋以后中國社會的平等思想。因缺乏權利意識的平等而表現為追求財富平均分配的理想, 形成了對于等級、差異的道德義憤, 對于等級制度的破壞沖動(何蓉, 2014)。 “均貧富”的含義也從關注人倫秩序、社會團結變為強調分配結果的平均主義的理想的中國特有的穩定的社會心態結構, 所包含的社會心智或精神氣質已經深深地植根于中國的文化與大眾心態之中(何蓉, 2014)。不同歷史時期, 根植社會中的這種“均貧富”心態成為社會變革的動力, 也成為各個時期的社會風險。不同時期的統治者和管理者都意識到“不均”的危機, 在“均富”無法實現的情況下, 努力避免“不均”, 而“寡”成為可接受的了, 于是中國歷史的變革都是在“寡”的背景下去求“均”, 多數時期由于社會成員多數為“寡”, “不均”就沒有那么突出, 社會主觀危機并不凸顯。
但從上個世紀初開始, 中國社會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變化, 這些變化反映在“寡”與“均”的顯著變化上, 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獨特的發展路徑使“寡”與“均”的特質發生了快速的階段性變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 由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統治和長期戰爭, 使中國社會經濟十分落后, 人民生活極端困難(于昆, 2014), 廣大民眾仍處于“寡”的狀態; 新中國成立后到1952年底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 首先實行了新民主主義(陳文通, 2021), 之后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了社會財富平均分配。直到人民公社制度下實行“平均主義”, 人和人之間的地位和財富差距極大地縮小, 實現了真正的“均”, 從“寡”且“不均”到生活有所改善后的“均”的狀態; 但是長期的平均主義分配模式阻礙了社會生產(張志學, 2006), 到文化大革命結束,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國民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陳東林, 2008), 典型“均”的狀態下表現新的危機, 民眾生存危機嚴重。為了化解這種危機,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市場經濟, 打破了“大鍋飯”, 提倡引入競爭機制。并明確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不均”的社會政策, 但長遠的目標是逐漸實現共同富裕。之后, 國家經濟長期高速增長, 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另一方面貧富差距卻不斷擴大, 呈現出逐漸“不寡”但“不均”的模式。在短短的20多年的時間里, 中國已經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 轉變為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差距超過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吳忠民, 2005)。到2020年中國全面實現脫貧, 標志著真正達到了“不寡”的社會狀態, 但“不均”的程度更加嚴重。在這樣的主觀危機下, 政府確定的未來社會的目標是推動共同富裕, 通過長期努力而達到“不寡”且“均”的“均富”社會形態。如圖1所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至今, 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兩個維度三個階段, 一個是經濟維度上的“寡—寡—不寡”, 一個是分配維度上的“不均—均—不均”, 那么伴隨兩個維度上的公平感是如何變化的?經歷了幾十年經濟增長的由“寡”到“不寡”和財富分配模式由“不均”到“均”, 再到“不均”的劇烈變動后, 民眾的公平感知和評價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顯然, 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主義, 也不是“均貧富”, 目前的公平感現狀將可能影響到從傳統“均貧富”理念到共同富裕理念的過渡, 共同富裕的推行是否會使民眾“均”的感受提高?

圖1 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和財富分配模式下“寡”與“均”的階段性
1.3 公平感的研究視角和方法
國內公平感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后期, 并在2000年之后開始受到重視, 最初的研究多在討論組織管理中的公平感(張永山, 1992), 后逐漸轉向對社會整體公平狀況的評價[1]以“公平感”為關鍵詞在知網中檢索會發現1600多篇文獻, 始于1988年但數量很少, 每年一兩篇, 到2002年增加到11篇, 之后逐年增加, 到2011年達到了112篇, 之后保持在100篇以上, 2017年達到了141篇的最高峰, 檢索日期2020年11月29日。。公平感的研究有宏觀與微觀兩個視角, 宏觀的公平感也稱為社會公平感(perceptions of social fairness, 或perceived societal fairness) (胡小勇等, 2016; 張書維, 2017), 是對全社會范圍內的資源分配狀況是否公平合理的評價(Brickman et al., 1981; 高文珺, 2020; 李煒, 2016)。社會學對公平感的研究多采取宏觀視角, 并用大樣本問卷調查的方法了解民眾對社會整體公平狀況的評價(李煒, 2019; 許琪等, 2020); 微觀公平感則是個人對具體領域里的公平感知, 如對收入所得是否公平合理的評價(Brickman et al., 1981; 李駿, 吳曉剛, 2012; 李瑩, 呂光明, 2019; 王元騰, 2019)、個人獲得教育(孫百才, 劉云鵬, 2014)、就業(田志鵬, 2020)、醫療(何曉斌等, 2020)、媒介使用(朱斌等, 2018)等資源的機會是否公平, 以及在不同情境下對結果公平和程序公平的評價(張光等, 2010)。心理學更多采取微觀視角, 并集中在組織公平感領域(隋楊等, 2012; 趙書松等, 2018; 周浩, 龍立榮, 2015), 傾向于在一定的實驗情境下研究公平感(孫倩等, 2019; 呂颯颯等, 2021; 徐富明等, 2016; 張書維, 2017), 隨著社會心理學對于社會階層問題的關注, 也有學者開始關注宏觀的社會公平對個體心理的影響(郭永玉等, 2015)。
無論是微觀還是宏觀研究視角, 多數都是對公平感以及影響因素的靜態考察, 而近年來有學者開始注意到公平感變遷的問題, 例如有學者關注了公平感結構和公平感總體評價的變化,分析了2006到2017年的CSS數據, 發現對社會公平的總體評價在2013年出現下降后又上升(李煒, 2019);還有學者根據CGSS 2005和2015年的調查分析了市場化與公平感變化之間的關系, 發現民眾的結果公平感在10年間有明顯提升, 機會公平感則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許琪等,2020)。少量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存在不一致, 而且也沒有反映“均”“寡”的現實變化對公平感的影響。
目前公平感的研究比較忽視歷時性視角, 但研究社會變遷下的公平感變化意義重大, 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公平、平等和正義狀況, 其變化是對社會發展質量的檢驗, 關系到未來社會治理策略的優化。我國經歷了“均”與“寡”階段性劇烈變化, 這些不同階段的經歷者將會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打下烙印, 個體生命歷程嵌入歷史的時間和他們在生命歲月中所經歷的事件之中, 同時也被這些時間和事件所塑造(Elder, 1974)。因此, 本文引入了生命歷程理論, 這一理論試圖找到一種將生命的個體意義與社會意義相聯系的方式, 而時間維度是尋找這種聯結的重要方向(包蕾萍, 2005)。社會變遷涉及到三種時間維度:年齡(age)、時期(period)和世代或隊列(cohort), 三者雖然均為時間維度, 但所代表的意義是不同的。年齡效應代表了個體的生命周期階段, 是受生理意義上的力量的影響; 時期效應是由某個時期的瞬時作用引起, 包括特殊歷史事件、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以及科技發展等(李婷, 2018); 出生隊列(世代)指的是出生在相同年代的一批人, 他們在相同的生命階段經歷了共同的社會變革和歷史事件, 社會變遷在他們身上形成了集體歷史烙印, 并逐漸產生緩慢的累積效應, 因此同一出生隊列在主觀感受和價值觀念上就存有某種共性。相應地, 任何歷史事件對生命歷程的影響也依據隊列所處生命階段的不同而不同(Elder, 1974), 這造就了獨特的“隊列效應”或“世代效應”。公平感的隊列差異本質上就是對社會變遷的主觀反映, 也代表了個體成長經驗效應, 包含了早期生命經驗和后期連續暴露于歷史和社會因素所帶來的總體效應, 通過隊列這個時間維度可以呈現國家力量、社會變革和歷史發展對個體公平感的影響。
因此, 基于中國人幾千年來“均貧富”的心態以及近幾十年來我國社會“均”和“寡”的階段性劇烈變化, 本文擬通過多期全國綜合調查數據, 從縱向視角對我國居民公平感的時代變化進行探究。考察居民公平感在年齡、時期和出生隊列維度上的整體變化趨勢, 同時也考察了這種變化趨勢的群體差異, 并結合宏觀層面“均”和“寡”的社會變化特征試圖對公平感的時代差異進行闡釋。
2 數據及方法
2.1 數據與樣本
本文將中國人民大學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0、2011、2012、2013和2015年數據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 2006、2008、2013、2015、2017年數據進行合并, 獲得跨度12年的重復截面數據, 以考察公平感在時期維度上盡可能長的變動性。并通過隊列比較的方法, 使出生隊列從時間維度上延展至建國以來的歷史過程。為了保證模型穩定性, 本文保留了18~90周歲的調查群體, 在剔除缺失數據后, 獲得CGSS數據45042個, CSS數據41702個, 共獲得有效樣本86744個。考慮到兩份調查的抽樣框不盡相同, 本文創建了一個二分類變量納入模型以控制CGSS與CSS數據之間的差異性(陳云松, 范曉光, 2016)。本文也對兩份數據在2013和2015年的公平感進行了單獨描述分析, 發現分布較為一致。
2.2 因變量
本文因變量是我國居民的公平感。該問題在CGSS中為“總的來說, 您認為當今的社會公不公平?”, 在CSS中是“您覺得在當前社會生活中以下各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總體上的社會公平狀況”。CGSS的回答為1“完全不公平”, 2“比較不公平”, 3“說不上公平不公平”, 4“比較公平”, 5“完全公平”; 在CSS中, 2006年的選項為1“很不公平”, 2“不大公平”, 3“比較公平”, 4“很公平”, 5“不大確定”, 2008年中5為“不清楚”, 2013~2017中5表示“不好說”。為了計算和解釋的方便性, 對10期數據進行重新編碼, 將“說不上公平不公平”、“不清楚”和“不好說”合并為3[2]關于利克特5分制量表, 只有當調查對象按照預期將中點理解為真正中性含義時, 中點存在才有實質性意義, CGSS五次調查中使用的中間點為“說不上公平不公平”, 我們咨詢過調查員, 受訪者會將其作為中間含義, 中間點具有實質性意義。在CSS調查中, 受訪者在不確定時會傾向選擇不大清楚、不好說或者不大確定(Chyung et al., 2017), 但在分析中刪除不大清楚、不好說和不大確定三個選項與保留選項的結果無異, 因而本文保留了所有個案。。即1“非常不公平”、2“比較不公平”、3“一般”、4“比較公平”、5“非常公平”。
2.3 自變量
由于本文主要探討公平感在時間維度上的變化, 因此年齡、時期和出生隊列是核心自變量。已有研究對年齡和公平感之間的關系存在爭議, 有學者認為年齡大的人更傾向于對不公平行為持正向態度(張海東, 畢婧千, 2014), 但有學者則認為, 受到計劃經濟時期平均主義政策的影響, “年齡較大的人認可較少的不平等, 因此其公平感會低于年輕群體” (李駿, 吳曉剛, 2012), 還有學者認為公平感同年齡的關系是非線性的, 老年人和年輕人的公平感要高于中年群體(懷默霆, 2009)。為了驗證兩者的關系, 本文使用年齡以及年齡平方作為自變量, 以驗證年齡同公平感是否存在非線性關系[3]本文也分別使用了年齡的開方和3次方進行擬合, 發現納入年齡及其平方項擬合效果最佳。; 時期變量包括2006、2008、2010、2011、2012、2013、2015、2017年共8個調查年份; 為了能夠考察中國社會從建國初期的“寡”、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對于“寡”的改善, 再到改革開放后逐漸實現“不寡”的歷史階段, 本研究用隊列分析來覆蓋歷史時期。除了1931年之前出生以及1995年以后出生的樣本量較少, 因此各自合并成一個出生隊列之外, 其余每3年合并為一個出生隊列, 共獲得23個出生隊列。每3年作為一個隊列既保證了模型可識別性, 也盡可能呈現不同出生隊列的變異特征。
為了盡可能排除其他因素對于時間效應的影響, 本文還納入了個體層面能夠體現“寡”的程度的家庭年收入及其平方項變量[4]有研究表明收入和公平感是一種非線性關系(Alves & Rossi, 1978), 本文沒有采納個人年收入變量, 一是因為我國居民主要以家庭為單位, 家庭年收入能夠更好的體現對個人的影響, 二是在CSS2006年調查中缺少個人收入的問題。本文也對個人收入與公平感的關系進行了驗證, 與家庭收入結論一致。, 除了客觀的社會地位外, 主觀階層地位也納入到模型中。此外, 為了尋找影響公平感的宏觀因素, 將一些公認的能夠反映“均”和“寡”的宏觀指標, 比如人均GDP、基尼系數、各出生隊列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納入到模型之中, 市場經濟后財富分配差距拉大, 市場化程度是體現“不均”的重要指標, 隊列的出生人口規模大小意味著同齡人競爭的激烈程度, 也可能造成“不均”, 因此這兩個指標也納入模型[5]GDP、基尼系數和出生人口規模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和歷年《中國人口統計年鑒》, 人均GDP以1978年為基期, 并通過CPI進行調整; 市場化指數參見王小魯等《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常規控制變量包括戶口、性別、婚姻、受教育程度、工作狀況、黨員身份以及地區。具體變量描述如表1。
2.4 使用方法
由于年齡、時期和隊列(APC)具有不同的內涵, 因此本文將考察公平感在年齡、時期和出生隊列維度上的變化趨勢, 同時考察趨勢變化的群體差異。然而, 對公平感等主觀心態變化的描述, 三種時間效應是糅雜在一起的, 在分析某種時間維度變化時, 必然會混入其他兩種時間效應。由于年齡、時期、隊列存在完全線性關系(時期 = 年齡+隊列), 模型設計矩陣為非滿秩奇異矩陣, 矩陣(X'X)不可逆, 因此無法求得模型參數唯一解, 即年齡?時期?隊列(APC)模型存在“不可識別”難題(Fienberg & Mason, 1978)。如果只考慮兩種效應, 其暗含的假定是剩余的時間效應沒有影響, 這種假設將導致模型設定有誤, 最終結果有偏。為了解決APC模型“不可識別”問題, 近年來研究者們提出了一系列估計方法, 其中分層隨機交叉模型(HAPC)較好的解決了三者共線問題(Yang, 2008)。HAPC模型實質上是分層模型, 該模型將出生年份進行隊列分組, 保證每個隊列至少有兩個及以上的出生年份, 這樣年齡就可以被嵌套在出生隊列和調查年份中, 該方法將調查年份和隊列作為第二層變量, 而年齡作為第一層變量, 三者的共線關系被打破, 模型“可識別”。在分層模型中, 不同年份和出生隊列的隨機效應即代表了公平感在時期和隊列上的波動趨勢。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表1 使用變量描述統計
層一模型:
EQUAL=0jk+1AGE+2AGE+
3X+e, e~(02) (1)
層二模型:
0jk=0+0j+0k+mj+nk0j~
(0, τ)0k~(0, τ) (2)
合并模型:
EQUAL=0+1AGE+2AGE+3X+
mj+nk+0j+0k+e(3)
其中0jk表示第j個時期和第k個隊列公平感的平均得分;1為年齡系數,2為年齡平方系數,3表示層一其他自變量的固定系數,表示自變量,mj和nk分別表示時期上的宏觀變量(如市場化指數)和隊列上的宏觀變量(如隊列出生人口規模);e是個體層面的隨機誤差, 表示個體與所在組平均值的差異, 假定服從均值為0, 方差為2的正態分布;0代表總截距, 表示當時期和隊列隨機效應取均值, 其余自變量為0時的總平均值, 反應了公平感的總體平均得分;0j為隊列效應取均值時, 時期j的隨機效應, 假定服從均值為0, 方差為τ的正態分布;0k表示時期效應取均值時, 隊列k的隨機效應, 假定服從均值為0, 方差為τ的正態分布。0+0即公平感在時期上的總體變動趨勢, 而0+0則代表了公平感在隊列上的總體變動趨勢。
本文的因變量公平感是定序變量, 分值越高代表公平感越強。對應的是序次Probit或Logit分層回歸模型, 但線性分層模型的解釋更具有直觀性(Ferrer-i-Carbonell & Frijters, 2004)。在分析過程中, 線性模型結果同logit模型結果近似, 考慮到序次模型結果解釋比較復雜, 依照統計簡約性原則, 本文采用線性分層模型進行分析(模型2的分層logit結果見網絡版附錄表1)。
2.5 分析策略
本文在控制了個體層面的人口學和社會經濟變量對公平感的影響后, 利用HAPC模型以期能夠獲得年齡、時期和隊列三個時間維度對公平感的純粹效應, 并在分析過程中逐步引入市場化指數、出生人口規模等時期和隊列層面可以量化的指標, 以驗證公平感變遷是否受到這些宏觀因素的影響, 當這些因素無法消除公平感在時間維度上的差異時, 則進一步基于建國以來“均寡”劇烈變化的歷史事實, 借以推斷“均寡”社會變遷對主觀公平感知的影響。
此外, 由于所處社會位置和擁有的社會地位不同, 即使是同年代的不同群體在面臨社會財富變動時, 其面臨的機遇和財富獲得也會存在很大差異, 比如相對于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而言, 在改革開放后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在財富獲得方面就更具有優勢。從生命歷程視角看, 這些差異會影響到群體后續的生命結果, 并有可能表現為公平感知的群體差異性。在我國, 城鄉差異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區別一直是影響居民財富分配和獲得的重要因素, 因而本文在探討了居民公平感的總體變化趨勢后, 進一步利用HAPC模型從城鄉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兩個方面討論公平感的群體性差異, 借以探索“均寡”社會變遷的歷史事實對不同群體產生的效應差別。
3 分析結果
3.1 總體趨勢
分層隨機交叉模型結果見表2。模型1為基準模型, 納入了年齡、年齡平方、性別、婚姻狀況、黨員身份、受教育年限、戶籍性質、工作狀況以及地區等基本變量, 并將時期和隊列作為隨機效應放入第二層。年齡及其平方項對公平感的影響都是顯著的, 這表明公平感與年齡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 而時期和出生隊列的隨機方差也同樣顯著(τ= 0.002,=0.019;τ= 0.009,= 0.034), 說明居民公平感存在顯著的隊列和時期差異。為了更好呈現公平感在年齡、時期和隊列上的波動趨勢, 本文以圖的形式進行展示。
圖2是在控制了個體因素及時期和隊列的干擾效應后, 公平感在年齡上的變化趨勢。年齡與公平感是一種非線性關系, 居民公平感隨著年齡的增長呈現類似“J”型結構。從18歲開始, 居民的公平感在緩慢下降, 到了40歲左右下降到最低點, 隨后又開始緩慢上升; 圖3是在控制了隊列和年齡影響后, 公平感的時期波動走勢。從2006年到2008年公平感呈現上升趨勢, 且在2008年達到頂峰, 不過在2010年又出現了明顯下降, 雖然2011年公平感有所回升, 但在2012~2013年連續兩年持續下滑, 隨后在2015年和2017年, 公平感逐漸回升, 到2017年恢復到近似2008年的水平。
圖4展示了在控制年齡和時期效應后, 不同出生隊列的公平感差異。1931年之前出生的群體公平感最低, 之后出生的隊列公平感逐漸升高, 且1932~1943年出生群體的公平感保持了相對平穩性; 隨后在1944~1946年出生隊列中出現第一個高峰; 1947~1949年出生隊列又有所下降, 雖然在1950~ 1952年出生隊列中有所回升, 但隨后開始持續下降, 直到1959~1961年下降到第一個低谷; 1962~ 1964年出生隊列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出現第二個高峰; 隨后出生隊列雖有小幅度波動, 但整體上呈現下跌趨勢, 直到1980~1985年出生的群體跌到低谷, 隨后公平感開始緩慢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 “95后”的公平感較前邊的出生隊列呈現陡然上升趨勢。

表2 HAPC模型分析結果
注:***表示< 0.001, **表示< 0.01, *表示< 0.05, +表示< 0.1。

圖2 公平感的年齡變化效應

圖3 公平感的時期趨勢效應

圖4 公平感的隊列趨勢效應
表2還呈現了個體因素對公平感的影響(模型2)。家庭收入與公平感之間存在倒“U”關系, 在年收入超過約786元后即出現了拐點, 隨著年收入的增長, 公平感呈現出下降趨勢。而樣本中家庭年收入低于786元的群體不到總體的1%, 因此公平感隨著客觀經濟地位的提升反而出現下降; 主觀階層變量與公平感之間存在明顯的正向關系, 主觀社會地位越高, 公平感就越強, 這與相對比較理論的觀點一致; 在控制變量中, 婚姻對公平感沒有顯著影響; 黨員公平感更高; 受教育年限越長, 公平感反而越低; 農村居民公平感高于城鎮居民; 有工作的群體公平感更強。
3.2 群體差異反映在公平感隊列上的變動趨勢
中國社會的不同階段在“均”與“不均”上表現出群體性差異, 進而可能影響公平感的變化, 本文進一步分析了不同群體在時期和隊列上的“均”與“不均”與公平感之間的關系。盡管城鄉差異和接受高等教育在時期上的隨機效應具有顯著性, 表明公平感在時期上存在一定的群體差異, 但鑒于時期效應對全體成員影響的一致性, 不同群體在時期上的變化趨勢與總體趨勢保持了較高的一致性, 未能表現出明顯的變化差異。因此本文重點分析隊列變化趨勢的群體差異。
3.2.1 城鄉公平感的隊列變化
表2中的城鄉模型考察了城鄉居民公平感在出生隊列上的隨機波動。圖5表明, 農村居民的公平感整體上高于城鎮居民。在1964年之前的出生隊列中, 農村居民的公平感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穩定狀態, 而且城鄉居民之間的公平感差異也比較大; 但從1962~1964年出生隊列之后, 這種分化開始縮減, 農村居民公平感在緩慢下降, 而城鎮居民的公平感則緩慢上升; 從“90后”開始, 城鎮居民的公平感有所下降, 但農村居民的公平感則持續回升; 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居民, “95后”的公平感都呈現上升趨勢。

圖5 公平感隊列趨勢的城鄉差異
3.2.2 不同受教育群體公平感的隊列變動
圖6表明, 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居民公平感要低于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居民, 而且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的隊列波動更明顯。1949年之前出生并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公平感較低; 隨著出生隊列的后延, 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的公平感有下降跡象, 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的公平感則波動上升; 到整個“80后”, 公平感差異幾乎消失, 不過接受過高等教育的“80后”, 其公平感較之前的出生隊列并沒有保持繼續上升, 甚至1983~1985年出生的隊列還出現了陡然下跌; 在隨后的出生隊列中, 高等教育群體的公平感又恢復到之前隊列的水平。
4 討論
4.1 公平感的年齡和時期效應
通過HAPC模型分析可以獲得居民公平感在年齡、時期和隊列上的變化。年齡效應與個體生命周期有關, 在控制了時期和隊列效應后, 并不會受社會財富多寡和分配均與不均的影響。年齡與公平感是一種非線性關系, 居民公平感隨著年齡的增長呈現類似“J”型結構, 中年群體比年輕群體和老年群體的公平感更低, 這與懷默霆(2009)的研究結論一致。
在時期上, 從2006到2017年的十多年間, 我國社會都處于前述的“不寡且不均”階段, 2006到2008年公平感呈現上升, 2010年出現下降, 2011年有所回升, 2012~2013年連續兩年下滑, 2015年和2017年漸回升到接近2008年的水平。為了考察這段時期“不均”對公平感的影響, 模型3引入市場化指數、基尼系數以及人均GDP等宏觀變量, 基尼系數和人均GDP沒有統計顯著性, 市場化指數與公平感顯著負相關(β = ?0.016,< 0.001), 且時期效應也變成了邊際顯著(β = 0.014,= 0.059), 市場化程度帶來了更深的貧富差距, 社會變的更加“不均”, 降低了公平感。我國經濟在2006~2008年及以前連續多年快速增長, 促進了就業和收入的增加, 迅速脫“寡”的效應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均”的問題沒有凸顯, 也可能是因為中國人本身對不平等有很高的容忍度(Xie & Zhou, 2014), 公平感出現了上升。2008年后全球性經濟危機出現, GDP增速回落, 經濟發展速度下行、就業難度增加、貧富差距擴大以及房價飆升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使“不均”的問題顯現, 公平感下降。2015年以后中央對于社會保障建設的力度不斷加大, 有效促進了社會公平, 可能是公平感出現回升的重要原因。

圖6 不同受教育群體公平感的隊列差異
4.2 “均”、“寡”階段性變遷與公平感的隊列差異
本文首先在隊列分析中引入了每一出生隊列的出生人口規模、家庭年平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年限這些指標以試圖解釋公平感的隊列差異。出生人口規模大會造成同齡人擠壓效應, 隊列成員在接受教育、職業選擇和地位獲得等方面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 資源的有限性導致規模較大的出生隊列資源分配更容易出現“寡且不均”, 可能造成公平感下降。由于改革開放前實行計劃經濟, 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 城鎮居民則實行工作分配, 缺少競爭機制, 使得人口規模的擠壓效應不顯著。實行市場經濟以后, 就業競爭環境使同期群效應開始顯現[6]在只分析1974年以后出生的隊列時, 出生隊列人口規模與公平感呈現負相關(β = ?0.042, p = 0.012)。, 在“70后”之前的出生隊列, 人口規模變動與公平感的變化趨勢并無明顯的聯系, 但是從“70后”開始, 人口出生規模與公平感的變化呈現了明顯的相反趨勢(網絡版附錄圖1)。此外, 隊列平均收入越高公平感反而越低, 不過出生隊列平均受教育年限沒有顯著效應。
在加入了隊列層面變量后, 公平感的隊列效應依然顯著。從生命歷程的范式角度講, 隊列效應(或曰世代效應)反映了每一出生隊列獨特的生命歷程, 而生命早期的社會環境尤其能夠影響個體發展和價值觀形成(李春玲, 2020), 代際社會學就特別強調每一隊列生命早期的社會經驗對其價值觀形成產生的重要影響。因此本文嘗試結合各出生隊列在生命早期遭遇的社會“寡”、“均”變化的經歷對公平感的隊列差異予以分析。圖4可以看到幾個明顯的分界點, 1909~1931年隊列公平感極低, 1932~1943隊列雖高于前一隊列, 但整體都比較低, 1943年及以前出生的隊列在對公平有所體驗的成人早期正處于建國前后到大躍進的時期, 這些隊列的成人初期是經濟水平較差的時期, 也就是“寡”的時期, 小時候和成年初期“寡且不均”的生活經歷可能影響其一生的公平感知。
1944~1946年隊列公平感高于之前的出生隊列, 1947~1949年隊列略低于前一個隊列, 但1950~ 1952年隊列也接近1947~1949年隊列, 我們把這三個隊列看作隊列的第一個高點, 這個時期出生的人成人初期正處于新中國成立后經濟恢復發展、實行人民公社和單位制度時期, 也就是“寡且均”的時期。在這個歷史階段, 單位制度和人民公社為代表的社會制度提倡大公無私的集體主義精神, 集體主義文化強調將自己視為整體的一部分(Triandis, 2001), 人們通過群體來追求自身利益(Yamagishi, 1988), 與社會支持網絡聯系緊密(Huppert et al., 2019), 生命早期“均貧富”的社會經驗使這代人公平感較高。
但1953年以后的出生隊列公平感是比較低的, 且1959~1961年隊列的公平感最低, 這些隊列在他們成人時期恰好處于改革開放初期, 正面臨從“寡且均”向“不寡且不均”的轉折點, 在婚育、擇業等人生關鍵期遭遇日益“不均”的社會現實, 生命早期的這些經歷導致他們公平感整體偏低; 不過1962~1964年隊列的公平感是很高的, 這個高點的隊列在成人初期同樣處于80年代初的市場經濟初期, 這與我們預期的公平感與“均寡”現實變動的關系有一定出入。
之后隊列的公平感低于1962~1964年出生隊列, “80后”的公平感明顯低于其他出生隊列。而且低公平感覆蓋了整個“80后”以及“90后”隊列的初期, 他們的公平感甚至低于1949年前出生的隊列, 這些隊列成年初期進入到了貧富差距拉大的時期, 也就是“不寡且不均”的典型時期。私有制經濟的興起使公社和單位安全網的社會保障作用大幅度削弱, 中國經濟高速騰飛的代價是短時期內貧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市場經濟雖然帶來了高效率的經濟速度, 但也強烈沖擊了在改革開放后步入勞動市場的“80后”和“90后”, 就業競爭加劇, 教育和醫療成本提升, 特別是房價上漲給他們帶來更大的生存壓力。收入不平等大大降低了人們的自我階層定位(陳云松, 范曉光, 2016), 機會公平感出現了顯著下降, 由此導致的對“階層固化”現象的關注也成為了一種社會性焦慮(陳云松等, 2019)。同時, 這一時期集體主義在不斷衰落(蔡華儉等, 2020; 黃梓航等, 2018), 個體主義不斷上升, 而個體主義文化價值更注重公平(Huppert et al., 2019), 因此趨向個體主義文化的80、90后對社會不公的敏感性更為強烈。面對“不均”的社會現狀, 盡管絕對“寡”的貧困問題被逐漸消除, “不均”的社會現實與傳統文化中“均貧富”理念的距離導致他們的公平感偏低。但值得注意的是, “95”后公平感是所有隊列中最高的, 該隊列的成人初期大約是2015年前后, 正是國家重視社會保障, 強調分配公平, 開始推動實現“不寡且均”的時期。當然調查中的“95”后大部分仍在求學, 并未完全踏入社會, “95”后的公平感效應仍需后續數據觀察。
以上不同隊列之間的公平感存在明顯的階段性, 經歷過從“寡且不均”進入“寡且均”變化的隊列的公平感較高, 但隨后出生隊列的公平感便降低了, 這意味著“寡且均”并沒有解決公平問題,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命題是不成立的; 改革開放提高了民眾生活水平, 在生命早期經歷這段變化的隊列的公平感也出現了高點, 但其后出生隊列的公平感依然較低。生命早期遭遇典型“不寡且不均”社會事實的隊列的不公平感甚至超過了經歷“寡且均”時期的隊列, 這意味著“不均”對公平感的影響要大于“寡”, 這樣似乎是“既患寡也患不均”, 只是“寡”與“均”二者對公平感的影響權重會有差異; 之后出生隊列較高的公平感似乎說明, 在“不寡”基礎上對“均”的追求具有更明顯的效果。
4.3 公平感變化的群體性差異
本文在數據部分同時探索了城鄉和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感隊列差異。在城鄉的隊列差異中, 1935年以后出生的農民恰逢建國初期無償獲得土地和生產資料, 在生命早期享受到社會資源重新變“均”的政策對他們的公平感產生了持久的正向作用。在改革開放后, 家庭聯產承包制使生活得到改善, 之后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進入城市, 多種因素影響下農民收入增加, 由“寡”逐漸到“不寡”, 但家庭聯產承包制也拉開了農村貧富差距, 即變得“不均”, 同時進城農民也可以直觀感受到城鄉差距, 在這個時期步入社會的“60”、“70”以及“80”后農民更能夠體會到社會的貧富差距, 公平感低于之前的隊列。城市居民的公平感雖然一直低于農民, 但后續出生隊列的公平感是變高的, 城鎮居民是改革開放中財富積累的受益者; 從教育的隊列變動趨勢看, 建國初期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公平感更低, 但1950年及以后出生隊列的公平感逐漸變高。市場經濟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在社會財富分配中優勢凸顯, 盡管社會逐漸走向“不均”, 但在“寡”逐步得到解決的過程中, 財富向這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傾斜, 他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 因而“50后”、“60后”和“70后”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的公平感較高。但“80后”的公平感卻比較低, 這可能與“高校擴招”后就業競爭加大、財富分配不再占優有關。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群體的公平感保持了與總體隊列近似的變化趨勢。
4.4 社會變遷、生命歷程與公平感
需要明確的是, 很多宏觀因素并不容易被測量, 本文也只是選用了人均GDP、市場化指數、出生人口規模等幾個可以量化的指標。本文主要是借鑒了生命歷程視角, 嘗試結合建國以來中國社會財富分配的“均”與“寡”變遷過程為公平感的時間變化提供一種解釋思路。然而個體不會只受到社會財富“均寡”一種事實的影響, 一系列歷史事件和社會政策都會對生命結果產生長期影響, 這在個體生命早期經驗中尤為突出。比如1940年之前出生的隊列, 不僅僅面臨“均”“寡”的問題, 而且這些建國前出生的隊列在兒時和青年階段也經歷了動蕩的戰爭年代, 這直接影響了他們接受教育、組建家庭、婚育以及工作, 生命角色轉變的延遲、機會喪失經歷導致的累積劣勢有可能降低他們的公平感知; 再比如在1959~1961年出生的隊列恰逢三年自然災害, 這種不幸經歷同樣會干擾其后續的發展, 加重了該隊列的不公平感; 而1962~1964年隊列出生時則錯開了災害時期, 而且其成年步入社會時“十年動亂”也結束了, 社會再次趨于穩定, 雖然該隊列在成人初期同樣面臨逐漸“不寡且不均”的變化, 但其公平感卻較高; 再比如“文革”等政治運動和“上山下鄉”政策對建國前出生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負面影響更大(Meng & Gregory, 2002), 這些歷史事件改變了知識分子的人生軌跡和發展機遇, 也降低了他們的公平感。生命歷程中的社會政策和歷史事件都能夠對個體生命結果產生結構性影響, 這些就可能體現在對公平的主觀感知上。
本文使用HAPC模型對中國居民公平感的年齡、時期和隊列變化趨勢予以了分析, HAPC模型能夠對年齡、時期和隊列三個時間維度各自的純凈效應進行剝離, 有助于精確把握宏觀社會因素對個體生命結果產生的影響。本文基于中國社會近幾十年獨有的“均”“寡”變遷事實, 為中國居民公平感的時代變化提供了一種解釋思路。本文大致得到如下結論:(1)公平感的提高包含兩條路徑, 通過經濟增長達到“不寡”或富裕, 通過財富分配制度實現“均”, 這兩條路徑不能單獨實現社會公平的提高; (2)不同歷史時期所表現出的“寡”與“均”的特征對公平感的變化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寡”和“均”這兩個經濟增長變量和財富分配變量共同影響著公平感; (3)“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定的條件下是適用的, 但僅靠提高“均”不能解決公平問題。圖1中從階段1到階段2, 也就是從“寡且不均”階段到“寡且均”階段是我國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嘗試, 從“不均”到“均”的社會變革初期確實提高了民眾的公平感, 但很快就開始下降; (4)依靠經濟增長解決“不寡”的問題, 是提高社會公平感的基礎, 但如果沒有適當的分配制度相配合, 公平感甚至會更低。從階段2到階段3, 由經濟不發達到經濟快速提高, 民眾生活狀況極大改善, 同時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初期公平感出現提高, 但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 不公平問題甚至更加突出; (5)在擺脫貧困后財富分配制度對于公平感的提高效益極其明顯, 近些年共同富裕政策實施明顯快速提高了社會公平感。這是中國獨特發展道路中社會治理經驗的總結, 也是這一研究對未來中國共同富裕政策實施的啟示。
1949年前后到現在, 中國經歷了社會制度的巨變, 社會經濟政策的大調整, 仿佛經歷了一個 “寡”與“均”的社會實驗, 可以看到“寡”與“均”兩個因素對公平感的影響。幾千年來信奉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并非無條件的, “均”并不能化解歷史積淀的“均貧富”社會心態危機, “既患寡也要患不均”, 這需要新的變革, 需要中國人的智慧來實現共同富裕, 達到“富”與“均”的均衡。
Alves, W. M., & Rossi, H. R. (1978). Who should get what? Fairness judgments of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3), 541–564.
Bao, L. P. (2005). Reflects on the timing view of life-course theory.(4), 120–133.
[包蕾萍. (2005). 生命歷程理論的時間觀探析.,(4), 120–133.]
Brickman, P., Folger, R., Goode, E., & Schul, Y. (1981). Microjustice and macrojustice. In M. J. Lerner & S. C. Lerner (Eds.),(pp. 173–202). New York: Plenum.
Cai, H. J., Huang, Z. H., Lin, L., Zhang, M. Y., Wang, X. O., Zhu, H. J., … Jing, Y. M. (2020).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A literature review.(10)1599–1618.
[蔡華儉, 黃梓航, 林莉, 張明楊, 王瀟歐, 朱慧珺, … 敬一鳴. (2020). 半個多世紀來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變化——心理學視野下的研究.,(10), 1599–1618.]
Chen, D. L. (2008).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2),63–72+127.
[陳東林. (2008). 文化大革命時期國民經濟狀況研究述評.(2),63–72+127.]
Chen, W. T. (2021). Three revolution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3),31–56.
[陳文通. (2021).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三次革命(上).,(3), 31–56.]
Chen, Y. S., & Fan, X. G. (2016). Social class self-position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mobility (2003-2013).(12),109–126.
[陳云松, 范曉光. (2016). 階層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觀流動感知(2003—2013).(12),109– 126.]
Chen, Y. S., He, G. Y. & Ju, G. D. (2019). Uncorrelated perception of mobilit: Is China under social immobility?(6),49–67.
[陳云松, 賀光燁, 句國棟. (2019). 無關的流動感知:中國社會“階層固化”了嗎?(6),49–67.]
Chyung, S. Y., Roberts, K., Swanson, I., & Hankinson, A. (2017). Evidence-based survey design: The use of a midpoint on the likert scale.(10),15–23.
Elder, G. H. (1974).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errer-i-Carbonell, A., & Frijters, P. (2004). How important is methodology for the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8)641–659.
Fienberg, S. E., & Mason, W. M. (1978).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age-period-cohort models in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archival data. In K. F. Schuessler (ed.),(pp. 1–67)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Gao, W. J. (2020).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5)28–44.
[高文珺. (2020). 社會公平感現狀及影響因素研究.(5)28–44.]
Ge, H. P., & Wu, F. X. (2019).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context and mechanism of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China.(5),21–28.
[葛和平, 吳福象. (2019). 中國貧富差距擴大化的演化脈絡與機制分析.(5),21–28.]
Guo, Y. Y., Yang, S. L., Li, J., & Hu, X. Y. (2015). Social fairness researches in perspectives of social class psychology.(8),1299–1311.
[郭永玉, 楊沈龍, 李靜, 胡小勇. (2015). 社會階層心理學視角下的公平研究.(8),1299–1311.]
He, R. (2014).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in Chinese history.(5),140–164+243.
[何蓉. (2014). 中國歷史上的“均”與社會正義觀.(5),140–164+243.]
He, X. B., Liu, J. K., & Zhang, Y. L. (2020).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 of doctors' trust and its mechanism: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tive of the sense of fair.(6),109–118.
[何曉斌, 柳建坤, 張云亮. (2020). 醫生信任的城鄉差異及其形成機制——基于公平感視角的實證分析.(6), 109–118.]
Hu, X. Y., Guo, Y. Y., & Li, J., & Yang, S. L. (2016). Perceived societal fairness and goal attainment: The differnet effects of social class and their mechanism.(3), 271–289.
[胡小勇, 郭永玉, 李靜, 楊沈龍. (2016). 社會公平感對不同階層目標達成的影響及其過程.(3), 271–289.]
Huang, Z. H., Jing, Y. M., Yu, F., Gu, R. L., Zhou, X. Y., Zhang, J. X., & Cai, H. J. (2018). Increasing individualism and decreasing collectivism?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 around the globe.(11),2068–2080.
[黃梓航, 敬一鳴, 喻豐, 古若雷, 周欣悅, 張建新, 蔡華儉. (2018). 個人主義上升, 集體主義式微?——全球文化變遷與民眾心理變化.(11),2068–2080.]
Huppert, E., Cowell, J. M., Cheng, Y., Contreras‐Ibá?ez, C., Gomez‐Sicard, N., Gonzalez‐Gadea, M. L., ... Decety, J. (2019).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references for equality and equity across 13 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 cultures.(2), e12729.
James, M. (2009).. (Z. M. Miao, Trans.).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5)
[詹姆斯·米奇利. (2009).(苗正民譯). 上海:格致出版社.]
Li, C. L. (2020). Intergenerational sociology: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values and behavior patterns of the new generation in China.(11), 26–42.
[李春玲. (2020). 代際社會學:理解中國新生代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的獨特視角.(11), 26–42.]
Li, J., & Wu, X. G. (2012).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urban residents view of equ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3), 114–128.
[李駿, 吳曉剛. (2012). 收入不平等與公平分配對轉型時期中國城鎮居民公平觀的一項實證分析.(3),114–128.]
Li, L. L., Tang, L. N., & Qin, G. Q. (2012). "Fear of inequality, but more fear of unfairness”: Sense of fairness and consciousness of conflict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4), 80–90.
[李路路, 唐麗娜, 秦廣強. (2012). “患不均, 更患不公”——轉型期的“公平感”與“沖突感”.(4),80–90.]
Li, T. (2018). Which generation is happier? An age-period- cohort analysi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residents.(1), 90–102.
[李婷. (2018). 哪一代人更幸福?——年齡、時期和隊列分析視角下中國居民主觀幸福感的變遷.(1), 90–102.]
Li, W. (2016).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aluation on social justice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past ten years., (6),3–14.
[李煒. (2016). 近十年來中國公眾社會公平評價的特征分析.(6),3–14.]
Li, W. (2019). The sense of social fairness: Structure and trend——An analysis of the trend of public social fairness between 2006 and 2017.(6),110–121.
[李煒. (2019). 社會公平感:結構與變動趨勢(2006-2017年).,(6), 110–121.]
Li, Y., & Lv, G. M. (2019). Perception of income fairness, prospect of mobility and preference for redistribution—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GSS 2013.(4), 35–49.
[李瑩, 呂光明. (2019). 收入公平感、流動性預期與再分配偏好——來自CGSS2013的經驗證據.(4),35–49.]
Li, Y. S. (2019). The value basis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social policy: On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policy.(3), 76–88.
[李迎生. (2019). 中國社會政策改革創新的價值基礎——社會公平與社會政策., (3),76–88.]
Li, Z. Q., & Wang, Y. J. (2014).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people's sense of justice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8), 99–105.
[栗治強, 王毅杰. (2014). 轉型期中國民眾公平感的影響因素分析.(8),99–105.]
Liu, X., & Hu, A. N. (2016). Perception of income fairness: A sociological new institutionalist explanation.(4),133–156.
[劉欣, 胡安寧. (2016). 中國公眾的收入公平感:一種新制度主義社會學的解釋.,(4), 133–156.]
Lu, Z. (1996).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陸震. (1996)..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Lv, S. S., Sun, X., Shen, L. L., Wu, Y. Q., Zhao, S., Wang, F., & Wang, Z. J. (2021). Effect of group membership on unfairness perception under coexperience conditions.,(7),773–787.
[呂颯颯, 孫欣, 沈林林, 武雨晴, 趙紓, 王霏, 汪祚軍. (2021). 群體共同經歷影響不公平感知.(7),773–787.]
Martin, K. W. (2009). Views of Chinese citizens on current inequalities.(1),96–120.
[懷默霆. (2009). 中國民眾如何看待當前的社會不平等.(1), 96–120.]
Meng, X., & Gregory, R. G. (2002). The impact of interrupted education on subseque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 cos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4), 935–959.
Messé, L. A., & Watts, B. L. (1983). Complex nature of the sense of fairness: Internal standards and social comparison as bases for reward evaluations.,(1), 84–93.
Piotr, S. (2011).(J. R. Lin, Trans.).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3)
[彼得·什托姆普卡. (2011).(林聚任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Sui, Y., Wang, H., Yue, Q. Q., & Fred, L. (2012). The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follower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ocedural justice.(9),1217–1230.
[隋楊, 王輝, 岳旖旎, Fred, L. (2012). 變革型領導對員工績效和滿意度的影響:心理資本的中介作用及程序公平的調節作用.(9),1217–1230.]
Sun, B. C., & Liu, Y. P. (2014). Estimating educational equality between regions and genders in china —— based on gini coefficients of education from 2002 to 2012.(3), 87–95.
[孫百才, 劉云鵬. (2014). 中國地區間與性別間的教育公平測度:2002-2012年——基于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基尼系數分析(3), 87–95.]
Sun, L. P. (2007).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ons of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China., (3), 96–105.
[孫立平. (2007). 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特征與原因.(3),96–105.]
Sun, Q., Long, C. Q., Wang, X. X., & Liu, Y. F. (2019). Fairness or benefit? the effect of power on distributive fairness.(8),958–968.
[孫倩, 龍長權, 王修欣, 劉永芳. (2019). 公平或是利益?權力對分配公平感的影響.(8),958–968.]
Tian, Z. P. (2020). Analysis of ethnic education access and sense of employment equity——Basing on the 2017 and 2019 Chinese social survey data.(5), 70–79.
[田志鵬. (2020). 少數民族教育獲得與就業公平感的分析——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5), 70–79.]
Triandis, H. C. (2001).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personality.(6), 907–924.
Walter, S. (2019).. (P. F. Yan, Trans.).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8)
[沙伊德爾. (2019).——(顏鵬飛譯). 北京:中信出版社.]
Wang, L. G. (2021).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 new goal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4), 5–10.
[王靈桂. (2021). 實現共同富裕:新發展階段的嶄新目標.(4),5–10.]
Wang, X. L., Fan, G., & Hu, L. P. (2019).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王小魯, 樊綱, 胡李鵬. (2019).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Wang, X. Q. (2013). On the justice though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s conversion to modern value.(2), 83–86.
[王曉青. (2013). 傳統文化中的公正思想及其現代價值轉換.(2), 83–86.]
Wang, Y. T. (2019). Reference groups, relative position and micro-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permanent migrants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ese metropolis.(5), 203–240.
[王元騰. (2019). 參照群體、相對位置與微觀分配公平感——都市戶籍移民與流動人口的比較分析.,(5), 203–240.]
Wu, Z. M. (2005). Current situation and tendency of social justice in China., (2), 82–88+ 238.
[吳忠民. (2005). 中國社會公正的現狀與趨勢.(2), 82–88+238.]
Xie, Y., & Zhou, X. (2014).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19), 6928–6933.
Xu, F. M., Shi, Y. W., Li, O., Zhang, H., & Li, Y. (2016). Mechanisms and measures of the public’ sense of income unfairness: Dual viewpoint of reference dependence and loss aversion.(5),665–675.
[徐富明, 史燕偉, 李歐, 張慧, 李燕. (2016). 民眾收入不公平感的機制與對策——基于參照依賴和損失規避雙視角.,(5),665–675.]
Xu, Q., He, G. Y., & Hu, J. (2020). Marketization and change of perceptions about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hina: 2005–2015.(3), 88–116.
[許琪, 賀光燁, 胡潔. (2020). 市場化與中國民眾社會公平感的變遷:2005–2015.(3), 88–116.]
Xue, J. (2007). Investigation on some citizens’sense of justice in China.(5), 87–95.
[薛潔. (2007). 關注公民公平感——我國部分公民公平感調查報告.(5),87–95.]
Yamagishi, T. (1988). Exit from the group as an individualistic solution to the free rider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6),530–542.
Yang, Y. (200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2 to 2004: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2),204–226.
Yu, K. (2014)..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于昆. (2014)..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Yu, K. P. (2017). Rethinking equality, fairness and justice.(4),5–14.
[俞可平. (2017). 重新思考平等、公平和正義.,(4), 5–14.]
Zhang, G., Jennifer, R. W., & Yu, M. (2010). Chinese farmers perceptions of justice: An analysis based on a survey about village elections.(1), 64–84.
[張光, Jennifer, R. W., 于淼. (2010). 中國農民的公平觀念:基于村委會選舉調查的實證研究.(1), 64–84.]
Zhang, H. D., & Bi, J. Q. (2014). The alienation of city residents: Based on data of 2010 shanghai survey.(4), 94–109.
[張海東, 畢婧千. (2014). 城市居民疏離感問題研究—以2010年上海調查為例.(4), 94–109.]
Zhang, S. W. (2017). Social justice,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public cooperation intention.(6), 794–813.
[張書維. (2017). 社會公平感、機構信任度與公共合作意向.(6), 794–813.]
Zhang, Y. M. (2020). The appeal of the slogans of peasant uprisings in the ancient China and its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9), 111–114.
[張宜民. (2020). 歷代民變口號訴求對社會秩序重建的啟示.(9), 111–114.]
Zhang, Y. S. (1992). The sense of fairness of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my country structure and cause analysis.(3),23–29.
[張永山. (1992). 我國國有企業職工的公平感結構及成因分析., (3), 23–29.]
Zhang, Z. X. (2006). For the Chinese concept of distributive justice.(2), 157–190.
[張志學. (2006). 中國人的分配正義觀.(2), 157–190.]
Zhao, S. S., Zhang, Y. J., & Zhao, J. (2018). The third-party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Research perspective, content and design.(12),2216–2229.
[趙書松, 張一杰, 趙君. (2018). 第三方組織公平:研究視角、內容與設計.(12),2216–2229.]
Zheng, X. F., & Huang, Y. Z. (2020). The effect of fairness perception on peasants’ participation in new rural pension insurance program—Evidence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5),3–18.
[鄭雄飛, 黃一倬. (2020). 社會公平感知對農村養老保險參與行為的影響——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實證研究.(5), 3–18]
Zhou, H., & Long, L. R. (2015). How to make justice judgment of multiple referents: Bandwagon effect and snob effect.(2),70–76.
[周浩, 龍立榮. (2015). 參照對象信息對分配公平感的影響:攀比效應與虛榮效應.(2), 70–76.]
Zhou, Q., Qin, X. Z., & Liu, G. E. (2018). To worry more about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an poverty——Impact of relative living standard on mental health among Chinese population.(9),48–63.
[周欽, 秦雪征, 劉國恩. (2018). 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對生活水平對居民心理健康的影響.(9), 48–63.]
Zhu, B., Miao, D. L., & Li, L. L. (2018). The internet and justice perception: A paradox and explanation.(6),78–89.
[朱斌, 苗大雷, 李路路. (2018). 網絡媒介與主觀公平感:悖論及解釋.,(6), 78–89.]

附表1 模型2序次logit回歸模型結果
附圖1 出生人口規模與公平感變化趨勢
Equalitarianism and wealth in China: Changes in perceptions of fairness
WANG Junxiu1,2, Liu Yangyang3
(1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School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uhhot 011517, China) (3School of Marxism,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256600, China)
The eradica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progress in achieving social equality in China, where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main social goal. However, since the founding of modern-day China, it has not only changed from poverty to wealth, but also from addressing imbalances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to an uneven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e great changes seen over the past century in China have impacted people who have adhered to the idea of equal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resulting in a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fairness. A sense of fairness is a subjective response to social equality, which is bound to fluctuate with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erefore, combined with dramatic social changes in recent decades, this paper discusses changes in residents’ sense of fairness and explores the path to resolving this equity cri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Chinese Society (CGSS) conducted by Renmin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the survey of social conditions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SS) from 2006 to 2017, this study examines cross-sectional data spanning ten years. The hierarchical age-period-cohort model (HAPC) is used to analyze trends in changes in Chinese people’s sense of fairness in three time dimensions: age, period, and birth cohort.
The study found that sense of fairness has a significant time effect in China. (1) The sense of fairness among middle-aged adults was lower than among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2) The sense of fairness was high in 2008, trended lower from 2010 to 2013, and started to rise again after 2015. (3)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ense of fairness of the birth cohort was low. The sense of fairness of the birth cohort was high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it has been lower since the birth cohort of 1953. In the early 1960s, the sense of fairness in the birth cohort rebounded, but after that, it continued to decline. The sense of fairness was the lowest after 1980, but there has been a sharp upward trend since 1990. (4)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of fairnes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level of educ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although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significant, wealth distribution has not been equitable, and that economic growth alone cannot improve social equity. These two variables jointly affect people’s sense of fairnes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people do not suffer from scarcity but suffer from inequality. Addressing scarcity is the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sense of social fairness. I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is unjust, people’s sense of fairness will be even lower. After eradicating poverty, a wealth distribution system would have obvious benefits for improving the sense of fairness. This conclusion is instructiv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policy.
sense of fairness, 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social change, hierarchical age-period-cohort model
B849: C91
2021-06-07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21JZD038)資助。
王俊秀, E-mail:wang_jx@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