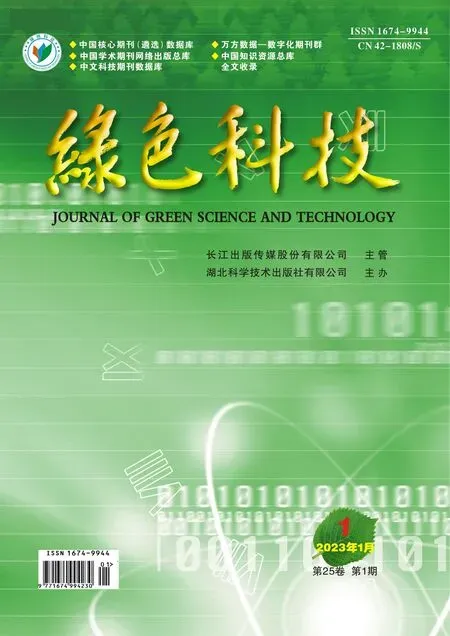數字鄉村建設中“底圖底數”數據體系建設與實踐
——以萬州區箱子村為例
曾 燕,楊 帆,吳高林,翟輝龍,梁 玲,胡 穎
(重慶市萬州區規劃設計研究院,重慶 404000)
1 引言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數字鄉村”概念,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實施“數字鄉村戰略”。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和鄉村振興建設部署和要求,鄉村建設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任務,也是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推進數字鄉村建設,將數字技術與傳統公共服務與管理融合,構建農業農村大數據體系,不斷提高面向農業農村的綜合信息化服務水平。隨著我國數字鄉村的發展,江浙地區、川渝地區、京津翼地區根據自身地理特征和發展優勢積極探索數字鄉村實現路徑,并依托成功建設經驗,對周圍區域起到輻射點帶動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數字鄉村發展路徑還不明確、系統框架也在完善之中、資金分散、資源分散、數據分散等實際問題。目前不管是國土空間總體規劃數據庫規劃、自然資源信息化建設總體方案,均側重在國家發展、城市開發、城市管理等宏觀層面和大尺度,鄉村的管理和發展很大程度上有別于城市,《數字鄉村白皮書(2021)》給建立數字鄉村、數字生態體系等作出解釋與探索,因此本文以數字鄉村建設為目標,搭建一套適宜數字鄉村“底圖底數”數據體系,探索制定相應數據規范標準,為數字鄉村建設搭建一套數據底座。
2 數字鄉村建設數據基礎建設現狀與問題
2.1 數字鄉村建設情況
數字鄉村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一環,數字技術將支撐農業現代化發展,提升農村信息化應用水平。加快推動數字鄉村建設與發展,既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也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數字鄉村建設整體水平明顯提高,信息化技術正全面賦能農業細分行業,為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近年來,信息惠農、直播帶貨成為新潮。一些地區從電商直播入手,發力鄉村建設;一些地區從智慧農業入手,改變農村面貌。在越來越多的地方,數字經濟觸角的延伸,融入鄉村生活眾多場景,改變著農業的點點滴滴(圖1)。

圖1 近年來數字鄉村指數
從整體發展來看,數字鄉村建設包括3個重點方向:①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升級,包括鼓勵開發適應"三農"特點的信息終端、技術產品、移動互聯網應用軟件,不斷豐富"三農"信息終端和服務供給等建設,2020年12月份,我國互聯網普及率為79.8%,其中農村互聯網普及率為55.9%;②智慧農業的建設,2020年,智慧農業市場規模268億美元,較上年增加37億美元,同比增長15.84%。智慧農業發展空間巨大,將具體產業與數字化相結合,包括國家農業農村大數據平臺、國家數字農業農村創新中心、"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等建設,用數字化能力賦能農業生產;③治理與公共服務,一方面用數字化賦能鄉村治理,包括農村地區"智慧法援"、農村地區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智慧化氣象災害預警體系、應急廣播主動發布終端覆蓋等建設;另一方面用數字化手段來提升公共服務能力,包括全國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提升工程、縣域遠程醫療專網、金融科技賦能鄉村振興示范工程等建設。
2.2 數字鄉村底圖底數建設現狀
由于鄉村村域廣、人口多,鄉村治理涉及面廣、事多、量大、管理壓力大,傳統基層治理面臨村民參與治理程度低,決策有失科學性、治理忽略時效性等挑戰。
數字鄉村,本質是“數據驅動的”,2021年9月3日,中央網信辦、農業農村部、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等多部門聯合制定的《數字鄉村建設指南1.0》公開發布,為全國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繪制出總體“施工圖”,但是數字鄉村建設最突出的短板就是缺乏數據,而且是統一標準、動態化更新的數據。如果沒有動態數據的有效支撐,建設數字鄉村相當于紙上談兵。構建數字鄉村數據庫,需要依托一個庫的數據內容,統一時空基準、統一數據標準,同時又可以適應于不同的業務應用,最終實現數據動態化更新、可視化展示、數字化分析、精細化管理。數字鄉村建設是數字化時代下的必然趨勢,針對數字鄉村不同的應用場景業務需求,定制開發應用平臺,以更好助力鄉村振興。
2.3 數字鄉村中數據體系建設存在的問題
2.3.1 “孤島”現象突出
目前,農業信息化管理平臺建設不完善,缺乏統一標準和規范體系,成為制約數字農業發展瓶頸,數據分散不統一,缺乏相關數據采集、處理和發布等標準,各物聯網設備或管理平臺之間無法實現共聯共享,信息數據完整性、關聯度不高,碎片化嚴重,信息孤島現象較為突出。
2.3.2 數字鄉村建設缺乏整體的規劃設計
鄉村振興戰略中已經提出“實施數字鄉村戰略,做好整體規劃設計”的要求,農業農村信息化有總體規劃,但數字鄉村依然處在自上而下各地自主探索中。全村的農業農村信息示范基地是以各地的政府、企事業單位為主體,而不是以某地鄉村為主體。同時各類智慧應用功能還處在各自為陣應用的狀態,還有待進行系統性的集成。
2.3.3 數字鄉村的支撐要素有待加強
隨著人口遷移,人才、資金等要素不足,制約了鄉村振興的發展,在數字鄉村建設的發展中,表現地更加明顯。一方面數字鄉村建設的人才不足,村、鎮領導對數字鄉村的認識有待加強,專業技術人才不足,作為參與者和應用主體的村民信息化素養有待提升。另一方面,農村信息化資金需求較大,對于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很難給予資金上的充分支持。
2.3.4 數字鄉村體系注重點單一
目前多地已經開展數字鄉村建設,但建設都圍繞某單一點進行應用開發,一方面存在缺乏面上體系設計問題,另一方面數字體系建設一般由專業團隊建設,可后期運行維護一般由村自行維護,因此在體系后期維護和數據動態更新缺乏考慮與研究。
3 數字鄉村底圖底數數據體系及標準建設
構建數據標準體系目標是通過統一的數據體系和標準,結合管理機制、數據系統控制等手段,能夠實現內部數據的完整性、有效性、一致性、規范性和共享性,為數據使用和管理提供規范化的有效依據。數字鄉村中的底圖底數則是圍繞鄉村振興實施規劃中以“人、地、產”為核心進行數據資源體系設計,有別于規劃數據成果庫,更多是從現狀、規劃、管理全過程的數據貫通體系設計,不僅將人地產進行關聯設計,更有助于后期進行數據更新以及運行和維護。
3.1 數據體系建設
數據體系建設主要是數據分類和數據具體內容2個部分。
3.1.1 數據分級分類
參照自然資源部的信息化工作方案和國土空間規劃數據庫規范中的數據分級分類標準,對村域級別的數據分級采用現狀數據、規劃數據、管理數據和社會經濟數據四大類不變,同時考慮本數據庫的數據是最直接用于基層村級管理,在此基礎上在社會經濟數據中增加重大項目管理類,用于重點項目管理。
3.1.2 數據內容
數據內容根據村級管理需求和實際情況,對數據內容進行微調,主要是調整數據原數據體系中沒有包含的鄉村一級的數據,如村組界線、村域規劃、農村宅基地等(表1)。

續表1
3.2 數據標準建設
從數據標準建設實施過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數據標準設計制定、數據標準評定、數據標準運行與維護。
3.2.1 數據標準設計與制定
數據標準從整體包括數據數學基礎、數據庫結構、數據要素編碼等。在數據標準設計過程中為了實現以信息查詢空間、以空間查詢信息、以人查地、以產查權利人等應用需求,數據標準設計時應充分考慮數據產生和流轉之間的關聯性,將人、地、產和空間信息建立標準化聯系,進而有效支撐數據體系、數據庫建設在數字鄉村中的實際應用。
具體數據標準設計中,標準是參考國土空間規劃成果、國土調查數據庫標準、土地利用數據庫標準等各類現行數據庫標準,保證數據庫的內容、要素分類代碼、數據分層、數據結構和元數據能夠與現行國標、行標或地標無縫對接,此外根據實際需求和使用邏輯,對數據庫標準進行合理增項,達到數據關聯、使用便捷的目的。
數據標準中的數據結構重點在深化重要指標、屬性信息,確保能夠實現精細化管理。例如歷年的國土調查成果一直是以權屬為主的,但權屬卻落在座落位置,具體項目或事件管理過程中也不能直接判斷涉及直接權利人;人地產房細化屬性和關聯,結合房屋調查和農村不動產登記確權信息,將房屋調查中的產權人、居住人與人口普查中的人口數據進行細化和關聯,即可以獲得每一套房子位置、屬于誰、居住人數、房屋結構、層數、建造年代等信息,人、房、地緊密關聯不僅有利于村管理人員日常管理、同時也能夠從不同視角印證數據合理與準確性。
按照以上邏輯對每一個數據逐一制定標準、逐一進行內在關聯,最終形成完整的數據庫標準(表2、3)。

表2 國土調查底圖數據庫標準

表3 農村房屋數據庫標準
3.2.2 數據標準評定
數據標準的評定是數據標準可用、能用、易用的關鍵環節。在數據標準和規范制定過程中需要充分了解數據生產、使用、管理等各個環節中的作用與角色,在標準初步完成后應再次與相關部分進行深入溝通,核實確認是否滿足應用需求;此外需進行專家咨詢與評審,充分論證標準的規范性、可用性等。
3.2.3 數據體系與標準運行
數據體系確定、數據標準規范完成后即可進行使用。各項數據在貫標執行中,因很多數據存在內在聯系,需要將標準體系的深層次的、數據存在內在關聯關系、易出錯之處對使用人員進行全面系統的培訓,同時也需對后期數字鄉村應用系統開發人員進行深入溝通和交流,確保數據和信息系統有序銜接、高效使用。
4 萬州區箱子村案例實踐
4.1 項目基本情況
箱子村位于恒合土家族鄉西南角,幅員面積7.4 km2,下轄6個村民小組。村委會所在地距離恒合土家族鄉場鎮約4.2 km,距離萬州中心城區約80 km,距離湖北利川蘇馬蕩旅游景區4.4 km。在鄉村振興建設中,箱子村重點培育茶葉和蔬菜種產業,本文從鄉村規劃編制和鄉村重點項目建設出發,探索了底圖底數數據庫在村管理角度的應用。
4.2 項目實踐
4.2.1 鄉村振興規劃編制
在鄉村振興規劃編制中,挖掘生態本底(圖2)、社會經濟本底和建設本底(圖3)提供基礎數據服務,并通過數據庫快速統計各類本底數據形成數據統計表,輔助形成各類規劃分析圖。

圖2 生態本底

圖3 建設本底
明確空間管制要素后,融合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飲用水源保護區、公益林、禁限養區、地災隱患點六大管制要素,依托數據庫和簡要的空間分析,得出村域內受管制空間總面積約396.09 hm2,占村域總面積的53.4%,為產業規劃和建設提供空間指引(圖4)。

圖4 各類管控要素分布與占地面積分析
4.2.2 重點建設項目管理
在鄉村振興中,輔助產業項目落地。在項目選址初期,通過“底圖底數”數據庫的數據應用,直接疊加管理數據,可獲取項目選址與各類管控要素的空間位置關系,并出具空間沖突要素圖;依托深化指標數據還可以統計分析得出,選址范圍內涉及多少農戶,各戶多少土地等等細化信息(圖5、表4)。

表4 蔬菜基地項目占地按戶統計

圖5 選址與沖突檢測
4.2.3 其他
通過對人口與住房掛接后,實現貧困戶人口空間分布、住房等信息互查,有利于駐村扶貧干部快速開展對口幫扶工作。
4.3 啟示
(1)數據標準實踐發現全面理清各類數據本底工作量大,各類數據關聯關系相互交錯,梳理數據內在聯系工作量更為龐大。案例中在具體梳理人、地、房、產一體化過程中,需要逐圖斑與相鄰產權人進行認定,在此過程中也暴露出地的底圖細分還不夠,存在一圖斑多產權人的情況,從側面反映要想做好村級數據管理,必須有一張將地表覆蓋劃分更為詳實的底圖。
(2)實踐表明要想做到各類數據靈活關聯,實現統計自由方便較為困難,例如本次案例中發現承包土地,可統計農民承包出土地獲得的相應受益,卻很難自由統計土地承包方在該土地上獲取的收益。因此在數據關聯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在具體數據標準制定前,需要確認數據標準具體使用人和使用方向。
(3)功能與應用。數據標準及數據庫的建立僅僅能夠實現較為簡單和原始的數據應用,而且數據庫操作需要專業技術人員,在鄉村管理中多為管理人員,因此為全面實現數據價值,需要研發相應信息系統,能夠將復雜、繁瑣操作封裝后,可將數據直觀可視化展示,定制開發功能便于村級管理人員直接使用。
5 結論與討論
數據體系和標準是數字鄉村建設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也是數字鄉村建設中的一項基礎設施建設。要充認識其重要性,以數字鄉村建設為目標導向,以實際需求和使用出發為出發點,從不同角度、深度和維度,充分研究數字鄉村建設中的數據體系、數據標準和應用方向,實現數字鄉村助力鄉村振興建設與發展。此外,數字和農村顯得格格不入,為深入融合數字和農村兩塊,需要在人才培養方面進行突破,培養懂農村、懂數字管理的符合型人才,從而推動數字鄉村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