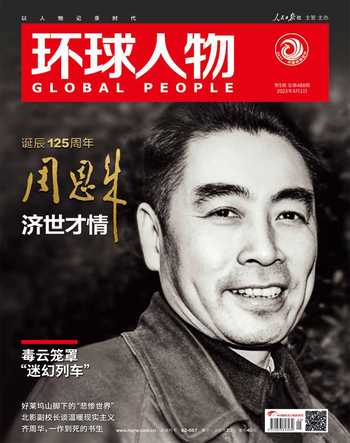李敬澤,文學(xué)館奇妙夜
陳娟

2023年2月25日,李敬澤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
1936年8月,病重的魯迅身體稍稍有一點(diǎn)好轉(zhuǎn),一天夜里醒來,叫醒了許廣平。
“給我喝點(diǎn)水。并且去開開電燈,給我看來看去的看一下。”
“為什么?……”許廣平明顯有些驚慌,大約以為他在講昏話。
“因為我要過活。你懂得么?這也是生活,我要看來看去的看一下。”聽完他的話,許廣平“哦”了一聲,給他倒了水喝,在房間里徘徊了一下,又輕輕地躺下,沒有去開電燈。
不久之后,魯迅在《“這也是生活”……》一文中詳細(xì)回憶了這一情景,表達(dá)了對許廣平不開電燈的“不滿”,寫下很重的一句:“我知道她沒有懂得我的話。”接下來,便是大家耳熟能詳?shù)哪蔷洌骸巴饷娴倪M(jìn)行著的夜,無窮的遠(yuǎn)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guān)。”兩個月后,魯迅去世。
這番話令很多人心動,作家李敬澤也是如此。2000年,36歲的他出了一本書,取名就叫《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如今,他又將“無窮的遠(yuǎn)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guān)”作為自己參與的最新人文談話節(jié)目《文學(xué)館之夜》的定位,“無窮的遠(yuǎn)方,無數(shù)的人們,星空下的大千世界,人類的生活,其實這一切,都與文學(xué)有關(guān)”,他說。
《文學(xué)館之夜》是發(fā)生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的7個奇妙的夜晚。作為主持人的李敬澤,每晚邀請三位好友在那里漫談,談故鄉(xiāng)、養(yǎng)貓文化與親密關(guān)系的建立、說話之道、父子關(guān)系、腦機(jī)接口、跑步文化等。“我們既談?wù)撆c文學(xué)有關(guān)的一切,也面向人們的生活。”他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說這話時,我們正坐在他的辦公室里,被書包圍著。
就在采訪的那個午后,不遠(yuǎn)處的北京圖書訂貨會正在進(jìn)行著,書山書海,人聲鼎沸,熱鬧極了。“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里,文學(xué)其實始終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類似于空氣和水。”李敬澤說。
作家、文學(xué)評論家之外,李敬澤還有一個身份: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分管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作為館長,他常常思考一個問題:文學(xué)館固然有它學(xué)術(shù)性的一面,同時作為博物館也有很強(qiáng)的公共性,那么它該如何面向公眾?如何將文學(xué)與公眾的生活聯(lián)系起來?
去年3月,經(jīng)過館內(nèi)多番調(diào)研、策劃、論證、再策劃,決定做一檔視頻節(jié)目《文學(xué)館之夜》,“用大眾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談?wù)摗鞑ノ膶W(xué)”。節(jié)目由李敬澤主持,每期定一個話題,從經(jīng)典文學(xué)出發(fā),4人圍坐漫談,互相碰撞、彼此激發(fā)。
第一夜,談?wù)摰氖枪枢l(xiāng)。“我們都是從故鄉(xiāng)出發(fā),無論是地理還是精神上,走向廣大的世界。”李敬澤說。在這期節(jié)目中,他和小說家雙雪濤等人,分享各自對于故鄉(xiāng)人、故鄉(xiāng)事的不同體驗與思考。雙雪濤是近幾年崛起的東北小說家之一,但在最初寫作時,他并未將筆觸伸向身邊的東北社會,直到寫小說《大師》,讓主人公說一口東北話,并以父親的方式做事,“突然之間找到了敘事的節(jié)奏。之后,我才發(fā)現(xiàn)了故鄉(xiāng)的存在,或者故鄉(xiāng)文學(xué)性的存在,對我個人來說,它才成了一個我可以適用的東西”。

《文學(xué)館之夜》第二夜,李洱、李敬澤、戴錦華、鸚鵡史航(從左到右)一起漫談。

《文學(xué)館之夜》第四夜“父子關(guān)系”錄制結(jié)束后,李敬澤(左)和梁曉聲在文學(xué)館漫步。
李敬澤自己則很少有“故鄉(xiāng)感”。他生于天津,后來因父母工作調(diào)動,在保定、石家莊幾個地方轉(zhuǎn),16歲考上北京大學(xué),此后便一直在北京生活。他回憶,和母親回河北姥姥家,自己說普通話,外人覺得“很高級、很洋氣”。母親則剛一到家,就將普通話切換為家鄉(xiāng)話,不然別人會覺得:“你裝什么裝。”
這期節(jié)目在元宵節(jié)當(dāng)天播出,不少在外地工作的人準(zhǔn)備離開故鄉(xiāng),因此引發(fā)了一場關(guān)于“故鄉(xiāng)”的大討論。
在已播出的4期節(jié)目中,最受歡迎的是第二夜的“養(yǎng)貓”。這源于冰心一生愛貓,她養(yǎng)的“咪咪”融入許多當(dāng)事人的記憶。在現(xiàn)代文學(xué)館,恰好有一只“館貓”,經(jīng)常趴在冰心的紀(jì)念碑上。節(jié)目中,李敬澤、李洱、戴錦華、鸚鵡史航4人談與貓的相處,談貓文化的演變,最后延伸到當(dāng)下流行文化中貓的意義。“他們愛的是一種一生都渴望獲得的某一種被寵溺,被關(guān)愛,被贊美的狀態(tài),(將之)投射到寵物身上。”戴錦華說。
“每一個話題都經(jīng)過層層篩選,最大限度地貼近人們的生活和日常經(jīng)驗,凝視和思考今天中國人的生活。”李敬澤說。他們談現(xiàn)代人的說話之道,“一句頂一萬句,頂?shù)阶詈螅蔷褪浅聊!薄爱?dāng)生活中沉默的時候,才需要文學(xué)。”談父子關(guān)系,從過去的緊張、對抗到現(xiàn)在的“肩并肩”;談腦機(jī)接口,與科幻文學(xué)、人工智能有關(guān)……
那段時間,李敬澤每天下午6點(diǎn)左右開始錄制,錄完天就黑了,滿天星斗。錄制“父子關(guān)系”那晚,結(jié)束后他和梁曉聲走出攝影棚,在文學(xué)館的院子里漫步,路過朱自清的雕像時,他佇立了許久。“在這個院子里那些星星就是魯郭茅巴老曹,是那些一直在精神上照耀著我們、指引著我們的人。”
“我們的語言、思維方式、情感方式、看世界的方法,實際上都是從文學(xué)中來,或者深刻地受到文學(xué)的影響。這種影響,有時是潛在的、不斷蔓延的。比如我們看到月亮,很容易就想到李白的詩,想到故鄉(xiāng),或者感受到純潔、幽怨、浪漫的情愫。一代一代的文學(xué),給我們提供了一套看世界、看月亮的方式。”李敬澤說,文學(xué)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我們現(xiàn)在要做的,是讓這種潛在的影響化為一種更加自覺的文學(xué)生活,或者更加自覺地讓它成為公眾生活的一部分。”
李敬澤之所以成為李敬澤,也與文學(xué)有關(guān)。“每個人小時候讀過的書,曾經(jīng)為之深深感動的那些文學(xué)作品,也是‘故鄉(xiāng)’。它們從根本上塑造了我們,指引著我們。在生命里,我們也需要不斷回到這個故鄉(xiāng),找到這個故鄉(xiāng)。”

李敬澤的作品《上河記》和《跑步集》。

2000年,李敬澤進(jìn)行了一場黃河之旅,圖為他在寧夏天都山山頂遠(yuǎn)眺。
他的文學(xué)觀念、閱讀趣味和寫作風(fēng)格的形成, 得益于少時。父母都是北大考古系畢業(yè),他童年時就在堆滿陶罐的庫房里奔跑,每天除了瘋玩,就只有一件事:看書。母親單位院里那個封存的倉庫就成為他最初的圖書館。
“那時候,我讀了很多歷史書,包括范文瀾的《中國通史》、郭沫若的《中國史稿》,也讀托爾斯泰、三島由紀(jì)夫等,雜亂無章地狂讀,完全無用的,既不是為了求知,也不是為了考試,就是覺得好玩兒。”在上大學(xué)之前,他已經(jīng)讀了許多同齡人讀不到的書,他對現(xiàn)代生活最初的感知就來自蘇聯(lián)小說,“哎呀,家里開著小汽車,吃魚子醬,還開舞會”。
1980年,16歲的李敬澤考上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畢業(yè)時,李敬澤面臨兩個選擇——總后勤部和《小說選刊》的編輯。他選擇了后者,文學(xué)道路就是這樣走上來的。他做文學(xué)編輯,每天看小說,一麻袋一麻袋地看,看得多了,受邀寫評論。三十來歲開始寫,先只是有一搭無一搭地,“別人說寫得好,便越寫越多”,無意中寫成了批評家;寫著寫著,寫作成了生命中的一個事;再寫著寫著,才開始涉及自我要求,覺得要寫好。
“我不想遵循什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更喜歡感性地自由表達(dá)。”李敬澤說。
1994年夏,在長江三峽的游輪上,他讀到了法國歷史學(xué)家布羅代爾的《15至18世紀(jì)的物質(zhì)文明、經(jīng)濟(jì)和資本主義》。在那個夜晚,布羅代爾帶他進(jìn)入15世紀(jì),那里有歐洲的城堡和草場、大明王朝的市廛(音同纏)和農(nóng)田;有500年前之人身上衣裳的質(zhì)地,簽約時所用紙筆……布羅代爾說,這就是“歷史”,歷史就在這無數(shù)細(xì)節(jié)中暗自運(yùn)行。
在布羅代爾的歷史觀的指引下,李敬澤開始了自己的冒險。他漫步于茫茫史料中,搜集起蛛絲馬跡、斷章殘簡,寫形形色色的外國人——莫名流落福建海岸的印度水手,16世紀(jì)大明王朝的葡萄牙囚犯,手舞足蹈地從事翻譯工作溝通兩國文化的通士……寫作時,他打破散文、隨筆和小說的界限,把想象、虛構(gòu)、歷史、事實混搭在一起。
2000年,這些文章集結(jié)成《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出版,17年后再版時更名為《青鳥故事集》。“這肯定不是學(xué)術(shù)作品。恰恰相反,它最終是一部幻想性作品。在幻想中,逝去的事物重新生動展現(xiàn),就像2000年前干涸的一顆荷花種子在此時抽芽、生長。”李敬澤說。
他多次表示對寫作的態(tài)度是“文人式的”。“中國文學(xué)有‘文’的傳統(tǒng),《莊子》《戰(zhàn)國策》《史記》是什么文體?你根本沒法定義。”他追求的是一種回歸傳統(tǒng)的“元寫作”。沿著這種“文人式”的寫作,他先后推出《詠而歸》《會飲記》《跑步集》等,雜花生樹、不拘一格,在文壇形成了一種“敬澤現(xiàn)象”。
好友、作家李洱也覺得將李敬澤和他的文章進(jìn)行歸類,是一件讓人犯難的事。“散文家、知識考古家、小說家,還是批評家?在我們熟知的文化場域之內(nèi),李敬澤的確具有多重身份,多到他自己可以在身體內(nèi)部隨時開個party。”
記者上一次采訪李敬澤是在2017夏秋之交,當(dāng)時他剛剛出版了談古人古典的《詠而歸》。6年過去,他清瘦了許多,“甩掉了10多斤肉”,因為跑步。
跑步的習(xí)慣正是在那一年養(yǎng)成的。他每次跑四五公里,不聽音樂,但會想事情。有段時間,他從公園跑完出來,路過一座天橋時總會停留,抬頭望望對面3棵漂亮的鵝掌楸。望著望著,他思緒飛揚(yáng),從鵝掌楸的歷史、瀕危的命運(yùn),到地球變暖、文學(xué),再到它的另一個名字“奧運(yùn)楸”。最終,他寫成一篇文章《跑步、文學(xué)、鵝掌楸》。“文學(xué)就是要把大地上各種不相干的事情、各種像星辰一樣散落在天上的事情,全都連接起來,形成一幅幅美妙的星圖。”
跑步之外,李敬澤也喜歡行走。他理想中的作家有兩種:一種如北京雨燕,日復(fù)一日毫不停歇地在天上飛;一種如唐三藏和孫悟空,用雙腳在大地上行走,丈量人世的艱難。前者如李白和曹雪芹,后者如杜甫。
2000年5月,他被“行走”一詞召喚,背上行囊,走過甘肅、寧夏、內(nèi)蒙古、陜西,從黃河之源走到黃河的入海口。他行走于西海固地區(qū),探訪一個個帶著“關(guān)”字的地名和山間的城堡;他拜訪榆林,在米脂街頭遇見一位民間剪紙藝人,剪下了《千年古樹開花,夢一場》,“繁華至極,又悲涼至極”;他在蘭州祁家村遇到一位老婦人,兩人談起了兒子、時間和死亡。
半年的行走結(jié)束后,李敬澤窩在家里寫了一本《河邊的日子》,2001年出版。去年底,這本書更名為《上河記》再次出版。
“重讀這本書時,我并不喜歡2000年的那個我,我一邊讀著一邊刻薄地嘲笑他。但我還是很感激他,記錄了那個時代黃河沿岸的日常與生活,是過去20年來巨大變化中的一個小小標(biāo)記,某種程度上也標(biāo)記了后來的我:對田野、對山河故人、對實際的而不是理念的人世與人事的持久熱情與向往。”李敬澤說。
寫了30多年,寫作之于李敬澤,已成為業(yè)余的另一份工作。“像一個游擊戰(zhàn)士一樣,這樣才會出其不意(哈哈)。我常常在工作間隙寫作,有時會覺得偷來、搶來的兩個小時特別香。”李敬澤說。6年前,他就廣而告之要寫一部《春秋傳》,因為那個時代給予他強(qiáng)烈的內(nèi)心沖擊,“春秋時代的人,無論善惡都精力充沛,活得開闊,既有義薄云天的高點(diǎn),也有地獄般的黑暗”。之所以四處嚷嚷,不是為了提前做廣告,而是給自己施加壓力:都喊出去了,趕緊寫吧。
對于這部未完成的、規(guī)模宏闊的作品,李敬澤覺得現(xiàn)在沒什么可說的。采訪接近尾聲,他與我們相約,或許5年后,《春秋傳》完成了,我們可以再選一個午后,盡情地聊一聊,聊春秋,聊有關(guān)文學(xué)的一切。
1964年生于天津,作家、評論家。曾任《人民文學(xué)》雜志主編,現(xiàn)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館長。代表作《青鳥故事集》《詠而歸》《上河記》等,近日由其策劃、主持的人文談話節(jié)目《文學(xué)館之夜》正在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