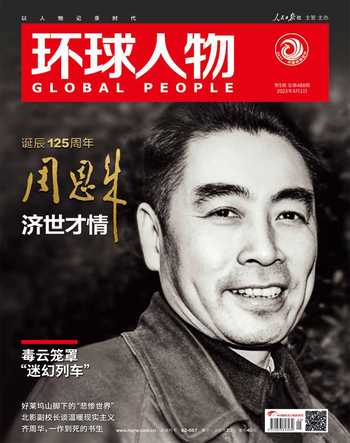聽李叔閑聊十年
高塬

李志明
李志明,人稱“李叔”。干過記者,搞過票務,當過CEO,37歲那年建了座“公園”——中文播客“日談公園”,此后就靠在里“跟人閑聊”混跡播客江湖,少有敵手。他曾夸下海口,“以前覺得一騎絕塵很酷,現在會覺得沒有同伴很孤獨”。“我的天吶,不是,我真的說過這話嗎?”當記者跟他證實這確是他兩年前親口所言,李志明哈哈大笑起來,熟悉的腔調和播客里的“李叔”如出一轍。
“日談公園”已做到500多期,每期節目累計收聽量穩定在200多萬。在播客這一小眾領域,200多萬是什么水平?火車上打電話,一張口經常會被人聽出來,“李叔,你的節目我每期都聽。”吃完飯去結賬,竟也能碰到粉絲,“李叔,我是您粉絲,飯錢結過了!”遼金歷史、UFO研究、愛情奇妙物語、不正宗料理……“日談公園”邀請各行各業嘉賓,和主播一起創作豐富多彩的泛科普內容,開放包容、老少咸宜。
從2013年第一次錄播客,到一躍成為頭部,入行10年,李志明依然樂此不疲。
成為“李叔”之前,李志明曾被人數落“夸夸其談、浪費時間閑聊天”,他表示同意,卻還是管不住嘴。
“2012年的時候,我們幾個非常好的朋友有個小組織,每周固定線下聚會,文學、電影、音樂什么都聊,只是很多精彩的內容聊過也就忘了。”李志明回憶,“想著是不是可以通過某種方式記錄下來,那時候身邊已有挺多朋友在做播客。哥兒幾個一商量,2013年6月份,我參與創辦的第一檔播客‘大內密談’就誕生了。”
作為數字廣播的一種形式,播客(Podcast)最早在2004年出現于英國。不同于有組織的調頻廣播,基于互聯網的播客更開放,任何人基于任何話題都可以做一檔自己的播客。因此,強烈的個人風格和即時交互是播客與生俱來的屬性。
“剛開始的時候別說有什么期待了,純粹跟讓我在班里聯歡晚會上唱首歌一樣,就覺得特別尷尬、局促、手足無措。”李志明說。但適應期很快就過去了,李志明憑著自己“閑聊”的本事,迅速從對播客感到匪夷所思到慢慢接受,再到享受其中。
彼時的“大內密談”正趕上中文播客行業的風口期,這股風潮,為喜馬拉雅、蜻蜓、荔枝等音頻平臺以及網易云、QQ音樂等傳統播放軟件吹開了新口子,“那幾年其實是一個原始紅利期,只要上線一個節目,從視覺到內容做得還不錯,能穩定更新,基本上就能夠覆蓋為數不多的中文播客受眾。”李志明說。
3年時間里,他不知疲倦地游走其中,白天是一名勤勤懇懇的“打工人”,開會干活;下班后化身播客主播,坐在話筒前,唾沫橫飛。原本“年輕、能造”的他,為播客犧牲掉了絕大部分業余時間。

李叔(右)和搭檔馮廣健在粉絲見面會上與聽眾合影。
也是在這一時期,他結交了一位重要的朋友。“我現在的搭檔馮廣健(人稱“小伙子”)就是在錄‘大內’的時候熟悉起來的,以前我只是他的粉絲。”李志明說,2008年,他在一場Livehouse(現場音樂演出) 中領略過“青年小伙子”樂隊主唱馮廣健的表現力,只是當時沒有機會深入接觸。直到后來,兩人在同一個播客節目里重逢,彼此相交,甚至成了創業伙伴。
2016年,李志明和馮廣健決定把播客認真地當成創業項目搞起來。“當時思路很清晰,之前是把聊天做成節目,現在要反過來,把節目做得像聊天。”
李志明清晰地記得,項目上線前的一個夏夜,在深圳的出租屋里,他給馮廣健撥了一通電話。凌晨3點多,電話那頭,馮廣健問:
“如果有一天你自由自在,不用為生活、地域、財務所困,你想做什么?”
“做個電臺。”
“我也是。”
所謂默契,不過如此。至于新播客的名字“日談公園”,是他們晚上經過北京日壇公園時,靈感乍現得來的。
“我想說的,你想聽的。大家好,這里是‘日談公園’。我是李叔,我是小伙子。”2016年9月26日,李叔和小伙子以全新的面貌出現,帶著他們合作創辦的“日談公園”與聽眾見面。
“日談公園”繼承了李志明的閑聊基因,邀請各行業嘉賓講解關于文化與藝術的那些事兒。
“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團長金承志來到“日談”,講合唱與音樂會的自然本源——你不需要懂得五線譜和各種樂理知識,你只要想唱,跟著音樂唱就可以了。“對,像我這種搖滾樂壇前輩都可以跟你們唱古典音樂。”小伙子總愛在這種時候抖機靈。單立人喜劇創始人石老板第一次上“日談”時,還認真地強調自己說的叫單口喜劇,不是脫口秀,轉頭李志明拆起臺來:“那你給我們講講拿了脫口秀比賽冠軍的事兒。”石老板干脆從起源到發展,從細節到特點,詳詳細細給李志明“科普”了單口喜劇與單口相聲、脫口秀的區別,說到底“我們更好笑!”幽默詼諧、插科打諢,在“日談”,不管什么話題都能在輕松逗趣的閑聊間展開。
至于為什么“日談”的文化類選題偏多,或許要歸因于主播李志明身上活躍的文藝細胞。

“日談公園”的泛科普內容矩陣。
“雖然說大學的專業是自動化,但是我一直喜歡文學、熱愛搖滾。” 2000年,李志明上大三,身為校文學社社長,集撰稿、編輯、排版、發行數職于一身,攢了學校第一份純文學報刊《青鳥》。等到畢業找工作,他也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準備了兩份面試簡歷,一份本專業方向,一份文字工作。
“沒想到真有報社通知我面試。”李志明對那段求職經歷,記憶猶新,“當時還有筆試,我就傻了,新聞專業的東西我都不會啊。”誰知,筆試題目是讓考生從考場出發到王府井大街采寫一條新聞。李志明借了旁人的錢,打車到了王府井。年輕人很機靈,先在報攤買了份報紙,臨時抱佛腳地學了學新聞寫作格式。之后,他開始在街上溜達。撓頭之際,眼前出現了一輛獻血車,他靈機一動便開始采訪起來,結束后自己也獻了回血。“那天我包里還帶了一個爸媽用了很多年的傻瓜膠卷相機,就拍了張照,洗出來帶回了考場。”
憑著這次的新聞“處子秀”,李志明成功入職報社,成為一名文化記者。這份工作幫他拓展了人脈,為他之后做播客打下了基礎,積累了經驗。
2018年左右,“日談”的內容矩陣開始逐漸成形,泛科普知識包羅古今中外,廣泛而駁雜。深諳日本罪案史料與社會文化的主播“淼叔”總講些重口味犯罪案件,卻被聽眾催更最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楊原主播的節目《我在故宮聊八卦》滿足了博物館愛好者;還有寶藏嘉賓梁子、關雅荻、瑛姐等,帶聽眾走進非洲大草原、感受連綿的海浪、體驗異域生活……
“這里是我了解世界的一個窗口。”“別的講歷史講知識的播客也聽過,感覺像上課,沒有‘日談’這樣吸引人。”“進之耳鼓,直抵心田!”“日談”每期節目都能收獲許多聽眾留言。
2020年,隨著小宇宙等一批獨立播客平臺的上線,中文播客迎來行業“元年”。《2021中文播客創作者報告》顯示,2020年國內播客數量同比增長40.5%,約為前4年總和的4倍。
“對于2020年播客行業的小爆發,我倒是比較冷靜。其實這些年也時不時聽到所謂的‘播客的春天要來了’‘播客復興’這樣的說法,我感覺在他們嘴里,我們都‘春天’好幾回了。”李志明接著說,“今年是我在這個行業的第十年,大概知道冰山下面是什么樣子,等它最終浮現出來,會不會突然‘咔嚓’一下天崩地裂,然后所有人都在聽播客、討論播客,我覺得可能沒那么容易。目前來看,把內容做好還是最根本的事情。”
“聲音最大的優勢,就是能夠給人更多的想象空間。短視頻把時間切割之后再切割,音頻則是把整個節奏盡量拉長,給你一個持續的、穩定的陪伴感。”李志明說,“看視頻和聽播客的人很可能就是差別很大的兩種人,所以我們不需要糾結于去和視頻載體競爭。”
“日談”開播前,李志明曾寫下一份“發刊詞”:錄電臺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緣際會,不同性情、不同經歷的聽眾,在世界上的各個角落和我們相遇,成為彼此最重要的陪伴。他把“日談”比作霧角——安裝在燈塔上,霧天里向過往船只發出音訊的號角,這支霧角已經響了7年,如今依然聲音嘹亮悠長……
1979年出生于北京,2013年進入播客行業,后創辦播客“日談公園”,與聽眾暢聊歷史文化等泛科普內容,成為最有影響力的中文播客創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