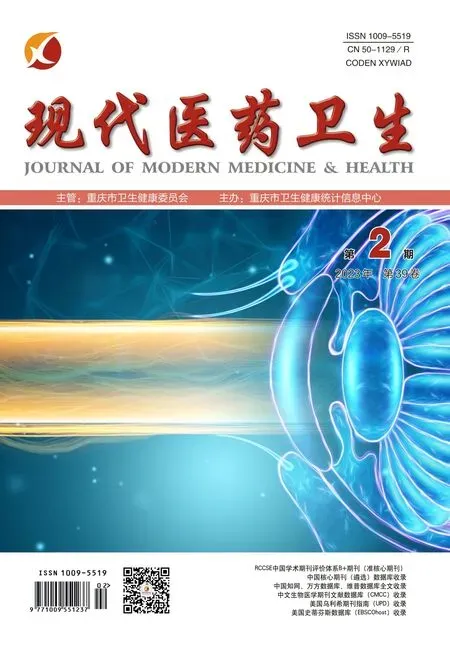施萬細胞在周圍神經疾病中的免疫調節研究進展
高 曌,駱天炯,宣 思 綜述,過偉峰△ 審校
(1.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南京中醫院老年病科,江蘇 南京 210022;2.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 南京 210009)
施萬細胞(SCs)是周圍神經系統(PNS)最豐富的神經膠質細胞,分為髓鞘化和非髓鞘化兩種。髓鞘化SCs包繞直徑大于1 μm的大口徑軸突,在相鄰SCs之間留下無髓鞘間隙,形成郎飛氏結節,有利于神經沖動跳躍式傳導,加快傳播速度。非髓鞘化SCs不包裹軸突,但直徑小于1 μm的小口徑軸突嵌在非髓鞘化SCs的細胞膜中,形成凹槽樣結構。幾個小口徑軸突有時嵌入同一個非髓鞘化SCs的細胞膜,稱為Remak纖維束。SCs對神經纖維的生物學特性具有動態調節作用,構成血液-神經界面,為軸突提供代謝支持,調節神經損傷反應。SCs還具有高度的分化可塑性,在損傷和疾病時可再分化和去分化,并積極參與再生和炎癥過程。因此,在生理和病理條件下SCs的作用對軸突功能至關重要。SCs在許多病理過程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包括損傷誘導的神經修復、神經退行性疾病、炎癥、神經性疼痛和癌癥,部分原因是其能調節免疫反應。現將近幾年開展的關于SCs在PNS損傷和病變時的免疫反應的研究綜述如下。
1 SCs與周圍神經損傷(PNI)后炎癥的研究
神經損傷觸發髓鞘化、非髓鞘化SCs轉化為一種專門促進修復的細胞表型,為PNI后軸突再生提供環境。損傷誘導的SCs重編程包括髓鞘化基因的下調與一系列修復支持特征的激活,包括營養因子的上調,作為固有免疫反應一部分的細胞因子水平升高,通過SCs髓鞘自噬激活導致的髓鞘清除及巨噬細胞募集,并形成再生軌道以引導軸突到靶點。近幾年關于PNI后SCs與巨噬細胞及炎癥因子的相關研究受到較多的關注。
一般關于損傷后第1周SCs基因表達的整體變化的知識主要基于整個坐骨神經在擠壓或橫斷損傷前后的數據,因此,并不能區分神經中SCs特異性的轉錄組變化和其他細胞類型的基因表達。LUTZ等[1]從未損傷和神經擠壓損傷后第3、5、7天大鼠坐骨神經中急性純化SCs,并進行高分辨率RNA測序(RNA-seq)轉錄分析。并且對全坐骨神經在同一時間點也進行了RNA-seq分析,結果顯示,損傷后SCs的分泌型磷蛋白1等基因明顯上調,而膠質細胞源性神經營養因受體α1、神經軸突生長促進因子2、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sparcl樣蛋白1 4個基因為SCs單獨上調,在髓內并沒有上調。提示PNI后神經炎癥的髓系和膠質成分的分化,并突出了SCs損傷反應的分子機制。
DUN等[2]發現,發生PNI后盡管SCs遷移在近端神經殘端軸突延伸之后才開始,但會在損傷后第5天取代再生軸突,并為再生軸突穿越神經橋提供通路。SCs、巨噬細胞、中性粒細胞、神經周圍細胞、神經成纖維細胞、內皮細胞是形成神經橋的主要細胞類型,在再生過程中調節彼此在神經橋中的募集、遷移和組織。要在神經橋中表達 Slit3基因的巨噬細胞和表達 Robo1基因的遷移SCs之間發出Slit3-Robo1信號,以保持SCs在神經橋內,再生軸突會跟隨SCs索并穿過神經橋。在Sox2、Slit3、Robo1敲除小鼠中坐骨神經橫斷損傷后SCs異常遷移,軸突再生遵循異位遷移SCs離開神經橋的路徑。
組蛋白去乙酰化酶在SCs損傷后的表觀遺傳調控有助于SCs經歷去分化和再分化過程,但其介導的延長炎性反應時間或持續時間的改變可影響隨后的修復和再生。YADAV等[3]在體內坐骨神經橫斷損傷模型中發現,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劑——苯丁酸鈉(PBA)可顯著抑制橫斷損傷部位的促炎細胞因子分泌,抑制延長的炎癥狀態,提高再生神經組織中蛋白基因產物9.5和髓鞘堿性蛋白的表達水平,為軸突再生和再髓鞘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微環境,增加了腓腸肌相對重量百分比,并保持了肌束的完整性。
LU等[4]發現,巨噬細胞來源的血管內皮生長因子-A(Vegf-A)在神經損傷后神經肌肉連接(NMJ)的神經再支配中不可或缺,并且與非髓鞘化終末SCs(tSCs)有關。tSCs在神經損傷后延伸NMJ之間的細胞質突起,誘導軸突生長和NMJ神經再生。神經損傷修復后末端靶肌中巨噬細胞數量和Vegf-A表達均增加。在體內實驗中使用Vegf受體2抑制劑——cabozantinib給野生型小鼠灌胃后與生理鹽水對照組比較,tSCs細胞質延長減少,NMJ神經再生減少。巨噬細胞中Vegf-A條件敲除小鼠表現出對NMJ神經再生更持久的不利影響和更差的功能肌肉恢復。
G蛋白偶聯受體126抗體(Gpr126)是一種黏附G蛋白偶聯受體,不僅對SCs髓鞘形成至關重要,對NMJ的tSCs也具有重要功能。JABLONKA-SHARIFF等[5]發現,神經切斷和修復后tSCs缺失Gpr126小鼠表現出延遲的NMJ神經再生,改變tSCs形態,降低中樞神經特異蛋白S100β表達,減少tSCs細胞質過程延伸,導致老年小鼠后肢出現NMJ維持缺陷;與對照組比較,NMJ神經損傷后促進神經再生的免疫反應也因巨噬細胞浸潤減少、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和細胞因子異常表達而改變。
XU等[6]在采用改良坐骨神經鉗損傷方法的大鼠模型中發現,經軟脂酸(PA)刺激后,SCs中的TNF-α、白細胞介素-6(IL-6)的表達和分泌被PA處理增強。此外,PA激活了toll樣受體4(TLR4)信號通路相關蛋白,并刺激TLR4和髓樣分化蛋白2(MD2)之間的強關聯,阻斷TLR4或MD2可逆轉PA誘導的炎性反應和TLR4下游信號通路。因此,推測飽和脂肪酸作為內源性配體激活TLR4/MD2,從而引發坐骨神經損傷時的SCs炎癥。
CHEN等[7]發現,白血病抑制因子(LIF)蛋白在大鼠坐骨神經損傷后的SCs中大量表達,抑制或升高LIF分別增加或降低SCs增殖率和遷移能力。LIF是一種刺激神經元發育和存活的多效細胞因子。在體內應用小干擾RNA對抗PNI后的LIF,可促進SCs遷移和增殖,軸突延伸和髓鞘形成。通過電生理學和行為學研究表明,抑制LIF有利于損傷周圍神經的功能恢復。
中樞神經損傷后的再生非常有限,然而PNS可以再生。周圍神經膠質的功能,特別是SCs起到神經營養和物理支持,有效吞噬和清除碎片的能力,以及調節炎癥環境的作用,被認為是PNS再生能力的關鍵。近年來,關于SCs在PNI的作用機制方面的認知不斷深入。早先的觀點認為,損傷后SCs經歷去分化,從有髓鞘/無髓鞘表型轉化為不成熟表型;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對損傷做出反應的SCs是通過重編程下調了髓鞘形成和軸突支持所需的基因[2,6]。上述研究關注PNI過程中SCs與髓質不同的分子表達及修復型SCs通過多種炎癥因子在不同時間點和不同分子通路對神經損傷后修復的調控,探討了SCs在PNI和隨后的神經修復全過程中的炎癥機制,不僅為通過SCs干預PNI后的神經修復提供了靶點,也成為目前的研究熱點,為PNI后SCs移植提供了精準調控的依據。
2 SCs與周圍神經病變炎癥的研究
2.1神經性疼痛 神經性疼痛是指由神經病變或疾病引起的疼痛狀態,包括自發性疼痛、痛覺過敏和痛覺超敏,與功能障礙、殘疾、抑郁、睡眠紊亂和生活質量下降有關。隨著對神經性疼痛機制研究的深入發現,其不僅與神經元有關,還與膠質細胞及在外周神經系統中與SCs密切相關。目前,SCs通過炎癥因子介入神經性疼痛的炎癥級聯反應及通道研究成為關注熱點。XIE等[8]研究表明,周圍神經的非髓鞘SCs的核因子-κB-環氧合酶-2(NF-κB-COX2)信號通路對維持體內神經性疼痛是必要的,其采用條件敲除小鼠,并使用floxed COX2基因特異性滅活COX2基因;使用四環素轉運激活劑系統抑制NF-κB的活化。有研究發現,在COX2 cKO小鼠及膠質NF-κB信號通路降低的小鼠中神經損傷后的神經性疼痛行為顯著降低。采用土霉素限制轉基因表達只對中樞神經膠質有影響,而不影響外周神經膠質信號。發現NF-κB-COX2單在中樞神經膠質中信號失活不能表現出鎮痛效果。表明外周神經系統的周圍神經非髓鞘SCs是COX2激活的細胞來源,對維持神經損傷后的機械過敏是必要的。MA等[9]發現,IL-1β激活神經損傷后的SCs參與神經性疼痛發展的關鍵基因,其采用RNA-seq方法識別IL-1β對大鼠SCs(RSC)96基因標記的影響發現,5個關鍵的顯著差異表達基因上調與免疫和炎癥相關過程、神經營養因子的產生和SCs增殖相關,并且采用大鼠慢性縮窄損傷坐骨神經免疫熒光技術證實了關鍵基因在SCs中的表達。此外,還發現IL-1β處理導致p38/細胞外信號調節激酶(ERK)磷酸化增加,p38/ERK激活物增強了IL-1β對一些關鍵基因表達的影響,而p38/ERK抑制劑可逆轉這些影響。HU等[10]通過實驗研究發現,纖毛神經營養因子(CNTF)在SCs中高表達,通過激活信號傳感器、轉錄激活因子3和IL-6介導神經炎性反應,揭示了CNTF-轉錄激活因子3-IL-6軸介導從外周至脊髓的炎癥級聯反應的發生和進展。CNTF缺乏可減輕背根神經節的神經炎癥和脊髓損傷后疼痛,用于感覺神經的重組CNTF再現了背根神經節和脊髓的神經炎癥,并伴隨疼痛的發展。SCs來源的趨化因子(C-X-C基元)配體1(CXCL1)通過調節小鼠巨噬細胞浸潤參與了人類免疫缺陷病毒1型(HIV-1)中糖蛋白120(gp120)誘導的神經病理性疼痛。gp120由HIV-1外殼蛋白的神經炎性反應產生,是與HIV相關遠端感覺神經病變的原因。NTOGWA等[11]在實驗中證明了來自HIV-1株的T淋巴細胞系X4 gp120誘導小鼠的機械過敏和自發的疼痛樣行為。經基因表達陣列確定,CXCL1、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的趨化劑在gp120處理的培養SCs中增加。重組CXCL1誘導了周圍神經的疼痛樣行為,并伴有巨噬細胞浸潤。反復注射CXCL1受體拮抗劑或CXCL1中和抗體可防止gp120治療小鼠的疼痛樣行為和巨噬細胞浸潤。
2.2PNS脫髓鞘疾病 PNS脫髓鞘疾病包括Guillain Barré綜合征,也稱為急性炎癥性脫髓鞘性多神經病、慢性炎性脫髓鞘多神經病變和多發性硬化。巨噬細胞吞噬髓鞘為其基本特征之一,機制尚不清楚。KOIKE等[12]研究表明,在個別病例中巨噬細胞似乎會選擇有髓纖維的特定部位,如SCs包裹形成的郎飛氏結節以啟動脫髓鞘,而SCs微絨毛表達的膜突蛋白抗體與巨細胞病毒感染后的急性炎癥性脫髓鞘性多神經病的聯系已被認為是相關的。
2.3周圍神經局部炎癥 周圍神經的局部炎癥是多種疾病的病理表現之一,SCs以炎癥因子為介質參與了周圍神經炎癥,并且對疾病的發生、發展有影響。MUSUMECI等[13]發現,將大鼠SCs暴露于脂多糖,模擬局部炎癥環境,促炎性細胞因子水平呈時間依賴性增加,包括IL-1β、IL-6、IL-18、IL-17A、TNF-α、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等。但保護性血管活性腸肽(VIP)和垂體腺苷酸環化酶激活多肽(PACAP)的表達水平升高,VIP、PACAP共同受體血管活性腸肽受體1(VPAC-1)和VPAC-2水平降低。下調的微小RNA(miRNA)包括miR-181b、miR-145、miR-27a、miR-340和miR-132,上調的miRNA包括miR-21、miR-206、miR-146a、miR-34a、miR-155、miR-204和miR-29a,提示免疫刺激下SCs培養物中異常調節的miRNA網絡與保護性VIP/PACAP神經肽系統的潛在交叉。PERMPOONPUTTANA等[14]發現,降鈣素基因相關肽可能在啟動外周神經系統炎癥過程中發揮著直接作用。降鈣素基因相關肽是一種內源性神經肽,通過環磷酸腺苷-蛋白激酶A-ERK信號級聯導致IL-1β、IL-6顯著生成,介導SCs中的炎性反應。但與TNF-α水平無關。PBA通過抑制組蛋白去乙酰化酶介導延長的炎癥狀態,以利于神經橫斷損傷后軸突再生和再髓鞘形成。在體外SCs炎癥模型中,PBA降低了脂多糖誘導的促炎性細胞因子——TNF-α的表達和分泌,還影響了NF-κB-p65磷酸化和易位的瞬時變化[3]。
2.4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癥(ALS) TRIAS等[15]發現,在ALS中SCs通過集落刺激因子-1(CSF-1)、IL-34、干細胞因子(SCF)的表達調控周圍神經炎癥。ALS的病理特征包括周圍神經中運動軸突缺失引起沃勒變性和失神經SCs并伴免疫細胞浸潤。該研究分析了ALS患者和癱瘓SOD1-G93A轉基因大鼠坐骨神經中的SCs表型,結果顯示,不同亞群的反應性SCs表達CSF-1和IL-34,并與大量神經內膜表達CSF-1受體的單核細胞/巨噬細胞密切相互作用,具有吞噬表型的SCs和神經內膜巨噬細胞表達SCF。SCF是一種通過c-Kit原癌基因吸引和激活肥大細胞的營養因子。在SOD1-G93A轉基因大鼠坐骨神經中Ki67+SCs的一個亞群表達了c-Kit;在ALS供體坐骨神經中c-Kit+肥大細胞也很豐富,但在對照組中沒有。特異性的c-Kit抑制劑——馬賽替尼(Masitinib)抑制CSF-1R和c-Kit,可顯著降低SOD1-G93A大鼠坐骨神經和腹根的SCs反應性和免疫細胞浸潤。
3 SCs與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DPN)免疫的研究
DPN是糖尿病最常見的慢性并發癥之一,也是周圍神經功能障礙的常見原因。高血糖狀態下SCs免疫激活、功能受損可能是神經纖維損傷的基礎,是DPN發病的第一步[16]。因此,高血糖狀態下SCs的病理變化受到關注,藥物對此的干預也是目前改善DPN的熱門靶點。
在糖尿病患者和嚙齒類動物模型的神經內膜和血漿中已觀察到神經營養因子受體p75(p75NTR)水平增加,表明該受體可能參與了糖尿病神經病變的發病機制。GON?ALVES等[17]利用SCs選擇性神經生長因子受體缺失(SC-p75NTR-KO)小鼠模型解決這一假設,高脂飲食誘導肥胖小鼠坐骨神經的電鏡觀察顯示,SCs的p75NTR缺失加重了軸突萎縮和c-纖維的缺失,RNA-seq證實了p75NTR與溶酶體、吞噬體和免疫通路相關。
XU等[18]研究表明,抗炎細胞因子——IL-10在體外可抑制糖基化終產物(AGEs)誘導的SCs凋亡,其從大鼠坐骨神經中分離培養SCs,AGEs作用48 h后SCs凋亡明顯增加,而IL-10預處理可抑制AGEs誘導的細胞凋亡,并且在AGEs作用下細胞內磷酸化NF-κB水平高,NF-κB核定位能力強,而IL-10作用下細胞內磷酸化NF-κB水平低,細胞質定位能力弱。表明IL-10可抑制被AGEs激活的NF-κB。
YUAN等[19]發現,石蒜堿可改善糖尿病小鼠周圍神經功能和自噬相關蛋白。體外高糖(HG)培養RSC96在石蒜堿處理下顯示自噬小體標志物——微管相關蛋白輕鏈3Ⅱ增強。此外,在HG刺激的RSC96中人自噬基因beclin-1和自噬相關蛋白3抗體降低,石蒜堿處理可逆轉這一現象,并且在石蒜堿處理的HG培養的RSC96中證實了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通路的激活。
涂世偉等[20]探討了葛根素(Pue)對HG條件下RSC系RSC96炎癥損傷的作用,結果顯示,Pue可減輕HG誘導的RSC96炎癥,其機制可能與NF-κB信號通路被抑制有關,其將RSC96隨機分為對照組、HG組、Pue預處理(HG+Pue)組和NF-κB抑制劑——吡咯烷二硫代氨基甲酸酯(PDTC)預處理(HG+PDTC)組。與對照組比較,HG組RSC96活力明顯降低,Pue預處理組細胞活力明顯提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對照組比較,HG組NF-κB-p65、p-NF-κB-p65、天冬氨酸半胱氨酸酶-3(Caspase-3)、活化的Caspase-3、IL-1β、TNF-α蛋白水平均明顯升高,經Pue或PDTC預處理后,上述蛋白水平均明顯下降,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HG組IL-1β、IL-6水平均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HG組比較,HG+Pue組、HG+PDTC組IL-1β、IL-6水平均明顯降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對照組比較,HG組NF-κB共定位系數較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HG組比較,HG+Pue組、HG+PDTC組共定位系數均明顯降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番木鱉苷是常用中藥山茱萸的主要有效成分,已被證明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神經保護作用。CHENG等[21]評估了番木鱉苷對HG(25 mM)誘導的RSC96損傷的神經保護作用,RSC96經番木鱉苷(0.1、1、10、25、50 μM)預處理后暴露于HG環境,HG處理后的RSC96持續喪失細胞活力,活性氧生成,NF-κB核轉位,P2×7嘌呤能受體和硫氧還蛋白相互作用蛋白表達,NLRP3炎癥小體(NLRP3、ASC、Caspase-1)激活,IL-1β、IL-18成熟,而番木鱉苷預處理可降低上述作用。提示番木鱉苷抑制NLRP3炎癥小體激活以防止RSC96焦亡。
丹酚酸A(SalA)是常用中藥丹參的主要水溶性成分。XU等[22]發現,SalA可減輕HG誘導的細胞活性和髓鞘形成,其機制為SalA除表現為較強的抗氧化作用外,還通過下調炎癥因子mRNA表達,顯著減輕神經炎性反應,HG損傷上調了炎性細胞因子——IL-6、細胞間黏附分子1、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COX2、TNF-α mRNA表達,而SalA處理顯著下調上述炎性細胞因子的表達。
4 SCs與癌癥相關性周圍神經病變的免疫研究
癌癥相關性周圍神經病變包括癌癥本身引起的周圍神經病變和化療引起的周圍神經病變。化療誘導的周圍神經病變的病理生理機制主要包括線粒體功能障礙、鈣穩態變化、氧化應激、凋亡途徑活化、髓鞘和非髓鞘纖維丟失、免疫系統活化及離子通道表達活性增加等,不同種類化療藥物導致神經病變的機制不同,SCs參與的機制也不盡相同。
DE LOGU等[23]發現,SCs通過瞬時受體電位錨蛋白-1(TRPA1)激活,釋放M-CSF和氧化應激維持癌痛,促進神經內巨噬細胞的擴張和促痛感作用。TRPA1靶向缺失揭示了SCs的TRPA1在坐骨神經巨噬細胞擴張和疼痛樣行為中的關鍵作用。
CIPN是紫杉醇類藥物嚴重的劑量限制性不良反應。KOYANAGI等[24]發現,SCs衍生的半凝集素-3在紫杉烷誘導下通過促進巨噬細胞浸潤和機械過敏,誘導CIPN的發生,血漿半凝素-3水平升高是紫杉烷治療乳腺癌CIPN患者和紫杉烷相關CIPN小鼠模型的共同病理變化,在小鼠多次腹腔注射紫杉醇后半凝集素-3水平在坐骨神經內的SCs中升高,但在其他外周器官或表達半凝集素-3的細胞中未升高,并且紫杉醇對RSC原代培養物的處理導致半凝集素-3上調和分泌,體外遷移實驗結果也顯示,重組半凝集素-3誘導小鼠單核巨噬細胞白血病細胞RAW 264.7的趨化反應。此外,對原始小鼠坐骨神經進行半乳糖凝集素-3神經周給藥,模擬紫杉醇誘導的巨噬細胞浸潤和機械過敏,結果顯示,半乳糖凝集素-3-/-小鼠缺乏或半乳糖凝集素-3抑制物可抑制紫杉醇誘導的巨噬細胞浸潤和機械過敏。
5 年齡對SCs在外周神經系統免疫功能中的影響
SCs在外周神經系統免疫中受到年齡的影響。SCHEIB等[25]采用年輕(2月齡)和年老(18月齡)Brown-Norway雄性大鼠進行坐骨神經移植,將1 cm年輕或年老大鼠神經移植入年輕或年老大鼠神經中,軸突被允許再生,直到神經移植物和遠端神經在1、3、7 d及2、6周被收獲,6周時老齡巨噬細胞延遲遷移至損傷神經,老齡RSC、巨噬細胞體外對髓鞘碎片的吞噬能力較弱。而分析損傷后1 d促炎和抗炎細胞因子表達水平發現,衰老神經中IL-6、IL-10、精氨酸酶1表達水平均下降。認為SCs、巨噬細胞對年老大鼠神經損傷的反應減弱,導致碎片清除效率低下和軸突再生受損。
6 以改善SCs炎癥為靶點治療的研究
SCs與損傷后周圍神經的再生密切相關,而其免疫調節是再生過程中的重要環節,目前,以改善SCs炎癥為靶點治療的研究多圍繞其對周圍神經再生的影響開展。EHMEDAH等[26]發現,B族維生素調節巨噬細胞- SCs相互作用的能力可能在治療PNI方面有前景,其以股神經運動支橫斷后端-端吻合重建作為實驗模型,分為假手術組、手術組和手術聯合B族維生素治療組,分離神經進行免疫熒光分析,結果顯示,PNI以時間依賴性方式調節巨噬細胞與SCs的相互作用,B族維生素復合物治療促進了m1到m2巨噬細胞的極化,并加速了從非髓鞘到髓鞘形成的SCs的轉變,表明SCs的成熟、B族維生素復合物對兩種細胞類型的影響均伴隨巨噬細胞-SCs相互作用的增加,所有這些均與損傷神經的再生有關。
淋巴細胞移植改善鼠坐骨神經再生。淋巴細胞移植后軸突、SCs、生長相關蛋白43在損傷后14~28 d內持續免疫標記。在神經擠壓后14、21 d時淋巴細胞移植小鼠巨噬細胞和免疫球蛋白G免疫標記也較高,在功能方面也觀察到淋巴細胞治療組感覺功能恢復更好[27]。
中性粒細胞肽1(NP-1)又稱為α防御素1,是α防御素家族成員,主要由中性粒細胞分泌。NP-1與PNI的修復密切相關。KOU等[28]采用不同濃度NP-1處理RSC96發現,NP-1影響神經再生相關多個因子的表達,其中NF-κB信號通路具有關鍵作用。提示NP-1可能通過NF-κB信號通路促進RSC96增殖和遷移,抑制細胞衰老和凋亡。
7 中藥對SCs免疫功能的調控
中藥對SCs免疫功能的調控常表現為對炎癥和SCs凋亡的抑制作用,不同的藥物作用靶點不同。LI等[29]發現,牛膝多肽k能有效降低血清剝奪引起的SCs凋亡,其抗凋亡作用與神經生長因子相當。牛膝多肽k在血管系統和免疫系統領域有更多的參與和優勢,特別是在血管生成調控方面,比神經生長因子更早開始,而且這些調控因子存在的時間也更長。
(-)-兒茶素沒食子酸鹽(EGCG)是綠茶中主要的活性成分。QIAN等[30]發現,載EGCG聚己內酯多孔支架培養的RSC表現出更高的增殖、抗氧化和抗炎狀態。認為EGCG具有清除自由基和減輕RSC炎癥的作用。
人參皂苷(SF1)可強烈抑制周圍神經退行性過程,并與其對SCs的作用有關。反式去分化是SCs在周圍神經退行性過程中所特有的。當SCs進行反式去分化時變得與未成熟SCs相似,從而迅速增殖。在SF1處理下神經纖維中溶酶體關聯膜蛋白1、p75NTR表達均下降;在SF1處理下SCs的Ki67表達低于未處理細胞,提示SF1在外周神經退行性過程中能顯著抑制SCs增殖[31]。
綜上所述,一直以來,SCs由于在其表面表達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類分子,被認為可能作為抗原呈遞細胞發揮作用。上述研究可見,SCs與巨噬細胞、T淋巴細胞相互作用,分泌多種細胞因子、促炎性細胞因子、抗炎性細胞因子、趨化因子等,發揮免疫調節作用,在PNS的病理機制和修復再生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SCs的免疫功能及去分化和再分化過程非常復雜,并且隨時間推移和病程發展而發生變化,因此,仍需進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