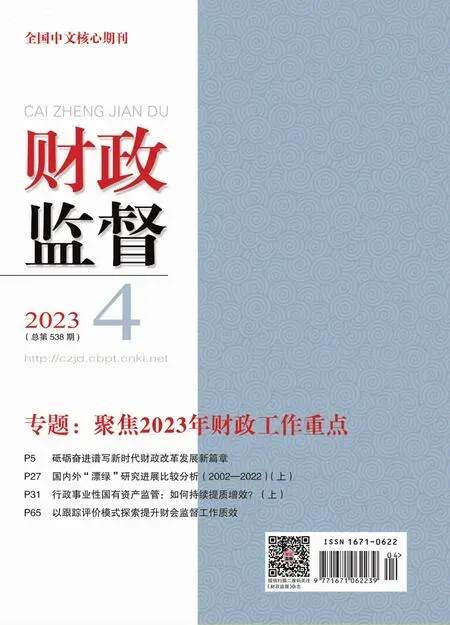國內外“漂綠”研究進展比較分析(2002—2022)(上)
——基于Citespace知識圖譜的可視化分析
●白彥鋒 王麗娟
一、問題及背景
黨的十八大以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綠色越來越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底色。信息披露作為綠色轉型的關鍵,有利于減少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市場失靈,展現了“雙碳”目標的政策導向和對綠色發展的價值追求。2022年2月8日起,生態環境部印發的《企業環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辦法》開始施行,明確依法披露的主體、內容、形式、時限和監督管理等基本內容,強化了企業生態環境保護的主體責任,是推進我國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近年來,隨著ESG(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ment, 譯為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投資理念在全球范圍內快速發展,得益于政策積極引導,我國綠色金融未來的發展前景十分開闊;但同時,資金規模達到一定體量時,很可能出現“漂綠”風險。在國家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實現 “雙碳”目標的背景下,綠色發展應該是企業內涵式發展的重要內容,而不能僅僅是“漂綠”包裝,一方面收獲消費者的“綠色溢價”,另一方面可能使企業在融資信貸、稅收優惠等方面獲得與實際不符的利益,從而扭曲政策效果。盡管我國“漂綠”相關主題的研究不斷增加,但關于“漂綠”的定義和動因尚未出現統一明確的結論,且綠色金融快速發展伴隨著“漂綠”行為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大眾對“漂綠”的認知存在一定誤解,仍停留在“虛假營銷”“綠色廣告”這一層面。
二、概念界定
“漂綠”(Greenwash)由“洗白、粉飾”(Whitewash)演變而來,指企業虛假綠色環保宣傳、粉飾牟利之實的行為,強調了其環保欺騙性(李大元等,2015)。這一概念起源于1986年美國環保主義者杰伊·韋斯特維爾德(Jay Westerveld)對美國酒店“回收毛巾”環保行為的反思,用于描述企業出于營利目的而做出的虛假環保宣傳行為。形式上,企業在公眾面前承諾承擔社會責任,但實質上,沒有采取相應行動甚至違背社會責任,“漂綠”是一種偽社會責任行為 (肖紅軍等,2013)。由于存在商業競爭,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有必要樹立綠色品牌形象,將生態友好作為一項重要資產(Bekk et al.,2016)。 蘇士梅(2022)認為“漂綠”廣告是為提升產品及企業的社會知名度和美譽,塑造其負責任的企業形象或產品形象的營銷策略;且基于語義操控和綠色崇拜,將“綠色”符號化,傳播過程中使投資者和消費者出現認知遮蔽。
深化綠色金融發展是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路徑,“漂綠”是制約其綠色發展的主要障礙。“漂綠”行為在綠色金融領域主要表現為:在投資端,投資人迎合資本市場對ESG投資的偏好,卻未能開展有效的ESG專項審查,而納入“非綠”標的;在發行端,綠色債券募集資金并未按照承諾的框架投放,未披露投放項目的環保效益,或投放項目未達綠色發展的承諾目標,造成綠色金融項目發展與綠色基礎設施建設間的不平衡。“漂綠”行為一旦曝光,會削弱投資者信任,對金融市場產生負面效應。于是本文梳理國內外“漂綠”相關研究文獻,繪制知識圖譜并進一步對比分析,一定程度上擴展了關于“漂綠”的研究述評。
三、研究工具與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國內和國外兩個部分,國內文獻取自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設置檢索主題為“漂綠”或“洗綠”或“綠色營銷”,國外文獻取自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數據庫,設置檢索主題為“Greenwash”或“Greenwashing”,精確匹配檢索發表時間為2002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后對文獻進行篩選、校對處理,剔除了書評、報紙、會議、新聞短訊等研究性不足的文獻,最終獲得153篇中文有效文獻和396篇英文有效文獻。本文使用美國德雷塞爾大學陳超美教授開發的Citespace v.6.1 R2版本軟件,繪制可視化知識圖譜,基于共詞分析、突現分析和聚類分析,更為直觀地從研究情況分布、科研合作網絡及研究關鍵詞等方面對國內外該研究領域的熱點主題進行具體解讀及趨勢預測。
四、研究現狀
(一)發文情況
如圖1所示,國內外近20年“漂綠”主題的相關研究,整體來看熱度持續增長。

圖1 2002—2022年國內外期刊“漂綠”研究年度發文量
國內相關研究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階段:2002—2008年為初步探索階段,期間相關研究成果極少,發文量≤1;2009—2018年為緩慢摸索階段,發文量≤10,基本達到穩中有升;2019—2022年為較快發展階段,發文量>10。而國外相關研究的總體發文量大多略高于國內,其期刊發文量爆發點略早于我國,自2008年起,年度發文量顯著上升,截至當前發文量已增長近13倍。國內出現“波動性緩慢增長”的原因是,我國“漂綠”相關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2008年,美國環境營銷公司Terra Choice發布綠色產品《漂綠六宗罪》調查報告,環保造假主要形式包括流于表面(Hidden Trade-off)、 毫無憑據 (No Prof)、 用詞含糊(Vagueness)、混淆視聽(Irrelevance)、避重就輕(Lesser of two evils)和欺騙公眾(Fibbing);后2009年增加崇拜認證(False labels),修訂為《漂綠七宗罪》,社會反響強烈。2009年,《南方周末》雜志頒布“中國漂綠榜”,才正式將“漂綠”的概念引入中國大眾視野。
國內外近20年的“漂綠”研究,總體均呈現上升態勢。階段分布關鍵節點的理論研究成果數量既與理論研究發展的自身規律相符,又與輿論重心、大眾需求和黨的重大政策方針息息相關。雖然已有不少學者對此進行相關研究,但國內外發文總量較少,尚未形成“井噴”態勢,說明“漂綠”相關主題的研究仍屬于新興領域,現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未來需要加強和深化對“漂綠”相關問題的研究。
(二)期刊收錄
國內收錄期刊153篇文獻,其中核心期刊收錄論文90篇,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收錄論文63篇,發文質量較高。如表1所示,發文量≥3的期刊均為省級以上期刊。其中,《財會月刊》《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國際新聞界》《財會通訊》《管理現代化》《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和《生態經濟》均為核心期刊,2021年平均復合影響因子約為3.050,對我國未來“漂綠”相關主題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有較大幫助。國外收錄期刊396篇文獻,其中科學引文索引(SCIE)收錄論文346篇,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HCI)收錄論文17篇,同樣發文質量較高。根據JCR期刊分區,各收錄期刊的影響因子至少在各領域排名前50%,收錄期刊所屬分類主要為環境科學與生態學(Sustainability,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社會科學(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和傳播學(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不難窺見“漂綠”相關研究的學科方向相對集中。然而,該領域總體發文量較少,表明當前國內外“漂綠”相關主題的研究成果刊發都比較分散,尚未形成較為明顯的核心學術集群。

表1 2002—2022年國內外“漂綠”研究成果期刊收錄情況
(三)發文作者
使用Citespace對國內外該研究領域的研究作者進行可視化分析,可以得到如圖2—3所示的研究作者共現圖譜。如圖2所示,國內研究作者共現圖譜的節點數量N=120,關系連線E=51,網絡密度Density=0.0071,對應年限中發文量最多的作者論文數量為7。根據普賴斯定律,關鍵作者的計算公式為其中,M指論文數量,Nmax指對應年限中發文量最多的作者的論文數量。因此,在國內“漂綠”研究中,當作者發文量>2時,該作者即可被視作高產作者,有楊波(7篇)、劉傳紅(6篇)、黃溶冰(5篇)、劉婧玲(5篇)、劉亦晴(5篇)、王積龍(3篇)、黃世忠(3篇)等。以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的楊波教授為例,楊波教授主要研究“漂綠”的行為演進及治理經驗,于2010年獨立發表《大型零售商漂綠行為的危害、成因與治理》,探究了企業“漂綠”產生的負面效應及根本原因,強調了政府、消費者、企業和NGO(非政府組織)多元主體的有效治理。2012年,楊波教授獨立發表《中國消費品市場中“漂綠”的治理分析:基于信任的視角》和《環境承諾為什么演變為漂綠:基于企業綠色過程模型的解釋》,分別通過不完全信息“漂綠”博弈模型和多維企業綠色過程模型,分析了“企業漂綠”的具體成因。2014年,楊波教授獨立發表了《漂綠的形態多樣性及演化研究》和《漂綠現象的第三部門治理研究》,認為“漂綠”治理的個體效應不佳,要注意企業、政府、公益性社會組織及綠色消費者的多元主體合作,尤其強調了第三部門的重要作用。同年,發表的《商品漂綠的中國本土特征與治理》和《西方發達國家治理漂綠的成效與挑戰》,則對“綠色消費”的概念作出了中國本土化的具體闡釋,并且積極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治理“漂綠”現象的有效措施和成功經驗。

圖2 2002—2022年國內“漂綠”研究作者共現圖譜
如圖3所示,國外研究作者共現圖譜的節點數量N=145,關系連線E=79,網絡密度Density=0.0076,對應年限中發文量最多的作者論文數量為5。根據普賴斯定律計算,在國外“漂綠”研究中,當作者發文量>2時,該作者即可被視作高產作者,分別是Lyon TP(5篇)、Du XQ(4篇)、Font X(4篇)、Seele P(4篇)、Zhang DY(4篇)、Chen YS(3篇)、Gatti L(3篇)、Karaman AS(3篇)等。 以密歇根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學院的講座教授Thomas.PLyon為例,Thomas教授聚焦環境信息披露和媒體關注效果的內外監督手段對企業“漂綠”行為頻率的影響,于2011年發表《戰略性環境披露:來自美國能源部的溫室氣體證據》和《漂綠:外部監督下的企業環境信息披露》,企業的戰略性自愿環境披露行為較少,通過經濟模型設計,研究發現企業預期環境績效與其環境信息披露間存在非單調關系,外部監督的壓力的確能夠有效阻止“漂綠”行為,但也促使企業更少地披露他們的環境表現。2013年,Thomas教授發表《社交媒體對企業漂綠的影響》,認為社交媒體的關注將減少企業“漂綠”的發生率。2015年,《漂綠的手段和目的》和 《企業可持續性披露中的夸張和謙虛》兩篇利用當時已有的社會科學研究對“漂綠”的機制進行理論化和建模,并衡量其對公司業績和社會福利的影響,同時擴展了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理論,再次確認外部審查對“漂綠”行為減少的有效作用。

圖3 2002—2022年國外“漂綠”研究作者共現圖譜
(四)研究機構
使用Citespace對國內該研究領域的所有研究機構進行可視化分析,可以得到如圖4所示的研究機構共現圖譜,其節點數量N=106,關系連線E=40,網絡密度Density=0.0072。主要的研究機構有鄭州航空管理學院經貿學院、大連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江西理工大學礦業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南大學商學院。表明我國“漂綠”相關主題的研究機構合作較為缺乏,各研究機構與高等院校之間、各高等院校之間的合作都有待加強。

圖4 2002—2022年國內“漂綠”研究機構共現圖譜
使用Citespace對國外該研究領域所有研究機構進行可視化分析,發現均為獨立節點,無關系連線。因此,國外“漂綠”研究機構部分得到如表2所示的統計結果。主要的研究機構有倫敦大學、密歇根大學、喬治亞大學、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斯威本科技大學、牛津大學、維也納大學、威斯康星大學等。其中,部分研究機構為高校系統(University of Michigan System和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指的是多所州立大學(分校)構成的大學系統,可能由于論文刊發的作者單位未細化至分校或二級學院,導致Citespace可視化分析不明顯。總之,國內外研究機構關于“漂綠”的研究大多仍處于“獨立作戰”狀態,相互間合作不夠緊密。

表2 2002—2022年國外“漂綠”研究機構共現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