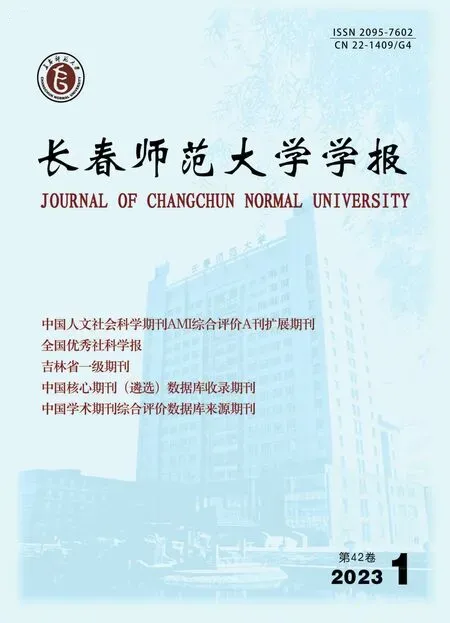伊犁流人祁韻士贈別詩初探
李彩云,任 剛
(1.伊犁師范大學 伊犁學研究中心,新疆 伊寧 835000;2.伊犁師范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新疆 伊寧 835000)
清代流放至伊犁的文人眾多。“在貶謫經歷的影響下,一些文人成為了當地詩壇巨擎,更由于流寓的生存狀態形成了他們與當地文化血脈相連的親近關系,進而使其作品爆發出了前所未有的洪鐘巨響”[1],祁韻士即是其中之一。祁韻士被流放至伊犁,他在完成《西陲總統事略》之余,創作了大量的詩歌作品。這些詩作保留于《西陲竹枝詞》和《濛池行稿》兩部詩集中,不僅有描寫天山、雪和松樹的風景詩,也有意味深長、寄托遙深的詠懷詩,還有令人感慨萬千、慨嘆離別的贈別詩。其贈別詩反映了詩人內心深處對親友的復雜情感,體現了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也寄寓了其深重的憂患意識和戍邊受命著史的家國情懷。
一、主題豐富,內涵深刻
(一)與親人和自己前半生的告別
《至家辭墓告別》[2]71是一首送別詩。該詩集中描寫詩人被流放邊疆后心理上遭受的沉重打擊和痛苦,詩人啟程之前,先歸家與家人告別。“焚黃廿有四年前,拜掃徒虛歲月遷”,初次入仕時,在祖先和父母墓前祭拜,至今已有二十四年。詩人感慨自己虛度年華,從未想到“一事無成今罷職,百年已半去投邊”。他想起自己前半生在朝為官,本該安享晚年,卻在暮年時被流放至邊疆,苦嘆“室家妻子心何系,險阻艱難命可憐”。家中的妻子兒女是他最大的牽掛,西行之路必將兇險重重,而這一切不敢向家中的親人哭訴,只好向地下的祖先和父母哭訴:“欲向雙親訴衷曲,九原不見淚如泉。”九原本是春秋時期晉國卿大夫的墓地,此處指代祁韻士祖先和父母的墓地。該詩是祁韻士詩集中感情表達最為沉痛的一首詩,不僅表現了詩人遭遇政治挫折后的傷痛,還體現了他對自己前半生的懷疑,這次打擊迫使詩人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和仕途。該詩在抒發情感之外,也展現了詩人完整的家族譜系圖。面對墓地的祖先和父母,詩人是兒子和后輩,他可以將自己內心的傷痛毫無保留地一一吐露;但回到家中,詩人是父親、是丈夫、是長輩,他是家中唯一的支柱,既擔心妻子孤苦無依,又擔心子女無有所托。這是一種政治上、情感上都進退兩難的處境,詩人為此傷痛不已。該詩沒有一個集中告別的對象,詩人既是對父母、對妻子、對子女進行告別,也是對自己的前半生進行告別。
祁韻士的送別詩體現了士人怨別和重土輕離的觀念,同時多了一份史地學家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展現出詩人暮年遭遇政治挫折時大起大落的心理歷程。“更為難得的是,由于貶謫、出任地方官職的經歷,他們將送別詩的創作活動從‘宮廷’擴大到‘江山’”[3]。祁韻士送別詩的創作內容,也從京城擴大到西北邊疆。
(二)與摯友和過去為之奮斗的理想告別
祁韻士不僅有寫給自己的告別詩,也有送給他人的贈別詩。《晤平涼太守閻柱峰賦贈》[2]111即是一首典型的贈別詩。“惻怛為仁政,賢名一郡知”,詩人從山西老家啟程,行至甘肅平涼。平涼知縣閻柱峰對其禮遇有加,詩人別時贈詩一首。此詩中的“太守”是一種擬古用法,實指知縣。該詩起句“惻怛”二字出自《禮記·問喪》“惻怛之心,痛極之意”[4],以此描述閻柱峰的仁政愛民之心。“我從所部過,民頌使命慈”,詩人來到平涼縣,聽到百姓對閻柱峰的稱頌,親身感受到閻柱峰的賢德。臨別時不忍分別,感慨“有子真堪慰,無錢莫自疑”。詩人替百姓高興,有閻柱峰百姓就有好日子。然而如此賢德的朋友即將分別,詩人內心充滿遺憾與不舍:“故人明日去,萬里寄相思”。全詩充滿了對閻柱峰仁政和賢德的贊頌,也體現出自己對閻柱峰的依依惜別之情。
《抵蘭州,蔡小霞方伯話別感賦》[2]116是詩人西行至蘭州時創作的一首送別詩。“何時脫駕到伊濱,且向蘭山一問津。”該句中“脫駕”表面指馬不再駕車之意,實則指自己脫離宦海沉浮,與過去為之奮斗的理想告別。“伊濱”貌似指流放地伊犁,但實指離開官場去鄉間水邊信步。韓愈《與崔群書》中云:“仆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于此,轉困窮甚,思自放于伊、潁之上,亦當終得之”[5]772。《祭十二郎文》:“自今已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于伊、潁之上,以待余年。”[5]1469詩人化用韓愈語詞,對自己前半生在朝為官頗有悔恨之意,他希望自己能像陶淵明一樣,離開渾濁的官場歸于鄉間穎水。在如此心境下遇到的蔡小霞可謂知己,詩中“蘭山一問津”即是此意。“念我艱難金石告,服君肝膽笑言親”,詩人想起自己被流放伊犁的痛苦,感念蔡小霞的坦誠相見與肝膽相照。“心交自覺情偏厚,贈別還思語最真”,詩人和蔡小霞推心置腹,還未分開,離別之感傷就已涌上心頭。“紉佩難忘良友意,始知古道屬同人”,詩人借助《離騷》意象表現自己和蔡小霞的高潔品格。詩中多次提及自己和蔡小霞心心相印,彼此引為知己,最后一句將全詩感情推向頂峰。
如果說《晤平涼太守閻柱峰賦贈》重在展現閻柱峰的賢德和政績,從客觀角度表達詩人對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那么《抵蘭州,蔡小霞方伯話別感賦》則是從主觀情懷、人品志趣等方面展現詩人和蔡小霞的情感契合,從而表達對友人的不舍之情。前者是送別詩客套中的不舍;后者則是發自內心的不忍分離,更是與自己過去為之奮斗的理想進行告別。祁韻士的送別詩大多表達對親友的不舍之情,但詩歌描寫的切入點和情感側重點各有不同,主題豐富,內涵深刻。
二、意蘊含蓄,意境幽深
(一)意蘊含蓄,送別中蘊含對戍邊生活的希望
《抵涼州劉葦亭觀察見招》[2]121是祁韻士送別詩中較有特色的一首。“馬蹄蹩躄下巖阿,日傍防秋故壘過”中“蹩躄”二字出于《莊子·馬蹄》:“及至圣人,蹩躄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6]“巖阿”則出自王粲《七哀詩》:“山岡有余映,巖阿增重陰。”[7]該詩起句描述詩人騎馬緩慢行過山腰,從白天行至傍晚時分,眼中看到“山外有山皆擁雪,水中無水尚名河”,幾乎看不到行人。“地鄰邊塞人煙少,路隔鄉關客感多”,此二句化用崔顥《黃鶴樓》“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8]語意,表現客愁思鄉之情懷,但這愁緒遠比崔顥的濃重。詩人獨自在雪路上愁緒萬千時,“愁里忽逢東道主,銜杯不覺醉顏酡。”東道主劉葦亭雪中送炭般給了詩人及時的溫暖,詩人心情開始好轉,不覺貪杯。“銜杯”二字與李白《廣陵贈別》一般無二:“系馬垂楊下,銜杯大道閫。”[9]可見詩人和劉葦亭相見之歡。該詩意蘊含蓄,描寫詩人一路西行時逐漸荒涼的外部環境,與之相應的是日益增加的內心愁緒。與上述送別詩中表達頌贊和引為知己的感情不同,該詩多了一層詠懷意味,可謂送別詩外衣,詠懷詩內在,詩歌形式整齊,讀來音韻和諧。該詩展現了詩人難得的歡顏,可以看出他對戍邊生活仍然抱有希望。
上述幾首贈別詩主要寫詩人和初見初識的人道別,《飲閻觀察署中》[2]127則描寫自己和老友重逢又道別的場景。該詩是一首五言律詩,全詩押“an”韻,具有鮮明的節奏感,富有音樂美,亦將詩人的哽咽之情表達得淋漓盡致,讀來感人至深。“一別竟三年,相逢到酒泉。那期今夕話,遠在塞云邊。”詩人三年前和老友分別,從未想到自己會被流放,更未想到和老友話別塞外,真可謂“相見時難別亦難”。此時,唯有就著滿腹的不舍將酒干盡。同時,詩人的不舍中蘊含了對戍邊生活的希望和憧憬。
(二)意境幽深,既是贈別也是對自我的慰藉
與致友人的贈別詩歌不同,《寄內》[2]129是寫給妻子的“報平安書”,該詩意境幽深,具有托物言志的特點。“一車兀坐當枝棲,終日馳驅任馬蹄”,詩人像離巢的孤鳥一樣,乘坐于西行的車輛上,不分晝夜一路西行。“鳳駕未過蔥嶺北,宵征已到玉關西”,早上還未過蔥嶺,晚上就行駛到了玉關。“鳳駕”指早上,《詩經·鄘風·定之方中》:“星言鳳駕,說于桑田”[10]88。“宵征”指夜晚出行,《詩經·召南·小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10]40。詩人年過半百日夜兼程,十分艱辛。“音書久隔憐兒輩,井臼親操念老妻”,長時間沒有兒孫的消息,內心十分掛念。想起家中老妻承擔家族的全部事務,詩人內心十分愧疚。讓家人得知自己過得很好,是寬慰家人的最佳方式。故詩歌結尾部分言:“手勒平安聊寄語,莫從風雨怨凄凄”。該詩寫得情真意切,蘊含著詩人對家中親人的無限牽掛。詩人在寬慰妻子的同時,也是在寬慰自己。
《途中呈丁立齋、鳳祥庵、遐九峰》[2]135一詩描寫了祁韻士和寶泉局前任同僚告別時的場景。嘉慶六年(1801),祁韻士奉旨擔任寶泉局監督,屬正三品。按照慣例,每任監督更替時,都是憑冊接任,并不盤點倉庫現貨。積年累月,虧空十分嚴重。祁韻士與前任監督交接,按慣例行事,對所轄倉庫物資沒有查點,為日后流放伊犁埋下了隱患。嘉慶九年(1804),寶泉局虧銅案發,朝廷將祁韻士等人發往伊犁效力贖罪。該詩記錄了虧銅案帶給詩人的痛苦之情。“何處最銷魂,西去過玉門。見沙不見草,無水竟無村”,流放地方圓幾百里都是戈壁沙漠鹽堿地,沒有水源。路長山青、風高日昏,即將經過玉門關,詩人內心沉痛不已。玉門關歷來被視為春風不度的地方,“此行偕舊侶,差幸笑言溫”,所幸有三個同僚相互照應,不至于孤苦無依,詩人內心有了些許的安慰和疏解。該詩意境幽深,送別中又寄寓了詩人對自我的慰藉。
三、結語
祁韻士的贈別詩數量不少,質量也頗為可觀,與其風景詩、詠史詩、詠懷詩、詠物詩相比毫不遜色。這些詩歌記錄了詩人流放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感,體現了詩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詩人經受政治挫折,反思自己的人生,一方面與親人、朋友以及自己的前半生進行告別,另一方面與過去之奮斗的理想進行告別。在經歷了與眾多親友的告別后,詩人無處安放、沉痛的心靈得到一絲安慰和解脫。詩人在送別中蘊含著對自我苦難人生的慰藉、對戍邊生活的希望和憧憬。生活并沒有辜負詩人,祁韻士到達伊犁后,遇到了賞識他的“伯樂”松筠。松筠時任伊犁將軍,受其委托,祁韻士著手編著西域史地叢書,實地考察民風民俗,最終完成了《西陲總統事略》《西陲要略》《西域釋地》等著作,記錄了清代西域的山川地貌、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該書文獻資料精煉詳實,為我們研究清代西域歷史文化提供了珍貴的史料。詩人在中原生活時甚少涉及文學創作,流放伊犁后,將所見所聞所感錄入《西陲竹枝詞》《濛池行稿》和《萬里行程記》三部文學著作中,其凄怨心情也逐漸得到消釋和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