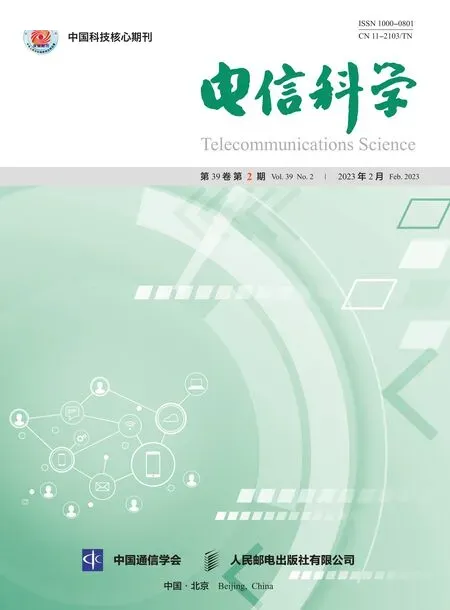一種基于耦合網絡的RD-IHSAT網絡謠言傳播模型
韓一士,徐雨欣,盧甜甜
一種基于耦合網絡的RD-IHSAT網絡謠言傳播模型
韓一士,徐雨欣,盧甜甜
(浙江警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3)
為探究謠言在社交網絡中的傳播規律,基于耦合原理,構建由巴拉巴西-阿爾伯特(Barabási-Albert,BA)無標度網絡與瓦茨-斯特羅加茨(Watts-Strogatz,WS)小世界網絡組成的沉默者、辟謠者、無知者、猶豫者、傳謠者、鐵桿傳謠者、疲憊者(reticent,debunker,ignorant,hesitated,spreader,adherent,tired,RD-IHSAT)謠言傳播模型。該模型在易感者、感染者、移出者(susceptible,infective,removal,SIR)模型的基礎上引入興趣衰弱機制、感知社會共識機制、沉默與反沉默的螺旋等因素,并融入猶豫者、鐵桿傳謠者、沉默者、辟謠者等角色,使其更加逼近真實情形。仿真結果顯示,耦合網絡極大地促進了謠言的傳播,不僅加快謠言爆發速度,而且擴大謠言傳播規模;提高對猶豫者的辟謠概率能夠極為顯著地抑制謠言規模,是控制謠言傳播的最有力因素;僅降低謠言傳播率對謠言控制作用較小;提高沉默群體的比例是遏制謠言傳播的關鍵一環;對辟謠時滯的把控極大地影響了辟謠效果。
謠言傳播;耦合網絡;興趣衰弱;社會共識;沉默的螺旋;RD-IHSAT模型
0 引言
在傳統社會中,謠言依托于親友間的人際關系網絡,以口耳相傳的形式緩慢傳播,其傳播速度與范圍均較為有限。而隨著互聯網和移動設備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人們通過訪問互聯網,廣泛而積極地參與到信息發布、分享和傳播的過程中,謠言的傳播形式也因此發生巨大的變化。線下人際關系網絡與線上虛擬社交網絡呈現進一步融合的趨勢,謠言傳播出現渠道聯動化的特點。換言之,謠言的快速頻繁傳播不只依賴于單一的線下或線上網絡,而愈來愈多地依賴于二者耦合關聯所形成的新型傳播網絡。
在一些發達國家,網絡普及率高、互聯網技術走在世界前列,網絡謠言亦是突出的社會問題。以1956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弗蘭奇(French)[1]發表的《社會影響力的形成理論》()一文肇始,國外一些學者陸續開始研究個體在網絡互動過程中如何對彼此施加社會影響,逐步建立起謠言傳播的模型基礎。此后,基于此種利用復雜網絡理論及其網絡拓撲特征來研究傳播行為的研究思路,Zanette[2]首創地把謠言傳播和小世界網絡環境結合在一起,并求得其傳播的閾值。Moreno等[3]將謠言傳播模型的背景環境替換成無標度網絡,融入平均近似場理論,通過變換BA網絡拓撲結構和設置不同的參數來改變信息的傳播,結果表明網絡的均勻性會對謠言傳播動力學產生巨大影響。Friedkin等[4]將多個邏輯相關的謠言統一至一個系統中進行研究,分析了其中邏輯關系如何影響傳播結果。Amelkin等[5]結合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理論,探索了現實世界中兩極觀點的演化方式。Düring等[6]基于微觀動力學的非齊次玻爾茲曼(Boltzmann)方程,探討了大規模網絡中的謠言傳播。
在國內,學者傾向于研究網絡謠言的分析、監測、演化和情感分類,與國外學者相比較,運用數據驅動方法對網絡謠言治理的研究較少。尹明[7]引入了西方的兩個傳播學理論——“共鳴效果”和“溢散效果”來闡述“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議程互動的方式”,但只是進行了定性分析,并未建立傳播模型。朱恒民等[8]基于WS小世界和Price網絡,通過設定網絡間的關聯關系實現了網絡的線上線下耦合,構建了SIR_2O跨層謠言傳播模型,實驗結果表明,不同網絡之間的耦合關系增大了話題傳播的速率和范圍。于凱等[9]針對網絡耦合方式中的同配、異配和隨機3種情況對信息傳播的影響進行研究,并基于認知不和諧理論和對稱模式構建了雙層耦合網絡(bilayer coupled network,BCN)模型,該研究結果表明,層間對稱模式擴大了信息傳播范圍并提高了信息傳播的速度。李丹丹等[10]構建了由線上社交網絡和線下物理接觸網絡構成的耦合網絡模型,計算穩態時的輿情傳播者比例,并得出雙層社會網絡上的輿情傳播閾值大于單層線上網絡輿情傳播閾值,而小于單層線下網絡輿情傳播閾值。劉泉等[11]在考慮個體間的差異的基礎上,構建了考慮個體屬性的線上線下耦合網絡的輿情傳播模型。魏靜等[12]基于傳播者的興趣衰減特征,結合耦合網絡理論構建模型,發現網絡的耦合加速了信息流動,用戶在不同社交網絡間的互動增強了信息的傳播能力,管控輿情傳播的關鍵是對層間互動的管控。李攀攀等[13]從輿情傳播的影響力出發,提出了一種基于最大熵理論的信息傳播影響力計算方法。
回顧現有的研究工作,關于耦合網絡及其傳播動力學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大多基于傳染病模型,對個體的知識水平、價值傾向、社交屬性、心理因素等特性考慮不足,傳統的以概率的方式同質地研究謠言的傳播與演化不能準確模擬其傳播規律。本文融合傳播學、社會心理學、復雜網絡傳播動力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知識,在傳統SIR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H(hesitated)態猶豫者、A(adherent)態鐵桿傳謠者、R(reticent)態沉默者、D(debunker)態辟謠者的群體劃分,建立了基于線上線下耦合網絡的RD-IHSAT(reticent,debunker-ignorant,hesitated,spreader,adherent,tired)傳播模型,并通過計算機仿真探索其傳播特點與規律。結果表明,提高對猶豫者和傳謠者的辟謠概率、降低傳謠者成為鐵桿傳謠者的概率能夠抑制謠言傳播,而單獨調整謠言傳播率對謠言控制作用較小。其中,提高對猶豫者群體的辟謠概率能夠極為顯著地抑制謠言規模,成為控制謠言傳播最有力的因素。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提出謠言干預與控制策略,對于化解輿情危機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1 模型構建
1.1 SIR謠言傳播模型


1.2 社交網絡結構分析
著名的“六度分離”現象[14]表明,線下社交網絡中陌生人由共同認識的親友相互連接,使得人際交往常集中在小圈子,反映在復雜網絡中表現為網絡平均路徑短、聚類系數大,具有明顯的小世界特征。因此本文以WS小世界網絡為載體構建線下社交模型。
線上虛擬網絡(例如微博、臉書、推特等)中的用戶通過關注與被關注建立聯系,超越了點對點的人際傳播形式,一條信息在線上虛擬社交網絡中可以同時推送給所有關注者,以“一呼百應”的勢態迅速傳播擴散。線上網絡中,小部分意見領袖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大部分網民影響力則較小,呈現較強的無標度特性,與BA無標度網絡模型較為契合。因此本文以BA無標度網絡為載體構建線上虛擬網絡。
針對謠言同時在線上虛擬社交網絡與線下人際關系網絡傳播的特點,每個節點在線上網絡與線下網絡分別對應不同身份,線上網絡與線下網絡的節點一一對應(本文暫不考慮一人持有多個線上賬號的情況),表示現實中同一個體在不同網絡中存在不同身份。


圖1 耦合網絡結構
1.3 RD-IHSAT網絡謠言傳播模型
1.3.1 興趣衰減機制
謠言傳播與疾病傳播不同,社會運作機理與個體特質差異會直接對傳播產生重要影響,最顯著的區別在于興趣衰減是公眾失去傳播動力的決定性因素[15]。德國心理學家艾賓豪斯揭示信息價值會隨時間的流逝呈現非線性衰減特征[16],受眾對信息的關注度會隨時間推移自然下降,導致“新熱點取代舊熱點”。因此模型建立時應當考慮信息時效性的影響,個體參與傳播一定時間后將由于興趣衰減自發退出傳播。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并考慮到艾賓豪斯遺忘曲線,采用指數形式的飽和函數構建疲憊者概率關于時間的興趣衰減函數,如式(2)所示:
其中,為轉化為疲憊者的概率,為接收到信息所經過的時間,為衰減因子。越大,越大。衰減因子的取值決定了興趣衰減曲線的變化速率,越大,個體對信息傳播興趣衰減越快,謠言也越容易因為興趣衰減而停止傳播。
1.3.2 沉默與反沉默螺旋
謠言傳播存在沉默與反沉默螺旋效應。在謠言傳播中,部分群體雖具備知識儲備,能夠鑒別謠言真偽,但為避免與主流意見沖突而被群體攻擊與孤立,最終仍選擇保持沉默,導致謠言信息愈發占據輿論高地,形成“沉默的螺旋”現象。然而一旦有個體敢于辟謠打破沉默,持相似觀點的沉默群體會迅速受到鼓舞,轉化為支持者附和表達,使得“少數派”激增甚至超越“優勢意見”,產生“反沉默的螺旋”現象。
基于以上理論,本文在SIR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沉默者和辟謠者:前者指擁有相關知識能夠鑒別謠言真偽,但由于群體壓力保持沉默,不愿主動辟謠的網民,其可能受辟謠者鼓舞轉化為辟謠者;后者則基于反沉默的螺旋,指能夠鑒別謠言真偽,并主動參與辟謠的網民。
值得注意的是,辟謠與傳謠并非同步進行,辟謠具有時滯性,只有謠言傳播達到一定規模時,辟謠者才能察覺到謠言的出現并開始辟謠[17]。
1.3.3 猶豫者和鐵桿傳謠者
SIR模型中,S態(未知態)網民接觸信息后只能轉化為I態(傳播態)或保持未知態。事實上,網民在接觸謠言后很少立刻相信并傳播,此時的個體處于“猶豫態”,即部分個體接收信息后,會因無法辨別其真偽,從而產生猶豫,暫不傳播,類似于疾病傳播中的“潛伏期”。該時段就是猶豫者暫停狀態轉化的猶豫期,也是最有可能改變其觀點的“辟謠期”。因此,在SIR模型的基礎上添加猶豫者狀態,若“辟謠期”內猶豫者接觸到反對信息,則有可能被辟謠;反之,若辟謠期結束后猶豫者仍未被成功辟謠,則會選擇相信謠言,猶豫者會自動轉化為傳謠者。
此外,SIR模型對I態(傳播態)節點未根據其傳播能力做進一步分類。研究表明,重復效應直接導致謠言信念的產生[18]。頻繁感知到的社會共識可以鞏固和維持對謠言的信念,在不斷強化下使相信謠言的個體成為謠言的“擁護者”“信徒”。因此,本文將傳播者進一步分化為傳謠者和鐵桿傳謠者。傳謠者指初參與傳謠,尚未形成謠言信念,容易被辟謠轉變態度的個體。與之相對的,頻繁感知到虛假的社會共識,在不斷強化下堅定認同謠言,對其糾正與辟謠收效甚微的個體定義為鐵桿傳謠者。鐵桿傳謠者的傳謠能力遠高于一般傳謠者,且其觀點難以被動搖,類似于疾病傳播中的“超級感染者”。
1.3.4 感知社會共識
關于謠言傳播的經典實驗[19]證實,反復接觸某一信息會增加其可信度。由于“感知社會共識”的影響,當個體同時與社會網絡中多個“傳謠者”接觸,其轉化為“傳謠者”的概率應高于單次接觸轉化的概率。反之,當個體所接觸的社會網絡中“辟謠者”占多數,其被辟謠的概率也會上升。
為表現耦合網絡中“感知社會共識”效應對個體狀態轉變的影響,本文運用飽和函數描述傳播概率隨社會網絡環境中同態節點個數上升而上升的情況。當節點同時與網絡中多個同態節點傳播時,其轉變狀態的概率如式(3)所示:

其中,表示上一時刻節點所接觸的相同狀態節點的個數,為單次接觸節點轉變狀態的概率,易得(1)=。
注釋1 事實上,當個體受到多個同態概率節點影響時,其轉變概率為:

假設個體的轉變概率相等,可得:

1.3.5 謠言的遏制與對抗機制
在信息傳播領域,大量多元觀點在傳播中互相爭奪話語空間,形成信息的競爭傳播。個體在耦合網絡中,可能同時受到傳謠者、鐵桿傳謠者和辟謠者的影響,從而發生狀態的改變,其最終狀態取決于角力雙方的轉化概率之比,個體狀態容易向著轉化概率大的一方轉化。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眾多傳謠者和鐵桿傳謠者影響下,個體仍存在不被環境態度左右、保持原有傾向的可能性。本文將保持個體狀態不變的概率定義為頑固性,用()表示,本文取()=0.5。
1.3.6 模型介紹與傳播規則
本文改進的RD-IHSAT模型結合社會心理學與信息傳播理論,將耦合網絡中的個體劃分為以下7類,RD-IHSAT模型示意圖如圖2所示。

圖2 RD-IHSAT模型示意圖
?I(ignorant)態:未知者,指從未接觸過謠言與辟謠信息的個體。
?H(hesitated)態:猶豫者,指接觸過謠言但無法鑒別其真假,暫未進行傳播的個體。
?S(spreader)態:傳謠者,指接觸過謠言并相信其真實性,會繼續傳播謠言的個體。
?A(adherent)態:鐵桿傳謠者,指受到感知社會共識影響,在“回聲室”中不斷加強謠言認同感,成為謠言堅定擁護者的個體,其擁有更強的謠言傳播能力,且無法被其他個體辟謠。
?R(reticent)態:沉默者,指擁有相關知識能夠鑒別謠言真偽,但由于群體壓力保持沉默,不愿主動辟謠的個體。
?D(debunker)態:辟謠者,指能夠鑒別謠言真偽,并主動參與辟謠的個體。
?T(tired)態:疲憊者,指參與傳播一段時間后,因信息失去時效,傳播興趣衰減從而退出傳播的個體。
模型的傳播規則下。
(1)未知者與傳謠者接觸,有概率成為傳謠者,否則必然成為猶豫者;未知者與鐵桿傳謠者接觸,有概率成為傳謠者(>),否則必然成為猶豫者。
(2)猶豫者與辟謠者接觸,有概率被辟謠,其中有概率0.6成為沉默者,有概率0.4成為辟謠者;若在為期1的潛在辟謠期內猶豫者沒有被成功辟謠,則轉化為傳謠者。
(3)傳謠者與辟謠者接觸,有概率被辟謠(>),其中有概率0.8成為沉默者,有概率0.2成為辟謠者;傳謠者與其他傳謠者、鐵桿傳謠者接觸,以概率轉化為鐵桿傳謠者。
(4)沉默者與辟謠者接觸,有概率成為辟謠者。
(5)辟謠者在2時刻參與傳播,產生辟謠效果。
(6)除未知者外,所有傳播參與者每時刻以概率成為疲憊者,興趣衰減退出傳播,是關于時間的飽和函數,退出概率隨時間的上升而上升。
(7)傳播結束后系統最終剩余未知者、疲憊者。
2 仿真實驗與結果分析
使用MATLAB構建各含有500個節點的WS小世界網絡和BA無標度網絡,建立雙層耦合網絡并分析謠言傳播過程。其中,每個節點代表社交網絡中的一個個體,線上和線下網絡中編號相同的個體為同一個體。
2.1 單層網絡與耦合網絡中謠言傳播過程對比
令=0.6,=0.8,=0.2,=0.1,=0.6,=0.6,初始沉默者1=30,初始辟謠者2=10,猶豫期1=3,辟謠延遲2=3,線下社交網絡節點狀態變化曲線如圖3所示,線上虛擬網絡節點狀態變化曲線如圖4所示。

圖3 線下社交網絡節點狀態變化曲線

圖4 線上虛擬網絡節點狀態變化曲線
由圖3、圖4可知,線下社交網絡中謠言幾乎沒有傳播開,在極小范圍傳播后自行消亡,而線上虛擬網絡中謠言在短時間內迅速擴散,傳播結束后網絡中絕大多數個體曾接觸過謠言信息,大眾普遍更早到達疲憊期,退出傳播。此外,線下謠言傳播中傳謠者與鐵桿傳謠者數量上升十分緩慢,直到=25時刻,未知者人數仍然超過50%。而線上謠言在=3時突然爆發,謠言傳播群體迅速攀升,在=9時達到傳播高潮。此時網絡中53.2%的個體為謠言傳播者或鐵桿傳播者,謠言在線上成為主流觀點。
耦合網絡節點狀態變化曲線如圖5所示。

圖5 耦合網絡節點狀態變化曲線
由圖5可知,當謠言在耦合網絡中傳播時,其傳播速度相較單獨線上與單獨線下網絡進一步加快,傳播范圍也有顯著擴大,謠言的覆蓋面是線上網絡的1.2倍,爆發速度亦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網絡的耦合尤其促進了謠言在線下的擴散。值得注意的是,耦合促進了猶豫者向傳謠者的轉化,網絡中大量謠言信息的充斥形成一個不斷放大的“回聲室”,使猶豫者難以接觸正確辟謠信息,被虛假的感知社會共識蒙蔽,導致辟謠針對的最主要群體“淪陷”。線下傳播的謠言引起網絡共鳴,使失真的信息在互聯網中迅速傳播,加劇形成謠言,同時大眾媒介特性使網絡話題快速溢散到各類人群中,合力促成線下事件。
2.2 狀態轉換概率對耦合網絡中謠言傳播的影響
通過對狀態節點轉換概率進行調整,探究其對謠言傳播影響的影響,從中選出控制謠言的關鍵因素。
2.2.1 傳謠者傳播力的影響
=0.5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如圖6所示,=0.4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如圖7所示。未知者與傳謠者接觸傳播概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傳謠者傳播力。圖6、圖7顯示,降低傳謠者傳播力,穩態下傳謠者、鐵桿傳謠者比例下降較為明顯,辟謠者數量緩慢提升,最大謠言傳播規模下降了19%,發展態勢得到一定控制。但是,謠言仍在觀點市場中略占優勢,和辟謠信息呈現分庭抗禮的態勢。同時,由于辟謠的滯后性,大眾最先接觸謠言信息,容易產生先入為主的印象。綜上所述,降低傳謠者傳播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削減謠言傳播趨勢,但削弱力度較小。

圖6 α=0.5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

圖7 α=0.4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
2.2.2 鐵桿傳謠者傳播力的影響
=0.7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如圖8所示,=0.6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如圖9所示。未知者與鐵桿傳謠者接觸傳播概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鐵桿傳謠者的傳播力。降低鐵桿傳謠者傳播力,穩態下傳謠者、鐵桿傳謠者比例略有下降。最大謠言傳播規模下降了14%,但辟謠者人數仍然未能超越鐵桿傳謠者,謠言傳播規模下降較不顯著。綜上所述,鐵桿傳謠者傳播力降低使對控制謠言傳播作用較小,無法起到遏制作用。

圖8 β=0.7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

圖9 β=0.6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

圖10 γ=0.4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
2.2.3 辟謠率對謠言傳播的影響
=0.4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如圖10所示,=0.5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如圖11所示。上調猶豫者與辟謠者接觸的辟謠概率,穩態下傳謠者、鐵桿傳謠者顯著減少,辟謠者數量顯著增加,增幅達到322%,首次實現了網絡中辟謠者的數量大于傳謠者,意味著個體在網絡中接觸到正確的辟謠信息的概率大于接觸謠言,謠言規模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綜上所述,提高對猶豫者群體的辟謠率能夠顯著有效地抑制謠言傳播。
2.3 初始沉默者比例對謠言傳播的影響
為了探討沉默者比例對謠言傳播的影響,控制其他參數不變進行仿真實驗,初始沉默者比例為5%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如圖12所示,初始沉默者比例為40%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如圖13所示。

圖11 γ=0.5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

圖12 初始沉默者比例為5%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

圖13 初始沉默者比例為40%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
根據仿真實驗,人群中具備知識素養,能夠鑒別謠言真假的“沉默者”比例直接決定謠言是否能夠傳播。當沉默者比例達到20%時,謠言的最大傳播規模從46%壓縮到35%,辟謠者群體比例高于鐵桿傳謠者,這意味著當公眾交流信息時,接觸正確的辟謠信息的可能性要大于接觸謠言。當沉默者比例達到40%,謠言幾乎沒有市場,無法爆發,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在小圈子中流傳,在=15時便逐步消亡。仿真實驗證實人群中具備知識素養的“沉默者”的初始比例是決定謠言能否傳播的決定性因素,提高民眾知識素養,煉成大眾鑒別謠言的“火眼”是謠言控制的關鍵。
2.4 辟謠時滯對謠言傳播的影響
辟謠時滯分別為2、4、6個時步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如圖14所示。謠言的傳播和發酵需要一定時間,只有在謠言傳播達到一定規模時,辟謠者才能察覺到謠言的出現,而此時謠言往往已有相當規模的受眾與市場,甚至培養出部分鐵桿擁護者。因此盡可能縮短辟謠的時滯,把握最佳辟謠期是將謠言影響降到最低的關鍵。根據仿真實驗,辟謠者參與傳播的時間越早,謠言越不容易成規模擴散,當辟謠時滯為4個時步時,辟謠信息已經無法戰勝謠言,謠言擁護者占據了輿論高地;當辟謠時滯大于或等于6個時步后,系統中出現“辟謠完全失靈”的現象,辟謠信息幾乎無法在網絡中傳播開,擁護謠言的觀點成為輿論場唯一的“主旋律”。因此,在謠言的控制中要嚴格注意辟謠時限的把握,加強謠言監測系統的建設,做到迅速察覺,寸秒必爭。同時,官方辟謠要絕對守住“辟謠完全失靈”這一關鍵時刻的底線與紅線,嚴防謠言成為社會普遍信仰與共識,造成難以挽回的危害。

圖14 辟謠時滯分別為2、4、6個時步的節點狀態變化曲線
2.5 RD-IHSAT模型與傳統SIR模型傳播結果比較
令=0.6,0.8,=0.2,=0.1,=0.6,=0.6,初始沉默者1=30,初始辟謠者2=10,猶豫期1=3,辟謠延遲2=3,謠言在RD-IHSAT模型的傳播過程如圖15所示。在式(1)所示的微分方程中令=0.1,=0.02,得到的傳統SIR模型傳播過程如圖16所示。

圖15 謠言在RD-IHSAT模型的傳播過程

圖16 傳統SIR模型傳播過程
根據仿真實驗,與傳統SIR模型相比,RD-IHSAT模型在角色定位上更加豐富,在傳統的未知者(S)、傳播者(I)、疲憊者(R)的基礎上增加了H態猶豫者、A態鐵桿傳謠者、R態沉默者、D態辟謠者的群體劃分,更加深入地探討了謠言傳播的內在機理,也更加貼合實際情況。其次,傳統的SIR模型基于均勻混合假設,即假定傳播個體之間完全均勻混合、隨機接觸,個體間接觸的概率相同,而本文提出的RD-IHSAT模型建立在復雜網絡的基礎上,考慮信息社交網絡上信息的傳遞規律,更加符合人際交往的實際情況。最后,傳統的SIR模型將人群視為同質化的個體,而本文考慮個體的差異,加入了頑固性的概念,以對社交網絡中不同人群的特性進行更好的模擬。
3 結束語
本文構建的基于線上線下耦合網絡的RD-IHSAT模型經過數值仿真驗證,在理論上合乎假設,在現實中有所對應。在SIR模型基礎上,增加了H態猶豫者、A態鐵桿傳謠者、R態沉默者、D態辟謠者的群體劃分,豐富了網絡群體的角色,使之更貼合實際。以BA無標度網絡和SW小世界網絡為基礎構建線上線下耦合的復雜網絡,克服了過去單一線上或單一線下網絡的傳播缺陷。通過設置恰當的參數以檢驗不同情況下節點狀態演化規律。
仿真結果發現,耦合網絡極大地促進了謠言的傳播,不僅加快了謠言爆發速度,而且擴大了謠言傳播規模。此外,在同樣的概率幅度變化下,下調謠言的傳播概率對控制謠言傳播發揮的作用較小,社會中知識素養較高、能夠“明辨是非”的沉默者群體比例是遏止謠言傳播的關鍵,辟謠時限的把握也極大影響了政府辟謠效果。值得一提的是,提高對猶豫者的辟謠率是抑制謠言的最有力手段,微小的概率上升即可顯著促進謠言治理,將輿論場中的謠言規模控制到最小。因此,在謠言的預警與控制中,應當重視對猶豫者群體的辟謠工作,即將工作重心放在辟謠期內,通過規模化發布辟謠信息與對猶豫者的針對性辟謠并舉,爭取還未確信謠言真偽的猶豫者,以達到謠言抑制效率最大化。
本文構建的雙層耦合網絡假設了一個互聯網化程度較高的社會現實,每個現實個體都存在唯一確定的線上虛擬社交網絡賬號。在以后的工作中,筆者會進一步考慮線下個體沒有線上賬號,以及線下個體存在多個線上賬號的情況。此外,本文采用仿真的方式對模型進行驗證,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下一步研究將使用真實數據更好地反映現實中輿情事件中謠言傳播的規律。
[1] FRENCH J R. A formal theory of social power[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56, 63(3): 181-194.
[2] ZANETTE D H. Dynamics of rumor propagation on small-world networks[J]. Physical Review E, Statistical, Nonlinear, and Soft Matter Physics, 2002, 65(4): 041908.
[3] MORENO Y, NEKOVEE M, PACHECO A F. Dynamics of rumor spreading in complex networks[J]. Physical Review E, Statistical, Nonlinear, and Soft Matter Physics, 2004, 69(6): 066130.
[4] FRIEDKIN N E, PROSKURNIKOV A V, TEMPO R, et al. Network science on belief system dynamics under logic constraints[J]. Science, 2016, 354(6310): 321-326.
[5] AMELKIN V, BULLO F, SINGH A K. Polar opinion dynamics in social networks[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2017, 62(11): 5650-5665.
[6] DüRING B, WOLFRAM M T. Opinion dynamics: inhomogeneous Boltzmann-type equations modelling opinion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segreg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2015, 471(2182): 20150345.
[7] 尹明. 網絡輿論與社會輿論的互動形式[J]. 青年記者, 2009(2): 26-27. YIN M. Interactive form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social public opinion[J]. Youth Journalist, 2009(2): 26-27.
[8] 朱恒民, 楊柳, 馬靜, 等. 基于耦合網絡的線上線下互動輿情傳播模型研究[J]. 情報雜志, 2016, 35(2): 139-144, 150.ZHU H M, YANG L, MA J, et al. Study on public opinion propagation model based on coupled networks under onlineto offline interaction[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6, 35(2): 139-144, 150.
[9] 于凱, 榮莉莉, 郭文強, 等. 基于線上線下網絡的輿情傳播模型研究[J]. 管理評論, 2015, 27(8): 200-212. YU K, RONG L L, GUO W Q, et al. A model of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on online-offline networks[J]. Management Review, 2015, 27(8): 200-212.
[10] 李丹丹, 馬靜. 雙層社會網絡上的輿情傳播動力學分析[J]. 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 2017, 37(10): 2672-2679. LI D D, MA J. Public opinion spreading dynamics in a two-layer social network[J]. 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 Practice, 2017, 37(10): 2672-2679.
[11] 劉泉, 榮莉莉, 于凱. 考慮多層鄰居節點影響的微博網絡輿論演化模型[J]. 系統工程學報, 2017, 32(6): 721-731. LIU Q, RONG L L, YU K. Public opinion model of micro-blog network with influence of multi-layered neighbor nodes considered[J]. Journal of Systems Engineering, 2017, 32(6): 721-731.
[12] 魏靜, 黃陽江豪, 朱恒民. 基于耦合網絡的社交網絡輿情傳播模型研究[J]. 現代情報, 2019, 39(10): 110-118. WEI J, HUANG Y, ZHU H M. Research on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model of social network based on coupling network[J]. 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 2019, 39(10): 110-118.
[13] 李攀攀, 謝正霞, 王贈凱, 等.開放互聯網環境基于信息熵的信息傳播影響力計算方法[J]. 電信科學, 2022, 38(4): 90-100.
LI P P, XIE Z X, WANG Z K, et al. Calculation method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based oninformation entropy in public internet[J]. Telecommunications Science, 2022, 38(4): 90-100.
[14] MILGRAM S. The small world problem[J]. Psychology Today, 1967, 2(1): 60-67.
[15] 覃志華, 劉詠梅. 基于三層微信網絡的謠言傳播模型仿真研究[J]. 情報科學, 2017, 35(5): 119-124. QIN Z H, LIU Y M. Simulation investigation of rumor spreading model base on three-layer WeChat network[J]. Information Science, 2017, 35(5): 119-124.
[16] EBBINGHAUS H. Memory: a contribution to experimental psychology[J]. Annals of Neurosciences, 2013, 20(4): 155-156.
[17] 唐梁鴻緒, 王衛蘋, 王昊, 等. 新冠疫情下的SEIRD時滯性謠言傳播模型及辟謠策略[J]. 工程科學學報, 2022, 44(6):1080-1089. TANG L H X, WANG W P, WANG H, et al. Time-lag rumor propagation model and rumor-refuting strategy of SEIRD under COVID-19[J]. Chines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2022, 44(6): 1080-1089.
[18] PEDERSEN A, DUDGEON P, WATT S, et al. Attitudes toward indigenous Australians: the issue of “special treatment”[J]. Australian Psychologist, 2006, 41(2): 85-94.
[19] BEGG I M, ANAS A, FARINACCI S. Dissociation of processes in belief: source recollection, statement familiarity, and the illusion of truth[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992, 121(4): 446-458.
A model of RD-IHSAT rumor dissemination based oncoupling network
HAN Yishi, XU Yuxin, LU Tiantian
Zhejiang Police College, Hangzhou 310053, China
To explore the spread of rumors in social network,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upling network, the model of RD-IHSAT was established on Barabási-Albert (BA) scale free network and Watts-Strogatz (WS) small world network. The classic model of SIR was optimized, by combining it with three concerns, the interest decay, the social consensus and the spiral of silence effect, and adding four roles, hesitated, adherent, reticent and debunker. Result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s are as follows: an information outbreak can be triggered by coupling network, not only the spreading speed but the scale as well; the dissemination can be markedly suppressed when the probability of rumor-refuting for the hesitated and spreaders arises; the chances of transition from spreaders to adherents drop;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silent groups is a key part of curbing the spread of rumors; the control of the time lag in refuting rumors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effect of refuting rumors.
rumor dissemination, coupling network, interest decay, social consensus, spiral of silence, model of RD-IHSAT
TP391.9
A
10.11959/j.issn.1000-0801.2023023

韓一士(1990-),男,浙江警察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輿情傳播與引導。
徐雨欣(2000-),女,浙江警察學院在讀,主要研究方向為傳播學。

盧甜甜(1987-),女,浙江警察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迭代學習控制。
2022-09-12;
2023-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