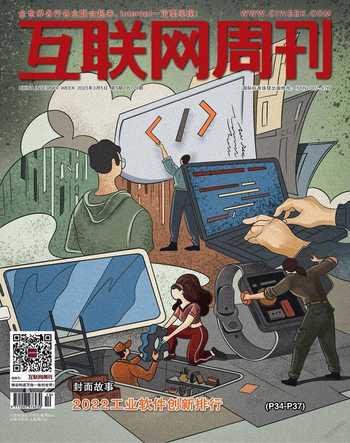何謂“生”,何謂“活”?(下)

3. 技術角度的“生”與“活”
接下來我將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待“生”與“活”。
我們向大家推薦的第二本書是法國著名思想家貝爾納·斯蒂格勒寫的《技術與時間》。這套書共有三本,第一本叫《愛比米修斯的過失》,書里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過去認為技術是死板的東西,它怎么會和“活”聯系在一起呢?
斯蒂格勒從“生”與“活”這樣一個角度把技術分成兩種,一種叫普羅米修斯技術,一種叫愛比米修斯技術。普羅米修斯技術就是“生”這種類型的技術,愛比米修斯技術就是“活”這種類型的技術。這是怎么回事?
其實普羅米修斯和愛比米修斯是兄弟兩個,在古希臘神話里面一個負責給萬物賦能,一個通過盜火為人類賦能。
首先我們來看“生”的技術。按照斯蒂格勒的描述,普羅米修斯類型的技術代表的是工具理性,獲得火就是人類掌握工具理性的象征。工具理性是沒有生命的,它只是工具。這種技術導致一切都向著機器靠攏。人們的思維也開始像工具理性一樣變成一種教條,但技術本身卻不是只有這一種取向。
斯蒂格勒指出,相反還有一種使事物從機械、統一的狀態變成靈活、差異化的技術取向,它就是愛比米修斯技術。
愛比米修斯技術在現代對應的是信息技術和生命技術,它恢復了整個系統的活性。這種“活”的狀態,也就是變化。大數據就是來簡易地把握世界的千變萬化,它的下一個階段將進入大模型的階段,同樣是為變化來建立模型,強調變的本身不變,把這一點作為最高的原則。
基于此,這種技術在變化過程中產生了我們所說的個性化、差異化的經濟形態,這種技術形態的根源就是“活”的技術。
愛比米修斯技術實際上指的是,像信息技術、生命技術這種活性的技術,一旦它們和經濟社會融合起來,將會使信息社會沿著和工業社會相反的方向演進。
4. 經濟角度的“生”與“活”
下面,我們來討論從“生”到“活”的經濟意蘊。
技術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經濟是人與人的關系。在經濟中“生”與“活”又是如何區別的?如何從一種以“生”為主,即以生存發展的物質需求為主,向自我實現這種精神滿足為主的方向發展的?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我推薦的第三本書是法國著名思想家喬治·巴塔耶的書,叫作《被詛咒的部分》。
《被詛咒的部分》同樣是一個三部曲,這三部曲統稱為普遍經濟學。巴塔耶被稱為“經濟學的尼采”。
他的普遍經濟學認為,經濟學家說的經濟學都是關于“生”的經濟學。“生”的經濟學是沒有生命力的,它是為生產而生產,最后把世界搞機械化了的經濟學。他希望“活”的經濟學成為一種更普遍的狀態,所以他的理論稱為普遍經濟學。其中的第一部分叫作被詛咒的部分。
第一個觀點,“生”是為生產而生產。
什么部分被詛咒了?詛咒的就是“生”,也就是為生產而生產,以致達到過度生產。所以巴塔耶的普遍經濟學首先是建立在對工業經濟的批判上。工業經濟雖然有它的歷史進步之處,也就是帶來了高度的專業化發展。但它也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單一、單調,越來越從有生命的這樣一種“活”的狀態,進入沒有生命的一種機械的狀態。走向極端就會帶來異化。
比如,眾所周知,工業化造成的機械化和自動化把人變成了機器,變成了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即使在信息社會,人們仍然熱衷于拿信息技術去搞自動化。當然了,必要的自動化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把全部社會都變成了一部精密的機器,這個時候犧牲的是什么?犧牲的就是人的活力狀態。每個人在這部機器體系里,被滅活了,他的能力、潛力難以得到釋放,這種機會被抑制,這就是過度的理性化,或者說這就是為生產而生產造成的問題。
但從東方的觀點看,“活”既不是生也不是死,而是向死而生的過程本身。也就是如何把工業社會這樣一個機械體系盤活,也就是我們不應該執著于物的那種非黑即白的狀態。正如互聯網不能執著于節點a或者節點b,而是通過互聯互通把它的活力激活。經絡是干什么?經絡是為活而存在,也就是生生之德,使“活”得以存在。
對經濟來說,也存在這樣一個問題,需要向死而生。因為生產,即對GDP的狂熱,對生活造成了一種壓迫。就像加在人身上的詛咒一樣,人類需要消除這種詛咒。
第二個觀點,“活”是綻放。
如果剛才從反面的角度講,在“生”的反面,“活”是對物化的一種否定。正面的主張是什么呢?我們用一個詞“綻放”來表現。
綻放在巴塔耶的理論里被稱為耗費,這個詞有多種譯法,它的含義是什么?
我們首先來看他是如何提出這個問題的。我們的消費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我們的消費現在變成了為了解決生產的問題而促銷,促銷是為了讓過剩的產能有地方去消費,而不是出于消費本身的意愿去生產。
巴塔耶的意思是,要把經濟從物的狀態變成“活”的狀態,從生存發展這種物質需求發展成自我實現這樣一種“活”的過程。所以他認為要解決的是生命問題,因為生命是活的。
人類不能為了生產而生產,必須得是讓人的這種活性得以釋放,也就是解決經濟生命化的問題,從機械化向生命化的過程去升級,為此而提出了耗費這樣一個概念。
我們把耗費換成燃盡這種說法,更貼切。
燃盡的第一個含義是指物質的毀滅,也就是不是為了物質而物質,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物質和生產作為手段,最終是要被毀滅的,也就是否定手段之后再來實現目的。
燃盡第二個含義是什么?是重生。從物質的毀滅里,向死而生。重生的是什么?是精神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重生。比如說創新,比如說快樂幸福,這是人自我實現的目的,這種需求是高于生產的。
我們把兩個過程結合起來,就可以理解為我們所說的“‘活是一個向死而生的過程”,這個過程最好的表現就是涅槃,也就是從一個生生死死的狀態,變成了一個生命過程的延續。
巴塔耶曾經轉譯維吉爾的一句詩——給我滿把的百合花。他的意思說工業社會過度理性造成人們的物化,使每一個小人物都不能實現自我,使精神受到抑制。他希望野百合也有自己的春天,使每一個小人物的活力能夠釋放出來。比如通過創業、創新,把小人物的能力、潛力、可能性釋放出來,這才是耗盡這個詞的真實意思。所以最后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是一種綻放。
在整個工業社會中,每一個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是非常灰暗的,他們為物質而奔波,活得灰頭土臉。但是巴塔耶說,從出生到活著這個過程,意味著我們小人物,在一生中也總要有一個高光時刻。
比如我可能在五分鐘之內成為網紅,就像櫻花一樣迅速地綻放,哪怕只綻放一刻,但是我曾經綻放得無比精彩。
如果經濟也能把我們從這種物化的狀態變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釋放狀態,我們對于克服整個工業經濟的弊端就可以實現,更不用說在未來的信息社會,人們將普遍地綻放。
我們為衣食住行而投入的這個過程,將來可能在十天里邊用一兩天就完成了。剩下的時間干嗎呢?每個人都像網紅似的天天綻放,無時無刻不在綻放自己。這個就是從經濟角度,從“生”到“活”這樣的一種轉變。
我把今天的發言概括一下。從“生”到“活”實際上是從理性向意義升級的一個過程,也就是我們從為了物質的存在,向著自我實現的存在轉變,這正是信息社會向我們展示的未來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