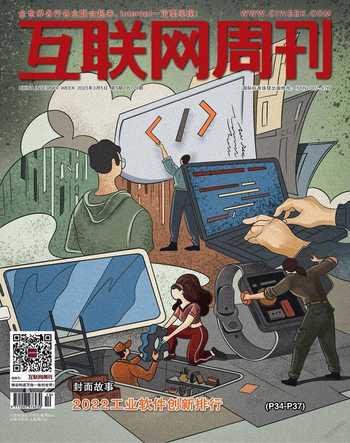數字社會視域下城市社區治理的空間轉向研究

摘要:數字社會建設已經成為國家戰略。在數字社會建設過程中,人們的生活習慣、認知模式、互動方式等都發生了改變,個體和組織及社會之間的內在關系被重新構建,生成了新的社會生活空間,這就不可避免地沖擊著業已存在的社會秩序和規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和風險。本文通過研究提出解決問題、規避風險的可行方案。
關鍵詞:社區空間;數字社會;社區治理
1. 空間轉向與社區空間
空間可以通過自身的結構去重新優化整合其內在的社會力量及社會關系,從而將進入空間的社會力量和關系重構成新的生活秩序和社會關系。社區是社會結構與社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社會建設背景下,人的生活習慣、認知模式、互動方式、資源分配等都發生了改變,形成新的社會空間。與傳統自然的社會空間不同的是,原來的客觀、基于經驗認知等特點逐漸消逝,逐漸轉向了具有明顯主觀和基于身心感受等特征的社會空間。也就是說,空間轉向重塑了社區空間。
2. 空間轉向造成社區空間失序
2.1 熟悉的陌生人:鄰里空間的“內應”和“排斥”
在新媒體新興技術的加持下,我們正走在推進數字社會建設的高速路上。然而,鄰里之間的社會距離、心理距離并沒有因為空間轉向而得到有效拉近,社會空間的距離感、陌生感、疏離感卻更加明顯了。信任是人際關系建立的基礎。信任的基礎在于關系的親近,空間轉向導致人與人之間交往減少,鄰里之間的信任關系已經岌岌可危。可以說,空間轉向解構了“人際信任”關系,而相應的信任制度則還不完善,從而造成了信任的“斷裂”。這樣,鄰里間的沖突可能會被進一步激發,甚至會造成新的鄰里間沖突的發生。
2.2 紊亂的兩棲人:生活空間的“錯位”和“斷裂”
社區居民原有的生活空間經歷了多年運轉,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慣性。如今,居民可能由于空間轉向原因而增加了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錯位”和“斷裂”的現象出現在熟悉的生活世界中,居民個人存在的不確定性被變得空間化和個體化。空間轉向瓦解了傳統的維系空間穩定的社會基礎,社區居民作為自然空間日常生活主體的“我”因現實與虛擬的分離,在新空間的生產中逐漸喪失熟悉的“自我感”,換句話說,居民的生活實踐被各種由生活空間抽象出來的符號所支配和主宰,從而不得不遵守空間中的種種規則。
“我”在和“熟悉的陌生人”或者說“他我”的交流互動中產生了復雜的相互交織的自卑感與優越感,居民個體的焦慮感則因其不確定性而確定化了,這就更加劇了個體空間的異化以及群體共享價值的割裂。網絡空間本身就是由技術發展推動構建的新型空間,蘊含其中的一切社會關系與空間生產活動自然受到技術的賦權或約束。技術變革的速度往往超前于規范的制定,這就導致了網絡空間的治理往往滯后于技術發展,出現各類網絡沖突失序現象。
空間轉向的表現之一是交往空間的變化。跟傳統社會的自然空間相比,數字社會的社會空間得到了極大拓展。在傳統社會中,人與人都是在固定的地點進行面對面的交往,而在數字社會的空間中,人與人出現了新的交往方式,人們可以在沒有固定地點的虛擬網絡里進行非面對面的缺場式交往。數字社會的空間與時間雖然得到了極大擴展,但居民的日常活動、生活和工作的身體卻仍然依賴于線下的物理空間,且數字社會的空間和自然的物理空間的社會行動,會同時被以往相同相似的思想觀念所主導和支配,從這個思路來看,可以探察線上與線下空間持續不斷通過思想觀念發生著日益繁雜的聯系。
多種網絡群體的產生與形成是空間轉向的第二個表現,社區網民在網絡空間中因交流溝通和互動逐漸形成共識,使得居民間的情感和價值維系的有限空間變得無限,社區中分散的獨立的個體和一些群體被重新整合,形成了網絡群體。雖然他們的利益訴求各不相同,價值取向和追求也千差萬別,但這些被凝聚起來的網絡群體成員在溝通、互動的過程中,同樣會起到互相影響、社會動員的作用,并且很有可能在網絡虛擬空間中形成集體的狂歡與興奮。這不僅能夠引發網絡輿論能量聚集、能量爆燃,對社會輿論走向產生影響,還可能會引發大量網民的現實行動,形成網絡缺場行為和特定場所中的在場行動之間的聯動關系,進而形成更加難以掌控的不確定性。在這種背景下,就需要構建一種基于空間轉向不確定性的新的社區治理的范式。
2.3 自我迷失的本我:公共空間的“缺場”和“社群”
數字技術的日漸普及,使居民生活空間的內涵逐步延伸。人與人之間物理距離的增大及生活節奏的加快,使得人們在缺場的情況下也可以進行交往,居民傳統的日常生活空間也逐漸被網絡空間所支配。在場空間也一再被缺場空間擠壓,使得居民對在場公共空間的感受與使用日漸弱化,公共空間危機也由此產生,且較為嚴重。
隨著居民越來越多地通過網絡進行情感的維系,基于不同特征的網絡社群被構建出來,與此同時,私人空間與網絡空間、“自我”和“本我”的差異,都通過網絡進行彌合。傳統社會居民通過血緣、親緣、地緣等關系形成一定的心理邊界,形成典型的熟人社會。人口的流動性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而增大,社區居民成分變得越來越復雜,很難形成一定的心理邊界,對社區缺乏嵌入感和歸屬感,難以形成“共同體”。數字社會的建設,更進一步拓展了社區居民的物理邊界,但心理邊界更加難形成。
空間轉向促進了各種網絡群體的形成。傳統社會中,人們的群體關系的發生要求人們共同“在場”,多種互動場景則由物理空間所提供。而在新興的網絡空間,即使居民缺場,也能與其他人進行交往。
缺場交往時,語言與信息在網絡中出現,并能被最大化地減少限制。因此,居民在網絡空間中逐漸演變出一種新的對象化形態,即數字自我,其本質是數據體,來自居民的行為和意識的數字化表達及數字化痕跡。基于這種虛擬性,他們的身份和角色很容易被隨意塑造出來,并具有難識別、難追溯的特點,因此網絡空間中滋生了大量具有多種角色、不明身份的甚至和現實自我相差甚遠的數字自我。
數字自我是數字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有人卻把數字自我變成了與自己不同的對抗性形態,割裂成現實自我的對立面。很多網民受網絡群體的影響,表現出“盲動主義”,與生活中的理性自我形象不符,其慣性也延伸到現實生活中,使現實與網絡的界限日漸模糊。因平臺和算法對部分網絡行為的引導,致使數字自我與現實自我差距更大,從而造成網民在創造和經營多個數字自我形態中徹底迷失。
3. 從空間轉向到空間彌合的社區治理之道
3.1 強化鄰里信任,重塑鄰里空間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區建設不能光靠錢,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1]。“兩鄰”理念關注的焦點是重塑新時代社區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強調社區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要守望互助,實現社區治理的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社區關系最基本的就是鄰里關系,這是建立人際信任的開始,也是和諧社會的基礎。
現如今,幾乎每個城市社區都是一個小型的陌生人社會,社區居民來自不同地域,缺少傳統親緣和地緣信任基礎。同時,由于居民相對封閉的居住方式的影響,其自我防護意識進一步強化,時刻保持著疏離和警惕。盡管物理距離很近,心理距離卻很遙遠,情感冷漠,信任度低。居民之間不相識、不往來、不走動,關系疏遠,樓上樓下甚至是隔壁鄰居,都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網絡社會中,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的藩籬被缺場交往打破,可以說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這樣一個虛擬的網絡社會有時表現卻非常真實,甚至比在場社會更加真實。這正是不在場的特性使人們敢于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而現實社會中的在場交往,人們卻可能受到各種制度、權力、社會等因素的制約,而呈現出很多偽裝與假象,如官話、套話、虛情假意、口是心非等。而網絡社會中的道德規范、社會規范是由所有平等的個體共同建構的,反而使得人們能夠更加互相信任。
因此,我們可以通過搭建數字化社交溝通平臺,創造不同類型的鄰里空間,通過虛擬空間的交往,結合現實的社會交往,拉近鄰里之間的距離及關系,強化鄰里信任,重塑良好的鄰里空間,讓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油然而生。歸屬感的形成需要兩個空間因素:一是“家”的空間,二是鄰里空間。社區歸屬感與鄰里關系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社區居民之間可以通過不同的微信群進行交往,逐漸形成了網絡空間各種不同的社群,幾乎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疫情期間小區居民們通過微信群互通信息,一起團購日用品,這種新式的鄰里關系大大拉近了人們之間的距離。這些群體的淺層關系會逐漸影響到社區的鄰里關系,使鄰里關系更加親近。
3.2 再造公共空間,織密網絡共同體
數字社會建設過程中,社區公共空間[2]由傳統的社會空間向網絡空間轉向。空間的轉向,導致在場群體的邊界消解,地域性治理被突破,新的生活場景創造著新的連接形式。這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再造社區公共空間。社區公共空間再造,即在現有的社區特色與建筑格局的基礎上,對社區空間進行融合,通過提高社區多元主體參與度,重新建構各主體間的角色、關系,推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增進社區交往和認同等多種形式,重新塑造社區公共空間,從而達到其“公共性、服務性和交往性”作用的過程[3]。
隨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發展,社區公共空間以現實社會公共空間(如圖書室、閱覽室、展覽館等)為基礎,根據不同部門、主題設立不同的社交媒體平臺(如微信公眾號、微信群、討論組等),從而構成虛擬的公共空間。這些社交平臺上信息流動性更強,討論范圍更廣。線下傳統公共空間和數字化網絡空間相互交織、疊加與融合,從而形成新的社區交往場景。線上跨越時空的缺場交往給予居民交往的便利,線下面對面的在場交往給予居民以感情維護,通過“現實+數字化”空間的溝通與互動,來消解城市社區生活的封閉性所產生的疏離感,進而實現社區居民在場和缺場兩個公共空間及公共生活的和諧與繁榮,織密居民網絡共同體。
社區公共空間再造還要提升多方主體參與度。單一的社會治理主體已經不能適應新時期社會治理的要求。社區治理需要強化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提升居民參與治理的意識,使其參與社區治理的渠道暢達。另外,還要充分發揮志愿者團隊在社區治理中的作用,可以利用大數據,給具有不同專業技能的志愿者匹配相對應的志愿活動,實現志愿者資源的高效利用。微信群的建立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把控不好,反而可能破壞鄰里關系,如涉及各種沖突、負能量的事件在群里的傳播等。這些都是我們在再造社區公共空間、織密居民網絡共同體過程中所需要避免的問題。
3.3 促進空間融合,構建治理共同體
數字社會建設中,社會形態以及社會結構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社區已經不僅僅是物理意義上的地域單元,還是虛擬空間與物理空間的結合體。當今的社區治理自然需要融合線上線下的空間,構建社區治理共同體。由于互聯網的去中心化特性,社會正在被重新發現且正在自我發現,公民與國家及社會在互聯網上的力量格局正在發生逆轉。同時,網絡空間與現實社會空間已經逐漸達到同步或異步對應。許多網絡群體性事件都與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相互關聯,事件的發展也都是在現實社會空間與網絡空間進行交織互動。因此,網絡空間許多問題的根源在社會現實空間之中、現實社會里,這就是現實社會意見癥候群的網絡社會空間影像。
2021年,國家發改委發布《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要求逐步引入社會組織及社區志愿者等共同參與社區治理。新興網絡技術的產生與融入,給社區治理機制體制及理念等各方面的調整帶來了契機,從而加速推進了城市社區智治的進程。傳統的線下互動渠道的影響力逐漸減弱,快節奏的日常工作狀態對社區居民產生了極大影響,使得他們在生活空間和公共空間之間沒有有機融合,出現了“兩張皮”的情況。數字技術讓居民跑腿變成了“數據跑腿”,使社區治理更加智能化、便捷化。如,公眾號、小程序及微信群等有利于為居民提供在線的公共交往空間。社區政務等信息及時通過線上線下雙渠道向社區發布,實現社區與居民間的信息暢達,也方便居民進行監督,助推社區多元主體間的協同聯動,從而實現社區參與的機制化與系統化,助推社區治理共同體構建。
結語
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新興科學技術,為新時代社區治理提供了高效智能的技術工具,助力我們推進智慧政務、智慧社區建設。如“互聯網+社會治理”“大數據+鐵腳板”“網格+網絡”等模式,都是探索基層治理的新模式。綜上,空間視角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構建社區治理共同體。
參考文獻:
[1]習近平總書記在遼寧省沈陽市沈河區大南街道多福社區考察時的談話[N].法制日報,2013-09-02.
[2]林曉珊.空間生產的邏輯[J].理論與現代化,2008,(2):90-95.
[3]曾莉,周慧慧,龔政.情感治理視角下的城市社區公共文化空間再造——基于上海市天平社區的實地調查[J].中國行政管理,2020,(1):46-52.
作者簡介:陳石英,碩士,助教,研究方向:數字化轉型及新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