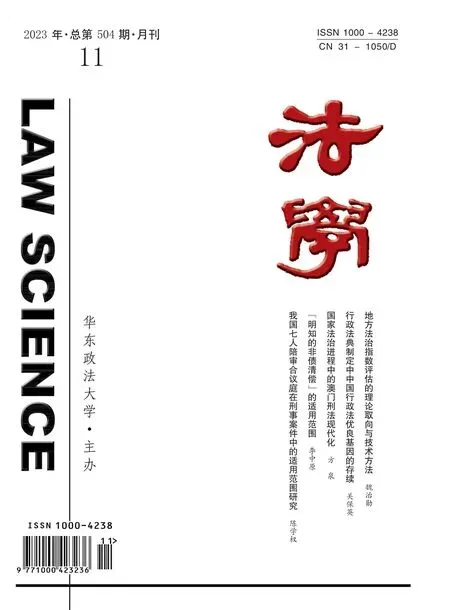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探究
●孫靖洲
肖像許可使用合同是肖像商品化的法律工具,包括使用肖像推銷產品或服務,或者直接利用自然人形象謀取利益。所有類別的許可使用合同都是通過將生產要素許可給他人使用而獲得物質或非物質收益,其目的是通過契約自由優化資源配置。然而,我國《民法典》為肖像許可使用合同設立了特殊的規則,具體包括禁止轉讓肖像權、要求法院對爭議條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以及賦予肖像權人基于“正當理由”的特殊解除權(《民法典》第992 條、第1021 條、第1022 條第2 款)。不難看出,這些規則不僅限制當事人自治,而且偏離合同法一般原則。對此,我國學界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人格利益優先于財產利益,即相對于肖像使用的財產利益,肖像權人的人格權益應當被優先考慮。〔1〕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人格權編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253 頁;王利明:《人格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296 頁。第二種觀點認為,肖像權人在與商業實體進行談判時通常處于弱勢地位,法律需要為其提供更多的保護措施,以彌補雙方的權力差距。〔2〕參見陳甦、謝鴻飛主編:《民法典評注·人格權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241-242 頁。這兩種觀點均存在可商榷之處。
人格利益優先的觀點雖然道明了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特殊規則的立法本意,但沒有說明何種人格利益應當如何被優先保護,這導致實踐中鮮少適用肖像許可使用特殊規則,〔3〕例如,有關“練習生”的演藝經紀合同通常會包含長期且獨占的肖像許可使用條款,但法院對此基本不會給予特別關注。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6)滬01 民終3998 號民事判決書;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2015)虹民一(民)初字第3275 號民事判決書。雖然上述糾紛發生在《民法典》頒布前,但在《民法典》生效后,法院依舊未考慮“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以及賦予肖像權人基于“正當理由”的特殊解除權等法律規則。參見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2)京03 民終14881 號民事判決書。而在僅有的相關判決中,人格保護水平不一、交易安全性較低等問題也較為突出,關于肖像權人的處分權能、對爭議條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以及肖像權人基于“正當理由”的特殊解除權等法律規定均亟待理論澄清。須特別保護弱勢肖像權人的觀點實質上與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人格保護屬性無關,而是為了維護交易的實質公平。換言之,肖像許可使用合同規則的運用完全取決于交易雙方的強弱之勢。這與《民法典》設置該規則的初衷不符,也與現今流行的肖像商品化場景不相匹配。
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作為肖像權人自治高度發展的產物,對其人格利益予以保護何以必然?應如何設置其人格保護規則以合理解決自治和人格尊嚴的沖突?正因為針對這些問題的學理研究付之闕如,學界對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護規則的設立和調整尚缺乏共識,〔4〕參見李宇:《十評民法典分則草案》,載《中國海商法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6 頁;徐滌宇、張家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評注(精要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1056 頁。也導致實務界極易陷入或者過度保護人格權益而忽視交易安全,或者重視交易安全而弱化人格權益保護這兩種境地。鑒于此,本文首先探究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護規則的屬性,闡明人格保護規則的目的和特征,后者為現有研究所普遍忽視,卻為后續形塑人格保護規則提供理論基礎。其次,反思既有相關規則的價值預設和保護效果,針對《個人信息保護法》中“可撤回的同意”規定對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影響,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最后,區分締約和合同履行兩個不同階段,在充分吸收比較法經驗且遵循已有立法和解釋構架的基礎上,運用法教義學充實和調整既有規則。
一、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護規則溯源及其屬性
在肖像商品化場景中,肖像許可使用合同體現了肖像權人以一種受拘束的方式處分其人格利益的意思表示,是其與相對人基于共同意志而對合作關系的形塑。通過履行合同,肖像權人既能獲得財產收益,又能實現向外界展示和表達自我的精神利益。可見,承認肖像權人針對其人格利益的自主決定即體現了對其人格的保護;相反,過度偏向肖像權人的人格保護規則會顯著提高肖像權人尋覓合作伙伴的難度和成本,其甚至不得不通過讓渡更多的財產利益以換取合作機會。〔5〕See Brian Bix, Contracts, in Franklin Miller & Alan Wertheimer (eds.), The Ethics of Consent: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51-280.從這一點看,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恐將成為限制肖像權人事業發展和人格自由的桎梏。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明確在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引入人格保護規則的正當性和必要性。
(一)人格權一元理論的基礎與內在要求
我國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立基于人格尊嚴價值優先的立法選擇。〔6〕參見王利明:《人格尊嚴:民法典人格權編的首要價值》,載《當代法學》2021 年第1 期,第9、12-13 頁。一方面,當個人自治與人格尊嚴發生沖突時,個人自治須讓位于人格尊嚴。因此,肖像權人不得轉讓肖像權,其與相對人自愿排除特殊解除權的合同約定亦應無效。另一方面,當財產利益的實現與人格尊嚴的保護產生沖突時,后者亦被優先保護。于是,在當事人對肖像許可使用條款的理解產生爭議時,應作出有利于肖像權人人格權保護而非有利于相對人債權保護的解釋,肖像權人也可基于人格發展的需要隨時解除有期限的肖像許可使用合同。
然而,個人自治是人類尊嚴的應有之義。限制個人自治,即否認每個人是其個人事務最好的管理者,本身就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對個人理性和人類尊嚴的貶低。道德的最高原則是承認人作為理性和自主性的存在,進而認可人們在思想和行為上的自主決定和自我負責。〔7〕Vgl. Immanuel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Einteilung der Rechtslehre, 1797, zitiert nach der von Wilhelm Weischedel (hrsg.),Werksausgabe, 1997, Bd. VIII, S. 345.與之相應,立法者應當以尊重個人自主決定的方式維護人類尊嚴和人格自由發展,即法律應當允許人們自由地選擇和追求其目標,并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該目標。〔8〕Vgl. Heinrich Hubmann, Das Pers?nlichkeitsrecht, 1967, S. 175.換言之,尊重人格尊嚴也即尊重肖像權人自主和多樣的利益排序和追求。
正是源于人格尊嚴與個人自治的內在關聯,以及人格權益保護和交易安全維護的密切聯系,一味強調人格尊嚴和人格權益相對于個人自治和交易安全的優先性,既不能合理解決它們之間的沖突以實現利益平衡,也難以實現法律保護人的主體性和優先性的目標。誠然,完全承認自主意愿對法律關系形成的決定作用,秉持“意志高于理性”的自治原則,極易使人格利益受制于財產利益,進而導致人淪為商品。〔9〕See Jennifer Rothman, The Inalienable Right of Publicity, 101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85, 205 (2012).以美國的人格利益保護二元模式為例,其通過隱私權保護自然人獨處的精神利益,將“公開權”(the right of publicity)即商業性利用個人肖像、姓名等身份標識的排他性權利設定為財產權,允許其自由流轉。〔10〕See Edison v. Edison Polyform Manufacturing Co., 73 N. J. Eq. 136, 67 A. 392 (1907); 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97 Supreme Court 2849 (1977); Melville B. Nimmer, The Right of Publicity, 19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3-223 (1954); California Civil Code, Section 3344.這種二元模式雖然通過充分尊重個人自治而顯著降低交易成本,使資源配置得以最大程度地實現優化,但會使人們終局性地喪失對自己身份標識的控制力,進而嚴重制約其自我展示和自我表達的能力。例如,美國法院認定包含10 歲童星裸照在內的公開權轉讓合同合法、有效,〔11〕See Shields v. Gross, 58 NY 2d 338.平臺可以通過“用戶協議”免費或以極低的報酬永久地獲得用戶所有的公開權〔12〕See Dancel v. Groupon, Inc., 940 F. 3d 381, 383 (7th Cir. 2019); Perkins v. LinkedIn Corp., 53 F. Supp. 3d 1190 (2014); Fraley v.Facebook, Inc., 966 F. Supp. 2d 939, 944 (N. D. Cal. 2013).即為著例。
概言之,人格尊嚴作為個人自治的終極目的,內在于人格權利的積極利用之中,而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正是實現該價值選擇的保障措施。換言之,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護規則的設置,關乎能否合理解決個人自治和人格尊嚴的沖突,以及充分平衡人格權益保護和交易安全維護。從另一個角度看,則需要剖析人格權的本質以及權利主體處分人格權的目的。在為權利主體保留不可讓渡的人格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允許其個人自治空間隨著科技、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倫理道德觀的變化而持續拓展,以自我決定和自我負責的方式處分人格利益并最終達致促成人格發展與成熟的結果。
我國的人格權保護取徑于德國的人格權一元理論(monistische Theorie),即由于人格權所蘊含的財產利益和精神利益不可分割,因此人格權也必須同時涵蓋其財產利益和精神利益,即一元權利。〔13〕Vgl. Horst-Peter G?tting, Pers?nlichkeitsrechte als Verm?gensrechte, 1995, S. 138 f.; Benedikt Buchner,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im Privatrecht, 2019, S. 218 ff.自然人不能轉讓人格權中的財產利益,因為其與精神利益相互交融且相互影響。肖像商品化的運行邏輯正是將消費者對肖像主體的注意、喜愛或信賴“轉移”到產品或服務上,其價值基礎是肖像權人的形表、身份、人品、聲譽和影響力等完整的人格利益。〔14〕參見楊立新、林旭霞:《論人格標識商品化權及其民法保護》,載《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1 期,第78 頁。因此,對人格標識的利用也是對整體“人格利益的許可使用”(我國《民法典》第993 條)。〔15〕參見王利明、程嘯:《中國民法典釋評·人格權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55 頁;楊立新:《人格權法》,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193 頁。譬如,肖像、姓名等人格標識盡管具備財產利益,但也是自然人形成自我、認識自我和表達自我的工具,對它們的使用在具體場景下會影響自然人人格的形成和社會身份的建構,因此,權利人不能與肖像權、名稱權等已經客體化的人格權利相分離。〔16〕參見孫靖洲:《德國肖像商品化權:淵源與流變》,載《德國研究》2021 年第4 期,第134 頁。
以作為普遍現象并被廣泛接受的肖像商品化為例,一方面,為防止他決,即肖像權人只能被動接受他人的商品化行為并通過侵權損害賠償獲得救濟,法律應當允許民事主體基于自主意愿而積極利用肖像,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展示和表達個人形象;〔17〕參見王利明:《人格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296 頁。另一方面,為維護自決,法律必須確保肖像權人的處分符合其真實的自主意愿,并且永遠保有人格自由發展的可能性。于是,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旨在使肖像等人格標識盡可能地保留于主體自我決定的范疇。〔18〕Vgl. G?tting/Schertz/Seitz, Handbuch Pers?nlichkeitsrecht, 2018, § 10 Rn. 16.
不少美國學者也認識到權利主體保有公開權對實現個人自治的重要意義,認為將公開權定性為財產權屬于對其正當理據的誤認。就權利基礎而言,無論是洛克的勞動理論還是以市場失靈為基礎的激勵理論都不能證成公開權。〔19〕See Dogan & Lemley, What the Right of Publicity Can Learn from Trademark Law, 58 Stanford Law Review 1161 (2006). See also Michael Carrier, Cabi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rough a Property Paradigm, 54 Duke Law Journal 43-44 (2004).根據勞動理論,明星在成名之路上的勞動即使值得保護,其價值也難以全部歸功于名人自身的努力。運營團隊的“包裝”和“粉絲”對“愛豆”(idol)的貢獻通常是偶像商業價值的主要來源,因而勞動理論難以解釋公開權緣何由明星獨享。激勵理論的正當性在于公開權可以激勵更多的人投身娛樂產業,從而促進文化娛樂市場的繁榮,而如果允許第三方不付成本、坐享他人的明星價值,則會使社會公眾承擔“搭便車”行為的負外部性,即文娛市場的萎縮。姑且不論是否需要激勵如此之多的有生力量進入娛樂市場,單就公開權闕如而言,文娛市場大概率也不會陷入缺乏明星的困境,因而激勵理論難以立足。
探究公開權的起源,可以發現其與隱私權是人對人格標識自決權的一體兩面。“隱私權之父”沃倫和布蘭代斯從作者享有決定是否公開自己作品的權利入手,證成個人有權決定是否和如何公開私人事務是一項普通法原則。〔20〕See Waren &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4 Harvard Law Review 198 et seq. (1890).但由于沃倫當時備受小報記者的侵擾,其僅討論了該普通法原則在消極防御層面的意涵,未能論及個人自治的積極利用層面,即公開權的權利基礎。〔21〕See Felix Cohen, Transcendental Nonsense and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35 Columbia Law Review 815 (1935).質言之,公開權保護人們選擇對外展示個人事務以及以多少對價進行公開的權利。因此,僅關注公開權的財產屬性就會遮蔽其在流轉過程中對權利主體精神利益的影響。例如,當脫衣舞俱樂部在社交媒體上使用模特的照片宣傳其場所,某醫生的肖像被用來給治療性功能障礙的藥物做廣告時,權利主體的隱私權和公開權就會同時受到侵害。〔22〕See Geiger v. C&G of Groton, Inc., No. 3:19-CV-502 (VAB), 2019 7193612 WL (D. Conn. Dec. 26, 2019); Lopez v. Admiral Theatre, Inc., No. 19 C 673, 2019 WL 4735438 (N. D. Ill. Sept. 26, 2019); Underwood v. Doll House, Inc., No. 6:18-cv-1362-Orl-31GJK,2019 WL 5265263 (M. D. Fla. Aug. 15, 2019); Yeager v. Innovus Pharm., Inc., No. 18-cv-397, 2019 U. S. Dist. LEXIS 18095 (N. D. Ill. Feb. 5,2019).于是,有美國學者主張限制公開權的永久轉讓,并賦予權利人在特殊情形下解除合同的權利。〔23〕See Jennifer Rothman, The Inalienable Right of Publicity, 101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85, 205 (2012); Barbara Bruni, The Right of Publicity as Market Regulator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41 Cardozo Law Review 2231-2232 (2020).究其原因,公開權的行使亦有邊界,即人不能以放棄自由的方式實現自由。〔24〕See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Batoche Books, 2001, p. 212 et seq.; Joel Feinberg, Legal Paternalism, 1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5 (1971); Gerald Dworkin, Paternalism, 56 The Monist 64 (1972).
(二)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護規則的法律家長主義屬性
美國學者詹姆士·Q.惠特曼關于歐陸法上的人格權維護尊嚴而美國法上的隱私權捍衛自由的觀點固然正確,〔25〕See James Q. Whitman, The Two Western Cultures of Privacy: Dignity Versus Liberty, 113 Yale Law Journal 1151-1221 (2004).但是忽視了自由與尊嚴的內在聯系。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就是以對個人自治一定程度的否定來擴充人們實現自我價值的選項,進而促成人格尊嚴作為終極目的在法律上的實現。〔26〕參見楊立新、林旭霞:《論人格標識商品化權及其民法保護》,載《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1 期,第78 頁。這種像父母保護孩子一樣,通過否定個人選擇以防止其受到傷害并使其過上“好的”生活的法律安排,具有鮮明的“法律家長主義”(legal paternalism)特征。〔27〕See John Kleinig, Paternali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66.一方面,世界各國普遍承認并積極運用具備正當理據的法律家長主義。〔28〕“法律家長主義”規范多見于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勞動法》等保護性法律和法規。例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為保護債務人,認定其與銀行簽訂的高利貸合同無效;〔29〕Vgl. BVerfG 19.10.1993, NJW 1994, 36 [38].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為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而干涉勞動合同的契約自由。〔30〕See West Coast Hotel Co. v. Parrish, 300 U. S. 379 (1937);Owen Fiss, Why the State?, 100 Harvard Law Review 790-794 (1987).另一方面,具備正當性的法律家長主義也會因超出必要性或一味迎合立法者的價值偏好而喪失合理性。〔31〕See David Shapiro, Courts, Legislatures, and Paternalism, 74 Virginia Law Review 546 (1988).法律家長主義的濫用不僅忽視了個人追求的自主性和多樣性,而且極易因過度保護而成為人們理性發展的桎梏,甚至會因罔顧社會現實而適得其反。因此,學界普遍要求嚴格審查法律家長主義的設立條件,確保其具有正當理據、積極的保護效果和必要性,以避免法律對當事人自由意志的不當干預。〔32〕參見黃文藝:《作為一種法律干預模式的家長主義》,載《法學研究》2010 年第5 期,第13 頁以下;Joel Feinberg, Legal Paternalism, 1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5 (1971).
鑒于此,須參考家長主義的設立條件,謹慎設定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人格保護規則,以協調私法自治所保障的消極自由和法律干預所追求的積極自由。〔33〕參見易軍:《民法基本原則的意義脈絡》,載《法學研究》2018 年第6 期,第57 頁。為此,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在設立上應遵循下述原則。
其一,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旨在盡可能將人格權利的自決保留于主體自我決定的范疇。這種對肖像權人的特殊保護與肖像權人在合同關系中的強弱地位無關,但在解釋和適用規則時仍需要考慮雙方在信息掌握和法律地位上的對稱性,因為一個人越難以作出理性判斷,其錯誤選擇的后果越嚴重,法律家長主義保護的正當性也就越強。〔34〕Vgl. Eidenmüller, Eきzienz als Rechtsprinzip, 4. Aufl., 2015, S. 384 f.例如,在韓國“偶像練習生”產業中,大多數“練習生”都是未成年人,其對復雜的演藝經紀合同缺乏足夠的認知和理解能力,更難以準確意識到動輒上百萬元的違約金和十幾年的合同期限對其人身的拘束力乃至對其人生發展的影響。〔35〕在韓國發達的“偶像練習生”產業下,年輕人為獲得專業訓練和參加比賽、演出的機會,通常不得不與大型的經紀公司簽訂長期、無報酬且包含巨額違約金的“奴隸契約”。See Lucy Williamson, The Dark Side of South Korean Pop Music,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pacific-13760064, last visit on May 20, 2023.此時,法律可以考慮介入當事人的締約過程,通過設置權利保留規則幫助肖像權人充分理解其權利處分變動和后果,并在合同履行階段通過解釋規則保障肖像權人對其人格利益的控制力。
其二,肖像權人理性自治水平的提高是人格保護規則具備積極保護效果的體現,即肖像權人可以通過管理肖像利益控制行為后果并承擔自主責任。在實踐中,通過寬泛解釋“正當理由”,或者以肖像權人事后的主觀標準作出“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雖然可以強化對肖像權人人格利益的保護,使其免于承受錯誤決定帶來的不利后果,但是,于挫折中鍛造心理韌性也是自治能力發展和人格成熟的重要方式,對肖像權人的過度保護無疑會使其談判能力和締約理性難以進步和發展。〔36〕See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Batoche Books, 2001, p. 252; Duncan Kennedy, Distributive and Paternalist Motives in Contract and Tort Law, 41 Maryland Law Review 640 (1982).因此,人格保護規則應盡量避免對合同法律效果進行直接干預,而應通過事前規則和柔性規則豐富肖像權人管理肖像利益和控制相對人行為后果的方法。
其三,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應當通過學理和教義學予以構造,僅在必要時對肖像權人的自主意愿作出限制和調整。在實踐中,藝人經常會與經紀公司簽訂“一攬子”人格標識獨家許可使用合同,將其所有依法可以商品化的人格標識全部許可給經紀公司使用,由后者經營管理,包括與企業和廣告商的營銷合作,以及針對第三人侵權行為的維權訴訟等。〔37〕參見張紅:《人格權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版,第246 頁;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2)京03 民終14881 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21)京0105 民初25623 號民事判決書;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0)渝01 民初1035 號民事判決書。該類許可的優勢十分明顯,不僅能顯著簡化雙方的交易過程、提高交易效率,還可以使二者各司其職、豐富文化娛樂產品的供給。因此,不問是否存在其他更為緩和的手段亦能實現防止肖像權人讓渡重要人格利益的目的,而是直接禁止肖像權人給予此類許可,不僅可能違背肖像權人的真實意愿,而且有超出必要性之嫌。〔38〕See David Shapiro, Courts, Legislatures, and Paternalism, 74 Virginia Law Review 546 (1988).
其四,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既要與合同法等民法教義相協調,也要關照肖像商品化的發展。在實踐中,藝人與經紀公司簽訂的肖像許可使用合同(條款)一般包含在演藝經紀合同中,而后者涵蓋范圍廣,還包括有關職業規劃的委托合同、培訓和演出合同等,所以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人格保護規則不應嚴重偏離合同法的一般規則,而應以合同整體作為依據,根據具體情勢進行調整,力圖形成與其他權利義務協調一致的解釋方案。
二、對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護規則價值預設的反思
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不僅來源于《民法典》中特殊的肖像許可使用合同規則,還存在于《個人信息保護法》中的個人信息保護規則。雖然兩者都基于人格保護的目的而干涉肖像權人的自治,但亦存在嚴重沖突。于是,既需要對《民法典》中肖像許可使用合同規則的價值預設進行闡釋和反思,也有必要分析并應對《個人信息保護法》中同意規則對肖像許可使用合同提出的挑戰。
(一)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護規則的價值預設及其反思
在我國《民法典》中,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雖然僅有3 條,但是分別在締約和合同履行兩個不同階段保護肖像權人的人格利益。在締約階段,肖像權人不得轉讓肖像權,只能許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而不能許可他人制作和公開肖像(《民法典》第1018 條第1 款)。在合同履行階段,當對“肖像使用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時,法院應當作出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民法典》第1021 條);在合同存在明確期限時,肖像權人可基于“正當理由”隨時解除肖像許可使用合同(《民法典》第1022條第2 款)。
上述人格保護規則的價值預設即在于精神利益需要絕對保護,以及一般性地將肖像權人定位為合同關系中的弱者。〔39〕參見王利明、程嘯:《中國民法典釋評·人格權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306 頁。詳言之,由于肖像的制作、使用和公開所指向的肖像利益性質不同,所以似有必要限定許可的客體以保護精神利益完滿無虞。通過將原本處于私密狀態的肖像置于可被不特定且數量不少的人接觸到的狀態,肖像的公開關涉肖像權人精神利益的保護,因此不宜作為許可的客體。〔40〕參見王澤鑒:《人格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141 頁。肖像的制作是指將自然人的外部形象固定在有形或無形載體上的再現行為(《民法典》第1018條第2 款),其關注的是肖像從無到有的生成過程,因而保護的利益寬泛且抽象,甚至可以包括自然人不受監控或偷拍的行動自由和隱私利益。〔41〕參見王利明:《人格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283 頁;BGH GRUR 2009, 150 - Karsten Speck; GRUR 1957,494 - Sp?theimkehrer; GRUR 1967, 205 - Vor unserer eigenen Tür.因此,肖像的制作也不適宜直接作為許可的客體。在實踐中,商業實體與肖像權人經常面臨信息和權力的不對稱,所以有必要以犧牲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為代價保護肖像權人,實現利益平衡。〔42〕參見王利明主編:《中國民法典評注·人格權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272 頁。肖像權人的特殊解除權即是著例。再如,法院通常認為,除非有明確約定,否則不承認肖像許可使用合同包含了對商業使用肖像的許可,以防止肖像權人因不了解行業規則而錯誤處分了人格利益。〔43〕參見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縣人民法院(2019)云2922 民初370 號民事判決書;北京互聯網法院(2022)京0491 民初20902號民事判決書。
然而,反對上述價值預設的理由更為充分。其一,依據行為所關涉的利益性質“分而治之”的做法,看似可以使肖像權人的精神利益不受許可拘束,但是該理解既不符合人格權一元理論,也難以與生活實踐相契合。肖像權人的精神利益和財產利益不可分割且相互交融地構成了肖像利益。在典型的肖像商品化案件中,也只是肖像權人的財產利益立于臺前而精神利益隱于幕后;〔44〕所謂典型的肖像商品化案件是指使用者以積極和美化的方式,未經同意而商業使用肖像權人的肖像。Vgl. BGH GRUR 2000, 709 - Marlene Dietrich; BGH NJW 2021, 1311 - Urlaubslotto.而且允許他人商業使用肖像亦可基于肖像權人的精神需求。在實踐中,大量的肖像商品化合同均包含肖像的制作和公開,如廣告肖像合同、人體模特合同等。〔45〕參見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2015)閔民一(民)初字第20354 號民事判決書;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粵03 民終17807 號民事判決書;湖南省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永中法民三終字第465 號民事判決書。人為割裂商業實踐以尋求不同類型的授權實不可取。其二,肖像權人并不當然處于弱勢地位。明星等專業人士普遍具有較高的談判地位。隨著網絡平臺特別是社交媒體平臺的發展,傳統的經紀公司不僅要與新出現的多頻道網絡(Multi-Channel Network,MCN)競爭,而且要與自主運營賬號的“網紅”爭奪商業資源,它們在娛樂產業和廣告宣傳上的壟斷優勢逐漸被削弱。〔46〕參見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3)京03 民終984 號民事判決書;河南省柘城縣人民法院(2022)豫1424 民初1743 號民事判決書;崔國斌:《姓名商品化權的侵權認定思路》,載《清華法學》2021 年第1 期,第121 頁。與此同時,許多新興MCN 機構的專業程度和資源優勢均較低,經常會因沒有明確約定合同履行時間、范圍等重要內容而承受法律上的不利益。因此,商業實體相較于肖像權人的優勢地位已經不再顯著。
究其根源,既有規則的價值預設產生于對司法裁判經驗的總結和提煉,因而偏向于采用原則規定和事后干預對不平等的肖像許可使用合同進行糾偏。然而,為實現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護規則的目的,與其預設“資強勞弱”的交易環境而強調合同實質公平的形塑,毋寧通過彈性和柔性的規則保障肖像權人對人格利益自決的控制,并提高其實現個人自治的能力。
(二)個人信息保護規則的價值預設與沖突化解
在肖像商品化場景下,對肖像權人和相對人契約自由更為極端的干預可能來自個人信息保護規則。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13 條第1 款第1 項和第15 條第1 款)與歐盟《個人數據保護條例》(GDPR)都允許信息主體隨時撤回同意,以終止信息控制者的信息處理活動。由于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和GDPR 都沒有在法律協調適用方面作出特別規定,〔47〕德國舊《聯邦數據保護法》(Bundesdatenschutzgesetz)規定了有關肖像權法律的優先適用性,但由于GDPR 沒有類似的法律適用條款,其與德國法上肖像權乃至人格權的沖突問題至今仍懸而未決。且肖像屬于個人信息,所以可撤回同意的強制適用可以讓肖像權人隨時從有期限的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解脫”出來,并且無須給出任何理由。換言之,如果認為個人信息保護規則在適用上具有優先性,肖像許可使用合同對肖像權人而言將不再具有拘束力,人格保護規則亦無創設之必要。〔48〕See Jingzhou Sun, Personality Merchandising and the GDPR: An Insoluble Conflict?, 2022, p. 206 et seq.
可見,個人信息保護規則與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護規則的目的一致,均旨在使人格利益盡可能地保留于主體自我決定的范疇。兩者發生沖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價值預設不同。在個人信息處理的場景下,信息主體囿于其專業知識和風險預見能力,難以充分理解信息處理活動對自身的影響以及信息控制者提供的隱私保護水平的高低;〔49〕Vgl. Hans Peter Bull, Sinn und Unsinn des Datenschutzes: Pers?nlichkeitsrecht und Kommunikationsfreiheit in der digitalen Gesellschaft, 2015, S. 75 ff.而且讓信息主體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閱讀、理解和比較不同信息控制者提供的隱私保護承諾,并在充分知情的基礎上作出理性選擇既難以實現,也是對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50〕See Daniel J. Solove, Privacy Self-Management and the Consent Dilemma, 126 Harvard Law Review 1892-1893 (2013).因此,立法者將信息主體對個人信息的處分模式限制為可撤回的同意,使信息主體在認識到信息處理的問題后可以即時撤回同意以保護個人信息。可見,可撤回的同意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在信息控制者頭上以警示其極其不穩定的法律地位。反觀在肖像商品化場景中,交易雙方的專業水平和風險承擔與預見能力大致相當,結構性矛盾也并不突出。更為重要的是,穩定的法律關系亦符合肖像權人和商業實體共同合作、互為成就的利益訴求。
職是之故,不應將“數據家長主義”(Datenpaternalismus)的規制毫無保留和修改地套用至肖像商品化場景中。〔51〕Vgl. Christoph Kr?nke, Datenpaternalismus, Der Staat 3 (2016), 319.據此,有學者提出通過限制個人信息保護規則的適用范圍,〔52〕參見施鴻鵬:《任意撤回權與合同拘束力的沖突與協調》,載《政治與法律》2022 年第10 期,第174 頁;Malte Engeler, The EDPB’s Guidelines 02/2019 on Art. 6(1)(b) GDPR, Privacy in Germany, 151-152(2019).或是確認肖像許可使用合同規則的優先適用性,〔53〕參見楊芳:《肖像權保護和個人信息保護規則之沖突與消融》,載《清華法學》2021 年第6 期,第126-127 頁;Schantz, in:Simitis et al., Datenschutzrecht, 2019, Art. 6 Rn. 32.排除可撤回的同意在肖像商品化場景中的適用。然而,上述觀點未能明確可撤回的同意與許可合同的關系及其適用范圍。在前述美國社交媒體平臺案中,平臺就主張將隱私保護協議認定為包括公開權的許可使用或轉讓在內的合同,從而確立信息主體承諾的拘束性。
為解決上述問題,有學者提出將同意視作肖像權人基于許可使用合同而負擔的給付義務,進而肖像權人可基于個人信息保護規則隨時撤回同意,但在無正當理由時,可能會因怠于履行許可使用合同的給付義務而產生違約責任。〔54〕參見林洹民:《個人數據交易的雙重法律構造》,載《法學研究》2022 年第5 期,第41 頁;鄭觀:《個人信息對價化及其基本制度構建》,載《中外法學》2019 年第2 期,第497-498 頁;Riesenhuber, Die Einwilligung des Arbeitnehmers im Datenschutzrecht, Recht der Arbeit (2011), 257, 258.該觀點的可商榷之處在于,可撤回的同意應有獨立的法律基礎和地位。一方面,在生活中大量的照片分享場景中,肖像權人的同意都不具備其愿意受該意思表達拘束的含義。另一方面,對使用許可過于寬泛的認定很可能導致信息主體動輒承擔違約責任,這并不符合個人信息保護規則設置可撤回同意的本意。〔55〕同上注,鄭觀文,第498 頁。
為給予同意獨立的法律地位,有學者主張重新定義同意,認為其包含可撤回的同意和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兩個含義:當肖像權人的同意意指后者時,就不能隨時撤回同意;而當肖像權人的同意不具備拘束意思時,就可以類推適用個人信息保護規則。〔56〕參見程嘯:《論人格權的商業化利用》,載《中國法律評論》2023 年第1 期,第52 頁;楊立新:《人格權法通義》,商務印書館2021 年版,第348 頁。細究之下,該觀點也存在可斟酌之處。其一,肖像權人給予的是可撤回的同意還是使用許可仍有待確認。更重要的問題是,在肖像商品化過程中發生爭議時,肖像權人可否主張其給予的是可撤回的同意而非使用許可,且因該爭議屬于對使用條件的爭議而要求法院采取有利于其的解釋。其二,可撤回的同意源于個人信息保護規則,其在民法教義體系上的地位從何而來也有待說明。
“同意”(Einwilligung)指當事人不得就自己同意遭受的損害獲得補償。〔57〕法諺“volenti non fit iniuria”出現在《學說匯纂》(Ulp. D.47.10.1.5)中,所涉及的案例是一個自愿為奴隸的人就不能再主張別人對他的侮辱具有違法性。See Terence Ingman, A History of the Defence of Volenti Non Fit Injuria, 26 Judicial Review 2 (1981).因此,同意一直作為排除行為不法的理由而鮮少受到民法學者的重視。然而,同意之所以能夠排除他人行為的違法性,是因為自然人有依其意志處置事務的權利,并且他人的行為是根據其要求實施的。〔58〕Vgl. Canaris,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 1971, S. 428; Mayer-Maly, Fikentscher & Lübbe-Wolf,Privatautonomie und Selbstverantwortung, in: Lampe (hrsg.), Verantwortlichkeit und Recht - Jahrbuch für Rechtssoziologie und Rechtstheorie,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1989, S. 277.換言之,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民事主體可以通過同意處分利益或者行使權利,同時需要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59〕Vgl. Joerden, Drei Ebenen des Denkens über Gerechtigkeit: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einiger rechtsethischer Regeln und Prinzipien, Das 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1988), 307, 314; Ansgar Ohly, volenti non fit iniuria - Die Einwilligung im Privatrecht, 2002, S. 143.這也被稱為同意的積極含義,〔60〕參見劉召成:《人格權法上同意撤回權的規范表達》,載《法學》2022年第3期,第83頁及以下;萬方:《個人信息處理中的“同意”與“同意撤回”》,載《中國法學》2021 年第1 期,第177 頁。并通過“允諾的階梯”(die Stufenleiter der Gestattungen)理論加以具體化和教義化。〔61〕Vgl. Ansgar Ohly, volenti non fit iniuria - Die Einwilligung im Privatrecht, 2002, S. 143 ff.
具體而言,根據權利人的允諾對其自身拘束力的強弱,“允諾的階梯”理論將其由高至低地排列為“繼受讓與—設權讓與—設定負擔合同—可隨時撤回的同意”。詳言之,“繼受讓與”(translative Rechtsübertragung)是指使權利人完全喪失權利的轉讓行為。“設權讓與”(konstitutive Rechtsübertragung)是指在權利主體不變的前提下,只轉讓使用權、用益物權等從原始權利中派生出的子權利。設定負擔合同意味著權利沒有發生轉移,相對人僅獲得了針對權利人的債權。對權利人拘束力最弱的是可撤回的同意(狹義的同意)。〔62〕Vgl. Ansgar Ohly, volenti non fit iniuria - Die Einwilligung im Privatrecht, 2002, S. 147-177.可見,允諾即廣義的同意,可以涵蓋民事主體所有的行權模式。我國《民法典》也在廣義的語境下使用“同意”一詞。例如,共有人的同意可以實現對共有的不動產的處分(《民法典》第301 條),民事主體通過同意可處分身體權和健康權(《民法典》第1006、1008 條),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可以讓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法律行為生效(《民法典》第145 條第1 款)。
據此,狹義的同意(或稱可撤回的同意)也是權利人處分自己利益的方式之一,即權利人向相對人表明其雖然可處分自己的利益,但自己亦得隨時撤回同意而使其后續的處分行為轉為非法。狹義的同意的可撤回性意味著權利人既不受法律對意思表示撤回的限制,〔63〕例如,患者無須在同意到達醫生之前撤回,而是可以隨時撤回針對診療手段的同意。這同樣適用于《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同意的定義。也不能與法定解除權混淆。〔64〕例如,歐盟第29 條工作組(數據保護工作組)明確要求,數據主體在撤回同意時無須負擔任何賠償責任,以防止數據主體憚于行使撤回權。See WP 29 Opinion 4/2010 on the European Code of Conduct of FEDMA for the Use of Personal Data in Direct Marketing (WP 174) and the Opinion on the Use of Location Data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Value-added Services (WP 115).由是觀之,可撤回的同意可以顯著增強權利人對相對人行為的控制力,通過塑造“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法律效果,確保權利人的決定得到實時貫徹。譬如,對親密行為的同意就是可撤回的同意,而且相對方不能在伴侶撤回同意后要求其賠償自己的損失,因為可撤回的同意沒有為其創造出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相對方對可撤回同意的接受就意味著其接受了法律地位的不確定性。
在肖像使用的場景下,如果肖像權人給出的是可撤回的同意,那么其撤回無需類推適用個人信息保護規則,亦無須給出正當理由或承擔違約責任。與之相反,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成立基礎必須是肖像權人具有拘束力的意思表示。可撤回的同意雖然能使相對人的行為合法化,但其特性排除了成立合同的法律效果。我國《民法典》為肖像許可使用合同設立的人格保護規則不能適用于可撤回的同意,因為肖像權人不能既主張自己訂立了合同,又認為自己的同意不具有拘束力。誠然,根據私法自治原則,如果相對人認可,可撤回的同意也可作為肖像商品化的法律基礎,但是這與肖像商品化的價值預設和追求的穩定法律關系不相符。換言之,可撤回的同意雖然從法律上強化了肖像權人對人格權益的控制,但很可能“迫使”肖像權人通過讓渡更多的核心利益來補償相對人失去的交易安全。基于上述考慮,除非存在明確的約定,肖像商品化的法律基礎應排除可撤回的同意。
立基于“允諾的階梯”理論,本文建議對個人信息保護規則中可撤回的同意與肖像許可使用合同進行體系解釋,將可撤回的同意作為肖像權人處分肖像權益時的“安全網”:當作為合同主義務的肖像制作、使用和公開等行為為履行肖像許可使用合同所必需時,該肖像許可使用合同即為信息控制者處理個人信息的合法基礎(《個人信息保護法》第13 條第1 款第2 項),可撤回的同意不能適用;在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約定的肖像處理活動不符合《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的必要性要求時,對超出必要范圍的肖像處理活動適用可撤回的同意,允許肖像權人隨時撤回同意以保護其對個人信息的強控制力。〔65〕See Jingzhou Sun, Personality Merchandising and the GDPR: An Insoluble Conflict?, 2022, p. 240 et seq.; Andreas Sattler,Personenbezogene Daten als Leistungsgegenstand, JuristenZeitung (2017), 1036, 1043.值得注意的是,僅憑在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有所約定,并不能證明具體的肖像處理活動是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而應當遵循信息處理的必要原則,審查具體的肖像使用行為與實現肖像許可使用合同所期達成目的之間的相關性和必要性,確保肖像權人僅在必要范圍內受其使用許可拘束,而此處的協調性可以通過“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來實現。〔66〕See Jingzhou Sun, Personality Merchandising and the GDPR: An Insoluble Conflict?, 2022, p. 242.
三、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締約階段的人格保護規則及其調整
為使肖像等人格標識盡可能地保留于主體自我決定的范疇,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可以提前介入當事人的締約階段,通過對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形式和內容提出彈性要求,使交易雙方在合同訂立之時,就充分知曉肖像權人愿意以何種方式讓渡何種肖像利益以實現何種人格發展目的。與此同時,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還應明確肖像權人不能讓渡的人格核心利益,即對肖像等人格標識的自決權,并通過缺省規則豐富肖像權人管理其人格利益的方式,保障肖像權人在授權后仍然可以施加對人格利益的持續控制,而不是只能在“忍無可忍”后解除合同。
(一)肖像許可使用合同成立的必要之點
《民法典》對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成立要件并無特別規定。《廣告法》雖有廣告主須獲得肖像權人書面同意的規定,〔67〕《廣告法》第33 條規定:“廣告主或者廣告經營者在廣告中使用他人名義或者形象的,應當事先取得其書面同意。”但因其旨在“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第1 條),所以書面性作為對廣告主和廣告發布者施加的合規義務,不應成為民法上的效力性強制規定。〔68〕參見王紹喜:《〈民法典〉時代肖像權保護解釋論》,載《法律適用》2021 年第11 期,第30 頁。由于肖像許可使用合同屬諾成合同,而肖像商品化往往涉及拍攝、(廣告)制作、宣傳等一系列商業活動,并且各個階段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因此雙方經常就是否存在商業許可使用發生爭議。對此,法院的判決也迥然不同:有法院認為肖像權人參與選美比賽即是對后續商品化的許可;有法院則主張接受“宣傳大使”證書不能使企業對肖像的商業利用合法化,肖像權人對廣告制品的稱贊也不表示其給予肖像使用許可。〔69〕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757 號民事判決書;浙江省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浙湖民終字第458 號民事判決書;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縣人民法院(2019)云2922 民初370 號民事判決書。
這些實踐難點皆源于人們尚未就肖像許可使用合同成立的必要之點達成共識。通說認為,合同的成立不需要當事人就《民法典》第470 條列舉的所有合同內容達成合意,僅需在必要之點上達成一致即可,并且應當根據合同的類型確定該類合同的必要之點,以實現私法自治。〔70〕參見韓世遠:《合同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103 頁。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作為肖像權人愿意以何種方式讓渡何種肖像利益以達成何種人格發展目標的意思表示,肖像的使用范圍、許可類型和對價構成其成立的必要之點,而其中又以對價最為重要。
首先,對價關系(quid pro quo)作為契約最核心的要素,能夠說明肖像權人為獲得對價,愿意以一種受拘束的方式處分肖像利益。〔71〕See Jed Lewinsohn, Paid on Both Sides: Quid Pro Quo Exchange and 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 129 Yale Law Journal 3 (2020).有觀點將肖像權人的職業作為判斷標準,認為職業模特因了解行業規則而接受拍攝邀約即意味著許可合同成立。〔72〕參見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2015)閔民一(民)初字第20354 號民事判決書;湖南省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潭中民一終字第46 號民事判決書;徐滌宇、張家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評注(精要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1056 頁;張紅:《民法典之肖像權立法論》,載《學術研究》2019 年第9 期,第67 頁。然而,以商業授權作為其收入來源的專業模特應更注重授權內容,不會含糊其辭地放棄其“生存利益”,何況以職業為判斷基準的觀點已稍顯過時。在一起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糾紛案中,二審法院也認同“童星”原告及其母親的觀點,認為一審法院將原告同意拍攝認定為肖像許可使用合同成立存在錯誤,因為雙方尚未就費用達成一致。〔73〕參見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陜01 民終4354 號民事判決書。
其次,對價的高低也可以幫助判斷肖像許可使用的范圍。例如,國際明星受邀參加宣傳活動和接受小禮品,當然不能被認定為給予了相對方代言許可,〔74〕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757 號民事判決書。但公司可以將明星的照片掛在宣傳欄里。〔75〕Vgl. BGH GRUR 1992, 557 ff. - Joachim Fuchsberger.又如,100 元的報酬不能構成將照片印在2 萬張音樂節門票和數個巨幅展板上的授權,但可以使經紀公司的宣傳冊合法化。〔76〕參見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縣人民法院(2019)云2922 民初370 號民事判決書。對價不等同于報酬,而是包括任何財產性利益。以剛入行的模特常與專業攝影師簽訂的“免費約拍”合同為例,前者獲得后者的專業指導和免費提供的場地、服裝,應當認為其許可包含允許攝影師使用前者肖像宣傳自己的工作室,否則,后者無法利用其作品補償自己付出的時間和勞動,這種互惠的商業實踐將不會再存續,初出茅廬的模特也更難以發展事業。〔77〕參見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粵01 民終16859 號民事判決書;LG Frankfurt am Main, Urteil vom 30.5.2017 - 2-03 O 134/16 - Time-for-Print-Vertrags.值得注意的是,在沒有報酬的情況下,相對人需要承擔舉證責任,證明肖像權人為什么愿意在沒有報酬的情況下允許其商業性使用肖像。〔78〕參見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閩民申4015 號民事判決書;北京互聯網法院(2022)京0491 民初20902 號民事判決書;四川省樂至縣人民法院(2021)川2022 民初65 號民事判決書。
最后,對價的內容也與許可類型緊密相關。在僅創設負擔義務的普通許可模式中,相對人支付的對價往往僅為金錢或其他金錢性給付,例如拍攝和底片服務。而獲得排他許可或獨家許可的相對人通常需要支付的對價更為復雜。具體而言,藝人為從龐雜的經營管理工作中解脫出來,更專注于演藝工作,會通過授予相對人(通常是經紀公司)排他許可或獨家許可的方式,賦予被許可人對抗第三人的權利,乃至對抗肖像權人自己商業使用肖像的權利。與之相應,相對人需要履行經營管理藝人形象、規劃演藝事業和維護合法權益等義務。可以說,商業使用肖像的對價內容越豐富,肖像權人與相對人的利益關系就越復雜,所選擇的許可類型也可能呈現對肖像權人更強的拘束力。
由此,通過對相對人支付的對價進行綜合考量,可以判斷肖像許可使用合同是否成立,即肖像權人是否以一種受拘束的方式處分了自己的肖像利益。這相當于在肖像商品化的場景下對一般合同成立要件進行了簡化適用,以順應日益頻繁和“生活化”的肖像商業使用之發展趨勢。盡管這可能導致在司法實踐中更容易認定存在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但不會影響肖像權人的人格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會幫助其更加重視和珍惜自己的形象。一方面,這可以促使相對人積極主動提供報酬,讓肖像權人了解自己的肖像在市場中的價值,并使其參與肖像使用的談判而提升理性自治的能力。另一方面,無期限合同中的隨時解除權實際上賦予肖像權人隨時反悔的權利。在相對人未明確期限利益但給予肖像權人報酬時,例如,餐廳要求顧客在社交媒體上發送用餐照片,推廣、宣傳餐廳以獲取優惠,應當認為雙方之間成立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但肖像權人可以隨時解除合同,且其在履行合同義務之后要求解除的,餐廳不能要求肖像權人返還優惠。
(二)“拘束性權利轉讓”許可的缺省規則
如前所述,排他性或獨占性的肖像許可使用在商業實踐中屢見不鮮。雖然有學者持禁止肖像權人給予此類許可的見解,因為設權讓與模式不僅會使肖像權人與創設的子權利相分離,而且會減損肖像權人因人格保護規則而享有的保護水平;〔79〕參見王澤鑒:《人格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297 頁;王利明:《人格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121 頁。但是排他性或獨占性的肖像許可使用是社會專業化分工的必然結果,它可以通過為相對人提供更為獨立和穩定的法律地位,鼓勵其投入更多的資源以實現權利人的自主意愿。作者與出版社的圖書出版關系即為著例,前者需要后者投入大量的出版和宣傳資源以實現自己“名利雙收”的愿望,而出版社也需要作者提供相對完整和長期的授權以保障自己的經濟利益。于是,為解決作為一元權利的著作權不能與著作權人分離,且需要特別保護其中人格利益的問題,德國學者為著作權許可發明了“拘束性權利轉讓”(gebundene Rechtsübertragung)模式,以實現著作權人對轉讓的使用權的控制。根據“拘束性權利轉讓”模式,被轉讓的子權利在內容、時間和空間上都受權利人目的的拘束,而且與保留在權利人手中的母權利緊密相連并受后者的影響和控制,因而權利人在有充分理由(正當理由)時可以隨時收回其轉讓的子權利,而且子權利在其所保護的利益喪失后也自然回歸至母權利的主體手中。〔80〕Vgl. Forkel, Gebundene Rechtsübertragungen, 1970, § 6 VII, S. 44 ff.
由此,可以考慮在同為一元權利的肖像權許可使用類型中引入“拘束性權利轉讓”模式,即在肖像權人給予相對人排他性許可或獨家許可時,被許可人雖然獲得了對抗第三人的權利,但是其所獲得的權利范圍須受肖像權人目的的拘束,而且受始終保留在肖像權人手中的肖像權的影響和控制。〔81〕Vgl. Forkel, Lizenzen an Pers?nlichkeitsrechten durch gebundene Rechtsübertragung,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1988), 491, 494;黃芬:《商品化人格權的定限轉讓》,載《河北法學》2017 年第1 期,第67 頁。“拘束性權利轉讓”不僅可以順應肖像商品化實踐需求,而且能在擴大肖像權人自治空間的前提下有效保護其人格利益。需要注意的是,“拘束性權利轉讓”的前提是人格利益的客體化。從目前來看,它只適用于肖像、名稱和姓名等已經被普遍承認的、作為商品而在一定程度上與民事主體分離的人格標識。
設權讓與類許可合同對肖像權人的拘束力極強,且合同履行時間一般較長,所以有必要在締約階段就引入人格保護規則,這主要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目的:一是為提示肖像權人審慎處分權利,實現理性自治;二是為在一段較長的周期內使肖像利益仍盡可能地保留于肖像權人自我決定的范疇;三是為合理平衡肖像權人的人格利益與相對人的信賴利益。
從提示肖像權人權利變動的范圍和效果角度出發,可以考慮類推適用《著作權法》中將合同成立與合同內容、形式相關聯的規定,要求設權讓與類許可合同應為要式合同,強制要求該合同列明許可使用人格標識的種類以及使用權的可轉讓性(第27 條),并且要求再轉讓須獲得肖像權人的同意。由此不難看出,書面合同實際上賦予肖像權人在簽訂肖像許可使用書面合同前的反悔權,旨在督促其謹慎、嚴肅地對待權利。當然,將設權讓與類許可合同規定為要式合同并不意味著雙方的口頭協議無效,而是對后者適用對肖像權人拘束力更弱的處分模式,即債權合同,這意味著此時相對人不得主張該許可的對世效力,而只能獲得債權請求權。
在恢復肖像權人的自治地位層面,可以參考德國有關肖像商品化合同的司法實踐,為肖像權人創設一些合同權利以豐富其管理和控制肖像利益的方法和手段,用以對抗經紀公司因過于注重商業和短期利益而作出與藝人價值觀抵牾或違背其身份認同的商業決策。〔82〕Vgl. G?tting/Schertz/Seitz, Handbuch Pers?nlichkeitsrecht, 2019, § 38 Rn. 44 f.; Pfaff/Osterrieth, Lizenzvertr?ge:Formularkommentar, 2018, S. 407 ff.在實踐中,因投資的階段性和手中藝人資源的豐富性,經紀公司很容易忽視單個肖像權人的人格發展和長期利益,所以授予排他性許可的肖像權人急需對自身形象規劃的最終同意權,以防止“營銷翻車”“偶像失格”的情況出現。〔83〕例如,某對明星夫妻分別代言不同品牌的奶粉,并表示他們的孩子只喝自己所代言品牌的奶粉。這種明顯虛假的產品代言會嚴重損害兩位名人的可信度。參見《郎朗和妻子吉娜代言不同品牌奶粉,網友:他家孩子到底喝哪個》,https://www.sohu.com/a/477418700_99930840,2023 年5 月20 日訪問。除此之外,關于賬目信息的知情權對于長期合同而言也較為重要,因為它既可以保證肖像權人隨著自身形象價值的提升而獲得相應的合理收益,還可以在違約糾紛發生時有效抗辯相對方索取畸高的違約金。〔84〕Vgl. Schertz, Merchandising: Rechtsgrundlagen und Rechtspraxis, 1997, Rn. 405.
總體而言,相對于事后的解釋規則和解除權,事前的形式要求和權利保留更有利于維護交易安全和肖像權人的聲譽。一方面,明確約定雙方權利義務的書面合同可以證明被許可人享有肖像使用權或轉授權的權利,方便其經營管理和后續授權;在發生爭議時,書面合同還能夠幫助法院還原雙方的談判過程和目的,使其根據合同目的解釋雙方的權利義務。另一方面,解除權的行使無疑會破壞交易相對方的市場預期和雙方的信賴關系,肖像權人在市場中的聲譽通常也會被損害。相反,肖像權人的最終同意權和對賬目信息的知情權均有助于使相對方的使用行為服務于肖像權人的人格發展目標,不必以兩敗俱傷的代價保護其人格利益。
四、肖像許可使用合同履行階段的人格保護規則及其調整
相較于合同締約階段的柔性和彈性規則,肖像許可使用合同履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雖然能夠有效保障肖像權人對人格利益自決的控制,但因屬于事后規則而極易損害交易安全。因此,僅應在必要時對肖像權人的自主意愿予以限制和調整,以實現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護規則的本旨。同時,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也需要與合同法的一般規則相協調。
(一)對爭議條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
針對《民法典》第1021 條規定的對爭議條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規則,有學者主張排除合同解釋的一般規則以加強人格權益的保護,〔85〕參見程嘯:《人格權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122 頁。也有學者提出僅在肖像權人與相對人地位顯著不平等時適用該條規定,〔86〕參見徐滌宇、張家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評注(精要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1056 頁;陳甦、謝鴻飛主編:《民法典評注·人格權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241-242 頁;張紅:《民法典之肖像權立法論》,載《學術研究》2019 年第9 期,第67 頁。還有學者針對具體爭議作出回應。〔87〕參見王利明:《人格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296-297 頁。可見,目前學界不僅對該條的立法意旨認識不同,而且在有利于肖像權人的判斷標準上也存在分歧。這導致實踐中對爭議條款的解釋,時而以某一類人的價值偏好為標準,片面認為對精神利益或財產利益的保護有利于肖像權人;時而以肖像權人的事后主張解釋合同條款,忽視其在訂立合同之時的意思表示。這不僅嚴重損害了交易安全和相對人的信賴利益,亦是對肖像權人在合同訂立之時自主決定的否定。尤為重要的是,《民法典》第1021 條雖然僅要求對“肖像使用條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但其涵蓋范圍可謂相當寬泛,包括使用類型、內容、時間、對價和效果等,甚至賠償責任、競業禁止條款亦可被納入其中。因此,有必要明確和統一“有利于肖像權人”的判斷標準,以形成適用于所有“肖像使用條款”的解釋標準;否則,對肖像權人的保護極易導致“贏了戰斗,輸了戰爭”的結果。
依據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護規則的本旨,對合同的解釋應使肖像等人格標識盡可能地保留于主體自我決定的范疇。這意味著對發生爭議的“肖像使用條款”的解釋,既要以具體的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目的為基礎,確保肖像權人能夠實現當時處分肖像利益的具體目的;又要將肖像權人處分的人格利益限制在實現合同目的絕對必要的范圍內,以保障對肖像等人格標識的自決權盡可能地保留在肖像權人的手中。
具言之,肖像許可使用合同是肖像權人實現個人自治并確立社會身份的工具,其目的具有自主性、多元性和多樣性。因此,首先需要根據合同解釋的一般規則確定發生爭議的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目的,具體的方法包括分析合同內容,考察合同訂立的背景以及行業內和雙方的交易習慣等因素。〔88〕參見謝鴻飛:《〈民法典〉法定解除權的配置機理與統一基礎》,載《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0 年第6 期,第26-27 頁。需要說明的是,合同的具體目的是指當事人雙方追求的一致的私法效果,即肖像權人愿受義務拘束而希望達成的具體的人格發展目標。在此基礎上,再對發生爭議的肖像使用條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認定肖像權人僅在實現合同目的絕對必要的范圍內處分了人格利益,除非其明確地表示允許相對人以超出合同目的的方式使用肖像。〔89〕Vgl. OLG K?ln ZUM 2014, 416; OLG K?ln AfP 1999, 377; OLG Hamburg ZUM 1996, 789, 790.
由此可見,“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應當是對合同一般解釋規則的補充而非替代,〔90〕Vgl. Christian Donle, Die Bedeutung des § 31 Abs. 5 UrhG für das Urhebervertragsrecht, 1993, S. 51; Ansgar Ohly, in:Schricker/Loewenheim, Urheberrecht, 6. Aufl., 2020, § 31 Nr. 52.而且該解釋路徑有利于肖像權人。其一,它盡可能地將肖像利益保留在肖像權人的手中。其二,在發生爭議時,它將舉證責任轉移給了相對人,除非后者能夠證明爭議內容為實現合同目的所必需,或是肖像權人給予了明確授權,否則一律認為肖像權人未授予該使用許可。
通常而言,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雙方都因專業性、長時間的合作關系等不會對合同目的進行細致說明。因此,根據合同內容和雙方的交易動機判斷合同的目的尤為關鍵。首先,如果肖像權人通過肖像商品化獲得財產收益的動機非常強(如專業模特),而簽訂的肖像許可使用合同卻沒有約定報酬或者報酬極少,那么在有爭議時就不應當認為該合同包含了肖像商品化,因為這樣的授權條件無法實現肖像權人的目的,除非相對人能夠證明肖像權人為了專業指導或是曝光機會免費授予了商業許可。其次,當肖像權人與經紀公司就授權的排他性存在爭議時,根據“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規則,經紀公司(被授權人)須主動證明排他性的授權方式、授權范圍和時間為實現合同目的所必需。換言之,僅在權利人想要讓相對人獲得對抗第三人的法律地位的目的非常明確時,其才可以選擇以“拘束性權利轉讓”的方式處分其人格利益。譬如,藝人(肖像權人)明確想要從繁雜、瑣碎的經營管理工作中解脫出來,以便更專注于演藝工作;經紀公司為防止初出茅廬的藝人遭遇不公平待遇,需要獲得轉授權許可,以代表藝人與廣告公司等其他商業實體談判。與之相反,動輒長達十幾年的許可期限,乃至對肖像的低俗呈現等,都明顯超出了實現合同目的的必要范圍,甚至無助于肖像權人實現人格發展的具體目標,因此當屬未獲得肖像權人的許可。
(二)肖像權人基于“正當理由”的特殊解除權
針對《民法典》第1022 條第2 款,有學者主張寬泛解釋解除的“正當理由”,允許肖像權人為維護特定形象和保持外界良好評價而隨時行使解除權。〔91〕參見王利明、程嘯:《中國民法典釋評·人格權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313 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人格權編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260 頁。也有學者要求嚴格解釋“正當理由”以防止其破壞合同信守原則,主張肖像權人(或其親屬)僅在受許可人的違法行為致肖像權人死亡或肖像權人遭受生命威脅時,方可解除合同。〔92〕參見郭少飛:《新型人格財產權確立及制度構造》,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5 期,第52 頁;程嘯:《人格權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121 頁。還有學者提出對《民法典》第1022 條第2 款和規制法定解除權的第563 條進行體系解釋,將“正當理由”理解為合同生效后發生的“重大事由”,主張在個案利益衡量的基礎上,判斷該變化是否導致履行合同義務對肖像權人而言已無期待可能性。〔93〕參見王洪亮:《民法典中解除規則的變革及其解釋》,載《法學論壇》2020 年第4 期,第27 頁;劉召成:《人格商業化利用權的教義學構造》,載《清華法學》2014 年第3 期,第132 頁。另有學者借鑒比較法經驗對“正當理由”進行類型化,包括可以源于肖像權人自身的重大事由,譬如信仰和觀念的重大改變、雇傭關系的結束,以及諸如相對人的重大丑聞、對肖像權人形象的丑化等外部環境的顯著變化。〔94〕參見楊芳:《〈民法典〉第1022 條第2 款(有期限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法定解除權)評注》,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4 期,第44 頁。
綜合比較后可以發現,嚴格解釋雖然有助于糾正寬泛解釋的過度家長主義保護傾向,但將人格利益限制在人身利益的范圍內會顯著減損法定解除權的保護效果,而且難以與《民法典》第990 條對多元化人格權益的廣泛保護相協調。在實踐中,我國法院早已通過創設“酌定解除”,允許藝人以其演藝才能和活動受到嚴重制約為由解除合同。〔95〕參見劉承韙:《論演藝經紀合同的解除》,載《清華法學》2019 年第4 期,第132 頁及以下。肖像商品化合同雖不及演藝經紀合同綜合性強,但其對肖像權人的形象以及人格發展的拘束不亞于后者,因此不宜過分限制“正當理由”的解釋而造成對兩類合同的“保護差”。體系解釋的優點在于回歸解除權的教義基礎,這有利于實現合同雙方的利益平衡,但有狹隘理解“正當理由”構成類型的可能性,有弱化人格權益保護之嫌。此外,如果完全依據個案的利益衡量,那么法院不僅要將合同履行時間、權利人的年齡納入考慮范圍,還需要考量經紀公司在組織培訓、營銷管理以及監管評估上所投入的大量資源和承擔的商業風險。這很可能導致肖像權人依據相同的人格限制理由而主張特殊解除權的結果不盡相同。一方面,這似乎未能體現《民法典》以人的主體性和優先性為基礎的理念;另一方面,對相對人信賴利益的保護可以通過酌定肖像權人的損失賠償金額來實現,無須否定肖像權人的特殊解除權。
基于上述認識,本文主張將解除的“正當理由”置于人格尊嚴和個人自治的整體脈絡下進行解釋。一方面,肖像商品化作為肖像權人實現社會身份和發展事業的重要方式,在其結果與肖像權人對自己所展示形象的預設發生沖突時,必然會對肖像權人的身份認同和職業前景產生消極影響。因此,為維護肖像權人的人格尊嚴和人格自由發展,可以相對寬泛地理解正當理由的構成類型,允許肖像權人基于自身或他人的原因,以及外部環境的顯著變化,從具有拘束力的合同中“解脫”出來。另一方面,由于之前具有拘束力的許可是由肖像權人自主決定的,所以解除權的行使本身就是對其個人自治的否定。于是,肖像權人必須證明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人格保護規則為什么應當允許其推翻之前作出的針對人格利益的拘束性決定,以實現法律保護個人自決的目的。〔96〕Vgl. BAG, Urteil vom 11.12.2014 - 8 AZR 1010/13.質言之,肖像權人“出爾反爾”的理由必須要使法院相信如果不允許肖像權人以相反的方式行使其自決權,法律將人格利益自決權保留在肖像權人手中的目的就會落空。
舉例而言,在德國有女明星曾試圖通過主張解除權阻止雜志社再度刊登其多年前拍攝并許可公開的性感照片。然而,德國法院雖承認肖像權人信仰和觀念的重大改變可以構成解約的正當理由,但是不認為法律有必要通過允許解除合同的方式保護其后續塑造的相反“人設”。一方面,該女星訂立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決定是自覺、自愿的,其當時能充分了解該決定的含義和效果,并且寄希望于通過性感照片開拓事業。另一方面,對人格利益的自決并非賦予每個人按照意愿刪除其過往經歷的權利,更何況早年的性感照片并不妨礙其后續改變和發展新的“人設”。肖像權人沒有令人信服地證明這些照片的再度出版會嚴重影響乃至壓制其人格的自由發展。〔97〕Vgl. OLG München, NJW-RR 1990, 999 - Wirtin; LG K?ln, AfP 1996, 186 - Model in Playboy, 188.
為緩解人格尊嚴和個人自治之間的矛盾,平衡人格權益保護和交易安全維護,本文主張在寬泛理解肖像權人解除的正當理由構成類型的前提下,嚴格審查以此為理由解除合同的必要性,即為維護肖像權人的人格利益是否必須否定其之前的自我決定。由此,《民法典》第1022 條第2 款中的“正當理由”應當指在合同簽訂后出現的、具體而緊迫的、嚴重損害人格利益的事由。例如,如果肖像權人只出現在其受雇公司廣告的背景中,并且在離職后的長時間內都沒有提出反對意見,那么在對相對人具體的合同履行利益與肖像權人受到的一般抽象風險的衡量中,法院需要偏向前者。〔98〕Vgl. BAG, Urteil vom 11.12.2014 - 8 AZR 1010/13.此外,《民法典》第1022 條第2 款對解除合同理由正當性的要求體現了利益平衡的屬性,即法院需要在肖像權人與相對人的對抗性利益之間權衡,以確保在該具體情形下排除肖像權人的違約責任具有客觀正當性。
五、結論
作為規制肖像商品化的制度創新與其他人格權益處分的準用規范,肖像許可使用合同規則集中體現了我國人格權保護理念的發展與變化,同時反映了《民法典》對實踐經驗的制度化。立基于人格權一元理論,立法者以對個人自治一定程度的否定來擴充人們實現自我價值的選項,使自然人在充分享受物質與技術發展福利的同時,實現理性自治和人格多樣化發展。質言之,作為個人自治的終極目的,人格尊嚴內在于人格權利的積極利用之中,而人格保護規則正是實現該價值選擇的制度保障。
基于人格權一元理論,人格保護規則不應建立在精神利益需要特別保護或是一般性地將肖像權人視為弱者的基礎上,而應當使肖像等人格標識盡可能地保留于主體自我決定的范疇。在具體設置人格保護規則時,應盡量避免對合同法律效果的直接干預,通過事前規則和柔性規則,發掘和實現肖像權人的自主意愿,豐富肖像權人管理肖像利益和控制相對方行為的方法,并盡量通過學理發展和教義學構造使其與合同法等民法教義相協調。
為厘清個人信息保護規則中可撤回的同意與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適用范圍,本文主張借助“允諾的階梯”理論對兩者進行體系解釋,在信息主體明確以拘束性方式處分其個人信息時,應優先將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作為個人信息處理的合法基礎,同時將可撤回的同意作為信息主體處分個人信息的“安全網”,即在合同約定的肖像使用范圍超出了實現合同目的所必需的范圍時,默認當事人可隨時撤回關于這部分信息處理的同意。同時,肖像許可使用合同的成立基礎必須是肖像權人具有拘束力的意思表示。可撤回的同意雖然也可作為肖像商品化的法律基礎,但因其既不能實現肖像權人的真實意思,又不能給其帶來實質利益,所以除非存在明確的約定,否則不應認為肖像商品化的法律基礎是可撤回的同意。
為使肖像等人格標識盡可能地保留于主體自我決定的范疇,并僅在必要時對肖像權人的自主意愿予以限制和調整,在梳理比較法經驗、反思本土已有立法和解釋架構的基礎上,本文建議區分締約和合同履行兩個不同階段,運用法教義學方式充實和調整既有規則。具體而言,在締約階段,應將肖像許可使用范圍、許可類型和對價作為合同成立的必要之點,以對價關系作為考察的核心,解釋和判斷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的權利義務關系;引入“拘束性權利轉讓”模式為排他性許可設置必要的形式和內容要求以及缺省規則,保護肖像權人對人格利益的控制和自決能力。在合同履行階段,對爭議條款作出“有利于肖像權人的解釋”,即意味著在發生爭議時肖像權人僅在實現合同目的的絕對必要范圍內處分了肖像利益,并將解除的“正當理由”置于人格尊嚴和個人自治的整體脈絡下進行解釋。在寬泛理解解除的“正當理由”構成類型的背景下,應嚴格審查其必要性,并將其限定在合同簽訂后出現的、具體而緊迫的、嚴重損害人格利益的事由上。通過保障肖像權人始終控制對人格利益的自決權,實現肖像許可使用合同中人格保護規則的制度功能,即合理解決個人自治和人格尊嚴的內在沖突,并平衡人格權益保護和交易安全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