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chǎng)域視閾下的建安文學(xué)
——論田曉菲《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guó)》的還原研究
胡菀麟
(西南大學(xué) 文學(xué)院,重慶 400537)
漢獻(xiàn)帝建安時(shí)期(196—220年)的文學(xué)歷來(lái)頗受海內(nèi)外研究者關(guān)注。在這一領(lǐng)域,陳寅恪、劉師培、周振甫、羅宗強(qiáng)、袁行霈、袁濟(jì)喜、劉躍進(jìn)等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先后從文學(xué)批評(píng)、文獻(xiàn)整理、文人心態(tài)、時(shí)代思想等多個(gè)角度展開(kāi)了精彩論述,鈴木虎雄、青木正兒、傅漢思 (Hans Hermannt Frankel)、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海外學(xué)者對(duì)這一話題亦新見(jiàn)頻出。可以說(shuō),時(shí)至今日,建安文學(xué)的研究成果已然蔚為大觀。在這一過(guò)程中,作為一個(gè)耳熟能詳?shù)奈膶W(xué)概念,“建安文學(xué)”逐漸被程式化乃至單一化地打上“慷慨任氣”“剛健悲涼”的風(fēng)格烙印。然而,田曉菲的《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guó)》(下稱《赤壁之戟》)指出,今日所看到的“建安”是由后世共同建構(gòu)所致,建安文學(xué)在誕生之初與今日呈現(xiàn)的面貌不盡相同,是歷代文人的有意闡釋和意義摘取導(dǎo)致了這樣的改變。[1]從某種程度上說(shuō),田曉菲意欲通過(guò)《赤壁之戟》勾勒建安文學(xué)的形成及流變史,甄別后世文人對(duì)建安文學(xué)所作的刪選加工,還原建安文學(xué)的本然狀貌,從而達(dá)成“撥開(kāi)云霧見(jiàn)天日”的目標(biāo)與效果。因而以該書為例分析得失利弊,或許能為探本窮源的文學(xué)還原研究提供不少啟示。
一、情感偏差與視點(diǎn)下移:社會(huì)場(chǎng)域下的建安文學(xué)
國(guó)內(nèi)較早以場(chǎng)域理論分析魏晉文學(xué)的學(xué)者王欣認(rèn)為,在場(chǎng)域中分析中古文學(xué),有助于迫近觀察文學(xué)走向自覺(jué)的演變過(guò)程。[2]將建安時(shí)期作為中古文學(xué)的起點(diǎn),即是出于對(duì)此時(shí)期特殊社會(huì)空間的考慮。基于建安時(shí)期社會(huì)背景的復(fù)雜性與特殊性,剖析社會(huì)場(chǎng)域下的建安文學(xué)便成為首要一環(huán)。
文學(xué)概念寄寓的情感差別,是社會(huì)場(chǎng)域下建安文學(xué)的突出表征。首先,田曉菲敏銳地感覺(jué)到“建安”“三國(guó)”概念在能指與所指方面存在的偏差——二者指向大致相同的歷史階段,但前者更多地表現(xiàn)為對(duì)文采、文化的懷念,突顯出雅文學(xué)的性質(zhì);而后者更多是對(duì)武德、武藝的書寫,充斥著俗文化的流行氣息。在大多數(shù)國(guó)人的潛意識(shí)里,二者所引起的文化想象截然不同,正是這份割裂感促使田曉菲探析其背后的成因。按照吉川幸次郎的理論,建安時(shí)期發(fā)生了社會(huì)氛圍的轉(zhuǎn)向。[3]群雄逐鹿中原、政權(quán)更迭頻繁的混亂背景,加上瘟疫橫行的不幸現(xiàn)實(shí),共同促進(jìn)了時(shí)代文學(xué)倫理觀念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體現(xiàn)在作者的創(chuàng)作心理方面,即憂時(shí)傷世、緬懷逝者。袁濟(jì)喜教授指出,漢魏士人在經(jīng)歷了長(zhǎng)期戰(zhàn)亂、時(shí)疫和政壇之禍后,逐漸養(yǎng)成了孤獨(dú)心態(tài)。[4]這樣的心態(tài)反映在文學(xué)作品中,即表現(xiàn)為獨(dú)特的孤凄之美。這一時(shí)期的文人受到親友密集死亡的現(xiàn)實(shí)刺激,產(chǎn)生心理震撼,因而文學(xué)作品中人生苦短、及時(shí)享樂(lè)的主題并不鮮見(jiàn)。據(jù)此,田曉菲認(rèn)為建安文學(xué)在誕生之初就已經(jīng)帶有時(shí)代的死亡氣息。正是這種對(duì)時(shí)間的空前敏感,促使建安文人產(chǎn)生了積極立言的心理,被黑暗氣息籠罩的建安才會(huì)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學(xué)理論蓬勃發(fā)展的“活水之源”。而待到西晉、唐宋時(shí)期,社會(huì)場(chǎng)域的再次變動(dòng)促使社會(huì)氛圍再次發(fā)生轉(zhuǎn)向。在這一轉(zhuǎn)向下,建安時(shí)期的主要文學(xué)意象(如銅雀臺(tái))本身所具有的哀傷氣息和文學(xué)內(nèi)涵,也慢慢因后世文人政治傾向上的“反魏”而“變味”——原本寄寓其中的進(jìn)取、簡(jiǎn)樸內(nèi)涵逐漸被奢靡、享樂(lè)替代。后世對(duì)曹魏的道德批判使“建安”呈現(xiàn)出與早期不盡相同的面貌,而“三國(guó)”得益于后世的不斷改造、演繹,逐漸在民間廣泛傳播。對(duì)“建安”和“三國(guó)”這兩個(gè)概念所寄寓情感差異的察覺(jué),是《赤壁之戟》還原研究的獨(dú)到之處。
視點(diǎn)下移,是社會(huì)場(chǎng)域下建安文學(xué)的又一面相。《赤壁之戟》一書第二章論述文學(xué)群體時(shí),作者建議關(guān)注點(diǎn)從建安七子之類的文學(xué)集團(tuán)移開(kāi),轉(zhuǎn)而關(guān)注更多社會(huì)群落,如謀士集團(tuán)、武官階層;同時(shí),書中亦強(qiáng)調(diào)須從文化事業(yè)建設(shè)者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些社會(huì)群落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這一觀點(diǎn)正是國(guó)內(nèi)學(xué)界歷來(lái)所倡導(dǎo)的。多年前,建安文學(xué)的研究對(duì)象集中于三曹七子、鄴下文人集團(tuán),目光也多集中于“建安風(fēng)骨”“文學(xué)自覺(jué)”等論題,而對(duì)魏晉邊緣文人和吳地、蜀地文人缺乏有效討論。對(duì)于這種局面,傳世資料較少固然是重要緣由,但集體無(wú)意識(shí)情境下的習(xí)慣性忽視也應(yīng)當(dāng)引起重視。施建軍教授對(duì)此總結(jié)道:“在解放后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間內(nèi),建安文學(xué)研究偏重于詩(shī)歌研究,對(duì)建安文學(xué)特色的探討幾乎等同于對(duì)建安詩(shī)歌特色的探討,而對(duì)建安詩(shī)歌特色的探討則又幾乎等同于對(duì)‘建安風(fēng)骨’的探討。”[5]基于此,我們可以說(shuō),建安文學(xué)研究若要跳出陳陳相因的結(jié)論循環(huán)和程式沉疴,在現(xiàn)有基礎(chǔ)上引入跨學(xué)科、多視角的方法,實(shí)現(xiàn)對(duì)建安文學(xué)的宏觀把握和微觀補(bǔ)充,不失為一種可行之策。可喜的是,近些年來(lái),隨著學(xué)界的研究視點(diǎn)逐漸下移與泛化,建安文學(xué)研究從文化名流轉(zhuǎn)向普羅大眾儼然成為一種趨勢(shì),對(duì)彼時(shí)流派、群體、社團(tuán)甚至平民的討論也相較此前更為豐贍。這無(wú)疑有助于對(duì)建安文學(xué)進(jìn)行全方位考察,也有助于對(duì)建安文學(xué)進(jìn)行創(chuàng)辟性延展。
二、三方勢(shì)力的話語(yǔ)博弈:文學(xué)場(chǎng)域中的建安文學(xué)
在《赤壁之戟》一書中,文學(xué)場(chǎng)域話語(yǔ)權(quán)斗爭(zhēng)是貫穿全書的敘述主線。誠(chéng)然,在建安文學(xué)的營(yíng)構(gòu)中,曹魏政權(quán)始終掌握較多的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但其中亦彼此穿插、融織著曹魏政權(quán)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建構(gòu)者、助力者以及扭轉(zhuǎn)者三方勢(shì)力的博弈與斗爭(zhēng)。
(一)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的建構(gòu)者
田曉菲明確指出,文學(xué)場(chǎng)域下建安文學(xué)內(nèi)部有“企圖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人”,這個(gè)人便是曹魏政權(quán)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的掌舵人——君主曹丕。目前學(xué)界對(duì)曹丕的文學(xué)研究多集中于詩(shī)歌特色、三曹文學(xué)地位評(píng)價(jià)及“文氣說(shuō)”批評(píng)理論等幾個(gè)“老生常談”的方面。田曉非雖也從曹丕的文學(xué)理論層面入手,但在比較曹丕的“七子”說(shuō)與曹植的“七子”說(shuō)后,她發(fā)現(xiàn)曹丕在創(chuàng)作時(shí)常常對(duì)已逝文人進(jìn)行關(guān)涉,這從側(cè)面反映出曹丕在權(quán)力建構(gòu)之初就已將死亡氣息帶入建安文學(xué)之中,也意欲標(biāo)舉自己于彼時(shí)文壇的霸權(quán)地位。不言而喻,曹丕存在顯豁的文化爭(zhēng)霸之野心,因而他格外重視對(duì)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的爭(zhēng)奪。以文化霸權(quán)理論來(lái)看,誰(shuí)能獲得文化事業(yè)的霸權(quán),誰(shuí)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政治正統(tǒng)性,而政治正統(tǒng)性更確切地反映在誰(shuí)掌握話語(yǔ)領(lǐng)導(dǎo)權(quán)的問(wèn)題上。因此,作為建安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的建構(gòu)者,曹丕基本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文學(xué)、政治、法理等多個(gè)領(lǐng)域的統(tǒng)御。
田曉菲在說(shuō)明曹丕爭(zhēng)奪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的問(wèn)題時(shí),主要將其書信作為例證。建安時(shí)期的尺牘書信遺留較多,國(guó)內(nèi)較早系統(tǒng)討論建安書信文學(xué)的是陳廷玉的《建安文學(xué)尺牘研究》。[6]該文對(duì)建安時(shí)期的尺牘進(jìn)行了詳細(xì)分類,但文中的理論分析較為單薄。而邱曉鵬在對(duì)曹丕的書信進(jìn)行專題研究時(shí),多關(guān)注其文學(xué)主張、藝術(shù)特色而較少討論政治目的。[7]在爬梳整理曹丕的書信、詔書、傳記等多方位資料時(shí),田曉菲特意從公、私兩個(gè)層面關(guān)注曹丕對(duì)增強(qiáng)魏國(guó)文化軟實(shí)力、實(shí)現(xiàn)魏國(guó)文化霸權(quán)的明顯需求。于私而言,曹丕在書信中對(duì)衣食品評(píng)表現(xiàn)出情感分明的個(gè)人喜好。借由書信,曹丕展開(kāi)了與劉禎、繁欽、鐘繇等人的言語(yǔ)角力,力圖在內(nèi)容和修辭等各方面取得全面優(yōu)勢(shì)。田曉菲認(rèn)為這種強(qiáng)烈的勝負(fù)欲、將自身的愛(ài)憎喜好作為統(tǒng)一的強(qiáng)制化行為,正是古代帝王御人術(shù)、文化霸權(quán)的體現(xiàn),是曹丕試圖成為文化支配性力量的嘗試。與此類似,福柯(Michel Foucault)也指出權(quán)力正是通過(guò)“全面禁止”“不得如此”等禁令被應(yīng)用到所有的社會(huì)形式和所有的從屬關(guān)系中。[8]政治精英階層制定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反映的不僅是個(gè)人的審美取向,更是特定群體、社會(huì)、時(shí)代的審美趨向,對(duì)社會(huì)造成的影響廣泛而深遠(yuǎn)。于公而言,田曉菲由記錄宴會(huì)的碑文出發(fā),認(rèn)為魏國(guó)頻繁舉行宴飲的原因是該行為具有團(tuán)結(jié)各方、安定民眾的社會(huì)功效。宴會(huì)席上的表演不僅是音樂(lè)雜技的演出,更是一種帶有強(qiáng)烈政治目的的舞臺(tái)展現(xiàn)。田曉菲憑借大量實(shí)證材料,證明了曹丕意圖控制文學(xué)世界的野心,達(dá)到對(duì)曹丕文學(xué)作品進(jìn)行重新闡釋的目的。而這一過(guò)程中,知悉作品情感的背后成因,剝離個(gè)人附著于作品之上的私心企圖,便成為理所當(dāng)然。由此觀之,在研究書信、尺牘等私人文學(xué)作品時(shí),應(yīng)立足于寫作人身份與寫作動(dòng)機(jī),并對(duì)動(dòng)機(jī)之下的隱秘心理進(jìn)行深入思考。此種探究理路無(wú)疑皴染著田曉菲個(gè)性化的研究特色。自《塵幾錄》問(wèn)世以來(lái),她一直堅(jiān)信所有文本皆不能超越其社會(huì)歷史而存在。[9]從《赤壁之戟》一書對(duì)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的分析來(lái)看,這一理念也一如既往地貫穿其中。
(二)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的助力者
對(duì)曹魏集團(tuán)的建安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建構(gòu)而言,當(dāng)代及后世的貴族文人也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有生力量。《赤壁之戟》中同時(shí)討論了曹魏集團(tuán)麾下的臣僚王粲以及進(jìn)入北方文化的南方人陸氏兄弟等幾股力量,對(duì)助力建立曹魏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的各色文人進(jìn)行了詳細(xì)闡釋。
建安時(shí)期,王粲作為傳統(tǒng)世家大族的代表,是“前代文化記憶與文化知識(shí)的傳遞者”[1]80。其不僅在公開(kāi)場(chǎng)合稱贊曹操遠(yuǎn)勝袁紹、劉表,還在酒宴上自覺(jué)扮演“守分豈能違”[1]80的門客角色。從王粲創(chuàng)作的《公宴詩(shī)》等文學(xué)作品中不難看出,其與曹魏集團(tuán)之間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利益共同體關(guān)系。王粲個(gè)人的政治傾向,代表的是建安時(shí)期依附曹魏集團(tuán)、服膺文化權(quán)威的一批世家文人的立場(chǎng),但權(quán)力的流程是動(dòng)態(tài)、雙向的,上下雙方處在一個(gè)動(dòng)態(tài)博弈的過(guò)程中。因此,在分析文學(xué)場(chǎng)權(quán)力關(guān)系時(shí),重點(diǎn)在于觀察統(tǒng)治者與貴族文人之間的依賴形式和結(jié)果。[10]從這一角度來(lái)看,即使王粲等世家文人依附曹魏集團(tuán),他們也深度參與到了曹魏政權(quán)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的建立與鞏固過(guò)程之中。《赤壁之戟》認(rèn)為,君臣宴會(huì)可以被看作一場(chǎng)利益交換活動(dòng)。作為宴會(huì)賓客的臣下(如王粲)需獻(xiàn)詩(shī)以明忠誠(chéng),作為宴會(huì)主人的君主(如曹丕)則為之提供食物等獎(jiǎng)賞以作報(bào)酬。在此過(guò)程中,被助力者需要得到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上的認(rèn)可與支持,助力者亦需要得到相應(yīng)的回報(bào)及保障。
西晉時(shí)期,從東吳來(lái)的陸機(jī)、陸云兄弟出于對(duì)曹魏文學(xué)權(quán)威的仰慕,自發(fā)提供了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上的助力,進(jìn)一步鞏固了曹魏集團(tuán)的文學(xué)霸權(quán)。田曉菲認(rèn)為,他們的“北方書寫”常常表現(xiàn)出對(duì)曹魏王朝的向往和懷舊之情。例如陸機(jī)為曹操遺令打動(dòng),寫下了《吊魏武帝文》。在這篇吊文和序言中,陸機(jī)對(duì)曹操的臨終場(chǎng)面進(jìn)行了歷史場(chǎng)景的想象描繪。此舉不僅意外保存下曹操的遺令,更使得銅雀臺(tái)帶上悲涼的氣氛成為三國(guó)想象的核心意象。于是“這一想象的場(chǎng)景從此成為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中最著名的場(chǎng)景之一”[1]162。陸云則在游歷宮殿場(chǎng)所時(shí)試圖通過(guò)對(duì)“鄴城”的書寫,在逝去的曹魏與當(dāng)下的自身之間建立共同性聯(lián)系。由此可以認(rèn)為,陸氏兄弟也是建安文學(xué)建構(gòu)脈絡(luò)史上的關(guān)鍵文人。
此外,南北朝時(shí)期蕭梁王室的數(shù)位皇子也可被視作曹魏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的助力者。他們?cè)诓芪何膶W(xué)中找到了心理共鳴,進(jìn)而通過(guò)有意識(shí)地在《文選》中篩選、收錄部分文學(xué)作品,將其對(duì)建安的文化想象進(jìn)一步固定。總之,借由對(duì)建構(gòu)脈絡(luò)史上助力者的梳理,田曉菲進(jìn)一步佐證了建安文學(xué)在后世會(huì)發(fā)生嬗變的觀點(diǎn)。
(三)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的扭轉(zhuǎn)者
在文學(xué)與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中,田曉菲充分關(guān)注到權(quán)力的可持久性問(wèn)題。曹魏政權(quán)辛苦建立起的建安文學(xué)統(tǒng)序,正如其政權(quán)命運(yùn)一般,無(wú)法實(shí)現(xiàn)“千秋萬(wàn)代”的永固愿景。失去政權(quán)的庇護(hù),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就難免存在權(quán)力轉(zhuǎn)向的可能。
在梳理建安文學(xué)的建構(gòu)脈絡(luò)時(shí),田曉菲注意到,建構(gòu)者會(huì)不自覺(jué)地帶入自身及其所處時(shí)代的相關(guān)特征。因此她在觀照建構(gòu)者身份的同時(shí),對(duì)建構(gòu)者進(jìn)行了心理分析。例如《赤壁之戟》第三章提到,由東吳進(jìn)入北方的陸機(jī)“把自己的南方身份帶入了北方詩(shī)歌”[1]151。在樂(lè)府詩(shī)中,陸機(jī)強(qiáng)勢(shì)干預(yù)曹魏遺留下的經(jīng)典話語(yǔ),轉(zhuǎn)而融入自己作為南方來(lái)客的身世感想,對(duì)北方樂(lè)府已有的題材進(jìn)行了創(chuàng)新與改寫。在五言詩(shī)、擬古詩(shī)領(lǐng)域,陸機(jī)以詩(shī)歌象喻和重新敘事的方式對(duì)建安留下的文學(xué)作品進(jìn)行再闡釋,以期留下更符合其內(nèi)心對(duì)建安文化想象的作品。最為明顯的是,建安詩(shī)歌所表達(dá)的“南方”與“北方”的地域?qū)α?到了陸機(jī)筆下卻被扭轉(zhuǎn)為“胡”與“越”的種族、文化對(duì)立。陸機(jī)此舉,意在使來(lái)自南方的自己避免站在建安曹魏文學(xué)的對(duì)立面。類似這樣對(duì)北方文學(xué)權(quán)威的種種改寫與重塑,還深切影響到后世蕭梁王朝《棹歌行》等樂(lè)府詩(shī)歌中對(duì)“文化南方”的建構(gòu)。
在陸機(jī)之后,還有謝靈運(yùn)在建安題材詩(shī)歌中透露出的清議色彩,《三國(guó)志》在解讀《短歌行》時(shí)加入的虛構(gòu)描寫,唐代杜牧《詠史》對(duì)赤壁的再闡釋,崔國(guó)輔、李邕、劉商、李賀等人借銅雀臺(tái)表達(dá)對(duì)曹魏的批判,宋代文人對(duì)銅雀瓦硯的書寫以及蘇軾在《赤壁賦》中加入的哲理思辨等顯著例證。歷史不斷變遷,文學(xué)思想的轉(zhuǎn)變側(cè)面反映出曹魏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的旁落。其實(shí),曹魏政權(quán)文學(xué)話語(yǔ)權(quán)發(fā)生扭轉(zhuǎn)這一實(shí)例,正是布爾迪厄所提到的場(chǎng)域策略具體類型中的顛覆策略——場(chǎng)域中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人和顛覆者形成文化斗爭(zhēng)關(guān)系,這樣的關(guān)系反映的是雙方在場(chǎng)域的相對(duì)位置而非具體需求。《赤壁之戟》一書中,作者以文本細(xì)讀的方式,結(jié)合清晰的邏輯理路,于細(xì)枝末節(jié)處將司空見(jiàn)慣的文獻(xiàn)解讀出不一樣的意味。但書中部分結(jié)論較難令人徹底信服,易被認(rèn)為犯了新歷史主義弊病。據(jù)此,學(xué)者冉瑩曾在英文版《赤壁之戟》的書評(píng)中重點(diǎn)思考應(yīng)如何把握建構(gòu)和解構(gòu)的尺度,隨后她提出不應(yīng)過(guò)度迷戀解構(gòu)的建議。[11]論述不足和過(guò)度解讀會(huì)消弭文學(xué)作品本身?yè)碛械膶徝酪馓N(yùn)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這也是田曉菲歷來(lái)飽受爭(zhēng)議的核心問(wèn)題。
三、利益驅(qū)動(dòng)與女性參與:經(jīng)濟(jì)場(chǎng)域里的建安文學(xué)
建安三國(guó)時(shí)期的故事在明、清兩代被不斷改編成戲曲、小說(shuō)、話本,在民間廣泛傳播。改編文學(xué)的流行反映出民眾對(duì)三國(guó)文化的喜愛(ài),但在這一表象的背后,卻是戲班與書商在巨大利益驅(qū)使下的“精準(zhǔn)營(yíng)銷”。圖書出版業(yè)的持續(xù)興旺,使得江南、蜀地、湖廣地區(qū)的刊刻作坊層出不窮,話本小說(shuō)在民間迅速普及。以江南為例,因文人群體較為集中、文化積淀濃厚、藝術(shù)領(lǐng)域成就突出、經(jīng)濟(jì)消費(fèi)水平較高,文化生產(chǎn)多布局于此,文化教育向下層民眾普及的速度遠(yuǎn)超國(guó)內(nèi)其他地區(qū)。這一時(shí)期,書籍消費(fèi)市場(chǎng)的目標(biāo)客戶也逐漸由上層文人轉(zhuǎn)向中下層文人甚至庶民。需求決定市場(chǎng),文學(xué)生產(chǎn)活動(dòng)在逐利本質(zhì)的驅(qū)動(dòng)下,將話本小說(shuō)帶入創(chuàng)作和消費(fèi)的高潮。為了迎合通俗閱讀,書商們開(kāi)始干預(yù)文學(xué)創(chuàng)作。他們?cè)谖膶W(xué)生產(chǎn)中或輔以大量插圖,或?qū)局谱鞒筛∏杀銛y的樣式,或?qū)⑽谋究s減、改編,這些轉(zhuǎn)變無(wú)一例外地導(dǎo)致原本紛繁復(fù)雜的建安文學(xué)逐漸被簡(jiǎn)單化、扁平化,立體飽滿的歷史人物逐漸被臉譜化、娛樂(lè)化,后世對(duì)建安文學(xué)的接受逐漸粗淺化、片面化。在明清經(jīng)濟(jì)場(chǎng)域的干預(yù)下,簡(jiǎn)化版的建安文學(xué)逐漸為大眾讀者所熟知,然而這其實(shí)已是被“多手加工”后生產(chǎn)出來(lái)的文學(xué)成品,與其本然狀貌已相去甚遠(yuǎn)。
同時(shí)還應(yīng)注意,文學(xué)場(chǎng)在場(chǎng)域理論中時(shí)常處于從屬地位,受到來(lái)自政治場(chǎng)、經(jīng)濟(jì)場(chǎng)的擠壓。進(jìn)入21世紀(jì)后,現(xiàn)代的文學(xué)書寫以及當(dāng)今學(xué)者對(duì)古代文學(xué)作品的闡釋已無(wú)法完全排除經(jīng)濟(jì)場(chǎng)的“侵?jǐn)_”。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迅猛發(fā)展使文學(xué)場(chǎng)逐漸向經(jīng)濟(jì)場(chǎng)妥協(xié),經(jīng)濟(jì)場(chǎng)的商業(yè)邏輯進(jìn)一步支配文學(xué)場(chǎng)。[12]這樣的現(xiàn)象同樣延續(xù)至今。雖然布爾迪厄一再?gòu)?qiáng)調(diào)純文學(xué)的非功利性,但經(jīng)濟(jì)場(chǎng)漸趨成為文學(xué)場(chǎng)的主導(dǎo)力量是必須肯認(rèn)的現(xiàn)實(shí)。《赤壁之戟》“余論”處的“東坡赤壁”以及“銀屏赤壁”部分即重點(diǎn)談及當(dāng)下經(jīng)濟(jì)場(chǎng)對(duì)文學(xué)場(chǎng)進(jìn)行影響的種種現(xiàn)象。以歷史影視化問(wèn)題為例,作為一種藝術(shù)創(chuàng)作,歷史影視劇存在虛構(gòu)情節(jié)無(wú)可厚非,但若觀眾疲于思考,也易將歷史影視劇當(dāng)作正史看待,這往往會(huì)導(dǎo)致對(duì)歷史事件的分析和對(duì)歷史人物的評(píng)價(jià)產(chǎn)生一定程度的偏差。又如網(wǎng)絡(luò)同人小說(shuō)、卡牌游戲及同人音頻等建安三國(guó)文化衍生品,顯見(jiàn)這類文化衍生品在市場(chǎng)上具有巨大流量。但應(yīng)該警惕的是,流量背后的資本趨向遵循單一的利益邏輯,在推廣和傳播時(shí)片面追求效率或曝光度,從而對(duì)建安三國(guó)歷史文化進(jìn)行過(guò)度扭曲和改寫。
雖然經(jīng)濟(jì)場(chǎng)域中衍生出種種負(fù)面效應(yīng),但《赤壁之戟》一書也提到了一端益處,即現(xiàn)代女性開(kāi)始參與到建安文學(xué)的同人生產(chǎn)和消費(fèi)中,這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古代眾多文人建立起來(lái)的政治話語(yǔ)體系。然而,田曉菲也發(fā)現(xiàn),創(chuàng)作建安時(shí)期男性文人的同人作品,在直觀反映出女性深度參與到建安文學(xué)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的同時(shí),卻也會(huì)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覺(jué)地強(qiáng)化建安男性的話語(yǔ)權(quán)地位。至于強(qiáng)化過(guò)程、效果如何等問(wèn)題,書中沒(méi)有繼續(xù)深論。這固然會(huì)使得全書在內(nèi)容布置上充滿張力,為讀者敞開(kāi)廣闊的闡釋空間,但也難免造成邏輯線索上的過(guò)度跳躍以及意義生成上的戛然斷裂。不可否認(rèn)的是,田曉菲對(duì)當(dāng)下經(jīng)濟(jì)場(chǎng)域利弊的辯證討論另辟視角,饒有趣味,啟人思考。
四、意義闡發(fā)與辯證看待
對(duì)還原研究而言,《赤壁之戟》一書啟示性意義有三:一是厘清研究對(duì)象的范圍。雖然張朝富教授曾提出建安文學(xué)應(yīng)特指曹魏文學(xué)集團(tuán)而與吳、蜀文學(xué)相分離的觀點(diǎn)[13],但現(xiàn)今學(xué)界仍將魏、蜀、吳等不同地域的文學(xué)劃入建安文學(xué)的研究范圍。既然建安時(shí)期不只存在以三曹為首的北方文學(xué)集團(tuán),那么文學(xué)史研究與文學(xué)史書寫就不應(yīng)忽視對(duì)北方小眾文人以及吳地、蜀地文學(xué)團(tuán)體的討論。例如書中“不像‘建安’的建安”[1]68一節(jié),就注意到阮瑀、陳琳等人的部分詩(shī)歌有著與時(shí)代共性不符的特點(diǎn)。又如書中第三章對(duì)陸機(jī)、陸云兄弟的討論,便是以東吳政權(quán)的視角進(jìn)行切入并展開(kāi)。這類視角如同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側(cè)面寫真,既有助于在區(qū)分中捕捉研究對(duì)象未被關(guān)注到的新特性,也有助于在觀察中還原研究對(duì)象更生動(dòng)、完整的面貌。歸而言之,便是明晰研究對(duì)象所涉及的“面”與辨別“面”中存在的盲點(diǎn)同步推進(jìn)。二是對(duì)研究對(duì)象所涉及的重要概念進(jìn)行多角度觀照。例如對(duì)于建安文學(xué)的“建安”與“三國(guó)”這兩個(gè)概念,田曉菲不僅關(guān)注到二者在文化想象上的割裂,亦看到二者之間存在以詩(shī)歌、酒宴、瘟疫為共同意象的相通之處。《赤壁之戟》第一部分的結(jié)構(gòu)安排即以此為據(jù)。故對(duì)還原研究而言,打破惰性思維,對(duì)研究對(duì)象涉及的基本概念進(jìn)行重新審視,有助于從不為人覺(jué)處掘出新意。三是研究分析可運(yùn)用跨學(xué)科視角,在全景式通覽視野下進(jìn)行多維度展開(kāi)。田曉菲在《赤壁之戟》中對(duì)部分詩(shī)歌的中心內(nèi)涵進(jìn)行了重新解析,并運(yùn)用心理學(xué)理論分析了文人的隱晦心理,還從女性視角重估了元雜劇《隔江斗志》的文獻(xiàn)意義。這些都為建安文學(xué)研究提供了獨(dú)特的視角和新穎的切入點(diǎn),也為推動(dòng)建安文學(xué)研究走向深層次、多元化探討提供了助力。除面向建安文學(xué)研究之外,這些新思維、新路徑、新視角的效用對(duì)其他時(shí)期的文學(xué)研究同樣行之有效。要特別指出的是,《赤壁之戟》最大的優(yōu)勢(shì)便是其通覽式全局視野,這對(duì)今后的文學(xué)還原研究具有范式意義。其價(jià)值不僅在于對(duì)研究對(duì)象進(jìn)行整體性把握以及對(duì)研究路徑進(jìn)行開(kāi)拓性完善,更在于對(duì)研究?jī)?nèi)容的現(xiàn)代意義進(jìn)行深度性開(kāi)掘。如《赤壁之戟》末章對(duì)當(dāng)代三國(guó)同人文學(xué)、電子游戲、電視、漫畫、卡牌游戲廣泛流行的討論,昭示著今人對(duì)建安文學(xué)的建構(gòu)仍在繼續(xù)。此種貫通古今的嘗試,雖有幾分從影響史、接受史角度切入古典文學(xué)研究的意味,但須承認(rèn)的是,此舉確實(shí)有利于增強(qiáng)古典文學(xué)與現(xiàn)代社會(huì)之間的交流,從而有利于糾正古典文學(xué)局限于“古”的狹隘理念。雖言無(wú)古不成今,但今日所見(jiàn)之“歷史”是被歷代共同建構(gòu)出來(lái)的存在。正如敦煌石窟里被層層覆蓋的壁畫,其原始面貌早已被遮蔽,今人所看到的不過(guò)是各個(gè)時(shí)期加工之作的疊加。所以,對(duì)“歷史”若不加擇選地附和,往往會(huì)遮掩真正的史實(shí)原貌;對(duì)“共識(shí)”無(wú)條件式地盲從,也往往會(huì)阻絕更多的詮釋空間。而還原研究的現(xiàn)實(shí)必要與重要意義便由此處生發(fā)。
福柯曾言:“知識(shí)是被權(quán)力建構(gòu)的,而知識(shí)處在變化之中,它不停地轉(zhuǎn)換自身的視角。”[14]歷史雖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要申明的一點(diǎn)是,還原研究仍要格外注意闡釋的尺度問(wèn)題,而不能流于主觀臆測(cè)和過(guò)度解讀。《赤壁之戟》畢竟是以西方的理論結(jié)構(gòu)及研究范式對(duì)中國(guó)古代的社會(huì)現(xiàn)象和文學(xué)作品進(jìn)行分析,在這一分析過(guò)程中,勢(shì)必引起較大爭(zhēng)議。正如陳洪教授所言,徘徊于“還原”與“建構(gòu)”二者之間可能是學(xué)科基本屬性使然,也是一種正常的、良好的狀態(tài)。[15]歷史既已永久消逝于一維性時(shí)空之中,而遺留下來(lái)的文學(xué)作品便成為現(xiàn)今唯一可視、可控、可解的實(shí)際證據(jù),也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實(shí)際存在。所以,還原研究既需要新理論作為獨(dú)特視角,亦需要以文本細(xì)讀為基礎(chǔ)路徑,二者兼顧,方能避免于文本之外過(guò)度闡發(fā),憑借公正平允的事實(shí)依據(jù)逐漸尋回失卻的話語(yǔ)。逝者已矣,后世的建構(gòu)往往表現(xiàn)為一種單方面、永無(wú)回應(yīng)的詮釋。但有趣的是,前人亦未曾將自己全盤交付。蛛絲馬跡隱藏于故紙堆的只言片語(yǔ)間,只待研究者拂去塵埃、一一還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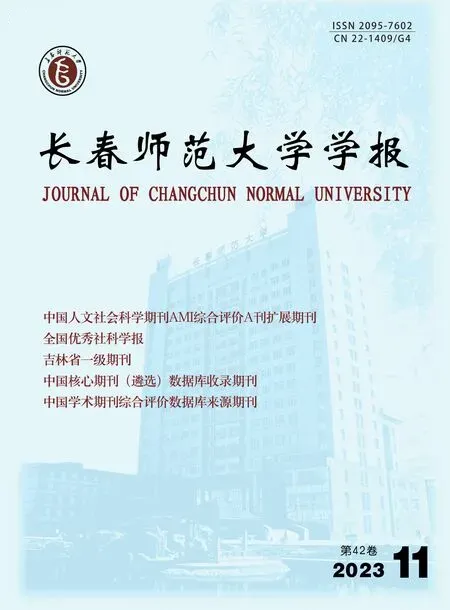 長(zhǎng)春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3年11期
長(zhǎng)春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3年11期
- 長(zhǎng)春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中美英語(yǔ)新聞?wù)Z篇批判性話語(yǔ)對(duì)比研究
——以“人民幣匯率”為例 - 遼代吉林地區(qū)錢幣初探
- 禪思何由潛入詩(shī)
——六朝詩(shī)歌佛源詞尋蹤 - 高中英語(yǔ)閱讀教學(xué)中批判性思維能力培養(yǎng)國(guó)內(nèi)研究綜述
- 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背景下SPOC翻轉(zhuǎn)課堂混合式教學(xué)改革實(shí)踐
——以梧州學(xué)院“高級(jí)英語(yǔ)”課程為例 - 5G背景下高職院校“產(chǎn)學(xué)研用創(chuàng)”五位一體人才培養(yǎng)模式創(chuàng)新實(shí)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