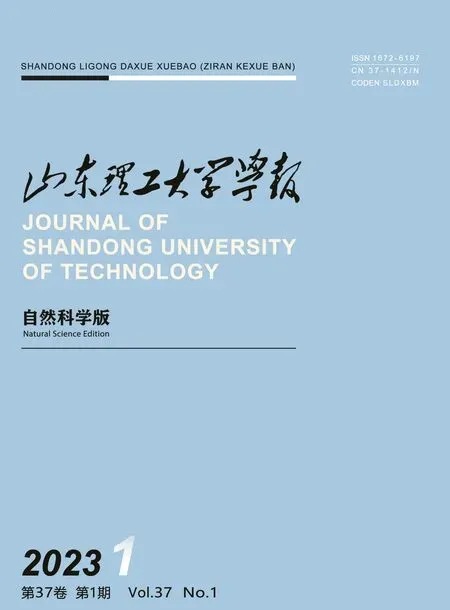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度分析
李明星,趙金寶,徐月娟,劉文靜,姜嘉偉
(山東理工大學 交通與車輛工程學院,山東 淄博 255049)
隨著我國高速鐵路與高速公路的建設與發展,山東省的高鐵網與公路網布局愈發密集。在經濟發展一體化中,交通運輸一體化是首要因素,同時也是影響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基本條件。研究經濟發展與交通可達性的耦合協調關系,有助于改善城市發展不平衡問題。經濟與交通的關系歷來是各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常運用模糊數學評價[1]、灰色關聯[2]、閾值回歸[3]、引力模型、熵權法[4]等模型與方法探究交通與經濟的關系。就研究對象而言,部分學者主要集中于研究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性規律,分別從國家、城市群[5-7]、省域[8-10]、單一城市[11-12]等層次研究兩者的相互關系。在交通可達性方面,國外學者Hansen[13]首次提出可達性是評價交通網絡的一項綜合性指標。就研究方法而言,大體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基于空間視角,借助大數據平臺,結合各城市節點的最短旅行時間等構建交通可達性模型。徐鳳等[5]和姚一民[14]利用權重法,建立加權平均旅行時間模型;程鈺等[15]針對濟南都市圈路網問題以縣域為視角,提出將加權平均旅行時間指標與路線系數結合,構建交通可達性模型。另一種是利用權重法對交通設施賦值評分以及量化各交通指標建立交通可達性體系。于尚坤等[10]選取高速公路里程、公路密度、客貨運量等5項指標構建可達性評價指標體系;李健霆等[11]通過研究站點可達性、網絡可達性及可達性變化率構建湖南省長沙市的可達性評價體系;劉傳明等[16]通過校核可達性測算和投入產出比分析區域交通可達性。
總結現有成果,多以單一模型為主,綜合考慮兩種交通可達性方法的研究較少;經濟和交通指標系數多采用熵值法、AHP層次分析法等確定,其權重值僅考慮數據大小,不能反映數據間的相互關系;關于實證分析的研究缺乏綜合系統的評價方法和規劃建議。
本文以山東省16個地市為例,以地區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增加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支出、衛生機構基數、高校基數等6項經濟指標構建經濟規模指數模型,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各經濟指標權重。基于公路、鐵路、航空、水路4種運輸方式,綜合考慮市域內通達性和省際間通達性,結合加權平均旅行時間建立市域內交通可達性模型;選取交通基礎設施等級、公路相對評分值、運輸能力等5項指標構建省際間交通可達性模型,通過客觀賦權法確定各交通指標系數。利用交通與經濟的耦合協調模型,研究交通可達性與區域經濟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合理性規劃建議。
1 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域概況
山東省地處黃河下游,東臨渤海、黃海,西北與遼東半島隔海相望,自北向南依次與河北、河南、安徽、江蘇四省接壤。根據數據顯示,2021年山東省的GDP總量為83 095.9 億元,首次突破8 萬億大關,位居全國第三,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 705元。山東省鐵路營運里程6 881 km,居全國第5位;公路通車總里程達28.68 萬km,居全國第2位;全省共有29座在建高鐵車站,四通八達的綜合交通運輸網絡正在加快構建。
1.2 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數據來源于山東省、廣東省、江蘇省三省的《統計年鑒2021》及各地市的統計年鑒、三省的《交通年鑒2021》、12306網站、各機場官網等關于交通及經濟的數據。利用ArcGIS 10.2軟件進行數字化和拓撲處理;公路、鐵路旅行時間來源于百度地圖和高德地圖;原始經濟和交通數據經過量化處理后,分別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客觀賦權法,得到各指標評分系數。
2 模型建立
2.1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模型
為充分反映地區經濟的整體水平,本文考慮到地區醫療條件、教學條件等能較好地反映地區經濟水平,選取GDP、人均消費支出、衛生機構基數、高校基數等6項經濟指標,作為經濟規模指數f(xi)的測度指標,計算公式為
(1)
式中:f(xi)為i市的經濟規模指數;Xij為i市第j項的經濟指標;n為城市個數,n=16;m為經濟指標個數,m=6;aj為在經濟規模指數中的權重,其值由主成分分析法確定。
2.2 交通可達性模型
交通可達性是指在交通網絡中從某一節點到達其他節點的便捷程度,市域內的通達性反映聚集程度,有助于加強核心城區的輻射作用,影響物流集疏的時效性,省際間的通達性反映對外貿易、經濟交流的便捷性,因此綜合交通可達性可以分為市域內可達性與省際間可達性。
2.2.1 市域內交通可達性模型
山東省內的交通方式主要依賴公路和鐵路,故針對這兩種交通方式的最短旅行時間,以經濟規模指數f(xi)為權重構建市域內可達性模型。計算公式為
(2)
式中:Mi為城市i的最短加權旅行時間;Ti為城市i到達其他節點的最短旅行時間(h),如表1所示。

表1 山東省各地市最短旅行時間 單位:h

(3)
2.2.2 省際間交通可達性模型
山東沿海港口泊位數有597個,總運輸能力達8.6億t,民航機場12座,飛國內、國際航線共670余條,水路、航空的交通便捷性不容忽視。故結合公路、鐵路、水路、航空4種交通方式,采用交通基礎設施等級、公路相對評分值、運輸能力等5項指標綜合評價省際間的可達性。交通基礎設施包括機場、火車站、港口;公路相對評分值由公路、高速公路總里程決定;運輸能力由含公路、鐵路、航空和水路等4種交通方式的客貨運量決定。參考文獻[17]并根據客貨運量和技術作業量等,分別對機場、火車站、港口劃分等級并計算其相對評分值(見表2)。

表2 交通設施等級劃分及賦值

(4)


表3 對外通達性指標評分系數
注:提取方法為客觀賦權法。
2.2.3 綜合交通可達性模型
綜合交通可達性結合了市域內可達性和省際間可達性,能反映城市的整體交通水平,其計算公式為
(5)
式中:g(yi)為城市i的綜合可達性指數,其值越大表明整體交通水平越高,反之越低;b1、b2分別為市域內可達性和省際間可達性在綜合可達性中的系數,由層次分析法確定,取b1=b2=0.5。
2.3 耦合模型
耦合反映兩個及以上的模塊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18]。參照相關研究[19],利用耦合度分析交通可達性與經濟規模指數的相互關系,構建耦合度模型,其計算公式為
(6)
式中,Ci為城市i的交通可達性與經濟規模指數的耦合度,Ci越大說明f(xi)和g(yi)交互關系越緊密。作為補充,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可進一步反映交互作用水平的程度,其計算公式為
(7)
式中:w1和w2分別為f(xi)和g(yi)的系數,在此認為,兩者的重要程度相當,取w1=w2=0.5;Di為城市i的耦合協調指數,其值越大,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與交通運輸的交互作用越好。
3 結果分析
3.1 區域經濟規模指數f(xi)
將山東省16個地市6項經濟規模指標量化處理,指標權重由主成分分析確定,得出經濟規模系數矩陣如表4所示。KMO和巴特利特檢驗結果大于0.8,表示各指標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

表4 經濟規模指標評分系數
注:提取方法為主成分分析法。
將上述經濟指標的權重值代入經濟規模指數模型計算,得出山東省各地市經濟發展水平關系圖(見圖1)。

圖1 山東省各地市經濟發展水平關系圖
由圖1可知,山東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落差較大,形成了魯東沿海經濟圈以青島為中心、魯中地區以濟南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的狀態,排名前五的地市為青島、濟南、煙臺、濰坊、東營,聊城、棗莊、日照排名后三。日照是交通制約經濟發展的典型城市,相比于具有相同市域面積、地理優勢的威海,兩者的經濟規模指數差距明顯。主要原因是日照城區之間缺乏足夠的擴展空間,僅有的東港區與嵐山區無法連片發展,城市核心區域的主干道較短,且日照作為國內吞吐量前十的煤炭和鐵礦石大港,缺少足夠可用的港口腹地,因而加強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是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淄博、濟寧、臨沂等地經濟發展仍有足夠的提升空間。
3.2 交通可達性指數g(yi)

表5 山東省各地市交通可達性計算結果
圖2中交通可達性系數大于1的城市有青島、煙臺、濟南等地,同時三地的經濟發展規模也位居山東省前列。可見,經濟發展與交通可達性呈正相關。山東省各地市的整體可達性水平參差不齊,存在個別錯位現象。交通基礎建設滯后城市如淄博、東營,交通建設嚴重影響經濟發展;交通基礎建設超前城市菏澤,經濟發展滯后于交通基礎建設。

圖2 山東省各地市交通可達性關系圖
3.3 耦合協調度
山東省16個地市交通可達性與經濟規模指數的耦合度Ci和耦合協調度Di計算結果如表6所示,f(xi)、g(yi)、Ci三者的關系如圖3所示。

表6 山東省各地市交通可達性與經濟規模指數耦合協調度計算結果
由圖3可知,山東省16個地市的交通可達性指數與經濟規模指數的耦合度趨于1,說明兩者具有較強的相互關系。但兩者的耦合協調度相差較大,根據數據特點,得出山東省交通與經濟耦合協調度關系(見圖4)。

圖3 綜合交通可達性與經濟發展水平耦合關系圖

圖4 山東省交通與經濟耦合協調度關系圖
由圖4可知,山東省各地區交通與經濟的耦合協調度多集中在0.6~0.8,處于高水平耦合的城市較少,東西部發展相對失衡。
3.4 發展建議
對標GDP位居全國前兩名的廣東省、江蘇省,山東省GDP位居全國第三名,但與南方經濟發達地區明顯不同,山東遠離中國的經濟中心,與長三角、珠三角等超級城市群的交通可達性低[20],且環渤海城市群分散,像濟南、青島等核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虹吸作用小,不能抱團發展。現將3個省份的耦合協調度發展階段劃分為5個階段(見表7—表9)。

表7 山東省各地市耦合協調度劃分結果

表8 廣東省各地市耦合協調度劃分結果

表9 江蘇省各地市耦合協調度劃分結果
由表7可以看出,現階段,山東省7個城市仍處于拮抗階段,整體水平不高,差異性顯著。對標廣東省和江蘇省,兩省的耦合協調度集中分布在磨合階段和高水平耦合協調階段,分析兩省的主要優勢為國家級綜合交通樞紐城市多,交通網絡建設以多支點城市為源,呈現出“核心-外圍”的圈層式輻射分布格局,城市間聯系緊密。
相較于粵蘇兩省,山東省在高鐵建設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截至2020年底,山東、廣東、江蘇3個省份中已通高鐵的城市在省內城市總數中的占比分別為81.3%、95.2%、100%,江蘇省、廣東省的高鐵通車率遠超山東省,可見山東省交通基礎建設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21]。基于此,山東省要加快高速鐵路建設、完善高速公路網絡布局,實現基礎設施品質化,同時借鑒粵蘇兩省對于自身特點需求、發展機遇關鍵點和未來趨勢的把握能力,在建設交通強省的進程中保證基礎設施高質高效,領先發展。
山東省可將青島作為軌道上的新支點,以點帶面輻射全省,加快東營、菏澤以及聊城三市的高鐵建設。加快打造綜合交通客運網,實現省會、膠東、魯南三大經濟圈內1小時通達、省內各地2小時通達、與全國主要城市3小時通達。
基于交通可達性計算結果,重點建設淄博、日照、東營三地的綜合交通基礎設施,著力完善臨沂、聊城、泰安等地對內交通發展不平衡問題。
根據耦合協調度結果分析,突出建設低水平耦合階段和拮抗階段城市。對于交通滯后城市,如淄博、東營等地,應改善城市公共交通、加快鐵路網建設、強化與核心城市的交通聯系。對于處在磨合階段的城市應完善相關交通政策,盡快進入高水平耦合階段。
4 結束語
本文以山東省16個地市研究對象,結合公路、鐵路、航空、水路運輸方式,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客觀賦權法分別確定經濟規模和交通可達性指標系數,綜合考慮不同數據間的相關性。針對各市的耦合協調度結果,分別對處于不同階段的地區提出合理的規劃建議,促進山東省綜合交通與經濟發展一體化的進程。但本文僅在空間尺度上分析了山東省各地市的經濟發展規模和交通可達性的相關性,下一步可以基于時空角度綜合分析,為山東省的全面發展提出合理化建議。
——山東省濟寧市老年大學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