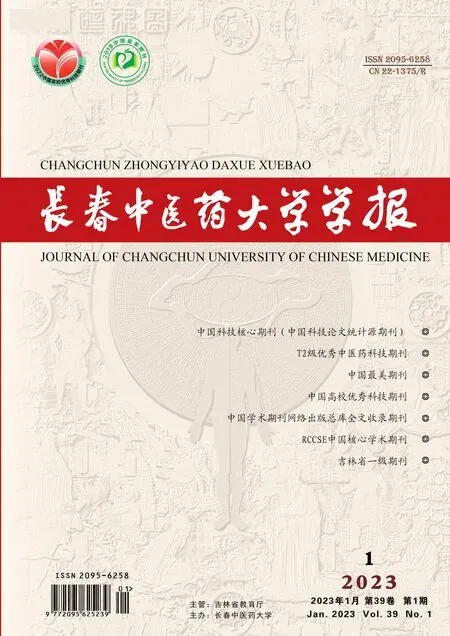異食癖證治探賾
馬金針,崔 為
(長春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長春 130117)
異食癖,又稱為異食癥、亂食癥,怪食癥,《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將其歸為喂食及進食障礙。其診斷標準為:持續食用泥土、頭發、玻璃等非食用非營養物質至少一個月以上;食用非營養物質與個體發育情況不符;此進食行為不屬于文化或正常社會實踐部分;若異食行為與其他精神障礙及身體疾病相關,則需結合臨床關注。此外,異食癖在小兒、成人等任何群體都可出現[1]。異食癖歸屬于中醫癥瘕、疳癥、蟲癥、奇癥等范疇,隋唐以前便已有相關記載,由于病理機制復雜且所嗜食之物較為隱晦,故少以獨立病證載于醫案,多以零散的癥狀附于其他疾病之中。故本文從古今記載異食癖的文獻入手,探尋古今異食癖的因機證治,并進行系統梳理,以期對現代臨床研究和治療異食癖有所助益。
1 異食癖之“癖”
“癖”為“辟”的后起形聲字,首見于《靈樞·水脹》,謂“癖而內著”,強調“癖”與積聚性疾病有關[2]。“癖病”最早見于晉·王叔和《脈經·平雜病脈第二》,言“弦急,疝瘕,小腹痛,又為癖病”[3]。即小腹寒痛、有癖塊。后《諸病源候論》對癖病的記載更為詳細,列“癖病諸候”,認為其病因為“飲水漿過多,便令停滯不散,更遇寒氣,積聚而成癖”[4]。另外,在古辭書《正字通》和《康熙字典》中記載:“癖,嗜好之病”。可知,癖可以概括為兩意,一指飲食不能消化吸收而導致的腹部疾患,二指對某種事物的偏好,寄托情感,積久成習,后逐漸發展為一種文化概念。
在《千金方》中載有“米瘕”一證:“好食生米,不得米則胸中清水出……其人常思米,不能飲食”[5]。便有食入于胃久積不化,化而成癖之義。后在李時珍《本草綱目》中記載了一則嗜食燈花案,言“明宗室富順王一孫,嗜燈花……時珍診之曰:此癖也。以殺蟲治癖之藥丸,服一料而愈”[6]。李時珍將此異食行為稱之為“癖”,從其治法可知,此異食癖當為嗜食不化,致成蟲積,亦有積聚為患之義。此外,“癖”作為一種文化概念,濫觴于魏晉時期,如王粲的“驢鳴癖”、嵇康“鍛鐵癖”等,16世紀時期“癖”成為晚明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湯賓尹在 《癖史》中說:“士患無癖耳。誠有癖,則神有所特寄”[7]。
將癖作為值得鼓勵的個性和價值追求。
然正常的嗜好有助于陶冶情操、樹立人格,過于偏頗甚至病態的嗜好則會對自身及社會造成不良的影響及后果。如張耀翔《心理雜志選存》所言:“癖,嗜好之變態也,凡人皆有嗜好,但使所嗜之對象和程度與一般人同,則不得以變態視之。變態云者,必其所好大有異乎常人,以一百萬人中或能尋出一二同好為標準”[8]。異食癖所嗜食多為土塊、生米、炭塊等異于常人的無營養、非食用物質,張耀翔在《感覺心理》中將這種特殊的食癖稱之為變態味覺[9]。
1.1 古代非醫文獻中的異食癖
在史書及歷代筆記小說中早有對這一異常食癖的記載。如《南史》載“劉邕襲南康郡公爵位,此人生性嗜食瘡痂,認為其味美似鮑魚”;唐·溫庭筠《乾巽子》載:建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權長儒嗜食爪甲;明·馮夢龍《墨憨齋三笑》中載:唐朝舒州刺史張懷肅、左司郎中任正名、李棟都好服人精,明朝的射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的陰津、月水;另有古籍記載賀蘭明好啖狗糞,吳江一婦人喜食死尸腸胃等。后被清·俞震收錄于《古今醫案按·癥瘕》,俞震言“此種皆系癖疾”。因這種類型的醫案,未記載治療,故不能歸入醫案,補充診籍,只能證明異食癖很早之前便出現了。
1.2 古代醫籍文獻中的異食癖
早在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中便有異食癥的相關記載,如《病源·癥瘕病諸候》中的“虱癥候”言“人有多虱,而性好嚙之……俗云虱癥人見虱必嚙之,不能禁止”[4]。此外,《病源·癥瘕病諸候》中還載有“米癥候”與“發癥候”,為生米、頭發之物停聚于胃,積而成癥,說明古醫籍中早有嗜食各種異物者,并可見因于久食異物、積而不消導致的癥瘕、臟腑虛弱等一系列病癥。現將古籍文獻中常見的異食癖按嗜食異物種類,作一簡單的分類概述。
1.2.1 食發 古醫籍中,將因食發而產生的疾患稱為發瘕或發癥,與當今異食癖中的食發癖相似,見于《病源》“因食飲內誤有頭發,隨食而入成癥”,《舊唐書·方技傳·甄權》中也記載了名醫甄權治療尼明律發瘕證。在古籍記載中,發瘕證以飲油為主要癥狀表現,如《千金方·卷第十一》言:“治發癥,由人因食而入,久即胸間如有蟲,唯欲飲油,一日之中,乃至三二升,不欲飲食者方”[5]。清·沈源在《奇癥匯》中進行了詳細論述,言“有人飲油至五斤方快意,不爾則病。此是發入于胃,氣血裹之化為蟲也”[10]。其病因為食發,發積于胃、化而為蟲,從而引發嗜油之癥,可知,隋唐以前已出現因食發而產生的疾患,并有相應的治則治法,可為當今不明原因的嗜食頭發癥提供治療思路和啟迪。
1.2.2 食炭 食炭,在醫籍文獻中多與疳癥相聯系,如明·陳文治《廣嗣全訣》所載:“疳熱,面黃吃炭土,羸瘦”[11]。此外,食炭等異食癖還與患者自身的疾病有關,如清·陳士鐸《石室秘錄·奇治》中便載有一則與癲癇病相關的嗜食木炭案例。言:“癲癇之癥……喜食炭者,蓋心火為痰所迷,不得發泄,炭乃火之余,與心火氣味相投,病患食之,竟甘如飴也”[12]。患者久患癲癇,痰濁蒙蔽心竅,心火不得外發,故欲求助于外火,炭有火之余氣,故患者嗜炭。唐曉蘭以嗜食為主要發作形式的癲癇[13]。除癲癇外,還發現其他與異食癖有關的疾病。唐劍華記載1例腦瘤患者以嗜食竹筷、肥皂、香蕉皮等[14]。故在臨床診療中,應重視軀體自身疾病及嗜食異物之間的相互關聯性。
1.2.3 食土等其他異物 古籍文獻中,食土多見于小兒。我國現存最早的兒科專著《顱囟經》中已將吃土行為與小兒脾疳聯系起來,見載:“小兒一眼青揉癢是肝疳,二齒焦是骨疳……七愛吃泥土是脾疳”[15]。北宋·錢乙《小兒藥證直訣·諸疳》言:“脾疳,體黃腹大,食泥土”;南宋·劉昉《幼幼新書》中對脾疳的描述更為詳細,認為脾疳即食疳,其癥候為腹壁多青筋、喘促氣粗、面色萎黃、愛吃泥土等,并提出脾疳糞內有蟲[16]。后《保嬰全方》言:“小兒疳積在脾,面黃腹急,咬指甲,挦眉毛,要吃泥土、炭、茶紙”[17]。《小兒衛生總微方論》也提及“甘疳之候……身色黃黑,食泥土生米”[18]。可見宋代,將異食癖與小兒疳癥并提已比較普遍。古醫籍中,疳證又常與“蟲”這一病因掛鉤,如《太平圣惠方·小兒五疳論》中便有疳蟲一名,認為小兒疳疾由飲食、寒溫不調、腹內生蟲所致。故異食癖也多見于古醫籍中的蟲證,如明·《萬病回春》載“治五疳皮黃肌瘦……好食泥、炭、茶、米之物,或吐或瀉,腹內積塊,諸蟲作痛”[19]。明清時期,異食癖與蟲癥掛鉤普遍見于醫籍文獻之中,如明·孫一奎《赤水玄珠》中列吃泥門,吃生米門,言“小兒吃泥,乃胃中熱;吃生米者,此胃中有蟲”[20]。
成人異食癖在古籍醫案中也多常見,如清·趙竹泉在《醫門補要》中記載:“一婦人,一見生米,口即流涎,得啖始快”,又有“一女瘦弱不堪,常食臭襪布,及臭污泥”,及見“一人起居如常,時喜喫金鐵土石物”[21]。可知,在古代,異食癖已被醫家所認識,成人、小兒均可患此疾。
2 異食癖的病因病機
2.1 飲食不消,積而化蟲
明·龔廷賢《壽世保元》中明確提出,異食癖的病因病機為痞積不化,致成蟲積,見載“諸般痞積,面色萎黃,機體羸瘦,四肢無力,皆緣內有蟲積,或好食生米,或好食壁泥,或是茶、炭、咸、辣等物者,是蟲積”[19]。明·周之干《慎齋遺書》也言:“小兒吃土米、瓦灰等物,有疳蟲也”[22]。此外,明·孫文胤認為,蟲須借助天地之氣和外物方能成形,如草腐生螢,肉敗生蛆,蟲生于腸胃,不能無憑而生蟲,當為飲食入胃,停滯不化,濕熱膠著,氣血相搏而生蟲。并提出“大凡難化之物皆能生蟲……誤吞頭發羽毛,尤其易生……有茶癖、酒積之癥,久之亦變成蟲。成于茶者常思食茶,成于酒者必酷嗜酒,一日不獲所欲,則一日不能暫安”[23]。同理,頭發、泥土、瓦塊等屬于難化之物,久積于胃則可蘊熱化蟲,形成特殊的食癖,因于發者則嗜發,因于泥土、瓦塊者則嗜食泥土、瓦塊之物。
2.2 胃熱內蘊,中焦失調
在明·江瓘《名醫類案》中載有一則嗜食污泥的案例,言:“玉田隱者治一女忽嗜河中污泥,日食三碗許,以壁間敗土調水飲之,愈。丹溪曰:吃泥,胃氣熱也”[24]。河中淤泥,其性偏涼,因于患者胃中有熱,故欲食外界寒涼之物以濟之。《景岳全書·雜癥漠·飲食門》中也言:“凡喜食茶葉、喜食生米者,多因胃有伏火,所以能消此物”[25]。此外,清·趙竹泉也言:“時喜吃金鐵、土石物,毫無所礙,此肝胃火旺極生蟲,故能磨此堅剛之物”[21]。胃寒則食谷不化,胃熱則消谷善饑、能消難化之物;或由于異物久積于胃,郁而化熱,而生異常味覺,從而形成異食癖,治當清胃熱、養陰津。
2.3 臟腑虛損,精氣不足
脾胃為水谷之海,飲食五味皆入于脾胃,故異常的味覺、食癖,其病位與脾胃密切相關,久食異物,必定會對脾胃功能造成傷害,導致脾胃虛損。早在《素問·五臟生成篇》中便言:“多食酸,則肉胝?而唇揭”。李祥云《奇難怪病治愈集》中也記載了嗜食醋、甘、鹽等證,其食用量均數倍于常人,因所食之物常見,故不多贅述。現選用幾則與臟腑虛損有關的嗜食特例進行論述。段世彪等記載了1例嗜食豬油的案例,患者因患風濕,久服溫燥之藥,進而出現胃脘嘈雜等胃陰虛癥候,須頓服豬油六兩以上方能緩解[26];孫淑霞記載了1例產婦因產時失血過多,出院后嗜食黃土案例[27];以上案例中的異食行為均與脾胃氣血陰陽虛損有關,脾胃虛損則欲求外物以補之,其理論源于《黃帝內經》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又如《錦囊秘錄》所言:“臟各有神,凡酷嗜一物,皆其臟神所欲。斯臟之精氣不足,則求助斯味以自助……”[28]故異食癖與臟腑精氣的虛損有關。
此外,還應重視情志在異食癖病證中的重要性,情志與心肝脾密切相關,情志失調易影響心肝脾等臟腑的功能,從而形成異食癖。
3 異食癖的治則治法
關于異食癖的治療,現代醫學多從營養及微量元素缺乏、寄生蟲感染、鉛中毒、社會及家庭環境等心理因素方面入手;祖國醫學則多從審證求因、辨證論治方面進行考量,因整理古籍文獻時發現異食癖主要與蟲積、胃熱、臟腑虛損有關,故從這三個方面進行探討論治。
3.1 殺蟲去積,調理脾胃
針對異物停積于胃,蘊而化蟲所致的異食癖,古代醫家多采用殺蟲去積、兼調脾胃之法。如唐·甄權用雄黃治療發瘕證;李時珍用殺蟲治癖之藥治療嗜食燈花證;趙竹泉用十數貼殺蟲藥治療嗜食臭襪布、污泥之癥;重在殺蟲積以除病因。在殺蟲的同時,也需注重固本,因異物久積,易傷脾胃,故在殺蟲之時,應注重調理和固護脾胃。薛立齋在治療小兒嗜食泥土一證時,用六君子湯及四味肥兒丸治愈,取意殺蟲兼健胃補脾。因小兒缺乏辨別事物的能力,更易出現亂食行為,如吳鞠通《溫病條辨·解兒難》中提到小兒患疳積者,有的愛吃生米、黃土、石灰、紙、布一類,是緣于小兒無知,不拘何物即食之,導致脾運失常,久積生蟲,后愈愛食異物,并提出治法,當暫運脾陽,有蟲者兼殺蟲。
3.2 清胃瀉火,兼理脾土
元·朱震亨《丹溪心法》言:“吃泥,胃氣熱也”,用黃芩、石膏為主藥以清胃熱,兼輔以陳皮、白術、茯苓健脾,以達清胃熱兼理脾之效。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引姚和眾《延齡至寶方》,“取好黃土煎黃連汁和之,曬干與食”治療小兒食土,黃連主清胃熱,黃土取象比類屬脾土,取以形、味補脾土之意,也意在清瀉胃熱,兼理脾土。《萬病回春》中言:“治小兒愛吃泥土,乃脾虛胃熱所致,清胃養脾湯主之”[19]。此外,《醫門補要》中記載喜食金鐵土石等物,是緣于肝胃火旺,蘊熱生蟲,并提出用大青葉煎飲,清肝火而愈[21]。這種治法對后世醫家治療異食癖影響深遠,如近代名老中醫王鵬飛在臨床治療異食癖時,主張用清胃熱之法,療效頗佳。
3.3 健脾益氣,補虛和中
異食癖病位在脾胃,異物久積,影響脾胃氣血生化,日久則現脾胃氣血兩傷,形體羸弱,如李東垣言:“喜食土者,胃不足也”。古代醫家治療時多注重調補脾胃,在《備急千金要方》中便載有一則治療小兒食土證的治法,言“取肉一斤,繩系曳地行數里,勿洗,火炙與吃之”[5]。脾主肉,五行屬土,其以繩系肉行數里,意在以形、味補脾土。又如,錢乙《小兒藥證直訣》曰:“脾疳,體黃腹大,食泥土,當補脾,益黃散主之”[29]。緣于當今信息發達,異食癖廣泛出現于我們的視野之中,現治療異食癖的案例中以脾虛濕盛證多見,慶進卿等所載的脾虛濕盛嗜食青石板癥,用健脾化痰兼調氣機之法[30];馬哲河記載的青少年心脾兩虛嗜食生米,用調補心脾之法治愈[31]。臨床治療中,注重中醫辨證施治對治療異食癖極有意義。
4 異食癖的社會環境因素及現代醫學研究
飲食與社會環境、宗教信仰、地域文化等因素息息相關。如我國古代因為戰爭、天災等因素盛行的食觀音土;基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出現的地域性食癖,如雷州嗜吃檳榔等。在一些非洲國家,吃土的行為在文化習俗上是被認可的,據研究,異食癖在懷孕的非洲和非裔美國女性中更為普遍,甚至有專門售賣泥土的市場。但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發布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將屬于文化和實踐活動部分的異食癖排除在外,故不多做贅述。
現醫學研究認為,異食癖的形成多見于學齡前期兒童,由于對客觀世界缺乏認識,喜歡亂吃東西,隨著年齡增長若沒被及時糾正,久之便會形成一種心理依賴,長大后易形成心理失常的強迫行為[32]。此外,醫學研究表明,體內缺乏微量元素及鉛中毒、寄生蟲感染、社會環境等心理因素也會引起異食行為。現代研究尤其重視心理因素在異食行為中的影響,如陳瑩等運用接納承諾療法治療初中生異食癖案例[33]。此外,白茹系統論述了自閉癥群體異食行為的診斷、評估、表現和干預方法,補充了國內異食癖研究空白[34]。
5 結語
當今社會,異食癖已逐漸步入大眾的視野,其病因病機等現有研究仍有不足,在臨床治療過程中進展緩慢。祖國醫學中雖無異食癖之名,但其相似病證早已散見于歷代醫籍之中,古醫籍文獻中多將異食癖歸為蟲癥、疳癥、奇癥等范疇,究其緣由,并未發現這些病證與異食癖之間有直接聯系。乃是歷代醫家在長期經驗積累中發現異食癖多見于這幾種病證,又無法解釋異食癖的病因,方將異食癖歸為這些病證范疇。但醫籍文獻中關于異食癖的辨證論治,對當今治療異食癖具有借鑒意義。臨證治療異食癖時應注重中西醫結合、互相借鑒,同時中西醫在治療異食癖時也有一些共通之處,如皆認同“蟲”這一因素在異食癖中的重要性。故在臨證治療時,應注重中醫辨證論治與西醫的現有研究、科學技術相結合,同時,若通過各種現代醫學治療仍無法治愈的異食之癥,注重采用中醫辨證治法,也常有意外收獲。此外,在臨證治療異食癖時還應重視患者的心理和社會環境、軀體自身疾病等因素,以便有效地進行異食癖臨床研究和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