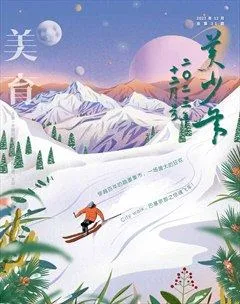歐洲植物插畫的科學演變
小莊
植物插圖曾是記錄植物物種的主要方式之一,這項工作需要高超的繪畫技巧和豐富的園藝知識。一些研究者認為,植物繪畫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經出現了。希臘圣托里尼島有一幅繪制于米諾斯文明時期的壁畫,被認為是最古老的可識別植物圖,上面刻畫了一種被稱為加爾亞頓百合的植物。在后來的羅馬和希臘藝術中,也能找到許多草藥、花卉和樹木的形象,主要作為裝飾用途。

在埃及的卡納克,有一座修建于公元前1400多年的神廟——圖特摩斯三世神廟。在它的殘垣斷壁上雕刻著多種植物的輪廓,其中一些植物至今仍然清晰可辨。
隨著人們對植物的認識不斷加深,植物繪畫的使用范圍也不斷擴大,除了仍然用于裝飾之外,還用來幫助人們識別草藥。
公元前一世紀,本都王國國王米特拉達梯六世的御醫克拉泰夫阿斯創作了第一部藥用植物圖譜,對后世的藥理學和醫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遺憾的是,這套圖譜并沒有保留下來。
同時期的古羅馬學者老普林尼對試圖用插圖來描繪植物的做法很不以為然,因為這些插圖很可能無法還原植物的本來面貌,從而影響人們辨認。但無論如何,草藥識別的需求是客觀存在的。第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由希臘醫生狄奧斯科里迪斯所著的《藥物論》。這本書在此后1000多年的時間里都被認為是植物學方面的重要圖鑒。
由于年代久遠,這本著作的原始手稿已不復存在,只留下了各個時期的手抄本。其中最古老的手抄本可追溯至公元512年左右,是為了獻給當時的統治者安妮西亞·朱莉安娜公主。后來它流落民間,輾轉各地,陸續有人在旁邊留下了希臘文字的注釋,以及阿拉伯文、希伯來文的動植物名稱。14世紀中葉,維也納皇家圖書館購入此書。它被世人稱為安妮西亞·朱莉安娜抄本或維也納抄本。
維也納抄本中的彩色插圖用色大膽、明亮,呈現出一種生機勃勃的自然主義風格。這些插圖的繪畫水平參差不齊,很可能并非出自同一位藝術家之手。而且插圖中只表現了草藥的大致外觀,在物種鑒定方面的作用很小。更糟糕的是,在那以后極其漫長的一段時期內,這些所謂的草本藥典都是對前人作品的抄襲,甚至還加入了各種迷信的解釋,這與植物鑒定所需的寫實性與精確性漸行漸遠。
正如藝術歷史學家威爾弗里德·布朗特在針對這段歷史的評論中所述:“植物插畫史的第一個千年并沒有顯示出從原始作品到自然主義作品的穩步發展,而是逐漸衰落……”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東方,對植物的描繪則走上了另一條路。布朗特的研究中也提到:“花卉繪畫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不受醫學或其他實用因素的影響,早在公元七、八世紀就在中國開始熱情高漲地發展著。”
作為文人畫的一種,中國的花鳥畫在五代時期就已經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形成了兩大不同風格的花鳥畫流派,分別以徐熙和黃筌為代表。黃筌的工筆花鳥畫強調細筆重彩,而徐熙則融入了水墨的技法。他們的作品都展現出一種成熟的寫實風格。
在博物學研究領域,中國現存最早的植物志是《南方草木狀》,約公元304年問世,作者是晉代竹林七賢之一嵇康的侄孫嵇含。書中共記載了80種植物,最初版本或許有配圖,很有可能已在傳抄過程中遺失。明代永樂四年(1406年)成書的《救荒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野生食用植物的著作,為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橚所撰,其中讓畫工依照實物繪制了大量用來辨識的圖,其精美和逼真程度在同時代的植物學圖譜中都十分出色。

時間步入16世紀。隨著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植物插畫的技法也將迎來巨大的變革。兩位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大師為此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其中一位就是意大利著名畫家列奧納多·達·芬奇,另一位則是德國杰出畫家阿爾布雷希特·丟勒。
在達·芬奇流傳下來的手稿中,迄今仍能找到幾十張類型各異的植物素描。這些素描極有可能是為后來繪制大型作品中的植物元素所做的研究——如《麗達與天鵝》和《巖間圣母》中都描繪了豐富的植物元素。收藏于盧浮宮的《巖間圣母》,畫面里出現了花荵、耬斗菜、鳶尾等眾多花卉,或許還有棕竹和一種難以辨認的蕨類植物。達·芬奇偶爾還會在植物速寫旁邊記下一系列的觀察結果。


丟勒則創作了一系列精致的植物水彩畫,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一大塊草皮》。這幅作品描繪了雞腳草、蒲公英、大車前草等多種草本植物,這些植物看似雜亂地生長在一起,但每一株都刻畫得十分準確,非常容易進行物種鑒定。丟勒對自然物體的描繪表現出超高的現實主義水平,因此受到了藝術史學家們的一致贊揚。他于大約1500年創作完成的《耬斗菜》也讓人嘆為觀止,畫面中的植物比之前的任何植物插畫都要逼真。
雖然達·芬奇和丟勒都不是專門繪制植物的畫家,但他們以敏銳的眼光捕捉到了前人所不曾注意到的細節。可以說,這兩位藝術家為此后的植物插圖樹立了極高的標準,他們的創作不僅僅是美學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將科學價值引入到了此類作品當中。從此,繪制花草樹木的準確性變得和遵循人體比例的解剖學知識一樣重要。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植物插圖發展史上具有跨時代意義的出版物——版畫家漢斯·魏迪茨參與繪制的《本草寫生圖譜》應運而生。魏迪茨擺脫了對過去圖像的依賴,堅持根據植物標本進行精確描繪,從花瓣上最細微的卷曲到根部最小的纏結,毫無遺漏。


20世紀30年代初期,有人在伯爾尼大學植物學院的閣樓里發現了許多魏迪茨創作的植物水彩畫。為了確保所描繪植物的清晰度,魏迪茨特地在花朵下面襯托了黑色背景,展現了他對植物學繪畫的深刻理解,即準確性高于藝術性。
在《本草寫生圖譜》的帶動下,此后的植物學著作都開始以“精準”為目標繪制圖示。德國蒂賓根大學醫學系的教授萊昂哈特·福克斯出版了《植物志》,并且在繪制過程中牢牢地把控著科學與審美的平衡。
《本草寫生圖譜》和《植物志》使植物插圖的創作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標準,以至于在之后很長的時間里,人們在這方面的實踐都沒有新的突破。下一次的重大飛躍,將要等到一個世紀之后了。

知識拓展:
米諾斯文明
希臘克里特島青銅時代中、晚期的文化。又稱克里特文明。
——摘自《中國大百科全書》
徐熙畫派
為五代花鳥畫派的一支,代表畫家徐熙,與黃筌的“富貴”風格相對,標立了“野逸”風格:造型松秀、用筆落墨為格、題材汀花野竹,抒寫著“志節高邁”“放達不羈”的文人性情。徐熙(生卒年不詳),五代南唐畫家,鐘陵(今江蘇南京)人,出身于江南顯族,卻布衣一生。其“野逸”與黃家“富貴”,標志著中國花鳥畫的最初風格分野。徐熙的“落墨法”,曾自撰《翠微堂記》云:“落筆之際,未嘗以傅色暈淡細碎為功。”沈括《夢溪筆談》云:“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
——摘自《中國畫論大辭典》 周積寅 編著
黃筌畫派
為五代花鳥畫派的一支,代表畫家黃筌(903—965),字要叔,四川成都人。五代西蜀畫院權院事。他的花鳥畫全面傳承了唐代花鳥畫的工筆成就,劉道醇《圣朝名畫錄》列其為神品。其題材多為宮廷珍禽異卉,造型嚴謹,用筆工整,賦色明麗,風格特點是“富貴”。沈括《夢溪筆談》說其主要畫法為:“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染成。”今故宮博物院藏《寫生珍禽圖》是其代表作。
——摘自《中國畫論大辭典》 周積寅 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