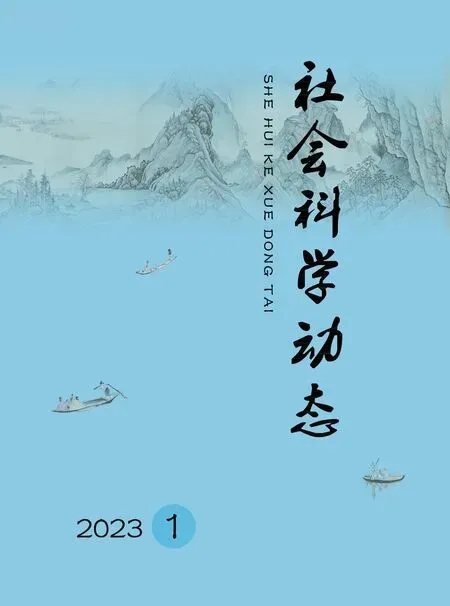中國(guó)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研究:基于文獻(xiàn)視角
公茂剛 張 云
一、引言
農(nóng)業(yè)作為弱質(zhì)產(chǎn)業(yè),其生產(chǎn)面臨著較高的自然風(fēng)險(xiǎn)和市場(chǎng)風(fēng)險(xiǎn)。同時(shí),農(nóng)業(yè)是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的基礎(chǔ),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事關(guān)國(guó)計(jì)民生和國(guó)家糧食安全。事實(shí)上,農(nóng)業(yè)對(duì)我國(guó)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xiàn)。我國(guó)在工業(yè)化建設(shè)初期需要大量的原始資本積累,自1952年至1997年期間,中國(guó)農(nóng)民以這種 “工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剪刀差” 形式為國(guó)家工業(yè)化發(fā)展貢獻(xiàn)了12641億元的資本積累①,達(dá)到了發(fā)展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羅斯托提出的經(jīng)濟(jì)起飛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條件,有力地推進(jìn)了我國(guó)工業(yè)化發(fā)展和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隨著城鄉(xiāng)人口流動(dòng)限制逐步取消以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水平提高產(chǎn)生了大量農(nóng)村剩余勞動(dòng)力,進(jìn)城務(wù)工的農(nóng)村人口為工業(yè)化建設(shè)提供了大量廉價(jià)勞動(dòng)力。工業(yè)化建設(shè)需要大量的土地,農(nóng)民得到的土地征收補(bǔ)償款低于土地價(jià)值,賣地收益中的大部份被用于城市和工業(yè)建設(shè)。一言以蔽之,農(nóng)民在我國(guó)工業(yè)化建設(shè)過(guò)程中所需要的資金、勞動(dòng)力和土地等生產(chǎn)要素的投入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
因此,當(dāng)我國(guó)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并已經(jīng)全面進(jìn)入工業(yè)化時(shí)代和達(dá)到中等收入水平之時(shí),國(guó)家提出了工業(yè)反哺農(nóng)業(yè)的戰(zhàn)略方針。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huì)上提出了 “兩個(gè)趨向” 的重要論斷:在工業(yè)化初始階段農(nóng)業(yè)支持工業(yè)、為工業(yè)提供積累;當(dāng)工業(yè)化達(dá)到相當(dāng)程度后,工業(yè)反哺農(nóng)業(yè)、城市支持農(nóng)村。2004年12月,中央經(jīng)濟(jì)工作會(huì)議再次指出,現(xiàn)在我國(guó)總體上已經(jīng)進(jìn)入以工促農(nóng)、以城帶鄉(xiāng)的發(fā)展階段。從2004年開(kāi)始,國(guó)家逐步取消了牧業(yè)稅、農(nóng)業(yè)特產(chǎn)稅和農(nóng)業(yè)稅,在此基礎(chǔ)上,還加強(qiáng)了對(duì)農(nóng)業(yè)的財(cái)政補(bǔ)貼。2020年,農(nóng)機(jī)具購(gòu)置補(bǔ)貼和農(nóng)業(yè)支持保護(hù)補(bǔ)貼的總額達(dá)到1374.28億元。除此之外,國(guó)家還通過(guò)糧食最低收購(gòu)價(jià)政策、糧食臨時(shí)收儲(chǔ)政策、政策性農(nóng)業(yè)保險(xiǎn)補(bǔ)貼政策、救災(zāi)資金補(bǔ)助政策等加強(qiáng)了對(duì)農(nóng)業(yè)的支持。政府給予農(nóng)業(yè)補(bǔ)貼支持的最終目的是提高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增強(qiáng)其即使沒(méi)有農(nóng)業(yè)補(bǔ)貼也能內(nèi)生發(fā)展的動(dòng)力和能力,實(shí)現(xiàn)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內(nèi)生化。而過(guò)度的農(nóng)業(yè)扶持和保護(hù)或者扶持方式不合理均會(huì)導(dǎo)致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惰性和對(duì)外依賴性,使其喪失內(nèi)生發(fā)展的動(dòng)力和能力。
從長(zhǎng)遠(yuǎn)來(lái)看,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必然要走可持續(xù)內(nèi)生式發(fā)展之路,不僅要擺脫對(duì)政府投入的過(guò)度依賴,還要形成農(nóng)業(yè)按照價(jià)值規(guī)律來(lái)持續(xù)吸引各類要素投入的機(jī)制和路徑,即實(shí)現(xiàn)農(nóng)業(yè)的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要增強(qiáng)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的動(dòng)力與能力,促進(jìn)鄉(xiāng)村新內(nèi)生式產(chǎn)業(yè)振興,重點(diǎn)促成脫貧攻堅(jiān)與鄉(xiāng)村振興的有效銜接,逐步實(shí)現(xiàn)鄉(xiāng)村發(fā)展由粗放型發(fā)展模式向集約型發(fā)展模式的轉(zhuǎn)變。本文基于文獻(xiàn)視角從四個(gè)部分進(jìn)行論述:首先,梳理相關(guān)文獻(xiàn),闡明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的內(nèi)涵;其次從發(fā)展稟賦、發(fā)展理念以及農(nóng)業(yè)體系三方面論述中國(guó)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的約束條件;隨后基于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提出鄉(xiāng)村治理和農(nó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促進(jìn)內(nèi)生發(fā)展的先決條件,以期有效整合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內(nèi)外力量促進(jìn)農(nóng)業(yè)發(fā)展;最后提出以農(nóng)業(yè)與其他產(chǎn)業(yè)的深度融合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重點(diǎn)在于深化農(nóng)業(yè)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加強(qiáng)地方特色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民主體地位建設(shè)。
二、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相關(guān)概念
(一)內(nèi)生式發(fā)展內(nèi)涵及外延
內(nèi)生式發(fā)展模式起源于20世紀(jì)60年代末。當(dāng)時(shí)紛紛獨(dú)立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開(kāi)始尋求各自的現(xiàn)代化之路。以可持續(xù)發(fā)展為理念,依靠本土資源稟賦,追求生態(tài)、文化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相協(xié)調(diào)的內(nèi)生發(fā)展模式在各國(guó)的發(fā)展實(shí)踐中得到推廣和應(yīng)用②。1971年,聯(lián)合國(guó)經(jīng)濟(jì)及社會(huì)理事會(huì)針對(duì)不發(fā)達(dá)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強(qiáng)調(diào)居民的參與及對(duì)發(fā)展成果的共享,并特別重視環(huán)境保護(hù)的徹底性。1975年,瑞典Dag Hammar skj ê ld財(cái)團(tuán)在提交給聯(lián)合國(guó)的報(bào)告中正式提出了 “內(nèi)生式發(fā)展” 這一概念。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內(nèi)生式發(fā)展的相關(guān)理論及實(shí)證研究開(kāi)始延伸至多個(gè)學(xué)科③。在環(huán)境和區(qū)域經(jīng)濟(jì)學(xué)領(lǐng)域,強(qiáng)調(diào)解決發(fā)展問(wèn)題需要賦予并保障居民更大的自主權(quán);在社會(huì)學(xué)領(lǐng)域,強(qiáng)調(diào)內(nèi)生發(fā)展需要居民積極參與,并主動(dòng)尋求和實(shí)現(xiàn)本區(qū)域發(fā)展目標(biāo)。可見(jiàn),日益完善的內(nèi)生發(fā)展理論強(qiáng)調(diào)以人為中心是發(fā)展的目的、尺度及條件④。
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在各國(guó)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中內(nèi)生發(fā)展模式得到廣泛采用。許多國(guó)家重視依托本地的產(chǎn)業(yè)、文化和資源來(lái)制定發(fā)展戰(zhàn)略,賦予本地居民對(duì)土地和資本的管制權(quán)力,體現(xiàn)當(dāng)?shù)鼐用褚庵荆攸c(diǎn)開(kāi)發(fā)附加值回歸本地且主要由當(dāng)?shù)鼐用駞⑴c的產(chǎn)業(yè)⑤。區(qū)域內(nèi)生發(fā)展的實(shí)質(zhì)是轉(zhuǎn)換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發(fā)展動(dòng)能,培育基于本地內(nèi)部的成長(zhǎng)能力,提升區(qū)域產(chǎn)業(yè)競(jìng)爭(zhēng)力,謀求健全和可持續(xù)的地區(qū)發(fā)展,同時(shí)保持和維護(hù)本地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及文化傳統(tǒng),以期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政治、社會(huì)、文化和生態(tài)等長(zhǎng)期效應(yīng)的結(jié)合⑥。
(二)基于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概念
由于一些鄉(xiāng)村長(zhǎng)期依靠粗放式投入獲取產(chǎn)品來(lái)維持生計(jì),使得這些鄉(xiāng)村地區(qū)陷入 “貧困陷阱” ,生產(chǎn)力發(fā)展受到嚴(yán)重制約。提高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和保護(hù)農(nóng)村環(huán)境的雙重目標(biāo)催生出指導(dǎo)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可持續(xù)協(xié)同發(fā)展的新理念⑦。農(nóng)村區(qū)域發(fā)展強(qiáng)調(diào)復(fù)原力、地方規(guī)劃、 “自下而上” 、村民參與等新內(nèi)生發(fā)展理念⑧,重視區(qū)域空間系統(tǒng)內(nèi)要素重組、空間重構(gòu)、功能提升⑨。基于本國(guó)國(guó)情,歐洲各國(guó)鄉(xiāng)村復(fù)興重視區(qū)域聯(lián)網(wǎng)和社會(huì)創(chuàng)新,協(xié)調(diào)整合內(nèi)力與外力;日本則通過(guò)建立 “地域循環(huán)共生圈” ,實(shí)現(xiàn)城鄉(xiāng)共生對(duì)流,并引進(jìn)社會(huì)力量參與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建設(shè),提升地域循環(huán)共生圈抵御外部風(fēng)險(xiǎn)的能力,培育農(nóng)村內(nèi)源發(fā)展動(dòng)力,實(shí)現(xiàn)農(nóng)村的多功能和可持續(xù)發(fā)展。
農(nóng)業(yè)空間異質(zhì)性使得農(nóng)業(yè)轉(zhuǎn)型升級(jí)需要著重考慮資源配置、人地關(guān)系矛盾、空間地理?xiàng)l件等關(guān)鍵異質(zhì)影響因素。因此,有必要借用地理學(xué)的方法將鄉(xiāng)村具體化為一個(gè)個(gè) “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 空間單元⑩,既保留社會(huì)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核心內(nèi)涵,又強(qiáng)調(diào)依賴特定區(qū)域背景,還能以整體視角應(yīng)對(duì)全球化、市場(chǎng)化等外部力量對(duì)鄉(xiāng)村發(fā)展產(chǎn)生的結(jié)構(gòu)性沖擊,進(jìn)而整合內(nèi)外資源,強(qiáng)化社會(huì)聯(lián)系,培育根植于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內(nèi)部的發(fā)展動(dòng)能。農(nóng)業(yè)發(fā)展只有脫離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的封閉循環(huán),從 “行政推動(dòng)” 向 “內(nèi)源發(fā)展” 轉(zhuǎn)型,才能提升農(nóng)業(yè)自我積累與發(fā)展能力,實(shí)現(xiàn)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基于農(nóng)業(yè)地域系統(tǒng)視角,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根植于本地,以具有社會(huì)包容性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作為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與外界聯(lián)系的橋梁,以本地資源和當(dāng)?shù)厝藚⑴c為基礎(chǔ),以本區(qū)域與外部空間動(dòng)態(tài)互動(dòng)為特征,強(qiáng)調(diào)權(quán)利配置、利益關(guān)聯(lián)機(jī)制、地方影響以及農(nóng)村作為地域系統(tǒng)與外界的互動(dòng)聯(lián)系。
三、中國(guó)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的障礙
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的實(shí)現(xiàn)一定是多種因素耦合作用的結(jié)果,單純依靠政府資金投入以及社會(huì)扶持無(wú)法產(chǎn)生農(nóng)業(yè)持續(xù)發(fā)展的驅(qū)動(dòng)力。我國(guó)農(nóng)村的傳統(tǒng)小農(nóng)思想根深蒂固,農(nóng)業(yè)規(guī)模化生產(chǎn)和市場(chǎng)化經(jīng)營(yíng)的制約因素包括不限于:農(nóng)業(yè)發(fā)展缺乏合理的目標(biāo)規(guī)劃,農(nóng)村產(chǎn)業(yè)融合發(fā)展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薄弱、發(fā)展環(huán)境滯后、融合程度低下,土地、資金、人才等農(nóng)業(yè)發(fā)展要素瓶頸問(wèn)題嚴(yán)峻,農(nóng)業(yè)主體地位不明確等。同時(shí),農(nóng)業(yè)內(nèi)部也在發(fā)生明顯變化,農(nóng)業(yè)的外部環(huán)境更加復(fù)雜,因此,實(shí)現(xiàn)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之路障礙重重。
(一)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資源稟賦匱乏
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必然要依賴經(jīng)濟(jì)、文化、資源、環(huán)境相互聯(lián)系和作用的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我國(guó)農(nóng)業(yè)粗放式經(jīng)營(yíng)造成耕地嚴(yán)重浪費(fèi),城市用地?cái)D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用地現(xiàn)象突出?。農(nóng)村人口基數(shù)大,整體受教育水平不高,存在明顯的兼業(yè)化、副業(yè)化趨勢(shì),土地均分制使得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細(xì)碎化,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力難以選擇和使用現(xiàn)代化農(nóng)業(yè)裝備和技術(shù),農(nóng)業(yè)組織化程度低,阻礙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的提升,致使農(nóng)業(yè)長(zhǎng)期囿于傳統(tǒng)生產(chǎn)水平。農(nóng)業(yè)特色資源并未得到有效開(kāi)發(fā),依然停留在傳統(tǒng)種植業(yè)模式,農(nóng)村水電、道路建設(shè)、互聯(lián)網(wǎng)等基礎(chǔ)設(shè)施與基本公共服務(wù)還處于初級(jí)階段,由于投入成本過(guò)高致使沒(méi)有得到大范圍推廣?。同時(shí),要素流動(dòng)很大程度上受城市偏好以及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體制機(jī)制不完善的影響,存在從農(nóng)村凈流入城市的問(wèn)題?。農(nóng)村資源受農(nóng)村承包地、宅基地以及集體建設(shè)用地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開(kāi)放性長(zhǎng)期滯后的影響,流動(dòng)性和配置效率偏低?。
(二)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制度安排不完善
以農(nóng)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為代表,近年來(lái)推行的 “三權(quán)分置” 改革政策提出了放活宅基地使用權(quán)和農(nóng)地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基本要求,對(duì)于放活的方式、范圍、幅度等問(wèn)題仍缺乏具體的制度安排,致使農(nóng)村土地?zé)o法在市場(chǎng)上規(guī)范有序地流轉(zhuǎn)?,導(dǎo)致空心村面積不斷擴(kuò)大、隱形流轉(zhuǎn)加劇等弊端。城市偏向政策造成的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愈發(fā)加劇了農(nóng)村社會(huì)邊緣化窘境,長(zhǎng)期得不到延伸和擴(kuò)展的農(nóng)村社會(huì)服務(wù)網(wǎng)絡(luò)限制了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所需的生產(chǎn)要素獲取和整合能力?。農(nóng)村社會(huì)保障在居民覆蓋面、保障支持水平、繳納標(biāo)準(zhǔn)設(shè)計(jì)方面取得突出成績(jī)的同時(shí),也面臨著頂層設(shè)計(jì)體系不健全、資金供給能力有待提升、智能化技術(shù)應(yīng)用不佳等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
(三)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缺乏產(chǎn)業(yè)聚集力
由于農(nóng)業(yè)設(shè)施投入大、周期長(zhǎng)、盈利薄等原因,農(nóng)業(yè)規(guī)模性特色產(chǎn)業(yè)難以形成,而我國(guó)現(xiàn)有的農(nó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不足以支撐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集聚?,政府引導(dǎo)力度不足,品牌認(rèn)知度較低,不利于農(nóng)業(yè)內(nèi)生價(jià)值再創(chuàng)造。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信息供需不匹配現(xiàn)象突出,尤其是農(nóng)戶在資源統(tǒng)籌和市場(chǎng)對(duì)接等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環(huán)節(jié)存在很大缺陷,以至出現(xiàn)產(chǎn)前、產(chǎn)中、產(chǎn)后價(jià)值鏈斷裂的情況?,部分涉農(nóng)企業(yè)組織協(xié)同能力差,缺乏緊密的利益聯(lián)結(jié)機(jī)制,對(duì)小農(nóng)帶動(dòng)能力弱。分散的小農(nóng)經(jīng)營(yíng)使得機(jī)械維護(hù)、技術(shù)服務(wù)等成本過(guò)高,農(nóng)業(yè)智慧化、信息化以及數(shù)字化建設(shè)領(lǐng)域較為滯后,既無(wú)法為產(chǎn)業(yè)基礎(chǔ)薄弱、生產(chǎn)資源分散的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帶來(lái)規(guī)模優(yōu)勢(shì),也無(wú)法充分挖掘本區(qū)域獨(dú)特的農(nóng)業(yè)資源稟賦。
(四)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市場(chǎng)化程度不足
我國(guó)農(nóng)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存在 “兩張皮” 現(xiàn)象,農(nóng)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缺乏激勵(lì)機(jī)制與風(fēng)險(xiǎn)補(bǔ)償機(jī)制,其理念滯后、人才短缺,種種現(xiàn)實(shí)困境使得我國(guó)農(nóng)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長(zhǎng)期居于低水平狀態(tài),阻礙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的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的新業(yè)態(tài)變革進(jìn)程?,進(jìn)而影響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的生產(chǎn)效率。另外,我國(guó)農(nóng)業(yè)要素市場(chǎng)尚在發(fā)展初期,滯后于經(jīng)濟(jì)的市場(chǎng)化進(jìn)程。例如,土地作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最重要的生產(chǎn)要素,高成本的土地流轉(zhuǎn)限制了土地的配置效率,無(wú)法大規(guī)模集中形成規(guī)模農(nóng)業(yè),不利于高標(biāo)準(zhǔn)農(nóng)田建設(shè),影響了優(yōu)質(zhì)農(nóng)產(chǎn)品市場(chǎng)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由于農(nóng)業(yè)信息不對(duì)稱,進(jìn)而促使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產(chǎn)生盲目決策行為,影響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加劇農(nóng)產(chǎn)品市場(chǎng)波動(dòng)。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社會(huì)發(fā)展網(wǎng)絡(luò)還不完善,目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要素難以與外部的市場(chǎng)體系進(jìn)行有效的銜接和交換,只能內(nèi)嵌于村莊社區(qū)結(jié)構(gòu)并受其制約?,無(wú)法延長(zhǎng)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鏈和提升價(jià)值鏈,且缺乏現(xiàn)代組織方式鏈接外部市場(chǎng)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農(nóng)業(yè)市場(chǎng)化改革,不利于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
(五)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缺乏韌性,抗風(fēng)險(xiǎn)能力差
由于農(nóng)業(yè)本身無(wú)法避免不確定性風(fēng)險(xiǎn)的沖擊,當(dāng)自然災(zāi)害等不可抗風(fēng)險(xiǎn)到來(lái)時(shí),上述農(nóng)業(yè)資源稟賦、內(nèi)生制度、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等約束條件使得現(xiàn)有的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內(nèi)生發(fā)展能力根本就不足以抵御農(nóng)業(yè)風(fēng)險(xiǎn)。長(zhǎng)期的粗放式農(nóng)業(yè)發(fā)展方式造成了嚴(yán)重的農(nóng)村環(huán)境和生態(tài)問(wèn)題,同時(shí)由于缺乏合理規(guī)劃使得城鄉(xiāng)一體化、產(chǎn)業(yè)園區(qū)化、鄉(xiāng)村智慧化與智能現(xiàn)代化、高質(zhì)量農(nóng)業(yè)綜合體等有助于農(nóng)村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改革政策難以落地農(nóng)村,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無(wú)法產(chǎn)生強(qiáng)大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發(fā)展韌性,無(wú)法保障農(nóng)業(yè)與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穩(wěn)定發(fā)展。此外,土地生態(tài)韌性不足會(huì)減少優(yōu)質(zhì)高產(chǎn)糧田的數(shù)量,降低糧食生產(chǎn)潛力,不利于 “藏糧于地” 糧食安全戰(zhàn)略的實(shí)施。
四、基于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優(yōu)勢(shì)
基于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的鄉(xiāng)村空間治理和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有助于塑造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優(yōu)勢(shì),破除延緩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進(jìn)程的障礙。完善鄉(xiāng)村多層次、非線性空間治理,拓展和強(qiáng)化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聯(lián)結(jié),既有利于提升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動(dòng)力,發(fā)展多功能農(nóng)業(yè),也有助于強(qiáng)化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穩(wěn)健性,增強(qiáng)農(nóng)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及風(fēng)險(xiǎn)應(yīng)對(duì)能力。
(一)鄉(xiāng)村空間治理為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提供地域支撐力
現(xiàn)在是推進(jìn)國(guó)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關(guān)鍵期,構(gòu)建現(xiàn)代鄉(xiāng)村治理體系成為鄉(xiāng)村振興和推進(jìn)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的重要內(nèi)容?。要根植于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的資源稟賦,通過(guò)鄉(xiāng)村空間差異化治理推進(jìn)制度改革、環(huán)境整治和規(guī)劃創(chuàng)新,搭建鄉(xiāng)村空間治理架構(gòu),全方位協(xié)調(diào)地方自然條件與人文屬性,形成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下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合力。
1.鄉(xiāng)村空間治理提供了健全的基層組織保障
鄉(xiāng)村空間治理的創(chuàng)新和完善,可以提升鄉(xiāng)村基層組織效率,推進(jìn)農(nóng)村制度、法律、政策的實(shí)施?,優(yōu)化城鄉(xiāng)格局,加快構(gòu)建以農(nóng)民為參與主體的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組織平臺(tái),滿足地域農(nóng)業(yè)發(fā)展需求。具體來(lái)看,鄉(xiāng)村空間治理通過(guò)創(chuàng)新基層組織機(jī)構(gòu)設(shè)置、農(nóng)村工作方式方法、黨員管理和激勵(lì)機(jī)制以及黨員干部培養(yǎng)和選拔方式,完善農(nóng)村基層黨組織的政治領(lǐng)導(dǎo)功能、致富帶動(dòng)功能等,保障鄉(xiāng)村公共領(lǐng)域系統(tǒng)有序、和諧運(yùn)作,以主動(dòng)適應(yīng)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發(fā)展新形勢(shì)。比起政府和社會(huì)資本,鄉(xiā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主導(dǎo)的鄉(xiāng)村振興更具有新內(nèi)生發(fā)展能力和韌性,可以作為農(nóng)村治理改革的重點(diǎn)之一?,要充分發(fā)揮集體經(jīng)濟(jì)在輻射帶動(dòng)、市場(chǎng)導(dǎo)向、要素來(lái)源、品牌盈利等方面的組織引領(lǐng)能力,有效地聯(lián)結(jié)從生產(chǎn)到銷售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因地制宜地推動(dòng)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
2.鄉(xiāng)村空間治理提供了成熟的制度環(huán)境保障
鄉(xiāng)村空間治理的重心在于拓展鄉(xiāng)村治理的制度空間?,通過(guò)鄉(xiāng)村空間治理能夠明確界定收益權(quán)利、減少信息成本以及降低交易的不確定性,調(diào)動(dòng)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主體積極性,充分發(fā)揮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中制度的激勵(lì)和信息功能,從而化解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的制度約束,進(jìn)而有效引導(dǎo)資源流轉(zhuǎn),撬動(dòng)資本、技術(shù)、人才、信息等要素投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另外,鄉(xiāng)村空間治理能有效緩解城鄉(xiāng)二元差距,減輕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對(duì)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投資要素配置的阻滯效應(yīng),建立完善的戶籍管理制度、城鄉(xiāng)社會(huì)保障制度以及城鄉(xiāng)收入分配制度,提高農(nóng)村公共服務(wù)供給質(zhì)量,構(gòu)建城鄉(xiāng)共享的優(yōu)質(zhì)公共服務(wù)體系,減輕城鄉(xiāng)收入分配差距以及農(nóng)民權(quán)利受損的嚴(yán)重程度,優(yōu)化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的制度環(huán)境。
3.鄉(xiāng)村空間治理提供了旺盛的鄉(xiāng)土文化保障
新時(shí)代背景下鄉(xiāng)村空間治理可以為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注入鄉(xiāng)村文化新內(nèi)涵,將鄉(xiāng)土文化傳承置于鄉(xiāng)村空間治理的框架體系內(nèi),拓展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充分利用鄉(xiāng)村空間特點(diǎn)和鄉(xiāng)土文化資源,重視地方性因素與力量?,挖掘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承載的多元鄉(xiāng)土文化內(nèi)涵,整合本土的知識(shí)、文化傳統(tǒng)以及資源要素,形塑農(nóng)村地域文化價(jià)值體系,建設(shè)現(xiàn)代鄉(xiāng)土文明。具體來(lái)說(shuō),一方面,鄉(xiāng)村空間治理通過(guò)改善農(nóng)村社會(huì)秩序以及農(nóng)民的精神、生活狀態(tài),尤其是文化與認(rèn)知壓力,發(fā)展根植于地域內(nèi)部、利益趨農(nóng)化的可持續(xù)內(nèi)生農(nóng)業(yè)模式;另一方面,通過(guò)克服帶有依附和被支配屬性的鄉(xiāng)村文化在城市化和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脆弱性,將 “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 作為新內(nèi)生發(fā)展平臺(tái),利用地域文化基因形塑地域文化發(fā)展屬性,改善農(nóng)民的思維觀念和行為方式。
(二)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提供農(nóng)業(yè)資源整合力
農(nó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是由農(nóng)村發(fā)展中的各個(gè)要素和發(fā)展環(huán)節(jié)構(gòu)成的,農(nóng)村區(qū)域系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發(fā)展資源稟賦匱乏,且與外界存在資本、技術(shù)、信息等關(guān)鍵要素的流動(dòng)障礙。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強(qiáng)調(diào)通過(guò)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將地方與更廣泛的區(qū)域甚至國(guó)際市場(chǎng)聯(lián)系起來(lái),從而產(chǎn)生農(nóng)業(yè)市場(chǎng)價(jià)值吸引外來(lái)資本,形成農(nóng)村地區(qū)可持續(xù)的內(nèi)生發(fā)展動(dòng)力。
1.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為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培育新型經(jīng)營(yíng)主體
農(nó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能充分結(jié)合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的區(qū)位結(jié)構(gòu)和資源稟賦,合理參照最新的農(nóng)業(yè)市場(chǎng)形勢(shì),通過(guò)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聯(lián)結(ji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要素集聚、農(nóng)業(yè)技術(shù)滲透、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管理體制創(chuàng)新等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為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提供有效的組織結(jié)構(gòu)。同時(shí),在農(nóng)業(yè)新型經(jīng)營(yíng)主體的培育過(guò)程中,農(nó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利用通暢的交易與合作信息傳遞渠道,既能有效克服信息不對(duì)稱、科技含量低等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基本約束,又能在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成長(zhǎng)培育過(guò)程中把握公平與效率的尺度。
2.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促進(jìn)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
從城市主導(dǎo)的空間集聚為特征的城鄉(xiāng)區(qū)域發(fā)展逐步走向城鄉(xiāng)互動(dòng)、空間融合的區(qū)域發(fā)展,需要農(nó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的持續(xù)推動(dòng),打破城鄉(xiāng)二元壁壘,實(shí)現(xiàn)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要素優(yōu)化組合。農(nó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可以有效打通產(chǎn)業(yè)、生態(tài)、教育、醫(yī)療、文化等多維一體的城鄉(xiāng)通道,積極發(fā)揮社會(huì)資本的協(xié)作再生產(chǎn)的優(yōu)勢(shì),還可以通過(guò)合理調(diào)節(jié)農(nóng)產(chǎn)品動(dòng)態(tài)供需平衡,打通農(nóng)業(yè)發(fā)展內(nèi)循環(huán),滿足農(nóng)業(yè)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環(huán)境需求?。農(nó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還具有吸收干擾和沖擊的復(fù)原能力,通過(guò)一個(gè)或多個(gè)具有社會(huì)意義的關(guān)系節(jié)點(diǎn)的交互反饋,確定驅(qū)動(dòng)和障礙因素,通過(guò)節(jié)點(diǎn)拓展和聯(lián)結(jié)重建來(lái)調(diào)解矛盾,進(jìn)而進(jìn)行再創(chuàng)新和再變革來(lái)提高城鄉(xiāng)交流發(fā)展的能力。
3.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改善農(nóng)業(yè)人力資本
由于我國(guó)耕地分布分散化、碎片化的特點(diǎn),現(xiàn)有以小農(nóng)為核心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組織模式在短期內(nèi)無(wú)法實(shí)現(xiàn)根本性變革。借助農(nó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可以不斷縮小城鄉(xiāng)人力資本差距,逐步提高農(nóng)民現(xiàn)代化水平,利用農(nó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引進(jìn)高素質(zhì)人才,構(gòu)建掌握農(nóng)業(yè)資本、管理、技術(shù)、信息等發(fā)展要素的人才結(jié)構(gòu),推動(dòng)人力資本動(dòng)態(tài)累積。此外,還能搭建良好的協(xié)作參與機(jī)制,培育農(nóng)業(yè)主體創(chuàng)新能力?。
4.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催化農(nóng)業(yè)創(chuàng)新引擎
為主動(dòng)適應(yī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新常態(tài),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之路應(yīng)聚焦農(nóng)業(yè)創(chuàng)新,提高農(nóng)業(yè)科技進(jìn)步貢獻(xiàn)率,搭建農(nóng)業(yè)全產(chǎn)業(yè)鏈創(chuàng)新體系,為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提供引擎動(dòng)力。農(nó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能加快資本、技術(shù)、信息等要素的流動(dòng),擴(kuò)散農(nóng)業(yè)技術(shù),促進(jìn)多領(lǐng)域、多行業(yè)、多環(huán)節(jié)協(xié)同創(chuàng)新,增加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鏈的技術(shù)優(yōu)勢(shì)。基于農(nó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內(nèi)生優(yōu)勢(shì)的農(nóng)業(yè)創(chuàng)新既能實(shí)現(xiàn)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的增值效益,又使得農(nóng)業(yè)創(chuàng)新收益最大程度內(nèi)化于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促進(jìn)農(nóng)業(yè)創(chuàng)新目標(biāo)由生產(chǎn)向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和社會(huì)綜合發(fā)展的目標(biāo)過(guò)渡?。
五、以產(chǎn)業(yè)融合促進(jìn)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
我國(guó)進(jìn)入新發(fā)展階段,農(nóng)產(chǎn)品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日益激烈,消費(fèi)者對(duì)農(nóng)產(chǎn)品品質(zhì)的要求越來(lái)越高,這既為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chǎng),也對(duì)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融合提出了新要求。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融合以新型經(jīng)營(yíng)主體為引領(lǐng),通過(guò)利益聯(lián)結(jié)推動(dòng)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功能拓展,提升區(qū)域農(nóng)業(yè)競(jìng)爭(zhēng)力,最終實(shí)現(xiàn)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
(一)發(fā)展高質(zhì)量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和服務(wù)組織,發(fā)揮社會(huì)協(xié)同優(yōu)勢(shì)
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2020年印發(fā)《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和服務(wù)主體高質(zhì)量發(fā)展規(guī)劃(2020—2022年)》強(qiáng)調(diào),創(chuàng)新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和服務(wù)主體,以推進(jìn)農(nóng)業(yè)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激發(fā)農(nóng)業(yè)內(nèi)生動(dòng)力。中國(guó)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融合的首要任務(wù)是構(gòu)建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體系,完善與創(chuàng)新經(jīng)營(yíng)主體之間的利益聯(lián)結(jié),帶動(dòng)農(nóng)業(yè)全產(chǎn)業(yè)鏈,打造多功能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模式下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組織要高度重視農(nóng)民發(fā)展主體權(quán)利、構(gòu)建農(nóng)企利益共同體,促進(jìn)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結(jié)構(gòu)與農(nóng)村地域系統(tǒng)資源稟賦相契合,通過(guò)農(nó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匹配農(nóng)業(yè)消費(fèi)需求。高質(zhì)量的農(nóng)業(yè)服務(wù)組織能夠通過(guò)市場(chǎng)化實(shí)現(xiàn)小農(nóng)戶和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的有機(jī)銜接?,在 “產(chǎn)前、產(chǎn)中、產(chǎn)后” 三階段服務(wù)上形成 “多層次、多形式、多主體” 的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化服務(wù)格局,不斷加強(qiáng)涉農(nóng)重點(diǎn)領(lǐng)域政府、社會(huì)扶持,探索區(qū)域內(nèi)生式社會(huì)化服務(wù)模式,助力提升農(nóng)業(yè)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力?,打好防范化解農(nóng)業(yè)重大風(fēng)險(xiǎn)攻堅(jiān)戰(zhàn),將農(nóng)業(yè)利益最大化趨向 “三農(nóng)” 。
(二)強(qiáng)化技術(shù)要素?cái)U(kuò)散滲透力,提升融合主體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
我國(guó)已經(jīng)進(jìn)入高質(zhì)量發(fā)展階段,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融合應(yīng)積極強(qiáng)化農(nóng)業(yè)技術(shù)滲透,提升本地農(nóng)業(yè)資源價(jià)值和產(chǎn)業(yè)融合競(jìng)爭(zhēng)力。要將農(nóng)業(yè)創(chuàng)新作為 “三農(nóng)” 工作的重點(diǎn)推進(jìn),提升新內(nèi)生式農(nóng)業(yè)共同創(chuàng)新能力,緊緊圍繞 “以科技創(chuàng)新驅(qū)動(dòng)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加快發(fā)展” 謀篇布局。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強(qiáng)調(diào)要因地制宜地激發(fā)農(nóng)業(yè)創(chuàng)新動(dòng)力,參照區(qū)域生物自然性和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階段性,因地制宜地開(kāi)展農(nóng)村區(qū)域創(chuàng)新研究,增強(qiáng)技術(shù)元素對(duì)農(nóng)村產(chǎn)業(yè)融合的滲透支持。加快促進(jìn)農(nóng)業(yè)科技向應(yīng)用實(shí)踐轉(zhuǎn)化,通過(guò)提供有利的技術(shù)環(huán)境支持和技術(shù)擴(kuò)散效應(yīng)促進(jìn)鄰域間產(chǎn)業(yè)融合,提高農(nóng)業(yè)科技貢獻(xiàn)率。政府應(yīng)該建立新的政策支持體系,完善農(nóng)業(yè)科技推廣的創(chuàng)新激勵(lì)體制和風(fēng)險(xiǎn)補(bǔ)償機(jī)制,搭建長(zhǎng)期穩(wěn)固的技術(shù)依托制度,壯大農(nóng)業(yè)科技推廣隊(duì)伍,提高農(nóng)民科技文化素質(zhì),借助信息化、網(wǎng)絡(luò)化等技術(shù)手段促進(jìn)產(chǎn)學(xué)研、農(nóng)科教結(jié)合,開(kāi)展科研院校同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的技術(shù)合作,提高產(chǎn)業(yè)融合主體的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
(三)深化土地流轉(zhuǎn)等機(jī)制改革,促進(jìn)城鄉(xiāng)統(tǒng)籌發(fā)展
在已有的農(nóng)地流轉(zhuǎn)制度框架下,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強(qiáng)調(diào),在統(tǒng)籌地域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發(fā)展水平、勞動(dòng)力文化素質(zhì)、社會(huì)保障水平等基礎(chǔ)上?,繼續(xù)創(chuàng)造性地開(kāi)展農(nóng)地流轉(zhuǎn)模式改革探索,順應(yīng)農(nóng)業(yè)市場(chǎng)化、規(guī)模化、信息化以及調(diào)動(dòng)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積極性等方面的發(fā)展要求。同時(shí),推進(jìn)城鄉(xiāng)土地產(chǎn)權(quán)同權(quán)化和資源配置市場(chǎng)化改革,在堅(jiān)持保護(hù)耕地的原則下,構(gòu)建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建設(shè)用地市場(chǎng),保障集體成員依法平等享有土地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流轉(zhuǎn)收益?。新時(shí)期推進(jìn)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應(yīng)著眼于城鄉(xiāng)地域系統(tǒng) “人+地+業(yè)” 協(xié)同發(fā)展,積極引入城鄉(xiāng)融合協(xié)作機(jī)制,創(chuàng)新城鄉(xiāng)土地配置與管理制度,探索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的科學(xué)路徑。只有從根本上改革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制度,才能產(chǎn)生干預(yù)和治理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的內(nèi)在推力,實(shí)現(xiàn)內(nèi)生于農(nóng)村的農(nóng)業(yè)自我積累和持續(xù)?,而非打造 “城市附屬品” 或 “城市贗品” 。
(四)重塑農(nóng)民參與主體地位,推動(dòng)人才振興帶動(dòng)農(nóng)業(yè)振興
產(chǎn)業(yè)融合的推進(jìn)既要堅(jiān)持扶農(nóng)、惠農(nóng)、富農(nóng)的原則,更要培養(yǎng)農(nóng)民的自身發(fā)展能力。農(nóng)民獲益多少取決于資源支配能力的大小,為農(nóng)民 “賦能” 可以改善農(nóng)民的弱質(zhì)性,增強(qiáng)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jì)交換力、政治協(xié)商力以及文化感召力。以增加農(nóng)戶權(quán)益為導(dǎo)向,推進(jìn)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制度、農(nóng)村政治制度以及農(nóng)民保障制度改革,激發(fā)農(nóng)民參與農(nóng)業(yè)發(fā)展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主動(dòng)性,增強(qiáng)農(nóng)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此外,就地取 “才” ,加強(qiáng)農(nóng)民教育培訓(xùn),注重鄉(xiāng)村本土人才建設(shè),滿足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融合在不同階段對(duì)不同類型農(nóng)業(yè)高素質(zhì)人才的需求。促進(jìn)參與型農(nóng)業(yè)創(chuàng)新,重視 “行動(dòng)中的知識(shí)” ,將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 “創(chuàng)新者” 和 “受益者” 合二為一,鼓勵(lì)農(nóng)民參與農(nóng)業(yè)創(chuàng)新,提高農(nóng)民農(nóng)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真正發(fā)揮農(nóng)民主體在農(nóng)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帶動(dòng)方面的內(nèi)推力。
(五)加強(qiáng)農(nóng)業(yè)供給側(cè)改革,推動(dòng)中國(guó)特色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
新內(nèi)生發(fā)展要求農(nóng)業(yè)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應(yīng)結(jié)合中國(guó)特色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其內(nèi)涵和發(fā)展道路要根據(jù)資源稟賦的客觀地域異質(zhì)性有所差別。當(dāng)前我們應(yīng)加強(qiáng)農(nóng)業(yè)供給側(cè)改革,以價(jià)格機(jī)制、確權(quán)改革、新型經(jīng)營(yíng)主體培育、支農(nóng)扶農(nóng)機(jī)制改革為重要著力點(diǎn)?,結(jié)合農(nóng)業(yè)市場(chǎng)需求和農(nóng)業(yè)宏觀發(fā)展趨勢(shì),形成高效的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和新型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化服務(wù)體系,挖掘農(nóng)村地域發(fā)展優(yōu)勢(shì),健全農(nóng)業(yè)長(zhǎng)效發(fā)展機(jī)制,從而推動(dòng)農(nóng)村產(chǎn)業(yè)融合,激發(fā)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動(dòng)力,有助于形成具有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保證國(guó)家農(nóng)業(yè)安全。
六、總結(jié)與展望
通過(guò)上文基于文獻(xiàn)視角的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研究可以看出,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為中國(guó)鄉(xiāng)村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jī)。基于 “重城輕鄉(xiāng)” 的農(nóng)村歷史遺留問(wèn)題,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亟需內(nèi)生發(fā)展動(dòng)力。鑒于我國(guó)處于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和鄉(xiāng)村振興的關(guān)鍵期,應(yīng)構(gòu)建中國(guó)特色的分析框架模型,探索中國(guó)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式發(fā)展的最優(yōu)路徑。本文通過(guò)對(duì)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約束和動(dòng)力機(jī)制的剖析,提出探尋實(shí)現(xiàn)農(nóng)業(yè)新內(nèi)生發(fā)展的模式,實(shí)現(xiàn)區(qū)域內(nèi)外各因素整合聯(lián)動(dòng),緩解農(nóng)業(yè)資源稟賦匱乏等約束條件,挖掘根植于本地的內(nèi)生發(fā)展動(dòng)力。為了更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鄉(xiāng)村內(nèi)生發(fā)展的重要性,仍然需要基于文獻(xiàn)研究和實(shí)地調(diào)查資料去完善中國(guó)農(nóng)業(yè)的內(nèi)生發(fā)展動(dòng)力機(jī)制解釋,進(jìn)行實(shí)證分析。
注釋:
① 孔祥智、何安華:《新中國(guó)成立60年來(lái)農(nóng)民對(duì)國(guó)家建設(shè)的貢獻(xiàn)分析》,《教學(xué)與研究》2009年第9期。
② [哥]埃斯科巴:《權(quán)力與能見(jiàn)性:發(fā)展與第三世界的發(fā)明與管理》,載《發(fā)展的幻象》,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頁(yè)。
③ 王志剛、黃棋:《內(nèi)生式發(fā)展模式的演進(jìn)過(guò)程——一個(gè)跨學(xué)科的研究述評(píng)》,《教學(xué)與研究》2009年第3期。
④ 參見(jiàn)[日]守友裕一:《內(nèi)発的発展の道》,農(nóng)山漁村文化協(xié)會(huì)1991年版,第121頁(yè)。
⑤ 參見(jiàn)[日]宮本憲一:《環(huán)境経済學(xué)》,巖波書(shū)店1989年版,第45頁(yè)。
⑥ M. Barke, M. Newton, The EU Leader Initiative and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gram in Two Rural Areas of Andalusia, Southern Spain,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97, 13(3),pp.319-341.
⑦ P. Midmore, J. Whittaker, Economics for Sustainable Rural Systems,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0(35), pp.173-189 ;X. Ji, J. Ren, S. Ulgiati, Towards Urban-Rural Sustainable Cooperation: Models and Policy Implicatio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213,pp.892-898.
⑧ 張丙宣、華逸婕:《激勵(lì)結(jié)構(gòu)、內(nèi)生能力與鄉(xiāng)村振興》,《浙江社會(huì)科學(xué)》2018年第5期。
⑨ 劉彥隨、周揚(yáng)、李玉恒:《中國(guó)鄉(xiāng)村地域系統(tǒng)與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地理學(xué)報(bào)》2019年第12期。
⑩ Y. Li, P. Fan, Y. Liu, What Makes Better Village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of China?Evidence from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Typica Villages,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9,83, pp.111-124 ;Y. Li, T.Zhou, et al., Spatial Pattern and Mechanism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in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of Qingzang Plateau, Geography and Sustainability, 2021, 2(3), pp.139-150.
? 朱啟臻、楊匯泉:《誰(shuí)在種地——對(duì)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力的調(diào)查與思考》,《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1年第1期。
? 陳雨生、陳志敏、江一帆:《農(nóng)業(yè)科技進(jìn)步和土地改良對(duì)我國(guó)耕地質(zhì)量的影響》,《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wèn)題》2021年第9期。
? 王頌吉、魏后凱:《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視角下的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提出背景與內(nèi)在邏輯》,《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19年第1期。
? 魏后凱:《深刻把握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的本質(zhì)內(nèi)涵》,《中國(guó)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20年第6期。
? 郭曉鳴:《中國(guó)農(nóng)村土地制度改革:需求、困境與發(fā)展態(tài)勢(shì)》,《中國(guó)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11年第4期。
? 葉興慶:《在暢通國(guó)內(nèi)大循環(huán)中推進(jìn)城鄉(xiāng)雙向開(kāi)放》,《中國(guó)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20年第11期。
? 張?jiān)吕颉⒎澹骸掇r(nóng)業(yè)集群品牌提升的關(guān)鍵影響因素研究》,《經(jīng)濟(jì)經(jīng)緯》2015年第1期。
? 劉俊顯、羅貴榕:《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中的問(wèn)題和路徑探究》,《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2021年第9期。
? 曾億武、宋逸香、林夏珍、傅昌鑾:《中國(guó)數(shù)字鄉(xiāng)村建設(shè)若干問(wèn)題芻議》,《中國(guó)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21年第4期。
? 張兆同、周應(yīng)堂:《論市場(chǎng)化農(nóng)業(yè)的制約因素與解決思路》,《經(jīng)濟(jì)問(wèn)題》2005年第1期。
? 戈大專、龍花樓:《論鄉(xiāng)村空間治理與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地理學(xué)報(bào)》2020年第6期。
? 張建國(guó):《鄉(xiāng)村振興視閾下鄉(xiāng)村治理體系優(yōu)化路徑研究》,《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2021年第9期。
? 方志權(quán):《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若干問(wèn)題》,《中國(guó)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14年第7期。
? 呂德文:《鄉(xiāng)村治理空間再造及其有效性——基于W鎮(zhèn)鄉(xiāng)村治理實(shí)踐的分析》,《中國(guó)農(nóng)村觀察》2018年第5期。
? 孫九霞:《新時(shí)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傳承與空間治理—— “文化傳承與空間治理” 專欄解讀》,《地理研究》2019年第6期。
? 何仁偉:《城鄉(xiāng)融合與鄉(xiāng)村振興:理論探討、機(jī)理闡釋與實(shí)現(xiàn)路徑》,《地理研究》2018年第11期。
? 張環(huán)宙、黃超超、周永廣:《內(nèi)生式發(fā)展模式研究綜述》,《浙江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7年第2期。
? M. Bogers, The Open Innovation Paradox :Knowledge Sharing and Protection in R&D Collabor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1, 14(1),pp.93-117.
? 潘錦云、汪時(shí)珍、李晏墅:《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改造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的理論與實(shí)證研究——基于產(chǎn)業(yè)耦合的視角》,《經(jīng)濟(jì)學(xué)家》2011年第12期。
? 秦秀紅:《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與農(nóng)村金融創(chuàng)新的關(guān)聯(lián)性研究》,《統(tǒng)計(jì)與決策》2012年第10期。
? 孔祥智、樓棟:《農(nóng)業(yè)技術(shù)推廣的國(guó)際比較、時(shí)態(tài)舉證與中國(guó)對(duì)策》,《改革》2012年第1期。
? 包宗順、徐志明、高珊、周春芳:《農(nóng)村土地流轉(zhuǎn)的區(qū)域差異與影響因素——以江蘇省為例》,《中國(guó)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09年第4期。
? 張勇、包婷婷:《農(nóng)地流轉(zhuǎn)中的農(nóng)戶土地權(quán)益保障:現(xiàn)實(shí)困境與路徑選擇——基于 “三權(quán)分置” 視角》,《經(jīng)濟(jì)學(xué)家》2020年第8期。
? 公茂剛、王學(xué)真:《農(nóng)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對(duì)農(nóng)業(yè)內(nèi)生發(fā)展的作用機(jī)理及路徑》,《新疆社會(huì)科學(xué)》2018年第3期。
? 梅學(xué)書(shū):《堅(jiān)持新的發(fā)展理念激活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內(nèi)生發(fā)展動(dòng)力》,《決策與信息》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