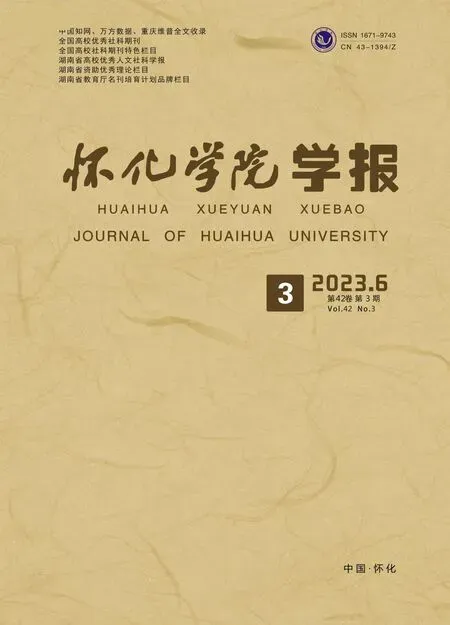論明中后期遼東地權關系的轉變
孟艷霞
(渤海大學,遼寧 錦州 121013)
明代遼東因地處邊疆,戰略位置極為重要,因此其土地管理形式與中原地區不同。明初,遼東推行軍屯田,土地完全公有化;明中后期,軍屯制逐漸被破壞,地權關系也由公有制逐漸向私有制轉化。地權關系的轉化不僅保證了遼東軍糧的供應,更為遼東邊疆的土地開發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同時直接反映了明代對遼東邊疆治理政策的調整過程,是遼東邊疆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軍屯制的破壞
洪武初年,朱元璋因遼東戰略位置的重要性,于此地大量駐軍,并開荒屯田。關于遼東軍屯田最早始于何時,文獻中并無記載,但洪武七年(1374)正月,“戶部言定遼諸衛初設,屯種兵食未遂,詔命水軍右衛指揮同知吳邁、廣洋衛指揮僉事陳權率舟師出海,轉運糧儲,以備定遼邊餉”[1],由該條記載看出,在洪武七年以前,遼東地區就曾推行過屯田,但未能成功,屯田之制也就此擱淺。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因遼東海運屢有海難發生,且勞民傷財,因而再次于遼東推行屯田。是年,國子監祭酒宋納獻《守邊策》曰:“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陛下宜選其有智謀勇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五百里屯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賊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2]朱元璋采納了宋納的安邊之策,在全國邊地開始推行屯田法,遼東于此時也逐漸推行屯田,并逐漸形成規模,進而達到巔峰。洪武永樂時期的屯田軍糧完全可供軍食,且倉有余糧。成化十九年(1483)九月,總理糧儲戶部郎中毛泰奏曰:“洪武初,遼東糧科俱從太倉海運,其后,罷海運置屯田,八分屯種,二分戍邏,每軍限田五十畝,租十五石,以指揮千百戶為田官,都指揮為總督,歲夏秋二征,以資官軍俸糧。自洪武至永樂,為田二萬五千三百余畝,糧七十一萬六千石有奇,當時邊有儲積之饒,國無運餉之費,誠足食足兵至要道也。”[3]洪武永樂時期,遼東的屯田達到25 300 余頃,糧71 萬余石,如此軍糧數量在整個明代達到了巔峰。
遼東屯田制的破壞開始于宣德年間,宣德四年(1429)二月,戶部尚書郭敦奏報:“洪武、永樂年間,屯田之例,邊境衛所,旗軍三分四分守城,六分七分下屯,腹里衛所一分二分守城,八分九分下屯,亦有中半屯守者。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提督秋成比較依例賞罰,倉有余糧。近年各衛所不依舊例,下屯者或十人,或四五人,雖有屯田之名,而無屯田之實。”[4]遼東大體也是如此。成化十九年(1483)九月,總理糧儲戶部郎中毛泰奏曰:“宣德以后,屯田之法雖曰寖廢,軍士猶余四萬五千四百,而糧亦視舊不減三分之一。”[5]成化年間的毛泰雖對宣德時期的屯田持肯定的語氣,但不難看出,宣德年間屯田已經寖廢,屯糧較之前也減少近三分之一。至正統年間,屯田制破壞更加嚴重,自然災害頻繁,導致屯軍生活艱難,無法交納科糧,此為屯田遭到破壞的主要因素之一。正統元年(1436)閏六月:“遼東定遠等衛奏:往年旱潦,所負屯田子粒上納艱難”[6]。正統六年(1441)十二月,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李浚奏:“今歲遼東、廣寧、寧遠等十衛屯田俱被飛蝗食傷禾稼,屯軍缺食,并乏下年種糧,愿于官廩借給,俱候秋成,抵數還官。從之。”[7]此兩條記載雖為旱災、蝗災導致屯糧不足,屯田不濟,但也足可證明此時倉糧儲存已不足,導致屯軍在遇到災害時出現缺食的現象。正統九年(1444)正月,巡撫遼東監察御史李純奏:“遼東各衛隊伍并帶管驛遞鋪鹽鐵場旗軍下余丁,除老疾幼小不成丁外,其少壯者五萬四千八十六名,中間有六七丁、八九丁者,耕種自食,多不納糧。乞行遼東都司從實勘數,每軍除與一丁幫助,其余每三丁摘撥一丁,與田五十畝屯種,年終照例比較子粒于該倉交納備用。”[8]奏議得到了準許。顯然李純已經認識到屯軍逃逸是導致屯田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提議通過增加屯田人員的辦法來補足。
遼東屯田之法盡壞于成化年間,這從總理糧儲戶部郎中毛泰的奏議中就可得到印證,成化十九年(1483)九月,毛泰奏曰:“近被邊方多事,屯田之法盡壞。巡撫官相繼興復,其數少增,又歲運銀十萬,兼開中淮浙鹽所用,尚乏。都御史滕昭乃于操練馬軍內遴選弓馬生疏者三千余名退歸屯田,歲省各軍所支糧豆六萬余石,而得屯糧三萬余石。至成化十二年,都御史陳鉞仍以昭所選屯軍勒歸操練,遂罷徵糧,又減除無名屯軍六萬余名,以五年計之,共減糧三十萬石。故今所存正軍惟一萬六千七百余名,而歲徵糧止一十六萬七千九百石,又以荒歉蠲免,歲不足七八萬之數,較于舊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故遼東三十二倉通無兩月之儲。”[9]毛泰在奏議中指出“邊方多事”,屯田軍士嚴重不足,是造成屯田之法盡壞的主要原因。朝廷也曾采取各種措施試圖恢復屯田,但都于事無補,以至于到成化十九年(1483)時,屯軍只有16700 余名,每年的屯田糧167900石,再因荒歉蠲免,歲征糧不足七八萬,倉庫儲糧嚴重不足,可見此時屯田制的破壞已經相當嚴重。以至于在成化二十年(1484)八月,毛泰再次奏曰:“遼東軍士舊以二分守城,八分屯種,而今乃反是,其都司衛所官員又調以修筑邊墻,致誤農事,乞申永樂三年赦諭屯田官軍紅牌事例,一面,永為遵守,今后凡有修墻等務,止以見在一十八萬舍人、余丁輪番調撥,其屯田軍士不許擅科擅役。”[10]毛泰試圖通過保證屯軍數額的辦法恢復屯田,奏議雖然得到允許,但屯田并未得到恢復,屯田積弊反而愈積愈繁。弘治十二年(1499)三月,戶部覆奏總理遼東糧儲郎中史學所言遼東四事,其一謂:“遼左屯田為弊最多,請行移巡撫、巡按會同本官逐一清查,其屯田官軍不許別衙門更調差遣。”[11]顯然毛泰的提議并未奏效,屯田積弊并未得到改善,反而愈加嚴重,甚至在全國邊地屯田中“為弊最多”。屯田軍“擅科擅役”“更調差遣”,不能保證屯田軍士正常耕種,耽誤農事,是造成該時段屯田遭到破壞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采取的各項補救措施也是圍繞著如何保證屯田軍士數額以致不誤農事展開的。
除了屯田軍士“擅科擅役”,外逃也是造成該時期屯田遭到破壞的主要因素。弘治十四年(1501)十二月,監察御史胡希顏查遼東邊儲以及邊備事宜時奏:“遼東舊額軍士十八萬有余,今物故逋亡過半,勾考不前。請并行巡按御史照清軍事例,將遼東見在軍冊與兵部所藏宣德間軍冊查對,以便勾考。”[12]說明遼東軍士逃亡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軍士的外逃造成田地大量荒蕪,無人耕種,于屯田而言,無疑是致命的。
田地荒蕪,糧食供應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遼東的需求。在此情況下,營田制出現。營田制以步兵營為單位佃種屯田或開墾荒地佃種,其最早當出現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是年三月,遼東巡撫王之誥提出于遼東開墾荒地的八條建議:具體為以營為單位,“以田九百頃為率”,“將各營見在步軍六千四十余名更番撥用”。“每牛一具,種田一頃五十畝,牧者一人,耕者三人,其牧者給草料,免其雜差,惟耕時隨牛下田,與三人同力合作”。“計田九百頃,用種子二千四十石”。“每營開田一百五十頃,軍夫四百名,委官五員,約工百日該費口糧六百一十五石、牛百具,該豆七百五十石、草萬束,俱于本田收獲糧草動支”。“每種田九百頃存積柴草”,除部分留以飼牛,其余變賣以補牛具農器。及時修補倉儲,“除收貯屯鹽二糧外,余倉悉收營田子粒”。并“責成宜將河西營田行接管都御史,河東營田行巡按御史,互相督責,各道并大小將領以實舉行,其奉行不力及因循誤事者,歲終查明參究,仍乞敕接管都御史協心共濟以圖成效”。[13]此八條建議經過戶部議覆后,俱從之。以營為單位,每營開田900 頃,在營步軍輪番耕種,并配給種子、耕牛及農具。關于此次推行營田制的效果,文獻中沒有明確的記載,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軍士不斷外逃、土地勞動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屯田制已經完全被破壞,與之相仿的營田制也不會收到很好的成效。這從明代留存下來的遼東檔案中可以得到印證。遼東檔案中隆慶四年(1570)二月“遼海東寧道右參政呈報各衛所原額屯田荒蕪已種新增及收獲谷豆等清冊”記載,定遼前衛“步軍佃種營田一十三頃,征谷豆二百八十六石”。[14]另有某衛“步軍佃種營田二十七頃,該征谷豆五百九十四石”。[15]根據該檔案的記載,定遼前衛和某衛佃種營田的規模都比較小,可見并沒有實現大規模推廣。
二、科田大量出現
至嘉靖年間起,屯田大量荒蕪,屯糧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遼東的需求,頻頻告匱,于此背景下,一種新的承種方式開始出現,即召民佃種荒蕪的屯田,也即文獻中記載的“召人佃種田”。關于召人佃種方式的出現最早始于何時,文獻中并無記載。但明代遼東地區留存的關于屯田的檔案中明確記載有隆慶四年(1570)二月召人承種田之田畝數。上文所述“遼海東寧道右參政呈報各衛所原額屯田荒蕪已種新增及收獲谷豆等清冊”檔案中詳細記載了各衛所屯田、承種田等的地畝數額,如其中記載蒲河中左所“原額屯田一百一十一頃,共谷豆二千三百七十六石,谷一千五百一十八石四斗,豆八百五十七石六斗。已承種田一百二頃六十畝共谷豆二千二百五十七石,谷一千四百四十二石四斗,豆八百一十石六斗。節年承種并上年復過召人佃種田九十二頃二十畝,征完谷豆二千二十八石,谷一千二百九十六石四斗,豆七百三十一石六斗。今次復過召人佃種田一十頃四十畝,該隆慶三年征完谷斗二百二十九石,谷一百四十六石,豆八十三石”。[16]關于承種田的記載,并非蒲河中左所一處,撫順所、定遼前衛、定遼左衛等皆明確記載承種田數額。檔案中記載“今次復過召人佃種田一十頃四十畝,該隆慶三年征完谷斗二百二十九石,谷一百四十六石,豆八十三石”。說明隆慶三年(1569)承種田就已經存在。檔案中標注時間為隆慶四年(1570)二月,正值冬末,非耕種時節,那么其記載田畝額當為隆慶三年(1569)數額。隆慶三年承種田已經規模化,則可見,承種田當出現于嘉靖年間。
另外,一件隆慶六年(1572)名為“定遼后衛東寧衛原額屯田荒蕪已種佃種及收獲米谷豆清冊”的檔案詳細記載了定遼后衛東寧衛屯田已經佃種田的數額,即“定遼后衛原額屯田674 頃,已承種田406 頃77 畝5 分,節年承種并上年復過召人佃種田404 頃77 畝5分,今次復過召人佃種田2 頃。東寧衛原額屯田263頃50 畝,已承種田140 頃50 畝,節年承種并上年復過召人佃種田126 頃50 畝,步軍佃種營田13 頃,今次復過召人佃種田1 頃”[17]。至隆慶年間,承種田已經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甚至有些衛所承種田畝額已經與屯田畝額相當。承種田的出現相當大程度上彌補了屯田的不足,因此一經出現就被大范圍地推廣開來。伴隨著承種田的出現以及推廣,科田逐漸出現并迅速發展。
科田出現有兩種形式:一為民人佃種軍田或開墾荒蕪屯田而得之田;一為官員隱占屯田,終發展為科田,科田的出現標志著遼東地權關系向私有化發展。關于第一種形式科田出現的時間,文獻中亦無記載。隆慶三年(1569)五月,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提出了《遼東屯田使宜十一事》,其中有“無論民兵有力能開荒者,給以牛種,寬限起科,若逼近虜巢,永不徵稅……開荒之初即苦,徵歛無利有害,往往中廢,宜限六年之后方酌遠近肥瘠定則起科”[18]的記載,雖然龐尚鵬于隆慶三年(1569)提出鼓勵開荒“寬限起科”的提議,但其實佃種或開荒科田在隆慶三年(1569)以前就已經出現,并且已經具有了相當的規模。那么這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呢?如上文所述,此種形式的科田是伴隨著召人承種田而出現的,即此亦出現于嘉靖年間,這從遼東檔案文獻中亦可得知。
遼東檔案中有嘉靖二十五年(1546)正月二十三日金州等城指揮僉事為周鐸等軍余聯名報請開荒情愿照例起科事給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的呈文。記載曰:周鐸、牛伯安等十三人具系金州衛前所百戶黃流所納糧軍余,因“各軍田土續被大河連年□□……為率,止存其一,糧草上納……□□糧從地出,節因虧累不過。竊見本屯附近,挨連官……佃一區,素無開墾,欲便告報耕種,奈無明文,未敢擅專。今蒙□合事例許令開墾,伏望可憐,準委公正官員踏撥,準給有名軍余承種,情愿照例起科,有此投明,具狀上告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老爺處施行”。[19]周鐸、牛伯安等十三人的請求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初三日得到允準,令地方官員會同周鐸等人“從公踏勘,得堪種荒佃二段,丈量一頃三十畝,其水洼去處不堪開種,照舊牧畜,除將堪種者撥給周鐸等一十三名領種,照依下等田事例,每畝納谷五升,共六石五斗,合候呈詳允日,行令該衛,收入籽粒循環冊內征納”。[20]在實際踏勘中,“原踏地名龍鳳寺荒佃一頃三十畝,并今復踏出盜開相連荒佃五十四畝五分,共一頃八十四畝五分,俱給周鐸等一十三名領分均種,通取庫收領狀繳照”。[21]以上記載中,關于軍余開荒起科的事例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以前當已經出現,不然周鐸等人也不會貿然請求開荒,只因當時沒有明文規定,故而上文請求,并得到準許。另外,在實際踏勘時發現盜開荒地五十四畝五分,一并將其分給周鐸等十三人耕種,照例起科。說明遼東地區盜開荒地的現象已經普遍存在,這些私自盜開的荒地雖沒有明文規定屬于個人,但實際已經成為私有財產,可見土地的私有化過程已經在悄然進行。
至隆慶年間,科田面積迅速擴大,其規模已經超過屯田,成為遼東耕田的主要部分。上文所述“遼海東寧道右參政呈報各衛所原額屯田荒蕪已種新增及收獲谷豆等清冊”中除了記載有屯田、承種田等田畝額,對科田亦有詳細記載,其中定遼左衛“原額屯田一千一百三十一頃,共谷豆二萬四千八百八十五石三斗四升。……原額復過新增科田共四千二百二十頃八十□畝二分一毫九絲,米谷豆二萬二千三百□十石九斗三升四合五勺六抄六撮六圭五粟”[22]。由此可見,至隆慶三年(1569)時,定遼左衛屯田1131 頃,新增科田4220 頃,在該地區科田已大面積存在,其規模遠遠超過了屯田。
官員隱占屯田是科田的又一主要來源。關于官員隱占屯田的記載最早出現于正統十年(1445),是年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李純曰:“遼東東北地方廣闊,軍馬眾多,官軍俸糧、馬草俱憑供給,近年都司衛所多私役軍余,將膏腴者耕種收利入己,磽薄者撥與軍屯,有名無實,致軍人饑寒。”[23]之后官員隱占屯田的現象愈演愈烈,甚至達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成化十三年(1477)春正月,戶部議覆整飭邊備兵部右侍郎馬文昇關于遼東的奏議中記載:“遼東各衛近城膏腴田地多被衛所官員占種。”[24]弘治十五年(1502)十月,右少監劉恭“在遼陽私役軍余千余人,占種官地三百余畝”[25]。嘉靖八年(1529)五月,巡按遼東監察御史王重賢奏曰:“遼東鎮守太監白懷,已故鎮守總兵麻循,監槍少監張泰,遼陽副總兵張銘,分守監丞盧安,參將蕭滓、李鑒,游擊將軍傅瀚各占種軍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頃,少者十余頃,宜追奪罰治。”[26]嘉靖年間官員隱占屯田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為官者多有隱占,下起衛所官員,上至鎮守總兵、鎮守太監、副總兵、參將、游擊將軍等各階層官員皆有隱占。規模不等,多者達到了二百五十余頃,少者也有十余頃。被官員隱占屯田的現象屢禁不止,因而朝廷不得不承認此類田地的存在,那么該類田地也就成為了私有財產,并規定按歲起科,如此該類田地也就成為了科田。
萬歷十年(1582)三月,遼東巡撫周詠對遼東田地進行了一次清理,“丈出屯地八千九百三頃五十余畝,屯糧一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余石,科地米地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八頃七十余畝,科糧地米九萬九百余石”。[27]由該記載可以看出,至該時期,遼東的耕地分成了兩類,即屯田地和科地,總地畝額為33 092 頃20 余畝,屯田地8903 頃50 余畝,占總耕地的26.9%,科地24188頃70 余畝,占總耕地的73.1%,科地面積已經遠遠超過了屯田地面積,遼東田地私有化已經相當嚴重。至崇禎年間,遼東地區的田地已經完全私有化。崇禎二年(1629),在論及遼東屯田時,給事中汪始亨“極論盜屯損餉之弊”,畢自嚴曰:“相沿已久,難于復實,請無論軍種民種,一照民田起科。……帝是其議。”[28]畢自嚴的提議得到了崇禎帝的認可,并推廣開來。至此時,遼東的田地已經完全成為科田。
三、私自開墾無科田
隱種無科田是明代中后期遼東地區土地私有化的又一主要表現,即民人私自開荒,盜種而不納糧的田地。上文所述,嘉靖二十六年(1547),在準許周鐸開荒起科的批文中,在實際踏勘撥付田地時,就曾勘出盜開相連荒佃五十四畝五分。由此可見,無科田的出現當早于科田。關于無科田的規模文獻中鮮有記載,從撥付周鐸開荒起科田時,偶然丈得有人私盜開荒田一事中可以看出,私自開荒現象并非一時一地,其他地方亦是存在的,但規模并不會很大,畢竟私自開荒無科田不被制度所允許。
其實在科田出現以后,無科田也是一直存在。一份明代遼東檔案就記載了定遼前衛清查高承德等隱種無科田畝的事件,其記載萬歷三十三年(1605)六至七月“犯人高承德等七名到官,查得原告……倉等情,未經踏丈,有礙問理,擬合就行。為此,牌仰……鄰臺長人等,將高承德各所種無科田畝挨段逐一丈量明白……無科若干,是否隱種,果否虛實,□做等第,一同開具的數,以憑……生事,徇情遲延,惹究未便。須至牌者。計押去犯人七名:高承德、高承棟、高承柏、高承亮、高承功、高承才、高承善(原告人)。”[29]“前事。蒙批,本司……高景(“承”之訛)善隱種肥田十頃,無……便,押帶一干人犯,眼同彼處地鄰……明白,要見有科若干,有無倉串可憑……呈來,以憑問理轉報施行,本官勿得生事……”[30],該檔案為定遼前衛清查高承德等隱種無科田畝的文件,共有七件,此為第一、二件,為憲牌,三、四、五、六為呈文,七為稟狀。經過實地踏丈,高承德等人確有隱種田畝的事實,共計十頃有余,單東寧衛地方疙疸(“瘩”之訛)寺屯一處計五頃九畝五分。另“查照東寧衛循環薄籍□□科田二十六段,該田一頃八十一畝七分五厘七毛。照下等每畝納科谷五升,該谷九石八升八合。……(無科田)四十段,該田四傾四十九畝三分六厘四毛,照下等每畝納科谷五升,該納科谷二十二石四斗七升五合”[31]。在對高承德等人私自開荒無科田實際丈量后,按照土地的等級對其進行了科糧的追繳。
由該檔案記載可以看出:第一,高承德等人隱種無科田數額是很大的,達到了十頃有余,這較嘉靖二十六年(1547)勘得隱種田地的規模有了擴大,如此大規模的隱種在其他地方亦當存在,可見,至萬歷年間無科田逐漸規模化。第二,高承德等七人本為定遼前衛人,但卻到與之相鄰的東寧衛開荒種田,可見當時土地管理是相當混亂的。這種混亂的局面更加劇了土地私有化的進程,在政府鼓勵開荒的大背景下,民人相繼開荒墾種,多有民人隱報開荒田畝數額避免納科,無科田的存在使遼東土地私有化更近了一步。
四、田地買賣出現
無論是召人耕種還是隱占屯田或者無科田,私有化田地的出現必定會帶來田地買賣的出現,田地買賣現象的出現標志著地權私有化的進一步加深。
明代遼東檔案中有記載田地買賣的檔案,有一件檔案記載金州衛桑景秀等買田納糧的清冊。正統二年(1437),在官桑景秀故祖桑政用青犍牛一只買何仲文田八十畝,納糧十六斗。正統十年(1445)九月,在官陳和故祖陳榮用綿布二十匹買田六十畝,納糧一石二斗。弘治年間,“張鎮所故丁程子敬田七十五畝,代納科糧……本衛百戶王尚賢所故丁李彬田四十畝,納糧……兩,買伊衛百戶周昂所未到余丁陳祥田八十畝,納……一百一十匹,買伊衛百戶韓月所故丁商見田七十畝”。[32]另有其他人等買田記錄。檔案資料多有漫漶,但從有限的記載發現:第一,此處的“買賣”當具有轉讓的性質,由“代納科糧”四字可見,轉讓后由買主代替原田地耕種者繳納稅糧,另外,該檔案只記載了轉讓的情況,但并沒有契約,而土地的買賣是需要簽訂契約的。可見,此檔案中記載“買賣”的田地當為屯田之間的相互轉讓,非實際的買與賣;第二,“買賣”的田地需要繳納規定的糧食或布匹;第三,在“買賣”田畝中多有在官之人以及軍下余丁、故丁,說明土地轉讓在官籍以及軍下余丁中普遍存在;第四,由檔案中記載時間來看,至少自正統年間開始,田地轉讓就已經存在,并一直有延續。
另有檔案載:“嘉靖年間有明本堡,在官軍人劉趕兒故祖劉海四缺費,將伊祖業科田二日(每日六畝左右),立契絕賣與今告王朝親伯王春耕種,代納口糧二斗五升,又將田二典與□官張天祿耕種。”[33]劉海四因缺費,將祖業科田約十二畝賣與王春耕種,又將兩處田地典當給張天祿耕種。另一件檔案為蓋州衛指揮下舍丁張近伯賣給金七的土地契約,標注時間為萬歷三十年(1602)七月,其中載曰:“立契人張近伯,系蓋州衛指揮下舍丁,因為無錢使用,情……祖田一塊,門東,言出賣與金七名下承種,言地價錢銀……整,當日交足,并不短少,其田不論遠年近日,錢到取贖,□□無憑,立地契存照。”[34]舍丁張近伯因無錢使用,將一塊祖田賣與金七。以上兩件檔案中記載的田地買賣與上文所述金州衛桑景秀等買田有實質的區別,桑景秀等買田為屯田之間的相互轉讓,并未實現地權的私有化。但該兩件檔案中記載的田地買賣,為實際的買與賣,并立有田地買賣契約,已經完全實現了地權的私有化。
雖然關于明代遼東地區田地買賣的檔案文書并不多,但從有限的檔案資料中可以窺見明中后期遼東地區田地買賣的概況。在科田、無科田出現以前,遼東地區的田地多為屯田,田畝是不可以買賣的,但可以相互轉讓。隨著科田、無科田的出現,田畝之間可以自由買賣。上文中劉海四、張近伯所賣出的田地皆為科田,可見,田地的買賣是伴隨著科田的出現而出現的。
綜上所述,遼東地區的地權關系經歷了從公有到私有的轉化過程,此過程也是伴隨著軍屯制的破壞而產生的。明初,遼東推行屯田制,在洪武永樂時期達到高潮,屯田25 300 余頃,屯糧達到71 萬石有奇,此時遼東的田地皆為軍屯田,即田地皆為公有。自宣德年間開始,屯田逐漸遭到破壞,屯糧大量減少,屯軍嚴重不足是造成屯田遭到破壞的主要原因。至隆慶年間,營田制出現,但營田制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在田地大量荒蕪、糧食收入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召人佃種屯田、鼓勵開荒的方式來增加糧食收入,佃種田以及科田出現,使遼東的地權開始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轉化,至崇禎二年(1629),遼東的田地已經完全科田化。另外,在科田出現的同時,無科田也大量出現,更加劇了土地的私有化。隨著地權由公有向私有的轉化,田地買賣成為普遍現象,標志著私有化進程的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