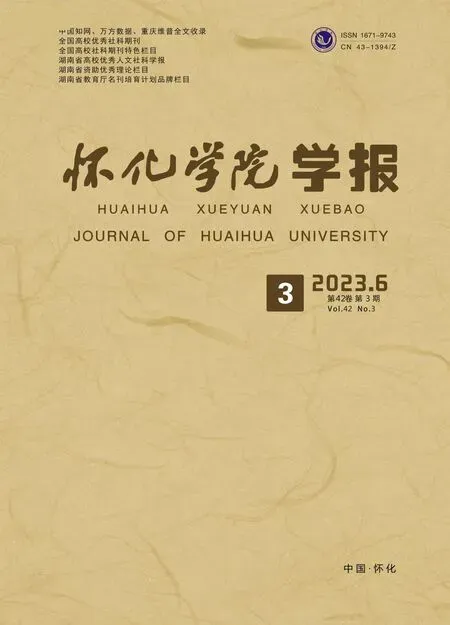明代推官的職能演變及其對地方政治的影響探析
夏 瑩
(皖南醫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與省級政府的三權分置不同,明代府級政府的權力相對集中。知府作為一府之長,一府小大之政“咸掌之”,不僅政務繁雜,權力亦過重。有鑒于此,明廷在設置佐貳官協助知府疏理庶務的同時,也分走了知府相當一部分權力。其中,推官的設置便是為了分知府的“獄訟”之權。明代推官自洪武三年設立之后,其職能從最初“職專理刑”到中后期“亦兼察吏”。推官獲得了司法權之外的監察權,在地方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對于明代推官,學界在有關明代地方制度以及明代基層司法體系的研究中已有所討論,但多為推官司法職能方面的單向考察,對明代推官的設置、職能演變及其對地方社會的影響等方面的綜合研究,則明顯不足。有鑒于此,筆者在系統搜集資料的基礎上,對上述問題作一初步考察。
一、明代推官的設置
洪武三年,監察御史鄭沂向明太祖進言:“人命至重,古人所矜,各府宜設推官一員,專掌刑名,不預他政,庶責有所歸,而人無冤抑。”[1]明太祖采納了鄭沂的建議,于各府設推官一員,推官的設置遂成為有明一代的定制。
(一)明代推官的來源
關于明代推官的來源,吳艷紅指出,“在推官選授中,進士以及舉貢生是最重要的兩大選人群體”。[2]不過,根據明代選舉制度的相關記載,還可以對其觀點進行一些補充。
推官作為明代“體制”內的官員,其選任與明代的“取仕”制度大體相合,即以科目為核心,其他途徑為補充。如吳艷紅指出推官的兩大選人群體——進士及舉貢生皆是出身科目。除科目之外,還有出身吏員或布衣者,可以被選任為推官。吏員之所以可以被選任為推官,與明代實行的吏員升轉制相關。明人丘浚稱:“我朝選舉之制比漢、唐、宋為省,科舉之外止有監學歷仕、吏員資次二途以為常選。”[3]吏員資次即是所謂的吏員升轉制。明初由于人才缺乏,選官不拘流品,由吏員出身而擔任府州縣官的例子并不少見。擔任一府推官的,亦大有人在。如郭子貞,杭州人,初為吏員,洪武二十二年任建寧府推官[4];嚴迪聰,分宜人,永樂間任黃州推官[5];王得仁,初為衛吏,以才薦授汀州府經歷,再遷為汀州府推官[6],等。除吏員外,布衣出身者亦可擔任推官。明初,朝廷一再下令求賢,薦舉大興。洪武年間,薦舉甚至一度成為明廷選補官員的主要途徑。《明史·選舉志》稱,其時“吏部奏薦舉當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馀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馀人”[7]。這么大批次的除官,留為京官者只是少數,大多數則被分散到天下各府州縣,擔任地方官。其中擔任推官的亦不在少數,如漳州府推官王得閏,以儒士舉;延平府推官陳濟,以孝廉舉;興化府推官林文遠,以明經舉[8],等。
得益于吏員升轉制和薦舉制的興盛,明初推官的來源并不僅限于科目出身。而后資格漸循,推官的選授也越來越嚴格。成化時,吏部奏稱:“正七品之職知縣、推官俱簡任,不輕授,人多闕少,往往有壅滯之嘆。”[9]至弘治年間,吏部尚書馬文升稱:“我朝舊例,……及各府推官有缺,俱于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10]可見當時推官的除授已經非科目出身者不可了。
(二)推官的行取
《明史·職官志》稱:“給事中、御史謂之科道。……自推、知入者,謂之行取。”[11]即行取是指推、知入為科道官。然而,潘星輝則認為:“‘行取’意謂‘行文取用’,其實施對象并無限定。隨著科道選人的更變,大約自明中期開始,一般特指科道急缺行取。”[12]考之《明史》,筆者認為,推官的行取大致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推官擢升為科道官;其二,推官除授為部寺官,主要為六部各清吏司主事和大理寺評事。①
雖然蘇嘉靖認為推官、知縣行取為科道官的制度確立于成化六年[13],但筆者認為此觀點是值得商榷的。成化六年吏部的行取意見主要是針對御史而言,并無明確規定今后推官、知縣可以行取為六科給事中。事實上,直到弘治十二年,監察御史余濂才首次提出給事中“以知縣、推官補之”,不過,吏部卻以“給事中品從七,知縣、推官品正七,難以選補”為由駁回。[14]到正德末年,“大臣畏忌新進敢言,乃盡廢進士考選之例”,給事中“始以在外推官、知縣照御史例選補”;世宗登極,詔令悉復舊例,給事中以進士考選,“然應詔止于一行而旋復寢”。[15]直到此時,推知行取為六科給事中的制度才最終確定,推知行取為科道官的制度也因之固定了下來。而推官行取為部寺官的制度大致確立于弘治年間。弘治十二年,監察御史余濂建議“給事中、御史、主事有缺,以知縣、推官補之”[16]。首先確立了推官、知縣行取為各部主事的制度。而后,至弘治十八年,監察御史曾大有又提及此事,“謂今后部屬等官有缺,請如六年、九年考滿到部進士、舉人出身推官、知縣、教官,曾經旌保政績可驗者,與進士相兼銓補”[17],事下所司,基本上確立了推官行取為部寺官的制度。
至于推官是行取為科道官還是部寺官,根據記載,大致“考選之例,優者授給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18]。雖然各部主事及大理評事的品級高于給事中、御史,但是在推官的行取中卻屬于“下下之選”,這一點可以從明人的態度中略窺一二。如嚴州推官陸樹德,“行取當授給事、御史”,會其兄陸樹聲“拜侍郎”,出于回避的需要,“乃授刑部主事”[19];杭州推官蔡懋德因不愿屈事顧秉謙,“以故不得顯擢。授禮部儀制主事”[20],等。無論是行取為科道官,還是部寺官,對推官來說,都是在他們的仕途上開辟了一條快速升遷的捷徑。以“下下之選”的部寺官而言,再進一步,都會升為員外郎、郎中等官,而后外放地方積累年資,一旦年資積滿,入京便可為卿貳②。而御史更是“俟有勞績,兩考而擢京堂,不期月而簡開府,年例則一歲而轉方面,誠重之也”[21]。當然,這種行取上的優待,并非所有推官都能享受到。《明史》稱,“推、知行取,則進士十九,舉貢才十一”[22],這意味著進士出身的推官行取的可能要遠高于舉貢出身的推官。不僅如此,在之后的仕途升遷上,進士出身的推官也遠比舉貢出身的推官有優勢。明人管志道稱:“舉貢出身之推官、知縣,例得選御史而補部曹。然以政事稱最者,終不得與翰林文學之臣并顯。”[23]不過,對舉貢出身的推官來說,行取制度的實行還是為他們打開了一條從地方通往中央的捷徑,因為在通常情況下,“京官非進士不得考選”,而“推、知則舉貢皆行取”。[24]
二、明代推官的職能演變
推官最初設置的目的,是為了協助知府疏理一府“獄訟”。成化三年,直隸新城縣縣丞邢政上言稱:“切(竊)見各都、布、按三司及各府俱有斷事、理問、推官等官,專理刑獄,所以少有冤抑。”[25]明代推官的職能,一般都說是“專理刑獄”或者“專掌刑名”。然而到了萬歷四十八年,吏部尚書趙煥稱:“推官職司理刑,亦兼察吏,必無瑕者處之,乃可。”[26]《明史·職官志》亦稱:“推官,理刑名,察屬吏。”[27]這就與推官最初設置時的“獨專刑名”有很大改變。那么,明代推官的這種職能上的改變起于何時呢,在改變的背后又有著怎樣的動因呢?
(一)地方雙重監察體制的敗壞與推官監察權力的獲得
洪武九年,明太祖朱元璋廢行省,設三司。其中,作為三司之一的提刑按察司擔負了審刑監察,肅清地方的重任。至永樂年間,“遣御史分巡天下,為定制”[28]。于是,提刑按察司與巡按御史共同監察地方的雙重監察體制開始形成。[29]在雙重監察體制下,按察司與巡按之間并無統屬關系,正如《明會典》所言:“國初遣監察御史與按察司分巡官巡歷所屬各府州縣,頡頏行事。”[30]一個“頡頏”,便點明了二者之間的關系。大約從弘治開始,這種情況悄然發生了改變。弘治六年,孝宗下令:“今后朝覲之年,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31]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原來對于方面官的考察系于吏部與都察院,現在卻把此權力交給撫按,這為巡按凌駕于監司之上提供了制度支持。巡按既然獲得了對布按二司的考察舉劾權,其監察權力自然大增。原本與巡按“頡頏”行事的按察司,只能俯首聽命。于是,地方官吏之賢否皆系于巡按。明人葉春及稱:“天下司府州縣官吏賢否,獨在撫按。”[32]明人趙南星亦稱:“安民之道,莫如察吏,察吏之道,莫如責成撫按”[33],實際上是巡按,因為巡撫的主要職責并非監察。然而,隨著巡按權力的膨脹,相應的人員配置卻并未隨之增加。據《明會典》載:“凡監察御史巡按,許帶書吏一名,照刷文卷,許帶人吏二名。若應用監生,臨期奏請。”[34]僅憑這一二人等,在“歲一更代”的情況下,巡行一省數千里之地,面對“吏職如棊置,吏弊如絲棼”[35]的復雜局面,想要有所刺察,力實未逮。于是,在地方上設置耳目,協助監察,便成了巡按的必然選擇。
而推官之所以會被巡按青睞,原因不外有三:其一,推官郡縣刑名所系,所關甚重。御史巡按地方,除督責考察有司之外,也不過是“征錢糧,理詞訟”而已[36],而推官本身便是“理詞訟”之官。巡按在地方錄囚徒,理冤枉,若有推官相助,往往會有事半功倍之效,可以極大地節省時間、精力,提高效率。其二,御史巡按郡縣理刑錄囚,推官常常得以相從,朝夕在傍,于是,得見信重,與論政事。明人對此有明確的認識,所謂“部使者(巡按)巡行州縣,即司理(推官)亦得從之。巡行州縣,故長吏之能否、民間之利病,部使者廉而問之,司理得以告也”[37]。其三,推官與御史存在“行取”上的聯系,是當之無愧的“自己人”。尤其是進士出身的推官,往往有科道之望,好攬權結黨的御史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提攜“后進”的機會。明人管志道就曾指出,御史在外巡按,“自府佐以至州縣正官,一經保薦,則終其身尊之曰老師,而自稱曰門生”[38]。這種老師、門生的關系,也是巡按樂于提攜推官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從“職司理刑”到“亦兼察吏”
明代推官在最初設置時,更多是出于司法方面的考量,而非監察。正如監察御史鄭沂向明太祖說明推官的設置意圖時所言:“各府宜設推官一員,專掌刑名,不預他政,庶責有所歸,而人無冤抑。”[39]一個“專掌”,一個“不預”,便將推官的職能完全固定了下來。弘治以前,推官在理刑之外,雖然多有其他差使,但這些差使多系臨時,推官的主要職能依舊是在理刑折獄方面。
從弘治開始,隨著地方雙重監察體制的敗壞,推官的職能逐漸發生了變化。至嘉靖年間,推官協助御史監察地方已經成為一項慣例,如衛輝推官劉效祖便根據“司理以風聞應直指”的“故事”,“察舉一二豪猾,及事之重且大者鞫報”[40]。明人稱:“嘉隆之際,直指(巡按)行縣以司理隨,無所不寄耳目,于是司理重。”[41]此時的推官已然成為巡按御史在地方上的重要監察耳目。作為巡按耳目,推官最重要的監察職責是協助巡按考察地方官吏,因為這事關朝廷對地方官的考察大計。御史巡按地方本就是明廷“大計群吏”的組成部分,推官則起到了協助御史考課的作用,即《明史·職官志》中所謂的“贊計典”[42]。如:公家臣,字共甫,蒙陰人,隆慶五年進士,遷廣平司理。萬歷十一年大計,“部使上群吏治行,豫以所刺察”,請公家臣“實狀”[43]。馬猶龍,字玄甫,萬歷十一年進士,授廬州推官。“品騭諸郡之吏治,直指使者賴之。”[44]至萬歷十五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詹仰庇在上陳御史“出巡事宜”時,建議“考語宜責司道守巡、府州縣正官開報,不必專任推官”[45]。這里考語開報,指的便是御史巡按期滿,要給司府州縣各官開具官評,呈于吏部,以備考察。詹仰庇的建議從側面反映出,至遲到萬歷年間,巡按考課地方官吏幾乎全賴推官襄助。明人稱:“今夫世之所以嚴重司理者,豈非以司理為直指耳目哉?計典而留,惟直指留,惟司理賜。……計典而去,惟直指去,惟司理去。”[46]一個“賜”字便完全點出了推官在考課官吏中實際所起到重要作用。
(三)推官監察權力的來源
明代推官從職司理刑到亦兼察吏的職能演變,是和明代地方監察制度的演變息息相關的,隨著明廷在地方上設置的雙重監察體制的敗壞,巡按御史監察權力的擴大,推官的監察功能也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推官雖然擁有一定的監察權,并且在協助御史考課地方官吏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它始終不是朝廷法定的監察官員,他們之所以能夠監察地方官吏,主要原因在于巡按御史對監察權力的讓渡。
明人稱:“朝廷設官寄耳目者,內之惟臺諫,外之惟臺察,而臺察之耳目又惟在司理。”[47]明人始終把推官當成巡按的耳目官,而非朝廷監察體制內的監察人員。隆慶年間的內閣首輔高拱上疏稱:“(巡按)托其(推官)查訪,凡二司之賢否,悉出舌吻。”[48]一個“托”字,足以說明即便當時的推官可以考察方岳重臣,但這種考察權力實來自巡按的“托付”。換句話說,其時的推官雖然在地方監察領域有了很大的話語權,但他們始終不是朝廷法定的監察官員,其監察權力并不穩定,權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巡按的信任程度。如汀州府推官程材,為御史胡華所重,“巡郡必挾君以往”,以至于“文事武備,悉以委之”[49];桂州推官李道先,為巡按腹心耳目,“諸凡查官、評讞、獄訟,皆藉手焉”[50]。這些被巡按大加倚重的推官,威權之大,也不過亞于直指而已。當然,這些可稱腹心耳目者,在一省之中,也不過數人而已。明人所謂“今大吏所藉為耳目者,不過郡理官數人”[51],并非虛言。
三、明代推官對地方政治的影響
在明代府級政府中,以品秩而論,推官是府中的“四把手”,較同知、通判亦有不如。但事實上,由于推官掌握著地方司法和監察大權,在地方上的地位和影響絕非一般同知、通判所能比擬。明人稱:“司理而任,即吏與民俱受福焉;不任,即吏與民俱受病焉,其職重最難稱也。”[52]有鑒于此,筆者將從正反兩方面對推官在地方上造成的影響進行探討。
(一)積極影響
首先,明代推官是明代基層司法公正的捍衛者。這一點可以從廣州府推官顏俊彥的案牘集《盟水齋存牘》中略窺明代推官在維護地方司法公正中所做的努力。如在《讞略》一卷中,收錄有“強盜陳拱瓊”一案,其中對案中吳簡可的處置上,兵巡道與府理刑廳意見相左。兵巡道認為,吳簡可作為強盜陳拱瓊、瓦鬼三的同伙,原來擬罪與瓦鬼三皆當“徒”,而現在卻“一辟一脫”,出入甚大,發給刑廳復審。顏俊彥再審依舊堅持原判,認為吳簡可系受牽累,當時并未參與搶劫,兵巡道于是將審理意見轉詳至巡按御史。巡按批復:“吳簡可既系牽累,姑杖釋之”[53],即大體同意顏俊彥的審理意見。再有,如《翻案》一卷中,有“人命梁夢春”一案。死者陳高第與梁夢春乃是密友,梁進祿則是陳高第的家奴,梁進祿因陳高第“束戒嚴緊”,遂起“殺主之謀”。原審審理認定梁夢春與梁進祿為同謀者,當斬。此案發給顏俊彥復審,顏俊彥通過審理認為,梁夢春應為無罪,原因有三:其一,梁進祿想要謀殺主人,卻輕易與主人的密友謀劃,此極不合情理;其二,梁夢春沒有理由舍棄所親厚的貴公子,而與一介逆奴為伍,雖然證詞中有梁進祿的六百金許諾,但這不過是空言而已,梁夢春絕不至于愚蠢到輕信逆奴許諾;其三,證人袁亞福“始報模糊,屢變其說”[54],其證詞顯然是不足為信的。有此三點,顏俊彥認為梁夢春應是無罪,當改釋。上述兩例只不過是《盟水齋存牘》的冰山一角,從《盟水齋存牘》中與上級相左的案例及翻案等大量的案例中,我們既可以看出顏俊彥法律知識的豐富,同時亦能感受到其維護司法公正態度的堅決,對上級的批復不輕易附和,遇有意見相左,往往能夠據法以爭。
其次,明代推官在地方行政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劉世杰在考察雷州推官歐陽保的政績時,亦談到了歐陽保地方行政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如興辦學校、修建文塔、主持纂修《雷州府志》,等[55]。雖然明代推官的職能主要集中在司法和監察方面,但在理刑、察吏之外,推官往往還有眾多的臨時差遣,如賑濟,青州府推官邊憲,“計口給食,處之有法,所全活者甚眾”[56];核算錢糧,荊州府推官陸鰲在“給事中、御史使楚”時,被委以“閱錢谷”之任[57],等。此外,在知府、知縣缺員時,明代推官照例可以暫署府事、縣事,代行地方行政大權,如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二年進士,遷延平府推官,攝郡事,“毀淫祠,創社學”,“盜阻尤溪為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略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余黨百二十人”[58];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江推官,攝府事,時“倭犯境,鄉民攜妻子趨城,時來悉納之。客兵獷悍好剽掠。時來以恩結其長,犯即行法,無嘩者。賊攻城,驟雨,城壞數丈。時來以勁騎扼其沖,急興版筑,三日城復完,賊乃棄去”[59],等。
最后,明代推官是整肅地方吏治的中堅力量。從嘉靖時起,推官逐漸成了巡按在地方上的監察耳目,在協助巡按監察考課官吏的同時,亦為整肅吏治、革除吏弊作出了重要貢獻,如漳州府推官黃直“馭吏嚴急”,以致“寮寀(同僚)祗畏,無敢縱肆”[60];潮州府推官楊載鳴,對“廣中吏故有貼班銀,曰:‘助衙錢’”,進行“罷免”[61],等。明中后期,隨著地方“雙重監察體制”的崩壞,推官借助巡按力量,在地方監察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這一點可以從上下級官吏對推官的態度中,略窺一二。明人稱:“故事,推官為巡按耳目,卑而要,每新到官,奸胥于此覘夷險。即甚簡易,亦先為煩苛,令可畏憚。”[62]可見,每值推官新任,府衙奸吏為了能夠逃避監察,常常用煩苛的政務拖住推官的精力。與府衙奸吏暗中刁難推官不同,布、按二司對推官則是大加拉攏,尤其是科甲出身、深受巡按信任的推官。明人高拱稱:“(二司)遇其(推官)來謁,每留飲幕中,親陪談笑,以結其歡心”[63],推官監察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見。
(二)消極影響
首先,“明代推官在上任之初,并無足夠的法律知識儲備”[2]。故而問刑及文移詳讞常假手于府衙中的胥吏,然而吏多狡獪,往往趁推官上任之初,對刑名事務尚不熟悉之際,對推官進行一定程度的試探。如南康府推官李應升,甫上任,“牘案委積,老吏以公少年,嘗試之”[64];紹興府推官袁祖庚“其始,人猶以少年易之”[65],等。這些被奸吏試探的推官,若表現出“詳慎明決”的一面,那么奸吏自然斂跡,如其不然,便只能“止憑奸吏任情出入”[66]。此外,還有些推官大搞司法腐敗,這在明代的話本小說中多有反映。小說《醉醒石》中的魏推官即是一例。魏推官原是進士出身,登科之后,舉債聽選,選上了江陵府的推官。江陵府中有一大戶名陳箎,“專在大江做私商勾當,并打劫近村人家”,一次劫了官船,黨羽被捕,巡道將案件發刑廳復審,陳箎害怕同伙將其招供出來,于是,便通過府衙小吏向魏推官后宅奉送了六百金,走通了魏推官的門路,最終竟然脫罪。[67]小說雖是虛構,但多是現實生活的反映。
其次,有些推官熱衷攬權,從而導致地方上的權力斗爭更加激烈。如汀州府推官程材善決獄,以致“獄訟不之守而之推”[68],這嚴重侵奪了知府的訟獄之權,因為通常情況下,“一般性的案件有推官審理,而知府則親理比較重要的或認為應由自己審理的案件”[69]。很明顯,“獄訟不之守而之推”,對知府的獄訟之權是一種削弱,所以守才會“以是嗛之”。不僅“嗛之”,而且在巡按御史胡華面前,“守言,每含怒以待”[70]。可見二人的矛盾之深,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不過,值得慶幸的是,二人的權力之爭并未在地方上造成動蕩,影響亦不甚大。相比之下,正德年間邵武府推官高璉與通判馮希哲爭權事件所造成的影響要遠甚于此。正德十四年,福建邵武府軍士動亂,此事起因于“推官高璉欲奪管糧通判馮希哲事任”,爭權未果,高璉于是懷恨在心。后來馮希哲有“別差”,高璉暫管軍糧,適逢軍士支取月糧,高璉故意延緩并謊稱是出自馮希哲的指使。于是,“王福生等遂擁眾三百人入府,欲歐(毆)希哲,不獲。闔城門窮索,希哲為所執,又疑教諭洪鼐,知縣蕭泮等為希哲營救,亦執而歐(毆)之”。此事造成的政治影響極其惡劣,史載:“未幾,建寧、福州悍卒效尤,相繼煽亂。”[71]
最后,明中后期,隨著推官“可專官吏賢否”,在地方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明人稱:“夫其重也,不為守而重于守也。”[72]權位既重,一些推官不免因此驕橫貪暴、一手遮天。永平府推官鄭之范即是一“典型”。萬歷四十七年,后金大軍進攻開原,鄭之范以推官代守開原。但是由于其只知聚斂,而不組織防守,最終導致開原被后金輕易攻陷。事后,遼東經略楊鎬彈劾鄭之范“貪婪異常,致失軍心”。據該城官生軍民告揭,鄭之范聚斂“贓私巨萬”[73]。此外,還有些推官還過分逢迎巡按,以致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嘉靖十三年,直隸廣平府發生兵變。此事起因于巡按李新芳在廣平縣被城門發銃所驚,于是污蔑知縣周謐謀害自己。推官楊經因“新芳怒盛”,誣陷周謐及典史田經“侵分修城緡,坐以監守自盜律”。廣平府知府李鵬霄遂因此事與李新芳起爭執,李新芳隨即遣推官楊經、秦新民捉拿李騰霄。最終“騰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佩,經歷吳高質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死者甚眾”[74]。在此事件中,推官楊經羅織罪名、制造冤獄,推官秦新民怙勢作威,二人為迎合巡按御史李新芳,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與李新芳共同釀成了這場人禍。直隸府尚且如此,其他各府可想而知。
推官始于唐代幕府之屬官[75],宋以后,逐漸轉變為地方官員,至元代,成為專掌刑名的地方司法官員。明代推官最初沿襲元朝舊例,職專平刑,之后,隨著地方雙重監察體制的敗壞,推官漸漸掌握了監察地方官吏的權力,這是明代推官區別于前代推官的歷史特點。清初沿襲明制,推官在理刑之外,仍作為巡按耳目,監察地方,至順治十八年,清廷裁廢巡按御史,以巡按御史為中心的地方監察制度就此崩潰,推官的監察功能也因此幾乎喪失了運轉的動力。[76]至康熙六年,推官全部被裁,它的司法功能被地方上的刑名幕友吸收,推官制度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總之,對于明代推官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將明代地方監察的研究延伸到府級政府。明代推官作為巡按御史的監察耳目,是基層政府最主要的監察人員,對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了解明代府級政府的監察運作,這對整個明代監察體系的研究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補充。另一方面可以深刻地認識明代地方政治格局的演變。嘉靖以前,推官的職能主要集中在地方司法方面。嘉隆之際,推官獲得了司法權之外的監察權,在地方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這對地方行政格局產生了深刻影響。
注釋:
①關于推官入為大理評事,《明史》中僅有一例,即姜志禮,萬歷十七年進士,歷建昌、衢州推官,入為大理評事。不過,在其他資料中,有不少關于推官入為大理評事的記載,如鐘庚陽,隆慶戊辰進士,由太平推官入為大理評事(《經義考》卷十九書,《鐘氏庚陽尚書傳心錄》,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游樸,萬歷甲戌進士,由成都推官入為大理評事(《明詩綜》卷五十七,《游樸(三首)》,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曹征庸,萬歷戊戌進士辛丑殿試,由延安推官入為大理評事(《靜志居詩話》卷十六,《曹征庸》,清嘉慶扶荔山房刻本)等。可見,推官行取為大理評事的制度是存在的。可能是由于大理寺是“專掌詳讞”的慎刑機構,明廷對人選要求較嚴,所以,推官行取為大理評事的人數較六部主事為少。
②如徐問,由廣平推官遷刑部主事,歷兵部,出為登州知府,累遷廣東左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召為南京禮部侍郎(《明史》卷二百一《列傳第八十九》);葛守禮,由彰德推官入為兵部主事,遷河南提學副使,再遷山西按察使,進陜西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入為戶部侍郎(《明史》卷二百十四《列傳第一百二》);王紀,由池州推官入為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擢光祿少卿,自太常少卿升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遷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召拜戶部尚書(《明史》卷二百四十一《列傳第一百二十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