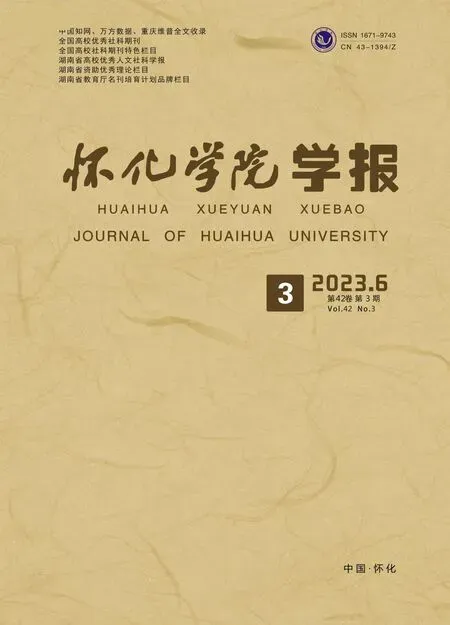湘西的實義與詩義
——1930 年代中期以前的沈從文創作新論
周之涵, 曾 妍
(重慶工商大學,重慶 400067)
不過,這樣一種觀念和實踐,并非源于沈從文突如其來的文學靈感,也不是他崇高的文學理想所致,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文學寫作者在生活、事業上摸爬滾打,歷經甘苦,并在時代的因緣際會中逐漸形成、明晰起來的。考察沈從文1930 年代中期以前的這段文學經歷,對于還原一個真實的沈從文,領會他在生命當中那些隱伏的哀痛,并理解作為個人的沈從文與時代、社會語境之間的關系,或許不無裨益。
一、生計困厄中的湘西選題
1926 年底,文學事業剛起步的沈從文,請遠在湘西的表弟代為收集家鄉鳳凰鎮筸一帶的山歌野曲。收到這些來自湘西的山歌野曲后,沈從文據此整理而成四十余首《筸人謠曲》,發表于《晨報副刊》第1449、1500 號。在《晨報副刊》第1448 號發表的“前文”里,沈從文在對五四新文學一番不以為意的表示后,欣然自得地向讀者推介起他的湘西“土儀”來:
近來生活到了逼到我非寫一點文章不可的境地,做詩是方便極了,但“夜鶯”“玫瑰”這類字眼我運用時常感到萬分的困窘,雖有“悲哀”,卻又與“天鵝絨”異樣,心兒是否當真成了“零零碎碎的片子”也不能知,也從不彈斷過什么“心的琴弦”,做詩大概是與我無緣了。除了做詩是做小說,但仍然是不成。這或者是正因為聽到有那種異樣的呼聲,正在那里大喊其否認舊文學科學,建設新東西,因為想看看別人建設的是些什么東西,所以氣便餒了吧。
我謝小表弟,及其他的副爺們,所寄來的一部分歌謠,卻給了我一個頗感趣味的工作了。雖然所寄來的東西是不多,我卻從這些類乎芹菜蘿卜的不值錢的土儀中,找出了些肥壯一點的大紅薯在未能匯成集子以前揀出來,加以解釋,供大家嘗嘗新。[1]
已有研究指出,沈從文之所以會對湘西民歌發生興趣,源于此時以北京大學為發祥地的中國現代民俗學熱潮的興起。但是,沈從文這時所“發現”的湘西及其民俗,與其說是“標志著作家從自傳式鄉土記憶轉向立足湘西、關切民族的自覺書寫”[2],還不如說是聰敏的沈從文發現湘西原來是一個可以扭轉他寫作困境,從而擺脫此時生活窘境的文學富礦。
眾所周知,1924 年初到北京的沈從文貧病交加,居無定所,事業無成,不得已寫信向郁達夫求救。從郁達夫有感而發所寫的《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一文可知,這時沈從文的生活確實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雖然此后由于得到徐志摩、胡適等文壇前輩的一些幫助,作品逐漸有了發表的地方,但靠賣文為生,艱苦打拼的文學生涯一直持續到20 年代末。巴金也在其回憶性散文《懷念從文》中提及他1932 年與沈從文第一次見面時沈從文急著售稿的情形:“他身邊有一部短篇小說集的手稿,想找個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換點稿費。”[3]大凡讀過沈從文早期作品的讀者,都會對他在一些場合頻頻表示自己堅持寫作,急著賣稿來緩解生活燃眉之急產生深刻的印象。比如現存沈從文書信中最早的一封,于1927 年9 月2 日寫給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說:“我的錢又不即得,她們情形□□□□□□□□,無法辦,只想書鋪開恩早妥貼,則大家均活矣。”[4]她們,指的是沈從文此時從湘西接過來一起在北京生活的母親與九妹沈岳萌二人。人口的增加直接導致經濟壓力加重,這迫使沈從文唯有更加賣力地寫作。但即使夜以繼日,筆耕不息,仍舊杯水車薪,不能維持日常開銷。1928 年底,身陷生計危機的沈從文又寫信向徐志摩托情,希望能由他出面從《新月》雜志為其先行墊付稿費,以應付目前一家人生活上的困難,“最低限度我總得將我家中人在挨餓情形中救濟一下”[5]。直到1929 年,他寫出了《柏子》《阿黑小史》《龍珠》等小說而在文壇小有名氣后,經濟條件仍然沒有太大改善,一家三口竟到了斷炊的地步。他只能四處向朋友籌借,壓力日甚一日,生活難以支撐。10 月下旬,在給胡適的信里抱怨說,本來想搬家到學校來,但“生活青黃不接”,到月底“非有三萬字不能解決”,如果寫不出文章,“不但搬不成家,就是上課也恐怕不到一月連來吳淞的錢也籌不出了”[6]。而在生活如此入不敷出的情況下,自1928 年至1930 年三年間,從北京到上海,他又為其妹聘請外文教師學習英語同法語,“我真愿意她到法國或美國去,學一些讀書以外的技能,學跳舞或別的東西”[7]。這些額外的開支,無疑大大加重了沈從文的經濟負擔。
為了迫不得已的生計,這一時期的沈從文不得不提高自己的作品產量,以市場為導向成為他這一時期最為顯著的文學行為。根據《沈從文著作中文總書目》的統計,自1924 年底始發文章到1934 年印行《從文自傳》之前,近十年間他已經出版了38 個單行本,平均每年4 到5 本,這還不包括篇目相同,曾以不同書名或由不同出版社出版、翻印的作品。[8]文學史上,一般將沈從文的“多產作家”頭銜,指認為是左翼文壇對其文學事業的蔑稱,但從上述資料所統計的情況來看,沈從文的創作量和單行本的數量相比于同時代作家確實要多,所以“多產作家”的名頭對于沈從文來說并不冤枉。即使是與沈從文無立場過節而較為持中的蘇雪林,也在《沈從文論》一文中將沈從文定位為“一個以作品產量豐富迅速而驚人的作家”[9],并順次羅列了他在1934 年前出版的二十多個單行本著作。而根據1982 年沈從文返鄉在吉首大學的一次演講,他也承認這個多產的頭銜,是“要解決生活問題,有時不得已,不是好現象”[10]。
我左沖右突,從密密的樹叢中擠過去摘了兩丫桃花,臉上居然劃了一道血口子,不留神讓一株狗兒刺拉了一下。學著紳士的模樣,我畢恭畢敬地獻給女友,一臉虔誠,“嫁給我吧,親愛的。”
事實上,生計困厄委實給沈從文帶來了很大的煩惱,幾讓他在追求文學的事業上心生退意。對沈從文生平了解的讀者都知道,初到京城的他曾有重操舊業的打算。到1926 年,沈從文又致信曾經在湘西軍隊中共事、此時已在廣州革命政府任職的舊友。由于該信已佚,尚不清楚信中所寫內容,但從對方復信好言相勸,要沈從文放棄他的文學理想面對現實來看,沈從文或確有因諸事不順,有過打退堂鼓的一念之想。而在前文提到的給徐志摩那封托情信里,沈從文又曾相當激動地說道:“實在沒有辦法,在最近,從文只好想方設法改業,文章賭咒不寫了。”[11]這或是一時的負氣之語,但從中也可窺測一個有志青年在經濟壓力面前可能會產生的自暴自棄。
現實中的這種窘迫境況,在其虛構的藝術世界同樣也有所反映。比如,1925 年發表的幾個短篇小說,就是寫他在擔任香山慈幼院圖書管理員時,因生活無著備受歧視的屈辱經歷。如《棉鞋》寫主人公“我”,因為穿了一雙破爛的棉鞋而遭受各類人物憎嫌,頂頭上司更是用他手中的打狗棒直接敲打這雙棉鞋。另一篇《用A 字記錄下來的事》寫一次盛大的壽宴上,其中一個卑微的“他”與周圍人群格格不入的寂寞難堪。兩年之后寫作的《草繩》,則把這種經歷轉移到了遙遠的湘西,故事在隱微曲折中充滿了鄉土異趣,可作詳論。小說講的是沱江邊上一對靠打草鞋度日的叔侄,因為沱江春漲,臆想從河中打撈到好處而改變晚運的故事。但這件事在明眼人看來,其實只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幻想。河水的漲落只由天定,而他所相信的河水上漲卻是因為“年齡與地位的尊貴為資格”的橋頭老兵“夢到是水還要漲”。到了第二天,河水果然在一夜之中消退了,這個老人悵惘若失,作者借此感慨道:
為了老兵的夢,沙灣的窮人全睜眼做了一個歡樂的好夢,但是天知道,這河水在一夜中的消退!老兵為夢所誑——他卻又誑了沙灣許多人。河里的水偏是那么退得快,致使幾多人第二天在原地方扳罾也都辦不到,這真只有天知道!老兵簡直是同沙灣人開了一個大玩笑,得貴為這玩笑幾乎累壞了。
從此那個正派人還是做著保留下來的打草鞋事業,待著另一回晚運來變更他的生活——二力自然沒有去做攔頭工,也不再想做。[12]
如果諳熟沈從文早期在文學事業上的坎坷,并明晰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政治的變動,就能深味作者在小說結尾這段自白里所隱含的苦衷。“老兵的夢”,很顯然是當時由魯迅、胡適、郁達夫等五四新文化、新文學先驅們為新青年營造的一個文學之夢。“河水一夜消退”,其實講的是新文化運動走向尾聲,漸趨沉寂。沈從文在這里所暗諷的是國民大革命后,文學青年們紛紛放棄了文學,投入到與之無關的革命和政治。老人“得貴為這玩笑幾乎累壞了”,可以大致理解為沈從文對于自己追求文學理想而付出的代價和犧牲的自嘲。而最后作者又說這個正派人還是回到“打草鞋”的事業上,無非是在為自己當初的選擇打氣,言下之意是說不管生活、事業遭遇如何,外界的政治局勢、社會時勢如何變化,也不會動搖自己的文學初心。
1980 年,沈從文赴美講學,在《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這篇演講稿中,沈從文曾對其事業起始階段的這段生活經歷有過深情緬懷。他說:“我從事這工作是遠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字還掌握不住,……為了對付生活,方特別在不斷試探中求進展。”[13]如果從沈從文1924 年來到北京算起,那么至少到1929 年,在他為數眾多的小說、散文中出現的湘西,充其量只能算作是為寫作而準備的藝術題材,這并不像1920 年代以魯迅、臺靜農等為代表的鄉土寫實小說那樣,借了故鄉的民俗風物、人倫世情旨在對國民性進行文化批判。而到1929 年,沈從文已經寫出了《柏子》《龍珠》《豹子·媚金·與那羊》《阿黑小史》等引起文壇關注的作品。由此可以推測,至少在1930年以前,湘西并非沈從文用以自覺建構個人身份,傳達某類特定觀念的媒介。或許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還只是“為了對付生活”而在文學創作上“不斷試探中求進展”的一種手段和方法。
二、愛欲苦悶中的湘西浪漫抒情
伴隨在生活、經濟壓力左右的,是青年沈從文愛欲的滋生蔓長及其挫敗后的情感苦悶。若干年后,沈從文在《水云》這篇哲理性散文中對于這一時期被壓抑的愛欲有過自查。他說:“我的過去痛苦的掙扎,受壓抑無可安排的鄉下人對于愛情的憧憬,在這個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完全排泄與彌補。”[14]“不幸故事”,指的是為他帶來巨大聲譽的代表作《邊城》,但事實是沈從文個人情愛上的“不幸故事”由來已久。1924 年9月,沈從文從遙遠的湘西邊地來到新文化運動的漩渦中心北京,渴望在那里學習新知,進而尋求不同于湘西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話說,正是“因一個五四運動的余波,把本人拋到北京城”[15]。沈從文因在湘西地方軍隊中擔任文職而接觸到新文化、新文學,并對此有了向往之情,產生新的人生憧憬。在這番表面的自陳之外,恐怕也與他第一次戀愛無疾而終不無關系。1932年,沈從文在《從文自傳》中用了一個十分藝術化的標題《女難》來追憶、撫平這段難言之隱。對于沈從文來說,這次“女難”,不僅因被“一個臉兒白白的身材高的”女孩騙取了變賣祖產所得資費而讓他愧對自己的母親,也使其深感青年人生的苦悶與寂寞,因為在家鄉沒人聽他“陳述一分醞釀在心中十分混亂的感情”,并給予他“啟發與疏解”。[16]年輕的沈從文正是帶著這樣的情感苦悶離開湘西而遠走北京的。
不過,北京并非一個可以化解沈從文情欲之苦的清凈之地,相反,此時新文化運動余波蕩漾的這個中心之城根本就是一個情愛的是非之所。在思想啟蒙、個性解放、男女平等、戀愛自由等五四新文化的洗禮下,沖決網羅后的新青年們至少在思想上欲離傳統儒家的男女大妨觀念而去之,普遍經歷了情愛意識的覺醒。“沒有花,沒有愛”成為那時在青年文化間十分流行的一句寂寞口號。1924 年,魯迅曾作“擬古的新打油詩”《我的失戀》,揶揄當時新青年泛濫的情愛游戲。作者在談到寫作該詩的初衷時說:“……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17]這雖是魯迅的“開開玩笑”,但也從消極一面證明了戀愛自由已成為當時頗為時尚的社會風氣。可以略作推想,20年代郁達夫、徐志摩等文人那些大膽、熱烈的情愛故事及其文風,很可能影響到了想在文學上有一番作為而又正值青春期的沈從文。如果注意到沈從文貧困交加之際為什么只向郁達夫求救,并在《晨報副刊》投稿成功后與徐志摩相識,而且過從甚密,大概就不能否認其間所存在的一些聯系。
然而,雖然說是戀愛自由了,但男女青年在情愛場上的戀愛機會及戀愛成功的幾率其實也因人而異。一般來說,那些能夠進入高等學校,家庭優渥,身份平等,性格開朗的新青年,自然可以獲得較多且成功率較大的戀愛機會。比如說與沈從文一起創辦《紅黑》雜志,被他稱為“海軍學校學生”、出生于戲劇世家的胡也頻1925 年就向丁玲求愛成功,并結成連理。而對于初來乍到,生活貧苦,言訥口拙,學歷自卑,且又毫無身份地位可言的“鄉下人”沈從文來說,其在戀愛上的經歷就沒有那么幸運了。甚至這時的他連戀愛對象也沒有,無人可愛。1926 年9 月,與沈從文同病相憐的文學青年劉夢葦貧病交加,病逝于北京,得知噩耗的沈從文感慨萬千,特意寫了《讀夢葦的詩想起那個“愛”字》一詩。而據他們志同道合的好友于賡虞追憶,劉夢葦之死“卻另有著可痛的原因”[18]。“可痛的原因”是什么?詩人朱湘曾說其實是他追求此時正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上學的女友龔業雅不得“失戀”所致。[19]可見,沈從文所寫的這首詩顯然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之作。除了痛惜友人,劉夢葦的死還觸及到了沈從文被壓抑的愛欲,即對此時自己事業無成、愛情無著的悲嘆與無奈。所以沈從文才會在該詩開頭就說:“我雖是那么殷殷勤勤的來獻,你原來可以隨隨便便的去看。”[20]表面上是為好友鳴不平,但又何嘗不是說的自己?此時沈從文的獨身境況,正如1927 年發表在《晨報副刊》上的小說《怯漢》所描繪的那樣,在陌生的北京城里,一個無所事事,孤獨徘徊于街頭,“看那些打扮得好看的年青女人買東西。……我又隨到這些本來有著男子陪到走的年青女人后邊聽他們談話”,幻想著“這些高的矮的難道不是拿來陪到男人晚上睡覺盡人愛的么”[21],卻又自憐無份于女人與愛情的多余人形象“我”,便是這一時期沈從文最為典型的自畫像。
這種被壓抑了的愛欲,在沈從文這一時期的小說、散文、戲劇中可謂比比皆是。僅以涉及湘西題材的愛欲故事來說,早在1925 年發表的獨幕劇《野店》,其實就是力比多欲望的露骨宣泄。該劇寫湘西荒郊野外一個簡陋的旅店里,一位夜宿的“客人”意圖不軌,趁黑摸到店主“苗婦”房內與之調情風流的故事。又如1927年的短篇小說《連長》,講述的是湘西軍中一位連長與駐地一位寡婦情愛糾纏,欲罷不能的浪漫傳奇。到1929年創作的短篇小說《旅店》,又虛構了苗區一個名為“黑貓”的寡居婦人,因愛欲重燃而與商旅男客私會偶合的故事。甚至有研究者將這種愛欲書寫向下推至1934 年的《邊城》,認為這篇小說暗寓沈從文個人的愛欲隱衷。如劉洪濤就指出,“《邊城》是他在現實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誘而又逃避的結果”[22],并考證其中的女子原型為某某某。這種說法是否準確,或許見仁見智,但其意在于彰明沈從文文學創作中的愛欲主題,卻并非沒有一些道理。
如果從1930 年代當時文壇對于沈從文這一類型小說因為暴露欲望,缺乏節制而招致不少左翼人士的批評和指責來看,這也可從反面佐證這一時期沈從文確實在借用文學這個白日夢來宣泄淤積心中的愛欲之苦。如1931 年3 月1 日的《文學生活》雜志第1 卷第1 期,左聯成員韓侍桁就曾刊文,毫不避諱地指出在形式上沈從文的創作選用的是“一種最易于模仿而是輕飄的文體”,其作品取材范圍狹小。他總結為四點,其中有兩點直指作品中類型化的愛欲主題:“一、描寫城市青年男女的性的誘惑與戀愛的關系;二、描寫鄉村沒有教育的男女的本能的性的沖動。……他就在描寫一幅田園風景里,他都要加以‘性’的點綴。”[23]韓侍桁的批評,若拋開當時國內急遽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偏見不說,其實也并不完全是誣指。沈從文自己就曾在1930 年《新月》第3 卷第1 期發表的評論《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一文中,對于郁達夫及其代表作《沉淪》贊賞有加,認為“郁達夫那自白的坦白,仿佛給一切年青人一個好機會,這機會是用自己的文章,訴于讀者,使讀者有‘同志’那樣感覺。這感覺是親切的。”[24]而在此之前的1926 年,沈從文在一篇自白文章《此后的我》當中,就坦承自己有過“郁達夫式悲哀”。文章開頭便說:“近來人是因了郁達夫式悲哀擴張的結果,差不多竟是每一個夜里都得賴自己摧殘才換得短短睡眠,人是那么日益不成樣子的消瘦下去,想起自己來便覺得心酸。”[25]這“郁達夫式悲哀”,很顯然是作者此時愛欲壓抑,不得合理伸張的自憐自艾。
與這一問題相關的是沈從文與魯迅的關系,在此值得一說。文學史上一般將沈從文與魯迅之間有過的芥蒂視為一場誤會。然而,就丁玲之弟去函魯迅而導致后者誤以為是沈從文隱隱曲曲的求情一事,后來雖得以澄清[26],但二人在文學觀念和道路上的殊異恐怕是這場誤會更為深層的原因。因為我們知道,新文學運動伊始,魯迅曾對鴛鴦蝴蝶派小說沉滯猥褻的格調流弊有過激烈的批評,指斥它是“清末小說的末流”,“并沒有什么好成績,學到的大抵是糟粕”[27]。又在1930年的《萌芽月刊》上撰文批評張資平為“三角戀愛小說作家”[28],而予以否定。由此可以推測,沈從文這一時期這些愛欲主題的小說,很可能得不到魯迅的肯定。而據學者任葆華的研究,其實1930 年4 月間,沈從文與魯迅在一次朋友的婚禮場合有過同處機會,但彼此“并無近距離的接觸和交談”。[29]
總結前文一、二節所述可知,生活、事業上立足未穩,加之青年人心靈、情感上的苦悶,左右了沈從文這一時期的文學行為。有論者指出,沈從文早期的文學創作表現了一個文學青年在文學學步階段所感受到的“生的苦悶”與“性的苦悶”,尤其是后者。[30]這種說法難免會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但卻為我們比較切實地再現了作為一個青年的沈從文在生活與情感上摸爬滾打的心路歷程。
三、湘西與沈從文的身份建構
1930 年,國立青島大學在時已停辦的原省立山東大學和原私立的青島大學基礎上籌備成立。這所在蔡元培關照、楊振聲主持下,循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辦學方針,網羅了聞一多、梁實秋、陳夢家、趙太侔、方令孺等一批新文化運動后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大學,對于此時身在武漢且早已厭倦了“這里每天殺年青人”[31]的沈從文來說,無論是與上述新月同人的私交,還是遠離南方政治漩渦,青島顯然更能引起沈從文的興趣。1931 年,經好友徐志摩推薦,沈從文辭去此前短暫任教武漢大學的教職,于8 月間前往青島大學執教。就在生活稍顯從容的同時,沈從文自1930年起與張兆和之間的戀愛關系,也隨著1933 年兩人在上海訂婚后塵埃落定。一份有固定收入來源的職業,一個新組建的家庭,一個有著較為一致審美趣味的社交圈,加上青島海天水云的宜人風景,理論上說應為沈從文創造了一個較為寬松的文學外部環境。
這時他筆下的那些湘西浪漫傳奇,已較為明顯地弱化了為引起讀者感官興味而有的獵奇色彩和愛欲抒情,升級換代為一種建構個人身份的鄉土體認。可以作為例證的是他1932 年利用暑假時間寫完的《從文自傳》。文學史家一般把這部作品看作是沈從文前半生的傳記材料,學術界到目前為止的沈從文傳記著述,大多以此為藍本加以援引。然而,正如法國思想家菲力浦·勒熱訥((Philippe Lejeune)在《自傳契約》中所說的那樣:“(自傳)寫自己的歷史,就是試圖塑造自己,這一意義要遠遠超過認識自己。”[32]因此,真正的自傳寫作,不是要揭示歷史的真實,而是展示寫作者自己內心的真實。它所追求的不是資料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而是完成自我存在的意義和統一。另外,從常識上說,一個年齡剛邁過三十的年輕人,要為自己立傳恐怕還為時尚早。事實上,沈從文寫這部傳記的本意也非如此,據學者張新穎研究,“寫自傳的直接原因,是上海的邵洵美打算新開一個出版社,預先策劃了一套自傳叢書”[33]。沈從文自己也在1980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從文自傳》附記中說道:“后一部分……,個人還是不免受到些有形無形限制束縛,不能毫無顧忌的暢所欲言。”[34]因此,這部自傳嚴格意義上來說大概只能算作是一部以個人為背景的類自傳性作品。在這部作品中,沈從文雖然對他遠走他鄉追求文學理想前的湘西家世背景、童年往事和浪跡沅水流域的行伍生涯有過詳細交代,但其通過對個人生命發展歷程中這段湘西經驗的鉤沉,在自覺、不自覺中確認新的文化身份,可能是更為重要的深意。如果我們將《從文自傳》中的《懷化鎮》與1926 年創作的《槐化鎮》加以比較,或許就能大致明了其中一二。
“懷”與“槐”互通,“懷化”即“槐化”,這是當時湘西沅水流域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就題材而言,這兩篇文章前者其實只是后者的重寫擴充,都是講沈從文當年擔任湘西地方軍隊文職時在這個小鎮的見聞。然而,就內涵而言,它們之間又不完全是重寫擴充的關系。《槐化鎮》中,沈從文為讀者勾勒出一個浪漫異趣的湘西小鎮。這個小鎮上,有神奇迷幻的風洞,有柴米油鹽的鄉土日常,有靡靡詩情的落雨,甚至連小鎮上喘氣冒煙的镕鐵工廠在作者筆下也滿是濃濃人情。如果從作者在文中自道“那地方給我的印象,有頂好的也有頂壞的,……我是但愿能記得到那一部分好點的”[35]來看,這篇小說無疑只是一個身在異鄉的“北漂”青年單純的思鄉情緒寫照,并無特別旨意。但是,六年之后重寫的《懷化鎮》雖然也有對地方鄉土人情、民俗風物的傾心描寫,但文中的鄉土記憶明顯摻揉了他的都市體驗,其著意點是城鄉之間的鮮明對比。沈從文如此說道:
我在那地方約一年零四個月,大致眼看殺過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狀態下被把頭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許多所謂人類做出的蠢事,簡直無從說起。這一分經驗在我心上有了一個分量,使我活下來永遠不能同城市中人愛憎感覺一致了。從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過的蠢事,聽了些平常人不聽過的喊聲,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過的氣味;使我對于城市中人在狹窄庸懦的生活里產生的作人善惡觀念,不能引起多少興味,一到城市中來生活,弄得憂郁強悍不像一個“人”的感情了。[36]
在這里,浪漫化了的鄉土記憶不是作者情緒的重點,而只是借此貶抑病態都市而建構其“鄉下人”身份的一種手段。它的確關涉沈從文個人的鄉土經驗,但這種經驗是沈從文通過對比北京、上海、武漢、青島等現代商業化都市和政治化都市而凸顯出來的。巧合的是,沈從文批判現代都市道德墮落,知識人“閹寺性”性格的那些作品,如1931 年的《紳士的太太》,1932年的《都市一婦人》,1935 年的《八駿圖》,大都寫于此時及其后,這恰恰說明了新身份的確立在其文學思路上所產生的指導性影響。
但是,城鄉對比視野下的浪漫化湘西并非沈從文身份建構的唯一途徑,另一個或許更為重要的途徑是對湘西地方政治混亂無序的觀察和批判。在這種觀察和批判中,一個反對暴力政治,堅持人性啟蒙,主張藝術自律的新文化知識分子形象躍然紙上,成為他的另一重身份。人所共知,這本自傳涉及暴力殺戮的文字不僅眾多而且顯目,如上述《懷化鎮》中的引文寫湘西軍閥濫殺無辜,草芥人命,這在《清鄉所見》其實還有更為細致的展開和形象化描述。而像《辛亥革命的一課》所描述鳳凰城內那些翻來覆去的暴力,打打殺殺的流血,在批判暴力這一文化主題上,又何嘗不是《一個大王》中下級兵士為上級長官所殺,而上級長官又為另一更大勢力所滅的復寫?但沈從文對于這些暴力殺戮的描寫、感受以及批判,并不是要揭示歷史的真實,事實上它早已脫離了原初的歷史,而與1920 年代末以來五四新文化知識分子日趨政黨化、政治化的時代語境緊密相關。有研究者甚至指出:“《從文自傳》中家庭和生平的許多情況都語焉不詳,尤其是其中寫殺人處,有夸大之嫌等情況。”[37]夸不夸大暫且不論,自傳中那些暴力殺戮描寫背后所隱含沈從文的去政治化傾向卻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的。因為在1930 年代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里,暴力其實只是政治的孿生物。通過揭露湘西地方軍閥的無知濫殺,鞭撻暴力,保持與政治的距離,從而建構一個自由主義人性論的新文化知識分子形象,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這本自傳寫暴力殺戮的思想背景。凌宇指出,隱伏于《從文自傳》當中的敘述脈絡如果“從作者對自我生存處境的反應方式看,則是從對社會的現存秩序與觀念的被動接受、承認,走向懷疑與不信任”[38]。所謂“走向懷疑與不信任”的歷史內容,即沈從文自覺區別于1930 年代革命氛圍下青年的政黨化、政治化身份。其實,這種身份自覺在寫作《從文自傳》的前一年,即1931 年就有很明顯的表露。是年8 月間,沈從文寫完《記胡也頻》,追憶半年前這位因思想“左傾”而被國民黨秘密殺害的昔日友人。在沈從文看來,胡也頻之死雖然與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政治有關,但問題的關鍵恐怕還是出在胡也頻自己身上,即文中沈從文曲折表達的“這個海軍學生近來特別強悍了一點”[39]。近來特別強悍了一點,指胡也頻加入左聯后思想的日趨激進化,這是沈從文對于友人背離文學初衷,與政治越走越近,并最終罹難的不滿和微詞。
可以說,將湘西地方軍政的暴力所暴露出的人性貧困簡陋與傳奇的家世背景、浪漫的鄉土記憶加以對比,揄揚后者而貶斥前者,這幾乎是這本自傳最為顯著的情緒基調。表面上看它們彼此對立,但其實這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二者都統一于沈從文希望借由重新觀照人生前三十年的經歷,來妥帖安置自身這一自我身份確認的目的之下,是二而一的關系。因此,正是通過這本自傳,沈從文從過去的經驗中重新“發現”了自我區別于當時新文化知識分子日趨政黨化、政治化的質素。在這一重新“發現”的過程中,過去被“照亮”,人生青年階段的湘西經驗不再混沌一片。重新組織和敘述后的湘西,成為了沈從文自我確認和身份建構的關鍵媒介。由此,沈從文打開了一個新的意義空間。
四、倫理化的湘西及其現代文學史意義
在個人生存困境得以緩解,并獲得一個新的身份以后,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便不再以市場為導向而成為個人生活資費的經濟來源,或以宣泄力比多愛欲而成為浪漫抒情的抽象符號,而具有了更多的倫理承擔。至1934 年代表作《邊城》問世,湘西所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0],成為反思現代都市文明道德頹下,生命畸形的自我救贖,成為超越黨派政治,守護人性自由的生命實踐。這反映出一個文學寫作者,有了生活上的余裕,并形成明確的自我認知以后,而與集體、社會和時代大潮匯流。廣義上來說,這是人的社會化過程。具體來看,這也是中國近代以來啟蒙與救亡主題下知識分子的必然歸宿。沈從文如是,與沈從文在生命長河里有過直接或間接交集的郭沫若、丁玲等左翼文人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們殊途同歸!沈從文特殊的地方只是在于,在一個遠離鄉土的現代化都市構造中,他以偏遠僻靜的湘西立言,自覺背負起挖掘湘西在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過程中,所應也所能發揮的文化功能這一歷史使命。這與1930 年代左翼文壇一道,一從地域的、人性的文化態度,一從國族的、集體的文化立場,既延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范圍疆界,也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