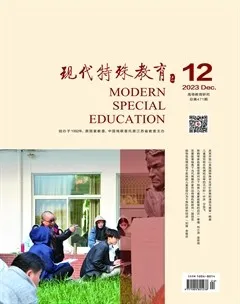指導性反饋應用于孤獨癥兒童言語行為干預的研究綜述
劉茜 余菊芬



劉茜,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特殊教育學前融合教育。E-mail:18101246360@163.com。
通訊作者:余菊芬,碩士,教授;研究方向:特殊教育師資培養、特殊兒童康復與護理。E-mail:932081583@qq.com。
[摘? 要]? 為探究指導性反饋應用于孤獨癥兒童言語行為干預的研究現狀與進展,對14篇國外相關實證研究的文獻進行系統梳理和分析,歸納其在干預對象、干預情境、使用材料、評估工具、實驗設計、干預目標和干預效果等方面的現狀和特征。據此,提出應進一步重視指導性反饋實證研究的開展、注重指導性反饋干預的效果追蹤、優化指導性反饋干預的實施方案,開展指導性反饋結合其他干預方法的綜合研究等建議。
[關鍵詞]? 指導性反饋;孤獨癥譜系障礙;兒童;言語行為
[中圖分類號]? G760
一、引言
孤獨癥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以下簡稱ASD)是一種廣泛性發育障礙[1],其核心癥狀表現為言語溝通社交障礙、興趣狹隘和重復刻板的行為方式[2]。雖然隨著《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診斷標準的變化,語言行為發育障礙不再作為ASD的核心障礙[3],但無論是在臨床醫學還是有關ASD的研究,都發現ASD兒童語言行為障礙仍十分明顯。有研究指出,ASD者大多伴隨語言發展遲緩[4],在語言學習中缺少靈活性[5],較難形成言語學習的生成性技能[6],大約26%—29%的ASD者無法獲得功能性語音語言[7]。
語言障礙可能會廣泛地影響ASD者認知、社交和學術成就等功能領域的發展[8]。斯金納基于行為主義理論提出了言語行為理論,他將言語定義為一種可以習得的行為,強調可以通過控制動機、強化、前提刺激等環境變量對言語行為的習得進行控制[9]。斯金納將言語行為的范疇擴展至語音、書寫、肢體動作、說者行為、聽者行為等內容[10-11]。金寧等人基于言語行為理論將兒童言語行為的發展分為初級言語行為階段、中級言語行為階段和高級言語行為階段,并指出ASD兒童初級言語行為主要有聽者行為(Listener Behavior)、提要求(Mand)、仿說(Echioc)、命名(Tact)和對話(Intraverbal);中級言語行為包括知名(Naming)和自動附加(Autoclitic);高級言語行為包括閱讀和寫作[12]。言語行為理論也成為近年來ASD者溝通領域干預的重要理論基礎,語言行為作為直接影響ASD兒童日常生活和社會參與的重要因素,一直都是國內外研究者關注的重點。
指導性反饋(Instructive Feedback,以下簡稱IF)是一種教育策略,是基于ABA原理在言語行為教學過程中一種可靠、有效的方法[13]。Werts等人將IF定義為在隨后的教學試驗事件中向學生呈現額外的、非目標的刺激[14]。已有研究表明,向學齡前到成年的普通和特殊學習者提供IF刺激,可以在沒有額外指導的情況下獲得更多的額外目標,能夠有效提升學習者未來學習的效率,有助于其有效獲取未來行為[15-16]。現有研究表明,IF在不妨礙教育主要目標技能獲得的同時,還能夠有效促進ASD兒童包括命名、交互式對話、反向對話等多種言語行為的發生[17]。因此,本研究將對IF應用于孤獨癥兒童言語行為干預相關的實證研究進行系統綜述,以期為孤獨癥兒童言語干預實踐和研究提供一點啟發。
二、研究方法
①
注:VB-MAPP(Verbal Behavior Milestones Assessment and Placement Program),言語行為里程碑評估及安置程序;
②? DAYC(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of Young Children),幼兒發展評估;
③? VABS(Vineland Adaptive Behavior Scales),文蘭適應行為量表;
④? PPT(Progressive Prompt Delay),漸進式提示延遲;
⑤? Stanford-Binet(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s,Fifth Edition),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第五版);
⑥? PPVT-IV(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Fourth Edition),皮博迪圖片詞匯測試(第四版);
⑦? EVT-II(Expressive Vocabulary Test,Second Edition),表達性詞匯測試(第二版)。
首先,以“autism”“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與“instructive feedback”“IF”和“language”“verbal responses”為關鍵詞,在Web of Science、ProQuest、 SpringerLink、 Google Scholar以及ERIC等外文數據庫進行檢索,將時間限定為2010—2022年。對檢索到的文獻進行篩選,篩選標準為:(1)研究類型為實證研究,進行了干預實驗;(2)被試為ASD兒童;(3)干預方法至少包括(IF;4)研究目的是探究IF對ASD兒童言語行為干預的效果。刪除無關和重復文獻,共獲得14篇運用IF對ASD兒童言語行為進行干預的實證研究文獻。
三、研究結果
對收集到的14篇文獻進行系統的整理和分析,分別從干預對象、干預情境、使用材料、評估工具、實驗設計、干預目標和干預結果等方面進行歸納,文獻內容分析結果詳見表1。
(一)干預對象
所選取的14項實證研究均以ASD兒童為干預對象,且都有一定的語言學習需求,部分被試同時伴有智力障礙、學習障礙、語言發育遲緩和唐氏綜合征等。現有研究共涉及42名ASD兒童,其中男性31名,女性11名。從性別占比的情況上來看,男性干預對象占比高達73%,性別數量差異較大。在干預對象年齡方面,年齡最小為3歲,最大為13歲,年齡跨度較小,且主要集中在學齡前階段。與此同時,在研究的被試數量方面,研究被試數量大多集中在2—4名,最多為9名。
(二)干預情境
納入分析的14項實證研究涉及的干預情境主要包括治療室、教室和家庭等。干預情境可以根據干預目的的不同,具體分為控制環境和自然環境兩大類型。目前,大部分IF實證研究主要是在控制環境下進行的,研究大多在特定的實驗室、治療室和“一對一”教室開展干預,研究人員會對環境進行嚴格的處理和安排,盡可能地控制可能影響干預效果的因素,保證實證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如Sarah等人聚焦于行為干預診所的環境下使用IF干預ASD兒童的聽者反應和交互式對話水平的研究[32]。近些年的IF實證研究越來越重視IF在較為自然情境中的運用效果,開始關注環境控制對IF干預效果泛化的影響,逐漸開始注重探尋IF在自然情景中的適用情況。如Casey等人將干預放在兒童家庭中,通過實證研究觀察IF對ASD兒童言語內反應的影響情況[33]。Guangyi Lin聚焦于運用IF提升ASD兒童在家庭環境中語言詞匯的獲得和使用情況[34]。
(三)使用材料
所有研究都對其使用的材料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說明,大多研究都有圖片、強化物、攝像機、數據表和計時器等材料。在圖片的選擇和制作上,部分研究根據干預對象和研究設計的具體情況,將圖片的顏色、形狀和尺寸大小進行了詳細的說明,如有的研究圖片材料是14.6cm×11.4cm的尺寸,有的是7.62cm×7.62cm的尺寸。與此同時,近些年的研究也注重將電腦、iPad等電子設備納入實證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內容中,通過電子信息技術的支持,有效地提升了干預研究數據收集和處理的效率。
(四)評估工具
研究都運用了專業評估工具評估了被試的先備技能并進行了詳細報告。VB-MAPP是納入的所有研究中使用最為廣泛的,在7項研究中都有使用。VB-MAPP是桑德伯格基于言語行為理論開發的語言和社會能力評估訓練系統,在ASD康復領域被廣泛應用[35]。PPVT-IV和EVT-II使用也相對較多。
(五)實驗設計
通過對已有研究的實驗設計方式進行分析和梳理,發現14項研究均是采用單一被試實驗設計,其中包括8項多基線實驗設計、5項交替實驗設計、1項多基線和交替組合的實驗設計。在8項多基線實驗設計中又包括跨行為與跨情境的多基線實驗設計,如Christopher等人將3名ASD兒童的較長語言反應作為IF目標進行干預,并在研究中探究了目標的維持效果[36];Casey等人使用交替實驗設計,探究IF目標在連續陳述和間歇性陳述中獲得的有效性和效率,研究結果顯示,間歇性陳述中次要目標的呈現比連續陳述中次要目標的呈現更有效[37]。
(六)干預目標
干預目標是指在針對某一主要目標行為進行干預教學和反饋的過程中使用IF這一方法來呈現的次要目標。IF目標區別于主要目標,是指被試在對主要目標(如被試在三類水果的圖片中正確選擇出蘋果的圖片)作出正確反應后,使用IF的干預方法對主要目標進行內容補充或完成延伸后的次要目標(如被試成功選擇蘋果的圖片后,研究者使用IF說明蘋果是水果,即IF目標為被試者掌握蘋果的類別這一目標)。不同研究因其干預情景等條件的差異對其干預目標的定義也各不相同。如Valeria等人在其研究中將配對、重復、名稱命名、名稱指認、特征指認、特征命名、交互式對話中的填空式、Wh式問題和反向對話等言語操作進行了詳細的操作性定義[38]。所納入的14項研究中,有2項研究的干預目標為命名,有2項研究的干預目標為聽者反應,有4項研究的干預目標為交互式對話,有4項研究的干預目標為語言詞匯的掌握,有5項研究的干預目標為ASD兒童的言語內反應。已有研究大多將命名、交互式對話、聽者反應等目標綜合納入干預中,探尋IF對ASD兒童多種類型言語行為發展目標的影響。
(七)干預流程
1.前期評估
現有研究都會在正式實施IF干預之前進行偏好物和先備技能的評估。如Sarah等人采用無放回偏好物評估來確定ASD兒童喜歡的物品作為其完成任務之后的強化物[39]。在先備技能評估階段,首先,研究者會綜合使用多種專業評估工具來了解ASD兒童的語言發展現狀;其次,會對ASD兒童的配對、名稱命名和名稱指認等與IF目標相關的言語行為進行評估,每個階段都包括了三個目標行為回合,當1—2個預熱回合和3個干擾回合的正確率都達到89%時,研究者將正式進入干預階段[40]。
2.預熱
正式進入IF干預之前,干預者大多會對參與的ASD兒童進行預熱,通過1—2個回合的動作模仿、仿說等內容幫助ASD兒童熱身,干預者對兒童的正確反應進行表揚等積極反饋,對錯誤的反應進行矯正。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預熱環節的目的只是幫助兒童熱身并簡單熟悉流程,所以無論被試的反應是否正確,都不會影響干預進入目標任務流程。
3.正式干預
研究中關注IF干預的操作流程,重視區分整個干預過程中的主要目標和使用IF干預所呈現出的次要目標。如針對特征指認這一言語操作,干預者會同時呈現正確的樣本卡片和兩張干擾卡片,告訴被試:“指一指××。”當兒童在三張卡片中選出對應的正確卡片時,干預者對兒童進行表揚和強化,同時向兒童展示卡片,并增加IF陳述,內容可以是該目標的特征。如以“醫生”為選擇目標,那么IF陳述可以是“他在醫院工作”。IF陳述結束后,干預流程即結束,此刻便不需要對被試對IF陳述做出的任何行為給予強化或糾正。若被試在第一步指認目標時已經出現錯誤反應或無反應,那么干預者可以進行反復操作,直到兒童反應正確。
(八)干預效果
干預效果將從即時效果和維持效果兩個方面進行討論。在即時效果方面,大部分研究均產生了良好的即時效果,但也有部分研究未發現IF干預的效果。如lara等人對4名孤獨癥兒童進行干預的研究結果發現,僅有1名兒童獲得了良好的IF干預效果,另外3名并沒有明顯的效果。研究者也指出,使用的IF類型、IF呈現的形式、IF的目標與兒童興趣匹配程度和兒童自身的興趣動機等其他變量都有可能導致效果的差異[41]。在維持效果方面,5項研究明確報告了干預研究取得的維持效果,但整體觀測的維持時間都相對較短。
四、討論
(一)研究的總體情況
1.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以3—6歲的男性ASD兒童為主,14項研究的被試均為ASD兒童,且大多伴有智力落后、癲癇等問題。研究被試的年齡跨度較小,主要集中在學齡前階段(3—6歲)的ASD兒童,對學齡期、青春期和成年期ASD者的關注相對不足。這可能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ASD者的言語水平會有所提升;或者是由于對成年ASD者的言語水平進行IF干預的難度較大,程序也較為復雜。在干預對象的性別方面,現有研究中干預對象大多為男性,性別數量存在較大差異,這一點與ASD患病率的性別差異有著直接的關系[42],現有研究也未就性別對IF干預效果的影響進行報告。因此,未來有關IF的實證研究還需要更多關注ASD者所伴隨的不同類型的障礙以及不同年齡階段ASD者在IF干預中的效果差異和實施注意事項,進一步關注ASD者的類型、年齡等因素的影響,從而更全面細致地探尋IF對ASD者言語發展的干預效果。
2.研究場景
研究大多集中于較強控制的環境。早期的IF干預場景大多集中在單獨的房間,如治療室、干預室和教室等,研究者會對干預的環境進行控制,盡可能地排除環境中的干擾因素,從而有效提升干預的效率。目前的研究則主要集中于具有較強控制的環境、“一對一”教學安排、被試數量較少等條件,對IF在自然環境下、小組教學中和ASD兒童日常生活中泛化效果的探索研究相對較少,對IF在集中教學環境下的使用效果還不太清晰,對控制情境和自然情境IF使用效果的比較研究暫未見到。因此,未來運用IF干預ASD兒童言語發展的實證研究可以更多聚焦于不同控制情境、不同的自然情境以及兩種情境的結合等干預場景,還可以進一步關注IF干預由較強控制的環境轉換、泛化到自然環境的路徑、作用及其注意事項。
3.使用材料
研究使用的材料大多相似,部分內容會根據干預目標進行靈活選擇和調整。現有IF干預ASD兒童言語行為的實證研究使用材料大多為擋板、書寫用具、圖片、卡片、計時器、數據表、攝影機和兒童偏好物等。不同干預使用的材料也各不相同,研究者會在實際工作中根據ASD兒童的具體情況和教學干預的項目靈活地進行調整和運用。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聚焦于不同材料以及不同材料組合對IF干預ASD兒童言語行為的影響,從而嘗試開發IF的不同主題的材料包,有助于IF在教育干預實踐過程中被廣泛運用。
4.研究設計
研究主要以單一被試實驗設計為主。單一被試實驗可以針對個體行為做出全面、深入且細致的分析,追蹤個體行為變化的內容和原因,從而有效判斷干預方法對個體行為的影響情況[43]。目前,現有研究設計主要還是較為單一的多成分設計和多基線設計等單一被試實驗設計,雖然也有將多成分設計與多基線設計相結合的實驗設計,但相較而言,現有關于IF的實證研究在實驗設計上還需要進一步探尋和更新。隨著對IF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入,對使用IF干預具體問題的討論更加深刻,未來的研究也應該考慮運用更具多樣性和綜合性的實驗設計類型來探尋IF的干預效果。
5.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均證實IF對ASD兒童言語行為的干預有著積極效果。在干預目標的獲得程度方面,所有研究都在獲得主要目標的基礎上,通過IF干預有效獲得了IF目標,在更短的干預時間內學習到更多,有效提升了教學效率。在目標的泛化程度方面,IF干預有助于ASD兒童進一步泛化學習概念,獲得更多言語行為技能。在目標的維持效果方面,Christoph等人和Sarah等人都在研究中報告了IF干預有著較好的維持效果[44-45]。
(二)IF的優勢與局限性
IF能夠有效提升ASD兒童言語教學的效率。IF干預使兒童在掌握主要目標的同時,也獲得了IF語句呈現的次要目標,明顯提高了教學的效率。以Casey等人的研究為例,在其研究中,兩名ASD兒童都在掌握主要目標的同時掌握了部分次要目標,教學效率得到有效提升[46]。
但目前,IF在自然情境泛化的效果存在爭議,IF的干預目標在ASD兒童日常生活中的泛化效果也存在差異。與此同時,IF干預ASD兒童言語行為的效果受不同IF類型影響較大,如平行IF(目標刺激相同的反應)、擴展IF(對所教授的概念進行拓展)和無關IF(概念上與目標行為無關)的影響效果并不同[47-49]。Delmolino等人在研究中明確指出,不同類型的IF對ASD兒童教學效果影響也存在一定差異[50]。
五、建議
(一)重視實證研究
通過不斷的循證實踐,IF逐漸成為公認的能夠有效干ASD兒童言語行為的方法之一,在這個過程中,IF的操作和研究也越來越規范化和科學化。近年來,國內研究者高度重視循證實踐研究的作用和價值,強調循證實踐有助于進一步明確干預方法的有效性和明晰干預方法使用的注意事項[51-52]。目前我國關于IF的實證研究較少,基于本土情況的IF實踐探索較為不足。我國后續研究應該重視在循證研究中對IF進行探索,通過對國外研究經驗的學習和拓展,對IF干預程序進行本土化處理和完善,在實證研究中不斷豐富IF的理論和實踐發展。
(二)注重IF干預的效果追蹤,開展持續的追蹤研究
國外關于IF持續追蹤的研究較少,涉及效果追蹤的研究也大多只關注較短時間內(如兩周內)的延時效果,對更長時間的效果追蹤關注則較為不足。由此,我國研究者可以在國外學者研究的經驗基礎上,對IF的實證研究進行較長時間的追蹤,關注IF干預的維持效果。通過追蹤研究的問題反饋,不斷反思和更新IF的使用方法、操作步驟和注意事項等內容,從而更加高效地幫助ASD兒童提升其言語行為水平。
(三)開展綜合的干預研究
首先,對IF與多種干預方法的結合進行探索。現有研究已經證實,IF可以與其他方法聯合進行干預。研究證實,在原有干預方法的基礎上,加入IF比沒有加入IF的教學效率明顯提高,干預對象在掌握主要目標的同時還獲得了IF目標,干預效果明顯增強[53]。一方面,ASD兒童言語行為問題較為復雜,使用多種干預方法對其進行干預,能夠使干預效果達到最佳;另一方面,IF作為承擔次要目標的方法載體,多與其他干預方法所承擔的主要目標聯合進行干預。所以,未來不僅可以注重探究不同干預方法與IF的組合,形成綜合性較強的干預模式;同時也可以進一步探索IF和不同干預方法結合的干預效果,從而為更高質量的干預實踐提供經驗借鑒和操作指導。其次,加強對參與IF干預人員的專業培訓,建立完善的IF干預人員專業培訓體系。將ASD兒童的家長、教師及同伴納入IF干預訓練中,為ASD兒童的家長和同伴提供有關IF干預方法的專業支持。眾多研究已經表明,家長執行式干預和同伴介入法都是對孤獨癥兒童有效的干預方式[54-55]。可以為家長和同伴提供IF的專業指導和支持,培訓其IF使用的流程和注意事項等內容,讓多方力量都加入ASD兒童的IF干預中,從而有效拓展IF的實施主體,形成一種較為多元、多方的干預模式。最后,隨著大數據在教育領域的不斷更新和發展,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技術逐漸被證明能夠有效提高教育的效率[56-57]。在特殊教育領域,具有多元化、高技術化特質的科技輔助技術已經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58]。在IF應用于ASD兒童的干預研究中,大數據的支持能有助于提升干預數據的錄入、提取和分析效率。因此,我國未來使用IF的干預研究要注重獲取新興技術的支持,形成科技與干預、教育相結合的綜合、全面、高效的干預模式。
[參考文獻]
[1]吳希如,林慶.小兒神經系統疾病基礎與臨床[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665.
[2]邵智,郝建萍,靜進,等.兒童自閉癥康復治療學[M].重慶:西南大學出版社,2018:3.
[3]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V[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2013:50-59.
[4]Edition F.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J]. Am Psychiatric Assoc, 2013(21): 591-643.
[5]荊偉,方俊明.自閉癥譜系障礙兒童詞語習得研究述評[J].中國特殊教育,2011(10):53-58+21.
[6]Ming S, Moran L, Stewart I. Derived Relational Responding and Generative Language: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Teaching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J]. European Journal of Behavior Analysis, 2014(2): 199-224.
[7]Rose V, Trembath D, Keen D, et al. The Proportion of Minimally Verbal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a Community-Based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me[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2016(5):464-477.
[8]Durkin K, Conti-Ramsden G, Simkin Z. Functional Outcomes of Adolescents With a History of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SLI) With and Without Autistic Symptomatology[J].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012(1): 123-138.
[9]Skinner B F. Verbal Behavior[M]. New York: Appeton-Century-Crofts, 1957: 59.
[10]Mason L L, Andrews A. The Verbal Behavior Stimulus Control Ratio Equation: A Quantification of Language[J]. Perspectives on Behavior Science,2019(2):323-343.
[11]王分分,祝卓宏.言語行為的關系框架理論視角:孤獨癥譜系障礙的新探索[J].心理科學進展,2017(8):1321-1326.
[12]金寧,戶秀美,馬永強,等.孤獨癥兒童言語行為教學研究述評[J].中國特殊教育,2020(4):46-53.
[13]Bennett K,Reichow B, Wolery M.Effects of Structured Teaching on the Behavior of You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J]. Focus on Autism and Other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011(3): 143-152.
[14]Werts M G, Wolery M, Holcombe A, et al. Instructive Feedback: Review of Parameters and Effects[J]. Journal of Behavioral Education, 1995(1):55-75.
[15]Albarran S A, Sandbank M P. Teaching Non-Target Information to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An Examination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Literature[J]. Journal of Behavioral Education, 2019(1): 107-140.
[16]Holcombe A, Wolery M, Werts M G, et al. Effects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on Future Learning[J]. Journal of Behavioral Education,1993(3):259-285.
[17]Wolery M, Ault M J, Doyle P. Teaching Stud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Disabilities: Use of Response Prompting Strategies[M]. London: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92:11-23.
[18][32][39][40][45]Frampton S E, Shillingsburg M A.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Verbal Responses Using Instructive Feedback[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2020(2):1029-1041.
[19]Reichow B, Wolery M. Comparison of Progressive Prompt Delay With and Without Instructive Feedback[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2011(2):327-340.
[20][41][50]Delmolino L, Hansford A P, Bamond M J, et al. The Use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for Teaching Language Skills to Children With Autism[J]. 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2013(6):648-661.
[21][38]Gavidia V L, Bergmann S, Rader K A. The Use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to Promote Emergent Tact and Intraverbal Control:A Replication[J]. The Analysis of Verbal Behavior,2022(4):1-26.
[22]Carroll R A, Kodak T. Using Instructive Feedback to Increase Response Variability During Intraverbal Training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J]. The Analysis of Verbal Behavior,2015(2):183-199.
[23][36][44]Tullis C A, Frampton S E, Delfs C H, et al. Teaching Problem Explanations Using Instructive Feedback[J]. The Analysis of Verbal Behavior,2017(1):64-79.
[24]Loughrey T O, Betz A M, Majdalany L M, et al. Using Instructive Feedback to Teach Category Names to Children With Autism[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2014(2):425-430.
[25]Tullis C A, Marya V, Alice Shillingsburg M. Enhancing Instruction via Instructive Feedback for a Child With Autism Using a Speech-Generating Device[J]. The Analysis of Verbal Behavior,2019(1):103-112.
[26]Zemantic P K. A Comparison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During High and Low Demand Contexts on Intraverbals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D]. Eugene: University of Oregon, 2019.
[27]Vladescu J C, Kodak T M. Increasing Instructional Efficiency by Presenting Additional Stimuli in Learning Trials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2013(4):805-816.
[28][33][37][46]Nottingham C L, Vladescu J C, Kodak T, et al. Incorporating Multiple Secondary Targets Into Learning Trials for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2017(3):653-661.
[29]Leaf J B, Cihon J H, Alcalay A, et al. Instructive Feedback Embedded Within Group Instruction for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2017(2):304-316.
[30]Nottingham C L, Vladescu J C, DeBar R M, et al. The Influence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Presentation Schedule:A Replication With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2020(4): 2287-2302.
[31][34]Lin G. The Use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for Teaching English and Familial Language Vocabulary to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D].Minnesota: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2022.
[35]白曉宇,Tawanda S M,祝卓宏.PEAK關系訓練系統:孤獨癥語言障礙康復的新方法[J].心理科學進展,2019(11):1896-1905.
[42]Maenner M J, Shaw K A, Bakian A V, et al.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mong Children Aged 8 Years-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onitoring Network, 11 sites, United States, 2018[J]. MMWR Surveillance Summaries,2021(11):1.
[43]韋小滿,劉宇潔,楊希潔.單一被試實驗法在特殊兒童干預效果評價中的應用[J].中國特殊教育,2014(4):27-30.
[47]Holcombe A, Wolery M, Werts M G, et al. Effects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on Future Learning[J]. Journal of Behavioral Education,1993(3):259-285.
[48]Stinson D M, Gast D L, Wolery M, et al. Acquisition of Nontargeted Information During Small-Group Instruction[J]. Exceptionality: A Special Education Journal, 1991(2): 65-80.
[49]Werts M G, Wolery M, Holcombe A, et al. Effects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Related and Unrelated to the Target Behaviors[J]. Exceptionality,1993(2):81-95.
[50]Delmolino L, Hansford A P, Bamond M J, et al. The Use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for Teaching Language Skills to Children With Autism[J]. 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2013(6):648-661.
[51]胡曉毅,翟鈺欣,孫蘊軒,等.孤獨癥兒童循證實踐研究發展及其對特教教師教育的啟示[J].教師教育研究,2021(4):7-13.
[52]傅王倩,黃曉磊,肖非.特殊教育中循證實踐標準設立的困境與應對[J].比較教育研究,2018(7):104-111.
[53]Reichow B, Wolery M. Comparison of Progressive Prompt Delay With and Without Instructive Feedback[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2011(2):327-340.
[54]曾松添,胡曉毅.美國自閉癥幼兒家長執行式干預法研究綜述[J].中國特殊教育,2015(6):62-70.
[55]連福鑫,王雁.融合環境下自閉癥譜系障礙兒童社會交往同伴介入干預研究元分析[J].教育學報,2017(3):79-91.
[56]劉革平,高楠,胡翰林,等.教育元宇宙:特征、機理及應用場景[J].開放教育研究,2022(1):24-33.
[57]雷江華,習妮.大數據背景下特殊教育現代化的內涵與路徑[J].現代特殊教育(基礎教育研究),2021(5):4-8.
[58]李歡,林佳英.近20年國際特殊教育輔助技術研究的演化路徑分析[J].中國特殊教育,2020(1):7-16.
A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structive Feedbackin Speech Behavior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LIU Xi1,2? YU Jufen2
(1.School of Education,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2.College of Special Education,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Sichuan? 614000)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to speech behavior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14 relevant foreign empirical studies we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and analyzed, and their curr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spects of intervention objects, intervention context, materials used, assessment tools, experimental design, intervention objectives and intervention effects were summarized.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empirical research,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tracking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intervention, optimize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intervention, and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instructive feedback combined with other intervention methods.
Key words:instructional feedback;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speech action
(特約編校? 孫?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