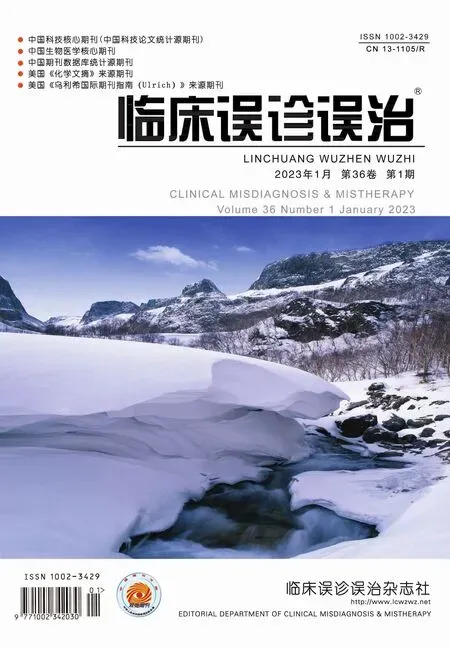乳腺浸潤性癌伴導(dǎo)管原位癌誤診為單純導(dǎo)管原位癌的臨床分析
黃 偉,吳 斌
隨著數(shù)字化乳腺X線攝影(DM)的廣泛應(yīng)用,新診斷的乳腺癌中單純導(dǎo)管原位癌(DCIS)的占比由原來的1%~2%急劇增加至20%[1-2]。在國內(nèi),術(shù)前對(duì)DCIS的確診主要依靠超聲引導(dǎo)下空芯針穿刺活檢的病理學(xué)結(jié)果。但空芯針穿刺活檢不能獲取完整的病變組織,在不同的文獻(xiàn)報(bào)道中,空芯針穿刺活檢導(dǎo)致病理學(xué)低估率可以達(dá)到40%[3],表現(xiàn)為術(shù)后切除病理診斷升級(jí)為更高級(jí)別的DCIS或浸潤性癌伴DCIS。此外據(jù)報(bào)道,術(shù)前診斷DCIS患者中行前哨淋巴結(jié)活檢后發(fā)現(xiàn)陽性淋巴結(jié)轉(zhuǎn)移的發(fā)生率為0.98%~13.00%[4-6]。因此,針對(duì)DCIS患者中可疑浸潤性癌的患者通過更嚴(yán)格的術(shù)前評(píng)估,能夠有效降低術(shù)前的誤診誤治概率,尤其是對(duì)類似三陰性、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陽性及腋窩淋巴結(jié)陽性的患者,若診斷為浸潤性癌,則可能納入新輔助治療范疇,有利于患者獲得更佳的預(yù)后[7]。納入我院2019年3月—2020年3月收治45例乳腺單純DCIS為研究對(duì)象,其中9例(20%)出現(xiàn)誤診。本文對(duì)誤診患者的臨床查體、影像學(xué)檢查、病理資料等進(jìn)行分析,旨在減少乳腺浸潤性癌的誤診。
1 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 本組9例均為女性,均已婚已育,年齡43~65歲,病程15 d~12個(gè)月。1例未絕經(jīng),2例處于圍絕經(jīng)期,6例已絕經(jīng)。所有患者皆為單側(cè)發(fā)病,其中右側(cè)7例,左側(cè)2例。所有病例在術(shù)后經(jīng)病理診斷有不同大小的浸潤性癌成分存在,浸潤性癌最大徑0.8~2.1 cm。
1.2臨床表現(xiàn) 本組均以乳房腫塊就診,其中1例伴有乳房皮膚改變,表現(xiàn)為乳頭旁皮膚水腫、增厚;1例伴有右側(cè)乳頭褐色溢液。1例腫塊位于乳頭旁,其余患者腫塊距乳暈1.5~7.0 cm,分布于各象限內(nèi),腫塊形狀不規(guī)則,大小(1.6~3.5)cm×(0.8~3.6)cm,質(zhì)地中等或硬,邊界不清,未與周圍組織粘連,活動(dòng)度均較差。可觸及同側(cè)腋下淋巴結(jié)4例,其中1例淋巴結(jié)觸診大小2.0 cm×1.5 cm,質(zhì)地較硬,活動(dòng)度可,未與周圍淋巴結(jié)融合粘連;余3例淋巴結(jié)觸診大小1.0 cm×(0.5~1.0)cm,質(zhì)韌,活動(dòng)度可,未與周圍淋巴結(jié)融合粘連。
1.3影像學(xué)檢查 本組均行乳腺超聲、DM、MRI等檢查。①超聲:共發(fā)現(xiàn)腫塊10個(gè),所有腫塊為形狀不規(guī)則、邊界不光滑(小葉、毛刺或蟹足狀)的低回聲腫塊且內(nèi)部回聲欠均勻,2例可見腫塊內(nèi)部散在點(diǎn)狀強(qiáng)回聲。乳腺影像報(bào)告和數(shù)據(jù)系統(tǒng)(BI-RADS)分類中1例4a類、5例4b類、2例4c類、1例5類,9例腫塊內(nèi)部及周邊血流信號(hào)均為Ⅱ~Ⅲ級(jí),收縮期峰值平均流速23.5 m/s,阻力指數(shù)均>0.7。同側(cè)腋窩淋巴結(jié)形態(tài)異常者3例,其中2例呈類圓形,皮質(zhì)明顯增厚>3 mm,皮髓質(zhì)分界不清,脂肪門消失,淋巴結(jié)內(nèi)部血流信號(hào)豐富;其余1例可見皮質(zhì)增厚而其余結(jié)構(gòu)未見異常。②DM:7例見高密度腫塊影,2例等密度腫塊影;2例見呈集群分布的細(xì)小多形性鈣化,1例見簇狀不定型鈣化,1例見多發(fā)點(diǎn)狀鈣化;2例見內(nèi)部沙粒樣鈣化;其余患者未見明顯鈣化影。③MRI:5例表現(xiàn)為類圓形或不規(guī)則形腫塊樣強(qiáng)化,邊緣不規(guī)則或清楚,內(nèi)部強(qiáng)化不均勻;4例表現(xiàn)為區(qū)域性或段樣非腫塊樣強(qiáng)化,對(duì)側(cè)乳腺無對(duì)稱病灶,內(nèi)部均勻強(qiáng)化。同側(cè)腋窩淋巴結(jié)呈圓形或類圓形4例,皮質(zhì)明顯增厚>3 mm,脂肪門均消失。
1.4病理學(xué)檢查 本組均采用巴德公司14G一次性活檢針(規(guī)格:MQ1410 14G*10 cm)取病灶組織,每例6根。本組術(shù)前穿刺活檢發(fā)現(xiàn)6例高級(jí)別DCIS,2例中級(jí)別DCIS,1例中-高級(jí)別DCIS;其中2例伴有粉刺樣壞死。分子分型:LuminalB/HER-2陽性3例,LuminalB/HER-2陰性2例,HER-2過表達(dá)3例,三陰性1例。
1.5誤診情況及確診經(jīng)過 本組術(shù)前均誤診為單純DCIS,均于入院3 d內(nèi)行完整病灶切除手術(shù)治療,經(jīng)手術(shù)病理檢查確診為乳腺浸潤性癌伴DCIS,誤診時(shí)間為9~19 d。
1.6治療及預(yù)后 本組均采用外科手術(shù)治療,6例行乳房全切術(shù),2例行保乳術(shù),1例行保留乳頭和乳暈的乳房重建術(shù);所有患者行同側(cè)腋窩前哨淋巴結(jié)活檢術(shù),4例前哨淋巴結(jié)活檢術(shù)后發(fā)現(xiàn)1枚轉(zhuǎn)移性淋巴結(jié),然后行腋窩淋巴結(jié)清掃。所有患者依據(jù)術(shù)后浸潤灶大小、病理類型、手術(shù)方式等,完成后續(xù)治療方案。預(yù)后均良好,隨訪期間未見復(fù)發(fā)。
2 討論
2.1疾病概述 根據(jù)2020年全球癌癥負(fù)擔(dān)數(shù)據(jù),女性乳腺癌成為全球第一大常見癌癥,預(yù)計(jì)年增加發(fā)病人數(shù)超200萬人[8]。如此龐大的新增乳腺癌患者預(yù)示著更多DCIS的出現(xiàn),對(duì)此類患者的精確診斷和治療值得引起臨床的重視。DCIS即癌細(xì)胞局限于導(dǎo)管內(nèi),故用術(shù)語“原位”來表示。因此理論上講,單純DCIS不會(huì)侵犯乳腺導(dǎo)管基底細(xì)胞層以外的鄰近組織、淋巴結(jié)和器官。一項(xiàng)納入1185例DCIS的單中心預(yù)后分析結(jié)果顯示,我國DCIS患者總體預(yù)后極好,5年總生存率、無局部復(fù)發(fā)生存率和無病生存率分別為99.9%、98.7%和96.6%,10年總生存率、無局部復(fù)發(fā)生存率和無病生存率分別為99.5%、97.8%和90.5%[9]。在臨床上,術(shù)前空芯針穿刺活檢病理診斷為DCIS的患者,由于其預(yù)后好于浸潤性癌,且治療以外科手術(shù)切除為主,臨床醫(yī)師容易掉以輕心,常盡快通過手術(shù)對(duì)病灶進(jìn)行切除,甚至直接將病灶默認(rèn)為單純DCIS,忽略了查體、影像學(xué)、病理學(xué)分型等方面可能對(duì)診斷和治療產(chǎn)生的影響。部分的浸潤性癌灶“偽裝”在空芯針穿刺活檢診斷的DCIS中,造成了對(duì)浸潤性癌患者的誤診、漏診,隨著新輔助治療在乳腺癌治療中的地位不斷提升,此類誤診、漏診將會(huì)影響患者的最佳治療順序,甚至影響患者療效。需要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降低誤診率, 提高臨床的診治水平。
2.2誤診原因分析
2.2.1臨床查體重視度差:臨床查體作為內(nèi)外科醫(yī)師的基礎(chǔ),在診斷疾病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本組9例均為可觸及乳腺腫塊,已有研究表明,可觸及乳腺腫塊與術(shù)后病理診斷中升級(jí)發(fā)現(xiàn)浸潤性癌有顯著相關(guān)性[10-12],而大多數(shù)臨床醫(yī)師忽略了這項(xiàng)提示信息。在腋窩查體方面,1例腋窩淋巴結(jié)可觸及明顯增大,達(dá)2.0 cm×1.5 cm且質(zhì)地硬,因病理診斷為DCIS,并未行腋窩淋巴結(jié)的病理學(xué)評(píng)估,最終導(dǎo)致該患者腋窩淋巴結(jié)陽性的漏診,還有3例查體可捫及腋窩淋巴結(jié)增大,均未行病理學(xué)評(píng)估,亦漏診。
2.2.2影像學(xué)檢查未能綜合評(píng)估:有研究表明,超聲提示腫塊直徑>2 cm和更高的BI-RADS分類是術(shù)后腫瘤病理升級(jí)的獨(dú)立危險(xiǎn)因素[13]。而本組中,7例腫瘤直徑>2 cm,所有患者BI-RADS分類均在4a類以上。國外一項(xiàng)納入52個(gè)研究的薈萃分析顯示,在DM上有致密腫塊的患者與無腫塊或僅有鈣化的患者相比,術(shù)后病理升級(jí)的可能性更高[14]。同時(shí),王富文等[15]指出,DM顯示伴細(xì)小鈣化灶患者術(shù)后發(fā)現(xiàn)DCIS病理診斷被低估的比例較大。在本組中DM均發(fā)現(xiàn)了致密腫物,6例可見明顯不同形狀及分布鈣化。LEE等[16]研究發(fā)現(xiàn),術(shù)前MRI表現(xiàn)為腫塊樣強(qiáng)化、不均勻或環(huán)狀強(qiáng)化等因素是術(shù)后標(biāo)本中有浸潤性成分的預(yù)測因素。趙雪等[17]的研究也指出,在MRI中,浸潤性癌的腫塊樣強(qiáng)化發(fā)生率明顯高于DCIS,且浸潤性癌患者病灶強(qiáng)化形式多表現(xiàn)為區(qū)域分布,內(nèi)部強(qiáng)化不均勻,更進(jìn)一步佐證了LEE等[16]的研究結(jié)果。本組中5例MRI表現(xiàn)為類圓形或不規(guī)則形腫塊樣強(qiáng)化且內(nèi)部強(qiáng)化不均勻。同時(shí),MRI對(duì)術(shù)前腋窩淋巴結(jié)轉(zhuǎn)移的預(yù)測也有較高的敏感度和特異度,甚至敏感度要高于PET/CT,淋巴結(jié)轉(zhuǎn)移在MRI上通常表現(xiàn)為淋巴結(jié)呈圓形或不規(guī)則形,皮質(zhì)增厚(厚度>3 mm),脂肪門消失[18-19]。本研究中,4例同側(cè)腋窩淋巴結(jié)呈圓形或類圓形,皮質(zhì)明顯增厚>3 mm,脂肪門均消失,最終該4例均發(fā)現(xiàn)腋窩淋巴結(jié)轉(zhuǎn)移。以上分析的影像學(xué)特點(diǎn),本組均至少符合2項(xiàng)及以上,可能是術(shù)后病理出現(xiàn)浸潤性癌的原因。典型病例影像學(xué)檢查見圖1。
2.2.3術(shù)前DCIS分級(jí)分型未重視:核分級(jí)高是病理學(xué)低估的重要危險(xiǎn)因素[10-11,14,16,20-21]。本研究中9例均為中、高級(jí)別DCIS。LEE等[16]、曹威等[21]、NICOSIA等[22]和MUSTAFA等[23]研究已表明,術(shù)前診斷分子分型為HER-2陽性的DCIS患者,術(shù)后病理伴浸潤性癌的可能性更大。以上分析的術(shù)前病理學(xué)特點(diǎn)均可能是病理學(xué)低估的原因。

圖1 誤診為乳腺單純DCIS患者術(shù)前超聲、DM、MRI影像學(xué)檢查圖像(女,63歲)
2.3防范誤診措施
2.3.1進(jìn)行全面而專業(yè)的查體:對(duì)DCIS患者應(yīng)更注重乳房及腋窩查體,對(duì)于可觸及的腫塊、異常的腋下淋巴結(jié),需更為謹(jǐn)慎的結(jié)合影像學(xué)及病理學(xué)檢查分析,必要時(shí),對(duì)腋窩淋巴結(jié)采取細(xì)針穿刺檢查甚至空心針活檢。
2.3.2多種影像學(xué)檢查聯(lián)合分析:在腫塊評(píng)估時(shí),對(duì)術(shù)前影像學(xué)檢查存在腫塊>2 cm、BI-RADS分類4a以上、DM顯示致密腫塊或存在異形鈣化、MRI顯示腫塊樣強(qiáng)化且內(nèi)部不均勻強(qiáng)化等征象的患者需提高警惕,若高度符合以上多項(xiàng)特征,必要時(shí)可再次對(duì)原發(fā)腫塊進(jìn)行穿刺活檢。國外有回顧性研究顯示,穿刺活檢的次數(shù)與病理低估呈負(fù)相關(guān)[10,24];對(duì)腋窩淋巴結(jié)評(píng)估時(shí),若影像學(xué)檢查發(fā)現(xiàn)淋巴結(jié)明顯增大、皮髓質(zhì)分界不清、皮質(zhì)增厚>3 mm、脂肪門消失,甚至部分有增大融合等征象時(shí),則必須對(duì)淋巴結(jié)行穿刺活檢,取得病理學(xué)依據(jù)。
2.3.3多維度解析術(shù)前病理:穿刺時(shí)多點(diǎn)多方位取材有利于降低病理低估率,對(duì)穿刺活檢提示較高級(jí)別的DCIS,或術(shù)前病理檢測提示HER-2陽性等高風(fēng)險(xiǎn)因素,可綜合評(píng)估影像學(xué)檢查和查體,若具備多項(xiàng)術(shù)后病理升級(jí)的高風(fēng)險(xiǎn)因素,需再次對(duì)腫瘤進(jìn)行穿刺活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