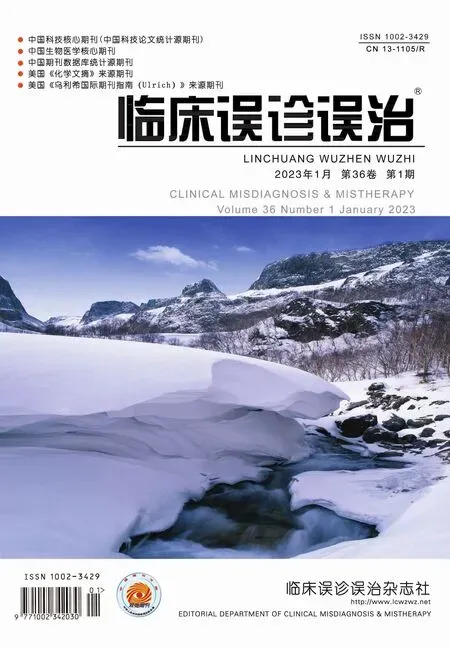肩關節鏡不同入路方式在創傷性肩關節脫位中的應用效果及安全性
王 琳,尚文強,李艷蔚
肩關節是功能、解剖最復雜的關節,其脫位發生率約占所有關節的50%,其中肩關節前脫位發生率高達85%[1-2]。肩關節前脫位主要是由間接或直接暴力引起,表現為肩關節疼痛、腫脹、活動受限,一旦處理不當,極易引起復發性肩關節脫位。肩關節鏡手術是治療創傷性肩關節脫位理想術式,其效果已得到諸多研究者肯定[3-4]。肩關節鏡前方雙入路手術需經后方、前下、前外3個入路共同完成,但前下、前外2個入路距離近,易互相干擾,且5點位錨釘較難置入,手術風險大。肩關節鏡前方改良單入路是由經典肩關節鏡手術演變而來,可有效彌補上述不足,保證手術順利進行,但其效果仍缺乏大量循證支持。相關研究指出,手術創傷及圍術期低體溫均會影響機體凝血纖溶系統,增加血栓形成風險,影響疾病轉歸[5]。因此,本研究回顧性分析肩關節鏡不同入路方式在創傷性肩關節脫位中應用效果及安全性。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8年6月—2021年6月我院收治的創傷性肩關節脫位102例的臨床資料。納入標準:經詢問病史、臨床表現、查體及影像學檢查確診新發創傷性肩關節脫位;單側脫位;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其他肩關節疾病(肩袖撕裂、肩袖損傷、先天性肩關節發育畸形);肩關節手術史;重要臟器器質性病變;術前凝血功能異常;術前2周服用抗凝藥物;合并血管神經損傷。根據手術方案分為改良入路組和傳統入路組,各51例。改良入路組男31例,女20例;年齡20~75(47.45±4.78)歲;受傷至手術時間1~14(8.42±1.18)d;左肩28例,右肩23例;受傷原因:砸傷8例,摔傷20例,運動傷13例,道路交通傷10例;傳統入路組男35例,女16例;年齡18~74(46.42±5.56)歲;受傷至手術時間2~14(8.11±1.34)d;左肩26例,右肩25例;受傷原因:砸傷10例,摔傷18例,運動傷16例,道路交通傷7例。2組性別、年齡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2組均由同一組醫師團隊實施手術操作,全麻,取側臥位,后傾10°,先行患肢牽引,傳統入路組行肩關節鏡前方雙入路手術,自肩峰后外側軟點入路,建立關節鏡通道,置入關節鏡,關節鏡下建立肩關節前方入路及前上外側入路,檢查病變位置、損傷類型等,松解盂唇粘連,刮匙處理關節盂邊緣,直至出血,明確并標記進釘位置,于關節盂緣軟骨面鉆孔,約3~5個,置入鈦合金帶線錨釘,縫合后沖洗手術切口。改良入路組行肩關節鏡前方改良單入路手術,自肩峰后外側軟點入路探查前方盂唇損傷情況,前方僅建立1個突旁入路,置入防水套管(8 mm),剝離盂唇組織,于擬置入錨釘骨床處行新鮮化處理,打磨盂唇邊緣軟骨,預置錨釘處鉆孔,并在與之相對應的腎盂偏遠端縫合,相應角度縫合鉤經此處盂唇及部分前關節囊,釋放Suturelasso,抓線鉗抓取Suturelasso末端,拉出套筒,將縫線經Suturelasso導入縫合處,調整尾線長度及張力,將錨釘順預置孔打入骨孔,剪斷尾線,同樣方法縫合腎盂,置入剩余錨釘,結合病變撕裂范圍置入2~3枚錨釘。術后2組均用肩關節外展支具固定6~8周,術后次日行肩關節主被動練習,術后1周做患肢前屈肌45°內外展活動,術后4周做外展位適度的外旋訓練。
1.3觀察指標 ①觀察2組圍術期指標。②凝血纖溶參數:分別于術前、術后1 d、術后3 d,取空腹外周靜脈血2 ml,肝素抗凝,應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測定血漿纖維蛋白原(FIB)、D-二聚體(D-D)、纖維蛋白降解產物(FDP)。③肩關節功能:分別于術前、術后6個月、術后12個月,以Constant-Murley肩關節功能評分量表[6],從功能活動、關節活動范圍、疼痛、肌力情況4個維度評價肩關節功能,各維度得分依次為20、40、15、25分,分值與肩關節功能呈正相關。同時記錄肩關節前屈、外展上舉活動度。④手術效果:術后12個月參照Karlsson標準[7]評價。優為患肩肌力正常,關節活動自如,X線顯示肩鎖關節復位;良為自覺患肩肌力減弱,關節活動略受限,X線顯示肩鎖關節半脫位;差為未達上述標準。優良率=(優+良)/總例數×100%。⑤觀察2組并發癥發生情況,包括切口感染、關節疼痛、外旋活動受限。

2 結果
2.1圍術期指標 改良入路組術中出血量少于傳統入路組,住院時間短于傳統入路組(P<0.01);2組手術時間、骨折愈合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2組創傷性肩關節脫位圍術期指標比較
2.2凝血纖溶參數 術前、術后3 d,2組凝血纖溶參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1 d,改良入路組血漿FIB、D-D、FDP水平均低于傳統入路組(P<0.01)。見表2。
2.3肩關節活動度 術前、術后6個月、12個月,2組肩關節活動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6、12個月,2組肩關節前屈、外展上舉活動度大于術前(P<0.05)。見表3。
2.4Constant-Murley肩關節功能評分 術前、術后6個月、12個月,2組Constant-Murley肩關節功能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6、12個月,2組肌力情況、功能活動、疼痛、關節活動范圍評分均高于術前(P<0.05)。見表4。
2.5手術效果 術后12個月,2組優良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2.6并發癥發生情況 2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6。

表2 2組創傷性肩關節脫位手術前后凝血纖溶參數比較

表3 2組創傷性肩關節脫位手術前后肩關節活動度比較

表4 2組創傷性肩關節脫位手術前后Constant-Murley肩關節功能評分比較分)

表5 2組創傷性肩關節脫位手術效果比較[例(%)]

表6 2組創傷性肩關節脫位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例(%)]
3 討論
創傷性肩關節脫位是肩部外傷后肱骨頭與肩胛盂形成的關節脫位,其發病率約占肩關節脫位的96%,若采取保守治療,肩關節脫位復發率可高達78%,給其個人及家庭帶來沉重經濟負擔[8-10]。隨著微創技術的不斷普及,關節鏡手術憑借微創、并發癥少、術后恢復快等優勢逐漸應用于肩關節脫位,且手術效果與開放手術相似[11-12]。
入路方式選擇是肩關節鏡手術研究重點內容,目前臨床關于肩關節鏡前方雙入路手術已有諸多研究報道,該術式主要是經后方軟點、前下、前外入路,后方軟點用于探查關節內病變,前下入路為主操作孔,負責置入錨釘、縫合過線;前外入路為第2觀察入路、輔助操作孔,用于前方盂唇病變評估、縫線管理[13]。臨床實踐發現,肱骨頭、肩胛緣、二頭肌長頭腱形成的安全三角面積有限,前方2個入路切口距離近,經前下入路孔置入錨釘或縫合時,易使前外通道無意退出,加以上述入路切口平行分布,需另外增加5點位入路,極易損傷周圍神經、血管,增加手術難度[14]。研究表明,創傷性肩關節脫位患者前方盂唇僅發生1~4點位的撕裂,且關節囊無明顯松弛,此時僅需建立一個喙突外下入路即可完成手術操作[15]。肩關節鏡前方改良單入路手術經前方喙突外下入路實施手術操作,相比于肩關節鏡前方雙入路手術具有以下優勢:手術切口小、疼痛輕、術中出血量少;有效規避前方2個入路相互干擾;無須5點位入路即可將錨釘置于肩盂前下方。同時關節鏡輔助手術,便于術者直接觀察關節內部結構,提高術野及操作精準度,進一步減少術中出血量,縮短康復進程。本研究結果發現,改良入路組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少于或短于傳統入路組,提示肩關節鏡前方改良單入路手術在創傷性肩關節脫位中具有獨特優勢。多數外科醫師認為,減少輔助操作孔必然會增加手術難度,延長手術時間[16]。本研究發現,2組手術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究其原因:①肩關節鏡改良單入路術中應用無節錨釘配合Suterelasso技術,可減少過線次數,簡化手術流程;②縮減1個入路方式,可縮短建立入路時間;③術者具有豐富理論知識及實操經驗。同時2組均未出現神經損傷、肱骨頭壞死等并發癥,且肩關節功能及手術效果相當,說明肩關節鏡下不同入路方式均能有效改善肩關節功能,提高手術效果及安全性,均可作為創傷性肩關節脫位手術方案。
有研究報道,手術創傷后應激反應是引起圍術期凝血纖溶系統異常的重要因素,加以術后長期制動,極易引起上肢深靜脈血栓形成,進而延長康復進程[17]。D-D是特異性降解產物,其水平升高提示凝血和纖溶系統雙重激活[18-19]。FIB是參與凝血與止血過程中的重要纖維蛋白,一旦凝血系統激活,可轉化為纖維蛋白,形成網狀多聚體,增加血栓發生風險[20]。FDP是纖維蛋白原降解產物,其水平升高提示機體纖溶呈亢進狀態[21-23]。本研究發現,術后1 d,改良入路組血漿FIB、D-D、FDP水平均低于傳統入路組,說明肩關節鏡下前方改良單入路手術對創傷性肩關節脫位患者凝血纖溶系統的影響較小,考慮原因與手術創傷小、應激反應輕有關。術后3 d, 2組上述指標趨于術前,說明2種術式所致凝血纖溶系統紊亂并未帶來長期影響。
筆者獲得如下體會與經驗:①肩關節鏡前方雙入路手術中,前下、前外入路通道需正確放置,以免影響錨釘固定及病變處創傷清理;應完全松解粘連、撕裂的盂唇-關節囊韌帶復合體,保證其固定至肩盂邊緣;②肩關節鏡前方改良單入路中,應充分考慮肩關節損傷范圍,若撕裂范圍適中,預計置入3枚及以下錨釘者,繼續實施手術操作;若撕裂范圍廣泛,預計置入4枚以上錨釘者,應建立前外入路,轉為傳統術式繼續手術。
綜上,肩關節鏡不同入路方式在創傷性肩關節脫位中效果相當,其中肩關節鏡前方改良單入路手術有助于減少術中出血量,縮短住院時間,且對凝血纖溶系統影響較小。但本研究屬于回顧性研究,可能存在數據偏倚,影響研究結果準確性,日后需開展多中心、大樣本的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進一步證實本研究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