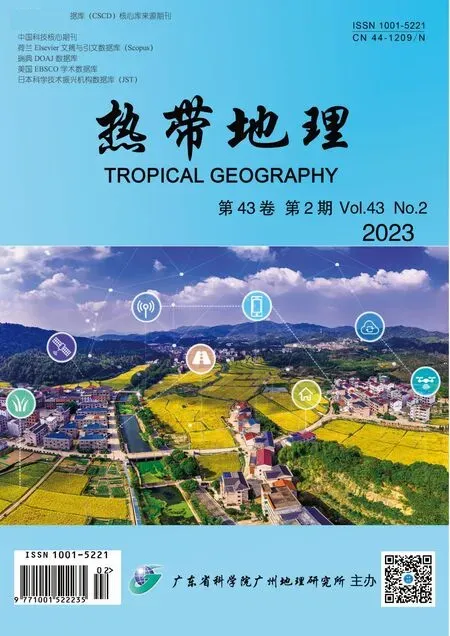可持續鄉村建設現狀及模式
——以長沙市為例
吳 秀,周 配,朱倚萱,龔玉蘭,賀艷華,c
(1.湖南師范大學 a.地理科學學院;b.研究生院;c.城鄉轉型過程與效應校級重點實驗室,長沙 410081;2.長沙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長沙 410014)
城市與鄉村是一個有機體,二者只有共同發展,才能相互支撐(劉彥隨,2018;李玉恒 等,2019)。一直以來,城市偏向發展戰略的實施,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 年,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已由1978 年的17.92%增長到63.89%,但與此同時,也使得鄉村資源要素流失,鄉村發展薄弱(鄭小玉 等,2018)。為此,黨中央自2004—2020年連續17年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三農”問題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重中之重”的地位,中共“十九大”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需要探尋一條可持續的鄉村發展之路,如何促進可持續鄉村建設成為當前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目前,可持續鄉村建設方面的相關研究主要涉及指標體系與評價、發展模式、時空分異特征、發展與轉型路徑等(Winther, 2017;曹智 等,2019;Zang et al., 2020;林藝,2021;Li et al., 2021;李玲燕 等,2022;吳丹丹 等,2022)。鄉村可持續性評價是探尋鄉村可持續發展路徑的前提,目前主要從經濟、社會、環境等方面展開(李小朋 等,2017;Gibbes et al., 2020; Zang et al., 2021;陳妍等,2022)。部分研究顯示,村莊空心化、主體老弱化、環境污損化等“鄉村病”嚴重制約著中國鄉村的轉型與可持續發展(劉彥隨 等,2016;鄭小玉等,2018),并因地域條件和轉型力量的差異,呈現鮮明的地域特征(楊忍 等,2015)。因此,不同地域不同類型的鄉村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需基于其特有的自然資源稟賦條件、社會經濟發展現狀和產業發展基礎等探索適應其區情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和差異化的發展路徑。因地制宜、分類實施(楊園園等,2019)。但目前直接從構建可持續鄉村視角來分析鄉村問題、提煉優化模式的研究并不多,對可持續鄉村內涵與系統構成的理解也有待深化。
近年來,長沙市作為省會城市,鄉村振興工作一直走在湖南省前列,并取得顯著成效。根據《長沙統計年鑒2021》(長沙市統計局 等,2021)和《湖南統計年鑒2021》(湖南省統計局 等,2021)的數據分析,2020 年,全市農林牧漁業總產值7 221 925 萬元,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4 754.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8 169.7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7,比全省平均水平低0.8,農村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得到明顯改善。但與此同時,也存在鄉村建設標準和品質不高、鄉村地域特色不夠明顯、產業發展依然薄弱和同質化、產業帶動農戶增收效果不明顯、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質量仍有待提高等問題。
基于此,本文以可持續發展理論和需求層次理論為指導,詳細闡釋可持續鄉村的內涵和系統構成,并以系統構成中農民生活空間的八大要素為依據,分析長沙市鄉村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共性問題與個性特征,以問題為導向,緊扣可持續鄉村系統的三大核心要素農民生活、農村產業和農村環境,提出差異化的可持續鄉村優化模式與實施路徑。以期為長沙市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理論依據。
1 可持續鄉村內涵和系統構成
1.1 可持續鄉村內涵界定
“可持續性”一詞最早于1972 年在英國出現,此后出現過多個不同的定義(Kidd, 1992)。直至1987 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首次將可持續發展明確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要能力的發展”(WCED, 1987),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Wu et al., 2013)。鄉村是人生活的地方,沒有人,鄉村也將不復存在(王曉毅,2019)。從這個意義上講,鄉村可持續是指鄉村對人有持續的吸引力,能持續地留住人。這樣的鄉村需要具備以下特征:獲得工作的機會;能提供經濟上可行的住宅和健康的居住環境;有便捷的交通和通訊設施;能提供公平的醫療、教育、養老服務;擁有和諧的鄰里關系;有足夠韌性和吸引力,并與外部形成相對穩定的交流合作關系(賀艷華 等,2020;Khomiuk et al., 2020)。此外,城市與鄉村作為相互作用的有機體,存在各種要素的雙向流動,在此過程中提高鄉村對各種要素的吸引力對于鄉村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而鄉村作為與城市相對的區域,具有區別于城市的鄉村性(黃震方 等,2015),如鄉土景觀、農耕文化、樸素的農民、鄉土產品等均是其表征(Cloke et al.,2006),正是這種鄉村性吸引城市居民走進鄉村,體驗與城市截然不同的鄉村生活,形成城市居民對鄉村性的消費需求(楊軍,2006),并使鄉村的獨特功能價值得以顯現,如農產品生產功能、生態環境保護功能、農耕社會文化功能等(陳錫文,2021)。鄉村可持續性強調鄉村性的可持續,更強調在此基礎上產生的鄉村功能的可持續,具體指鄉村地區在維系自然環境支撐力的前提下,為鄉村居民持續提供生計資本與生存空間,滿足其基本需求,同時在保護鄉村性的前提下,為鄉村之外的城市居民提供充足的農產品及其他生態、文化服務的能力(賀艷華 等,2020)。綜上所述,可持續鄉村是可以持續為本地鄉村居民提供優質的就業、居住、出行、醫療、教育、養老、交往等服務,也能不斷為周邊居民提供健康的農產品、良好的生態產品和文旅體驗的鄉村系統。前者主要是內部需求,是可持續鄉村建設的基礎,后者主要是外部服務,是可持續鄉村建設的支撐。
1.2 可持續鄉村系統構成
可持續鄉村是一個綜合系統,涉及社會、經濟、環境3 個維度(Gibbes et al., 2020),即可持續的農村產業、可持續的農村環境以及可持續的農民生活(賀艷華 等,2020)(圖1)。可持續的農民生活是可持續鄉村建設的主要落腳點,同時也是農村產業和農村生態環境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來源,需建立在8 個要素基礎上,即健康安全的居住環境、便捷高質的基礎設施、穩定的就業創業條件、生態宜人的景觀環境、有抵御外界風險的能力、公平高效的鄉村治理、優質共享的公共服務以及守望相助的鄰里關系。可持續的農村產業可以為可持續鄉村生活和可持續農村環境提供物質保障,是可持續鄉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城市居民對鄉村性的消費需求與鄉村發展的多功能化是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城市居民的消費需求包括農產品需求、生態需求、文化需求等,鄉村多功能化過程實質上是為滿足城鄉居民消費需求而發揮其在農產品生產、生態保護、農耕文化傳承等方面的多種功能價值的過程(戴柳燕 等,2019)。可持續的農村生態環境是實現可持續農村產業與可持續農民生活的前提(賀艷華等,2014),同時也是農村產業發展和農民生活空間優化需要堅守的底線和原則。

圖1 可持續鄉村系統構成Fig.1 Composition of sustainable rural systems
2.2 數據來源及樣點說明
采用統計分析、問卷調查、半結構化訪談等方法,對長沙市鄉村可持續發展現狀進行可量化調查與分析。主要數據來源包括:1)有關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如《湖南統計年鑒2021》《長沙統計年鑒2021》等。2)實地調研與農戶問卷,主要對長沙市4個村進行深度訪談和現場觀察(圖2),其中白箬鋪鎮光明村屬于旅游村,喬口鎮盤龍嶺村屬于農業村,大圍山鎮楚東村屬于傳統村,金井鎮蒲塘村屬于特色不明顯的一般村,共完成深度訪談問卷20 份,主要通過訪談了解樣本村發展現狀、問題以及農戶認知與需求,訪談對象涉及村干部和普通村民(表1)。農戶問卷主要通過問卷星在線發放,一共收回732 份問卷,其中根據家庭所在地址和戶籍類型設置,篩選出長沙市范圍內的鄉村戶籍問卷314 份,有效問卷272份,有效率為86.62%。問卷包括居住環境、生產就業、公共服務、基礎設施、景觀生態、鄰里文化、韌性安全、組織治理等內容。

表1 樣本村訪談對象與訪談重點Table 1 Sample village interviewees and interview focus

圖2 長沙市典型樣本村分布Fig.2 Distribution of typical sample villages in Changsha
3 長沙市鄉村可持續發展現狀問題
2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區概況
長沙市位于湖南省東部偏北,是湖南省省會,也是長江中游城市群和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節點城市,包括芙蓉區、天心區、岳麓區、開福區、雨花區和望城區6 個區,瀏陽和寧鄉2 個縣級市以及長沙縣,土地面積11 815.96 km2,占全省總面積的5.58%。2020年,長沙市常住人口數為1 006.08萬,其中農村人口175.10萬,城鎮化率達到82.60%,受快速城鎮化的影響,長沙市是湖南省甚至中部地區城鄉相互作用強度最為劇烈和城鄉矛盾最為突出的城市之一(譚雪蘭 等,2017),正處在城鄉快速轉型發展階段,鄉村可持續發展面臨諸多挑戰。因此,以長沙市的鄉村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可持續發展現狀,提煉可持續鄉村建設模式,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可為快速城鎮化地區的鄉村發展提供借鑒。
3.1 共性問題分析
3.1.1 本地就業機會少,外出務工比例較高 由于本地就業機會有限,加之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工資差異,使得外出務工經商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調查表明,66.50%的村民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于務工收入,21.30%的村民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于個體經營收入,其中鎮外就業占比達到72.9%,成為農村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76.76%的村民表示如果村里或附近鄉村有發展機會,外出就業的勞動力愿意回村發展。由此可見,生計需求是導致鄉村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而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失,使生產主體老弱化現象嚴重,農村耕作技術傳承出現斷層,并導致農村耕地荒廢化、鄉村產業勞動力與人才支撐不夠等問題(龍花樓 等,2017)。數據顯示,35歲以下的年輕勞動力中,不會種地的占比達到73.5%,會種但不想種的占13.6%,會種且常年在家種地的僅占1.1%。
3.1.2 鄉村人居環境建設品質不高,鄉村吸引力不明顯 人居環境是影響農村居民生活福祉的重要因素,美麗整潔、舒適宜居的人居環境有利于提升鄉村吸引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自2018年《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實施以來,長沙市鄉村人居環境臟亂差的局面得到明顯改善,基本實現干凈整潔有序,但建設品質依然不高,在污水處理、垃圾分類等方面還有待提升。調查顯示,垃圾集中處理率達到95.6%,但32.4%的村民未對垃圾進行分類處理,垃圾分類具體落實以及居民自身垃圾分類意識仍有待提升;不經處理直接排放污水的農戶家庭達到37.1%,這與農村居民點分散、人口少、地形復雜,難以實現污水集中處理系統全覆蓋有關。
3.1.3 鄉村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偏低,村民生活滿意度一般 城鄉公共服務的供給差距是影響村民生活滿意度、導致鄉村人口外流的重要因素。調查顯示,村民對村莊不滿意的原因中,醫療衛生水平低和收入水平低占比最高,缺乏休閑娛樂活動和就業機會少也占很大比重(圖3)。在對教育教學、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設施的滿意度調查中,村民的回答集中在“一般”層面(圖4)。公共服務設施滯后尤其是文化娛樂設施短缺導致村民的文化休閑活動較為單一,精神需求得不到多樣化的滿足,鄰里聊天、看電視、手機上網、棋牌活動等成為多數村民的日常休閑活動(圖5)。長期以來城市偏向的二元結構發展格局導致的鄉村資源大量流失是產生該問題的主要原因(寧志中 等,2020)。

圖3 對村莊不滿意的原因Fig.3 Reasons fo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village

圖4 公共服務滿意度調查Fig.4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survey

圖5 村民休閑活動方式調查Fig.5 Investigation on villagers ' leisure activities
3.1.4 鄉村留守主體老弱化,發展韌性不強 提高系統韌性是構建可持續鄉村的重要方面。一個有韌性的農村社區有能力應對來自外部環境的挑戰,并能在維持令人滿意的生活水平情況下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Li et al., 2019)。鄉村發展主體的身體健康狀況、勞動技能、防災知識、防騙意識等是影響鄉村韌性的重要因素,其中村民身體健康狀況和勞動技能水平對家庭能否具備可持續生計能力產
生直接影響。調查顯示,52.2%的村民家庭有慢性病患者、大病患者或殘疾患者;62.5%的村民家庭沒有掌握職業技能的勞動力,參加過職業技能培訓的勞動力僅占23.5%,這不僅不利于持續穩定就業,還會影響鄉村建設的效率和水平。防災知識和防騙意識體現村民應對災害風險和外部不利因素的能力。盡管調查顯示86.8%的村民對防災知識有一定了解,但仍有22.8%的村民遭遇過網絡詐騙,在降低村民對互聯網信任度的同時,增加了農村電商發展的難度,不僅不利于村莊的數字化轉型,也影響了鄉村的持續穩定發展。
3.1.5 鄉村自治水平不高,內生動力不足 鄉村發展持續與否,取決于當地居民所擁有的知識、能力和意愿(Li et al., 2019),提高村民的自治能力是建設可持續鄉村的關鍵。但目前看來,村民內生動力依然不足,主動參與村莊事務的積極性不高。調查顯示,能經常關注并參與村莊事務的村民僅占24.3%,知道村里有合作社的村民僅有50.4%,其中加入合作社的村民僅占47.45%。
3.2 個性特征分析
3.2.1 旅游型鄉村的旅游吸引力不強 鄉村旅游的目標市場主要是城市,以滿足城市居民回歸田園、體驗農家生活、觀賞鄉野風光等需求為出發點,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風民俗、原汁原味的田園風光和充滿野趣的鄉村生活等鄉村性特征是其得以發展的基礎和最大的吸引力(涂文學 等,2017)。通過對長沙市光明村的實地走訪與訪談發現,在該村的旅游業開發過程中,資本是主體,而農民生產和生活場景則趨于邊緣化,村民多從事餐飲、停車場等行業,導致鄉村旅游活動缺乏原真的鄉村性。當被問及旅游業的影響時,本地村民表示“旅游對我們的生活影響很小”“不過,設停車場的那種還是有增加收入的”。此外,旅游業態不夠豐富,難以滿足不同層次游客的旅游需求;游客表示“都是小孩玩的,但是也對大人收費”“如果單是大人出行肯定不會過來的”;旅游知名度不高,游客構成多是周邊城市居民,旅游活動時間短,鄉創中心的創客表示“游客都是當天往返,住宿很少”且“周一到周五游客少”。
3.2.2 農業型鄉村的帶農機制不足 目前,小農戶仍然是中國最主要的農業微觀經營主體,鄉村振興的關鍵也在于振興小農,而非振興資本,為此黨和政府采取多種措施,促進小農戶生產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包括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開展農業社會化服務等(葉敬忠,2018;魏后凱,2019)。但在調研中發現,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小農的帶動作用仍然有限。如盤龍嶺村現有帶農機制僅限于農戶土地入股—租金分紅和向企業(大戶)提供勞務—獲取勞務報酬2種方式。但由于戶均耕地面積僅0.25 hm2,且村內勞務機會有限,長期工僅需30余人,用工量最大時也僅需80余人。因此,盡管村級層面已經實現產業轉型,產業效益也得到提升,但大部分農戶未能從中受益。
3.2.3 傳統型鄉村的文化保護功能衰退 鄉村傳統風貌與傳統文化是鄉村有別于城市的靈魂所在,是鄉村性的標志之一。但調查發現,在城鎮化背景下,鄉村地區尤其是傳統村落的歷史文脈、文化個性等逐漸消失,一些代表地域特色的民俗、節慶活動等也隨著鄉村人口流失而逐漸淡出人們的日常生活,祠堂、戲臺等傳統鄉村公共文化空間也因缺少維護及管理逐漸衰敗。以長沙市傳統村落楚東村為例,由于早期傳統建筑保護與周邊風貌管控不到位,除已經集中改造過的河西街沿河傳統建筑外,其他片區的建筑風格相對凌亂或以現代樓房建筑為主,傳統村落的韻味不復存在;在傳統文化方面,楚東村原本擁有豐富的客家民俗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在開發過程中缺少對傳統文化的深度挖掘、保護以及傳承,以至于本村村民對其了解甚少,問到村莊特有的民風民俗時,村民的回答基本是“沒有”或“不了解”,鄉村傳統文化的挖掘與傳承工作任重道遠。
3.2.4 一般型鄉村的產業發展基礎薄弱 產業是鄉村發展的支撐,是鄉村振興的根本(趙毅 等,2018)。產業興旺,農民才能增收,村集體才會強大,農村才能穩定有活力,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振興。但目前長沙市仍然有一些村莊,在地理位置、資源稟賦以及地域特色等方面均處于劣勢,村莊產業發展緩慢。以長沙市蒲塘村為例,由于鄉村風貌特色不突出,村內文化資源特色也不明顯,并且缺乏特色農產品,導致產業發展滯后。盡管脫貧攻堅期在政府幫扶下發展了茶葉、黃桃、錐栗、五黑雞等脫貧產業,但目前多處于初期發展階段,規模小,產品缺乏市場競爭力,收益低,多數村民仍以外出務工為主,青壯年勞動人口大量流失導致村莊空心化嚴重,經濟活力不足。
4 長沙市可持續鄉村建設模式
基于長沙市可持續鄉村建設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針對旅游型、農業型、傳統型和一般型鄉村,提出4種適宜的可持續鄉村建設模式,即生態休閑旅游模式、高效生態農業模式、特色保護模式和融合發展模式。
4.1 生態休閑旅游模式
4.1.1 模式內涵及建設機制 生態休閑旅游模式是以滿足城市居民消費需求為出發點,依托鄉村田園風光、文化習俗、生態環境等鄉村性特征,結合生態化、低碳化和鄉土化的發展理念,設計休閑、娛樂、度假、體驗、教育等多樣化的鄉村旅游活動,持續提升鄉村生態旅游吸引力,實現產業持續發展、農戶持續增收、生態環境持續保護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圖6)。該模式適用于區位條件優越,生態環境良好,配套服務相對完善,具有一定旅游資源基礎但旅游發展特色不明顯,旅游利益分配不均的鄉村,長沙市光明村就屬于該類型。該模式一方面通過“企業+合作社+旅游協會+農戶”的組織形式,發動農戶深度參與旅游經營活動,進一步優化旅游產業參與主體結構,推動鄉村旅游系統各參與主體實現共贏;另一方面,在加入農戶生產生活元素的基礎上,通過旅游設施與景點的更新改造提質,進一步強化鄉村旅游活動的地域特征與鄉土特色,提升鄉村旅游吸引力。

圖6 光明村的生態休閑旅游模式Fig.6 Ecological leisure tourism mode of Guangming Village
4.1.2 主要建設路徑 1)提升鄉土特色,增強鄉村旅游吸引力。基于鄉村優美的自然生態環境、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以及充滿野趣的鄉村生產生活方式,對鄉村自然生態和傳統文化進行提煉與挖掘,從山水田林湖草居系統出發,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生態旅游項目,并利用文化力量賦能品牌升級;鼓勵村民參與,還原鄉村生活場景,提高鄉村旅游資源的鄉土性特征。
2)優化運營模式,實現利益共享。分別考慮旅游者、當地居民、旅游開發企業、旅游地社會團體需求,完善利益聯結機制,實現共贏;發揮合作社和旅游協會在村莊資源整合方面的紐帶作用和對農戶的帶動作用,通過入股分紅、利潤返還、就業帶動、服務帶動等方式,使農戶逐步成為鄉村旅游發展的主要參與者,讓農戶享受到鄉村旅游發展成果,提高農戶的參與度和獲得感,從而推動旅游地社會經濟和諧良性發展。
4.2 高效生態農業模式
4.2.1 模式內涵及建設機制 高效生態農業模式是基于本地農業資源基礎,利用生態化、智慧化技術,促進專業化、規模化生產與小農戶生產有機結合,打造生產、加工、銷售與廢棄物回收再利用一體化的生態農業模式,持續提高農產品供給能力與農業生態景觀功能,實現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協調統一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圖7)。該模式適用于生態環境良好、污染少,有一定農業發展基礎但農戶增收效益不明顯的鄉村,如長沙市盤龍嶺村。面對該類村莊,可通過“企業+合作社+農戶”與“企業+大戶+農戶”等組織形式,激勵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農戶建立穩固的利益聯結紐帶,發揮其對小農戶在數字化、生態化技術使用等方面的示范帶動作用(魏后凱 等,2019),實現農業的高效、生態、優質生產,發揮農業的多元價值與功能,帶動農戶增收。

圖7 盤龍嶺村的高效生態農業模式Fig.7 Efficient ecological agriculture model of Panlongling Village
4.2.2 主要建設路徑 1)應用生態農業技術。大力推廣農藥、農膜、化肥減量化技術以及農業生產廢物無害化、資源化處理技術,開展清潔生產技術培訓,提高農戶的生態環保意識與能力,并將農業補貼與生態生產行為掛鉤,促使農業生產向生態化生產轉型。
2)建設生態農業產業鏈。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特有生態農產品為資源稟賦,打造有機綠色農產品品牌,建立無公害農產品生產、加工基地;利用“訂單模式”“農產品電商平臺銷售模式”以及公益助農活動等拓展農產品營銷路徑,幫助農戶增收;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為從事農業生產的小農戶提供專業化、社會化服務,降低小農戶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王樂君 等,2019)。
3)應用智慧農業技術。將云計算、互聯網及物聯網技術與現代生物技術、種養殖技術相結合,建立水肥藥精準施用、精準種植、農機智能作業與監控系統,提升生態農業的數字化水平(袁延文,2021);通過大專院校的職業技術教育以及政府組織的智慧農業相關技能培訓等渠道,培養具備數字化素養、掌握智慧農業相關技能的新型職業農民,為智慧農業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完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研發適合農民操作的信息終端設備(侯秀芳等,2017)。
4)完善利益聯結機制。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在技術、用地、項目、稅收、貸款等方面向家庭農場、農業合作社傾斜,為其創造寬松的生產環境和良好的經營氛圍;同時注重其對小農戶的實際帶動情況,以是否與農戶建立利潤返還、股金分紅等穩固的利益聯結機制作為申請財政支持小農生產資金補貼的必備條件(魏后凱 等,2019)。
4.3 特色保護模式
4.3.1 模式內涵及建設機制 特色保護模式是以保護和傳承鄉村傳統文化與農耕文明等鄉村性為重點,依托鄉村特有的歷史文化遺產,結合鄉村田園風光、農事體驗活動和生態環境等鄉村特有資源,適度發展文化旅游及相關產業,最終實現保護與開發相統一,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圖8)。該模式適用于自然生態環境優美、傳統文化資源豐富但文化功能有所衰退的鄉村,傳統村落楚東村屬于該類型。對于該類型村莊,可通過“文旅企業+合作社+農戶”和“文旅企業+遺產保護協會+農戶”等組織形式,發揮遺產保護協會對鄉村傳統文化遺產的保護作用與合作社在農業發展方面對農戶的示范帶動作用,將傳統文化與農耕文化融入文旅產業的發展中,以文興旅,以旅帶農,實現保護和開發協調發展,旅游與農業融合發展,充分發揮傳統村落的農產品生產功能與文化功能。

圖8 楚東村的特色保護模式Fig.8 The characteristic protection mode of Chudong Village
4.3.2 主要建設路徑 1)保護傳統生活空間,增強旅游體驗感。原住民是傳統村落文化的組成部分,其日常的生產生活是傳統文化生長的土壤。因此,打造傳統宜居生活空間,維持鄉土生活節奏與生活方式,發展體驗式的鄉村旅游,減少大型旅游活動對村民日常生活的影響,讓村民在現代生活中融入傳統的文化內涵,對于持續提升傳統村落的旅游吸引力至關重要(劉軍民 等,2017)。
2)打造傳統村落風貌。緊扣當地鄉村景觀的自然特點,如河流水系、農田、村落、地形地貌等,在保護村落格局與肌理的基礎上,結合當地的傳統習俗、生產生活方式、社會活動等人文因素,營建山水田居景觀,打造具有品味的鄉村公共空間,如休閑空間、閱讀空間、商業空間等,為村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活動場所。
3)挖掘多元價值,推動產業融合發展。農業是傳統村落發展的主線,是其全部生產生活的基礎。除了文化價值外,傳統村落天然地具備農耕生產價值和田園生態價值,共同構成傳統村落獨特的吸引力。因此,以農業為主導產業,結合小眾的文化體驗式鄉村旅游,推動農旅融合發展是適合傳統村落的發展方式。
4.4 融合發展模式
4.4.1 模式內涵及建設機制 融合發展模式是在優化配置自身資源要素的基礎上,依托城市及周邊村鎮資源,發揮城市帶動作用,實現村鎮聯動發展,促進農產品生產、生態保育、社會穩定等多種功能有機融合與協調發展的綜合發展模式(圖9)。該模式適合于周邊村鎮發展好、生態環境優美、自身具有一定資源基礎但資源特色不明顯的一般村,如長沙市蒲塘村。該類村莊的發展主要依靠城市和周邊村鎮發揮帶動作用,建立城鄉互動機制,實現融合發展。一方面通過“合作社+農戶”與“企業+合作社+農戶”的組織模式,盤活本村資源,培育可持續產業;另一方面,通過“上級政府+鄉鎮企業+農戶”的組織模式,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

圖9 蒲塘村的融合發展模式Fig.9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l of Putang Village
4.4.2 主要建設路徑 1)村鎮聯動,培育鄉村特色產業。構建村內、村外2個發展環,通過內外環之間的連接實現城鄉互動、村鎮聯動。外部由鎮政府組織協調,一方面鼓勵本鎮村莊發揮比較優勢,通過資源整合形成合力,培育特色產業,打造鎮域公共品牌;另一方面通過招商引資,引進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實現本鎮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內部由村干部、鄉村能人共同協作,成立家庭農場、合作社、龍頭企業等,通過土地流轉,引進新技術新品種并帶動村民參與,逐步壯大村莊產業,帶動農戶增收。
2)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建設美好家園。打造鄉村生活圈,優化配置養老、醫療、購物、教育等設施,加強青年人休閑娛樂購物等方面的服務供給、老年人友好與兒童友好空間的營造,提升鄉村公共服務品質,打造可持續的鄉村生活空間,逐步縮小城鄉公共服務供給差距;滿足村民日益提高的物質生活與精神需求,尤其是教育質量、醫療水平、養老服務以及休閑娛樂方面的需求,提高其生活滿意度,同時吸引外出就業人員回村發展。
5 結論與討論
1)本文界定了可持續鄉村的內涵和系統構成,具體指可以持續為本地鄉村居民提供優質的就業、居住、出行、醫療、教育、養老、交往等服務,也能不斷為周邊居民提供健康的農產品、良好的生態產品和文旅體驗的鄉村系統,包括可持續的農村產業、可持續的農村環境以及可持續的農民生活3個方面內容。
2)長沙市鄉村可持續發展存在以下共性問題:本地就業機會少,外出務工比例較高;鄉村人居環境建設品質不高,鄉村吸引力不明顯;鄉村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偏低,村民生活滿意度一般;鄉村留守主體老弱化,發展韌性不強;鄉村自治水平不高,內生動力不足。在個性特征方面存在以下問題:旅游型鄉村的旅游吸引力不強;農業型鄉村的帶農機制不足;傳統型鄉村的文化保護功能衰退;一般型鄉村的產業發展基礎薄弱。
3)針對長沙市鄉村可持續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在綜合考慮各類型鄉村自然及社會經濟條件的基礎上,提出4種適宜長沙市的可持續鄉村建設模式,即生態休閑旅游模式、高效生態農業模式、特色保護模式和融合發展模式。
4)針對不同模式的發展難點,提出相應的建設路徑。①生態休閑旅游模式需重點提升鄉土特色,增強鄉村旅游吸引力;優化運營模式,實現利益共享。②高效生態農業模式需加強農業生態化管控,逐步實現農業生態化和無害化生產;延伸生態農業產業鏈;應用智慧農業技術;實現小農戶生產與規模化生產相結合。③特色保護模式需重點保護傳統生活空間,增強旅游體驗感;打造傳統村落風貌;挖掘多元價值,推動產業融合發展。④融合發展模式需通過村鎮聯動,培育鄉村特色產業;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建設美好家園。
本文系統梳理了可持續鄉村的內涵與系統構成,并以系統構成中農民生活空間的八大要素為依據,對快速城市化地區長沙市鄉村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共性問題與個性特征進行深度剖析,以問題為導向,以可持續鄉村系統的三大核心內容農民生活、農村產業和農村環境為目標,提出了差異化的可持續鄉村優化模式與實施路徑。本文可為解決同類鄉村在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生態環境惡化、產業發展滯后、帶農機制不足、傳統文化衰退等不可持續問題提供思路,為有效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提供科學依據。但鄉村系統是動態演化的,同一類型鄉村在不同演化階段面臨的外部環境與內部問題具有差異性,未來需對同一類型鄉村的不同發展階段進行研究,結合特定鄉村所處的發展階段,分析其可持續轉型的動力機制,探索因時制宜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與路徑。
致謝:感謝馬恩樸老師和陳妍、王秋蘭、常晨曦、溫楚冰、劉燚、李秋泓、羅云、彭楚璇、嚴紫漪等同學在調研工作中給予的幫助和支持,感謝于雪霞在校稿工作中提出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