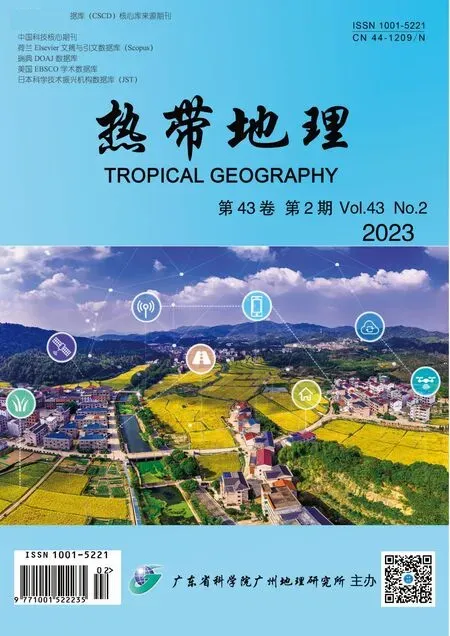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空間分布格局及影響因素
楊劉軍,朱戰強,b,c
(a.中山大學 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b.廣東省城市化與地理環境空間模擬重點實驗室;c.廣東省公共安全與災害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廣州 510275)
鄉村休閑旅游是促進農村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助力農民增收致富,振興農村經濟,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途徑(陸林 等,2019)。在鄉村產業振興與鄉村休閑體系融合發展的新形勢下,鄉村旅游正經歷由以旅游觀光為主轉變為以旅游休閑為主的多元化發展過程(趙霞 等,2013;胡世偉,2018)。鑒于游客日常休閑旅游中的觀光、體驗、回歸自然等多種需求正在從城市向郊區溢出,鄉村地區借助農業、景觀、人文資源基礎,以鄉土風情、田園生活為吸引,構建的集自然觀光和休閑娛樂等功能于一體的鄉村休閑旅游地,已成為促進城鄉居民消費的熱點區域之一。因此,在“發展鄉村休閑旅游,助推鄉村全面振興”的戰略布局下,系統研究鄉村休閑旅游地的空間格局及其影響因素,可為鄉村休閑旅游評價、資源配置和布局優化提供重要參考。
鄉村休閑旅游地是指包括旅游設施和服務以及鄉村旅游資源在內的旅游供給綜合體,同時也是鄉村旅游建設發展的重要組成和載體,其休閑旅游活動一般具有鄉村性的核心特征(張杰 等,2021)。鄉村休閑旅游地空間格局及分布規律研究一直是國內外關注的熱點。國外研究起步較早,研究視角多樣化,從以往的發展評價(Briedenhann, 2009)、發展趨勢(Ibanescu et al., 2016) 和游客體驗研究(Kastenholz et al., 2018),深入到促進區域多元化發展(Kyrylov et al., 2020)、發展模式演變(Jia et al.,2022)和游客感知影響(Soszyński et al., 2018)等方面。研究內容上從早期的旅游業對城鄉空間演變的影響機制探索(Davenport et al., 2006),逐漸發展到更加關注旅游地自身的地理空間結構(Sarrión-Gavilán et al., 2015),并注重鄉村休閑旅游行為與空間結構的關系。而國內研究在2000年前后才迅速增加,主要圍繞空間多尺度特征(胡美娟 等,2015a)、空間格局演變規律(殷章馨 等,2021)、空間格局影響機制(王鐵 等,2016)、空間結構優化(徐清,2009)等方面展開。研究尺度既涵蓋中宏觀層面的國家級(鄭光輝 等,2020)、省級(余瑞林 等,2018),也深入到微觀層面的市級(徐冬等,2018)、縣級(李濤 等,2021)等;研究方法逐漸從定性轉變為定量。如劉愛服(2005)探討了京郊空間鄉村旅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對策;沈剛(2007)基于生態系統視角,對鄉村旅游空間地域性進行研究;許峰等(2010)立足資源與環境約束,根據不同鄉村旅游地形態構建了穩健的多中心治理結構;李濤等(2014)引入鄉村旅游發展等級指數,對江蘇省鄉村旅游發展水平進行評價;劉大均等(2014)引入犯罪地理學的分析手段Ripley'sK函數,分析鄉村旅游點狀要素在不同空間尺度下呈現的集聚特征;王新越等(2016)利用最鄰近指數,分析鄉村旅游地的整體分布特征,并對其集聚的顯著性進行判斷;王秀偉等(2022)在空間格局的基礎上,使用地理探測器對造成重點旅游村空間分布的質異性因素進行探討,認為鄉村旅游地分布格局是多種因素共同驅動造成的。
總體上,國內外關于鄉村休閑旅游的研究內容豐富,角度多元,但仍有可拓展的空間。已有研究在方法上多集中在定性和單一的定量化分析層面,包括對鄉村休閑旅游地的評價與差異比較、發展動力與對策的探討等,缺乏結合地理學、計量學和經濟學等多種手段的定量化分析;同時,關于鄉村休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特征缺乏深入探索,對影響因素的研究涉入度較低,且多以單一定性分析為主,難以為戰略決策提供有力支持。從研究對象上看,對廣東省的關注度不足。因此,本文擬使用最鄰近指數,核密度分析以及Ripley'sK函數等方法,深入分析廣東省不同類型鄉村休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格局及其影響因素,并提出建議。以期為優化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資源配置和布局優化提供理論依據。
1 研究數據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廣東省境內陸地面積17.98萬km2,約占全國陸地面積的1.87%。優越的地理環境和豐富的嶺南文化使得廣東省休閑旅游資源數量及市場規模均排在全國前列,良好的旅游資源基礎也顯著地促進了鄉村休閑旅游產業的發展(圖1)。近年來,廣東省大力構建鄉村休閑產業體系,在空間維度上依托“四邊”,即“城邊、景邊、海邊、村邊”“三道”,包括“交通干道、綠道、南粵古驛道”“兩特”,即“少數民族特色居住區、古鎮古村特色村落”以及“一園——農產品加工旅游園區”進行建設發展。時間維度上充分利用農業生產季與農閑季進行合理的產品定制與產業規劃。總體上,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產業基礎堅實,業態類型豐富,具有一定的品牌效應。同時,全省各地大力打造鄉村振興示范帶,目前已累計建成廣州、佛山、茂名、汕尾等地的200 多條美麗鄉村風貌帶和570 條美麗鄉村精品線路,創建了10個全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

圖1 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空間分布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si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區)以及32個中國美麗休閑鄉村,有望在未來形成省域范圍內的大規模休閑產業集群。
1.2 研究方法
1)最鄰近指數 最近鄰分析用于描述空間上點的整體分布類型。首先計算實際最鄰近點對的平均距離與隨機分布模式中最鄰近點對的平均距離(李莉 等,2020),然后通過二者比值(NNI)判斷點的空間聚集性,計算公式為:式中:n為鄉村休閑旅游地數目;min(dij)為點i到j的最鄰近距離;A為整個研究區域面積。當NNI=1時,表示鄉村休閑旅游地呈隨機分布;當NNI>1時,表示呈均勻分布;當NNI<1 時,表示呈集聚分布。
2)變異系數 變異系數是概率分布離散程度的一個歸一化量度,其定義為標準差與平均值之比,用于檢驗空間分布類型。計算公式為:
式中:σ為鄉村旅游地Voronoi 多邊形面積的標準差;s表示Voronoi 多邊形面積的平均值。當CV<33%時,表示鄉村休閑旅游地呈均勻分布;33%<CV<64%時,表示隨機分布;當CV>64%時,表示集群分布。
3)核密度估計 核密度表示樣點空間分布的均衡度,本文用于衡量鄉村休閑旅游地空間分布及集聚狀況。計算公式為:
式中:f(x)為位置x處的密度計算函數;n為鄉村數量;x-xi表示估值鄉村點到區域Xi處的距離;h為寬帶(距離衰減閾值);k為空間權重函數。核密度值越大,表示鄉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越密集。
4)Ripley'sK函數 Ripley'sK函數可分析多尺度下點狀要素的空間集聚規模(胡美娟 等,2015b),本文運用Ripley'sK(r)函數分析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的空間集聚特征。計算公式為:
式中:K(r)表示鄉村休閑旅游地集聚程度;A表示研究區域面積;n表示點的數量;r表示空間尺度;Ir(uij)為變函數,uij表示點i、j之間的距離,當uij≤r時,Ir(uij)取1,當uij>r時,Ir(uij)取0;為保持方差穩定,構造L(t)函數,其模擬檢驗法所得最大值、最小值定義為上、下包絡線的數值。L(t)>0,且結果在上包絡線以上,表明鄉村休閑旅游地呈集聚分布;L(t)=0,結果處于上下包絡線之間,表明呈隨機分布;L(t)<0,結果處于下包絡線以下,表明呈均勻分布。
1.3 數據來源與處理
以涵蓋各類休閑旅游資源的鄉村為研究單元,鄉村點數據由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①http://whly.gd.gov.cn/發布,總數為650 個。該數據是為響應《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意見》工作安排,全面準確摸查全省鄉村休閑旅游資源現實狀況,從而對省內符合條件的鄉村進行組織評選形成。評選過程根據《廣東省鄉村旅游資源分類與評價標準》(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2022)進行,該標準以《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GB-GB/T 18972-2003)為基礎編制而成。因此,數據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
數據顯示,每個鄉村休閑旅游地所涵蓋的資源類型并不唯一,而是交叉融合了多種資源類型。因此部分鄉村休閑旅游地存在多重屬性,并產生多次計數的情況。結合廣東省實際情況,官方數據文件將其分為自然景觀類、民俗文化類、產業融合類、歷史遺存類、聚落建筑類5個主類和16個亞類。表1顯示,650個鄉村休閑旅游地中59.0%含有自然景觀類,而民俗文化類、產業融合類、歷史遺存類、聚落建筑類在整體鄉村休閑旅游地中的數量占比分別達到63.3%、57.0%、38.2%和72.4%。通過高德地圖地理編碼獲取所有鄉村點的經緯度坐標,并導入天地圖進行校準,形成不同類型鄉村休閑旅游地空間數據集。

表1 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分類統計Table 1 Statistics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si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此外,道路、水系、行政區劃數據來自國家自然資源部和廣東省自然資源廳,DEM數據來自地理空間數據云,經濟、人口數據來自《廣東統計年鑒-2020》(廣東省統計局,2020)及廣東統計信息網②http://stats.gd.gov.cn/,A級景區名錄來自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將所有數據導入ArcGIS 10.7建立平臺空間數據庫。
1.4 研究思路
在明確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分類體系的基礎上,對其空間分布格局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圖2)。首先,通過最鄰近指數判斷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在空間分布上是否存在集聚,在初步判斷旅游地的空間分布類型后,運用Voronoi 圖及變異系數法對鄉村休閑旅游地的總體空間分布特征進行驗證。由于最鄰近指數只能判斷旅游地是否存在集聚,并不能從空間上表明其集聚分布的方向特征與均衡度。因此借助核密度分析,定量計算均衡程度并對集聚程度進行等級劃分。其次,通過Ripley'sK函數對廣東省各類鄉村休閑旅游地分布進行空間多尺度格局分析。再次,構建影響因素體系結構,并綜合使用緩沖區分析、可達性分析、相關性分析以及基于距離衰減的影響值分析等探討各種指標對旅游地空間分布的影響程度。最后,對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發展規劃提出建議。

圖2 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空間分布格局及影響因素研究技術路線Fig.2 Technical rout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land in Guangdong Province
2 空間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
2.1 空間分布特征
2.1.1 空間集聚特征 由表2可知,在廣東省范圍內,整體鄉村休閑旅游地和各類鄉村休閑旅游地的最鄰近指數均<1,Z檢驗值<-2.58,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通過檢驗,表明其空間分布類型均屬于典型的集聚模式,特別是整體的鄉村休閑旅游地的NNI 為0.579,Z值得分為-20.51,即在整個研究區域內,整體較任何單一類型集聚更顯著。以旅游地為質心,對研究區域進行空間分割,測度Voronoi 多邊形的面積,以及面積均值和標準差。通過計算得到鄉村休閑旅游地泰森多邊形面積平均值為276.36 km2,標準差為329.68 km2,得到變異系數值為1.19,>0.64,屬于強變異類型,再次證明休閑旅游地在空間上呈顯著的集聚特征。

表2 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最近鄰分析結果Table 2 Results of 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si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2.1.2 空間分布均衡度 借助核密度分析(圖3),發現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空間分布不均衡,具體表現為“兩軸,多增長極”的分布模式。“兩條軸帶”第一條指汕尾—惠州—廣州—佛山—江門—中山—珠海沿線,基本與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相吻合;第二條分布在粵東、粵北的潮汕揭—梅州—韶關沿線,具有沿邊集聚的分布特征。“增長極”主要分布在清遠北部和云浮境內,并形成2個中高密度值和1個高密度值集聚中心。此外,對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空間自相關性進行分析,得到鄉村休閑旅游地的全局Moran'sI指數為0.806,且在α=0.01的顯著性水平通過檢驗,表明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的分布在整體上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即各鄉村休閑旅游地與周邊鄰域鄉村旅游地存在明顯的空間依賴。

圖3 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核密度分析Fig.3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si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2.1.3 空間格局多尺度特征 通過Ripley'sK函數對整體以及各類鄉村休閑旅游地分布進行空間多尺度格局分析(圖4),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空間的L(t)均>0,且曲線位于上包絡線之上,表明各類及整體鄉村休閑旅游地在空間上呈集聚分布,且集聚效果顯著,從另一個角度驗證最近鄰分析結果。另外,從L(t)函數曲線的變化趨勢看,各類以及整體的鄉村休閑旅游地均呈現先增后減趨勢。其中,整體鄉村休閑旅游地特征空間尺度為118.36 km,即在0~118.36 km 范圍內,L(t)曲線隨著空間尺度的增大逐漸遠離置信區間,集聚強度不斷增大,在118.36 km 處達到峰值,之后集聚強度隨著空間尺度的增大而不斷減小。
5 種類型鄉村休閑旅游地中,歷史遺存類鄉村休閑旅游地達到峰值的空間距離最大,為120.24 km,說明在較大的空間尺度內表現為較強的集聚性,區位布局的空間范圍最大。民俗文化類和聚落建筑類鄉村休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格局較為接近,兩者的特征空間尺度分別為118.08 和109.80 km,且前者的集聚強度高于后者。自然景觀類與產業融合類達到峰值的空間尺度小于其他類型,分別僅為72.12和85.31 km,這兩者受自身數量以及資源稟賦等因素的制約,區位布局的空間范圍相對較小。
2.2 空間特征的影響因素
2.2.1 影響因素體系構建 鄉村休閑旅游發展受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按照因素的來源可分為內部動力和外部動力(段兆雯,2012;陳志軍 等,2019),內部動力主要來自休閑旅游市場的供給、需求以及對于市場秩序的管理維護;外部動力主要包括政策扶持、政府宏觀調控以及生產要素的動態更新等。內、外部要素之間的耦合作用共同促進鄉村休閑旅游的發展,其中供給提供拉力,需求提供市場推力,政府管理增強支持因素,彌補市場缺陷,為鄉村休閑旅游發展提供重要拉力,創新為產品、服務、市場、制度理念、產業體系等注入活力,成為鄉村休閑旅游轉型升級以及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動力。結合已有研究(韓非 等,2010;張明星 等,2011;李志龍,2019)以及廣東省的實際情況,嘗試從“供給、需求、管理、創新”4 個角度構建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格局形成的影響因素體系結構(圖5)。

圖5 鄉村休閑旅游影響因素體系結構Fig.5 System structur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1)供給層面:旅游吸引物是鄉村休閑旅游的核心屬性,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主要包含自然景觀、聚落建筑、歷史遺存、民俗文化活動等類型的旅游資源。區位條件是客源地與旅游地之間連接的關鍵屬性,良好的交通與資源區位能有力地推動鄉村旅游業的發展。此外,豐富的旅游產品以及良好的旅游接待服務體系也是提高鄉村休閑旅游地吸引力的重要屬性。
2)需求層面:作為推動鄉村休閑旅游發展的基本動力,供給與需求相互影響。需求動力源于需求的持續增加,一方面,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以及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們有了更高層面的精神消費需求;另一方面,為滿足旅游客源在不同市場環境中的不同需求,旅游地定位與分布格局也會不斷進行調整,從而滿足客源市場的多樣性需求。
3)管理層面:政策法規從宏觀上把控鄉村休閑旅游的發展。旅游季、旅博會等重大事件可以改變旅游地的區位條件以及影響度,從而調節鄉村休閑旅游的空間分布。綜合需求與供給,對資源地進行規劃開發,能夠增強核心資源和吸引物的吸引力,增強支持因素和資源的質量以及有效性,為鄉村休閑旅游地整體發展提供重要保障。
4)創新層面:創新驅動鄉村休閑旅游的轉型與升級。創新的實質是供給、需求、管理層面的更新發展。產品創新將使鄉村休閑旅游資源更加優質多元且更具吸引力;業態創新將促進鄉村休閑旅游融合發展,挖掘鄉村多重價值;以滿足不同人群的體驗需求進行創新可有效保障休閑旅游的高質量發展;而體制機制、管理上的創新對于提升鄉村旅游宣傳營銷方式,優化旅游地發展格局至關重要。
2.2.2 影響因素分析 從可操作性及數據的可獲取性出發,重點選取供給層面的資源稟賦、交通可達、景區輻射,以及需求層面的人口經濟、客源市場指標對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空間分布格局的形成進行定量分析,并結合政策管理、創新發展2個維度進行定性解釋。
1)資源稟賦 地形、水系、用地等自然生態因素是構成鄉村休閑旅游景觀格局的初始條件,也制約著空間布局、規模、密度和擴張態勢(高蘋 等,2017)。優良的自然生態環境吸引各種類型的休閑旅游地不斷向其聚集,并逐漸形成一定規模的集聚區。
廣東省地貌類型復雜多樣,有山地、丘陵、臺地和平原。通過將高程值提取至鄉村休閑旅游地,并作分類統計(圖6-a),得出旅游地高程最高值為1 053 m,其中200 m 范圍內旅游地數量為527 個,占總數的81.1%;200~400 m內旅游地數量為84個,占總數的12.9%;400 m以上旅游地數量大幅減少,僅占總數的6.0%。兩者的相關系數r=-0.680,在P=0.01 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鄉村休閑旅游地高程與數量之間具有一定的負相關性。由此可以得出,良好的地形地貌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鄉村休閑旅游地的分布。

圖6 鄉村休閑旅游地分布與海拔關系(a)與水系緩沖區關系(b)Fig.6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creation and tourism sites in relation to elevation (a) and buffer zone of water system (b)
廣東省河流眾多,以珠江流域、寒江流域、粵東沿海及粵西沿海諸河為主,集水面積占全省面積的99.8%。通過最近鄰分析得出,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與水系的平均最鄰近距離為919 m,該半徑下緩沖區內的旅游地數量為420 個,占總數的64.6%。不同緩沖區半徑與旅游地數量關系曲線(圖6-b)所示,兩者的相關系數r=-0.864,并在P=0.01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兩者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水系是決定鄉村休閑旅游地分布的重要因素。
在用地上,水田、旱地、有林地和疏林地是鄉村休閑旅游的主要分布區域(圖7),4種用地類型上分布的鄉村休閑旅游地數量占比達到77.5%(圖8)。近年來,隨著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的快速發展,土地流轉進程加快,土地利用功能更加多元,部分農業種植用地開始改變利用方式,發展為具有觀光、體驗、娛樂功能的鄉村休閑旅游地,使得耕地、林地以及建設用地成為誘發鄉村休閑旅游集聚的重要因素。

圖7 廣東省土地利用類型Fig.7 Land use typ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圖8 鄉村休閑旅游地與用地類型耦合曲線Fig.8 Coupling curve between rural leisure tourism land and land use type
此外,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也極大地促進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的布局發展。首先,從鄉村休閑旅游地的類型及數量占比看,5 種類型的鄉村休閑旅游地中聚落建筑類和民俗文化類鄉村占比最多,分別達到72.4%和63.3%,另外有38.2%的鄉村休閑旅游地擁有豐富的歷史遺存資源。其次,從整體的空間布局看,珠三角、潮汕揭、梅州和韶關作為廣府、潮汕、客家三大嶺南文化的代表性地區,同時也是整個廣東省內鄉村休閑旅游最為集聚的地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歷史文化資源是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吸引物的關鍵因素,也是影響其布局發展的重要因素。
2)交通可達性 鄉村休閑旅游地多分布在大城市周邊幾十甚至上百公里的范圍內,與多乘坐飛機、火車等的出行工具前往大型旅游景點的方式不同,鄉村休閑旅游更偏向于選擇自駕前往,因而公路系統成為易達性的主要決定性因素。基于此,主要選取鐵路、高速、國道、省道、縣道為對象分析交通的可達性程度。根據現有研究(李巍 等,2014),將上述道路速度分別設定為200、100、60、50、30 km/h,以區域內任意點到最近旅游地所需要的時間對鄉村休閑旅游地的可達性進行分析(圖9),并計算廣東省道路密度(圖10)。

圖9 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交通可達性分析Fig.9 Analysis of traffic accessibility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pla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圖10 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道路密度Fig.10 Road density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si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可達性在1和2 h的區域分別占34%和67%,可達性在3 h 以內的區域高達85%,可以看出廣東省整體的鄉村休閑旅游地可達性較高,說明交通可達性是影響鄉村休閑旅游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通過分析各種類型鄉村休閑旅游地與廣東省道路密度的關系可以發現,自然景觀類中43.9%的鄉村休閑旅游地位于道路密度>3 km/km2的較高密度區域;民俗文化類、產業融合類分別為48.8%和43.5%;聚落建筑類對道路的依附性最強,占比達到58.7%;歷史遺存類占比最小,為29.1%,說明交通對歷史遺存類鄉村休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影響最小。
3)景區輻射 廣東省共有559 個2A 級以上景區,其中5A、4A、3A 和2A 級景區分別為15、192、340 和12 個。已有研究(盤瑤麗,2016)表明,某些位于景區周邊的鄉村休閑旅游地可依托現有景區的游客資源,并與所依托的景區形成互補式發展。即周圍景點對鄉村休閑旅游產生集聚效應,一般為距景點越近以及景點等級越高則其開發成功的潛力越大。根據廣東省現有2A 級以上景點空間分布及現狀景源等級表示對鄉村休閑旅游地分布的影響程度(徐曉偉 等,2012)。5A、4A、3A、2A級景點分別作為1~4 級影響因素,參考相關研究(王明正,2019),確定定級因素的作用半徑分別為5、4、3、2 km。根據歐式距離下,實際距離與最大距離的比值確定不同級別的衰減系數,并計算對應的影響分度值,最終將結果疊加得到基于距離衰減的總影響分值(圖11)。

圖11 廣東省A級景點距離衰減影響分值Fig.11 Distance attenuation impact score of A-class attrac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提取650個鄉村休閑旅游地的景區輻射影響分度值,按照等間距劃分為5個等級,分值越大,級別越高。從表3 可以看出,隨著距景點距離的增大,輻射影響分值逐漸降低,鄉村旅游地數量整體也呈現下降趨勢,表明廣東省現有A 級景點對鄉村休閑旅游地產生集聚影響,且集聚效應隨著距離增大逐漸減小。但鄉村數量并不是隨著影響分值呈線性減少,而是在衰減過程中出現一個峰值。分析其深層次原因發現,在輻射影響分值最強的區域內,現有景點分布密集且級別較高,此區域距離城市較近,基礎設施覆蓋完善且已形成成熟的旅游休閑體系,人們更傾向于選擇此類景源滿足日常休閑旅游需求,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鄉村休閑旅游的發展。因此,依托現有景點發展的鄉村休閑旅游地應結合實際情況選擇適宜的輻射范圍進行布局規劃。

表3 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景區輻射影響分值統計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radiation impact score of scenic spots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in Guangdong Province
4)客源市場 鄉村休閑旅游的客源主要來自于周邊城鎮(朱中原 等,2020)。而“環城游憩帶”理論認為,城市居民游憩活動空間會呈距離衰減式擴散(吳必虎,2001),因此以更小尺度的廣東省1 138 個鎮為客源提供對象,分析客源市場對鄉村休閑旅游地空間分布特征的影響。通過最近鄰分析發現,廣東省建制鎮與鄉村休閑旅游地之間的距離最小為134 m,最大為42 065 m,平均值為10 609 m。因此結合廣東省實際情況,以建制鎮為中心點,5 km 為緩沖半徑進行多環緩沖分析,形成0~5、5~10、10~15、15~20、>20 km 的同心圓游憩緩沖區間,得到回轉半徑(表4)。

表4 廣東省各類鄉村休閑旅游地回轉半徑統計Table 4 Turning radius statistics of various rural leisure tourism si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統計結果表明,隨著緩沖半徑的增大,各類鄉村休閑旅游地數量均逐步減少,且在建制鎮15 km范圍外幾乎為0。分布規律較為統一,在0~5 km內分布最為密集,且均占各自類型總數的60%左右,其中聚落建筑類對城鎮的依托最為顯著,占比達到該類型總數的67%;5~10 km 范圍內數量占比均為30%左右;10~15 km范圍內均不超過10%。可以看出,無論是整體還是各種類型的鄉村休閑旅游地,均對城鎮的依托作用明顯,在空間分布上表現出以鄰近城鎮為中心的空間距離衰減規律,即距離主要客源市場越遠,鄉村休閑旅游地的生存基礎越差。
5)人口經濟 在縣(區)級尺度上對廣東省2020 年人均GDP 進行統計,發現人均GDP 在0~3萬、3萬~6萬、6萬~9萬、>9萬元的鄉村休閑旅游地數量分別占17.6%、46.1%、23.7%、12.6%,可以看出,大多數鄉村休閑旅游地人均GDP較高,但人均GDP與旅游地空間分布數量的關聯程度一般,屬于影響空間分布的次級因素。經濟發展水平支持鄉村休閑旅游的發展,而消費需求是產業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隨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消費水平和旅游需求也不斷提高,從而形成一種正向反饋刺激旅游業不斷發展。因此,良好的經濟基礎,是鄉村休閑旅游轉型升級的巨大市場推動力。其次,人口是產業的基礎,也是助力產業振興發展的關鍵,人口密度水平能體現鄉村地區休閑旅游市場的規模和需求水平(李濤 等,2020)。隨著現有鄉村休閑旅游地輻射區內人口密度不斷增大,休閑旅游地的數量也隨之增加,并逐漸形成一定的集聚規模。
6)政策管理 2002年廣東省政府設立旅游扶貧專項資金,通過發展鄉村旅游推動扶貧工作。此后,省政府發布相關文件,如《關于試行廣東省國民旅游休閑計劃的若干意見》(粵府 [2009] 19 號)提出開始重點支持發展和完善一批鄉村旅游與休閑農業項目。《廣東省鄉村旅游與休閑農業發展規劃》(2013—2020 年)開啟了對鄉村休閑旅游的全面布局以及重點工程建設項目,提出力爭在10年內,將鄉村旅游和休閑農業打造成為廣東省鄉村的新興產業。目前已打造了三批“美麗鄉村”項目和“廣東省鄉村旅游精品線路”,形成諸多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鎮,并開始著手提升打造一批鄉村旅游示范項目,深度挖掘鄉村休閑旅游資源,促進鄉村休閑旅游全方位開發。此外,相關重大事件包括2018年廣東旅博會,梅州、云浮鄉村旅游季活動以及廣東省“互聯網+鄉村旅游”高峰論壇等,通過全面展示鄉村旅游資源和建設成果,極大地提高了鄉村旅游地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對當地鄉村旅游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7)創新發展 創新是關于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旅游的創新包括產品創新、過程創新、管理創新、市場創新和制度創新(Hjalager, 2010)。對于鄉村休閑旅游,創新發展實際也是供給、需求、管理3個層面的創新。首先,廣東省鄉村旅游為豐富供給,著力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韻”模式。充分利用農村、農業和鄉村文化資源,融合多個景點形成鄉村旅游精品路線,既充分發掘和利用鄉村旅游產品,又拓寬鄉村休閑旅游業態體系。各地還通過組織從業人員進行鄉村旅游培訓,不斷增強其服務品質,提升游客體驗感受。
其次,面對客源市場的不同需求,廣東省將鄉村旅游作為休閑度假旅游產品的重要載體,打造部分面向中高消費群體的鄉村休閑旅游地,以此有效地激發鄉村旅游的創新能力與發展活力,為進一步推進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提供有效保障。
此外,在管理層面上也開始轉變營銷理念與策略,選擇以鄉村豐富的資源為載體,營造具有鄉村特色的旅游體驗,以獨具回味的感受吸引消費者,致力于以體驗為導向發展鄉村旅游。而在產業體系建設方面,通過一產轉型升級、二產提質增效、三產爭創品牌,積極推進鄉村旅游業與三產融合發展,力爭將廣東省鄉村休閑產業打造成千億規模的經濟產業集群。在政策支持下,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的內核不斷更新,從“十二五”的發展“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轉變為“十四五”的推進“鄉村休閑”產業建設,更加符合新時代背景下的發展要求。
3 討論
通過ArcGIS 空間分析發現,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主要表現為空間集聚化與資源類型差異化的特征。“兩條軸帶”中第一條沿粵港澳大灣區環形分布,軸帶內鄉村休閑旅游地數量上以聚落建筑類和產業融合類為主導。粵港澳大灣區依托深厚的水鄉文化底蘊及民俗風物,形成眾多融合觀光、康養、體驗、休閑等多種產業的都市農業綜合體,完善的產業體系結構不斷促進鄉村休閑旅游地的集聚;同時,該地區地勢平坦,平原面積廣闊,因此鄉村休閑旅游地廣泛、均勻分布,全域覆蓋能更好地滿足較大的客源市場與休閑需求;此外,發達的交通體系和巨大的客源市場則在區位方面決定大灣區鄉村休閑旅游地軸帶式集聚分布的形成。
而“潮汕揭—梅州—韶關”組成的第二條軸帶地形以山地為主,鄉村集中分布在地勢平坦開闊的地區,因此造成休閑旅游地主要以單核或多核集聚,且集聚效果更加顯著。此外,近年來粵東、粵北大力發展鄉村休閑產業,粵東沿海地區以休閑漁業、濱海風情以及潮汕傳統村落聯動發展;粵北地區則建立了多處生態發展區,休閑產業生態化與農業生態化同步發展,并依托客家文化和少數民族風情全力打造粵北生態旅游圈,新增了大批鄉村休閑旅游開發資源。同時,粵東、粵北地區因毗鄰閩、贛兩省,客源市場較為廣闊,除部分游客來自珠三角城市外,也會吸引鄰近省份的游客,因此,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沿邊分布的鄉村休閑旅游集聚軸帶。
“增長極”主要位于云浮市境內及清遠北部地區。云浮鄉村休閑旅游資源豐富,同時處在連接西部省份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樞紐位置,擁有便捷的交通體系,良好的客源市場與消費需求進一步促進云浮成為鄉村休閑旅游集聚地。而從整體上看,云浮東、西部形成2個增長極中心,西部地形以盆地為主,面積較為廣闊,為田園綜合體等融合產業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并與豐富的民俗文化共同構成鄉村休閑旅游的主導產業;東部地形多為丘陵山地,受此限制,集聚于東部的鄉村休閑旅游地在旅游產業結構上更加依托于自然景觀與聚落建筑。2 個增長極的發展各有側重,并不斷向外擴散,共同組成云浮市全域鄉村休閑旅游格局。清遠市北部連州市形成另一個增長極中心,清遠北部毗鄰湖南和廣西,境內京港澳高速全面貫通,擁有廣闊的客源市場。同時,清遠素來有“珠三角后花園”之稱,北部地區環繞多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及國家森林公園,自然環境優越。此外,清遠北部地區歷史悠久,瑤寨民族風情濃厚。豐富的民俗文化、獨特的自然景觀及便利的交通體系共同促成該地區鄉村休閑旅游增長極的形成。
實際上,空間分布的集聚性與不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能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馬斌斌等,2020;呂麗 等,2022)。鄉村休閑旅游空間集聚分布,首先可通過集合土地、資金、資源、技術等要素優勢,節約生產成本,以此不斷完善基礎服務設施、提升服務品質。同時,對于擴大區域休閑旅游的品牌效應,實現鄉村產業振興具有實踐意義。其次,可利用核心聚集區的擴散效應,不斷擴大產業規模與輻射范圍,推進鄉村休閑旅游的全域化發展。基于此,對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發展提出幾點建議:
1)進一步優化空間規劃與布局,推動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均衡全面發展。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分布的集聚性較強,因此,首先應重點考慮在休閑旅游地分布稀疏、集中化程度不高的粵西、粵西北地區,加大資源開發和投入力度,提升產業集中度,促進區域相對平衡發展。其次,深入挖掘地方特色。大灣區歷史文化悠久,民俗活動豐富多樣,并且擁有眾多體系完善的休閑農業綜合體,粵東地區依托民俗文化、歷史遺存資源,粵北則憑借豐富的生態旅游資源與民俗風情成為省內主要的鄉村休閑旅游聚集地。粵西地區具有豐富的濱海漁業、山水田園風光以及眾多人文古色,應充分利用良好的山水生態文化以及資源優勢,進一步挖掘粵西自然景觀和產業融合類型資源的潛力,將自然生態景觀與歷史人文風貌有機融合,全力打造一批集觀賞性、體驗性、生態性于一體的新型鄉村休閑旅游地。
2)對于鄉村休閑旅游欠發達地區,首先應完善旅游交通系統。不僅要推進道路干線連接景區建設,還要積極完善各區域至周邊省域的交通網絡系統,有效提升各景點之間以及景點與客源地之間的交通可達性。同時,借助現有高星級景區輻射作用不斷加強鄉村休閑旅游地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提升服務品質,努力擴大知名度,突出品牌效應,吸引周邊城市及省域游客,穩定鄉村休閑旅游客源市場,從而有效提高鄉村休閑旅游發展水平。
3)對于鄉村休閑旅游較發達地區,首先可考慮進一步擴大產業規模、提升品質,持續增強示范帶動能力,推動鄉村休閑旅游高效集聚發展。其次依托中心城市,加強一體化的制度建設與政策供給,通過合理布局產業經濟、資源配置,從而實現城鄉休閑旅游一體化發展,形成居民共享城鄉雙空間的現代生活模式。同時,提供更多鄉村休閑工作崗位,減少鄉村人員外流,保證鄉村休閑旅游地充足的人口及服務供給,促進其轉型升級并保持高效持續發展。
4 結論
本文立足于“發展鄉村旅游,助力鄉村振興”的美好愿景,系統研究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格局及其影響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廣東省5種類型鄉村休閑旅游地在空間分布上均呈現顯著的集聚特征,整體表現為“兩條軸帶,多個增長極”的分布模式。在沿邊、沿海分布的基礎上,依核密度值的高低分級分布,且形成相對獨立的單核或雙核聚集點。同時,鄉村休閑旅游地具有顯著的空間自相關性。
2)廣東省各類鄉村休閑旅游地在不同空間尺度下的集聚特征均表現為先增大后減小,且存在一定的空間差異性。歷史遺存類分布的區域范圍最大;民俗文化類和聚落建筑類較為接近,但集聚強度前者高于后者;自然景觀類和產業融合類對資源的依賴性較強,空間分布的范圍最小。
3)資源稟賦為鄉村休閑旅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基礎,且更適宜在地形平坦、鄰近水源的耕地、林地等地區發展;交通可達是旅游地發展的重要基礎,各種休閑旅游地對良好的交通體系都具有較強的依賴性;景區對鄉村休閑旅游地具有集聚性,并逐漸形成依托現有景點發展的模式,但同時也需注意,此類鄉村休閑旅游地應結合實際情況選擇適宜的輻射范圍進行布局規劃;客源市場作為鄉村休閑旅游發展的生存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空間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表現為距離客源市場越遠,鄉村休閑旅游的生存基礎越差;良好的人口經濟基礎,為當地鄉村休閑旅游的發展提供更有利的支持性因素,是形成鄉村休閑旅游市場的巨大推動力;而宏觀上政策的調控為廣東省鄉村休閑旅游的發展提供重要保障。
本文從不同空間尺度下對鄉村休閑旅游地空間格局、結構類型的剖析有助于揭示鄉村休閑旅游地的空間分布規律和特征,為深入研究其空間演化奠定基礎;同時本文創新性地構建了基于“供給、需求、管理、創新”4 個維度的影響因素體系結構,并詳細論述了4個維度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可為全面細致探討鄉村休閑旅游地空間分布的影響因素提供基礎架構;此外,省級范圍的鄉村休閑旅游空間特征研究對更好認識和分析區域鄉村休閑旅游發展布局、規模及開發重點,幫助農村落后地區加快發展、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具有實際指導意義。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在數據選取方面,首次使用點狀鄉村旅游地作為研究對象,但未考慮鄉村旅游地中各種類型休閑旅游資源的體量,對于體量較大的面狀自然游憩空間的分析多停留在定性層面;此外,鄉村休閑旅游地空間分布格局的形成是“供給、需求、管理、創新”4 個維度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本文重點從供給與需求維度的資源稟賦、交通可達、空間集聚等方面展開,受限于鄉村社會經濟數據難以獲取以及“管理、創新”維度的因素難以量化表達,因此缺乏相關層面的指標影響分析。在后續研究中須進一步從2個方面展開。首先,從游客視角及當地居民視角開展實地調研,對比已有的供給、需求端相關分析,對鄉村休閑旅游理論與實踐進行豐富論證;其次,結合遙感、POI、手機信令、出行軌跡等多源時空大數據,進行空間格局的時間序列及動態演化分析,從而深化鄉村休閑旅游空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