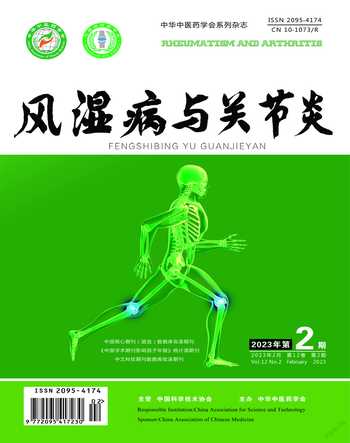晝夜節律的中醫認識及在痹病防治中的指導作用
劉佳妮 陳世賢 張丁丁 李娟
【摘 要】 通過總結中醫理論中諸多有關晝夜節律的理論,探討中醫天人相應、因時制宜觀點對現代痹病防治的啟示,歸納總結出隨陰陽消長顧護陽氣、五臟各主其時補益臟腑、隨晝夜變化分時服藥、結合子午流注進行時間治療等可應用于臨床實踐中的指導思想,以期中醫晝夜節律理論能夠在中西醫結合防治痹病中得到更廣泛的應用。
【關鍵詞】 痹病;晝夜節律;天人相應;因時制宜;中醫理論;防治
痹病是以肢體筋骨、關節、肌肉等處發生疼痛、酸楚、重著、麻木等異常感覺,或關節屈伸不利、活動僵硬,甚至腫大、變形為主要表現的病證。西醫學中的痛風、類風濕關節炎、強直性脊柱炎、骨關節炎等均屬“痹病”范疇。近年來,隨著學者們對人體晝夜節律的不斷探索,發現多種疾病的發生、病情變化均與此密切相關。早在《黃帝內經》《丹溪心法》等古籍中就有對疾病發生、發展與人體晝夜節律變化關系的相關闡述。筆者通過總結中醫典籍中晝夜節律及痹病的相關理論,結合痹病的臨床表現,分析探討中醫晝夜節律理論對痹病防治的指導作用。
1 晝夜節律的中醫認識
晝夜節律是指生物以24 h左右為周期進行的生命活動的變動,這是生物為了能夠適應自然環境中的晝夜變化而建立起的自身生理機能的規律周期[1]。早在《黃帝內經》時期,“天人相應”等理論已系統闡述了關于人體生命活動與大自然晝夜變化的聯系,從陰陽消長、營衛之氣運行、陰陽蹺脈循行、正邪盛衰、五臟主時等角度對晝夜節律有多方面的認識和理解,從中延伸出的子午流注理論也是中醫學對晝夜節律認識的獨特理論。
1.1 陰陽消長與晝夜節律 《靈樞·邪客》曰:“天有晝夜,人有臥起……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表明早在《黃帝內經》時期,古人就認識到人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性,提出中醫“天人相應”“天人合一”的觀點。《靈樞·衛氣行》曰:“陽主晝,陰主夜。”《素問·金匱真言論篇》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古人根據自然界光線、溫度等自然因素的變化規律,將其用“陰”“陽”二字概括為2種相對的范疇,中醫也將人體內的生理活動用“陰”“陽”來表達,認為人體內的陰陽消長變化如同自然界一般,表現出陽氣日長夜消的特點。《靈樞·寒熱病》曰:“足太陽有通項入于腦者……入腦乃別陰蹺、陽蹺,陰陽相交,陽入于陰,陰出陽,交于目銳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現代研究表明,生物鐘是調控晝夜節律的物質基礎,其分子基礎是由正向調控基因Bmal1、Clock和負向調控基因Period(Per1,Per2,Per3)、Cryptochrome(Cry1,Cry2)組成的轉錄-翻譯反饋環路[2],這種正負調節反饋正是中醫陰陽平衡理論的現代內涵。現代研究認為,哺乳動物位于下丘腦的視交叉上核(SCN)將內源性晝夜節律系統和外界的光-暗周期耦合起來,通過以光為主的授時因子引導生物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節律[3-6]。
1.2 正邪盛衰與晝夜節律 《素問·刺法論篇》曰:“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素問·評熱病論篇》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中醫學認為,疾病的發生是人體內正氣與邪氣互相交爭的結果。順應天地晝夜節律變化的不止是人體正常的生理活動,還有致病之邪氣。《靈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曰:“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臟,邪氣獨居于身,故甚也。”此則條文表明,在一日之中,人體的正氣與邪氣均是隨著時間消長變化的,白天正氣漸盛邪氣漸衰,至正午時分正氣最為充盛,能夠克制邪氣,病勢平穩患者安寧,傍晚正氣漸衰邪氣漸盛,至夜半時分人體正氣閉藏于內,邪氣占據形體,則表現為夜半至晨間病情更加嚴重,即疾病具有“旦慧、晝安、夕加、夜甚”的晝夜變化趨勢。例如哮喘多在夜間發病或加重,具有明顯的晝夜節律[7]。脾腎陽虛之晨瀉(五更瀉)晝夜節律也較明顯。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關節疼痛、僵硬、功能障礙等癥狀表現出明顯的晝夜節律特點,研究發現,與患者體內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6(IL-6)水平于6:00~7:00達到峰值,皮質醇的分泌相對不足,難以控制炎癥的晝夜節律關系密切[8-9]。類風濕關節炎及五更瀉的臨床表現雖與“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不完全吻合,但其晝夜節律較為明顯。筆者認為,依據不同疾病、不同晝夜節律進行深入的研究對于推動中醫理論的現代化,揭示疾病的發病機制,指導臨床治療均具有重要意義。
1.3 營衛運行與晝夜節律 柔和精專,營養周身之營氣,剽悍滑利,護衛御邪之衛氣,皆有晝夜節律。《靈樞·營衛生會》曰:“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于陰二十五度,行于陽二十五度,分為晝夜,故氣至陽而起,至陰而止。”人體晝夜節律中最重要的睡眠部分與衛氣運行息息相關,平旦,衛氣出于體表,由陰出于陽,故人寤,入夜,衛氣由陽入陰,故人寐。若營陰不能濡養衛陽,衛氣運行失常,衛氣行于陽而不能入陰,則會導致“不得臥”“目不瞑”等睡眠障礙。現代生物鐘研究提示,人體根據環境中亮-暗周期信號調整松果體分泌的褪黑素水平,以起到促進睡眠的作用,褪黑素缺乏會導致失眠及其他疾病的產生[4]。
1.4 五臟主時與晝夜節律 藏象學說是以心、肝、脾、肺、腎五臟為中心,研究人體生理功能、病理變化、相互關系的理論,是中醫學理論體系的核心。《靈樞·陰陽系日月》曰:“心為陽中之太陽,肺為陽中之少陰,肝為陰中之少陽,脾為陰中之至陰,腎為陰中之太陰。”五臟根據其所處位置、對應的五行及生理功能,進行陰陽屬性的劃分,與各臟在晝夜節律中的病理變化有關聯。《素問·藏氣法時論篇》曰:“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靜;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據此可推斷五臟各主其時:肝主平旦、心主日中、脾主日昳、肺主下晡、腎主夜半[10]。臨床研究發現,各類心律失常發作的高峰時段為23:00~次日1:00[11],腎絞痛以7:00~9:00發病率最高[12-13],小兒肺炎咳嗽則多發于19:00~21:00及5:00~7:00[14-15],雖未能與《黃帝內經》中闡述的發病節律一一對應,但仍可證明疾病發作和緩解時間可因病變臟腑而異。這為中醫在臟腑辨證的基礎上,遵循五臟系統的晝夜節律變化進行病因病機分析及擇時用藥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
1.5 子午流注與晝夜節律 子午流注學說以“天人合一,天人相應”的整體觀為理論基礎,是中醫理論中對晝夜節律劃分最為嚴格的一種,其認為人體十二經脈的氣血流注據一日之中的晝夜節律呈現出有規律的盛衰變化,將一日之中的24 h對應中國古代以十二地支命名的十二時辰,從23:00開始,每2小時為1個時辰,分別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別對應膽經、肝經、肺經、大腸經、胃經、脾經、心經、小腸經、膀胱經、腎經、心包經、三焦經。子午流注,簡單的說,即以子午言時間,以流注喻氣血,表示人體陰陽盛衰、營衛運行、經脈流注、時穴開闔均與自然界同樣具有節律變化。此理論廣泛應用于指導針灸、辨證、用藥和養生等方面,臨床上多應用于針灸治療中,依據不同時辰選取不同經絡上的相應穴位進行開穴治病[16]。
2 痹病的中醫學認識
痹病的病變部位可累及周身之經脈、關節、肌肉、筋骨。自古以來,歷代醫家對痹病的研究頗多,如《素問·痹論篇》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中藏經·論肉痹》曰:“肉痹者,飲食不節,膏粱肥美之所為也。”《濟生方·痹》曰:“皆因體虛,腠理空疏,受風寒濕氣而成痹也。”痹病之致病因素既有內因,又有外因,外感風、寒、濕、熱等邪氣為痹病發生的外在條件,先天稟賦不足、正氣虛弱,導致筋骨失養、衛外不固,是痹病發生的內在基礎[17]。素體虧虛,氣血虛弱,衛氣不固,則易外感風、寒、濕、熱等邪氣,或飲食不節,體內蘊痰,痰瘀互結,阻滯經絡,或年老久病,肝腎不足,肢體筋脈失養。主要病機為風、寒、濕、熱、痰、瘀、虛等相互轉化,引起經脈痹阻,氣血運行不暢,發為痹病。痹病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之痹病即外痹,是指以肢體筋骨、關節、肌肉等處發生疼痛、重著、酸楚、麻木,或關節屈伸不利、僵硬、腫大、變形等癥狀的一類疾病;廣義之痹病包含外痹與內痹,內痹常由外痹傳變而來,是指病位在臟腑的一類痹病。早在《黃帝內經》中便有“五體痹”“五臟痹”的論述,其臨床表現復雜,與西醫學中的結締組織病如類風濕關節炎、系統性紅斑狼瘡、干燥綜合征、血管炎等出現多臟器、多系統損害時的臨床表現非常相似[17]。
3 晝夜節律對痹病防治的指導作用
“天人相應”“因時制宜”等理論可用于指導臨床治療,即根據時間變化的特點,結合臨床癥狀的發生規律制定出適宜的治療原則。基于以上中醫理論對晝夜節律及痹病的認識,筆者認為,結合晝夜節律,對痹病的防治有以下指導作用。
3.1 護正御邪,補益陽氣 《丹溪心法·痛風》曰:“晝靜而夜發,發時徹骨酸痛,痛有常處,其痛處赤腫灼熱。”記載了痛風夜間發作,疼痛劇烈的特點,與西醫學中的急性痛風性關節炎多在午夜或清晨起病相似[18]。痹病多由風寒濕邪氣導致,風為陽邪,易襲陽位,寒、濕為陰邪,易傷陽氣。筆者認為,在治療痹病時,需注重顧護患者夜間的陽氣,可根據患者自身的情況辨證論治,使用適當的補益之劑以增強維護患者體內之陽氣,御邪外侵。同時可根據營衛晝夜運行理論,針對夜間癥狀顯著,甚至影響睡眠者,加以鎮痛安神藥物[19],改善睡眠質量,固護人體正氣。
3.2 五臟主時,補益肝腎 《素問·五藏生成篇》曰:“諸筋者,皆屬于節。”“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肝在體合筋,周身之筋膜、肌腱、韌帶等聯結關節肌肉者依賴于肝血的濡養,肝血充足則靈活有力,肝血不足則麻木虛弱。《素問·痿論篇》曰:“腎主身之骨髓。”腎藏精,精生髓,骨骼的生長發育依賴于腎中精氣,腎精充盈才能充養骨髓,腎精不足則骨骼脆弱,骨髓空虛。薛己《外科樞要》曰:“筋骨作痛,肝腎之氣傷也。”肝腎不足會導致痹病發生,痹病日久又易損及肝腎,此二臟乙癸同源,常需同治[20]。筆者認為,可根據“五臟各主其時”理論之肝主平旦,腎主半夜,及“子午流注”理論之腎經酉時(17:00~19:00)最旺而卯時(5:00~7:00)最衰[21],對痹病遷延不愈,尤其是肝腎兩虛證患者因時制宜,在肝腎對應時段內遣方用藥,在虛弱之時進行補益。明代醫家楊贏洲早在300多年前即提出補腎藥宜晨服的觀點,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中亦有“早補腎,晚補脾”的治法[22],現代臨床研究也提示,腎陽虛證患者卯時服用補腎方劑療效顯著優于酉時服用[23]。皮質醇分泌高峰在8:00左右,與陽氣生長相應,此時合用溫藥可以增強藥效,給予糖皮質激素(GC)能增強其對全身多系統的推動、興奮作用[24],溫補腎陽藥大多具有調節內分泌的作用,可以外源性地補充機體的不足,因此,晨服補腎藥對于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失調所引起的證候具備療效[25]。然而夜間GC與陽氣對應分泌減少,此時可給予小劑量GC防止病情加重,現有研究表明,小劑量GC夜間給藥治療效果優于晨間給藥[26-27]。為了評價潑尼松緩釋劑在時間治療學應用中的療效及安全性,現代臨床研究結果顯示,夜間服用潑尼松緩釋劑相較于夜間服用安慰劑,以及晨間服用速釋型潑尼松組療效顯著更優,且安全性無差異[28-29]。由此可見,補腎藥晝夜均可服,具體可在辰時補腎陽,在酉時補腎陰,可選用既能祛風除濕,通痹止痛,又入肝、腎二經的藥味,如獨活、川烏、路路通、秦艽、雷公藤、五加皮、桑寄生、狗脊等,祛邪扶正同時進行,注意補充肝血腎精。
3.3 陰陽消長,晝夜服藥 王好古《陰陽寒熱各從類生服藥圖象》曰:“假令附子與大黃合而服之,晝服則陽藥成功多于陰藥,夜服則陰藥成功多于陽藥。”指出晝夜節律會一定程度上影響藥物的療效,現代研究也得出相同結論[2,28]。傍晚至夜間,衛氣行于陰分,人體陰氣漸長,此時人體依賴陰血濡養,補陰藥、補血藥能夠滿足滋陰血的物質需求,更易發揮作用,清晨至午時,人體陽氣從里達表,逐漸旺盛,此時服用補陽藥有助于陽氣升發,服用補氣藥有利于陽氣提升及驅邪外出[30]。筆者認為,在治療痹病時,可根據方劑的陰陽偏性擇時服藥,以提高藥力,增強方藥效果,或采用晝夜方劑治療,晝服偏于溫陽補氣,祛風通絡之品,夜服偏于滋養陰血,活血祛瘀之品,配合人體陰陽消長之節律,掌握最佳服藥時間以起到增效減毒的作用。
3.4 子午流注,聯合針藥 目前臨床上子午流注理論指導痹病治療多運用在針、灸、穴位敷貼方面。聶彩云等[31]研究發現,選擇每日酉時給予膝痹病患者足少陰腎經之復溜穴和陰谷穴透藥治療,患者的疼痛緩解與功能恢復均優于對照組。洪昆達等[32]對不同證型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共200例進行子午流注灸法治療,有效率均在70%以上。劉懷省等[33-34]的臨床研究表明,酉時隔花椒餅督灸、酉時隔姜督灸有效緩解RA患者疼痛的作用較對照組更為明顯。筆者認為,臨床上除用中藥方劑治療痹病外,還可結合中醫特色之針灸、穴位敷貼等療法。根據子午流注理論,足少陰腎經旺于酉時,足厥陰肝經旺于丑時,可根據十二經所旺之時,選取相應經絡上的穴位,如足少陰腎經之太溪穴、復溜穴、陰谷穴,足厥陰肝經之太沖穴、中封穴、膝關穴,以及歸屬于其他經絡但對風濕痹痛具有良好效果的腧穴進行針灸、透藥等治療。
鑒于子午流注針法、灸法擇時治療痹病具有更好的臨床療效,依據子午流注理論,針對痹病的中藥復方時間治療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但目前鮮有研究報道,可借鑒針對其他疾病中藥復方擇時治療的經驗開展進一步的探索研究。例如彭爐曉[35]采用雙扶湯擇時服藥治療原發性高血壓脾腎陽虛證的研究表明,在脾腎兩經所旺的巳時(9:00~11:00)、酉時(17:00~19:00)服用組較常規時間服用組更能達到協同增效的效果。進一步深入研究基于子午流注理論的中藥復方擇時治療痹病,有助于推動該中醫理論的創新發展,并優化目前痹病的治療現狀。
3.5 未病防治,預防調護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治未病”體現了中醫預防醫學的思想,主要包括“未病先防”及“既病防變”兩個方面。在“未病先防”方面應對危險因素采取預防干預措施,人們的日常生活要順應自然的陰陽消長變化規律,避免感受風寒濕熱之邪;做到“飲食有節”“謹和五味”,避免過食肥甘厚味導致內蘊濕熱;做到勞作有度,“形勞而不倦”,避免勞逸不當、損耗精氣[36];適當參加體育鍛煉,同時注意避免跌仆外傷、損及筋脈。在“既病防變”方面,痹病的臨床表現多有晨起疼痛、僵硬等癥狀,因此,日常起居應注意保暖,尤其清晨時分,陽氣未復,溫度較低,應注意避免肢體感受風寒濕氣;在陽光充足時,適當接受日光照射,以增強體內陽氣,改善肢體關節的癥狀[37];飲食宜均衡,忌食辛辣、生冷等物,依據中醫體質學說,寒重者多食溫熱之品,濕重者多食祛濕之品,熱重者多食清熱之品;患者需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避免過度情志刺激;鼓勵患者通過練習太極拳、八段錦等鍛煉病變肢體;視具體病情及體質對患處采用合適的中藥方劑進行熏洗;可配合針灸、推拿等治療調和氣血、改善關節功能、增強機體免疫力[38]。
4 小 結
綜上所述,時間醫學的概念在中醫理論中由來已久,隨著近年來西醫學對人體生物鐘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臨床研究結果顯示,按照節律周期性治療取得了良好療效。筆者認為,中醫理論中晝夜節律觀點對痹病防治的指導作用主要有5點:一則依據正邪盛衰的病變規律,注重扶助正氣、顧護患者夜間陽氣,以助御邪外侵;二則參考五臟各主其時理論,按時補益肝腎二經;三則依照人體內部陰陽消長規律,晝夜分時服藥;四則根據子午流注理論,聯合針灸、中藥治療;五則按照自然界陽氣變化,起居有時,飲食適宜,注意保暖,避免感邪。
參考文獻
[1] 丁莉,王平,游秋云,等.晝夜節律在中醫臨床中的應用[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7,32(4):1485-1487.
[2] BUTTGEREIT F,SMOLEN JS,COOGAN AN,et al.Clocking in:chronobiology in rheumatoid arthritis[J].Nat Rev Rheumatol,2015,11(6):349-356.
[3] 康學智,賈麗娜.持續光照動物模型研究進展及其應用展望[J].中國醫藥導報,2015,12(8):42-45.
[4] 時雨杰,劉暢.生物時鐘與能量代謝的整合研究[J].中國細胞生物學學報,2017,39(3):261-270.
[5] 郭靜靜,段瑩,耿新玲,等.與睡眠有關的大腦和神經結構(三)腦內的生物鐘[J].世界睡眠醫學雜志,2015,2(6):339-342.
[6] 馬艷苗,賈躍進,柴智,等.淺述中西醫對失眠癥晝夜節律的認識[J].世界中西醫結合雜志,2017,12(9):1189-1191,1195.
[7] 曹憲姣,張偉.從“旦慧、晝安、夕加、夜甚”角度論支氣管哮喘晝夜發病節律[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16,18(9):153-155.
[8] 邢陳,宋倫.晝夜節律在調控免疫系統功能中的作用[J].軍事醫學,2017,41(3):233-236.
[9] STRAUB RH,CUTOLO M.Circadian rhythm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implications for pathophysiology and therapeutic management[J].Arthritis Rheum,2007,56(2):399-408.
[10] 張立平.《黃帝內經》對人體日節律的認識[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6,22(10):1288-1290.
[11] 陳英,黃春林.冠心病心律失常晝夜節律與子午流注時辰規律的聯系觀察[J].新中醫,2007,39(9):59-61.
[12] 吳天浪,李秦蓉.386例石淋猝發腎絞痛的時間與人體陰陽晝夜節律初探[J].成都中醫藥大學學報,2000,23(1):23,32.
[13] 向陽,高悅.232例男性腎絞痛患者疼痛發作時間的規律性分析[J].中醫藥導報,2009,15(1):37-38.
[14] 荀春錚,王孟清.小兒肺炎支原體感染后咳嗽發作時間與證候相關性初探[J].中國中西醫結合兒科學,2016,8(1):94-96.
[15] 王雪華.小兒肺炎支原體感染后咳嗽的特征及與發作時間相關性的臨床研究[J].首都食品與醫藥,2019,26(2):22-23.
[16] 李艷,郭暉,宋亞剛,等.子午流注與生物鐘[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9,34(10):4770-4773.
[17] 陳世賢,徐娟,朱俊卿,等.痹病內涵與外延研究[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18,38(10):1247-1249.
[18] 鐘佳,付至江.從時間節律出發探討痛風性關節炎的中醫特色化防治[J].按摩與康復醫學,2021,12(2):87-90.
[19] 王愛華,梁曉娟,李偉青.從中醫擇時用藥探討風濕病患者的服藥方法[J].中醫臨床研究,2014,6(20):38-39.
[20] 周曉紅,彭銳,李佳,等.基于晝夜節律探討從肝論治膝骨關節炎[J].中醫藥導報,2020,26(15):195-198.
[21] 成蕓,馮志海.淺析因時制宜在強直性脊柱炎治療的應用[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9,8(9):60-61.
[22] 殷越,王清玉,武文杰.《臨證指南醫案》中因時治療水病方法探討[J].中國醫藥導報,2021,18(5):146-149.
[23] 孫繼銘,白厚基.擇時服用補腎湯治療腎陽虛證的臨床研究[J].實用中醫內科雜志,2004,18(2):131-132.
[24] 肖勇洪,沈嘉艷,許飛,等.中醫理論佐證糖皮質激素治療風濕病的給藥時間[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8,24(4):513-514.
[25] 姚成增.中醫“腎”的時間醫學研究概況[J].皖南醫學院學報,2003,22(3):223-225.
[26] 李偉.小劑量糖皮質激素在類風濕性關節炎治療中給藥時間點分析[J].中外醫學研究,2018,16(24):11-13.
[27] 王文琴,陳颯,許盼盼.小劑量糖皮質激素不同時間點給藥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療效觀察[J].浙江中西醫結合雜志,2014,24(10):890-892.
[28] BUTTGEREIT F,DOERING G,SCHAEFFLER A,et al.Efficacy of modified-release versus standard prednisone to reduce duration of morning stiffness of the joint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CAPRA-1):a double-blind,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Lancet,2008,371(9608):205-214.
[29] BUTTGEREIT F,MEHTA D,KIRWAN J,et al.Low-dose prednisone chronotherapy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a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 (CAPRA-2)[J].Ann Rheum dis,2013,72(2):204-210.
[30] 劉倩,吳臘梅,鐘木英.基于中醫時間醫學理論探討擇時服藥法的應用[J].中國社區醫師,2019,35(13):12-13.
[31] 聶彩云,范卉,馬春霞,等.子午流注納子法中醫定向透藥治療膝痹病的效果及護理[J].中西醫結合護理(中英文),2018,4(6):38-41.
[32] 洪昆達,萬甜,張麗瑛.子午流注灸法治療不同證型類風濕性關節炎的臨床研究[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7,32(11):5233-5236.
[33] 劉懷省,韓文朝,欒淇景,等.酉時隔花椒餅督灸對中老年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疼痛的影響[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7,6(10):35-37.
[34] 梅陽陽,付長龍,龐書勤,等.擇時隔姜督灸對中老年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疼痛的影響[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6,5(7):20-23.
[35] 彭爐曉.雙扶湯擇時服藥治療原發性高血壓脾腎陽虛證的臨床觀察[D].長沙:湖南中醫藥大學,2020.
[36] 曹玉舉,李娜,秦濤,等.婁玉鈐教授應用“治未病”思想防治風濕病經驗[J].中醫研究,2010,23(2):63-65.
[37] 李梢.風濕病臨床防治的時間擇優化探討[J].中醫雜志,2000,41(10):581-583.
[38] 孫瑾,劉華.“治未病”思想在風濕痹病護理中的應用效果[J].臨床醫學研究與實踐,2017,2(3):161-162.
收稿日期:2022-08-10;修回日期:2022-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