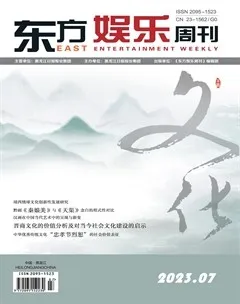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下醫療紀實類紀錄片的價值導向
陰曉帆
[摘要]在新媒體時代,隨著科技水平和醫療水平的不斷提高,在“健康中國”概念提出和醫患關系矛盾日益凸顯的背景下,社會和公眾對于醫療紀實的關注座越來越高,醫療紀實類紀錄片因與現代社會關系緊密,受到越來越多觀眾的期待。分別在2016年和2019年播出的《人間世》系列醫療紀錄片不同于早期的醫學知識科普和健康傳播,它以醫院作為敘事空間記錄了發生在醫療領域的真實人物和真實故事。本文分析《人間世》系列紀錄片的價值導向,既有拍攝內容創造的社會價值,又有對于今后醫療紀錄片的拍攝帶來的創作和拍攝價值。
[關鍵詞]《人問世》系列紀錄片;社會價值;創作拍攝價值
《人間世》系列紀錄片自播出以來,便得到了社會和公眾的廣泛熱議,其收視率甚至與當時的熱播劇相差無幾。不同于以往的醫療紀錄片致力于展現先進的醫療設備和醫療技術,《人間世》系列紀錄片聚焦了發生在醫院的真實的人物和故事。紀錄片作為一種以真人真事為創作素材,并對其進行必要的藝術加工以揭露事實本質,從而引發人們思考的藝術形式,在傳遞正確社會價值方面起到了橋梁和紐帶的作用,《人間世》系列紀錄片的內容傳遞了人文關懷和醫療知識,也引發了社會對于醫患關系、醫療狀態的思考。同時,隨著紀錄片制作水平的提升,《人間世》系列紀錄片對醫療紀錄片創作和拍攝,以及紀錄敘事方法及紀錄片醫生形象建構也具有一定的價值。
一、拍攝內容創造的社會價值
(一)科普醫療知識常識,展示真實醫療狀態
人類作為“有溫度”的群體,向來對“生病”“醫院”抱有敬而遠之的態度。醫院就像是痛苦壓抑的代名詞,使得觀眾大多耐心去了解有關醫療的知識與常識。而《人間世》系列紀錄片是記錄醫療工作的一個載體,以影像的形式展現真實、無奈或者喜悅的故事,不僅是展示一個外在的影像文本,也是一個蘊含意義的“文化文本”,表征著文化價值的外部運行,也體現著文化價值的內在邏輯。《人間世》系列紀錄片將醫療知識與常識滲透到了故事當中,比如在《人間世》第二季第一集中,骨腫瘤患者杜可萌以口述故事的形式,科普了骨腫瘤多發生在孩子身上,概率是百萬分之三,相當于連續拋22次硬幣都在同一面的概率。讓觀眾在故事中了解醫療知識和常識。
醫療類紀錄片通過對客觀事實的真實呈現,展示真實的醫院狀態。在以往的醫療紀錄片里,觀眾們得到的信息多數是醫院里充足的醫療資源、先進的醫療設備和技術、被成功救治的病人等。但是醫院本身就是一個充滿風險和未知的地方,所以《人間世》系列紀錄片將關注點更多地放在了真實的醫院醫療狀態上。比如遇到醫療資源與病人需求不對等的情況,在第二季第四集中,瑞金醫院病人對于血的需求和血庫的血存量出現了“矛盾”。臨床血科主管鄒瑋每天都要盤算,血庫的血要如何分,如急診病人急需用血,其他病人只能被迫延緩手術時間。這讓觀眾們清楚了,醫院本就是一個喜憂參半的空間,真實的狀態并不總是完美無缺的。
(二)合理引導、正確看待醫患關系
醫患關系一直以來都是社會爭論不休的話題,由于醫療糾紛引發的輿論問題比比皆是,當先進的醫療技術無法挽救病人的生命時,便加深了醫患之間的對立。而在新媒體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對于生活的需求發生了改變,對醫學和醫生的寬容度也隨之下降。近年來,關于醫患之間沖突的報道層出不窮,導致醫生形象變得負面。如何建立醫患之間的信任,如伺正確看待醫患關系,是醫療紀錄片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人間世》系列紀錄片中,《命運交響曲》直觀地展現了醫患之間的真實狀態,這一集中,既有理解也有沖突。導演秦博在瑞金醫院拍攝的第100例案例,是沒有遵循醫囑的病人術后出現了意外,于是病人的家屬占據了整個神經外科病房,導致醫護人員只能退到護士間為其他病人配藥。畫面中夾雜著哭聲、說話聲和吵鬧聲,走廊和病房里站滿了調解的醫護人員、警察和情緒激動的病人家屬,最終病人家屬動起手,畫面中的人扭打在了一起,走廊和病房不留一絲空隙,導演也調侃自己好像成了戰地記者。最后病人的主刀醫生孫青芳推心置腹的一番話,成功把鬧事的病人家屬“勸退”。除了醫患沖突,我們還可以看到程東峰醫生為了挽救病人做出的努力,以及沒能成功挽救后的無奈和惋惜。很少有醫生會在病人和家屬面前哭,這會被人誤會醫生承認自己有過失,但程東峰忍不住在家屬面前流了淚,以惋惜自己為這位病人做過的全部努力,病人家屬也給了程醫生最大限度地理解和肯定。
中國醫協曾公布過,中國有超過50%的醫生曾遭受過患者或家屬的言語暴力,并且有超過60%的醫生遭遇過醫鬧和醫患沖突。這種現象主要源于公眾的認知出現偏差,多數人并不了解醫院里的真實情況。《人間世》系列紀錄片在醫院進行了全景式的紀實拍攝:醫生為大出血病人用拳頭拼死堵住傷口;醫生向患者和家屬耐心講解手術風險;醫生救治成功發自內心的喜悅,以及搶救無效時醫生的遺憾……這些場面是公眾難以看到的,卻可以引發觀眾強烈的共鳴,緩和醫患之間的沖突,遏制醫患之間的矛盾。
哈貝馬斯在法蘭克福學派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理性溝通”。將這一理念應用到影視空間中,讓鏡頭真實展現出醫生與患者之間的關系,讓大眾看到醫生的救治是否成功其實并不能用非黑即白的眼光來看待。
(三)堅持主流價值導向,傳遞社會人文關懷
新媒體時代,網絡日益發達,如何通過影視作品探討社會話題、堅持社會主流的價值導向利用鏡頭和影像堅持正確的道德立場,傳遞人文關懷,同樣是媒體需要關注的問題。
《人間世》系列紀錄片不僅向觀眾真實地展現了醫患關系,也對社會現狀和矛盾進行了陳述,傳遞了人文關懷。比如《呼吸》中,導演通過鏡頭讓觀眾了解了塵肺病人的艱辛。除此之外,還闡述了塵肺病人難以治愈的社會原因:全國心腦死亡供體中符合移植條件的肺源僅有5%,除了器官資源緊張外,很多塵肺病人都是工人群體,卻因無法確定勞動關系,與職業病鑒定無緣,六七十萬的治療費用,讓許多塵肺病人家庭望而卻步。作為全國人大代表,肺移植專家陳靜瑜在2018年的兩會上建議將塵肺病的診斷和職業病的診斷分離開。他提交了關于放開塵肺病診斷權限的建議,他愿意做病人和政府之間的橋梁。而政府也投入了很多費用用于塵肺病人的救助。
以人為本是我國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以人為本要求我們當代的影視紀錄片關注人類生活的狀態,關注生命的尊嚴。《人間世》系列紀錄片真實反映了百姓群體生存的社會空間和社會醫療狀態,搭建患者與觀眾、患者與社會的橋梁,完成人文關懷的傳遞。
二、為今后的醫療紀錄片拍攝帶來的創作和拍攝價值
一部優秀的醫療紀錄片帶來的價值不僅只有內容的社會價值,一部紀錄片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它的創作和拍攝足夠成熟,可以為今后的醫療類紀錄片帶來借鑒價值。
(一)深入現場,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的方法要求拍攝者融入被拍攝者的群體,了解他們的社會生活,利用鏡頭記錄他們的生活。對于《人間世》系列紀錄片攝制組來說,深入醫院內部,了解醫生、患者的日常,與醫生、患者近距離拍攝,才能獲得最真實、最深度的信息。
《人間世》第一季共有8個攝制組,歷時8個月的時間,對比第一季,第二季的攝制組更多,花費的時間更長,拍攝了二百多個對象,拍攝素材達到216 T,片比更是達到600:1。《人間世》第一季《救命》中,開頭導演便強調為了在瑞金醫院蹲守采訪,他們經過了規范的醫學培訓,為了能夠在手術室進行拍攝,他們給攝影器材量身定制了防菌服。攝制組的鏡頭也化作醫護人員,它們與醫護人員共同進入手術室,像醫護人員一樣同患者共進退。
為了拍攝出一部高水平、高質量的紀錄片,《人間世》系列紀錄片攝制組“駐扎”在醫院里,近距離地觀察拍攝患者和醫生。《人間世》第二季,在一年半的時間里,共拍攝了二百多個案例,有骨腫瘤患者、精神病患者,也有兒科醫生、臨床醫生等。一年半的深入拍攝,讓他們早巳彼此熟悉。就像《煙花》中,杜克萌說拍紀錄片的哥哥們在病房里待了一年,大多數時候他們比較“懶”,但也喜歡陪患者小朋友們玩。
深入現場參與觀察,招他們(醫生、患者)當作朋友而不是當作單純的拍攝對象來看待,把最真實、最溫暖的鏡頭傳遞給觀眾,這也為今后的醫療類紀錄片的創作提供了寶貴價值。
(二)“紀實+故事”的敘事風格
真實是紀錄片的本質,但是一部好的紀錄片絕不是對客觀事實的照搬,一部好的紀錄片應當是對真實影像進行藝術性的加工,既體現紀錄片應有的真實性,又體現藝術化的故事進展。紀錄片創作中紀實手法的運用,更是將紀錄片的“真實”含義變成“事實所體現的價值”而不是事實本身。在《人間世》系列紀錄片中,就采用了“紀實+故事”的敘事風格,忠于紀實,卻不拘泥于紀實,這種敘事風格也為今后醫療類紀錄片提供了借鑒。
紀錄片的故事性應當建立在真實之上,有故事性的加入,紀錄片不再是“冰冷”的影像,同時故事性也增加了紀錄片的可看性。《煙花》中,患者杜可萌以自述的形式開篇,畫面中患者王松茗準備手術和化療,與此同時,杜可萌用方言介紹:“他經歷的這一切,我都經歷過,因為我們得了一種病,叫惡性骨腫瘤。”充滿感情化的敘述方式,輔之以震撼讓人心疼的視頻畫面,沖擊了觀眾的內心。值得一提的是,《煙花》中有一幕將杜可萌的夢以cos的形式變為影像出現在了畫面中,他們脫去了病號服,cos成自己喜歡的形象,他們拉開厚厚的鐵門,穿過迷霧,揮舞著武器砸向寫著“CANCER”的冰塊,醫生和他們的父母走過來擁抱了他們。這一段畫面,呈現的雖然不是真實的生活,但卻是患病孩子們真實的內心。
對真實進行故事化的講述,是一部好的紀錄片誕生的因素之一,同時也更能引起觀眾的共鳴。
(三)構建有血有肉的醫生形象
醫療類紀錄片通過對真實案例的表達,再現真宴的醫療場景。《人間世》系列紀錄片也為還原和建構醫生形象做出了貢獻。在以往的醫療紀錄片中,對于醫生形象的建構往往是無所不能的,這類紀錄片習慣采用“新聞報道”式的醫生形象建構模式:通常介紹患者的病情多么困難,手術難度多么大,對于醫生來說具有多么大的挑戰,而最后的結局是無論多么困難的手術,醫生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事實是,即便再厲害的醫生也無法成為神,就像《救命》中,面對搶救無效的鄒磊,車在前醫生哽咽說道:“你付出感情最多的,往往是可能會覺得……我們還是希望年輕人有更多的機會能夠活過來,但是有時候,你沒得選擇,就這樣吧……”《人間世》系列紀錄片摒棄了“新聞報道”式的醫生形象建構模式,在畫面中加入了更多的醫患情感表達,構建更加鮮活的醫生形象。
醫生首先是一個普通人,其次才是醫生。《人間世》第二季《命運交響曲》中有一位沒有露臉的醫生——x醫生。x醫生兩次奮力搶救的梗阻病人不幸去世,雖然最終的判定會議結果表示x醫生在醫學操作上沒有明顯過失,但x醫生還是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自責中。一段時間后,x醫生再次面對梗阻病人,他首先需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可喜的是最終病人手術成功。
技術可教,剛毅難學。沒有一位醫生無所不能,包治百病,醫生也需要成長。《人間世》系列紀錄片也為今后醫療紀錄片的醫生形象建構提供了參考價值:醫生形象要由“無所不能的英雄”向“人無完人的普通人”轉變。
三、結語
《人間世》這一標題其實來源于《莊子》內篇中的一篇文章,它表述了莊子所主張的處人與自處的人生態度。在如今的新媒體時代下,紀錄片的產出逐年增多,紀錄片的質量前途無量。《人間世》系列紀錄片無疑是成功的,它向社會普及了醫療知識,傳遞了人文關懷,讓社會認識了醫療狀況,了解了醫患關系。《人間世》系列紀錄片也為今后的醫療紀錄片在拍攝、敘事、形象建構上提供了指導。這正是紀錄片的力量。就像總導演秦博所說:“如果發現生離死別的時刻鏡頭在顫抖,請原諒,那是因為站在攝像機后的編導也是有血有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