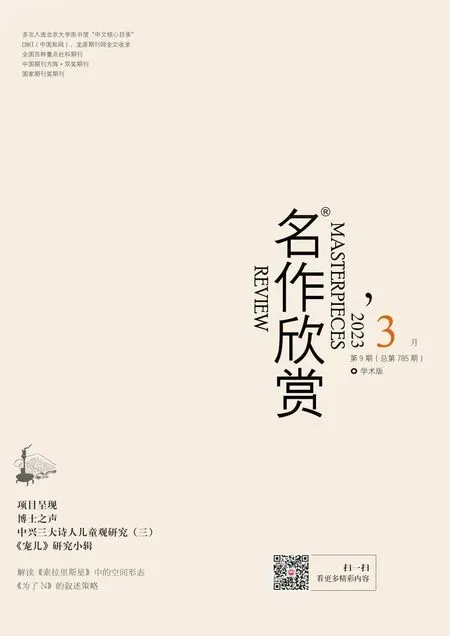論《讓子彈飛》之意義反叛性
⊙陳媛媛[四川大學,成都 610200]
《讓子彈飛》這部電影,有人已對其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有著重分析其黑色幽默式的題材,或是狂歡化的敘事傾向,也有專門從敘事策略和視聽語言角度對其進行分析的。本文重點想談的是《讓子彈飛》這部電影的意義反叛性,這種反叛性是在格雷馬斯、列維-斯特勞斯、伊瑟爾的相關理論視域下所挖掘的,本文將依據相關理論,從影片中呈現的“矩形方陣”“對立結構”“視點關系”這三方面闡述影片是如何進行反叛性意義的闡釋,并進而引發觀者之思的。
一、矩形方陣之“反叛性”
我們可以用格雷馬斯的矩形方陣對《讓子彈飛》中的人物關系進行梳理。在格雷馬斯的矩形方陣中存在著三種關系,分別是對立關系、矛盾關系和蘊含關系。如圖1所示,如果故事中的一項元素為S,那么S與反S便是互為對立的關系,S和非S、反S與非反S分別是兩組矛盾關系,而S與非反S,反S與非S則是蘊含補充的關系。①

圖1
在《讓子彈飛》中,土匪張麻子和惡霸黃四郎是一組對立關系,張麻子想要除掉黃四郎,奪回公平,而黃四郎想要除掉張麻子,穩固自己的權勢,整部影片即是圍繞著這兩人的爭斗展開的。張麻子的六個兄弟和湯師爺總體上又是從屬于張麻子的,輔助張麻子對抗黃四郎,胡萬一幫人是從屬于黃四郎的,也是起到輔助的作用,各自為蘊含補充關系;而張麻子和胡萬一幫人,黃四郎和六個兄弟及湯師爺,則分別構成了兩對矛盾關系,但他們并不是完全對立,因為在各自陣營中他們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反叛。上述整體人物關系如圖2所示:

圖2
在前人的論述中不乏借助格雷馬斯的“行動元模式”或“矩形方陣”來對《讓子彈飛》進行分析的,但他們大多只是借此對人物關系、故事情節進行梳理,并且往往將重點放在張麻子和黃四郎這組對立關系的分析中。但在筆者看來,在此結構關系圖中,最耐人尋味的并不是常見的兩大陣營的對抗,而是對各自陣營中反叛的設計和揭示,這種反叛是對觀者頭腦中固有范式的一種否定,既使得影片沖突更加復雜化,增加了影片意義的多元化,又激發了觀者從中尋找多重意義的欲望。
影片中黃四郎陣營的反叛集中體現在影片結尾時刻,武舉人得知“黃四郎”被殺后,便第一個提著他的人頭沖進了鐵門,并且還想對“假黃四郎”痛下狠手。此外,之前效忠于黃四郎的胡千也趁亂闖進黃府搶東西,這一反叛直接體現了黃四郎的不得人心,同時也充斥著對武舉人、胡千這類利字當頭、無謂忠義、趨炎附勢之小人的諷刺。
而張麻子陣營的反叛一方面體現在湯師爺的搖擺不定上,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影片中湯師爺在誤以為張麻子一方的靠山垮塌,轉而對黃四郎說“您才是我的恩人”這一場景中感受得尤為明顯;另一方面便體現在結尾時刻,張麻子的兄弟們及花姐選擇離開張麻子前往浦東,而不是繼續追尋張麻子,這其實也是一種平靜的反叛,可這種反叛的背后原因何在?湯師爺的反叛是自然的,他的人物設定本來就不是正義良善之人,他最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生存,若不合其利益,他便會及時倒戈;而兄弟們的反叛則給觀者留下了意義空白,之前出生入死的兄弟為何在打了勝仗后便拋棄了頭領?是累了,不愿再過這種膽戰心驚的生活了?還是被上海的繁華所吸引,拋卻了自己的理想?沒了兄弟的張麻子又會去向何處呢?是繼續當假縣長,還是回到山里當土匪頭子?是繼續追尋公平,改造社會,還是被社會異化?這些影片都沒有給出我們確定性的答案,但對于上述反叛性的揭示能夠引發我們去不斷思索背后的原因。
二、真假對立結構之“反叛性”
除了矩形方陣中所體現的反叛性外,若運用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分析原則②解讀影片,則可以發現貫穿影片的真假對立結構也增加了其意義的反叛性,而這一點也是前人在分析時所忽略的。首先從影片中三位核心人物身上我們便可以看到真假的對立。張麻子有著假縣長的身份,黃四郎有著替身,“湯師爺”實則是馬邦德,他們三人用不同身份行動時,往往會有不同的結果,如表所示:
由表1可知,這三位核心人物都有一個假的身份來保護真的自我,并試圖助自己達成目標(名利、公平、安全)。盡管目標有所差異,但最基本都是為了讓“真的自己”能繼續生存下去。

表1
由表2 可發現,在三位人物以假身份掩飾自我而開展行動時,往往會得到一個較好的結果,而以真實身份行動時,結果往往是失敗。而這其實表明在當時真假難辨的社會里,“真”難以存在,需以“假”示人,人們往往需以“假”來偽裝自己才能在社會中生存下去,才能達成自己的目標。影片中湯師爺和黃四郎的結局都是死去,而張麻子作為主人公存活了下來,但他是迷茫的。筆者認為,與其說他是對自己的未來迷茫,倒不如說他是對真假的迷茫,他是應該選擇繼續當假縣長,在這個真假難辨的鵝城生存下去;或是戴上新的假面具,去到另一個難辨真假的地方,繼續追求他想要的公平;還是應該卸下假面具,回到大山里?

表2
此外,從鵝城百姓難辨真假的表現中,觀者也可感受到真與假的交織。他們無法辨認小六子腸粉事件的真假,無法辨認真假縣長、真假師爺、真假麻匪、真假黃四郎……從這些事件中,與其說他們難辨真假,不如說他們是在權力的壓迫下變得“是非不分”,利益至上,因而才會在張麻子需要百姓進攻黃四郎府邸時,沒有人站在正義這方,跟隨張麻子,百姓眼里早已無所謂真假、是非,只有自身利益,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保全自身,在那個難辨真假的社會中生存下去。
這部影片的表層文本是,張麻子打敗黃四郎,惡霸黃四郎自殺,百姓奪回自己的錢財,正義終將戰勝邪惡。在前人的分析中除了論及表層的文本意義外,也談論到影片開放性結局中的多重意義,卻未曾注意影片真假對立結構中所蘊含的對表層意義的反叛。筆者認為上述的種種真假對立向我們所展示的影片的潛藏文本即是在諷刺當時社會的真假難辨,是非不分,價值觀念混亂顛倒,處處是“假”,“真”難存在的現狀,與表層文本理想化的意義頗為不合。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真假對立結構所帶來的對于主題意義的反叛,這種意義的反叛性能夠引導觀者去發現事物發展的另一面,對固有的社會規范和權威進行反思,而不是被動地接受一種話語。
三、對視點關系之反叛
伊瑟爾認為文本與讀者成功實現交流的條件之一便是文本要建立陳述者和接受者共同遵循的慣例,而“慣例”便是伊瑟爾所說的“保留劇目”③。在伊瑟爾看來,文學作品是各種不同視點的匯集,而保留劇目的諸因素則主要是分布在敘述者視點、人物視點、情節視點和為讀者標出的視點之中的,而人物視點是最能凸顯作者所選擇的規范的。這些視點在文本中相互交織,相互作用,不可明確區分,視點間也會形成一種相互間的特定關系,即伊瑟爾所說的平衡式、對立式、遞進式和系列式。
筆者認為,從總體上看,《讓子彈飛》中的視點關系屬于平衡式。所謂平衡式就是指“具有一套非常確定的視點系統:不僅是視點的性質和缺陷都被明確劃分出等級,而且本文的交流功能也很明確”。伊瑟爾以班揚的《天路歷程》為例,說明在平衡式視點中,主人公主要表現核心視點,次要人物的視點則附屬于主人公,由核心視點所展現的一套規范會在文中不斷得到加強,捍衛主人公規范的次要人物會堅持到最后,背離的則將會遭受懲罰或是消失,由此證明主人公規范的有效性。
張麻子作為這部影片的主人公,表現了主要視點,由他的行為舉止所形成的一套規范向觀眾展示了土匪式英雄是如何成功反抗上層的壓迫和剝削并最終獲得公平。張麻子的一套規范中有我們所常見的,如英雄式人物所具有的對理想信念(公平正義)的堅定追求,對壓迫人民的惡霸的深惡痛絕,對廣大百姓的同情以及在行動中所體現的果敢、有勇有謀的性格品質。在此基礎上,影片還強調了在推翻強權的道路上所必不可少的對于權力、武裝力量和人民力量的掌控。
至于影片中的次要人物,一方面可以看到,在影片中背離張麻子規范的次要人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懲罰。比如湯師爺,盡管表面上看他是張麻子陣營的,但實際上他始終是在兩大陣營間斡旋的,在他的規范中,個人利益得失是首位的,鮮有對窮人的同情,以及對公平正義的追求,這顯然是背離了張麻子規范的,因而在張麻子的征戰道路上,他迷失在了白花花的銀兩中。而黃四郎的規范則是通過權勢不斷壓迫剝削百姓,以各種作奸犯科之事來不斷擴增自己的既得利益,這顯然與張麻子的規范是完全敵對的,因而最后他與碉樓一起消失在了爆炸聲中。這些次要人物的消失或是遭受的懲罰證明了其人物規范的非有效性,也反襯了主人公規范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影片中捍衛主人公規范的次要人物則堅持到了最后。比如一直追隨著張麻子而看不慣貪官惡霸的土匪兄弟們,在輔助張麻子對抗惡霸黃四郎上發揮了極大作用,而以“想同麻匪們一起發銀子,聽窮人們笑”為理由加入張麻子陣營的花姐同樣也是起到輔助作用,所以他們最后都有一個較好的結局,這便反映了主人公規范的有效性。
此外,伊瑟爾認為在平衡式關系中,“次要人物身上所缺少的東西在主人公那里得到補充;主人公自己缺少的,他自己在努力補充,所以兩個視點便相互吻合”。影片中次要人物缺少的正義感、謀略、骨氣等在主人公身上均有所展現,而主人公在小六子被害事件中差點槍殺胡萬的舉動所表現出來的沖動,魯莽的性格缺陷則隨著情節的發展得以被其自身克服。整個文本的歷史背景是北洋軍閥混戰,惡人當道,民不聊生,由上述分析可知,文本通過主人公和次要人物視點的相互碰撞去不斷揭露,否定次要人物的規范,肯定主人公所表現的規范,提出了推翻壓迫、獲得公平的一套規范:一手拿槍,一手握權,發動群眾,從而達到最終的平衡。
以上論述闡釋了伊瑟爾所說的“平衡式”視點關系在《讓子彈飛》這部影片中的體現,但若仔細審視,筆者認為,這部影片其實暗中對“平衡式”視點關系進行了顛覆和反叛,即“對主人公規范的肯定中暗含著否定,偏離主人公規范的次要人物也并非都會遭受懲罰”。
筆者認為,在影片中,除了已死的小六子和老二,其他次要人物其實都是偏離主人公規范的。張麻子的兄弟們,盡管看似一直在捍衛主人公的規范,但其實當他們在看見白花花的銀兩那一刻,其規范便已經開始偏離。在未進鵝城前,這些兄弟們作為被壓迫的階級,心中還有對貪官和對惡霸的仇恨,對公平的向往,但是當他們看見兩大家族送來的銀兩后,金錢的誘惑使得他們所向往的不再是公平,而是上海的繁華,所以最后他們會選擇離開張麻子,前往上海。
除了張麻子的兄弟們,影片中還有一個龐大的群體——鵝城的百姓,也是偏離張麻子規范的,但是張麻子為了他們而奮斗。張麻子為鵝城的百姓除掉了惡霸,為他們換來了公平,換來了鵝城的太平。但縱觀整部影片,百姓卻從未站在張麻子一方:六子被害時,百姓是群麻木的看客;張麻子準備進攻黃四郎時,百姓卻遲遲不出現;在得知“黃四郎”被殺后,百姓不是發出迎來公平的歡呼,而是沖破鐵門,搶奪財物,連“縣長”坐的一把椅子最后也被這群百姓搶走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電影中的百姓早已喪失了對公平的追求,他們習慣了在壓迫下跪著生活,即使黃四郎被除,他們也沒能站起來,他們還是只能看到眼前的蠅頭小利,當新的“黃四郎”出現時,他們又會變成不敢言的看客,變成一群鵝,因為他們始終沒有反抗的意識,反抗的勇氣。
影片表面上一直在強調主人公規范的有效性,似乎給了我們一套追求公平的行之有效的規范,但從結局來看,我們能感受到一直堅守自己規范的主人公的落寞:銀兩一分未得,兄弟或死或離,苦心未得到百姓理解,而其最想實現的公平似乎只是幻影。
那么偏離其規范的人有著怎樣的結局呢?兄弟們、花姐可以去繁華的上海,尋找享樂;百姓們得到了大筆錢財;就連已死去的黃四郎和湯師爺在影片最后也被象征性復活,坐上了去上海的列車。因此,平衡式視點關系不斷被影片中這些細節所顛覆,表面上一直被肯定的主人公規范卻被暗中否定,究竟誰的規范是有效的呢?我們難道不應該追求公平嗎?若應該,那如何才能徹底地消除壓迫迎來真正的公平?這是以上影片的意義反叛性帶給我們的思考。
四、結語
其實,在前人的論述中多已涉及《讓子彈飛》的反叛性特征,但大多是從主題、人物、結局、語言等方面入手,筆者在本文中則是結合各種理論,運用結構主義敘事學、結構主義人類學和審美反應理論來對這部影片文本的意義反叛性進行一個深度挖掘。
在上述的矩形方陣、真假結構和視點關系這三方面中,可以感受到在英雄打敗惡霸、正義戰勝邪惡的大框架下,影片通過人物之間的糾葛、內部陣營的反叛、敘事結構中真假的對立轉換、人物視點關系中對于主次人物規范的肯定和否定,打破了觀者頭腦中的固有范式,給予觀者一定的意義生成空間,讓觀者可以從多個角度解讀出不同的意義,從而對其頭腦中固有的思想體系產生懷疑:不是所有被壓迫的人民都會為了公平正義而奮起反抗,他們可能只是一群利益至上的“麻民”;不是所有勝利者都會有一大批追隨者,到最后可能只剩他孤身一人,堅守理想;不是消除了惡霸,就會迎來公平,若人心未變,新一輪的壓迫與被壓迫會再次出現。
這便是由影片的意義反叛性所產生的思考,觀者(讀者)在其否定或矛盾之處參與意義建構的同時,也會對外在的現實符號產生疑問,找出流行的思想體系的缺陷,而不是一味地去接受,麻木于習以為常的話語體系之中。
①〔法〕A.J.格雷馬斯:《論意義——符號學論文集》,吳泓緲、馮學俊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頁。
② 列維-斯特勞斯在《神話的結構》一文中,從俄狄浦斯神話中提取了四組具有相同特征的神話素,并根據二元對立原則對其進行分析比較,從中發現了關于親屬關系的對立(高估與貶低)和關于人類孳生于土地這一問題的對立(肯定與否定),從這兩組對立中發掘出了關于人類起源的矛盾:生于土地和生于兩性,生于一和生于二。詳見〔法〕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1)》,張祖建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231頁。
③〔德〕沃爾夫岡·伊瑟爾:《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金元浦、周寧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頁。(本文有關該書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