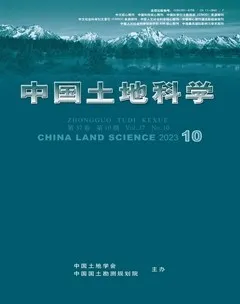面向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全域土地綜合整治適應性轉型與路徑優化研究
金曉斌 應蘇辰



摘要:研究目的:系統探究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適應性轉型框架、作用途徑、模式類型及優化路徑,為助力新時期區域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和決策借鑒。研究方法:歸納演繹法和理論解析法。研究結果:(1)全域整治是國土空間治理體系的重要工具之一,圍繞資金運作、整治模式、生態保護、設施保障、居所更新等方面亟待探索適應性轉型;(2)全域整治可依據要素整治、格局優化、功能強化、價值顯化、機制保障等途徑助力區域高質量發展;(3)從地理區位、產業資源和規劃導向維度解析差異化全域整治模式,提煉出傳統農業型、都市農業型、高效農業型等13種模式類型;(4)從管控端、引導端、利用端和保障端,分別總結強化底線約束和構建整治體系、下沉發展權利和制定開發計劃、探索差異路徑和配套用地準則、保障要素配置和創新整治機制等全域整治優化路徑。研究結論:全域整治仍應加強理論機制、效益評價和類型體系等研究,以更好服務于區域高質量發展目標。
關鍵詞: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區域高質量發展;適應性轉型;路徑優化
中圖分類號:F30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158(2023)10-0001-11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2271259);江蘇省自然資源科技計劃項目(2022009);四川省國土整治中心外協項目(kj-2022-38);成都市土地整治和生態修復中心外協項目(510101202101756)。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推動了國土空間和自然資源的高速開發及高強度利用,帶來了城鎮拓展、產業升級、收入提升、社會轉型等積極效果[1]。但以城為重、以量取勝、人地分離等不均衡開發模式,造成了城鄉分割、鄉村衰落、土地退化、生態污損等問題,不利于國土空間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2]。當前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對經濟增長、社會建設、城鄉轉型、生態保護等提出高水平目標[3]。國土空間作為經濟社會要素流動和集聚的場所,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以國土空間治理優化其要素、結構、功能,促進區域經濟、人口、資源、環境等均衡利用,也有效支撐了高質量發展的總體布局[4]。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共二十大以來重要的社會經濟發展導向,高質量的國土空間以人地協調、資源共享、城鄉共惠、生態共治等途徑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人民共同富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義[5]。因此,圍繞國土空間探索區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既是破解現實障礙的核心訴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趨勢。
20世紀90年代末起,土地整治逐步成為自然資源部門在特定范圍內,針對性運用農用地整理、建設用地整理、生態型整治等手段,實現用地潛力挖掘和空間布局調整,對農業、城鎮、生態空間展開獨立管理的政策之一,發揮了保障糧食安全、集約利用資源和改善人居環境等多重功能[6-7]。2019年起,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以下簡稱“全域整治”)緊密結合國土空間規劃“統一藍圖、統籌布局”的要求,基于傳統農用地、建設用地、生態修復等專項整治的成熟經驗,在鄉鎮或村莊等尺度協同各類用地要素,因地制宜開展資源提質、用地匹配、格局重構等綜合整治工作,旨在統籌提高區域的生產、生活、生態功能[8-9]。
針對新時期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多元訴求,傳統土地整治在對象、目標、機制、模式等方面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和不適應性,難以發揮盤活“人—地—業—錢”要素、統籌城鄉地域發展、協調提升“三生”功能、宜居宜業共同富裕等作用[10]。全域整治堅持“全系統全要素”“多主體多模式”綜合治理的轉型要求,為區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可能的支撐路徑。但當下全域整治仍處在深化探索階段,如何借助這一政策工具在“市—縣—鄉”等區域國土空間尺度助力高質量發展,探尋滿足可持續建設的適應性實踐路徑,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
1 面向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全域整治適應性解析
1.1 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義
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高效率、公平、可持續目標在經濟活力、創新驅動、綠色生態、民生福祉、社會宜居等維度的宏觀表征[3,11]。區域高質量發展應聚焦國土空間載體,進一步細化高質量發展要求。區域高質量發展是以區域國土空間內城鎮、城郊、鄉村等地域系統為載體的高效、均衡、可持續價值溢出過程,呼應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生態文明等戰略,實現高質量國土空間的產業布局、差異治理、生態保護、設施配套和居所更新,強調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的同步同向提升[12]。需合理運用法規、政策、技術等手段,從要素強化、結構優化、功能顯化等維度構建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國土空間布局和支撐體系[13]。
其中,高質量的產業布局要求合理應用各類生產空間,實現第一產業規模集聚、高效智慧,第二產業集約增效、降污減排,第三產業配套完善、多元共享,提高產業融合度及附加值;高質量的差異治理要求針對城鎮、城郊、鄉村等地域系統,結合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因地制宜確立開發模式,塑造多樣特色的國土空間利用格局;高質量的生態保護要求統籌“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保護修復和減排增匯,構建系統穩固的國土空間生態屏障;高質量的設施配套要求建設城鄉均等化的基礎和公共服務設施,涵蓋交通、教育、文化、康養、醫療等領域;高質量的居所更新要求城鄉生活空間適度集約更新,改善人居環境質量,釋放生產和生態留白空間。
1.2 國土空間治理視角下全域整治內涵解析
國土空間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關鍵環節,其核心是調控國土資源,實現對區域空間結構與功能的間接管理,進而影響載體之上的政府、社會、市場等運作行為[14-16]。“多規合一、城鄉一體、多級聯動”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建立以來,我國國土空間治理能力不斷提升,通過打破傳統空間治理職權分散或沖突的障礙,統籌城鄉地域系統差異化共治,協調多元主體的利益訴求,整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國土空間治理循環體系,推動治理目標逐層落實,實現自然和人文生產要素的優化提質、綜合配置和價值顯化,助力區域高質量發展[17-19]。目前,國土空間治理已形成“上位管控—治理傳導—利用落實”三級體系[20-21],其中管控涵蓋“五級三類”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土地管理法》、《城鄉規劃法》等法律法規體系,統籌國土空間治理頂層設計,明確治理基本邏輯和主要維度;傳導涉及國土空間用途管制機制,以落實國土空間規劃的功能分區、用地屬性、建設規模、建設強度、總體布局等具體要求,依規確定國土空間的利用方式[22];利用涵蓋街區、鄉建等小尺度的更新和設計,面向用地整合、結構優化和格局調整開展土地整治工作,針對污損退化的特定空間或生態系統開展具體的保護修復工作等[23]。此外,“三區三線”、主體功能區、自然保護地、自然資源監察審計等方面的政策制度,以及調查、評價、利用等類別的標準規范均覆蓋三級體系,保障國土空間治理(圖1)。
傳統土地整治以局地開發、潛力挖掘和污損修復為主要途徑,貫徹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長期處于國土空間治理的體系末端。新時期全域整治作為融合規劃和工程雙重屬性的政策工具,其科學的理論邊界尚不明晰,在國土空間治理體系的地位也有待進一步確定。亟待明確全域整治的特殊性、必要性和關聯性,梳理全域整治的內涵、作用、途徑、目標等。
全域整治是基于國土空間規劃目標愿景,對區域城鄉地域系統內,市、縣、鄉、村等靈活尺度國土空間全域全要素(含農用地、建設用地、生態用地、工業用地、城鎮低效用地、歷史文化用地等)統籌開展要素修復、結構優化、格局調整等工作,顯化“三生”空間功能的綜合整治活動,具備規劃管控和空間治理的屬性[24-25]。全域整治的核心作用包括:(1)承接多層級多類型國土空間規劃對區域功能分區、指標約束、產業布局、設施配套等管控或引導要求,落實國土空間規劃的分項目標;(2)制定國土空間規劃導向的地塊或工程精度整治方案,統籌陸域和海域、自然和人文、建設和非建設等資源要素調整的約束或許可,輔助落實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及其變更;(3)綜合考慮全域空間的現實障礙、發展階段和多元訴求,調動土地、資本、產業等生產要素在整治區域內流動,提高國土空間的生產、生活、生態功能,顯化經濟、社會、景觀等價值,塑造城鄉區域高質量發展格局。全域整治的主要手段包括:(1)方案規劃,轉譯國土空間規劃目標,常在縣(區)、鄉(鎮)、村(街道)等中微尺度開展全域整治實施方案的規劃,統領用地調整、工程布局、資金籌措等全局要求;(2)工程設計,針對方案規劃的多類專項土地整治工程開展具體設計,包括技術、尺寸、樣式、規模等;(3)保護修復,聯結“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為生態網絡,綜合運用底線約束、修復技術、景觀營造等促進整體保護和系統修復[26];(4)政策支持,給予永久基本農田調整和低效建設用地整合的可能空間,以“占補平衡”“增減掛鉤”等政策提高全域整治積極性,挖掘潛力空間支持全域整治;(5)資金機制,全域整治打破傳統土地整治財政資金壟斷支持的局面,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全域整治,調動主體積極性和整治可能性,滿足多方利益訴求。全域整治實現目標包括城鄉融合(市或縣等中觀尺度全域整治)、城鎮更新(區或街道等中微尺度全域整治)、鄉村振興(鄉鎮或村域等微觀尺度全域整治)、生態文明(采用減排增匯、生態修復等整治工程技術)等。
1.3 面向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全域整治適應性轉型框架
為有效支撐區域高質量發展目標,傳統土地整治至全域整治實現了以下適應性轉型過程(圖2)。
(1)由財政支撐向經濟循環的適應性轉型,以資源、產業、資本邏輯活化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傳統高標準農田、低效用地建設、礦山修復等多依賴財政投入,增加了政府債務和投融資潛在風險,難以高效配置資源、滿足多方利益和有序維持項目,不利于后期管護和長期效益發揮。全域整治依托多元融資機制,調動政府、農民、基層組織、新型經營主體、市場等主體積極性,以財政資金、社會資本、民間資本等渠道引導生產資源按需配置,順應產業迭代規律,支持產業深度融合,明確項目“建—用—護”主體和收益途徑,理順整治“投入—產出—盈利—管護”循環關系,促進全域整治效益持續發揮[27]。
(2)由通用工程向差異模式的適應性轉型,考慮區位、資源、規劃等因素,因地制宜建立全域整治特色路徑支撐區域創新高質量發展。傳統土地整治模式較為固化,簡單套用高標準農田、人居環境、生態修復等技術規范開展碎片同質化建設,追求短、平、快的整治短期效益,忽視資源特色和潛力。全域整治以規劃目標為牽引,圍繞產業、生態、歷史等特質資源,謀劃特定尺度下土地配置方案和城鄉轉型格局,并以系統集成、適度集約、協同利用、簡潔易用為原則開展場地尺度的設計,促進城鄉地域的差異化發展。
(3)由潛力挖掘向保護修復的適應性轉型,統籌土地的經濟和自然屬性,落實區域生態高質量發展[28]。傳統土地整治以農地整合、未利用地開墾、宅基地集約減量等手段,挖掘農業生產和城鎮用地擴張潛力,保障糧食安全和新型城鎮化戰略,但也間接侵占生態用地、打斷生態廊道和破碎生態網絡。全域整治面向特定區域范圍內的“自然—人工”系統,圍繞“山水林田湖草”共同體理念,涵蓋城鎮和鄉村地域進行整體保護修復和分類協同整治,強化全域的保護屏障、固碳釋氧、水土保持、景觀游憩等生態功能,建立生態價值持續轉換的渠道。
(4)由生產要素向公共產品的適應性轉型,以強化設施服務和城鄉均質保障區域民生高質量發展。傳統土地整治重視土地利用結構和功能提升,服務規模高效農業生產;重視鄉鎮用地的多類潛力挖掘,服務城鎮有序擴張,但常忽視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基礎性保障,忽略土地整治服務于人的社會效益提升。全域整治統籌“經濟—民生”偏好和“城鎮—鄉村”布局的關系,引導主管部門、地方政府、集體組織、農民等多層級利用主體參與,并優先考慮建設用地指標用于鄉村或街道的醫療、教育、康體等設施建設,減少基層民生權益被日益擴張的城鎮所侵占,優化區域民生權益配比并提高公共產品配置效率[29]。
(5)由以地為本向以人為本的適應性轉型,以人地協調和功能復合助力區域社會高質量發展。傳統土地整治局限在項目和地塊尺度,即項目在哪布局和地塊如何建設,就地論地,忽略區域用地要素的統籌布局,忽視土地利用主體的基本權益保障,可能導致人地關系失衡和整治目標偏頗[30]。全域整治考慮地方發展目標和實際情況,以“整好地、興旺業、留住人”為原則,強化生活空間的整治地位,包括人居環境更新、歷史傳承保護和設施配套提升,并聯動生產要素和生態要素,優化生活空間的功能韌性和復合性,進一步提升全域整治的公眾滿意度。
2 全域整治助力區域高質量發展的途徑解析
全域整治本質是針對區域國土空間要素進行開發或修復,重塑空間開發格局,優化產業、資金、人口等資源配置結構,強化功能和顯化價值的治理活動。擬遵循“要素整治—格局優化—功能強化—價值顯化—機制保障”邏輯分析全域整治助力區域高質量發展的途徑(圖3)。
(1)全域整治基于整治工程建設,激發土地要素并挖掘潛力。其中,農用地整理以土地平整、土壤改良、坡改梯、未利用地開發、小微生境建設等,挖掘耕地后備資源潛力,提升耕地地力、生態、利用等質量;建設用地整理以宅基地復墾、工礦廢棄地整理、設施建設等,挖掘生活居住和生產增值的潛力,提高人居環境、公共服務、產業設施等質量;生態保護修復以礦山修復、水土治理、植被復綠、廊道建設、景觀營造等,挖掘生態保育和修復潛力,提高生態系統的供給、調節、文化和支持質量[31]。
(2)全域整治基于區域規劃設計,優化土地利用結構和開發格局。圍繞上位規劃指引和“三區三線”的底線約束,結合詳細規劃或村莊規劃的多元目標,梳理空間布局的錯配、沖突、障礙等問題,制定全域覆蓋、地塊尺度及工程精度的實施設計方案,完成整治區域土地和權屬的綜合配置,提高單類要素的利用條件,如耕地規模連片、建設用地節約集約、生態用地網絡均質化,并發揮多元要素的協同成效,如耕地適度配置農產品加工用地,增加農業收入;居住用地適度增配基礎設施和服務用地,優化生活條件等[32]。
(3)全域整治基于城鄉要素統籌治理,強化地域多元功能并促進功能互補。基于土地要素優化和配置,促進城鄉地域的要素激活和流動,帶動城鎮或鄉村的產業重塑、資本進駐和人口遷移[33]。其中,以社會資本進駐、產業用地布局和新型經營主體培育,推動城鎮產業更新、農業規模現代化、鄉村產業融合發展等生產功能強化;以建設用地集約整合、人居環境整治、基礎設施建設和基層公眾治理,實現人居環境改善、設施服務配套、鄉風文明建設等生活功能完善;以面源污染治理、產業騰退升級、生態廊道建設、大地景觀營造等,增強景觀生態質量、生態系統連通度、生態環境品質等生態功能。
(4)全域整治基于不同功能載體的空間生產實踐,顯化區域綜合價值[34]。生產空間產出多元產品供給、增值經濟收益和就業保障價值;生活空間產出環境宜居、社會福利保障、公共服務支持、歷史文脈傳承等價值;生態空間產出安全屏障、水土保持、固碳釋氧、景觀游憩、經濟效益等價值。
(5)全域整治整合多類政策手段,完善區域高質量發展的保障機制[35]。以農田開發整理、建設用地整理、生態型整治等工程技術集成機制支撐要素整治;以永久基本農田調整、耕地占補平衡、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村莊規劃微調、土地權屬調整等動態變更機制支撐結構優化;以農業產業用地配置、建設用地入市交易、社會資本參與整治等配套運作機制支撐功能強化;以工程管護維護、生態補償制度、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等利用轉化機制支撐價值顯化。
3 差異化全域整治模式解析
為全面提升一定國土空間范圍內城鎮或鄉村的資源利用效率和社會發展水平,同步顯化區域高質量發展成效,可借助全域整治,從區位基底、資源優勢和規劃目標維度因地制宜探索實踐路徑,總結差異化全域整治模式。區位指某地域的自然地理位置,也蘊含與其他地域經濟社會的空間聯系,是全域整治的基礎,通常一定區域內的區位圍繞城鎮、城郊和鄉村探討[36]。城鎮或鄉村具有多元自然和人文資源稟賦,自然資源包括水、土、氣、生物、礦產等,人文資源包括歷史文脈、聚落形態、建筑形制、風俗禮儀等[37]。產業是鄉村振興和城鎮轉型的關鍵,以產業為牽引,有效整合、配置并利用地方資源,是全域整治的核心。第一產業整合耕地、水、氣候、生物等農業耕作資源,第二產業整合原料、用地、技術裝備、園區集群等制造加工資源,第三產業整合景觀風貌、歷史文化、康養娛樂等文旅游憩資源,均應力求產業融合。規劃導向是地方發展的指引,其確定了區域定位和利用目標,是全域整治圍繞特定尺度,開展生產資源配置的依據。在鄉鎮或村莊級實踐尺度常見的規劃引導策略包括減量撤并、維穩增效和融合提質,分別指城鎮存量減量發展和鄉村適度撤并搬遷;維持基本現狀并適度優化配置,提升生產效率和成效;促進城鄉融合和產業融合的轉型發展,提高“三生”空間品質[38](圖4)。
基于上述模式解析思路,可借助三維魔方法對模式類型做進一步梳理[39-40]。將地理區位(城鎮地域、城郊地域、鄉村地域)、產業資源(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規劃導向(減量撤并、維穩增效、融合提質)維度的子屬性依次編碼為1、2、3,三種維度間依次組合、窮舉和歸并,得到13種全域整治模式類型(圖5),相應內涵和整治重點詳見表1。
4 面向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全域整治優化路徑

4.1 自上而下:強化底線管控約束,構建多級整治體系
自2019年全域整治啟動以來,政策規范和地方試點尚處于改革探索期,既有多地域、多類型和多尺度的階段實踐成效,但仍存在空間底線不穩、整治質量不強、農民權益受損等情況,需要進一步完善全域整治頂層設計,保障全域整治科學有據、系統有序開展。一方面應強化全域整治的多類底線約束,明確管控基本邊界,為地方全域整治劃定合法依規的創新實踐空間。2023年4月,自然資源部下發《關于嚴守底線規范開展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試點工作有關要求的通知》,要求維護“三區三線”劃定成果,不得以整治名義隨意調整布局,應在農業、城鎮、生態空間相對獨立開展全域整治工作;防止耕地和永久基本農田階段性流失和質量降低,堅持耕地和永久基本農田調整“先補后占”原則,落實耕地保護目標責任,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維護整治區群眾的合法權益,穩慎開展合村并居,以人為本保障住宅建設和保護特色鄉村。另一方面,應立足區域國土空間治理的視角,構建“市—縣—鄉”三級全域整治體系,輔助規劃落實,并發揮全域整治的多層級協同作用。市級全域整治關注城鄉融合和區域統籌,明確全域整治的規劃要求、任務傳導和功能分區,統籌耕地、生態用地、城鎮建設用地、鄉村建設用地等整治目標;縣(區)級全域整治承接市級分區定位和指標傳導,結合鄉鎮特色落實類型分區,明確鄉鎮整治格局、方式和近期任務等,適當開展國土空間要素的縣域流動配置,也可依托流域、經濟區等功能片區開展跨縣區全域整治,強化流量資源的整合成效;鄉鎮級全域整治結合縣域要求和問題障礙,因地制宜編制地塊尺度的整治實施方案,以落實用地調整、產業布局、設施完善、居住更新、生態保護等子目標,指導整治工程具體落地。
4.2 自下而上:引導發展權利下沉,多類空間適度留白
傳統土地整治的作用對象和目標均較為明確,即挖掘耕地生產潛力、保障耕地動態平衡、促進建設用地節約集約等,由此自然資源部門引申出“新增耕地指標—占補平衡”“建設用地指標—增減掛鉤”等“指標+配套政策”的條狀管理方式。以指標產出、交易或流動等途徑完成耕地、建設用地等重點空間要素的底線約束和均衡配置,自上而下的審批授權模式較為簡潔直接,但也因管理抓手單薄,過于關注指標數量管控而忽視空間配置的合理性,降低了地方整治成效和要素配置效率。全域整治的綜合轉型,擴大了國土空間治理的范圍,整治管理的對象、責任和方式也更為多樣,但部分全域整治試點仍側重于指標控制和短期收益,在縣域及更大尺度統籌耕地和建設用地的指標配置,忽視鄉鎮發展的自主權,忽視生態用地、歷史文化用地、公共用地等與耕地、建設用地協同治理的必要性。全域整治應轉變管理邏輯,以基層治理成效為管控考核重點,將土地發展權配置進一步落實到可操作的鄉鎮單元,自下而上綜合考慮其人口、土地和經濟的發展訴求和優化布局,合理應用整治獲得的流動指標。在滿足全域整治底線約束和前期資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適度交易部分耕地和建設用地指標,在城鎮或鄉村的生產、生活、生態、游憩、文化等多類空間內,應預留并合理分配滿足產業建設、環境改善、設施配套等發展前景的流量用地空間,制定科學適宜的空間開發利用計劃。
4.3 由強到弱:探索差異整治路徑,制定用地配套導則
傳統土地整治多采用簡單統一、成熟同質的整治路徑以高效完成建設,但也容易因照搬照抄、盲目拆建、缺少設計等失去特色資源的發展優勢,降低同類街區或鄉鎮的競爭優勢,弱化區域內部的互補優勢。我國國土空間要素的類型、數量、質量、分布等存在較大差異,涉及的利用主體、開發方式、發展階段也千差萬別,圍繞國土空間治理的全域整治更要綜合考慮區域自然資源要素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平衡效率、特色和公平,挖掘全域空間資源組合方式,探索城鄉子系統的差別化整治路徑。主要從全域整治時序和類型思考,其中時序方面應對擬開展全域整治的區域進行全面基礎調查,包括人口結構、經濟產業、設施服務、歷史文化、國土資源等,從土地利用沖突、低效用地識別、生態質量評估、整治潛力評估等視角進行深入分析,結合實地調研經驗,確定區域關鍵問題和全域整治迫切性,并在更大尺度范圍統籌整治優先次序;類型方面應結合上位規劃定位,結合前述多元分析,充分挖掘區域的產業基礎、生態環境、礦產能源、歷史遺產、鄉風文脈等特質資源,確定可能的資源價值轉化路徑和整治組合介入方式,分類總結全域整治模式。全域整治本質為優化國土空間要素的配置,以土地要素為主,以產業、資金、人口要素為輔。為調動全域整治積極性,強化要素協同效應,應針對不同類型整治試點,制定合規有效的用地配套導則,如集聚提升型應配套一定比例的設施服務用地保障人民基本的運動、游憩、消費等公共活動訴求,三產融合型應配套一定比例的二產延伸配套、三產介入保障的流量用地,促進產業深度融合和循環增值。
4.4 由前到后:調動要素流動活力,創新多元整治機制
全域整治作為對象多樣、時序較長、流程復雜的國土空間治理活動,需要基于全生命周期視角建立完整的生產要素保障機制。規劃端應對接城鎮詳細規劃和村莊規劃創新全域整治方案設計機制,充分考慮基層和政府的利益訴求,不斷修正更新并做好產業導入、生態保護、生活保障、土地利用等精細化設計,重視規劃設計的前瞻性和有效性。投入端應強化多元資金參與機制,爭取涉農資金、專項資金、財政補貼等,拓寬“兩項指標”的交易主體及范圍,激發社會資本參與動力,激活多類整治參與主體,并健全收益分配循環制度,穩步提升人民和社會資本的綜合權益,落實多方監督和風險規避管理。實施端應建立多部門組織協調機制,統籌自然資源、農業農村、生態環境、住房和城鄉建設、水利、財政等分管主體,做好重大事項決策、政策聯動制定、資金運作、建設實施、考核獎勵等工作配合。監督端應落實綜合驗收和評價機制,驗收應對照鄉鎮規劃和村莊規劃進行實地核查,以多時點子項目驗收監測各類工程進度和質量是否達標,并在整治末期開展綜合驗收,確保耕地和永久基本農田數量和質量、建設用地規模、生態紅線突破、公眾滿意度等核心指標是否合格。評價應基于多時點和多主體,考慮經濟、生態、社會、投入、產出效益的綜合評估,面向產業、生態、文化、制度等特質資源開展特色評價,以備總結試點實施模式。管護端應明確管理、利用、維護等主體,并配套資金保障整治效益的長期發揮(圖6)。
5 結語
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以國土空間為載體,以土地整治既往經驗為基礎,以資源按需優化配置為核心,以新時期全域整治探索為抓手,創新全域整治支撐區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是當下資源科學學界和自然資源業界應共同關注的命題。本文立足區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從國土空間治理視角解析全域整治的概念、作用、手段等理論內涵,構建從傳統土地整治到全域整治的適應性轉型框架;遵循“要素—格局—功能—價值—機制”邏輯,提煉全域整治助力區域高質量發展的5類途徑;面向區域城鄉地域差異、等質和同步提升訴求,基于區位基底、資源優勢和規劃目標維度,提出差異化全域整治模式解析框架,總結傳統農業型、都市農業型、高效農業型等13種全域整治模式類型;最后從管控端、引導端、利用端和保障端,分別探討了面向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全域整治優化路徑。總體而言,本文構建了以全域整治為核心,集成轉型理論、作用機制、模式類型和優化路徑維度的研究框架,為助力區域國土空間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學理支撐。
區域高質量發展是面向廣大城鎮、城郊和鄉村地域,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等綜合效益的高效提質、公平共享和可持續增值的復雜過程。需要明確的是,以全域整治為抓手助力區域高質量發展,不僅是空間資源的模擬、優化和配置,更是以土地為基礎,活化資金、產業、人口等要素的利好平臺。后續應進一步探討全域整治帶動城鎮或鄉村綜合治理的理論機制,明晰全域整治的邊界,包括直接作用和協同影響范圍。全域整治助力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效益量化,是服務于行業管理和地方建設的有力支撐,構建覆蓋全流程、多主體及綜合目標的效益評價體系,剝離全域整治對于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成效貢獻度。差異化全域整治是擺脫千村一面、千鎮一面等重復建設、低效利用、同質競爭的關鍵,是支撐區域高質量均質發展的重點。基于區域地理單元,梳理歷史發展路徑和空間組織結構,挖掘內生資源比較優勢,分析外緣綜合需求,圍繞內部多元供給和外部多樣消費維度,建構全域整治模式類型的體系。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周國華,龍花樓,林萬龍,等. 新時代“三農”問題和鄉村振興的理論思考與實踐發展[J] . 自然資源學報,2023,38(8):1919 - 1940.
[2] 劉彥隨. 中國新時代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J] . 地理學報,2018,73(4):637 - 650.
[3] 張軍擴,侯永志,劉培林,等. 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要求和戰略路徑[J] . 管理世界,2019(7):1 - 7.
[4] 本刊特約評論員. 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空間治理現代化[J] . 中國科學院院刊,2020,35(7):793 - 794.
[5] 龍花樓,徐雨利,鄭瑜晗,等. 中國式現代化下的縣域城鄉融合發展[J] . 經濟地理,2023,43(7):12 - 19.
[6] 龍花樓,張英男,屠爽爽. 論土地整治與鄉村振興[J] . 地理學報,2018,73(10):1837 - 1849.
[7] 韓博,金曉斌,顧錚鳴,等. 鄉村振興目標下的國土整治研究進展及關鍵問題[J] . 自然資源學報,2021,36(12):3007 - 3030.
[8] 金曉斌,羅秀麗,周寅康. 試論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基本邏輯、關鍵問題和主要關系[J] . 中國土地科學,2022,36(11):1 - 12.
[9] 應蘇辰,金曉斌,陳艷林,等. 耦合ANT-SPO的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績效評價:方法與實證[J] . 中國土地科學,2022,36(10):81 - 90.
[10] 孔雪松,王靜,金志豐,等. 面向鄉村振興的農村土地整治轉型與創新思考[J] . 中國土地科學,2019,33(5):95 - 102.
[11] 李金昌,史龍梅,徐藹婷. 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探討[J] . 統計研究,2019,36(1):4 - 14.
[12] 樊杰,王亞飛,王怡軒. 基于地理單元的區域高質量發展研究——兼論黃河流域同長江流域發展的條件差異及重點[J] . 經濟地理,2020,40(1):1 - 11.
[13] 方創琳. 中國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規律性與重點方向[J] . 地理研究,2019,38(1):13 - 22.
[14] 戈大專,陸玉麒. 面向國土空間規劃的鄉村空間治理機制與路徑[J] . 地理學報,2021,76(6):1422 - 1437.
[15] GE D Z, ZHOU G P, QIAO W F, et al.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framework and perspectives[J] .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20, 30(8): 1325 - 1340.
[16] 龍花樓. 論土地整治與鄉村空間重構[J] . 地理學報,2013,68(8):1019 - 1028.
[17] 孫施文,劉奇志,鄧紅蒂,等. 國土空間規劃怎么做[J] .城市規劃,2020,44(1):112 - 116.
[18] 岳文澤,王田雨. 中國國土空間用途管制的基礎性問題思考[J] . 中國土地科學,2019,33(8):8 - 15.
[19] 劉彥隨,王介勇. 轉型發展期“多規合一”理論認知與技術方法[J] . 地理科學進展,2016,35(5):529 - 536.
[20] 張楊,王躍國,宋家寧. 對高質量發展背景下國土空間規劃的幾點認識[J] . 中國土地,2020(3):29 - 30.
[21] 董祚繼. 從機構改革看國土空間治理能力的提升[J] . 中國土地,2018(11):4 - 9.
[22] 林堅,武婷,張葉笑,等. 統一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制度的思考[J] . 自然資源學報,2019,34(10):2200 - 2208.
[23] 黃征學,王麗. 國土空間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涵及重點[J] . 中國土地,2020(8):16 - 18.
[24] 陳艷林,李晨. 開展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實踐與思考[J] .中國土地,2021(2):44 - 46.
[25] 李紅舉,曲保德.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實踐與思考[J] .中國土地,2020(6):37 - 39.
[26] 白中科,周偉,王金滿,等. 試論國土空間整體保護、系統修復與綜合治理[J] . 中國土地科學,2019,33(2):1 - 11.
[27] 肖武,郭既望,張麗佳,等.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與生態修復的市場化機制、模式與路徑[J] .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23,28(8):203 - 217.
[28] 王軍,應凌霄,鐘莉娜. 新時代國土整治與生態修復轉型思考[J] . 自然資源學報,2020,35(1):26 - 36.
[29] 黃雪飛,廖蓉,吳次芳,等. 土地整治轉型——基于公共品供給激勵視角的研究[J] . 中國土地科學,2019,33(4):84 - 92.
[30] 項曉敏,金曉斌,王溫鑫,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下的土地整治制度創新初探[J] . 中國土地科學,2017,31(4):12 - 21.
[31] 陳坤秋,龍花樓. 土地整治與鄉村發展轉型:互饋機理與區域調控[J] . 中國土地科學,2020,34(6):1 - 9.
[32] 盧丹梅,李易燃,趙建華.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視角下的鄉村高質量發展空間路徑研究——以云浮市鎮安鎮西安村為例[J] . 城市發展研究,2021,28(11):3 - 9.
[33] 戈大專,龍花樓. 論鄉村空間治理與城鄉融合發展[J] .地理學報,2020,75(6):1272 - 1286.
[34] 孫婧雯,陸玉麒. 城鄉融合導向的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機制與優化路徑[J] . 自然資源學報,2023,38(9):2201 -2216.
[35] 李紅舉,蘇少青,吳家龍.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助推自然資源要素配置的若干思考[J] . 中國土地,2023(8):48 - 51.
[36] 李小建,羅慶,楊慧敏. 專業村類型形成及影響因素研究[J] . 經濟地理,2013,33(7):1 - 8.
[37] 李玲燕,裴佳佳,葉楊. “資源—要素—政策”相協調下鄉村典型發展模式與可持續發展路徑探析[J] .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22,43(10):220 - 231.
[38] 王永生,劉彥隨. 綠水青山視域下中國鄉村振興模式提煉與分類研究[J] . 地理研究,2023,42(8):2005 - 2017.
[39] 葉菁,謝巧巧,譚寧焱. 基于生態承載力的國土空間開發布局方法研究[J] . 農業工程學報,2017,33(11):262 -271.
[40] 翁睿,金曉斌,張曉琳,等. 集成“適宜性-集聚性-穩定性”的永久基本農田儲備區劃定[J] . 農業工程學報,2022, 38(2):269 - 278.
Research on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for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JIN Xiaobin1,2,3, YING Suchen1,2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Carbon Neutrality and Territory Optimization,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Nanjing 210023, China; 3. Jiangsu Land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Technology Engineering Center,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mechanism, mode type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assisting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with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based on the goal of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concepts, functions, methods, and other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 space governance are analyzed.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has achieved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in terms of fund operation, consolidation mode, ecological protection, facility guarantee and residence renewal. 2) From the dimensions of element consolidation, pattern optimization, function strengthening, value manifestation, and mechanism guarantee, the approaches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to promote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3) Facing the differentiated and equal quality development goal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nsolidation modes is proposed based on location,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planning targets, and 13 modes are summarized, includ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urban agriculture and high-efficiency agriculture, etc. 4) The optimization paths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re explor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control, guidanc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i.e., strengthening constraints and building a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decentralizing development rights and formulating development plans, exploring differentiated paths and supporting land use guidelines, ensuring factor allocation and innovation consolidation mechanism. In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on theoretical mechanism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ypological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should be enhanced to suppor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erritorial space.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path optimization
(本文責編:張冰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