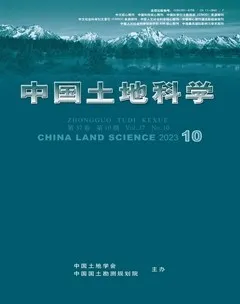農村宅基地季節性閑置與完全閑置的比較
胡明峰 曹廣忠 劉嘉杰 劉濤



摘要:研究目的:識別我國宅基地閑置的類型特征,分析不同類型的形成原因,為閑置宅基地科學管理、分類整治提供理論參考。研究方法:基于一項全國百縣調查數據,對宅基地季節性和完全閑置進行比較研究,利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考察二者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季節性閑置比完全閑置更為常見,平均程度更深,村際差異也更大。中部地區農村宅基地平均閑置率最高且以季節性閑置為主,區位偏遠農村季節性閑置更為普遍。人口遷移對宅基地閑置的解釋力最強,家庭化遷移直接導致宅基地閑置;地理條件差異是形塑宅基地閑置地域分異的基礎;確權頒證發揮產權固化的作用,對兩種閑置均有促進作用;基礎設施配套完善能有效抑制完全閑置,非農就業則明顯提高季節性閑置。研究結論:季節性閑置宅基地仍發揮居住功能,不應視為資源浪費;完全閑置才是宅基地資源浪費的典型,在具體整治時應予以重點關注。
關鍵詞:宅基地閑置;季節性閑置;完全閑置;家庭化遷移;農戶調查
中圖分類號:F30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1001-8158(2023)10-0049-11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2371201,42371231)。
在中國快速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宅基地閑置現象日益普遍[1],并呈現諸多類型。21世紀以來,農村人口持續外出引起的“人去屋空”[2]和農戶家庭結構及住房需求變化造成的“舊屋棄用”,促使農村宅基地呈現存量低效利用和增量無序擴張的并存局面[3]。加之各地農村的自然、人口、經濟等條件迥然相異,閑置宅基地在程度上輕重不一,類型上不盡相同[4]。從閑置時間來看,既有農戶長期性外出、建新棄舊、無人繼承等造成的完全(永久性)閑置,也有農戶短期流動和往復進城而出現的季節性(短期性)閑置[5]。這兩種閑置類型雖然都是宅基地低效利用的情形,但在解讀宅基地閑置現象和探索閑置宅基地治理模式時不可一概而論,需要予以區分。當前,閑置宅基地再利用是中國政府推進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6],在宏觀政策制定和地方政府實踐兩個層面均進行了系統推進和積極探索,摸索出了一些富有成效的閑置宅基地整治模式。然而,受限于閑置宅基地地域差異較大、閑置類型多元、利益關系復雜,全國層面可復制可推廣的治理模式尚未形成。因此,在中國穩慎推進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準確認知農村宅基地閑置的類型特征和形成原因,既是解讀中國鄉村空間轉型過程的關鍵環節,也是科學管理、分類整治閑置宅基地的前提,可為農村建設用地的存量資源高效利用和增量需求適度滿足尋求解決之道[3]。
現有研究對閑置宅基地的概念、類型、程度和機制等進行了廣泛探討。概念界定上,閑置宅基地是指一定期限內功能沒有得到有效發揮的宅基地得到較多認同[7],但不同研究者對閑置期限的判定未達成一致[8-9]。類型劃分上,現有研究對閑置宅基地有諸多分類方式,分別從宅基地閑置時間長短(季節性閑置、完全閑置)[10]、利用狀態(真實性、潛在性、周期性等)[11]、形成原因(建新不拆舊、繼承因素、批而不建、外出務工)[12]等方面予以劃分。現狀特征上,現有研究指出中國農村宅基地閑置現象十分普遍,平均程度在10%~15%之間[10,13-14],分布格局因農村所在區 域[15]、地形和城鄉區位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8,13]。影響因素探討中,研究發現一戶多宅、舉家遷移、老宅過剩等直接導致宅基地閑置[16],地理條件、經濟發展和制度管理等因素則在更深層次影響著宅基地的利用效率[17-18]。具體地,宅基地閑置程度與地形直接相關[19],山區農村的宅基地閑置率通常高于平原農村[20]。城鄉區位對宅基地閑置也產生重要影響,因村莊到城鎮距離的不同而出現分化[21]。另外,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推進效果也會影響其閑置程度[22]。
然而,現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1)在閑置宅基地的各種分類方式中,按閑置時間分為季節性閑置和完全閑置較為常見,但現有研究尚缺乏對二者的明確區分和深入比較[10,22]。事實上,這兩種閑置現象有著本質區別:一方面,農村人口出村進城引起部分宅基地處于常年無人居住、但過年或其他節假日有人居住的季節性閑置狀態;另一方面,由于農戶永久性遷出而保留宅基地、“建新不拆舊”、老人離世宅基地無人繼承等原因使得宅基地始終呈現無人居住的完全閑置狀態。雖然二者都是宅基地低效利用現象,但閑置特征和形成原因存在顯著差異,對二者進行特征描述和原因解讀有助于加深社會各界對宅基地閑置現象的理解[23]。更重要的是,這兩種閑置對宅基地制度改革、合理處置方案及農村土地資源再開發潛力測算等方面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有必要分別考察和對比分析。(2)由于缺乏農村宅基地閑置的基本統計數據,現有研究較多基于個別區域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對全國層面的現狀認識相對較少,在各地鄉村空間轉型不同步、特征差異較大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新近調查數據來刻畫與比較二者的總體特征和地域分異。(3)現有研究針對宅基地閑置影響因素的定量考察以整體閑置情況為主,對季節性閑置和完全閑置的對比考察相對不足,不利于學術界對宅基地閑置形成機理的認知深化。
基于此,本文嘗試回答3個問題:作為兩種閑置類型,宅基地季節性閑置和完全閑置的現狀特征有何差異?二者的形成原因和機制是否存在相似性與差異性?二者在閑置宅基地整治過程中是否需要實行不同的整治策略?利用一項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調查數據,本文擬刻畫比較中國宅基地季節性和完全閑置的現狀特征;建立影響兩種宅基地閑置類型的解釋框架和計量模型,考察兩種閑置類型的驅動因素,比較二者形成原因和機制的區別;以期深入理解中國農村宅基地閑置現象,同時可能為閑置宅基地分類整治、科學管理提供一些依據。
1 分析框架
1.1 閑置分類
宅基地閑置現象不可一概而論,現有研究從閑置時間[10]、利用狀態[11]、形成原因[12]等不同角度劃分出了不同的閑置類型。相較而言,利用狀態的角度更側重于反映理論意義上的土地利用轉型過程,形成原因的角度更側重于政策實踐意義上的分類治理,而本文從閑置時間的角度進行劃分,可以較好兼顧理論與政策意義。一方面,閑置時間差異反映了不同的利用程度與功能強度,長期閑置意味著宅基地居住功能的喪失,季節性閑置則意味著宅基地居住功能的有效性,二者在不同地域的特征差異實質上反映了不同的土地利用轉型過程。另一方面,閑置時間的判斷非常直接,村干部或鄰居都可對其進行準確判斷,這對于后續的政策實踐具有重要意義,可在精準識別不同閑置類型的基礎上實施具體整治策略。因此,本文結合宅基地的閑置時間長短和功能發揮情況[8,22],將宅基地閑置現象區分為季節性閑置和完全閑置兩類。宅基地季節性閑置與人口外出密切相關[24],是指宅基地常年無人居住、但在春節等節假日有人居住,是宅基地居住功能部分發揮的情況。完全閑置則是宅基地已不再發揮居住功能,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宅基地被廢棄或批而未建,二是農房連續2年以上無人居住,春節等節假日也無人居住的棄用情況。用季節性閑置、完全閑置宅基地宗數分別與農村宅基地的總宗數取比值得到季節性閑置率、完全閑置率。
1.2 解釋框架

第一,地理條件差異是形塑閑置宅基地地域分異的重要前提[26]。一方面,地形對宅基地閑置有基礎性影響,現有研究對此有諸多討論:有研究指出平原地區有較好的人口外出優勢,季節性閑置更高,整體閑置呈平原最高、山地次之、丘陵最低的分異特征[8];但也有研究認為山區居住條件較差、生計資本脆弱,因棄舊建新和人口外遷等導致宅基地閑置的程度更 高[27],呈現山地最高、平原其次、丘陵最低的分異特 征[13];亦有研究指出丘陵地區閑置率最高、山地和平原最低[19]。另一方面,城鎮資源的輻射強度會隨城鄉距離增大而逐漸衰減,但有研究指出宅基地的利用狀態呈現出與傳統競租模型中距離衰減規律所相異的特征[21],季節性閑置更可能隨距離增加而降低,完全閑置則呈現出由“兩端”向“中間”遞減的趨勢,反映了城鄉區位對兩種閑置類型有著差異化的影響。
第二,人口遷移對宅基地閑置的影響至關重要。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人口不斷外流,逐漸引起宅基地出現閑置[28]。一方面,多數農民進城就業較易,但安家落戶更難,外出農民多為短期“擺動式”流動,促使宅基地季節性閑置[24]。另一方面,隨著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的加快,家庭化遷移情形不斷增加,進城農戶在城鎮實現永久遷移后未對留于農村的宅基地進行合理處置,將引起宅基地完全閑置[29]。
第三,經濟因素對季節性閑置和完全閑置的作用途徑不同,需進一步細致考察[18]。其一,隨著經濟條件改善,農民建房或城鎮購房的需求和能力增強,因“建新棄舊”和完全城鎮化而造成宅基地完全閑置的幾率將增加[2]。其二,某些經濟落后的地方,雖然新建房屋或購房所導致的完全閑置相對較少,但農村人口持續地非農化轉移,因農民季節性“兩棲務工”而導致宅基地季節性閑置的情況更常見[23]。其三,對于基礎設施配套完善,農村居民點用地利用轉型較好的農村,即使存在一些新建宅基地,但完全閑置宅基地得到及時騰退,完全閑置程度較輕,對季節性閑置的影響則相對較弱[26]。
第四,宅基地制度從確權頒證和退出規定兩方面影響宅基地閑置類型與程度。一方面,根據宅基地制度改革部署,進行宅基地確權頒證工作,可從法律上明確其空間范圍和權屬關系[30],為閑置宅基地整治提供制度依據。現有研究認為宅基地確權頒證會影響宅基地的利用效率,優化農村土地資源配置[31],但宅基地確權對兩種閑置的作用不同。有研究指出,宅基地確權強化了農戶的產權安全意識,確權頒證后農民更安心地參與到人口鄉城流動中,進而加深宅基地閑置程度[32-33]。也有研究認為宅基地確權降低了農戶退出完全閑置宅基地的意愿[34],由于戶籍制度改革在一些地區的具體實施中嵌入了宅基地使用權退出機制[35],遷移進城農戶為謀求更大利益,不會完全放棄農村戶口,以便在宅基地確權時繼續保留家庭在農村的宅基地權益[36]。另一方面,部分地區已開始探索實施閑置宅基地退出的具體方式,理論分析認為在制度層面明確閑置宅基地退出的相關規定和具體做法,能夠有效降低農村宅基地閑置程度[22],且對季節性閑置的影響更強。
2 數據與變量
本文的研究數據源于2021年課題組組織的中國村鎮發展動態調查,調查范圍覆蓋全國29個省(自治區、市),調查內容包括農村宅基地、耕地、人口、產業發展、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等。調查采取分層抽樣和隨機抽樣結合的方法,首先以各省級單元全覆蓋為原則,在全國范圍內抽取得到100個區縣,受2021年疫情影響,西藏和新疆的調查未能成行,對樣本區縣進行調整。然后以覆蓋城市數量最大化、平衡地形和區位為原則,將處于同一城市或距離過近的區縣進行調整,最終得到100個樣本區縣。進而在每個區縣抽取2個鄉鎮、每個鄉鎮抽取2個行政村,確保樣本鄉鎮和行政村在地形、發展水平和到縣城及鄉鎮中心距離等方面的代表性和多樣性,得到200個鄉鎮、400個行政村樣本。問卷填報人員為行政村的支書、主任或熟悉本村情況的其他兩委成員。問卷中關于閑置宅基地的問題分別為“本村的宅基地宗數”、“本村中,常年無人居住,過年也無人居住的宅基地宗數”和“本村中,常年無人居住,但過年有人居住的宅基地宗數”。經數據清洗后,得到數據完整的383個行政村樣本進行分析。
解釋變量選取如下。地理條件方面,選取地形條件,考察地形差異對宅基地閑置的影響;選取村莊到鄉鎮政府和到縣政府距離兩個指標,檢驗城鄉區位差異對兩種閑置類型的影響。人口方面,選取外出人口比例、家庭化遷移比例和外來人口比例,檢驗人口遷出、家庭化遷移、人口遷入對宅基地閑置的影響。經濟方面,選取人均可支配收入、基礎設施類型數量和非農就業比例三個指標反映經濟發展水平。其中,農村基礎設施類型包括自來水、污水管道系統、燃氣管道系統、統一集中供暖、生活垃圾收集處理、公共廁所、路燈、統一灌溉系統。制度方面,選取宅基地是否完成確權和是否有閑置宅基地退出規定兩個指標,反映宅基地制度改革落實情況對于農村宅基地閑置程度的影響。此外,參考已有研究將調研村所在區縣的城鎮化水平[13]和調研村常住人口規模[33]作為控制變量。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3 兩種閑置的比較
3.1 總體特征
3.1.1 季節性閑置比完全閑置更普遍且程度更深
根據調查結果,季節性閑置現象的出現比例(89.7%)高于完全閑置(84.4%),在廣大農村中更為常見。在有閑置現象的農村中,3.9%僅出現完全閑置現象,9.2%僅有季節性閑置。這表明與人口流出密切相關的宅基地季節性閑置,在廣大農村中更可能單獨出現。閑置程度上,宅基地平均季節性閑置率為9.1%,完全閑置率為7.0%,季節性閑置的均值高出完全閑置2.1個百分點。可見,季節性閑置較完全閑置不僅出現的頻率更高,閑置程度也更深。兩種閑置類型加總得到中國宅基地平均總體閑置率為16.1%,略高于已有研究結果[7-8,13,16,37-38]。這一結果印證了調查數據的全國代表性,也反映農村宅基地閑置程度有加深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與城鄉流動人口規模持續增加[39]、大城市落戶難度依然較大[40]等現象相符。
3.1.2 兩種類型的閑置率分布均集中于10%以內的區間,但季節性閑置的村際差異更大
借助核密度估計曲線(圖2)分析宅基地季節性閑置率和完全閑置率在調研村中的分布特征。聚集程度上,季節性閑置率低于10%的區間內聚集了70.8%的調研村,完全閑置率低于10%的區間內聚集了超過80%的調研村;雖然二者的核密度高值區均位于10%以下,但完全閑置率的核密度估計值遠高于季節性閑置率。可見,宅基地閑置現象雖然在我國農村中廣泛存在,但70%以上農村中兩種閑置的程度均低于10%。分散程度上,調研村中季節性閑置率較完全閑置率更離散,季節性閑置率最高達到67.4%;完全閑置率最高為58.8%。季節性閑置率在10%~50%區間內的村莊數量多于完全閑置率,但在50%~60%區間內的數量要更少;在核密度估計值上則表現為二者的高低交錯、前者高于后者更普遍的雙重特征。可見季節性閑置的村際差異更大,可能因為其受到人口外出的影響更強,而人口外出具有顯著的村際差異。結合已有研究結果可以推斷[2],隨著農村人口外流規模增加,首先是季節性閑置程度的加劇,進而影響農村發展動力,家庭化遷移、無人繼承和人居環境退化等引發的完全閑置現象會愈加明顯。
3.2 地域分異
3.2.1 中部地區農村宅基地閑置率最高,且季節性閑置尤為突出
按照東、中、西的區域劃分,農村宅基地平均閑置率分別為13.6%、19.2%和15.3%(圖3)。與全國對比,東部地區季節性閑置率和完全閑置率均低于全國水平,前者低出2.2個百分點,后者低出0.3個百分點。中部地區閑置率最高,雖然季節性閑置率和完全閑置率均高于全國水平,但前者高出2.8個百分點,后者僅高出0.3個百分點,季節性閑置是中部地區整體閑置率高的主要體現。西部地區季節性閑置率和完全閑置率均略低于全國水平,與全國的差距不到1個百分點。區域差異上,東部和西部地區主要體現為季節性閑置的差別,完全閑置現象的東西部差距較小。可見,宅基地閑置的區域格局呈現與全國人口遷移格局類似的“中部塌陷”特征,結合已有研究可推斷[41],中部地區宅基地季節性閑置最突出與該地區鄉城遷移人口增速最快有關。

3.2.2 山地和丘陵農村中兩種閑置程度均高于平原
借助箱線圖(圖4)比較平原、丘陵和山地農村宅基地閑置程度及其分布狀況的差異。閑置程度方面,山地和丘陵農村的季節性閑置率相近,二者均高于平原;山地的完全閑置程度最深,丘陵次之,平原最低。這表明在自然資源稟賦差、土地人口承載力低、交通不便的山地地區,宅基地季節性和完全閑置的程度均較嚴重。分布狀況方面,三類地形中季節性閑置的波動均大于完全閑置,表明季節性閑置在村莊間差異性更大。各類地形中的宅基地閑置狀況均存在一些離群值,值得指出的是,山地和丘陵的季節性閑置程度接近,但丘陵地區有更多的離群值。這表明山地農村季節性閑置程度普遍較高,而丘陵地區的季節性閑置更可能受某些離群值的影響。可見,丘陵和山地的宅基地閑置程度要高于平原,受離群值影響,山地和丘陵地區季節性閑置率的波動幅度更大。
3.2.3 距縣城越遠宅基地閑置程度越高,到鄉鎮距離與宅基地閑置的相關關系較弱
城鄉區位反映城鎮對農村輻射作用的大小,距縣城越遠宅基地閑置程度越深,距鄉鎮距離與宅基地閑置的相關關系較弱(圖5)。一方面,城市資源輻射能力隨城鄉距離增大而衰減,農民到距離村莊較近的城鎮工作和生活,更能兼顧進城居業和返村維系鄉緣,宅基地閑置的程度相對較低;區位較遠村莊獲取城市資源輻射不足,農民進城居業更可能是遠距離、長時間,因而宅基地閑置程度更深[10]。另一方面,與鄉鎮相比,縣城提供更多更完善的就業崗位和公共服務資源,農民就近就業學習、就醫養老的首選往往是本縣縣城,更傾向于到縣城租房或購房,從而閑置村內宅基地。
3.3 影響因素
表2報告了宅基地季節性、完全閑置的回歸結果。經檢驗,所有模型中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小于2,不存在明顯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模型1— 模型10考察了地理條件、人口遷移、經濟因素、宅基地制度等分別納入和全部納入模型時對宅基地季節性、完全閑置的影響。此外,采用COHEN等提出的統計方法[42-43],構建季節性閑置與完全閑置差值為因變量,納入所有自變量進行回歸,以比較某一變量對兩種閑置的影響差異(表3)。所有模型均控制了調研村所在區縣城鎮化水平和村莊人口規模。
全國層面上,各因素對宅基地季節性和完全閑置的影響既有相似性,也存在差異。一方面,人口遷移、地理條件和宅基地制度雖然都對兩種閑置產生一定影響,但解釋力逐漸降低。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對兩種閑置類型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基礎設施配套對季節性閑置的影響顯著弱于完全閑置,非農就業對季節性閑置的影響要強于完全閑置。
人口遷移對宅基地閑置的解釋力最強,家庭化遷移將直接導致宅基地閑置,人口遷入對兩種閑置程度均有減緩效應。首先,計量結果表明人口遷移相較其他因素的解釋力更強,這是由于人口遷出、遷入和家庭化遷移均會直接影響宅基地的利用效率,是宅基地閑置與否的關鍵。其次,人口遷出對兩種閑置的影響有差異,能顯著促進季節性閑置而對完全閑置的影響不明顯。一方面,外出人口中包含了往復就業、就學和就醫等短期性、獨自遷移人口[10],他們家庭中仍有人留守,因此宅基地并不會閑置。另一方面,家庭所有成員雖然長期外出,但仍然“城鄉兩棲”,在過年等節假日仍會返回,此類情形會引起宅基地季節性閑置,對完全閑置則無明顯影響。再者,家庭化遷移意味著農戶舉家遷出,無論是臨時性還是長期性的家庭化遷移,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已部分或完全喪失,均會出現閑置。最后,農村有較多外來人口時,不僅避免了部分宅基地的閑置,也表明該類農村具有人口吸引力優勢,“人去屋空”的現象更少。以上結果印證了已有研究關于人口結構變化會引起宅基地閑置的論斷[2],表明了鄉城人口遷移從單人遷移到家庭化遷移的模式轉變深刻影響著宅基地從季節性到完全閑置的動態過程,同時在人口遷出、家庭化遷移和人口遷入等方面解釋了人口變化對兩種閑置的影響差異。

地理條件對宅基地閑置具有基礎性影響,引起宅基地閑置程度的地域分異。地形作為村莊稟賦條件的重要反映,對于兩種閑置類型都有顯著的影響,山地和丘陵地區對二者的影響均高于平原,且山地對完全閑置的影響尤為明顯。這一結果對現有研究既有印證,亦有補充。印證了山地農村居住條件欠佳和宅基地管理粗放會加快人口流失、增加“建新不拆舊”的情形,進而加劇宅基地閑置程度的結論[8];補充了平原地區在全國總體上季節性閑置、完全閑置均最低的新發現。縣城較鄉鎮能提供更多更完善的就業、教育、醫療等資源,更能吸引農民到縣城居住就業,因而距縣城越遠對宅基地閑置的影響越明顯,且優先促進季節性閑置。
宅基地確權頒證對兩種閑置類型均有正向提升效應。一方面,進行確權頒證有助于強化村民的宅基地權益意識,增加農民對宅基地“私有”的認知強 度[32]。對進城農民而言,確權頒證會提升其對于宅基地的價值預期,起到產權固化作用,在非農收益與農村權益兼得的心理下[36],他們會更加“珍惜”宅基地而不愿退出閑置。另一方面,宅基地確權頒證是在“一戶一宅”的原則下進行空間和權屬認定的,但在農村違規建房、一戶多宅等現象頻發的前提下[30],這部分宅基地更可能被視為閑置。
如表3所示,經濟因素對兩種閑置有差異化影響,體現為基礎設施配套和非農就業兩方面。基礎設施配套完善能有效降低宅基地完全閑置程度,與季節性閑置無明顯關聯。一方面,基礎設施建設是改善鄉村人居環境的關鍵[8],反映其生活功能的強弱。基礎設施建設落后、人居環境欠佳,村民更可能完全搬離,造成宅基地的完全閑置。另一方面,基礎設施建設與人口外出的相關性不強,季節性閑置是由農戶季節性、短期性外出決定的,與基礎設施建設是否完善并無直接聯系。
非農就業明顯提升宅基地季節性閑置率,但對完全閑置的影響較弱。農民離村進城從事非農工作,勢必引起與宅基地間粘度關系的松動,會優先促進季節性閑置[10]。模型估計結果顯示,農村非農就業比例與宅基地完全閑置率無顯著相關關系。這表明農民外出從事非農工作,會引起宅基地季節性閑置,但并不意味著進城農民會完全閑置宅基地。進城務工農民仍需要宅基地作為返鄉居所和鄉愁寄托[23],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仍十分重要。
4 結論與討論
伴隨中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農村宅基地閑置現象普遍。本文基于全國農村抽樣調查數據,對宅基地季節性和完全閑置進行比較,主要結論如下:(1)季節性閑置比完全閑置更常見且程度更深,村際差異也更大。(2)中部地區宅基地季節性閑置最為突出,山地和丘陵地區兩種閑置程度均高于平原,距縣城越遠季節性閑置程度明顯更高。(3)人口遷移對宅基地閑置的解釋力最強,人口遷出優先促進季節性閑置,家庭化遷移直接導致宅基地閑置;地理條件對宅基地閑置起著基礎性影響,引起宅基地閑置程度出現地域分異;宅基地確權頒證對兩種閑置類型均有正向提升效應。經濟因素對兩種閑置有差異化影響,基礎設施配套情況對季節性閑置的影響顯著弱于完全閑置,非農就業對季節性閑置的影響顯著強于完全閑置。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文發現宅基地季節性閑置和完全閑置雖都是宅基地低效利用的現象,但在總體特征、地域分異和影響因素3方面區別較大,不可將二者同等視為土地資源浪費現象。一方面,當前全國宅基地閑置以季節性閑置為主,這與農民進城務工、謀求生計密切相關。農民工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和城鎮化進程做出重大貢獻,一旦農民工被殘酷的市場淘汰,需要宅基地作為重要的回鄉保障,季節性閑置的宅基地雖然只發揮短期的居住功能,但對農民在村權益的保障仍十分重要。因此,對于農民進城務工所導致的季節性閑置不可直接等同于宅基地浪費[44]。另一方面,宅基地完全閑置才是造成農村土地資源浪費的關鍵所在,這不僅包括“建新不拆舊”、繼承宅基地閑置、批而未建、違規建造等農村宅基地管理行為造成的宅基地始終無人使用現象,還包括農戶已實現家庭化遷移但并不退出已完全閑置宅基地的情形。這些完全閑置的情形正是農村宅基地資源浪費的典型表現,在具體整治時應當予以重點關注。
當前,中國宅基地閑置現象并不局限于某些地區,而是廣泛出現于各地農村。在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的政策引領下,科學整治農村閑置宅基地既關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推進效果和總體成效,又涉及到鄉村振興用地保障和總體目標的實現。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形成如下政策思考:第一,閑置宅基地整治時需按差異化、精細化、精準化的思維分類推進,對于季節性閑置程度較高的農村應創造更多就近非農就業機會,進一步完善農村各項基礎設施,減緩或避免季節性閑置向完全閑置轉變。第二,根據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中的“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對季節性閑置情況可適當鼓勵進行使用權流轉,對完全閑置情況可優化使用權退出的補償政策。第三,重點鼓勵家庭化遷移農戶自愿退出已完全閑置的宅基地,避免出現宅基地已完全閑置但仍無法處置的情形,注意區分宅基地暫時性退出(使用權流轉)和永久性退出(使用權、資格權放棄)兩種情形,并在退出程序、補償保障、退后利用等方面加以明確。
此外,本文仍有一些不足之處。第一,中國鄉城人口遷移是一個多階段的過程,在從流動到定居以及落戶的過程中,人口遷移不同階段對于宅基地閑置的影響有待進一步分析[45]。第二,宅基地閑置歸根結底是農戶對于村內宅基地的利用行為結果[46],本文關注村莊層面匯總的宅基地閑置現象,下一步研究仍需補充農戶的決策機制分析。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劉彥隨, 劉玉, 翟榮新. 中國農村空心化的地理學研究與整治實踐[J] . 地理學報,2009,64(10):1193 - 1202.
[2] 劉彥隨. 中國鄉村發展研究報告: 農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M] .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46 - 50.
[3] LIU T, LIU H, QI Y J.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and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urbanizing China: insights from national land surveys, 1996-2006[J] .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5, 46: 13 - 22.
[4] 周靜. 農村宅基地的閑置與轉型方向[J] .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40(2):176 - 189.
[5] 張勇,周麗,賈偉. 農村宅基地盤活利用研究進展與展望[J] .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20,25(6):129 - 141.
[6] 孫曉勇. 宅基地改革:制度邏輯、價值發現與價值實現[J] . 管理世界,2023(1):116 - 127.
[7] 祁全明. 我國農村閑置宅基地的現狀、原因及其治理措施[J] . 農村經濟,2015(8):21 - 27.
[8] 李婷婷,龍花樓,王艷飛. 中國農村宅基地閑置程度及其成因分析[J] . 中國土地科學,2019,33(12):64 - 71.
[9] 史衛民,曹姣. 論農村閑置宅基地與農房收儲的制度構建[J] . 經濟縱橫,2021(10):114 - 121.
[10] 楊志鵬,許嘉巍,王士君. 東北地區農村宅基地閑置特征及影響因素研究——基于公主嶺市6鄉鎮實地調研數據[J] .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21,42(7):84 - 92.
[11] 趙立元,王興平,朱凱. 大都市地區農村住宅閑置的類型與多尺度空間特征——基于南京樣本的實證[J] . 現代城市研究,2021(12):12 - 18.
[12] 魏暉,鞏前文. 農村宅基地閑置的主要類型及分類治理對策[J] . 世界農業,2020(10):13 - 19.
[13] 宋偉,陳百明,張英. 中國村莊宅基地空心化評價及其影響因素[J] . 地理研究,2013,32(1):20 - 28.
[14] 宇林軍,孫大帥,張定祥,等. 基于農戶調研的中國農村居民點空心化程度研究[J] . 地理科學,2016,36(7):1043 - 1049.
[15] SHAN Z Y, FENG C C. The redundancy of residential land in rural China: the evolution process, current statu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 Land Use Policy, 2018, 74: 179 - 186.
[16] 艾希. 農村宅基地閑置原因及對策研究[J] .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5):74 - 77.
[17] 龍花樓,李裕瑞,劉彥隨. 中國空心化村莊演化特征及其動力機制[J] . 地理學報,2009,64(10):1203 - 1213.
[18] 楊亞楠,陳利根,龍開勝. 中西部地區農村宅基地閑置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甘肅的實證研究[J] . 經濟體制改革,2014(2):84 - 88.
[19] ZHOU T, JIANG G H, LI G Y, et al. Neglected idle rural residential land(IRRL)in metropolitan suburb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J]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78: 163 - 175.
[20] ZHOU T, JIANG G H, MA W Q, et al. Dying villages to prosperous villages: a perspective from revitalization of idl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RRL)[J]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4: 45 - 54.
[21] 高金龍,劉彥隨,陳江龍. 蘇南地區農村宅基地轉型研究:基于利用狀態的視角[J] . 自然資源學報,2021,36(11):2878 - 2891.
[22] 郭君平,仲鷺勍,曲頌,等. 宅基地制度改革減緩了農房閑置嗎?——基于PSM和MA方法的實證分析[J] . 中國農村經濟,2020(11):47 - 61.
[23] 賀雪峰. 論農村宅基地中的資源冗余[J] . 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4):1 - 7.
[24] 桂華,賀雪峰. 宅基地管理與物權法的適用限度[J] . 法學研究,2014(4):26 - 46.
[25] 張佰林,張鳳榮,曲衍波,等. 宅基地退出與再利用研究熱點與展望[J] . 資源科學,2021,43(7):1277 - 1292.
[26] 賈寧鳳,白怡鴿,喬陸印,等. 農村閑置宅基地空間分異及其驅動因素——以山西省長子縣為例[J] . 經濟地理,2020,40(12):166 - 173.
[27] LI P X, GAO J L, CHEN J L.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ecological stress of construction lands by quantity and location: case study in Southern Jiangsu, Eastern China[J] .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20, 22(2): 1559 - 1578.
[28] 郭遠智,周揚,劉彥隨. 中國農村人口外流的時空演化及其驅動機制[J] . 地理科學,2020,40(1):50 - 59.
[29] 金細簪,周家樂,儲煒瑋. 三權改革背景下土地權益與農民永久性遷移分析——來自浙江4個縣市4個行政村的實證[J] . 人口學刊,2019,41(5):101 - 112.
[30] 郭君平,仲鷺勍,曲頌,等. 抑減還是誘致:宅基地確權對農村違法占地建房的影響[J] . 中國農村經濟,2022(5):72 - 88.
[31] 張清勇,劉守英. 宅基地的生產資料屬性及其政策意義——兼論宅基地制度變遷的過程和邏輯[J] . 中國農村經濟,2021(8):2 - 23.
[32] 吳郁玲,石匯,王梅,等. 農村異質性資源稟賦、宅基地使用權確權與農戶宅基地流轉:理論與來自湖北省的經驗[J] . 中國農村經濟,2018(5):52 - 67.
[33] 王良健,吳佳灝. 基于農戶視角的宅基地空心化影響因素研究[J] . 地理研究,2019,38(9):2202 - 2211.
[34] XU H Z, LIU Y X.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impac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on peasants willingness to return rural residential lands: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in rural China[J] . Panoeconomicus, 2016, 63(1): 135 - 146.
[35] 張力,楊秋宇. 戶籍改革中嵌入農民退出地權機制的合規化分析——以溫江“雙放棄”模式為考察對象[J] . 農村經濟,2013(10):3 - 7.
[36] 陳思創,曹廣忠,劉濤. 中國農業轉移人口的戶籍遷移家庭化決策[J] . 地理研究,2022,41(5):1227 - 1244.
[37] 陳錫文. 從農村改革四十年看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J] . 行政管理改革,2018(4):4 - 10.
[38] LI J, GUO M, LO K. Estimating housing vacancy rates in rural China using power consumption data[J] . Sustainability, 2019, 11(20). doi: 10.3390/su11205722.
[39] 周皓. 中國人口流動模式的穩定性及啟示——基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數據的思考[J] . 中國人口科學,2021(3):28 - 41.
[40] 劉濤,劉嘉杰,曹廣忠. 中國城市人口戶籍遷移的估算及時空特征——新型城鎮化的落戶政策導向[J] . 地理科學,2021,41(4):553 - 561.
[41] 劉濤,彭榮熙,卓云霞,等. 2000—2020年中國人口分布格局演變及影響因素[J] . 地理學報,2022,77(2):381 - 394.
[42] COHEN J, COHEN P, WEST S G, et al.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M] . Mahwah, N. J: L. Erlbaum Associates, 2003: 30 - 40.
[43] LI X X, HSIEH J J P, RAI A. Motivational differences across post-acceptance information system usage behaviors: an investigation in the business intelligence systems context[J] .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13, 24(3): 659 - 682.
[44] 劉銳. 農村宅基地性質再認識[J] .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4(1):75 - 82.
[45] GAO J L, CAI Y Y, LIU Y S,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underutilization of rural housing land in China: a multi-level modeling approach[J]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89: 73 - 81.
[46] GAO X S, XU A Q, LIU L, et al. Understanding rural housing abandonment in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J] .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7, 67: 13 - 21.
Comparing Seasonal and Perennial Under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of 100 Counties
HU Mingfeng1,2,3, CAO Guangzhong1,2,3, LIU Jiajie1,2,3, LIU Tao1,2,3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Center for Urban Future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Protection,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accurately identify the types of underuse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to compar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discriminating governanc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as follows. Based on a national survey of 100 counties, seasonal and perennial under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re compared,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easonal underuse is more common and deeper than perennial underuse. The highest rate of underuse is the central region dominated by seasonal underuse, and seasonal underuse is more common in remote villages. Population migration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and family migration directly leads to underuse.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are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shaping the geographical variation of underuse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he issuance of certificates has served to solidify property rights, which contributes to both types of underuse. The improved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are more effective in curbing perennial underuse, while off-farm employ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seasonal underuse. It concludes that seasonal under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still serves a residential function and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the waste of resources. Perennial underuse is the typical wast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esources, and should be given governance priority.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ial land; seasonal underuse; perennial underuse; family migration; rural household survey
(本文責編:陳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