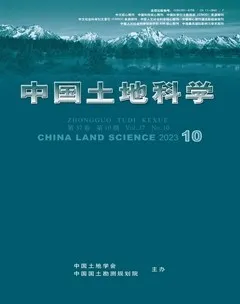家庭化遷移對農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
蔡俊 雷蕾 劉道壘 王偉業 項錦雯



摘要:研究目的:探究農民工家庭化遷移對宅基地退出意愿影響及城市融入的中介作用,為完善新型城鎮化機制和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參考。研究方法:基于新遷移經濟學理論構建理論分析框架,利用珠三角6個核心地市的典型調研數據,采用有序Logit模型、中介效應模型實證研究假說。研究結果:(1)家庭化遷移顯著提升農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2)城市融入4個維度中介效應顯著,中介效應占比排序為:心理融入>經濟融入>社會融入>居住融入,其中,居住融入最弱并呈現“遮掩效應”;(3)不同代際遷移階段以及宅基地退出模式中, 4個維度中介效應呈現次序分異。研究結論:從深化城鄉聯動改革、健全城市融入機制和公共服務體系、差別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入手,完善新型城鎮化機制與宅基地退出政策。
關鍵詞:家庭化遷移;城市融入;宅基地退出意愿;代際遷移;退出模式;中介效應
中圖分類號:F30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158(2023)10-0060-11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71203054);安徽建筑大學城市管理研究中心開放課題(2022ZR001);安徽省住房城鄉建設科學技術計劃項目(2023-RK035)。
國家新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驅動了農民工市民化、城市擴張與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也導致了農村宅基地閑置、空心村與農村留守等“農村病”[1-2]。2021年底,全國進城農民工總量29 251萬人,其中在城鎮居住的進城農民工13 309萬人[3],而進城農民工的農村宅基地依然保留現象使得農村建設用地呈現“人減地增”的態勢,造成了農村宅基地閑置與城市建設用地剛性供給不足并存[2]。據統計,全國農村宅基地平均閑置率為13.17%,個別村莊高于30%[4-5]。引導農民工自愿有償退出宅基地,對盤活農村閑置宅基地、實現農民工宅基地資產權益訴求、彌補城市建設用地供給不足具有重要意義。早在2015年,國家就在33個縣試點推行農戶自愿有償參與宅基地退出制度改革[6];自2018—2023年,每年中央一號文均明確要求各地穩慎推進進城落戶的農民工依法自愿有償退出宅基地。
相關調查結果表明,超過八成的進城農民工以家庭化模式離村進城[7-8],家庭化遷移已經成為農民工進城的主要態勢,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并逐步融入城市社會,轉變為市民,“農民—農民工—家庭化遷移—市民”逐漸成為一種常態。與此同時,家庭化模式離村進城農民工對宅基地居住與社會保障功能依賴減弱,為增強市民化資本,期望實現宅基地資產功能訴求日益強烈[2,9]。為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及市民化,鼓勵農民工自愿有序退出宅基地,國家發展改革委在《2022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中倡導農民工舉家遷移,并具體指示各地從城鎮住房、戶籍、子女教育、醫療社保與勞動技能補貼性培訓等方面提高農民工城市融合度與市民化質量,依法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工的農村“三權”,健全市場化退出機制[10]。在此背景下,探索農村家庭離村進城以及城市融入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對穩步推動宅基地退出與健全新型城鎮化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學術界對于農民工城市融入顯著影響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問題關注度較高[2,4],學者們主要從鄉土依戀與城市經濟融入[4]、退出補償與產權保有政策[11]、土地收益與生計資本[9,12]、非農就業與社保種類[13]、全退出與半退出模式[14-15]等視角,運用計劃行為理論[11]、成本收益理論[15-16]、結構方程模型[4]、中介效應模型[17]等理論模型進行深入探索。現有研究表明,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持續深化對宅基地退出提出了現實需求[4,18],但多數研究是基于城鎮住房[19]、身份認同[20]、非農收入[4]等城市融入的單一維度,分析其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同時,也有文獻綜合經濟、社會、心理等[18,21]多維度實證其影響,但探究城市融入各維度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機理還不夠深入。現有研究為農民工城市融入影響宅基地退出意愿提供了證據。然而,農民工城市融入不僅僅是個人,家庭融入才是目標,由于家庭城市融入是一個動態過程[22],農民工家庭成員的漸進式隨遷,住房[19]、經濟收入[23]、教育[24]、社會福利[25]、心理[26]等城市融入維度必然發生改變,這也勢必影響宅基地退出意愿。不同代際家庭化遷移階段、不同宅基地退出模式,給城市農民工家庭帶來的福利與支出有明顯差異[14],造成其城市融入程度不同,進而形成差異化的宅基地退出意愿[9]。在家庭化遷移已經成為農民工進城的主要態勢背景下,現有研究尚未能將農民工家庭化遷移過程納入到城市融入與宅基地退出意愿影響機理分析框架中。
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實證農民工家庭化遷移對宅基地退出意愿影響及城市融入的中介作用。本文的可能邊際貢獻:第一,試圖驗證農民工家庭化遷移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第二,嘗試深入分析城市融入的居住、經濟、社會與心理融入4個維度對宅基地退出意愿影響的中介效應。第三,企望分析不同代際家庭化遷移階段、不同宅基地退出模式中,城市融入4個維度的中介作用。
1 理論分析與假說
傳統遷移經濟學認為勞動力遷移的首要決策要素是個體工資差異,而新遷移經濟學指出勞動力遷移的決策要素不僅是個人因素,而且是家庭因素[22,25]。顯然,農村家庭化遷移與家庭城市融入會改變家庭資產結構與環境條件,也會改變其對宅基地退出政策認知,以及宅基地退出凈收益預期。因此,家庭化遷移與城市融入是農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決策模型中的核心影響要素。基于此,本文在新遷移經濟學基礎上,構建“家庭化(代際)遷移→城市融入→宅基地退出(模式)意愿”的農民工決策模型。
1.1 家庭化遷移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
在農民工決策模型中,宅基地退出意愿與家庭化遷移的演變過程密切相關。現有研究表明,農民工家庭化遷移是漸進式的,一般經歷二代家庭成員直至三代遷移過程,具體按照先配偶、后子女、最后老人的3個遷移階段[7-8,25]。不同的家庭化遷移階段,農民工家庭面臨的城市融入壓力、宅基地功能依賴與退出意愿呈現顯著差異。具體來講:第一階段是配偶隨遷進城務工。在這一階段,家庭未成年子女和老人留守農村,夫妻城市生活經濟壓力較小,家庭依賴宅基地居住功能,農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弱,即使有退宅進城意愿,也會等到子女隨遷完成后付諸行動。第二階段是家庭未成年子女隨遷進城,老人留守農村。在這一階段,未成年子女遷移使得核心家庭遷移完成,家庭城市生活經濟壓力變大,農村宅基地部分閑置,期望實現宅基地資產功能以增強城市融入力訴求增強。但是,農民工進城失敗的風險,對其宅基地退出意愿產生了一定的削弱作用[4]。第三階段是老人遷移至城市。在這一階段,農民工家庭城市生活穩定且經濟能力強,足以解決家庭留守以提升家庭福利[7],舉家離村進城及宅基地退出意愿強烈。
因此,提出研究假說1:農民工家庭化遷移正向影響宅基地退出意愿。
1.2 城市融入的中介作用分析
在農民工決策模型中,宅基地退出意愿與家庭化遷移及城市融入的演變過程密切相關,同時,家庭化遷移又作用于城市融入。現有文獻深入實證了農民工家庭化遷移對城市融入的積極影響,借鑒這些成果,從居住、經濟、社會及心理融入4個維度,分析農民工家庭化遷移對城市融入的影響[7-9,25]。具體來講:(1)居住融入。在農民工家庭化遷移初始階段,家庭城市融入度不高,城市居住條件相對農村下降,但是農民工家庭生活生產重心在城市,對農村宅基地居住與社會保障功能依賴下降[5],實現宅基地資產功能以提升城市融入資本訴求積極。因此,居住融入度下降,而宅基地退出意愿上升。隨著家庭化遷移推進,家庭經濟融入能力增強,足以購買城市住房,居住融入度上升[24],宅基地退出意愿也上升。(2)經濟融入。隨著家庭成員遷移入城,家庭成員分工細化[9],家庭經濟功能增強,家庭收入、長久就業及物價適應等經濟融入能力也隨之提升。(3)社會融入。隨著配偶、子女以及老人的隨遷入城,農民工感知到城市教育、醫療養老以及參與社會活動等公共資源供給服務的公平,社會融入感提升[22]。(4)心理融入。隨著家庭成員的遷移入城,一方面消除了家庭離散的痛苦,另一方面城市家庭歸屬、社交尊重與生活幸福感知增強,農民工城市心理融入感提升。總之,農民工家庭化遷移積極影響了城市融入,城市居留意愿與宅基地退出意愿增強[4,20];反之,如果農民工家庭化遷移加重了城市居住、經濟、社會、心理負擔,城市融入失敗,農民工家庭就會“進城后返鄉”,宅基地退出意愿減弱[16]。綜上,農民工家庭化遷移通過城市融入對宅基地退出意愿產生作用。
據此,提出研究假說2:城市融入在家庭化遷移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過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1.3 不同代際遷移階段與宅基地退出模式中的異質性分析
家庭成員漸進式遷移過程中,一般經歷二代家庭成員直至三代遷移過程,不同家庭成員離村進城后,為家庭城市融入帶來不同維度的福利與支出[8],同時,對宅基地功能依賴呈現分異,進而產生差異化宅基地退出意愿。
由此,提出研究假說3:不同代際遷移階段,城市融入4個維度的中介作用差異顯著。
梳理現有宅基地退出補償方式[27-28],可以歸納為2種主體補償方案,其一,經濟補償(貨幣或城市安置房)、社會保障與就業培訓等綜合補償方案(即“經濟補償+”),這一補償方案對應的是宅基地全退出模式。全退出模式凸顯了宅基地資產功能屬性,能夠一定程度增強農民工家庭城市融入資本。其二,農村新區安置地塊、部分經濟補償(部分貨幣或重建中高密度農村住房)、社會保障與就業培訓等綜合補償方案(即:“農村新區安置地塊+部分經濟補償+”),這一補償方案對應的是宅基地半退出模式[14,27]。半退出模式顯化了宅基地資產與居住社會保障功能的綜合屬性,農民工家庭既能獲得部分經濟補償以增強城市融入資本,也為翻修老宅、進城失敗、“鄉土依戀”提供居住社會保障。兩種宅基地退出模式,凸顯不同的宅基地功能屬性。
不同家庭成員離村進城后,城市融入及宅基地功能依賴呈現分異,進而,宅基地退出模式的偏好異化。反之,不同宅基地退出模式中,城市融入4個維度在家庭化遷移對退出模式決策作用過程中的中介作用差異顯著。
依此,提出研究假說4:不同宅基地退出模式中,城市融入4個維度的中介作用差異顯著。
綜上,構建“家庭化(代際)遷移→城市融入→宅基地退出(模式)意愿”的理論分析框架圖1。
2 數據來源、變量界定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珠三角利用產業、區位等優勢深度參與全球生產分工,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成為中國城市群中流動人口大量集聚典型區,隨著珠三角城市產業高級化、城市融入機制完善、公共服務質量提升等,更多省內外農民工通過積分入戶等方式轉化為戶籍人口,因此,以珠三角6個核心城市農民工遷移家庭為調研對象。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21年9—11月在珠三角6個核心城市 (廣州、佛山、深圳、東莞、珠海、中山,非戶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分別是46.23%、49.64%、64.45%、73.56%、40.01%和55.51%,數據來源于廣東省統計年鑒(2022年) 進行的農民工問卷調查。依據研究目的,借鑒相關文獻[7-8,22],調研家庭樣本包括三類在城市穩定工作生活家庭(6個月以上):已生育夫妻、夫妻攜未婚子女二代家庭、夫妻攜未婚子女和父母三代家庭。按照各城市非戶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分層分配各城市問卷調研數量,結合隨機抽樣(每個城市不低于30%樣本量)和滾雪球抽樣方法,共發放問卷 2 010 份,得到有效問卷1 992份。
整理問卷并統計樣本概況,單獨一人126戶(占比6.32%);夫妻453戶(占比22.74%);夫妻攜未婚子女或之一的二代家庭1 066戶(占比53.52%);夫妻攜未婚子女和父母三代家庭347戶(占比17.42%),其中包括子女之一和父母之一,家庭化遷移率達93.68%。愿意退出宅基地960戶(占比48.20%),其中,全退出模式324戶(占比16.26%);半退出模式戶636戶(占比31.91%)。
2.2 變量設定與描述性統計
(1)被解釋變量。退出意愿(Y)、全退出模式(Y1)與半退出模式(Y2)。
(2)核心解釋變量。借鑒現有研究從遷移規模、結構與模式等方面衡量家庭化遷移[7-8,22,24],本文從家庭遷移人數(X)、二代家庭成員遷移(X1)與三代家庭成員遷移(X2)測度家庭化遷移。
(3) 中介變量。關于城市融入(M)的測度,借鑒相關文獻[4,8,10,22,25],從居住、經濟、社會、心理融入等4個維度綜合表征并進行因子分析,指標設置見表1。信度和效度檢驗結果顯示,Cronbachs為0.815,大于0.7,信度較好;KMO為0.708,大于0.6,效度較好;Bartlett球形檢驗P值為0.000,在1%的水平下顯著,適合做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固定提取4個因子,依據成分得分矩陣,將提取的4個因子分別命名為心理、經濟、社會與居住融入,方差貢獻率分別為29.25%、25.36%、16.35%、11.87%,累計方差貢獻率為82.83%。以各個因子的貢獻率為權重,分別計算城市融入4個維度及綜合得分。
(4)控制變量。變量的設定及具體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2.3 研究方法
2.3.1 有序Logit模型

3 實證分析
3.1 基準回歸
為保證模型估計結果的可靠性,對解釋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VIF值均小于2,說明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明顯共線性問題。運用STATA27進行Logit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表2顯示,模型(1)中,家庭遷移人數(X)系數通過顯著性檢驗(P<0.01),表明家庭成員遷移規模的增加顯著增加了宅基地退出意愿概率。故假說1得到驗證。模型(2)中,X及M系數皆通過顯著性檢驗(P<0.01),且X系數值有所下降,這表明家庭化遷移與城市融入共同促進了宅基地退出意愿提升。模型(3)中,X作用于M系數通過顯著性檢驗(P<0.01),綜合模型(1)與模型(2)結果,這表明城市融入在家庭化遷移對宅基地退出意愿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
3.2 穩健性檢驗
3.2.1 測量誤差穩健性檢驗
運用調整樣本量結合改變估計方法,以檢驗測量誤差可能對基準估計結果穩健的影響。首先,刪除家庭遷移人口1人的樣本126,調整后的樣本量為1 866,Logit模型估算結果為模型(1)—模型(3)。其次,將宅基地退出意愿(Y)調整為二值響應變量,同時,將城市融入(M)與均值比較后,離散化為0、1二值響應變量,運用二值響應Probit模型進行估算,結果為模型(4)—模型(6)。表3為調整家庭遷移變量樣本和Probit估計的結果,模型(1)—模型(6)均表明家庭遷移與城市融入顯著增強了宅基地退出意愿,因此,表2估計結論具有穩健性。
3.2.2 內生性檢驗
考慮到變量因果倒置、遺漏或不充分可能導致內生性問題,采取工具變量法檢驗。鑒于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有序變量,同時,CMP模型對多階段內生性偏誤的解釋較為有效、可選擇被解釋變量為有序變量或二元變量等較為靈活的方程形式[29]。因此,采取 CMP模型進行內生性檢驗。
選取農民工“農村承包地流轉率”作為“家庭遷移人數”的工具變量,理由如下:農民工“農村承包地流轉率”是家庭離開農業土地而進城務工的重要前提,進而決策家庭遷移人數,同時,“農村承包地流轉率”對宅基地退出意愿與“城市融入”并不產生直接影響。選取農民工“年均回農村次數”作為“城市融入”的工具變量,理由如下:農民工“年均回農村次數”是測度“城市融入”成功如否的反向重要指標,同時,“年均回農村次數”對宅基地退出意愿并不產生直接影響。運用CMP檢驗結果見表4。
由表4可知,模型(1)中atanhrho_12值通過了內生性顯著檢驗(P<0.01),表明工具變量方程和主方程誤差項的相關性顯著不為 0,即“家庭遷移人數”的內生性顯著。“農村承包地流轉率”的系數顯著為正(P<0.01),表明其能夠較好的解釋“家庭遷移人數”。同理,模型(2)—模型(3)分別驗證了“城市融入”與“家庭遷移人數”的內生性顯著,同時,兩者分別能被“年均回農村次數”與“農村承包地流轉率” 較好的解釋。此外,第二階段的模型(1)—模型(3)估計結果顯示,“家庭遷移人數” “城市融入”的系數正負方向和顯著性方面與表2中模型(1)—模型(3)的結果一致,驗證了前文結論的穩健性。
3.3 城市融入的中介效應分析
在全樣本中,運用逐步回歸法檢驗城市融入4個維度的中介效應。結果見表5。
表5顯示:(1)X→Y總路徑c與直接路徑c′皆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0.01),假說1進一步得到驗證。(2)X→MR→Y、X→ME→Y、X→MS→Y與X→MP→Y的間接路徑系數a、b分別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0.05或P<0.01),因此,城市融入間接效應顯著,假說2得到驗證。中介效應占比排序為:MP(21.7%)>ME(16.8%)>MS(11.5%)>MR(9.2%),其中,MR最弱并呈現“遮掩效應”,即居住融入度下降,而宅基地退出意愿上升。這可能的解釋是:(1)農民工之所以漸進式家庭化遷移,進而融入城市,并有意愿退出宅基地,主要驅動力是其城市心理融入主觀意愿積極,城市相對于農村工資收入的優勢。(2)一方面,子女、父母等親屬隨遷提升了農民工家庭教育、醫療、社會活動機會公平感知;另一方面,親屬隨遷也擴大了家庭生活、教育醫療、養老及社會活動開支,社會融入壓力加大,而且也加劇了居住融入壓力。兩方面交織作用下,社會與居住融入作用相對弱;(3)城市居住條件相對農村呈現下降,但是農民工家庭生活生產重心在城市,期望退出宅基地以提升城市融入資本訴求積極。因此,居住融入最弱并呈現“遮掩效應”。
3.4 異質性分析
3.4.1 不同代際遷移階段的異質性分析
以單獨遷移及配偶隨遷樣本為參照,運用逐步回歸法檢驗二代與三代家庭成員遷移階段的城市融入4個維度的中介效應。結果見表6。

(1)在二代與三代家庭成員遷移過程中,X→Y總路徑c與直接路徑c′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0.01),假說1進一步得到驗證。(2)二代家庭成員遷移過程中,各間接路徑系數a、b分別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0.05或P<0.01)。中介效應占比排序為:MP(19.8%)>ME(17.7%)>MS(11.5%)>MR(6.7%),其中,MR最弱并呈現“遮掩效應”。二代家庭城市融入4個維度效應次序分異特征與全樣本驗證結果一致。(3)三代家庭成員遷移過程中,各間接路徑系數a、b分別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0.05或P<0.01)。中介效應占比排序為:ME(24.7%)>MP(23.6%)>MS(18.0%)>MR(9.3%),其中,MR最弱并呈現“遮掩效應”。比照二代家庭城市融入4個維度效應次序分異特征,三代家庭的ME效應顯著提升,這可能的解釋是,農民工父母尚具備勞動能力,城市家庭成員分工細化,這使得ME增強。綜上,假說3得到驗證。
3.4.2 不同退出模式的異質性分析
在全樣本中,運用逐步回歸法檢驗農民工家庭偏好宅基地全退出或半退出模式中的城市融入4個維度中介效應。結果見表7。
(1)在兩種宅基地退出模式中,X→Y總路徑c與直接路徑系數c′皆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0.01),假說1進一步得到驗證。由于采用線性回歸模型檢驗中介效應,因此,系數大小可以直接比較。半退出模式系數(c = 0.447,P<0.01)大于全退出模式(c = 0.235,P<0.01),即農民工更為偏好半退出模式。究其原因:一方面,農民工家庭獲得部分經濟補償以增強經濟融入資本;另一方面,也為探望留守老人、翻修老宅、進城失敗返鄉、“鄉土依戀”等提供居住社會保障。這也與相關研究結論一致[5,27]。
(2)在宅基地半退出模式中,各間接路徑系數a、b分別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0.05或P<0.01)。中介效應占比排序為:MP(18.2%)>ME(18.0%)>MS(10.0%)>MR(9.3%),其中,MR呈現“遮掩效應”。半退出模式中城市融入4維度效應次序分異特征與二代家庭樣本驗證結果一致,這可能的解釋是,調研區農民工家庭樣本主體尚處在二代隨遷階段(二代遷移家庭在總樣本中占比53.5%)。

(3)在宅基地全退出模式中,各間接路徑系數a、b分別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0.05或P<0.01)。中介效應占比排序為:ME(26.6%)>MP(22.8%)>MR(14.7%)>MS(14.3%),其中,MR提升,宅基地退出意愿隨之上升。這可能的解釋是,偏好全退出宅基地的農民工,大部分家庭實現了三代隨遷(三代隨遷戶在全退出樣本中占比75.0%),農民工父母尚具備勞動能力,城市家庭成員分工細化,ME能力強;城市家庭團聚使得MP隨之提升;而且,全部二代隨遷家庭及部分三代家庭實現了城市購房(城市購房戶在全退出樣本中占比62.5%),此時,全退出宅基地沒有后顧之憂,MR提升;但是,當前各城市高考回原籍、中小學借讀費、農村城市醫療報銷分離等城鄉二元制下,農民工“上有老,下有小”,提升MS壓力大。
綜上,假說4得到驗證。
4 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新遷移經濟學理論構建了理論分析框架,利用珠三角6個核心地市的典型調研數據為樣本,運用有序Logit模型、逐步回歸的中介效應模型,實證城市融入在家庭化遷移對宅基地退出意愿影響中的中介作用,并分析不同代際、不同退出模式的作用差異,主要結論如下。
(1)家庭化遷移顯著提升農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農村家庭人口離村進城越多,農民工對宅基地居住與社會保障功能依賴越弱,宅基地退出意愿越強。
(2)城市融入在家庭化遷移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比排序為:心理融入>經濟融入>社會融入>居住融入,其中,居住融入最弱并呈現“遮掩效應”。這反映了農民工之所以漸進式家庭化遷移,進而融入城市,并有意愿退出宅基地,主要驅動力是其城市心理融入主觀意愿積極,以及城市相對于農村工資收入的優勢,但社會與居住融入驅動作用相對弱。
(3)不同代際遷移階段以及不同宅基地退出模式中,城市融入4個維度中介效應呈現次序差異,其中,二代遷移階段與半退出模式中,其次序與全樣本檢驗一致,反映了當前農民工家庭城市融入的主體特征;三代遷移階段,經濟融入最強,居住融入最弱,即城市經濟收入是該階段主要驅動力,而城市住房是主要壓力;全退出模式中,經濟融入最強,社會融入最弱,即城市社會融入是農民工抉擇該模式的主要壓力。
依據以上結論,提出政策建議。
第一,深化城鄉聯動改革,保障家庭化遷移農村人口有序落戶城市及宅基地有序退出。重視農村人口家庭化遷移漸進式態勢,一方面,推動國家投資向吸納農民工落戶多的城市傾斜,省級政府同步制定建設用地指標、財政等相應配套政策,實施“人—財—地”掛鉤機制,有效激勵各地推進農民工家庭城市融入及宅基地退出。另一方面,完善農村教育、養老與“三權”保障等公共服務體系,保障農村留守兒童、老人與進城農民工權益,支持農村人口分步、有序落戶城市及宅基地有序退出。
第二,健全城市融入機制和公共服務體系,提升農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簡化城市積分落戶辦法、改革常住地戶籍登記制度,以提高農民工舉家進城落戶便利度;關注不同代際家庭成員遷移階段的社會融入及居住融入滯緩困境,從子女教育、醫療、養老保障和社會活動參與等方面完善農民工家庭在城市的公共服務待遇;特別重視居住融入的“遮掩效應”,加大經濟適用房供給,從首付比例、貸款利息等方面減輕農民工購房壓力,多渠道為農民工提供住房保障,力促“農民工”向“市民”轉變,保障宅基地退出工作的有序推進。
第三,差別化宅基地退出政策,匹配農民工家庭差異化需求。充分尊重農民工家庭因城市融入維度次序分異而產生的宅基地功能差異化訴求,避免宅基地退出政策“一刀切”。一方面,推動宅基地完全退出模式,滿足三代家庭成員遷移戶與增強城市經濟融入資本農民工訴求。另一方面,結合村鎮規劃,合理安排宅基地半退出模式,有序、分步推進宅基地退出。此時,農民工家庭既能獲得部分經濟補償,也為翻修老宅、進城失敗、“鄉土依戀”提供居住社會保障,同時,農村新區安置地塊建設的中高密度住宅,農村環境得以改善,宅基地實現集約利用,使農民工家庭、集體與國家目標達成一致。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劉守英,王一鴿. 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中國轉型的鄉村變遷視角[J] .管理世界,2018(10):128 - 146,232.
[2] 蔡俊,章磊,袁宏偉,等. 基于改進TAM框架的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意愿影響因素研究[J] . 資源科學,2022,44(5):899 - 912.
[3] 國家統計局.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EB/OL] .(2021 - 05 - 13)[ 2023 - 03 - 02] . http://www.gov.cn/ guoqing/2021 - 05/13/content_5606149.htm.
[4] 嚴金海,王彬,鄭文博. 鄉土依戀、城市融入與鄉城移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福建廈門的調查[J] . 中國土地科學,2022,36(1):20 - 29.
[5] 蔡俊,袁宏偉,王雪兵,等. 期望權益、確權效應與宅基地退出意愿及代際差異——基于合肥市近郊肥東縣615份問卷的實證分析[J] . 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1,35(12):23 - 29.
[6] 楊慶媛,陳鴻基,蘇康傳,等.中國農村宅基地資產化研究進展與展望[J] . 中國土地科學,2022,36(7):116 -126.
[7] 李瑤玥,任遠. 家庭化遷移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影響及其異質性分析[J] . 人口與發展,2021,27(3):18 - 31.
[8] 里昕. 親屬隨遷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了嗎 [J] . 農村經濟,2022(3):84 - 90.
[9] 錢龍,羅必良. 土地財產性收益對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影響[J] . 改革,2022(9):94 - 107.
[10] 李愛民,年猛,戴明鋒. 我國農業轉移人口深度市民化研究[J] . 中國軟科學,2022(8):67 - 78.
[11] 韓述,郭貫成,王俊龍. 風險承載力、政策規制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研究——基于拓展計劃行為理論的分析框架[J] . 中國土地科學,2023,37(4):62 - 72.
[12] 陳美球,鄺佛緣,魯燕飛. 生計資本分化對農戶宅基地流轉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實證分析[J] .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18,17(1):82 - 90.
[13] 許恒周,邢新澤. 非農就業、基本社會保險選擇對宅基地流轉的影響——基于2017年CRHPS追蹤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J] .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21,26(10):250 -263.
[14] 鄒夢玲,陳美球,張婷,等. 城鄉“兩棲占地”農戶宅基地退出的補償偏好及影響因素研究[J] . 中國土地科學,2022,36(11):75 - 84.
[15] WU Y Z, MO Z B, PENG Y, et al. Market-driven land nationalization in China: a new system for the capitalization of rural homesteads[J] . Land Use Policy, 2018, 70: 559 - 569.
[16] 胡銀根,余依云,王聰,等. 基于成本收益理論的宅基地自愿有償退出有效閾值——以改革試點區宜城市為例[J] . 自然資源學報,2019,34(6):1317 - 1330.
[17] 楊慧琳,袁凱華,陳銀蓉,等. 農戶分化、代際差異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基于宅基地價值認知的中介效應分析[J] . 資源科學,2020,42(9):1680 - 1691.
[18] YUAN Z Y, FU C C, KONG S J, et al. Citizenship ability, homestead utility, and rural homestead transfer of“amphibious” farmers[J] . Sustainability, 2022, 14(4). doi: 10.3390/su14042067.
[19] 楊慧琳,袁凱華,朱慶瑩,等. 農戶分化、城鎮住房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J] .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21,30(1):44 - 53.
[20] 錢龍,陳方麗,盧海陽,等. 城市人“身份認同”對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流轉的影響研究——基于浙江溫州農戶的調查[J] . 農業技術經濟,2019(8):40 - 52.
[21] 時鵬,余勁. 風險預期、市民化感知及農戶認知對易地扶貧搬遷農戶宅基地退出的影響[J] . 資源科學,2021,43(7):1387 - 1402.
[22] 鄧悅,鄭漢林,王澤宇. 家屬隨遷何以影響農民工城鎮化融合 [J] .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9(1):91 - 99,166.
[23] 黃瀟,羅俊超. 勞動力遷移對教育回報率階層差異及收入差距的影響——采用“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J] . 西部論壇,2019,29(2):36 - 45.
[24] 劉靜,張錦華,沈亞芳. 遷移特征與農村勞動力子女教育決策——基于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的分析[J] . 復旦教育論壇,2017,15(2):87 - 93.
[25] 孫偉增,張思思. 房租上漲如何影響流動人口的消費與社會融入——基于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J] . 經濟學(季刊),2022,22(1):153 - 174.
[26] 曾通剛,楊永春,滿姍. 中國城市流動人口心理融入的地區差異與影響因素[J] . 地理科學,2022,42(1):126 -135.
[27] WANG X J, KANG J F. Decision making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withdrawal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use rights in Suzhou, Anhui Province, China[J] . Land, 2023, 12(2). doi: 10.3390/land12020479.
[28] 梁發超,林彩云. 經濟發達地區宅基地有償退出的運行機制、模式比較與路徑優化[J] . 中國農村觀察,2021(3):34 - 47.
[29] 趙安琪,呂康銀. 家庭代際支持對勞動力遷移的影響——基于CFPS數據的實證分析[J] . 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22,44(12):77 - 91.
Influence of Family Migration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Intention: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 Based on Urban Integration
CAI Jun1, LEI Lei1, LIU Daolei1, WANG Weiye1, XIANG Jinwe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migration on migrant workers the inten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and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urban integration,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mechanism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stitutions.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as follow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are built upon the new migration economics theory. Based on the typical survey data of six core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orderly Logit model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are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amily migr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intention of migrant workers. 2) Urban integra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The proportions of mediating effects are as follows: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economic integration>social inclusion>residential integration, among which the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is the weakest and presents a “masking effect”. 3) In different intergenerational migration stages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modes, the four-dimensional mediating effect presents an order difference. In conclusion,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mechanism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policy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the aspects of deepening the urban-rural linkage reform, improving the urban integration mechanism and public service system and discriminating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policy
Key words: family migration; urban integratio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intention; intergenerational migration; withdrawal mode; mediating effect
(本文責編:郎海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