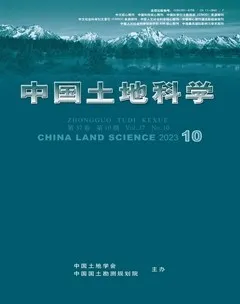村莊信用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影響路徑
胡學東 黃寶珍 鄒利林



摘要:研究目的:以江蘇省29個村莊為案例,探討村莊誠信度、合規度及踐約度信用資本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影響機制,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市場建設提供政策建議。研究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fsQCA)。研究結果:(1)構建了基于“村莊資本→信用評價→土地市場”的分析框架;(2)單一條件并非是高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必要條件,但是提高民間借貸活躍度和村莊信用戶比例對高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發揮著普適作用;(3)在信用資本評價模型下,江蘇省典型村莊通過整合自身資源提高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存在4種組態,可歸納為3種類型:誠信型、誠信合規型、誠信踐約型;(4)蘇南、蘇北地區根據發展情況,提高土地流轉效率的關鍵不同。研究結論:蘇北地區可通過加強黨組織建設、提升村莊集體經濟、理順村組織權責關系等方式,構建制度信任,降低委托代理風險;蘇南地區可通過加強集體組織建設、發揮鄉紳鄉賢鄉才協調作用、做好確權登記發證等方式,提高民間信用水平,降低農戶誠信履約風險,共同推動城鄉土地市場建設。
關鍵詞: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村莊信用;組態分析;土地市場
中圖分類號:F30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158(2023)10-0071-10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青年基金(42001195);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GD23YGL32);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2023A151 5010987);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課題(2022GZYB38)。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2023年中央一號文在“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中,進一步強調“深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探索建立兼顧國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有效調節機制”。由此可見,優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模式成為鄉村“賦權賦能”的重要路徑,流轉效率是衡量入市效果的重要指標,研究如何提升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對于深刻理解和深入推進農村土地市場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隨著2019年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出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法律障礙被破除。然而實踐中,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效果并不明顯,中央提出審慎穩妥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工作,地方也逐步放緩入市進程,離“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的目標還有一定距離。研究表明,土地市場受外部政策引導、經濟發展牽引、價格機制調控和公眾意愿驅動[1],同時也受金融支持程度、契約信用條件等影響[2],我國城市不動產交易是以信用評估為前置條件,從而保證了交易安全性和風險可控性,進一步促進了城市房地產交易。在資本下鄉大背景下,農村集體土地的資產化和資本化使鄉村地域更深地嵌入城市資本循環[3],然而與資本相伴而生的信用體系并未完善,與城市土地市場相比,農村土地市場還受農村獨特的差序格局與“關系”維系特征的社會環境影響,且交易對象更為特殊且關系復雜,從而在權能實現、市場偏好、契約能力、信任機制上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4],“三塊地”改革試點實踐表明,誠信履約風險和市場發育程度是制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交易活躍度的關鍵因素[5],實際上,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所有權在村集體經濟組織,使用權在農戶,社會各界對二者信用條件(包括簽約能力和誠信意識)的擔憂影響了用地者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相關權利保障性和穩定性的預期,同時也增加了流轉市場的談判成本,進而降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信用是交易的基礎,其在構建良好的人際關系、潤滑經濟交易、促進社會穩定以及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等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6],良好的信用關系或信用制度是交易順利實現的無形擔保,或者稱為一種“隱性契約”[7]。當前,學者們也關注到信用體系對農村土地市場的重要作用,有從土地流轉各環節分析了不信任的原因,如合同不規范、利益分配不平衡、市場化管理不善等均會引發不信任問題[8],有從農戶的信任感知來分析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流轉效果,有從土地資產化和市場化視角探索城鄉土地銀行制度設計,提出要融入“信用賦予”功能[9],也有從不同經營主體對于土地流轉價格敏感程度的差異性入手來分析信貸配套政策,進而提出通過構建信息化流轉平臺來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減少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風險[10],還有從政府視角提出可以通過政策供給和財政保障重建公眾對政府的信任,進而提高土地流轉意愿[11]。在實踐中,各地針對農村土地也逐漸開始探索土地信托、土地保險、信用合作社、整村授信等新型模式來提升土地抵押貸款效率[9],進而助推土地流轉。
現有研究與實踐更多以案例分析為主,聚焦于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定性化的描述,強調政策實用性,注重宏觀制度設計和對策建議,默認信用機制可行,對于信用如何影響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作用機理并未深究,更是缺少微觀層面的深入分析與實證。此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產權復雜,涉及多個主體,現有的信用機制更多關注單方面的信用評價,而忽視了“村莊共同體”在塑造信用和推動互動方面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在信用制度建設上僅僅關注某一產權主體而忽略其他產權主體,均無法消除用地者對于違約風險的顧慮[5,12],為此,在信用評價中須把所有產權納入到評價體系中來。基于此,參考村莊信任內涵,引入“村莊信用”的概念,來探究信用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作用機制與背后邏輯。與此同時,由于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戶異質性及所在村莊的社會網絡關系的差異性[13],相同的信用制度體系在不同的農村土地市場的作用路徑也各具特色,即不同作用條件和影響因素的相互匹配會形成差異化的模式與結果,而現有的定量分析方法關于自變量與因變量間統一對稱關系的假設限制了流轉效率提升的路徑選擇,限制了對村莊信用建設背后多重因素間協同匹配效應的理解。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借助“組態視角”,利用中國土地經濟調查的數據,使用fsQCA的研究方法,對不同村莊提高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背后的復雜機理進行深刻解剖,最終,為提高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決策提供參考。
1 理論分析與研究框架
1.1 概念內涵界定與解析
農村集體土地流轉是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內容,流轉效率的高低直接決定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成效。本文把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界定為:在一定城鄉發展水平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通過使用權流轉(包括一級市場的使用權出讓、出租等和二級市場的使用權轉讓、贈與、轉租或者抵押等),實現農村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的目標,以最小的要素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從制度演變、政策執行和關系互動三個維度來看,首先,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是強制性變遷和誘致性變遷的結合[14]。農地流轉制度變遷的速度及范圍直接影響農戶對政府的信任,進而影響農戶土地流轉的意愿,表現為土地流轉效率的高低。其次,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土地政策執行的重要主體之一,其身份具有矛盾性,導致其無法與村民之間形成交易共識與利益均衡,從而影響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提高。最后,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過程是一個復雜的互動過程,包括村民、集體經濟組織、社會企業等之間的互動,該互動受鄉土情結、熟人擔保、宗族聯合等一系列因素影響[15],故在實踐過程中常出現農戶毀約的情況,進一步證明了村莊主體社會網絡因素影響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
目前關于村莊信用的深入研究相對較少,主要集中于概念引用和對策建議方面,本文的村莊信用是一個多維度、制度化和綜合性的概念,是村莊信用資本的綜合衡量,具有村莊+信用的綜合表征,包括村民與村民、村民與集體之間的相互信任水平,其作用是為交易雙方提供穩定的心理預期,從而降低由于彼此間信息不對稱所產生不確定性而帶來的交易成本[16]。需要說明的是,不同于村莊信任強調個體與村莊規則的秩序關系[17],屬于組織或公共關系范疇,村莊信用則是強調整個村莊社會的政府與市場的作為結果,是一種規范性制度安排的結果,屬于經濟學或制度學范疇[18]。一般而言,良性的村莊信用可與理性的村莊信任在農村市場化和資本化進程中相互促進。分別從信用和村莊來看,信用是基礎,福山指出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乃是文化對經濟的影響途徑和表現形式,它會直接影響甚至決定經濟效率[19]。具體到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流轉過程中,較高的信用條件評價有利于降低誠信履約、委托代理、行為能力等風險,從而提高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村莊是評價對象,從文化和產權的角度而言,集體經濟組織的行為受到農戶集體意愿的影響,最終形成具有共同體特征的村莊形態,同時村莊包括所有權和使用權主體所對應的農村經濟組織和農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是村集體和農戶共有資產,村莊更適宜作為分析的起點[20]。選取村莊作為農村的分析單元,一方面是因為村莊的形成與發展更能準確地反映中國鄉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特征,另一方面,聚焦村莊共同體更能揭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交易活動所體現的社會信用關系的復雜性及其對土地交易活動的影響。
1.2 理論視角:三維信用評價體系
當前,村莊正處在經濟、社會急劇變革時期,一方面,傳統信任機制所依賴的關系、聲譽等因素雖然仍在支撐村莊發展,但作用越來越小;另一方面,基于法律和規則的現代信任機制仍未成熟,這種新舊機制轉型構成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的信用情境。在此情境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處于復雜環境中,面臨多重制度邏輯和成本選擇[21]。科斯在《論社會成本問題》中指出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WILLIAMSON沿襲科斯的思想,提出了交易費用理論[22],認為產生交易費用的主要三個因素為資產專用性、交易頻率、不確定性。一方面,我國實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在流轉過程中具有明確的用途,使用者不能私自改變用途,故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資產專用性較為穩定。另一方面,由于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屬于大宗商品,具有交易額度大、談判耗時長和合同約定年限固定等特點,難以在短時期內快速流轉,所以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交易頻率也較為穩定。由此可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受交易主體行為不確定性的影響較為顯著,因此,本文認為提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關鍵在于降低土地流轉中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主要包括農戶誠信履約風險、村集體經濟組織誠信代理風險,二者共同形成村莊信用評價維度。實際上,在交易過程中,交易主體對交易行為的風險感知將影響交易的成功率。交易主體對交易風險的判斷主要依賴于對交易對象信用水平的衡量,而降低不確定性的方法在于通過信用評價建立交易雙方的信任機制。本文采用WUs三維信用理論來開展信用評價,該理論認為信用的構成包括三個維度,即誠信度、合規度和踐約度[23]。其中誠信度由民間借貸活躍程度和信用認可度反映,其高低可以直接影響交易成本中的協商與決策成本、監督與執行成本,進而促進流轉進程,合規度由土地交易透明度和信息化程度反映,其高低也可以直接影響交易成本中的搜尋信息成本、監督與執行成本,進而為持續流轉提供保障,踐約度可分解為政府支持度和社會企業支持度,其高低可以直接影響交易成本中的協商與決策成本,維護流轉的交易環境。誠信度、合規度和踐約度是相互支撐、相互影響、相互轉化的,是一個復雜的聯動關系。信用評價的實踐經驗表明,對多重條件的組態分析有助于研究者進一步理清各個條件在影響評價結果上的復雜機理。
1.3 基于“村莊—信用—土地市場”的理論分析框架
差異化的資源稟賦、制度建設以及社會關系等因素直接影響村莊信任條件評價,進而推動村莊為應對土地流轉而形成差別化的信任條件整合路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是多方主體博弈的結果,同時村莊的行動場域對多方主體博弈具有約束和引導功能,結合前文論述,本文構建基于“村莊—信用—土地市場”的理論分析框架(圖1),來分析村莊信用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影響機制。具體解釋為:首先,村莊是信用評價的基本單元。一方面,村莊條件的異質性直接影響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價值,進而影響流轉過程中的履約能力評價;另一方面,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權利主體皆處于村莊場域下,農戶和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意愿和行為是影響村莊信用評價的重要因素。其次,三維信用是村莊信任程度的外在表征。基于村莊共同體的視角下,村莊信用評價是對村莊條件和交易不確定性的綜合衡量,三維信用理論將村莊信任條件的表征分為三個維度。其中,通過誠信度建設,能夠構建出適宜開展土地交易活動的社會信任環境,吸引交易主體;通過合規度建設,能夠遏制土地交易過程中的違規違紀行為,降低制度成本;通過踐約度建設,能夠減少資金流轉過程中的障礙,加速交易進程。最后,信用評價是城鄉土地市場的基礎。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的過程中,較高的信任條件評價有利于減少誠信履約、委托代理、行為能力等風險,從而提高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因此村莊信用對提高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具有潛在影響。
鑒于此,本文通過構建“村莊—信用—土地市場”三維分析框架,探究村莊信用影響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作用機制。同時,基于組態視角,誠信度、合規度和踐約度三種村莊信用的構成條件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影響并非相互獨立,而是通過一定的組合協同機制發揮作用。因此本文在“村莊—信用—土地市場”三維分析框架基礎之上,從組態視角,討論村莊誠信度、合規度和踐約度三重信任條件如何相互組合影響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本文利用2020—2021年中國土地經濟調查(China Land Economic Survey, CLES)的農戶與村面板數據作為數據源,該調查被廣泛應用于中國村莊經濟的相關研究中,項目于2020年完成了基線調研,基線調研范圍覆蓋江蘇省13個地級市,每個地級市調查2個縣,每個縣調查2個村,共計52個行政村、2 600戶農戶。由于追蹤調查中部分村莊數據存在缺失,為此需要遴選出符合研究條件的村莊案例作為樣本,基本原則與步驟為:首先在所有案例中剔除數據缺失的村莊樣本,其次再剔除沒有集體建設用地交易的村莊樣本,再者剔除數據填寫有誤和年度數據變異較大的村莊樣本。最終,在54個樣本中選取了29個村莊作為研究對象,村莊樣本覆蓋了江蘇省所有地級市,其中位于蘇南的村莊比例為48.3%,位于蘇北的村莊比例為51.7%,整體地域較為均衡。
2.2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組態視角,采用fsQCA進行實證分析,探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影響機制。fsQCA是一種案例導向型的研究方法,其基于集合論思想和組態思維,將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有效聯結,基本思想就是借助架構理論和布爾代數運算,從集合的角度考察前因條件及條件組合與結果的關系,從而解釋現象背后的復雜邏輯關系[24]。選擇該方法的原因在于:首先,傳統的回歸分析僅能解釋變量的凈效應,無法解釋多重復雜關聯,而現實情況中,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同時受多個維度的影響,fsQCA能夠幫助理解其影響機制;其次,fsQCA 不僅適用于大樣本分析,也能對中等規模樣本以及小樣本展開分析,滿足本文村莊案例數量的需求;最后,相較于csQCA和mvQCA,fsQCA能夠解決數據變化或部分隸屬等問題。本文中的數據均為連續數據,數據變化更為多樣,因此選擇fsQCA作為研究方法。
2.3 變量選擇
2.3.1 結果變量
本文的結果變量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以流轉比例和交易單價兩個指標來綜合衡量。面積比重測度和流轉單價是反映土地市場化程度最直接的指標,考慮到村莊的異質性問題,參考曲福田等[25]、曹建華等[26]的研究,綜合選取流轉比例與流轉單價兩個指標進行組合,通過控制權重減少村莊異質性對流轉效率的影響,最終結果變量=流轉比例×0.7+流轉單價×0.3。
2.3.2 條件變量
一是誠信度。誠信度是對村莊誠信意識條件的評價,本文選取民間借貸活躍程度和社會信用認可度兩個指標進行測量。一方面,民間借貸活躍程度是反映村民相互信任的最重要因素[27],活躍程度越高,則農戶的毀約風險相應降低,表征了個體層面的誠信度;另一方面社會信用認可度反映社會對不同主體的信任程度,能夠測量整體的誠信程度,反映組織層面的程度。村莊誠信度是由村民個人和村集體的誠信度構成,故民間借貸活躍程度和社會信用認可度可以較為完整測量村莊誠信度。本文選擇村莊問卷中“本村農戶間借貸的活躍程度”和“本村被農信社(或者農商行)評為信用戶”的戶數與“年末總戶數”比例,分別測量民間借貸活躍程度和社會信用認可度兩個指標。
二是合規度。合規度是對村莊遵守社會規定、行業規則的水平與能力的評價。本文選取土地交易透明度和數字化程度兩個指標進行測量。由于熟人社會的作用機制,造成村莊在進行土地流轉存在“非正式”契約的情況[28]。從信息不確定的視角看,土地交易不透明會降低農村土地流轉的速度。為了提高農地流轉的效率,政府層面除了出臺健全土地管理與流轉法規外,還通過使用數字化治理手段,提高土地流轉的合規度。數字化深入程度不僅體現了政府對土地流轉風險監管的能力,而且反映了村莊土地流轉的規范性。故本文使用調查問卷中“村中是否發生具有生產經營性質的農村建設用地出租、出讓或者入股情況”和“轉出土地是否通過土地交易平臺或中心”的比例,分別來測量土地交易透明度和數字化程度進行測量。
三是踐約度。踐約度是獲得交易對手信任的經濟資本,表現為信用主體在信用交易活動中遵守交易規則的能力。具體包括政府政策支持度和社會企業支持度兩個二級條件。在城鄉融合背景下,村莊發展的資金很大一部分來自政府的產業補貼,產業補貼數量反映政府對村莊公共事務治理行為的認可,中國情境下,戰略決策很大程度上受政治邏輯的影響,補貼越多的村莊其踐約能力受到官方認可[29]。同時,企業在行為決策時,會綜合考慮投資主體的信用情況,故引進企業越多則代表該村莊履約能力越強。綜上,本文使用問卷中產業補貼金額和村莊企業數的數據,分別衡量政府政策支持度和社會企業支持度。
2.3.3 變量校準
fsQCA將分析對象視為一個獨立的集合,條件、結果之間是集合關系,每個案例在這些集合中均有隸屬分數。因此需要對變量進行校準,給案例賦予集合隸屬分數。在已有理論和經驗知識的基礎上,本文根據各條件與結果的數據類型,運用直接校準法[30],并通過fsQCA 3.0軟件將數據轉換為模糊集隸屬分數,依據校準標準以及案例的實際情況,將案例樣本描述性統計數據的95%分位值、50%分位值與5%分位值作為校準的完全隸屬點、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點。
3 數據分析與實證結果

3.1 單個條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進行條件組態分析前,需要對各條件的“必要性(Necessity)”進行逐一單獨檢驗,即檢驗各條件變量(包括其非集)是否構成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必要條件,當結果發生時,有特定條件必然存在,那么該條件就成為結果的必要條件。一致性作為必要條件的重要檢測標準,當一致性大于0.9時,則該條件就是結果的必要條件。采用fsQCA 軟件對各條件變量的一致性水平進行檢驗(表1),結果表明,所有條件的一致性水平都小于0.9,說明各條件變量均無法構成解釋高水平土地流轉效率的必要條件,也間接表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是村莊信用并發協同產生的結果。
3.2 條件組態的充分性分析
組態分析試圖揭示由多個條件構成的不同組態引起結果產生的充分性。從集合論視角出發,探討由多個條件構成的組態所表示的集合是否為結果集合的子集。一致性也用來衡量組態的充分性,但可接受的最低標準和計算方法不同于必要條件的分析。一致性閾值和頻數閾值是判別條件充分性的重要參數,一致性閾值沒有統一標準,可采用0.8來判別[31],而頻數閾值應根據樣本量來確定,在具體研究中,也要考慮案例在真值表中的分布以及研究者對觀察案例的熟悉程度,一般認為頻數閾值以1為分界標準。結合研究案例情況,參考已有研究成果,最終確定的一致性閾值為0.8,頻數閾值為1,最后涵蓋29個樣本。
由于村莊社會發展的異質性,其在民間借貸活躍程度和信用認可度的表現均不同,有的村莊甚至可能不存在信用戶,因此本文對誠信度條件選擇“存在或缺乏”。本文選取的村莊案例均存在土地流轉,但有些村莊在交易過程中并沒有對此公示,村民并不了解土地交易情況,本文對土地交易透明度條件選擇“存在或缺乏”。數字化程度(土地交易平臺建設情況)在各村情況不一,從數據中可看出有的村莊土地流轉并不是通過統一的交易平臺,因此對土地交易平臺建設情況選擇“存在或缺乏”。社會企業支持度(村莊企業數)對高水平土地流轉的作用可能因為村莊的產業結構差異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對“社會企業支持度”選擇“存在或缺乏”。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政府對村莊的產業補貼對土地市場價值的作用具有關鍵影響,因此本文對政府政策支持度(產業補貼)選擇“存在”。
表2中呈現的 4 種組態,無論是單個解(組態)還是總體解的一致性水平均要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標準0.75,其中總體解的一致性為 0.885,總體解的覆蓋度為 0.691。4種組態均可被視為影響高水平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充分條件組合(表2)。
在組態1中,村莊信用戶比例的存在發揮了核心作用。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926,原始覆蓋度為0.465,唯一覆蓋度為0.209。在該路徑中,單一維度評價(村莊信用戶比例)構成解釋結果產生的充分條件,表明相較于其他評價條件,村莊信用戶比例對于提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尤為重要,因此本文將該組態命名為“誠信型”。這意味著,村莊對誠信意識的建設能夠借助金融機構的認可間接提高土地的經濟價值。對典型案例(前因隸屬度和結果隸屬度都高于0.5的案例)進行分析發現,案例集東村(0.501,0.839)所在的沭陽縣積極推動信用管理與服務創新,率先開展信用積分賦能鄉村治理的試點工作,信用體系建設較為完善。
在組態2中,村莊民間借貸活躍程度和土地交易透明度發揮核心作用。該路徑能夠解釋約38.4%的村莊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交易案例。在踐約度條件缺失的情況下,如果民間借貸活躍度高且土地交易透明度好,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也能達到高水平的狀態。在典型案例岔鎮村(0.501,0.599),村民對土地交易流轉的認知正確率達98%,土地交易透明度高。民間借貸活躍程度一般。其所在的儀征市是工業較發達的補償安置地區,土地征收發展早,制度建設較完善。經查閱相關政府網站,在土地征收過程中,關于補償安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流程完善、方案成熟、公示透明。完整透明的制度建設有利于保障村民的知情權,同時能夠規避集體行動的風險,減少甚至杜絕土地交易中的集體性事件,打造良好村莊形象,促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流轉效率。
組態3中,村莊民間借貸活躍程度和土地交易透明度發揮核心作用,土地交易平臺的存在發揮輔助作用。與組態2相比,土地交易平臺的存在進一步強化了合規度提高土地流轉效率的作用。實際上,土地交易平臺的建設與土地交易透明度是相輔相成的。該組態的一致性為0.902,能夠解釋約38.3%的土地流轉案例。由于組態2與組態3的驅動路徑由民間借貸活躍程度和土地交易透明度條件構成,我們將其命名為“誠信—合規型”。
組態4中,村莊民間借貸活躍程度和政府產業投入發揮核心作用,土地交易平臺建設與村莊企業數發揮輔助作用,該路徑能夠解釋約30.4%的村莊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案例。對典型案例許家莊村(0.501,0.979)進行分析,其借助鄉村振興、高標準農田建設的契機,用好政府產業補貼,發展“支部+合作社”發展模式,成立谷物種植農地股份合作社,推動產業多元化,大幅度提高村莊收入,并整合村莊資源推動集體資產流轉。對相關宣傳文件進行比較,許家莊村得到的政府注意力較高,村莊信用形象好,所吸引的企業數量相比其他村莊多,發展潛力大,經濟價值高。這種組態的驅動路徑主要由民間借貸活躍度和政府產業補貼構成,我們將其命名為“誠信—踐約型”。
3.3 模式選擇與政策啟示
受經濟發展水平、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等影響,蘇南、蘇北的村莊整合自身信任條件提高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路徑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以長江為分界線,結合江蘇省的行政區劃,將樣本數據分為蘇北地區和蘇南地區。通過對各地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比較分析,探索不同地區誠信度、合規度、踐約度條件對土地流轉效率影響的差異化,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蘇北地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存在2種組態。組態1表明,村莊信用戶比例對于提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是核心條件。組態2表明,土地交易透明度和產業補貼作為核心條件驅動高土地流轉效率。蘇南地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存在3種組態,3種組態中民間借貸活躍程度均是提高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核心條件。土地交易透明度、土地交易平臺建設、產業補貼、村莊企業數是輔助條件,這些輔助條件與核心條件的組合以“殊途同歸”方式促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提高,條件間存在相互替代、相互轉化的作用。基于上述組態的條件組成和評價維度結構,對蘇南、蘇北地區提高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提出針對性政策組合建議。
(1)蘇北地區在提高金融機構評價基礎上,重點需積極申請產業補貼,用好政府政策。通過對村莊的其他數據分析,發現蘇北地區村莊收入主要以種植業收入和其他收入為主,第一產業補貼較少,流出勞動力多,村民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至大專,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機構黨員數量較多。在村莊轉型過程中重點是防患市場對集體組織的道德風險沖擊,尋求官方機構的扶持。因此,為了提高土地流轉效率,首先要構建制度信任。在村民自治的前提下,加強村級黨組織建設,強化黨組織在農村建設中的引領與組織作用,鼓勵黨員干部為村莊的社會關系和村集體代理能力背書。把信任要素納入到“村規民約”中,鞏固農村社會的秩序,維系與提升村莊內部農戶與集體、農戶與農戶之間的信任水平,形成一種“軟約束”,改善現有信任條件;其次要提升村莊集體經濟。依托鄉村振興全面推進優勢,積極鼓勵村集體和村民參與鄉村建設進程,拓展農民增收渠道,提升村莊整體經濟水平,用活農村基礎設施冠名權,同時,進一步提高村組織在農村公共事務治理和經濟發展中的能力和地位,理順集體—村民的經濟委托代理關系及權責約束,以經濟基礎建設拉動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市場交易效率提升。
(2)蘇南地區在維護民間經濟活力的基礎上,關鍵是提升合規度建設。蘇南地區的村莊工業收入占比較高,外來勞動力人數多,村莊內發展了現代農業產業,現代化水平較高,但同時由于人口流動性強,關系變化相對不穩定,交易主體行為的風險可能更多來自農戶的契約履行。在一個共同體中,強大的非正式關系網絡力量有利于避免交易風險,即通過血緣和宗族紐帶使農戶高度關注自己的信譽、名聲以及家庭榮譽,從而嚴格遵守貸款合約,同時這種紐帶避免的勞動力流失能夠提供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未來發展的潛力。為此,這類村莊提高土地流轉效率的重點在于:一是加強集體組織建設,發揮黨員的模范帶頭與引領作用,充分發揮現有勞動力資源潛力,一方面有組織地引導勞動力積極參與鄉村建設行動的簡單事項,同時進一步強化集體榮譽感,制定相關積分與激勵機制,避免“搭便車”行為,另一方面,結合社會關系紐帶,鼓勵青年勞動力就近務工;二是充分發揮鄉紳鄉賢鄉才的協調與紐帶作用,利用“關系”與權威調解農戶矛盾和緩解農村沖突,在非正式關系欠缺的村莊類型中,可鼓勵鄉紳鄉賢鄉才參與村莊建設與管理工作,依托宗族基礎,做好頭雁工程,通過建立鄉紳鄉賢鄉才的聯動與管理機制,帶動村民—村民、村民—村集體間的相互信任;三是做好確權登記發證工作,在此基礎上激活土地從資源向資產轉變,加強政策宣講與落實,推動農用地、宅基地“三權”分置,進而促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產生更大財產收益。
4 結論與討論
本文基于制度轉型背景和村莊異質性,借助三維信用評價模型構建了基于村莊—信用—土地市場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分析框架,以江蘇省29個村莊為實證案例,通過 fsQCA方法探討土地流轉效率影響因素的協同效應和替代效應,進而提出針對性政策建議。研究發現:(1)單一條件并不構成提高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必要條件,信用資本條件“多重并發”,存在替代效應和協同效應。(2)村莊通過信用資本提高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存在4條路徑組態,其中,組態1中的村莊信用戶比例發揮核心作用,組態2的村莊民間借貸活躍程度和土地交易透明度發揮核心作用,組態3也是村莊民間借貸活躍程度和土地交易透明度發揮核心作用,但土地交易平臺的存在發揮輔助作用,組態4中村莊民間借貸活躍程度和政府產業投入發揮核心作用,土地交易平臺建設與村莊企業數發揮輔助作用。差異化路徑形成差別化效果,凝練4種組態為3種差異化模式:誠信型、誠信—合規性、誠信—踐約型。(3)蘇南、蘇北地區提升村莊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關鍵不同,蘇北地區可通過構建制度信任、提升村莊集體經濟、用好鄉村政策組合等方面,針對性地整合信任條件,降低委托代理風險,提高土地交易效率;蘇南地區可通過加強集體組織建設、充分發揮鄉紳鄉賢鄉才的協調與紐帶作用以及做好確權登記發證等方面,關注非正式關系的發展,提高民間信用,降低農戶誠信履約風險并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
本文從微觀層面對29個村莊案例進行了探索性分析,有一定代表性,但也具有時間和地域的局限性,后續可進一步增加樣本量和進行長時間序列跟蹤,對更多案例進行總結分析。除了村莊信用建設之外,影響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效率的因素還包括交易主體的職業、心理預期、收益預期、違法成本、法律環境以及對政策的理解等,這些可為后期繼續開展定量研究提供方向。另外,在宏觀的政策制度層面,頂層的權利規劃、用途管制、土地供需平衡以及監督監管等均是未來城鄉融合市場建設與發展的重要創新方向,值得進一步關注。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徐小峰,王克強,毛熙彥,等.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和作價入股的交易成本控制研究——基于上海市的案例證據[J] .中國土地科學,2022,36(11):124 - 134.
[2]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土地問題》課題組.土地流轉與農業現代化[J] .管理世界,2010(7):66 - 85,97.
[3] 曾鵬,李晉軒,任曉桐.中國公有制土地資本化的二重性效用及其優化路徑[J] .城市發展研究,2022,29(6):1 -7,33.
[4] 羅必良.農地流轉的市場邏輯——“產權強度-稟賦效應-交易裝置”的分析線索及案例研究[J] .南方經濟,2014(5):1 - 24.
[5] 宋志紅,姚麗,王柏源.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權能實現研究——基于33個試點地區入市探索的分析[J] .土地經濟研究,2019(1):1 - 29.
[6] 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J] .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1986, 5(3): 288 - 289.
[7] 蔣海.不對稱信息、不完全契約與中國的信用制度建設[J] .財經研究,2002,28(2):26 - 29.
[8] 王敬堯,王承禹.農地規模經營中的信任轉變[J] .政治學研究,2018(1):59 - 69,127 - 128.
[9] 夏方舟,楊雨濛,嚴金明.城鄉土地銀行制度設計:一個新型城鄉土地資本化制度探索[J] .中國土地科學,2020,34(4):48 - 57.
[10] 郭連強,祝國平,付瓊.農村土地流轉規模、流轉價格與規模經營主體信貸配給[J] .學習與探索,2022(5):94 -104,184.
[11] 劉鵬凌,蔡俊.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整備統籌入市的農戶意愿與行為響應[J] .中國土地科學, 2020,34(8):63- 71.
[12] 胡偉斌,黃祖輝.集體產權改革與村莊信任增進:一個實證研究[J]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52(8):28 - 46.
[13] 曲承樂,任大鵬.論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農村發展的影響[J] .中國土地科學,2018,32(7):36 - 41.
[14] 錢忠好,牟燕.中國土地市場化水平:測度及分析[J] .管理世界,2012(7):67 - 75,95.
[15] 劉錫良,陳鵬.農村商業金融與熟人社會信用聯結機制——雙水村擔保合作社模式[J] .金融發展評論,2011(1):127 - 140.
[16] 劉鳳委,李琳,薛云奎.信任、交易成本與商業信用模式[J] .經濟研究,2009(8):60 - 72.
[17] 胡必亮.村莊信任與標會[J] .經濟研究,2004(10):115 -125.
[18] 翟學偉.誠信、信任與信用:概念的澄清與歷史的演進[J] .江海學刊,2011(5):107 - 114,239.
[19] 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M] .郭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64 - 74.
[20] 王曙光.村莊信任、關系共同體與農村民間金融演進——兼評胡必亮等著《農村金融與村莊發展》 [J] .中國農村觀察,2007(4):75 - 79.
[21] 孔祥智,周振.我國農村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歷程、基本經驗與深化路徑[J] .改革, 2020(7):27 - 38.
[22] WILLIAMSON O 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M] .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15 - 42.
[23] 吳晶妹,張穎,唐勤偉.基于農戶信用特征的WUs三維信用評價模型研究[J] .財貿經濟,2010(9):22 - 28,63.
[24] 陶克濤,張術丹,趙云輝.什么決定了政府公共衛生治理績效?——基于QCA方法的聯動效應研究[J] .管理世界,2021(5):128 - 138,156,10.
[25] 曲福田,吳郁玲.土地市場發育與土地利用集約度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以江蘇省開發區為例[J] .自然資源學報,2007,22(3):445 - 454.
[26] 曹建華,王紅英,黃小梅.農村土地流轉的供求意愿及其流轉效率的評價研究[J] .中國土地科學,2007,21(5):54 - 60.
[27] 馬光榮,楊恩艷.社會網絡、非正規金融與創業[J] .經濟研究,2011(3):83 - 94.
[28] 馬薈,龐欣,奚云霄,等.熟人社會、村莊動員與內源式發展——以陜西省袁家村為例[J] .中國農村觀察,2020(3):28 - 41.
[29] 劉克春.糧食生產補貼政策對農戶糧食種植決策行為的影響與作用機理分析——以江西省為例[J] .中國農村經濟,2010(2):12 - 21.
[30]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 393 - 420.
[31] 程聰,賈良定.我國企業跨國并購驅動機制研究——基于清晰集的定性比較分析[J] .南開管理評論,2016,19(6):113 - 121.
Influence Path of Village Credit Affect on Transfer Efficiency of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Evidence from Multiple Villages by Configuration Analysis
HU Xuedong1, HUANG Baozhen1, ZOU Lilin2
(1. So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configuration effec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villages on the transfer efficiency of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redibility capital, compliance capital and contract fulfillment capita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29 villages by us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credit model,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transfer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transfer efficiency of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based on “village-credit-land market” is constructed. 2) A single condi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However, increasing the activity of private lending and the proportion of village residents with credit plays a universal role in increasing the transfer efficiency. 3) There are four path configurations that villages improve the transfer efficiency of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through credit capital. These configuration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types: credibility, credibility-compliance and credibility-contract fulfillment. 4)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e key to improve the transfer efficiency is different in southern Jiangsu and northern Jiangsu. In conclusion, for northern Jiangsu area, the targeted integration of trust condition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building institutional trust, enhancing collective economy of the village, making good use of rural policy combinations, to reduce principal-agent risks and to improve the transfer efficiency. For southern Jiangsu area,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should be enhanced. The coordination and linkage roles of local elites are suggested to be fully leveraged. Moreover, the proper registr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land rights are key measures. In addition, th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developing informal relationship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rust among farmers, and leveraging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labors.
Key words: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village credit; configuration analysis; land market
(本文責編:陳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