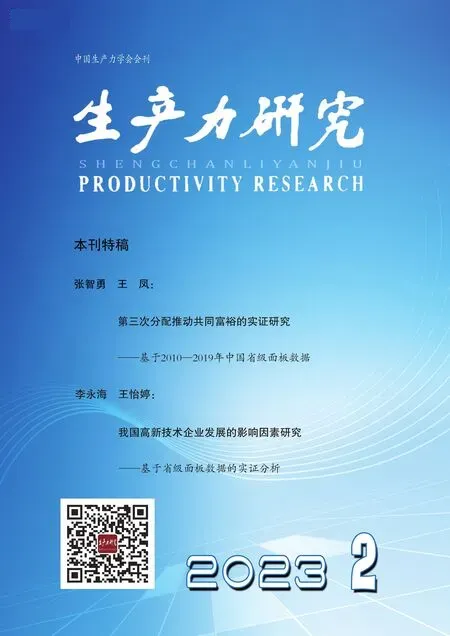第三次分配推動共同富裕的實證研究
——基于2010—2019 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
張智勇,王 鳳
(1.武漢科技大學 勞動經濟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0;2.武漢科技大學 法學與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一、引言
我國社會主義本質就是實現共同富裕。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第一次對扎實推動人類共同富裕提出了重大戰略規劃,這一舉動體現了黨中央對解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不充分不平衡問題的堅定決心。當下中國面臨著經濟逆全球化、國際間動蕩、疫情等不穩定因素,使得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越發突出,加快實現人人共享的物質富裕和精神富裕進程已成為中國的必然選擇。深化改革開放以來,通過解放生產力使得我國社會宏觀經濟環境有了較大的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斷完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也在隨之變化。人民群眾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紅利的同時伴隨著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失衡、貧富兩極分化等問題,這使得“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面臨嚴峻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公平和效率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都強調要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改善公民利益和財富分配格局。第三次分配的提出為解決當前我國突出矛盾問題指明了解決的方向。
第三次分配最初是由厲以寧在1992 年于《論共同富裕的經濟發展道路》一文中提出:指在道德力量驅動下,通過自愿行為的捐贈而進行的分配。隨著經濟進入新時代,學術界主要認為第三次分配主要是“以社會為主體,以閑置資源為對象,以利益共享為原則的社會資源有效配置”的過程。第三次分配是以解決區域差異、行業差距、城鄉差距等問題為核心的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帶來的巨大的經濟紅利,使得人民追求早期的物質紅利轉向為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品質需求。第三次分配是國家基于2035 年社會環境提出的大方向政策,它強調的是通過提高公民精神文化,樂意于公益慈善進一步進行資源調節,讓資源和財富進行流動,從而對當前收入分配格局進行優化。由于第三次分配在中國發展的規模相當有限,市場發育還不完善,對降低收入極化,促進共同富裕的效果還不明顯,第三次分配的各個方面還有待優化和完善。因此研究第三次分配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將變得十分有意義。
二、文獻綜述
學者們站在不同角度研究我國共同富裕進程等相關問題,國內大多數學者圍繞數字經濟、鄉村振興、科技革命、新型城鎮化、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升級等因素和我國共同富裕的關系進行理論研究,陳斌開和林毅夫(2013)[1]從經濟增長與發展的角度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結論:中國共同富裕指數隨著經濟發展呈現非線性的U 形規律,先下降后上升。李賓和馬九杰(2013)[2]則通過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在我國城市化發展進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對縮小貧富差異,推動共同富裕具有積極推動意義。雷根強和蔡翔(2012)[3]通過實證模型研究得出我國收入再分配制度對我國共同富裕進程有顯著性影響。沈家文等(2009)[4]從計劃經濟體制的視角入手,并利用實證模型研究,提出了我國的土地產權政策變革加大了貧富差距、減緩了共同富裕進程;劉長庚等(2016)[5]通過實證得出結論,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對國民收入再分配有著顯著性影響。姚耀軍和邵麗霞(2017)[6]通過VAR模型和協整分析顯示得出,金融發展程度與共同富裕存在高度正相關關系,攻克金融發展非均衡問題有利于解決收入極化問題。Park(1996)[7]通過59 個國家的橫截面數據實證檢驗得出,勞動力擁有較高的教育水平有推進共同富裕的作用,農村地區教育不平等導致收入差距不平等,教育差距增大了貧富差距。
除去以上傳統研究主題之外,中國當前經濟在新發展格局下,從社會收入分配的角度對縮小貧富差距問題的探究也越來越表現出其政策價值和學術意義。但對于第三次分配對貧富差距的影響研究較為匱乏,吳冰和羅新平(2010)[8]認為第三次分配能夠縮小貧富差距、避免社會矛盾和增強公眾社會責任感、凝聚力。馬家喜(2012)[9]則指出我國經過了前面的兩次分配已經較好地解決了分配的效率問題,在分配的公平方面上存在明顯的不足,可以通過第三次分配,增加社會的總的福利水平,直接解決我國貧富差距的問題。馬曉娜(2005)[10]認為第三次分配有利于社會持續發展,能夠實現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實現財富轉移,增加貧困人群的幸福感。相關研究已經多次證明,第三次分配能夠有效減緩我國貧富差距、推動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中的慈善捐贈事業、福利彩票等分維度對我國貧富差距的影響作用是否明顯還需要更深層次研究探索。印華清和王寶明(2005)[11]指出第三次分配是人們由于道德支配進行救助性志愿服務,即通過籌款、捐贈、購買福利彩票、資助等方式進行資源和財富再分配,達到縮小貧富差距目標的過程。莫非和賴勤學(2017)[12]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研究分析慈善捐贈事業對社會保障水平影響,結果顯示慈善事業的發展和社會保障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關系,慈善事業的發展可以加強社會保障,從而縮小我國貧富差距,推進共同富裕。王銳(2011)[13]利用線性回歸分析指出,慈善事業的發展推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而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我國收入極化的現狀。靳環宇(2012)[14]認為慈善事業的核心就是調整收入分配關系,自愿自發對貧困人群進行捐贈,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樊麗明和石紹賓(2003)[15]通過線性回歸研究發現通過福利彩票公益金轉移支付和補貼工廠等活動,可以提高弱勢群體的可支配收入,通過發行彩票提升供給公共品從而實現財富轉移,達到了緩解公民間貧富差距推進共同富裕的目標。
既有文獻大多認為第三次分配對縮小我國貧富差距、推動共同富裕和維護社會的穩定、促進可持續發展有積極推動作用,這為本文的研究分析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基礎和探索思路。但是,目前大多數學者主要是在局部和靜態層面上進行研究,相關動態研究分析較為缺乏。基于此,本文通過30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進一步研究第三次分配與我國共同富裕之間的動態關系,并分析其區域差異。
三、作用機制與研究假設
(一)第三次分配對共同富裕的直接影響
第三次分配對共同富裕的直接影響主要體現在全面性、普惠性和漸進性。
1.從全面性來看,共同富裕不是單一維度的富裕而是多個維度和領域的富裕,不僅要物質富裕還要精神富裕,需要對精神和物質兩手抓。第三次分配能發揮自身具有道德性和自發性優勢,積極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緩解社會焦慮,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還可以以精神為支柱支撐行動,充分彰顯出人道主義的慈善性和無私性。政府積極落實第三次分配政策,通過塑造良好的文化氛圍、執行稅收優惠獎勵政策等措施鼓勵更多人自發地發揮道德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在自我滿足情況下通過慈善捐贈等形式自發去援助他人,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
2.從普惠性來看,共同富裕不是部分人的富裕,而是全民富裕,必須將全部民眾推向富裕。第三次分配通過慈善事業的發展,改善了我國弱勢群體的收入,并通過引進技術和服務政策向不同群體提供服務援助,將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依托和服務的最終對象,弱勢群體不斷朝著富裕狀態邁進,最終實現全民富裕。
3.從漸進性來看,推進共同富裕進程需要逐步進行,不能一蹴而就,要有序地緩解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行業差距,最終實現全民富裕和全面富裕。因此,第三次分配發展能通過全面性、普惠性以及漸進性三個方面直接影響共同富裕。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1:
H1:第三次分配直接促進共同富裕。
(二)收入差距的中介效應
實現人民群眾追求的共同富裕美好愿望,首先要將蛋糕做大,讓貧困人群改變現狀,達到富裕的局面。第三次分配可以通過將閑置資源有償共享,發展共享經濟,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能,優化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實現經濟增長最大化。目前中國已經達到小康社會水平,農村經濟有了巨大改善,脫貧攻堅戰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長期執行城市偏向的經濟發展政策,城鄉經濟差距依舊沒有明顯的改善。第三次分配主要是要對目前中國收入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的現狀進行調整。第三次分配秉承共享發展理念,使得人民群眾收入趨向于均衡。第三次分配作為推動共同富裕進程的內生動力,驅動社會資源自動調節作用。第三次分配通過收入再分配,將社會財富的一部分轉移給弱勢群體或者社會福利保障機構,改變社會財富極化的局面。如通過民間捐贈彌補市場的不足,緩解社會財富分布不均,實現群體間財富流動,公民間共享財富,如在2020 年新冠疫情中,第三次分配發揮出關鍵作用,武漢市收到社會性捐款25.86 億元。在《2019 年度中國慈善捐贈報告》中統計數據顯示:2019 年中國內地收到物資和現金捐贈合計達到1 509.44 億元,其中企業捐贈款物金額合計達到931.47 億元,在捐贈總量中所占比例為61.71%,其中民營企業捐贈額占一半;而個人捐贈款物金額總計為398.45 億元,占26.90%,個人單筆捐贈金額超過10 萬元的人數日益增加[16],這些善款為支持抗疫和保障民生作出了貢獻。第三次分配引導群體間財富流動共享,緩解群體間貧富差距。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2。
H2:第三次分配可以通過緩解收入差距推動共同富裕進程。
四、模型構建及變量說明
(一)模型構建
為探究第三次分配對推動共同富裕進程的作用,構建如下基準模型:
式(1)中,GTi,t為省份i在t年份的共同富裕指數,Xi,t為省份i在t年份的第三次分配指數,向量Ci,t代表一系列可能對共同富裕產生影響的控制變量;μi表示省份固定效應,δi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α1為待估參數,預期系數顯著為正。
根據假設2 可知,第三次分配通過緩解經濟差距對共同富裕產生間接影響。因此,在基準回歸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采用中介效應模型考察第三次分配對共同富裕的傳導機制,模型設定如式(2)、式(3)所示。
具體檢驗步驟包括:第一,第三次分配指數(X)對共同富裕(GT)進行回歸,如式(1)中;第二,第三次分配指數(X)對中介變量收入差距泰爾指數(URR)進行回歸,如式(2);第三,第三次分配指數(X)及中介變量泰爾指數(URR)對共同富裕(GT)進行回歸,如式(3)。
(二)變量選取和描述性統計
本文構建計量模型,探究第三次分配與我國共同富裕的關系。為了控制好除第三次分配以外的對我國共同富裕進程的影響因素,本文基于現有的研究成果,并結合實際,選取了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狀況、財政支出占比、產業結構、城鎮化水平、對外開放程度、人力資本等作為控制變量。
1.變量選取。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共同富裕水平。參考相關文獻[17-19],結合省際層面數據可得性,運用熵值法從共同富裕的發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三方面測算出共同富裕指數,記為GT。如表1 所示,在穩健性檢驗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測算共同富裕指數。

表1 共同富裕指標體系
解釋變量。本文的解釋變量是第三次分配指數。據已有研究,衡量第三次分配標準沒有完全界定。參考黃有璋等(2021)對于第三次分配的分維度形式,得出第三次分配主要形式是參與慈善事業中,慈善事業主要包括慈善救助和福利彩票。具體來說,慈善事業主要利用社會捐助收入(W)來衡量,福利彩票是用其銷售總額(L1)和籌集社會公益金(社會福利基金)(L2)總量構建一級指標。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測算第三次分配程度,記為x。從表2 第三次分配均值來看,前期我國第三次分配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趨勢為先增大后減小再增大再減小。該數據收集于《中國民政統計年鑒》、國家非營利組織數據庫以及中國社會組織網等。

表2 第三次分配發展情況
控制變量。對城鄉收入差異有影響的因素較多。(1)市場干預:參考以下現有文章研究(帥承露和劉雅,2021;衣帆和陳一正,2021;于井遠,2021),本文利用地方財政支出占GDP 的比例(fiscal)來評估中央政府對區域經濟市場活動的市場干預程度。(2)產業結構:反映出地區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利用程度。它也對中國共同富裕產生了關鍵的影響:地區GDP 中第三產業所占份額,用thirdadd表示。利用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的占比可以體現出地方政府使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程度,該比例越大,中國貧富差距程度就越小,共同富裕程度也就越高。(3)對外開放:近年來,由于我國經濟逐漸全球化,對外貿易發達使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區域間的對外貿易發達程度和地區人員的就業率關系密切,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因此對外開放程度用“進出口總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trade)”來替代。(4)城市化發展水平:它見證了社會經濟發展、社會結構轉變、農村人口逐漸遷移到城鎮的過程。本文使用人口城鎮化率(urban)即城鎮人口數在總人口數的比例作為衡量標準。(5)人力資本:由于我國貧富差距導致區域間教育機會上的資源不均衡,從而造成人們就業機會的信息不對稱(趙修渝和李湘軍,2007)[20]。陳斌開等(2010)[21]的調查顯示:提高農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可以提升、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對于減緩貧富差距有正向推動效果。據徐現祥和舒元(2005)[22]的研究,人力資本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time)這一衡量指標。計算公式為:
城鄉平均受教育年限=(農村教育+城鎮教育)/2。各省人力資本=文盲率×0+小學文化程度人口比率×6+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率×9+高中(中職)文化程度人口比率×12+大專(高職)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率×16
中介變量:大多數研究經濟差距的指標有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標只體現收入情況,不能清楚體現城鄉之間人口流動和情況[23];基尼系數僅反映收入差距,體現不出群體階級差異,泰爾指數全面考慮以上情況,所以泰爾指數作為本文被解釋變量[24]。
2.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由于數據統計的可取性和真實性,本文采用了中國2010—2019 年省部數據。避免出現異方差和波動幅度較大的問題。文章對部分原始數據進行對數處理。本文中缺失的數據,均用插值法處理。
表3 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共同富裕程度(GT)的平均數值為0.292,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0.808和0.107,這些數據說明我國各個地區之間的共同富裕進程差別還是比較大的,并且波動幅度較大,從第三次分配指數來看,最大值和小值之間差距比較懸殊,這表明有些地區第三次分配的覆蓋范圍廣,有些地區第三次分配涉及范圍小。

表3 樣本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五、第三次分配對共同富裕進程的實證分析
(一)相關性檢驗
基于固定效應模型,本文對全部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Person 檢測結果如表4 所示。

表4 變量間的相關性分析
從2010—2019 年共同富裕指數與第三次分配指數及其子維度均呈現顯著正相關,假設1 得到初步檢驗,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之間相關系數均較小,表明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二)實證分析
1.面板單位根檢驗。經過上文中對不同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可以了解到不同變量的發展水平,并發現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與我國共同富裕有著必然聯系,但還必須再做進一步的研究檢驗變量是否平穩。因此本文對不同變量的平穩性作了檢驗來證明結果的正確性。檢驗結果如表5 所示。三種檢驗方式的結果表明:不同變量的水平序列在IPS 和PPFisher 等不同的檢驗方法下,都經過了1%的顯著性單位根檢驗,顯示出具有較強的平穩性。本文所選取的數據都是平穩序列,可在此基礎上對原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表5 各變量的單位根檢驗
2.基本模型回歸結果及分析。基于上文模型的選取與構建,本文將對我國省份在2010—2019 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故本文選擇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為消除異常值的影響,本文對變量進行1%的Winsorize 縮尾處理。
在表6 列(1)和列(2)中,核心變量第三次分配指數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通過了10%顯著水平檢驗,這表明第三次分配加快了共同富裕進程,但作用效果還有待提高。從表6 列(3)~列(5)中第三次分配的分維度來看,社會捐助收入、福利彩票銷售總額、社會福利基金的系數均顯著為正,但相關系數和顯著程度均不相同,這表明第三次分配中各個分維度對共同富裕推動作用有所差異,且作用效果為福利彩票銷售總額>社會捐助收入>社會福利基金。該基準回歸驗證了研究假設1,即第三次分配能夠積極推動共同富裕進程。對于控制變量,受教育年限、財政支出占比、第三產業占比、城鎮化率、區間開放程度均對共同富裕進程產生正向影響,即第三次分配能夠積極推動共同富裕進程。對于控制變量,受教育年限、財政支出占比、第三產業占比、城鎮化率、區間開放程度均對共同富裕進程產生正向影響。

表6 第三次分配影響共同富裕的基準回歸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根據上文的回歸結果,第三次分配的發展可以促進共同富裕,但其結果是否具有穩健性有待檢驗。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再次測算共同富裕指數并進行回歸,得出結果是穩健的(見表7),假設1 得到驗證。

表7 第三次分配影響共同富裕的穩健性檢驗
(四)中介效應分析
收入差距在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之間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表8 所示。在表8 列(1)證實第三次分配對共同富裕具有正向影響基礎上,在列(2)中第三次分配對收入差距的回歸系數為負,說明第三次分配能夠縮小收入差距,列(3)中加入中介變量泰爾指數之后,第三次分配對共同富裕的回歸系數同樣顯著為正,模型(3)中第三次分配對共同富裕的影響系數相比模型(1)有所下降,表明第三次分配可以通過緩解經濟差距間接促進共同富裕,假設2 得到驗證。

表8 收入差距中介機制檢驗的回歸結果
(五)區域異質性分析
目前我國地區間經濟發展階段存在較大差異,導致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水平都存在異質性。因此,本文將30 個省份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進行回歸估計,具體結果如表9 所示。
表9 列(1)、列(2)、列(3)分別為我國區域間的實證結果,檢驗結果表明:第三次分配顯著推動了對東中西部地區共同富裕進程,在東部地區這種作用不顯著。作用效應強度呈現出“西部>中部>東部”。表明第三次分配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具有區域異質性且西部地區優于中部和東部。異質性原因可能在于相對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快,利用地理和區位優勢最大,經濟差距相對較小,第三次分配效應最弱,而西部地區利用第三次分配很好地緩解經濟差距,推進共同富裕。

表9 第三次分配影響共同富裕的區域異質性
六、結論和建議
(一)結論
本文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第三次分配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主要結論如下:第一,第三次分配能促進共同富裕,且這一結論具有穩健性;第二,收入差距在第三次分配與共同富裕之間存在中介傳導效應,即第三次分配通過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第三,第三次分配子維度對共同富裕有異質性影響,捐贈性收入、福利彩票銷售額均能促進共同富裕,而社會福利額對共同富裕的促進效應不明顯;第四,第三次分配對共同富裕的促進效應在中部和西部地區較為顯著,而在東部省份不明顯。
(二)政策建議
基于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1.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體系。首先,為更好地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政府和國家須完善第三次分配的制度體系,將第三次分配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其次,加強對第三次分配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修訂與完善,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到第三次分配當中;最后,總結第三次分配的實踐經驗形成有效的政策體系,讓人民群眾享受到共同富裕帶來的幸福感和滿足感。
2.重視收入差距中介作用。第三次分配通過縮小群體間收入差距,改變社會財富格局。在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重視在第三次分配制度法規和其他財富轉移的方式,從而達到提升中等或弱勢群體收入、縮小群體間收入差距、實現財富合理分配的共同富裕目標。
3.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因地制策。在肯定第三次分配作用的同時,首先要認識第三次分配有限的補充作用[25]。政府應因地制宜制定區域政策,通過稅收政策和技術引進政策傾斜,引導資源和技術向低收入地區和群體流動,支持弱勢群體的創業就業,縮小群體和區域間差距,更好地促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