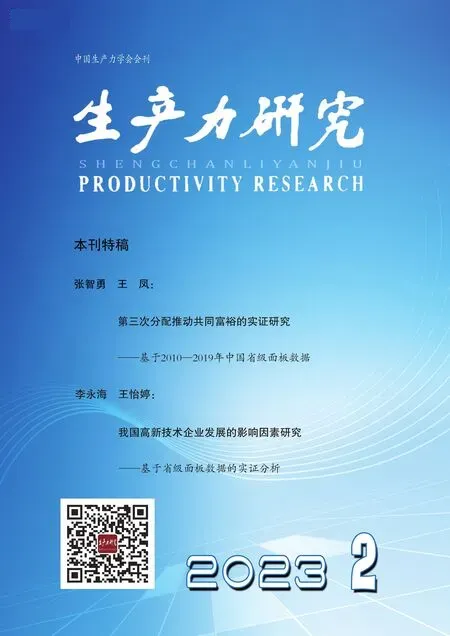數字經濟對市場交易效率的影響研究
王藝偉,余子鵬
(武漢科技大學 法學與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5)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歷年中國信通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顯示,2018—2020 年全球數字經濟規模分別為30.2萬億、31.8 萬億與32.6 萬億美元,占GDP 比重分別為40.3%、41.5%與43.7%,測算的47 個經濟體GDP平均增速為-2.8%,而全球數字經濟規模同比增長3.0%,顯著高于同期GDP-2.8%的增速,數字經濟逐步發展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力,在信通院劃分的數字經濟“四化框架”中,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發展過程的核心環節,指的是傳統產業通過運用數據這一新生產要素與新興數字技術帶來的產出增加與效率提升,涵蓋智慧農業、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數字商務等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從Williamson提出的交易三維度理解數字經濟如何影響交易效率:第一,通過大數據、云計算、傳感網、物聯網等技術實現生產無人化自動化管理,推動生產集約化規模化,降低小額交易頻率以節約人力倉儲物流等的成本;第二,諸如數據中心、工業機器人、工業互聯網平臺等的產生實現數據的泛在采集,加快信息內外部流轉,減少交易中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確定性;第三,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平臺經濟的興起以及在線教育、網絡醫療、電子政務等的服務新業態推進產業間深度滲透融合,減緩由資產專用性帶來的交易成本,改變原有的生產、創新及競爭格局。
現有研究對數字經濟的核算方式大致分為三種。第一,支出法。夏炎等(2018)[1]使用支出法通過建立非競爭型就業投入占用產出模型,測算數字經濟產業的消費、投資、出口以及其他數字經濟規模。第二,增長核算方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基于增加值核算方法構建包含信息和通信技術產品、個人交易產品、“免費”經濟的數據價值以及數字平臺流量價值四個部分的數字經濟核算框架;美國經濟分析局(BEA)基于數字商品與服務的劃分,分別測算數字經濟的名義增加值與實際增加值;國內方面,康鐵祥(2008)[2]結合輔助活動(非數字產業的數字活動)的概念,提出數字經濟規模是數字產業各部門的總增加值與輔助活動的增加值之和;許憲春和張美慧(2020)[3]同樣借鑒BEA 增加值測算方法,通過加總數字經濟相關行業的增加值測算數字經濟的總產出。第三,構建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中國信通院在測算數字經濟發展規模時,只對“四化”框架中的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部分進行核算;張蘊萍等(2021)[4]在測度數字經濟時,同樣從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兩個角度評價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對交易效率的研究首先需要參考早期國內外有關交易成本的研究。交易成本最早由Coase(1937)[5]提出,他指出交易成本由市場的價格機制產生,是企業在每次交易過程中反復發生的費用,如獲取信息、談判簽約等;Williamson(1985)[6]構建交易費用經濟學這一新制度經濟學分支,并指出交易成本由簽約的事前成本與事后費用構成;張五常(1999)[7]通過提出交易費用范式將交易費用定義為“制度成本”;高帆(2007)[8]指出交易成本是經濟活動中轉移所有權與使用市場價格機制的費用,包括技術型與制度型兩種類型。伴隨對交易成本不斷深入地研究,對交易效率的研究也應運而生。楊小凱(1998)[9]類比Samuelson(1952)關于“冰山成本”的概念,將交易過程中諸如運輸、損耗、稅收等的外生費用k 界定為外生交易效率系數;高帆(2007)[8]將交易效率定義為開展交易活動時交易主體的投入-產出關系,并外延交易費用的技術與制度分類,構建包括交通、信息、教育、市場、信用、信貸六個指標在內的交易效率衡量體系;鄭勇軍和李婷(2009)[10]將交易效率定義為交易過程中的收益與成本之比,并指出專業化與分工能夠進一步提高交易效率。交易效率概念逐步完善的過程中,如何測度交易效率也是相關領域的研究重點。趙紅軍(2005)[11]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出發,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從制度、信息通信技術與教育三個角度對交易效率進行測度;柳江(2011)[12]從基礎設施、市場化程度、城市化、公共服務、對外開放程度與政府行政效率六個方面分析衡量交易效率,并提出交易效率的提高源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制度進步以及外部治理環境的改善;韓璐等(2022)[13]從技術與制度兩個角度構建交易效率指標體系;除以上構建交易效率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方法外,還可以通過單一指標測算,如李穎慧(2020)[14]通過交通條件測算商品市場的交易效率;劉朝陽等(2020)[15]使用銷售、管理、財務費用與企業營業收入的比值來計算交易效率。
綜合已有文獻,與數字經濟相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對整個國民經濟部門高質量發展、對產業間融合與產業內轉型升級以及微觀層面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在數字經濟如何影響市場具體交易過程方面的研究則有所欠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與交易效率
依據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一派交易費用理論思想,并借鑒高帆(2007)[8]提出的交易效率研究框架,本文認為數字經濟對市場交易效率的影響主要來自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及經濟體制逐步完善帶來的交易成本的減少。具體路徑如圖1所示。首先分析技術進步方面。在對生產活動進行分析時,我們通常將去除要素投入增長外的余值增長表示為技術進步。參考續繼和唐琦(2019)[16]數字經濟帶來的信息技術進步對傳統生產、物流、銷售、通信等方式進行革新,這些數字技術的研發與應用都不同程度上對市場的交易效率進行改善。其次分析完善經濟體制方面。在研究市場均衡理論時,由于交易主體之間大概率存在信息不對稱,導致交易成本增加低效率完成交易。而隨著數字經濟發展帶來互聯網的普及與應用,可以增加市場中相關信息的透明度,減少交易雙方的搜尋與信息成本,同時在微觀企業方面也能夠緩解一部分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降低企業生產成本使交易更具有效率。綜上提出第一個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能夠提升市場交易效率。
(二)數字經濟、人力資本與交易效率
人力資本在數字經濟影響交易效率的過程中存在中介效應。人力資本主要在三個方面對數字經濟影響交易效率產生作用,如圖1 所示。第一,廣化效應。數字技術如工業互聯網平臺的興起,能夠有效解決勞動力市場中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摩擦性失業,緩解高質量勞動力的向下兼容,減少企業生產過程中的人力成本提升企業交易效率;另一方面,各地高質量人才引進政策帶來的人才空間集聚能夠產生知識與技術外溢帶來正外部性效應,并優化生產要素的資源配置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更好地形成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以提高交易效率。第二,深化效應。從需求端看,工業機器人的大規模使用與智能化生產的實現對勞動力提出了更高質量的要求,低技術勞動力逐漸被市場淘汰,高技能勞動力占比逐步上升;從供給端看,“在線教育”的發展拓寬教育模式與知識獲取渠道,自然勞動力會有意或被迫提高技能水平以升級自身人力資本結構,從而減少了企業生產的低效成本,提升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并提升市場交易效率。第三,職業創造效應。數字技術的發展催生出許多新興經濟模式諸如平臺經濟、分享經濟、免費經濟等,以及新興服務性質行業如外賣、快遞、編程、直播等。另一方面,Zigbee 技術、工業機器人等數字技術的應用促進生產自動化。數字技術的發展增加市場中商品與服務的技術復雜程度,從產品附加值角度提升市場交易效率。提出第2 個假設:

圖1 影響路徑
假設2:人力資本在數字經濟促進交易效率提升過程中發揮間接中介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綜合現有研究,本文認為數字經濟可以直接或間接對市場交易效率產生影響。為驗證假設1 檢驗數字經濟對交易效率的直接影響,借鑒張正平和王龍(2021)[17]的模型設定建立如下基本模型:
除式(1)表示的直接影響外,人力資本可能在數字經濟影響市場交易效率過程中產生間接影響,因此為驗證假設2,借鑒溫忠麟提出的中介效應模型設定如下模型:
其中,式(1)~式(3)中的下標i,t分別代表省份和年份;effi,t代表市場交易效率;digi,t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humani,t表示人力資本水平;controli,t表示控制變量,包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pGDP)、價格水平(rCPI)、市場化程度(mar)、產業結構(stru)、研發支出強度(RD)、人口紅利水平(demo)、老齡化水平(ageing);μi表示各省市i的固定效應,δt表示年份t的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市場交易效率(eff)。本文借鑒柳江(2011)[12]構建的評價體系,從交通運輸、通信技術、基礎設施、能源、制度環境、城市化水平六個層面對交易效率進行綜合評價,最終通過主成分分析得到市場交易效率指數。
2.解釋變量:數字經濟(dig)。使用數字經濟“四化”框架中的產業數字化部分,從農業數字化、工業數字化與服務業數字化三個產業數字化角度構建綜合評價體系,并通過主成分分析得到數字經濟發展指數。
3.中介變量:人力資本水平(human)。本文的人力資本水平表示高質量勞動力,因此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這一指標進行衡量。
4.控制變量:借鑒張正平和王龍(2021)[17]、韓璐等(2022)[13]的研究,選取地區發展水平(pGDP)、實際消費價格水平(rCPI)、市場化程度(mar)、產業結構(stru)、研發支出強度(RD)、人口紅利(demo)、老齡化水平(ageing)這七個變量為控制變量。
(三)數據來源與描述統計
本文采用2001—2020 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以及各地區統計年鑒等。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 所示。市場交易效率的最大值為6.188,而均值只有1.03,表明我國市場交易效率水平整體偏低,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表現出同樣的態勢,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均值為10.18,標準差為0.817,表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小;實際消費價格水平與市場化程度的標準差分別為20.43、20.2,表明各地存在顯著差異;產業結構水平的最小值為15.9,最大值為61.96,表明各地產業轉型升級的程度相差較大;研發投入、人口紅利與老齡化水平的標準差分別為2.304、3.069 與2.428,說明各地在這三個方面的差距較小。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及其分析
(一)基準回歸
在基準回歸前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低于0.7,且變量之間的方差膨脹因子均值為3.68 均低于10,因此模型不考慮多重共線性問題。其次進行豪斯曼(Hausman)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本文的實證分析應采用時間與地區的雙固定效應模型。
表2 中的列(1)、列(2)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市場交易效率的基準回歸結果。模型(1)、模型(2)分別為僅包含核心解釋變量與加入控制變量后的雙向固定效應回歸,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影響市場交易效率的系數為0.437,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也就是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提高一個單位,市場交易效率隨之提升0.437 個單位。控制變量中地區發展水平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地區經濟發展程度能夠正向影響該地的市場交易效率;從全部解釋變量角度分析,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顯著影響市場交易效率,各控制變量的加入也能夠更充分地解釋對交易效率的影響,驗證了假設1。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二)內生性分析
為解決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參考唐松等(2020)[18]的做法,將本文核心解釋變量也就是數字經濟做滯后一期處理并再次進行回歸,結果顯示為表2 中的模型(3)。其中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的系數依舊顯著為正,其他控制變量也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市場交易效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從兩個方面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是更換核心解釋變量,采用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評價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北大金融研究中心提供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對數字經濟的研究包括購物、理財、社交、保險、信貸、投資等,涉及生產生活與數字技術相關的多個層面,具有一定權威性;二是將樣本期縮短為2011—2020 年,截去數字技術發展初期的年份能夠更準確地對當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估計。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2 模型(4)所示,重新估計后的數字經濟仍顯著正向影響市場交易效率,表明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四)進一步分析
為探究數字經濟對市場交易效率產生影響的路徑,本文引入“人力資本水平”這一中介變量,并對其可能在數字經濟影響市場交易效率過程中產生的間接作用進行實證檢驗。實證結果如下表3 所示。第一列顯示的是數字經濟對市場交易效率的總效應,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的影響顯著;第二列檢驗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否對人力資本水平產生顯著影響,表明數字技術的發展可以促進區域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第三列檢驗人力資本水平是否在數字經濟的發展促進市場交易效率提升的過程中產生間接效應,結果依舊顯著表明人力資本的中介作用確實存在,驗證假設2。

表3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五、主要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對交易效率的研究主要帶來如下研究結論。第一,數字經濟發展能夠對市場上交易效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實證結果表明,提升1 單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能夠顯著提高0.4378 單位的市場交易效率;第二,在數字經濟影響市場交易效率的過程中,人力資本產生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比為16.17%;第三,由于歷史地理條件、經濟發展結構等的原因,東部和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較西部地區更能促進市場交易效率的提升。另外,研究不同時期數字經濟對交易效率的影響發現,數字技術越發展越有利于提升市場交易效率;第四,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研發投入強度與人口紅利均顯著正向影響市場交易效率,地區的老齡化水平則產生顯著負向影響。
依據上述實證檢驗得出的研究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從技術層面講,三大產業在轉型過程中應積極引入諸如5G 通信、物聯網、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利用數據的外部性、價值增值性等促進要素的產業間流動并增強其與其他生產要素間的連接性,促進數字技術與三大產業的深度融合,淘汰傳統低效的生產模式發展“互聯網+”,深度推進智慧農業、智能制造、電子商務、數字政府等新興經濟模式,降低生產、交易活動中的低效成本提升數字產品與服務的附加值,改善市場交易活動存在的低效率現象;從制度層面講,交易過程中的低效率很大程度是由于市場交易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因此,政府要促進工業互聯網平臺等的產生,增加市場中各交易主體的信息透明度緩解信息不對稱現象,以減少企業生產過程中的經營管理成本與交易過程中的事前與時候成本,提高整個市場所有主體間的交易效率。
第二,人力資本水平是數字經濟正向影響市場交易效率的有效路徑,因此各級政府應重視對高水平數字人才的培養與引進,通過數字人才聚集帶來相關數字產業空間集聚,營造良好產研融合環境提升地區數字經濟水平,通過產業整體規模提升帶來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以提高區域整體交易效率。
第三,政府要加快統籌規劃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數字技術水平,縮小與東部地區的生產技術差異,并因地制宜尋找適合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最優路線,提升西部地區市場活躍度;中部地區要加強與東部地區間數字經濟活動的交流,積極引進智能化、自動化的生產經營模式,提升數據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配置效率,降低數字產品與服務市場中的交易成本提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