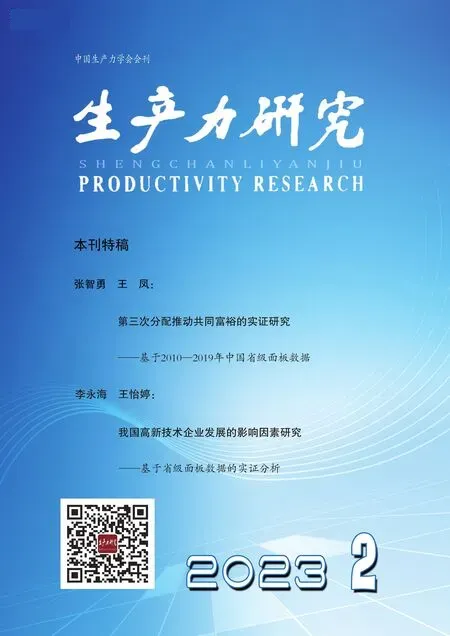如何助力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以數字經濟為視角
羅佳意
(寧波大學 商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規模持續擴大,在GDP 中占比逐年上升,目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領域,截至2020 年底,增長至39.2 萬億元。數字經濟不懼新冠疫情的負面效應,在逆境中加速前進,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為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效動力。數字經濟對于推動產業轉型方面的優勢也逐漸凸顯,我們需要緊緊抓住數字經濟帶來的契機,推進傳統產業結構向中高端產業前進,激發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所以現階段,研究如何發揮數字經濟時代優勢,探索數字經濟調整產業結構的新路徑,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文獻綜述
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數字經濟在經濟發展道路上的影響逐步加深。同時在學術界,數字經濟領域也不斷突破創新,目前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為該領域的研究重點。
(一)數字經濟內涵
在2021 年,國家官方機構對數字經濟進行了清晰的界定,具體分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部分。數字經濟是將數據資源作為關鍵生產要素、把互聯網作為傳播載體、合理運用先進的信息通信技術,最終以實現提高生產效率和改進產業經濟結構為目的的經濟活動。然而,學者們對于數字經濟暫時還未形成清晰的界定。丁志帆(2020)[1]認為數字經濟是一種新經濟形態,其核心內容是數字技術和創新。韓風芹和陳亞平(2022)[2]從技術層面、產業層面、場景應用層面和治理層面與傳統經濟時代加以區分。
在數字經濟核算層面也尚未形成統一標準。許憲春和張美惠(2020)[3]建立的數字經濟規模核算框架主要從四個方向分析,具體為數字化的交易、媒體、基礎設施和數字交易產品。李英杰和韓平(2021)[4]采用“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衡量數字經濟。宋洋(2020)[5]是通過計算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的增加值(直接效應)和數字經濟引致其他行業的增加值(間接效應)來衡量。
(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內涵
在產業結構優化方面,大部分學者主要都是從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合理化兩個方向研究(蔣瑛等,2021;戚聿東和褚席,2022)[6-7]。張俊等(2019)[8]創新地從產業結構、全球價值鏈升級和產業競爭力提升這三方面來界定產業升級。
(三)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研究
大部分學者經過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可以明顯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王奕飛等(2022)[9]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顯著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但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產生不利影響。陳曉東和楊曉霞(2021)[10]經過實證得出,對比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對產業結構轉型的優化效應更加顯著。秦建群等(2022)[11]認為與東部地區相比,我國西部地區數字經濟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具體表現尤為明顯。黃賾琳等(2022)[12]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對制造業有顯著的升級效應。周少甫和陳亞輝(2022)[13]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夠通過推動服務業結構升級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較多學者對數字經濟優化產業結構內在機制進行分析。白雪潔等(2022)[14]從需求側和供給側雙重角度分析數字經濟優化產業結構的內在機理。范曉莉和李秋芳(2021)[15]提出數字經濟會產生網絡效應、創新效應、產業融合和產業關聯效應來實現產業升級。丁守海和徐政(2021)[16]以新格局為背景,認為數字經濟通過創新、技術、降低交易成本、改變國內需求的消費端等路徑,促進結構升級并且產生新業態。田秀娟和李睿(2022)[17]從數字技術作為切入點,發現該技術與生產部門深度整合會長期助力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動能轉換的速度。涂心語和嚴曉玲(2022)[18]研究得出數字化為經濟增長賦能,國家可以通過政策導向,鼓勵企業生產方式進行數字化轉型,以此形成知識溢出效應,激發經濟內生增長動力。
(四)已有研究評析
1.已有的研究基礎。大多學者對于數字經濟的內涵有著不同的界定,在核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機制研究和實證研究也做了大量的創新,數字經濟通過創新、擴大內需、數字技術等路徑助力產業結構轉型,但不同地區間的促進效應有所差異。對于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內涵,國內學者沒有進行過多創新,幾乎都是從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兩個維度衡量。
2.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在現有的文獻中,大部分學者僅從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結構高級化兩個層面來評價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沒有進行額外的創新。但是,中國步入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產業結構轉型在現階段也體現出新內涵新特征,不是純粹追求經濟結構服務化,同時也要關注產業內技術升級支撐下的三次產業間比例變化。
3.本文創新。本文創新點在于:考慮到經濟高質量發展下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不只是包含宏觀層面一、二、三產業間的協調關系,還涉及到中觀層面和微觀層面,比如,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所以本文引入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為二級指標,聯合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服務化和三產占比,運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三、數字經濟發展驅動產業結構轉型的內在機制
結合現有的內在機制研究,本文主要從數字經濟激發內生動力層面分析產業結構轉型的內在機理。
(一)新需求創造機制
近年在來,數字經濟運用互聯網等技術將線上和線下經濟活動巧妙融合,在經濟發展中進一步發揮出積極作用。數字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消費者以往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改變了需求端,促使消費者開始消費新興產品,消費者對于產品的需求也趨于多元化發展,這對于資源的合理配置有一定的導向作用,吸引生產要素和資源流向高新技術產業,不斷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壯大。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可以為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提供強大的驅動力。數字經濟發展創造出新需求,充分激發中國的內需潛力,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二)新技術涌現機制
新經濟的出現,意味著新技術、新產品的爆發性發展,同時代表著當前社會生產方式將會出現重大的變化。數字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創造出新技術,這種技術具有高滲透性的特點,使其滲透至社會生產的各個環節,與實體經濟發展高度融合。數字經濟運用云計算等新技術,快速推動產業向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轉變。產業結構的升級離不開新技術的涌現,從企業層面來看,產業結構的升級需要依靠企業內的技術進步,不斷加快生產效率和提高產品品質,促進產品從低端向高端進步,從而推動產業升級。從產業層面看,利用數字技術的企業集聚形成新興產業,通過競爭效應實現優勝劣汰效應,最終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三)人才資本驅動機制
數字經濟發展在勞動力教育和學習技能方面具有長尾效應,有利于提升勞動力的綜合素質,放大人才資本價值。新經濟形態的出現推進了人力資本結構變動從中低端人才向高端專業性人才轉變。數字經濟發展通過高水平的人力資本來有效實現制造業的升級(黃賾琳等,2022)[12]。由于數字經濟的出現,加快了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的轉變,降低了對中低端人才的需求,加大了企業對高端專業性人才的需求。大量的中低端人才在被淘汰后將會主動進行再教育提升自身素質和專業化能力,向專業化高端型人才轉變。由此提高整體人力資本水平,促進人力資本結構的轉換,從而不斷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四、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為了檢驗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效應,本文把數字經濟引入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研究框架中進行分析,模型構建如下:
式(1)中,i代表各省市,t代表年份;uis為被解釋變量,即產業結構轉型升級;digit為核心變量,即數字經濟發展;xjit為控制變量;α0為截距項;μi為個體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干擾項。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高質量發展下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指數。借鑒崔丹等(2021)[19]提出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中的產業結構協調指標。本文將該指數分為四個部分,選取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標、產業結構服務化指標、第三產業占比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這四個代表性指標。與多數文獻中衡量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指標有所不同,由于技術市場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有顯著促進作用(張林,2022)[20],所以本文引入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作為二級指標。最后運用主成分分析法來測度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具體三級指標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測算指標
2.核心變量。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借鑒趙濤等(2020)[21]、汪文雅(2022)[22],依照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的內涵,選取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互聯網相關行業從業人數、互聯網相關產出、移動互聯網用戶數和數字金融普惠發展這五個代表性指標,運用主成分分析法綜合測度數字經濟綜合發展,具體三級指標如表2 所示。

表2 變量測算指標
3.控制變量。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具體包括:經濟發展水平(lnpgdp),即各省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取對數;人力資本水平(univ),即各省市的普通高等學校數量;城鎮化水平(urban),即各省市城鎮人口數占年末常住人口數比重;外商直接投資水平(lnfdi_gdp),即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占GDP 比重取對數;對外開放水平(lnopen),即各省市貿易進出口總額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取對數;基礎建設水平(lninfra),即各省市人均郵電業務量取對數;營商環境(market),即各省市市場化指數。
(三)變量描述與數據來源
1.變量描述。表3 為各個變量描述性統計。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
2.數據來源。由于西藏、港澳臺地區數據缺失較嚴重,因此本文選取中國30 個省市,年限為2011—2020 年的相關數據構成省級面板數據。本文選擇的因變量、核心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原始數據來源如表4 所示。

表4 數據來源
五、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首先本文需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中選擇其中之一來進行基準回歸。在此運用豪斯曼檢驗法,得出結果chi2(8)=29.23,prob=0.0003<0.01,因此本文選擇固定效應模型來進行面板回歸。基準回歸結果如表5 所示:

表5 基準回歸結果
從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無論是否納入控制變量,數字經濟的發展都會顯著促進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能夠實現助推產業結構轉型的目標。
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和基礎建設水平的提升會顯著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而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并沒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反而有抑制效應;經濟發展、城鎮化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存在正向影響,但效果不顯著;人力資本和營商環境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存在負向影響,但效果也不顯著。
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有明顯的激勵作用,這也驗證了技術溢出效應,發達國家在中國建立工廠投入資金,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技術溢出效應推動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基礎建設的完善能夠有力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基礎設施建設越完善,越有助于激發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術創新,加快產業結構升級速度(劉翠花,2022)[23]。
對外開放程度變量顯著,但其系數為負,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產業結構轉型,對產業結構轉型呈現負向影響,這是因為當前大多數第三產業仍然具有不可遠距離貿易的特征,導致國內外對于需求的消費品集中于工業制造品,國外對于我國的制造品的需求大多集中在低技術含量的制造品,而國內對于進口需求大多為高新技術產品,所以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
(二)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保證回歸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選擇滯后一期的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標,對基準模型進行回歸,表6 為穩健性檢驗結果,滯后一期的核心解釋變量(digit)仍然對被解釋變量(uis)存在顯著的影響,因此可得出本文結論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表6 穩健性檢驗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中國數字經濟規模迅速發展,不僅為經濟高質量發展賦能,而且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了強大的動力。鑒于此,本文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2011—2020 年中國省級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另外選擇七個控制變量,構建省級面板數據模型對其進行檢驗。研究得出:(1)數字經濟的發展能顯著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需要以數字經濟作為驅動力;(2)現階段中國對外開放程度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具有負向影響;(3)外商直接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根據以上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加快數字經濟發展,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政府應積極順應數字經濟時代,利用互聯網等技術為社會公眾和企業提供更加快速有效且方便的服務,積極構建大數據平臺,充分發揮數據資源優勢,加強數據要素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同時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搭建一個公平公正且合理的營商環境和制度體系,打破壟斷,進一步激發科研人員的科技創新熱情,為產業升級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第二,加強數字技術研發。由于數字技術是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不斷開發新技術、不斷進行精準創新,提高數字經濟的核心競爭力,推動數字經濟與各產業尤其是制造業和服務業深度融合,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不竭動力,最終服務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三,培養高水平數字型人才,打造高端數字化人才隊伍。數字經濟的進步,需要數字技術的不斷更新發展,對數字化人才的需求不斷擴大,因此在供給側方面,打造一支高水平的數字化人才隊伍是關鍵。現階段,我國數字化人才缺口較大,因此政府應增加教育資本投入,開設數字化學科課程,加強數字型人才的培養,提高整體人力資本水平。此外,數字化產業是涉及多學科、多領域、多技術的融合性產業,所以同時也需注重培養專業型人才和復合型人才。
第四,優化供給側,創造新需求。上述研究發現,因為國外需求主要集中在我國低技術含量的制造品,國內需求主要集中于國外的高技術含量產品,因此導致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升反而抑制了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所以企業需要利用數字經濟創新效應和提高技術來增加高新技術產品的供給,優化供給結構,充分運用數字經濟平臺,實現信息快速流通,擴大內需,來實現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第五,鼓勵投資多元化。外商直接投資水平提升可以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鼓勵外商在本國開辦企業,積極推動本土企業與外資企業間的技術交流學習,相互協作,在協作交流中,本國企業可借鑒國外的管理制度來提高管理效率,通過技術外溢效應,學習國外先進技術來提升企業自身核心競爭力;積極引進外資,合理利用外資,加大研發投入,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實現中國產業結構向中高端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