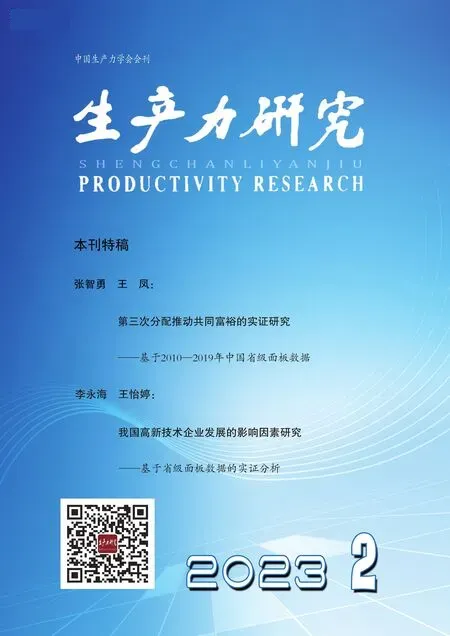產業轉型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機制研究
楊勝利,王 媛,陳 欣
(河北大學 經濟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外來加工業和對外貿易,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的重型制造業和輕工業,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人口在鄉城、地區之間大規模流動就業。2020 年“七普”顯示全國流動人口規模為3.76 億人,“鄉土中國”向“遷徙中國”的形態轉變已經形成。流動人口特別是流動勞動力資源已經成為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隨著人口轉變、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客觀上要求必須從以對外加工為主的低端產業,向擁有自主品牌自主核心技術的高端產業邁進。而產業轉型升級必然帶來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產生結構性的大規模群體性失業。當前,高質量發展背景下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主要方向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流動人口主要分布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尤其是分布在傳統的低端行業,大多數在次級勞動力市場工作,工資低、工作環境差、工作不穩定、勞動權益保障程度低,因此,在產業轉型升級中首當其沖受到影響。近年來流動人口失業率有所上升也說明了這一點,2018 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失業率為2.3%,比2011 年的1.5%上升了0.8 個百分點。那么探究產業轉型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程度多大?影響機制是什么?等問題對于揭示產業轉型升級與失業的內在機理,有效預防和控制流動人口群體性失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文獻評述
從國際上來看,“產業升級”一般指產業由低技術水平、低附加值狀態向高技術水平、高附加值狀態演變的趨勢[1]。國內學者中吳崇伯(1988)[2]最早論述了“產業升級”的概念,認為“產業升級”指的就是“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即“產業結構向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型轉化”。姜澤華(2010)[3]將中國產業升級模式歸納為傾斜拉動式、平衡驅動式和協調跨越式三種模式。潘冬青和尹忠明(2013)[4]認為產業升級包括產業結構高度化、加工程度高度化和價值鏈高度化三種表現。
產業轉型升級對失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數量和結構兩個方面:一是產業轉型升級使得勞動生產率提升,單位產出勞動力需求量減少,邊際就業彈性下降,從而增加了失業[5]。馬克思(1972)[6]認為技術進步會加速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進而導致對勞動力的需求增長速度放緩。熊彼特在1912 年首次提出“創造性破壞理論”,對周期性出現的失業危機進行了解釋。產業轉型升級破壞了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使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到影響,導致勞動者失業[7]。馮煜(2001)[8]研究發現1979—1996 年技術進步對我國失業率的貢獻度達到了23.89%。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技術創新的加快,使技術和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優勢日趨強化,失業狀況日益嚴重[9]。二是由產業轉型升級帶來的勞動力供需不匹配所造成的失業率上升。學者們普遍認為產業轉型升級中的失業更多的是結構性失業,在勞動力市場上表現為失業與崗位空缺并存[10];勞動者技能無法滿足勞動力市場需求或者居住地點不當無法獲得就業崗位[11]。同時,產業轉型升級對失業的積極影響也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部分學者認為產業轉型升級有利于增加勞動力需求,減少失業,中國服務業的發展和結構優化升級有利于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12]。同時,產業轉型升級使投資者被鼓勵依據新技術創建新的生產單位,賺取新技術帶來的利潤,會吸收新的勞動力,進而減少失業[13]。
學者們很早就開始關注勞動力在部門間轉移就業與失業的關系,劉易斯的城鄉二元結構模型中隱含的假設條件為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后全部就業。托達羅在劉易斯城鄉二元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流動人口預期收入和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同時存在是造成城市中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影響因素。Lilien(1982)[14]利用勞動力市場模型論證了失業率與勞動力在經濟部門間轉移的關系,提出了部門轉移假說,即當產業所需的技術改變,或勞動力與工作崗位所需技能不匹配時,會促使勞動力在產業部門間重新配置,但當產業吸收勞動力的速度慢于勞動力重新分配的速度時,會產生失業。Rissamn(1986)[15]在Lilien 勞動力市場模型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也發現一國產業升級會影響到其失業水平。
從流動人口就業特征來看,流動人口就業多屬于臨時性或非正規就業,就業穩定性差,失業風險高。吳紅宇和謝國強(2006)[16]調研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每人平均不到一年就變換兩次工作,還有研究顯示首次就業的新生代農民工一般三個月就辭職,流失率高達40%[17]。蔡昉(2013)[18]的研究發現農民工受教育過低,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6 年,而資本密集型的第二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的第三產業分別需求10.4 年和13.3 年。由于自身就業能力受限,流動人口過度集中在技術含量較低、替代性較強、工作條件較差的崗位中[19],社會保險參保率僅為8.22%,失業保險參保率為15.38%,接受過技能培訓的農民工比例為32.9%[20]。隨著產業轉型升級的加快,能夠吸收低端勞動力就業的行業紛紛轉型,造成這些勞動力被釋放出來無處可去而產生了結構性失業或者因就業崗位信息獲取難而產生摩擦性失業。與此同時,部分研究還認為產業轉型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存在群體差異性,比如:女性失業率高于男性、已婚者失業率低于未婚者、學歷越高失業率越低、流入地為中西部者失業率高于流入地為東部地區者等[21]。
綜上所述,流動人口的特殊性決定了有必要將產業轉型升級中流動人口群體性失業風險作為一個單獨的單元進行研究。2015 年流動人口失業率為4.94%[22],明顯高于同年城鎮登記失業率,在不返鄉的情況下,一旦失業,就會面臨較大的經濟壓力、生存壓力、家庭發展壓力、撫幼贍養壓力,需要引起社會關注。首先,已有文獻雖然對產業轉型升級與失業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但未深入區分流動人口與城鎮戶籍人口,多采用了城鎮登記失業率這一宏觀指標,沒有將流動人口考慮進來。其次,已有關于流動人口失業的文獻主要從微觀個體調查數據來分析失業的影響因素,又沒有考慮產業轉型升級這一重要的經濟環境變量,略顯不足。再次,已有將產業轉型升級作為自變量的文獻,對產業轉型升級的衡量方面多采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產業升級指數(各產業產值占GDP 比重的加總求和)等測算方法,數據均來自于某一年的統計年鑒,是一種年度發展結果的靜態體現,但是產業轉型升級是一種動態表現,不能夠有效的從縱向時間維度測量產業升級情況。因此本文利用中國2011—2018 年277 個城市面板數據和2011—2018 年國家衛計委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將影響流動人口失業風險的微宏觀因素結合起來,采用歷年各城市Lilien 指數從動態角度反映產業轉型升級,采用歷年各城市流動人口個體特征反映流動人口微觀屬性,探究產業轉型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風險的影響。
三、模型設定與數據來源
(一)模型設定
由于研究中主要關注流動人口在產業轉型升級中的失業風險,而流入地的宏觀經濟因素和城際特征均對其失業風險具有一定的影響,又存在變量選取偏差,所以采用面板數據模型來控制觀測不到的因素。本文的基準模型如下:
式(1)中,FURit為i城市在第t年的失業率,αi為城市固定效應,用來控制觀測不到的不隨時間變化的城市特征。γt為時間固定效應,用來控制觀測不到的年度特征對失業風險的沖擊。iduit為i城市在第t年的產業轉型升級情況,Xit為影響流動人口失業的其他變量。
流動人口失業風險(FUR)是本文的被解釋變量。失業風險可以用失業率隨時間的變動來衡量(周吉梅和舒元,2004)[23],也可以用失業(喪失工作)的百分比或發生率來衡量(張展新,2006)[24],后者是一個微觀數據分析方法,本文使用的是各城市宏觀數據,故此采用前者的方法來對流動人口失業風險進行衡量。從經濟學范疇來看,失業是指勞動力供給與勞動力需求在總量或結構上的失衡所形成的勞動者不能與生產資料結合的一種狀態。根據我國統計制度規定,失業人口是指非農業人口,在一定年齡內(男性為16~50 歲;女性為16~45 歲),有勞動能力、無業而要求就業,并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了求職登記的人口,即所謂的城鎮登記失業人口,與調查失業人口存在較大差異。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失業人員是指在一定年齡以上(通常16 歲及以上),在參考時期內沒有工作、目前可以工作而且正在尋找工作的人。國際上判斷失業人口具備四個條件:在勞動年齡范圍內、沒有工作、能夠工作、有就業意愿。考慮到我國新農保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規定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是60 周歲,參考以往文獻,本文將失業流動人口定義為16~59 歲,有勞動能力無工作,但有就業意愿,隨時可以投入到工作中的流動人口。根據問卷中的問題“五一前一周是否做過一個小時以上有收入的工作”判斷是否處于無業狀態,如果回答“是”則處于就業狀態,如果回答“否”則處于無業狀態,再通過問題“四月份是否找過工作”作為判斷是否有就業意愿的依據,若兩道題同時回答無業和四月份找過工作,方可界定為失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規定,就業人口加上失業人口等于經濟活動人口,經濟活動人口是16 周歲及以上,有勞動能力,參加或要求參加社會經濟活動的人口(這里采用16~59 歲的經濟活動人口)。失業率等于失業人口占經濟活動人口的百分比。
產業轉型升級(idu)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測量,本文認為產業轉型升級是一個動態過程的呈現,而不是一種靜態表現,故此,研究中采用Kuznets(1973)[25]和Kaldor(1961)[26]的做法,用勞動力在各個產業間的轉移速度來測度產業轉型升級。Kuznets 和Kaldor 認為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二產業,再轉移到第三產業是勞動效率驅使的結果。考慮到該方法的科學性和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Lilien 指數模型來測量產業轉型升級速度。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Ψ是Lilien 指數,表示流入地產業轉型升級(idu),j代表某一產業,i代表不同流入地區,EMP代表流入地每個產業的就業人數,TEMP代表流入地就業總人數,t代表時間區間。Lilien 指數越大表示在t時間內產業轉型升級越快。其中,idua為全部產業轉型升級,iduc為制造業轉型升級,idus為服務業轉型升級。
控制變量(X)包括宏觀和微觀因素,宏觀因素包括:經濟發展水平(lngdp),采用流入地GDP 的對數表示,并折算為可比價,反映各流入地經濟發展水平;就業密度(lnemd),采用流入地每平方公里從業人員數的對數表示,反映流入地勞動力供給量;產業結構偏離度(idup),用各產業的增加值比重和就業比重之比減去1 表示,反映一個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度;對外開放程度(opg),用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表示,反映一個地區貿易、開放程度和接受新技術的環境。
微觀因素方面根據前文理論分析,我們選了以下變量:流動人口年齡(age);性別(sex),這里用男性占比表示,變量賦值為男性=1,女性=0;婚姻(mar),這里用已婚者比重表示,變量賦值為已婚=1,未婚=0;戶籍性質(cit),用非農業戶籍人口比重表示,變量賦值為農業=0,非農業=1;受教育年限(edu),用各類學歷的人數乘以各類學歷的教育年限,再除以流動人口數,各類學歷的教育年限為0=沒上過學,6=小學,9=初中,12=高中,15=大專,16=本科,19=研究生及以上;社會融合(con),通過問卷中的問題“您是否同意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為其中一員”來測量,同意=1,不同意=0;流動距離(reg),用流動范圍表示,賦值為跨省流動=1,省內流動=0;參加失業保險情況(ser),用失業保險參保率表示,變量賦值為已參加失業保險=1,未參加失業保險=0。這些微觀變量采用流動人口監測數據所匯總出的每一個城市每一年的均值表示。
(二)數據來源
本文的宏觀數據來源主要是2011—2018 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由于西藏數據缺失比例較大,所以采用2011—2018 年277 個城市的面板數據作為樣本。關于產業的劃分,采用2012 年修訂后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12)的分類標準,共有門類20 個,大類96 個,中類432 個,小類1 094 個。第一產業是指農、林、牧、漁業。第二產業是指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包括: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貿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在分析制造業升級中選取了29 個行業,由于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和其他制造業等所占比重較小,在計算中沒有考慮。在分析服務業升級時,采用了統計年鑒中的所有14 個行業大類。微觀數據采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1—2018 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從原始數據中選擇出跨省流動人口,并將由于個人原因未工作人口從樣本中剔除,刪除個人屬性特征數據缺失的問卷,得到每一年的有效問卷,并將其按照流入地匹配到歷年的277 個城市中,再按照城市匯總其失業率、控制變量的平均值特征,進而得到各微觀變量的測度值,并以此作為實證分析依據。2011—2018年共涉及2 216 個城市,其中流動人口失業率均值為3.33%,平均失業時長為6.2 個月,總和失業率①總和失業率是指假設勞動力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度過勞動年齡階段,平均每個勞動力在勞動年齡期內的失業次數,是將勞動年齡人口(16~59 歲)按照不同年齡段進行統計,分別計算流動人口分年齡失業率,然后加總得到。為1.1 次(見表1)。

表1 模型變量的描述統計
四、估計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模型回歸結果
表2 模型(1)給出了沒有考慮城市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下產業升級對失業的影響。結果表明產業升級的lilien 指數每增大一個單位,失業率會升高0.093 個單位。同時,人口流入地屬性也會對失業率產生影響,在模型(2)中進一步考慮城市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之后,lilien 指數每增大一個單位,失業率上升0.142 個單位。綜合來看,考慮到固定效應后的模型中產業轉型升級對失業率的影響程度增大了1.53 倍,即不考慮城市和年份固定效應情況下,可能會嚴重低估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同樣可以從模型(5)和模型(6)制造業升級和服務業升級的檢驗結果可以驗證城市固定效應的存在。模型(6)在模型(5)的基礎上加入了城市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后,制造業升級和服務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率的影響系數分別從0.329 和0.097 上升到0.352 和0.109。可以看出,制造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程度要大于服務業升級。
表2 中模型(3)給出了僅考慮流入地宏觀因素條件下,產業轉型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結果表明,產業轉型升級每提升1 個百分點,流動人口失業率就會增加0.136 個百分點。模型(4)僅考慮了流動人口個人特征的微觀因素,結果表明,產業轉型升級每提升1 個百分點,流動人口失業率會增大0.113 個百分點。這表明流動人口個人特征對其失業的影響程度要大于宏觀經濟環境。相比于模型(2)而言,模型(3)和模型(4)中產業升級的回歸系數均相對較小。這說明,單獨控制宏觀經濟環境因素和單獨控制流動人口個人特征因素均會低估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程度。
表2 中模型(7)和模型(8)分別給出了只考慮宏觀經濟環境因素和只考慮流動人口個人特征因素條件下,制造業升級和服務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程度,結果表明制造業升級和服務業升級的回歸系數均低于模型(6),這也進一步證明制造業升級和服務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程度受到宏觀經濟環境和個人特征的制約。由模型(7)可以看出,制造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系數為0.107,大于服務業升級的回歸系數-0.019。模型(8)顯示控制流動人口個人特征條件下,制造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仍大于服務業升級,但是服務業升級也會增大流動人口失業率。相比于模型(6),模型(7)中服務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具有負向影響,即服務業升級降低了失業率,主要是因為模型(7)中未考慮流動人口個人特征。由于流動人口人力資本水平較低,人際關系較弱,鄉城流動比例大、就業波動性大等特征,所以服務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很大一部分可以由流動人口自身的弱勢特征和就業特征來解釋。同樣,相比于模型(4)和模型(8)在只控制流動人口微觀特征的回歸結果,模型(2)和模型(6)中對宏觀和微觀因素均進行了控制,結果顯示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程度均有所增大。經濟發展環境較差的地區,具備加快產業升級的后發優勢,但較差的經濟發展環境使其在技術進步中更多依靠技術引進和人才引進,形成了資本替代勞動的傾向,增加了產業升級中流動人口失業率。

表2 產業轉型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率影響的回歸結果
從控制變量來看,經濟發展水平、就業密度和對外開放程度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這說明促進經濟增長、加快人口集聚和擴大對外開放能夠有效降低失業率。模型(2)顯示,外商投資占GDP 的比重每增加1%,失業率就會降低0.11%,就業密度每增加1%,失業率就會降低0.51%。由于人口集聚除了會提升就業密度外,還會帶來技術外部性、勞動力市場稠密效應和學習效應,所以就業密度增大能夠提升流動人口人力資本水平,進而降低失業率。產業結構偏離度回歸系數顯著為正,意味著產業結構偏離度越大,失業率越高。產業結構偏離度較高,表明勞動力市場機制不健全,勞動力難以在產業間順利流動、轉移就業。在產業升級中,勞動力職業固化和流動轉移滯后,就會增加失業率。從個體特征各變量來看,性別、婚姻、流動范圍、社會融合、人力資本對失業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流動人口與當地人的關系越好、學歷越高,就業機會一般也會更多,其失業率也會越低。失業保險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失業保險體現了勞動與社會保障權益享受情況,模型(2)回歸系數為-0.193,是微觀因素中對流動人口失業影響程度較大變量。這說明勞動與社會保障權益是產業轉型升級中抑制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戶籍、年齡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流動人口中城城流動人口比重增大、年齡增大會增加失業率,而城城流動人口增多、年齡增大正是流動人口群體特征變動的現實趨勢。
(二)內生性處理
產業升級與失業率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內生性問題會影響到研究結論的穩健性。為此采用工具變量法來解決產業升級的內生性問題。城鎮化率反映了城鄉勞動力資源構成的匹配情況,城鎮化率提升與產業升級具有很強相關性,但不會對當前失業率產生直接影響。故此,選擇城鎮化率作為工具變量。Stock 和Yogo(2005)[27]認為一個良好的工具變量既要與內生變量具有強相關性,又要外生于經濟模型。只有這樣,兩階段最小二乘法(TSLS)才能優于OLS 回歸。從弱工具變量檢驗結果來看,一階段F值為27 和33,大于10 的標準值,也大于10%水平上的臨界值16.38,這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工具變量與lilien 指數之間存在較大相關性。表3中模型(1)和模型(2)采用城鎮化率作為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產業升級的回歸系數較表2中的OLS 回歸系數增大了0.013,制造業升級的回歸系數較表2 中的OLS 回歸系數增大了0.009,服務業升級的回歸系數較表2 中的OLS 回歸系數增大了0.023。這表明如果不考慮內生性問題,將會低估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影響。

表3 產業轉型升級與流動人口失業率的2SLS 回歸結果
同時,2011—2018 年流動人口失業是受該時期產業轉型升級影響,2010 年之前的產業級比較滿足外生性條件,并且與目前的產業升級具有很強的相關性,也不會對當前流動人口失業產生直接影響,是一個合適的工具變量。模型(3)和模型(4)為采用2001—2008 年各地區產業升級的Lilien 指數作為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一階段F值為38 和51,大于10,因此不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問題。模型(3)中產業升級的回歸系數較表2 中的OLS 回歸結果增大了1.87 倍,模型(4)中制造業升級的回歸系數和服務業升級的回歸系數分別比表2 中的OLS 回歸結果增大了1.44 倍和2 倍。這再次證明,由于內生性問題,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程度被低估了。
(三)穩健性檢驗
梁向東和魏逸玭(2017)[28]采用TRO(本地第i產業增加值/ 全國第i產業增加值)表示產業升級,徐敏和姜勇(2015)[29]構造了產業結構升級指數,計算公式為:ug=,1≤ug≤3,其中xi表示第i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已有文獻對產業升級的測算,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個地區當前產業結構層次的總體水平。故此,以產業結構升級指數作為衡量產業升級的指標來替代Lilien 指數,如表4所示,模型(1)和模型(2)檢驗了以產業結構升級指數作為衡量產業升級的指標時,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率的影響程度。檢驗結果顯示,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研究結論穩健可靠。

表4 產業轉型升級與流動人口失業率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由于流動人口在進入產業升級較快或較慢地區時,受不可觀測因素影響,所以可能存在選擇性偏差問題,本文采用Heckman 兩階段回歸來處理選擇性偏差問題。首先,采用probit 模型估計影響人口流入到產業升級較快地區(產業升級lilien 指數大于0.01;制造業升級lilien 指數大于0.15;服務業升級lilien 指數大于0.09)的因素,然后,在原回歸模型中加入逆mills 比例lambda,重新回歸。模型(3)和模型(4)顯示lambda 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基準模型分析確實存在選擇性偏誤,并且這種偏誤是向下的。這說明基準回歸模型中低估了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程度。在克服選擇性偏誤之后,產業升級對失業率具有更大的正向影響。模型(3)產業升級回歸系數較表2 中模型(2)的回歸系數增大了2.09 倍;模型(4)制造業升級的回歸系數和服務業升級的回歸系數分別比表2 中模型(6)的回歸系數增大了1.17 倍和1.61 倍。通過反事實計算來看,將進入產業升級快地區的流動人口樣本代入產業升級較慢地區回歸方程,發現流動人口失業率出現了下降。反之,將進入產業升級較慢地區的流動人口樣本代入產業升級較快地區回歸方程,流動人口失業率也會出現增大。這也印證了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率影響的穩定性。
(四)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率的影響機制分析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產業升級增加了失業率。那么產業升級對失業的影響機制是什么,還需要進一步討論,本文主要從技術進步效應、勞動力素質需求效應、社會化生產效應三個角度,對產業升級對失業的影響機制進行解釋。
1.技術替代效應。產業升級總是伴隨著技術進步,二者相互促進,呈螺旋式上升趨勢,技術進步一方面提升了勞動生產率,減少了單位產出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另一方面技術進步促使機器、流水線大量使用,形成了對勞動力的替代。因此,如果產業升級的替代效應存在,流動人口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的崗位就會出現大幅縮減,進而導致其失業率上升。本文使用萬人專利授權數作為技術進步的代理變量,使用流動人口失業率作為因變量進行檢驗。表5 中模型(1)~模型(3)檢驗了產業升級的替代效應是否存在。從表5 模型(5)~模型(6)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產業升級、制造業升級、服務業升級中,技術進步每增加1%,流動人口失業率分別上升0.066%、0.027%和0.031%,即技術進步增大了流動人口失業率。從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的交互項回歸結果來看,回歸系數均為正數,技術進步增強了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率的影響程度,即加劇了失業。

表5 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率的影響機制:技術進步效應
2.勞動力素質需求效應。產業升級為勞動力市場提供了大量的相對高端就業崗位,促使勞動力從低端崗位向高端崗位流動,但對勞動者技能和學歷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勞動者學習新知識、新技能需要一定時間,如果存在技能提升滯后性,產業升級就會帶來結構性失業。為了檢驗產業升級帶來的勞動者素質需求效應,本文采用流動人口受教育年限代替其素質情況,以流動人口失業率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由表2 可知,受教育年限對流動人口失業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表6 中模型(5)~模型(7)進一步給出了學歷與產業升級交互項的回歸結果。產業升級與學歷的交互項顯著為負,這說明提升學歷能夠縮小產業升級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問題。

表6 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率的影響機制:勞動力素質需求效應
表6 中模型(1)~模型(4)給出了按照學歷分組的回歸結果。樣本按照受教育程度分為流動人口學歷較高的城市(高中及以上學歷),流動人口學歷較低的城市(初中/中專及以下學歷)。模型(1)和模型(2)回歸結果顯示,產業升級、制造業升級和服務業升級對低學歷流動人口失業率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214、0.381 和0.137,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產業升級對低學歷流動人口失業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相比于低學歷流動人口,模型(3)和模型(4)中產業升級、制造業升級和服務業升級對高學歷流動人口失業率的影響程度較小。這也印證了產業升級會帶來結構性失業問題。
3.生產社會化效應。產業升級推動了勞動力不斷從傳統的低端行業向高端行業轉移,同時也帶來了傳統生產方式的破碎,即產業升級過程也是生產社會化的發展過程。自從工業革命以來,家庭手工業不斷被社會化大生產所替代,勞動者越來越難以依靠傳統的“父母帶子女”“師傅帶徒弟”“哥哥姐姐帶弟弟妹妹”的方式實現技能提升。每一次產業升級都在改變著生產力,推動著生產關系升級,把勞動者不斷地推向社會化生產。社會化生產把勞動者技能提升和勞動保障的責任主體不斷的由家庭、小作坊、微小企業推向社會保障。如果社會保障、就業培訓和技能提升等公共服務政策不完善,產業轉型升級就會帶來較大規模的失業率上升。如果產業升級帶來的生產社會化效應存在,則社會保障會降低流動人口失業率,反之則會增加失業率。本文使用失業保險參保率作為社會保障的代理變量,以流動人口失業率為因變量進行回歸檢驗。表(7)中模型(5)~模型(7)檢驗了社會化生產效應是否存在。從回歸結果來看,失業保險參保率與產業升級的交互項顯著為負,即社會保障降低了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率的影響程度。
同時,表7 給出了按照是否參加失業保險分組的回歸結果。模型(1)和模型(2)對應沒有參加失業保險樣本;模型(3)和模型(4)對應參加失業保險樣本。相比于模型(1)和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產業升級的標準化回歸系數要更小,這說明產業升級對沒有參加失業保險的流動人口的失業率影響更大。這也證明產業升級會進一步推動生產社會化,如果社會化的技能提升、學歷提升、就業培訓政策不到位就會加劇失業問題。

表7 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率的影響機制:生產社會化效應
五、主要結論與啟示
文章利用2011—2018 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和各城市宏觀經濟數據,分析了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風險的影響,并討論了這種影響的內在機制和異質性,并使用工具變量克服內生性偏誤,驗證結果表明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與以往文獻相比,本文中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影響程度更大,因為報告中加入了城市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并且本文采用了動態指標衡量產業轉型升級,克服了以往采用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靜態指標衡量產業轉型升級的弊端。并且考慮到了流動人口群體特征屬性這一微觀因素。
采用Heckman 兩階段回歸控制了選擇性偏差之后,發現進入產業升級較慢地區的流動人口要比進入產業升級較快地區的流動人口更具有人力資本優勢。學歷是流動人口選擇流入城市的重要影響因素。在控制選擇性偏誤后,受教育程度對流動人口失業的抑制作用變得更大。
進一步檢驗產業升級對流動人口失業的作用機制發現,產業升級通過技術替代、勞動力素質需求、生產社會化途徑對流動人口失業造成影響。產業升級中機器流水線的大量普及,必然會減少對勞動力總量的需求,進而產生失業;產業升級對勞動力素質的需求是流動人口結構性失業的主要原因。產業升級推動生產社會化,而勞動力市場機制不健全,公共服務不到位,也會提高失業率。
產業升級會帶來失業風險,因此流動人口要在流動和失業之間權衡取舍。考慮到經濟環境較好、公共就業服務較完善、勞動力市場較健全的地區對產業升級帶來的失業效應的對沖能力更強。可以認為,流動人口仍會進一步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集聚,但是受限于自身人力資本水平不高的現實,二線城市、三線城市、四線城市,甚至是縣城也將會是流動人口的主要集聚地,就近流動會越來越多。也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解釋流動人口對流動和失業的權衡,一是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在流動中才可以更好地發揮其在穩就業、增收入中的作用,所以部分人群仍會選擇長距離流動;二是隨著中小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的加快和鄉村振興的推進,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并且可以降低因長距離流動而帶來的失業風險,中小城市也成為流動人口集聚的新去向,所以部分人群會選擇就近流動或者不流動。
本部分研究結論得到以下啟示:
首先,產業升級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未來趨勢,應該充分重視產業升級帶來的生產社會化問題,盡早出臺政策,完善就業培訓和人力資本提升機制,做好應對生產社會化的問題的準備。推動勞動保障制度從依靠企業保障、家庭保障向依靠勞動者個人保障、社會保障轉變。
其次,伴隨著“西快東穩”發展格局的形成,考慮到經濟不發達地區失業率仍較高,而其產業升級速度較快的現實,要加快完善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本提升機制,尤其是加大對農村地區人口的教育投入,這對于進一步降低失業具有十分大的積極意義。
再次,應該采用多種措施,吸引流動人口回鄉創業或就地轉移就業。人口長距離流動仍然存在一定的負外部性。比如城市擁堵、高昂的生活成本、市民化困難、社會融合度低等問題,不僅不利于實現共同富裕,也不利于降低產業轉型升級的社會風險。
同時,發達地區應該采取更加包容的政策,將公共服務、就業培訓、社會保障、職業規劃、就業引導等盡快擴大覆蓋到所有勞動者,構建包括靈活就業、個人創業、兼職就業人員在內的勞動力市場動態監測機制。建議進一步完善援企穩崗、以工代訓等政策,將政策中的規定“直接將補助資金發放給企業”,轉為發放給勞動者個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企業生產經營具有自身規律,投資和用人需求都是一種理性選擇的結果,不會因為這部分補貼,而去多雇傭勞動力;二是這部分補貼對于經營不善、效益較差、瀕臨破產的企業來說沒有補救意義,也不會帶來就業效應;三是真正需求這部分補助的人員是已經失業或者需要培訓和人力資本提升、面臨就業困難的人員和大量徘徊在低端就業崗位的低收入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