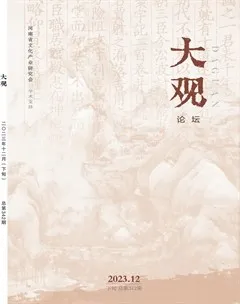八大山人藝術之表現
吳小燕
摘 要:品味八大山人的作品,就是在閱讀一個大孤獨、大悲寂的靈魂,如同站立在深秋或初冬的寒風中,枯葉從身邊掃過,人們會打一個寒噤。八大山人以自己對蒼涼人生遭際的感受入畫:他用大寫意手法畫出的一枝一葉,都是自己生命的骨血;他筆下深澗中的鳥,都是自己內心無聲的哭訴;他畫出的丑石怪魚,都是自己倔強與傲岸的寫真。“橫涂豎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這句“墨點無多淚點多”,夫子自道,最言簡意賅地道出了八大山人繪畫藝術特色和作品所寄寓的思想感情,只有沿著他所提示的這條線索,人們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欣賞這位偉大畫家的藝術作品。
關鍵詞:八大山人;筆墨;藝術表現
一、詩畫中的人品氣節
八大山人(1626—1705年),明末清初畫家,原名朱耷,八大山人是他晚年的號。他的山水畫簡潔疏曠、靜穆圓潤,看似漫不經心,筆筆無出法度之外,意境自在其中。八大山人特殊的人生經歷影響了他的藝術傾向,他常運用借物抒情的手法表現強烈的藝術個性,尤其在花鳥畫方面,其運用了多種象征手法進行創作,賦予了作品深刻的寓意。他的山水畫多為水墨的形式,給人以枯索冷寂、滿目凄涼之感,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簡樸之氣,反映出他孤憤的心境和個性。八大山人在其晚期的作品中,把客觀物象與自我精神融為一體,塑造出物我合一的藝術形象。他畫的石頭大多上大下小,有岌岌傾倒之勢。當人們試圖通過西方形式分析法理解八大山人的作品時,會發現這是一條行不通的路,這大概就是文人畫的魅力所在。文人畫本就是悅心而非悅目的,求于形式之外是蘇東坡以來文人畫的基本宗旨。基于此,在欣賞八大山人的繪畫作品時,往往需要關注其作品中的那些題詩,特別是八大山人的自題詩,否則會感到難以理解。八大山人的《魚樂圖》卷可以使人們在不同的生命階段產生不一樣的生命感悟。初讀時人們會感嘆于筆墨的精妙、意境的唯美,再讀時所見所思的是當下生命的超脫之美。觀此卷整體面貌,大體上可以將其分為三段。
第一段右上角以干筆和焦墨畫出幾抹墨影,很難描述出這是什么具象的實物,有點像懸崖或是河流,又像是煙霧籠罩的山巒。在該圖像的左邊,可以清晰地看到幾朵小花,但并不能看出是什么花,如果僅僅通過看圖形的方式了解這幅作品,顯然是十分困難的,但好在八大山人在旁邊題了一首詩:“去天才尺五,只見白云行。云何畫黃花,云中是金城。”相比八大山人其他晦澀的題詩,這首題詩較為簡單明了。“金城”在禪家口中是天府的意思,通過這首題詩,人們可以大概得知這段所繪的是天國景象。
《魚樂圖》卷的第二段為兩條魚和一塊怪石。八大山人畫的魚大概是我國繪畫史上最具特點的。該圖卷上的這兩條魚,一大一小,一左一右,都有著怪異的眼神。很多人說,八大山人借翻白眼的魚來嘲弄新政權,同時表明自己的立場。這兩條魚共同構成了一個“人”字,如同八大山人簽名中的“人”。兩條魚的上方有一首題詩:“雙井舊中河,明月時延佇。黃家雙鯉魚,為龍在何處?”。歷史上黃庭堅出生于江西雙井村,后人因此也稱該地為“黃雙井”。這首詩的前兩句頗有時間交錯的味道。雙井村的河還是過去的河(今天這條河被當地人稱為“明月灣”),而今天的明月就在雙井上靜靜地觀照著歷經了不知道幾千年的河流。“黃家雙鯉魚,為龍在何處?”,這句詩的意思是黃山谷家鄉的河中有兩條鯉魚,如果已經幻化為龍,而今龍又在何處?八大山人看似在說黃山谷的故事,實則是借黃山谷家鄉的河來說一個天地故事。畫面中的兩條魚,是八大山人心中的“雙鯉魚”,怪石的存在也頗為有趣。怪石橫亙在雙魚和金城之間,似乎就是一道坎,鯉魚躍龍門的龍門,豈不是這怪石?這怪石一點也不圓潤,棱角分明,要躍過這道龍門實在不易。大魚朝著怪石的方向,似乎在想著怎么躍過去;而小魚朝著相反方向,似乎想著“還是算了”。這如同人們人生中常常面臨的兩種抉擇,這種矛盾感同樣充斥在八大山人的心中。人在怪石前,左右抉擇何其艱難。躍過了怪石,便直奔金城,或者轉身朝向一個安逸的密林。看到這里,再聯想八大山人的生平經歷,似乎也能明了其中意義。
第三段畫的是深山高林。筆墨極為抽象,只用極為概括的線條勾勒出了山林的形態,濃墨、淡墨肆意染出一種迷幻的山林效果。這與傳統中國山水畫中的山林表現完全是兩種路子。八大山人已經完全摒棄了“形似”的部分,追逐的是心中的山林。山的下方似有荷葉叢生,中間的小魚正朝著荷葉深處游去,去尋一個幽閉之地,不再關心世事。左上方有題詩一首:“三萬六千頃,畢竟有魚行。到此一黃頰,海綿冷上笙。”前兩句形容的是浩渺無際的大海,有魚兒自由自在地暢游其中。天大地大,生命原本是自由的,就像一條魚在浩瀚的海洋中,無拘束、任逍遙。“到此一黃頰,海綿冷上笙”,詩意一轉,一條小魚在這云山云海之中,卻顯得如此孤寂無助。前兩句說的是八大山人心中的生命愿景,后兩句則是現實的生命際遇,體現在圖畫中,便是高山、密林與幽荷所構筑的一個大宇宙。生命在其間看似自由、無拘無束,卻時時因為自己不隨波逐流而感到無助和孤獨。每個平凡的“黃頰”都應該是獨立且有趣的,然而在這混沌的宇宙中,平凡終歸平凡,有趣終歸無趣。兩條魚在這混沌之中,似在水中游,又似在云中飛。游往何處?飛往何處?誰又能說得清楚明了?
他57歲時畫了一幅《古梅圖》,畫面中有這樣一棵古梅:樹根外露,主干空裂,樹頂光禿蟠屈,疏枝下垂,瘦硬如鐵,枝上數朵梅花用濃淡相間的墨色點成,形象挺拔古怪,雖然根不著土,但是卻顯示出頑強的抵抗力和生命力。畫的上方先后題了三首詩,其中有這些詩句值得人們注意:第一首里“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魚掃虜塵”的詩句正是作者驅逐韃虜、還我山河愿望的表露;在第二首的“梅花畫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的詩句里,思肖是畫梅專家,采薇指的是不食周粟的商代故臣伯夷和叔齊采薇首陽山的故事,這里體現了畫家懷念故國、效仿古人而不能的矛盾心理;第三首的“苦淚交千點”則使人們想到作者悲痛欲絕、淚流滿面的情景。八大山人作這幅畫的時間已經是康熙二十一年了,這時明代滅亡將近四十年了,他雖然有反清復明之志,但是看到清朝的統治日益鞏固,希望破滅的絕望和痛苦在他的內心交織,欲罷不能。作品筆墨簡練,加上作者所題的詩,詩畫合璧,充分體現了元代以來文人充滿趣味的繪畫風格特點,可謂筆筆含情、句句噙淚。
二、寄情于筆墨
八大山人熱衷于畫墨荷,他在《河上花歌》中寫道,“實相無相一顆蓮花子,吁嗟世界蓮花里”,從中大概可以判斷八大山人通過蓮的形象來看世界的實相和無相。在一幅荷花冊頁中,八大山人寫道,“一見蓮子心,蓮花有根柢,若耶擘蓮蓬,畫里郎君子”。蓮花代表著清涼的智慧與清凈的功德,八大山人自然懂得與蓮花相伴以觀心。《墨荷圖》中“八大山人”簽名下面有一枚“八還”朱文印章,“八還”源自《楞嚴經》。八還小印被大量使用于其晚年的作品之中。通過《楞嚴經》中的“八還”之意,可以對八大山人的“八還”進行基本的解讀,即追逐清涼無塵,向往光明之境。在《河上花圖》卷這幅人生寓言式的作品中,人們看到了八大山人人生中的四個階段,而在最后一個階段,即其晚年時期,八大山人顯然已經放下塵世的羈絆,專注于繪畫,或者專注于自己內心世界的光明,此時繪畫真正達到了不為悅目、只為悅心的境界。《墨荷圖》縱185 cm,橫91 cm,畫面中有一巨石,巨石旁邊有一叢荷葉,荷葉下部又有若干小石頭,墨色稍淡,用筆雖縱,但是可以看出八大山人在繪制這幅作品時,心境上也是平和的。畫面的下方看不出水的痕跡,荷葉的基底部分與石塊的基底處在同一個平面上,大致可以看出這是一處稍顯干涸的荷塘。當然,這也是八大山人繪畫的一個特征,即將空間抽象化,不作具象表現,給人一種超越空間的幻滅感。在八大山人其他作品中也可以看到這種脫離具體空間的表現手法。例如《魚》,畫中的魚仿佛游弋在水中,又仿佛翱翔在空中。話劇舞臺上的背景效果是極其戲劇化的,完全服務于舞臺內容,八大山人的繪畫作品同樣具有這種視覺效果。再看畫面下方,兩塊石頭如同一扇門,將外面荷塘的世界與一個神秘位置的世界連接在了一起,在白石頭上皴擦幾筆淡墨,效果仿佛那個神秘位置的世界里隱隱約約中呈現出來的幻想,墨荷的莖干用篆書的圓潤線條來畫,將荷莖的挺拔氣質生動地表現出來,荷葉的表現有抽象有具象、有淺有深,雖然總體上運用了淡墨,但依舊表現出極為豐富的層次感,中間顯然是一大片殘破的荷葉,但是這不妨礙荷葉本身所展現的生命力以及殘而不屈的品質,這就如同八大山人晚年對自己人生的態度,雖然經歷了人生中的各種磨難,但是依舊堅強,與命運倔強地抗爭著,而他抗爭的方式就是選擇放下塵世,在藝術的世界中尋找精神的寄托。在一片墨荷葉中,幾朵蓮花或盛開或半開地藏在大片的荷葉中間,就像世間每個人所處的狀態,有的面臨著江湖的風波,選擇將自己藏在一個安全的角落;有的極力想要走出重重困境,尋找向上的生存空間;有的則安于現狀,享受眼下不變的狀態,而八大山人顯然是另外一種。一朵碩大的荷花高傲地伸展著自己的“頭顱”,沖出荷葉,傲立于天地之間,潔凈的荷花花瓣似乎在陽光下散發著熠熠的光芒。荷花的莖干并不會因為荷花的重量而有所曲折,世界的一切都在荷花的俯視之下。這朵荷花沒有依靠,孤零零地立在風雨陽光中,立在天地宇宙中,使人很容易想到,這大概是在說八大山人自己。荷花的背景空白無一物,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本就是無一物而來,又無一物而走,人生而孤獨,這大概也是生命的本質。巨石上蔓延著一些花卉,它們相互依偎,緊靠大石,一簇簇、一叢叢盤踞在一個狹小局促的空間里,這種局促與荷花的自由形成了強烈對比,人們的視線不自覺地會在荷花上停留。孤立存在的荷花與攀附于巨石的花卉,象征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以及兩種不同的生命態度。世人多為攀附巨石的花葉,而八大山人是那孤零零屹立于天地之間的一朵荷花,這是一朵圣潔的荷花,一朵出淤泥而不染、不隨波逐流、不被環境所束縛的荷花,畫里“郎君子”說的正是八大山人自己。八大山人通過繪畫、題詩、篆刻等藝術形式,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生命美學,但是這些并不是有意而發的,繪畫也好、篆刻也罷,都是隨心而發的。從19歲開始,八大山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生命狀態,這段時間的八大山人是孤獨苦悶的,在生活中他也處處感受到這個世界帶給他的悲涼,也許八大山人天生就是一個內心敏感而脆弱的人。其生命的下一段旅程始于四處云游作畫,在這一時期八大山人創作了大量隨心而發的作品,這是八大山人對“隨意而往,觸物即成”智慧的踐行,他的繪畫也做到如此。人們所看到的八大山人這一時期的作品,并非人們傳統認知上的古典山水,花鳥也非傳統意義上的花鳥,一山一水、一花一鳥,無不是“心知所見”的呈現。從朱耷到八大山人的轉變是從他60歲開始的,過去的朱耷害怕孤獨,現在的八大山人則樂在孤獨中,那些孤獨的鳥兒、孤獨的足跡、孤獨的魚,無不是八大山人生命的真實寫照。
三、結語
八大山人的創作與徐渭的創作有共通之處,他們都不做太多的算計,其作品常常給人一種古拙或者怪異的感覺。一如陳洪綬的作品,有一種對古典藝術時代所形成模式的“背叛”,他們當然不是真正的“背叛”,而是將自己對生命的思考融入作品。《墨荷圖》中孤傲挺立的荷花是八大山人,也是繁雜的世界里每個生來孤獨的人們,無不如同這朵蓮花一般無依無靠地存在于這個世界,若干年之后,無不是荷塘淤泥中的一抹。八大山人曾提出“畫者東西影”的觀點,他對世界的看法不是具象的,而是抽象的,是一抹影子。因此其作品中的荷花、荷葉或者魚鳥,常常給人一種幻滅感,這些如同幻影一般的物像在經驗之外的時空中,被八大山人重新進行了架構,這種對圖像進行解構又架構的方式給觀者帶來一種陌生感,但是沒有人會認為他畫的不是荷花、荷葉,不是魚鳥,是因為八大山人心中的荷花、荷葉、魚鳥曾在每個人的生活中出現過。有所依靠便有了羈絆,有了羈絆便無法隨意而往,知道自己生無所依的八大山人,便可以做到隨意而往。人們常常會覺得不自由,是因為有太多的羈絆,如家庭的羈絆、情感的羈絆、事業的羈絆,甚至是夢想的羈絆。《小王子》里有一句話,“如果你想要與別人制造羈絆,就得承受流淚的風險”。因為有了太多的羈絆,面對內心的呼喚,人們只能無奈地躲在荷葉底下“流淚”。孤獨未必是不好的,孤獨同樣也可以很美。八大山人為人們呈現的繪畫作品有一種靜穆的美感,想必是其內心的孤獨使然。因為孤獨,其繪畫作品充滿了生命張力以及超脫之美,也因為孤獨,人們在八大山人的繪畫中讀懂了自己。千山萬水的風景,不及心中那朵孤獨的荷花身影,姹紫嫣紅的物象,不及心中那抹孤獨的墨色。
參考文獻:
[1]范曾.八大山人論[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5):130-138.
[2]楊彥霞.八大山人藝術風格研究[D].臨汾:山西師范大學,2014.
作者單位:
廈門城市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