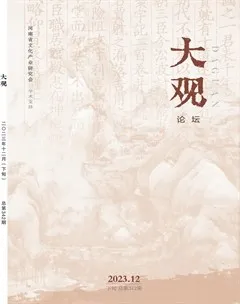鉛華洗盡時,清氣滿乾坤
易甜甜
摘 要: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宋人無名氏《百花圖》卷,以手卷的形式,純以水墨描繪了60余種各色草木花卉,其間點綴禽鳥草蟲、游魚青蛙,生意盎然,蔚為大觀,是中國古代繪畫史上的一件稀世珍品。以《百花圖》卷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和墨花墨禽的淵源來分析《百花圖》卷的繪畫語言、樣式和技法特點,探索《百花圖》卷獨特的文人審美情趣和豐富的筆墨世界,研究其在表現(xiàn)意境上各種技法的綜合性運用。
關(guān)鍵詞:《百花圖》;墨花墨禽;文人情趣;意境
墨花墨禽①自五代產(chǎn)生,兩宋逐步發(fā)展和壯大,元代趨向繁榮,明清達(dá)到鼎盛,用筆用墨達(dá)到極致。宋代作為墨花墨禽發(fā)展和逐步演變的一個重要過程,產(chǎn)生了大量經(jīng)典的藝術(shù)作品,如崔白的《寒雀圖》、趙佶的《琵琶山鳥圖》、趙孟堅《水仙圖》、佚名《百花圖》卷、法常的《松樹八哥圖》等是流傳至今的不朽經(jīng)典。本文探討的《百花圖》卷(以下簡稱《百花圖》)是著名的宋畫之一。《百花圖》以造化為師,在典雅寫實的宮廷院體畫的造型和勾染之外,采用清新、純凈的水墨形式表現(xiàn)了眾多花卉,塑造了真實、自然而又富于筆墨情趣的藝術(shù)形象,同時賦予眾多花卉神韻,與北宋的畫派有所區(qū)別,又與梁楷、法常等豪縱的水墨格調(diào)明顯不同,形成了一種新穎獨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推動了后世水墨花卉畫的發(fā)展,對中國繪畫史有著突出的貢獻(xiàn)。
一、《百花圖》與墨花墨禽的興起
在中國美術(shù)史上,宋代是一個重要的發(fā)展階段。由朱熹提出的“格物知致”[1]的口號,普遍應(yīng)用于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在美術(shù)形象的創(chuàng)作上特別在繪畫方面有著突出的表現(xiàn)。從皇家參與到文人士大夫引導(dǎo),從宮廷畫家的創(chuàng)作到民間畫家的競爭,12世紀(jì)初葉的中國繪畫發(fā)展到了相當(dāng)成熟的階段。在宋理學(xué)思想的影響下,宋代畫家對事物的真實再現(xiàn),較唐人有了深化,尤其在宋徽宗“形似”“格法”標(biāo)準(zhǔn)影響下以及帝王的親身參與實踐中,大批優(yōu)秀畫家和皇皇巨制的經(jīng)典藝術(shù)作品如雨后春筍般展示在世人眼前。
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宋代《百花圖》,正是中國古代繪畫史上的一件稀世珍品。作者在白麻紙上以水墨描繪了60余種草木花卉,其間點綴禽鳥草蟲、游魚青蛙,穿插布置,宛若天成,生機(jī)盎然,蔚為大觀,堪稱皇皇巨制。通過與存世的宋代花鳥畫作的對比,可以看出《百花圖》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和技法特色與趙佶、揚無咎、趙孟堅這三者有某些相似之處[2]。
從《百花圖》的墨筆運用也可以追溯墨花墨禽的淵源:一為五代興起的以徐熙為代表的江南花鳥畫派的影響;二為北宋中期文人士大夫簡逸畫風(fēng)的興起;三是宋代帝王的參與特別是徽宗趙佶的喜好和推動,將文人情趣引入宮廷繪畫,改變了自唐以來,富麗堂皇的宮廷繪畫追求裝飾性的傾向,為院體畫家打開了一道文秀抒情的大門。依據(jù)文獻(xiàn)資料,墨花墨禽繪畫自五代時期興起,以出生于江南地區(qū)的徐熙為首,其出身仕宦名門,常游園圃,志節(jié)高遠(yuǎn),其在《翠微堂記》自詡“落筆之際,未嘗以傅色暈淡細(xì)碎為功”[3]。他崇尚落墨之法,用筆無拘無束,作品題材多為寒蘆野鴨、雜禽花竹、蔬果魚蟹,其作不講究精細(xì)的描摹,這在當(dāng)時已是非常難得,李后主愛重其跡。
宋初宮廷畫院雖以黃筌富貴體為首,但并未完全摒棄徐熙之風(fēng)。劉道醇《宋朝名畫評》中記載,“太宗因閱圖書,見熙畫安榴樹一本,帶百余實,嗟異久之,曰:‘花果之妙,吾知獨有徐熙矣,其余不足觀也。遍示群臣,俾為標(biāo)準(zhǔn),為上所稱如此”。《宣和畫譜》中記載的北宋末的宮廷收藏中,徐熙的畫作達(dá)249件,同時給以“獨徐熙落墨寫其枝葉蕊尊,然后傅色,故骨氣風(fēng)神,為古今絕筆”的評價[4]356。許多文人鑒賞家對徐熙的評價也高過黃氏,劉道醇在《宋朝名畫評》中論及花鳥畫謂“(黃)筌神而不妙,(趙)昌妙而不神,神妙俱完,舍熙無矣”“宜乎為天下冠也”;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給予徐熙“學(xué)窮造化,意出古今”的評價;米芾認(rèn)為“黃筌畫不足收,易摹;徐熙畫不可摹”[4]356。由此可見徐熙畫藝高超。
這種典型的江南畫風(fēng)、“翎毛形骨貴輕秀”的野逸情趣、高古恬淡的風(fēng)格受到人們的喜愛。在徐熙的影響下,北宋時期產(chǎn)生了不少名家,如來自江淮以南的濠梁地區(qū),性情疏放的崔白,其花鳥畫體制清澹,善畫蘆汀葦岸的野逸之趣,受神宗青睞被招入畫院,其強(qiáng)烈的文人氣質(zhì)吸引了一大批上流之士的喜愛,進(jìn)一步打破了黃家富貴體在宮廷中的壟斷地位。這些擅墨花墨禽的宮廷畫家為南宋《百花圖》的創(chuàng)作在技法上奠定了基礎(chǔ)。而同一時期強(qiáng)調(diào)超凡水墨技巧的文人畫,也推動了墨花墨禽的發(fā)展,豐富了中國畫的表現(xiàn),給此時的畫壇帶來了生機(jī)。
產(chǎn)生于這一時期的《百花圖》精妙的用筆一方面體現(xiàn)了高超的院派技巧;另一方面,在社會大背景的影響下,其拋棄了以往濃艷設(shè)色的手法,轉(zhuǎn)用清新的水墨渲染。長卷式構(gòu)圖影響了后世的文人繪畫的格式,手卷便于攜帶,方便人們交流觀賞,這一形式更加適應(yīng)了文人們的需求,也打破了宋代以往團(tuán)扇小品、屏風(fēng)立軸等構(gòu)圖。嚴(yán)謹(jǐn)優(yōu)美的造型結(jié)合清新淡雅的水墨渲染,是當(dāng)時主流的審美傾向。《百花圖》對后世許多畫家的創(chuàng)作思想、表現(xiàn)技法和審美觀都產(chǎn)生了影響。
二、《百花圖》的藝術(shù)風(fēng)格探究
《百花圖》以白描為主,以濃淡變化豐富的水墨暈染而成。全卷縱31.5 cm,橫1 679.5 cm,繪有梅花、山茶、牡丹、芍藥、芙蓉、荷花、罌粟、萱草、碧桃海棠、梨花、錦葵、桂花、蘭草等花卉,以禽鳥小魚、草蟲蝴蝶點綴,生機(jī)勃勃,富于情趣。
其構(gòu)圖大方均衡,大致以冬春夏秋為順序,將諸多花卉規(guī)整地羅列其中,但是又有著起伏的變化,不會顯得呆板。穿插布置看似依據(jù)自然生態(tài)進(jìn)行,但細(xì)細(xì)體會其各個場景的安排,可以看出作者是經(jīng)過精心布置的,對于四季動植物的習(xí)性和特征有著較為深入的體察和研究,亦可看出作者對“經(jīng)營位置”的高超能力,將宋代花鳥畫構(gòu)圖精巧的特色體現(xiàn)了出來。《百花圖》的造型設(shè)計十分嚴(yán)謹(jǐn),對花卉的枝莖、花葉勾勒精細(xì)優(yōu)美,花瓣葉片翻轉(zhuǎn)自然流暢,紋理清晰可辨,用筆有力均勻,轉(zhuǎn)折之處變化精妙,可以看出作者應(yīng)是受過嚴(yán)謹(jǐn)?shù)幕B畫繪畫訓(xùn)練,功底深厚,墨色渲染流動有致,層層罩染深淺得當(dāng),結(jié)合精妙的用筆,產(chǎn)生了一種清新的風(fēng)格和淡泊的意境。
宋代的宮廷院體畫有著特有的藝術(shù)魅力,其濃艷的色彩,嚴(yán)謹(jǐn)?shù)牟季趾图?xì)致的用筆都給觀者帶來了巨大的視覺震撼。但是由于其富麗堂皇的風(fēng)格,以及創(chuàng)作者大都是宮廷畫家和貴胄的原因,也有人抨擊其過于艷麗,格調(diào)雖典雅富麗卻不夠高雅飄逸。在這方面,《百花圖》雖然沒有徹底跳脫出宮廷院體畫的框架,但是在整體的審美上營造了一種嶄新的意境——淡泊、幽靜、清新。
南宋的花鳥畫大體上是處于一個由設(shè)色工筆畫向文人水墨畫過渡的時期,從“富貴堂皇”向“清幽雅致”轉(zhuǎn)移是這一時期的特點。但是具體到畫面的表現(xiàn)上,則有多種選擇,如李安忠融合黃筌、趙昌、崔白的風(fēng)格創(chuàng)作的《野菊秋鶉圖》,構(gòu)圖上取山坡一隅,荊草杞菊叢生,鵪鶉覓食神態(tài)生動,富有活力,畫面經(jīng)營上比起北宋院體畫更多了一層詩意,但技法表現(xiàn)上基本還是秉承了北宋一脈的特點。而揚無咎的墨梅畫法對后世的文人畫家影響較大,《百花圖》中的梅花在構(gòu)圖上與其有相似之處。據(jù)記載,以墨畫梅始于北宋末年衡山華光僧仲仁,其弟子揚無咎不滿當(dāng)時朝廷黑暗多次拒絕做官,并以松石、水仙抒寫懷抱。揚無咎的《四梅圖》《雪梅圖》中的梅花“格韻尤高”,他畫梅畫竹是畫其影而得其韻,《百花圖》中的梅如出一轍。由此可見,南宋諸多流派的傳世作品均體現(xiàn)出“革新”和“過渡”的特征,而《百花圖》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和表現(xiàn)手法正是諸多可能性中的一種。
筆者認(rèn)為,《百花圖》的作者對于院體畫的勾勒用筆、層層渲染的嘗試是非常成功的。在師法自然、造型嚴(yán)謹(jǐn)?shù)那疤嵯拢尸F(xiàn)畫面的清雅感,表達(dá)了獨特的審美情操,符合當(dāng)時社會審美需求的同時又保留了自己的主觀創(chuàng)造性因素,值得后人學(xué)習(xí)借鑒。
三、《百花圖》的表現(xiàn)手法分析
正如上文在分析《百花圖》的創(chuàng)作背景時所談到的,此畫的風(fēng)格應(yīng)屬揚無咎一派,但在題材、內(nèi)容和表現(xiàn)手法上又有不同之處。取材上,畫面中60多種花卉草木,其屬種科類歷歷可辨,純用濃淡墨色來表現(xiàn),實屬不易。筆者認(rèn)為《百花圖》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可以歸納為兩點。
一是以造化為師,如實反映自然面貌。《百花圖》的作者遵循“師法自然”“以形取神”的原則,與文人水墨畫偏重筆墨情趣不同的是,其精確地表現(xiàn)了各種花卉的特征,甚至一些細(xì)節(jié)方面都十分考究。比如側(cè)開的百合,花朵是按一定的角度傾斜著的;盛開而已經(jīng)有凋謝勢頭的牡丹,花瓣舒展的同時又有起伏的趨勢;花瓣已經(jīng)怒放的石蒜,一枝枝獨立的花團(tuán)向四周呈放射狀開放,此時的葉子還未萌芽,作者準(zhǔn)確地抓住了石蒜花的典型特征;圖卷中最能表現(xiàn)作者對客觀對象的觀察能力以及嚴(yán)謹(jǐn)?shù)膭?chuàng)作精神的,莫過于畫面角落中的一株連翹,筆者在北京寫生的時候細(xì)致地觀察了自然界中生長的連翹花的特征,與《百花圖》中的表現(xiàn)別無二致,即先花后葉,花瓣已經(jīng)盛開而嫩葉還剛露芽,畫中這株連翹大約3 cm × 8 cm,在堪稱巨作的《百花圖》中,只是一個小小點綴而已,但作者對于細(xì)節(jié)嚴(yán)謹(jǐn)?shù)目坍嫼蛯Υ笞匀坏纳鷦釉佻F(xiàn),體現(xiàn)了《百花圖》獨特的魅力。
二是集眾家之長、表現(xiàn)手法多姿多樣。在《百花圖》中,作者對各家技法信手拈來,并恰到好處地應(yīng)用到對各種不同氣質(zhì)的花卉的刻畫中,變化多端而又互相交融、渾然一體,沒有突兀的感覺,對于筆墨的運用達(dá)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首先是卷首的梅花,從技法上看,與揚無咎的墨梅有密切的聯(lián)系,用勁利的墨線將枝干沒骨勾出,表現(xiàn)出末端梅枝的嬌嫩感。運用白描手法圈出花朵,沒骨點花托,并且加以淡墨烘染花瓣,襯托出寒梅潔白的感覺,亦保持了梅花迎風(fēng)傲霜的本色。雖比起揚無咎的《四梅圖》稍顯稚拙,但其與周圍的茶花搭配又顯得和諧含蓄,與整卷的氣質(zhì)一致。在畫石竹花和梨花時,則用沒骨的手法表現(xiàn)枝莖,先用淡墨寫出,于節(jié)梗的部分略加提染,梨花的花托部分亦是運用沒骨法,干凈利落。
其次,對氣質(zhì)雍容華貴的牡丹花的刻面,又換了另外一種手法,花瓣的長線勾勒細(xì)膩均勻,排列節(jié)奏起伏多變,位置考究得體,將花瓣的柔軟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似乎每一片花瓣都具有呼吸的韻律;花蕾則用形狀統(tǒng)一、著墨略重的小筆觸畫成,從局部看,每一小簇筆觸都呈有規(guī)律地、放射性地排列,從整體看所有筆觸又都向中心聚攏,渾然一體,將花蕾圓球狀的體積感完整地呈現(xiàn)了出來。用筆的粗、重、短也與花瓣的細(xì)、輕、長形成對比,營造了視覺效果上的空間感,具有裝飾美感。
宋人《百花圖》著重表現(xiàn)的是花卉,鳥蟲等只是點綴,但這并不代表作者在鳥蟲的刻畫上就沒有下功夫。畫面中有一只很不起眼的蜻蜓,放大仔細(xì)端詳,足足用了粗細(xì)輕重不同的數(shù)十筆去勾勒,翅尖渲染亦十分到位。有趣的是,蜻蜓的面部被處理成一個小小的人臉形狀,作者樂于在這一粟之大的角落刻畫出如此擬人的細(xì)節(jié),在稍作夸張的基礎(chǔ)上使畫面在細(xì)節(jié)上更加富有情趣。
細(xì)節(jié)上的精致追求并沒有使《百花圖》成為單純展示技法的圖譜。無論是折枝式的穩(wěn)重構(gòu)圖、花朵之間的繁簡穿插安排,還是鳥蟲與花卉的相映成趣、池塘游魚相嬉戲的生動畫面,作者想借此表達(dá)的,是一個生機(jī)勃勃的大自然,一個凝固在紙面上的有生命的花鳥世界。如此有情有趣的畫面,令人百看不厭。這便是“以小觀大”,即通過自然界的微小事物,反映出大千世界的無限生機(jī)。這是與自然交融之后,對造化由衷的禮贊,借助花鳥在自然中的狀態(tài),傳達(dá)一種“天人合一”的意境,并以此自喻,從而感染觀者。
四、結(jié)語
面對兩宋之間社會環(huán)境的巨變,《百花圖》對院體花鳥技法進(jìn)行了保留,用淡泊的水墨語言描繪出了一幅恬靜的畫面,表達(dá)了獨特的審美情操和清雅感覺,符合當(dāng)時社會審美需求。同時,《百花圖》營造了“靜”的境界,追求空靈、寂靜,以及高逸的文人審美趣味,對后世水墨花鳥畫的發(fā)展具有重要作用。這種純水墨的表現(xiàn)形式,也迎合了先秦哲學(xué)“以素為貴”的審美思想,開啟了花鳥畫的新風(fēng)。
注釋:
①本文所論的墨花墨禽,主要指以水墨或水墨淡彩工筆描繪的花卉禽鳥,包括工筆為主,局部沒骨或?qū)懸獾幕ɑ芮蔌B畫,不包括梅、蘭、竹、菊和龍、馬、畜、獸等題材。
參考文獻(xiàn):
[1]洪再新.中國美術(shù)史[M].杭州: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0:193-194.
[2]徐邦達(dá).從“百花圖卷”再論宋元以來的水墨花卉畫[J].文物,1959(2):46,77.
[3]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畫繼[M].長沙: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0:152.
[4]宣和畫譜:卷十七[M].長沙: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1999.
作者單位:
廣州城市職業(yè)學(xué)院關(guān)山月中國畫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