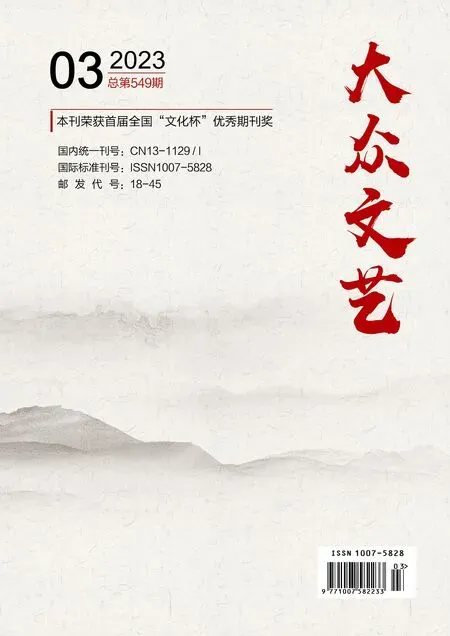末日、科技與自然
——阿特伍德作品探微
楊舒惠
(倫敦大學人文與藝術學院,倫敦 WC1E6bt;上海市建平中學,上海 200135)
1962年,《寂靜的春天》第一次在文學作品中觸及生態惡化這一話題[1]。Lawrence Buell,一位美國生態評論家,稱這本書開啟了文學作品的生態末日元年(289)[2],因為它描繪了環境帶來的滅絕,而不是“炸彈或屠殺”(295)[2]。此后,自七十年代,科幻作品中誕生了“生態轉向”。科幻開始專注于“被局限于一個資源有限且急劇萎縮的星球之上的人類該如何長久地存活下去”這一議題(Canavan 149)[3]。它呈現了人們對于嚴重的環境和生態問題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后果的擔憂。“或許在想象中深陷地獄”,人類才“有望日后在現實中得以超生”(Buell 295)[2]。
對人與自然的關注貫穿于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garet Atwood)的作品中。《羚羊與秧雞》發表于2003年,小說中人類濫用科技改造自然,瘋狂程度令人發指,秧雞——一個瘋狂的科學天才,觸發了災難的終極按鈕,以病毒結束了現世的人類,將世界交到他所創造的秧雞人手中[4]。雪人(又叫吉米)是一個孤寂的幸存者,故事以他的視角在他充斥著混亂和掙扎的往昔回憶中展開。2009年,阿特伍德的另一部作品《洪水之年》是《羚羊與秧雞》中反烏托邦構想的繼續。兩位主人翁,瑞恩和托比,在大流行病中生存下來,并遇到了他們已經加入上帝園丁(the God Gardeners)的老朋友[5]。他們對衰敗時代的回憶承載了被濫用的科技、被腐蝕的社會和被摧毀的自然之間激烈的沖突,而在這樣的末日災難中,浮上水面的是一個根本性的終極議題:人類在自然中的身份是什么?科技可以使用到何種程度?
末日災難已經是一個被大量討論的話題,它逐漸成為一種理應被讀者預先理解的文化預設(culturalpresupposition)。這個詞就像“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一樣①,是不證自明的。人類對于“末日”根深蒂固的恐懼是一種懸浮于人類社會上空的永恒的警示,以最可怖的圖景強迫人類面對可能的最糟糕的結局。但與此同時,正因為其極端性,它與現實的距離使得它永遠置于想象的領土內,讀者傾向于將它和現實聯系起來但不會錯認為它就是現實,讓你從近處凝望深淵,卻慶幸于尚未身處深淵。
末日隱喻的邏輯在Pavel的“距離原則(principle of distance)”和“相關性原則(principle of relevance)”中可以找到解釋。“人類想象活動最普遍的目的就是創造距離”(145)[6]。比如,丑聞,從群體體驗的親密性中被抽離出來,眾所周知但并無傷大雅(145)[6]。這種距離感有著雙重效果。一方面,通過虛擬世界中的放大(augmentation),它在感官上給予讀者最強烈的沖擊,另一方面,它不會使讀者完全陷入絕望,從而使他們可以去思考另外的可能性。然而,距離本身并不能影響讀者,真正使得讀者與故事產生鏈接的是“相關性”。Pavel認為“邏輯推論(logical conclusion)”和“道德普遍化(moral generalization)”可以催生這種相關性,即“因為某個做了錯事的x被施以嚴重懲罰,那么所有做了錯事的x都將淪落至相同的命運”以及“因為這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那么它也可能發生在我身上”(145-146)[6]。
將這一相關性原則應用于末日隱喻,即為:既然有盲目崇拜并濫用科技的人受到懲罰,那么所有濫用科技的人都會受到懲罰;我是人類之一,我也將受到懲罰。此外,正如阿特伍德本人所說,她的書中“呈現的一些普遍趨勢和細節十分接近事實,值得引起我們的警覺”(《洪水之年》445)[5]。所有的人造生物比如器官豬(pigoons)和狼犬獸(wolvogs)本質上都是對已經存在的生物科技的仿擬(mimesis)。而書中描寫的消費主義和大公司的腐敗更是自20世紀中后期就廣為人知的社會問題。
在距離性和關聯性的配合之下,末日世界成為一種試驗各種“備選項(alternatives)”的場地。在《羚羊與秧雞》和《洪水之年》這兩部小說中,末日是腐壞的舊世界的終結、擺脫人類掌控的新紀元的開始,即“千禧年的新展望(the millennial revelation of a new age)”(Synder 486)[7]。正如Canavan所說,“末日是我們這個時代唯一有希望撼動舊體系、創造新的自由空間、使得新的生命形式成為可能的力量”(139)[3]。優化(amelioration)已經不能夠解決問題,只有通過裂變(a radical break)。對于人類,秧雞已經徹底失望,所以他選擇毀滅,“把主人的武器對準主人”(Gutiérrez-Jones 146)[8]。他用生物技術創造了只傷害人類的大流行病。諷刺的是,人們都很樂于吃這種藥丸,因為它宣揚說可以預防一切性傳播疫病,保證無限的性能力和更持久的青春。
在《羚羊與秧雞》中,末日的到來幾乎不可避免,秧雞認為總有一天人類的需求將超越自然的給予,而他僅僅是加速了這個痛苦的進程。自然衰敗的背后,是人類社會無可救藥的腐敗,人類社會處于一種科技迷信(technophilia)之中,科技掙脫了最后一絲約束。只有“數字人(numberpeople)”才是被尊重的,而其中生物工程師更是精英。是否存在可以制約科技、恢復自然秩序的力量?政府?法律?道德?人性?很不幸,這些都不再重要。政府和法律名存實亡,維護秩序的是“公司警(CorpSeCorps)”。顧名思義,“公司警”掌握在公司手中。道德,尤其是生物道德,則是書中濃墨重彩書寫的一個重要方面。當去參觀“雞肉球(ChickieNobs)”和“狼犬獸”時,讀者正如書中的主人翁吉米一樣,不得不發出詰問:多少是太多?多遠是太遠?書中科技使用的細節難以逐一細細深究,那將是更深入的生物領域的話題,但可以確定的是,不同物種之間的,乃至人類和非人物種間的邊界都在不斷模糊,物種的自然身份不再是固定不變的。比如父母很樂意“定制”他們的孩子。走進商店,父母就可以選擇他們孩子的所有特征。在科技面前,自然喪失了造物的尊嚴。
然而,秧雞毀滅世界的決定,不僅僅來源于糟糕的現狀,還來源于他對人類文明整體的否定。如果人類本身就是最大的威脅,人類文明就是最嚴重的錯誤,那么人類是否還值得拯救?兩本書中,個人的悲劇和人類歷史更宏大的災難并置于末日世界的敘事中,形成了極度悲觀的情感氛圍。書中的每個人物故事,幾乎都充斥著不幸。吉米親眼看到他加入反叛隊伍的母親被公司警射殺;秧雞的父親由于發現了公司研制致病類藥物的秘密,而被推下橋身亡。至于這種藥物,設計的秘密則在于,“病人應該正好在傾其所有之前痊愈或死亡”(阿特伍德,《羚羊與秧雞》219)[4]。在《洪水之年》中,托比的母親正是死于此種病毒,而她的父親破產并自殺。個人的敘事遍布創傷,正如人類的歷史。
吉米與秧雞玩的一款游戲,“血和玫瑰”中,文明的輝煌與殘酷被同時放上審判臺,得出的結論令人失望,與鮮血相比,玫瑰是那樣微不足道。“沒有一部文明史不是野蠻史”(Benjamin 256)[9]。既然文明是一場恐怖,歷史是一頭怪物,人類是最大的錯誤,那么末日,憑何值得吊唁?談道《羚羊與秧雞》,正如阿特伍德本人所說:“我們有什么可取之處?誰想拯救我們?”[10]“這些想法與多數評論者所持觀點不同,他們認為人性是流動的、順從的,并且認為人性總能對客觀現狀作出反應”(Garrard 224)[11]。從這個角度來說,阿特伍德本人并不認為人性可以依據現實情況作出調整和反應。秧雞觸發末日的按鈕,毀滅的不是世界,而是人類,在人類的毀滅中,世界重獲新生。它宣布人類退出世界史,這不是世界史的終結,而是人類世(Anthropocene)的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后人類生物——秧雞人(crakers)。
秧雞人類人,但不是人類,他們尚沒有文明,也尚未有罪惡。在災難后的世界,雪人的處境很像“最后的人”(The Last Man),代表著在優異超然的新物種面前腐壞的舊人類。秧雞人挑戰了雪人所代表的人類的地位和尊嚴,迫使他——也迫使我們,思考后人類世紀作為人類意味著什么(Adami 258)[12]。這一想象本身就挑戰了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是對人類的愚蠢和自大的戲謔。
《洪水之年》中的宗教元素是原始主義之外另一個值得探究的方面。Gutiérrez-Jones認為,書中宗教元素以末日預言的形式存在,無水之水將使得人類遭受如此巨大的損失,在這樣巨大的損失面前,人類對自然種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維定式將難以為繼(143)[8]。此時末日是一種宗教神話——最初的約束人類的傲慢的方式并提醒他們在認知之外更有無可抗拒的力量存在。亞當堅信,在艱難的自然和社會條件下,人類并不關心其他物種。至于懲罰,不論是否有“上帝”這一不可抗拒的力量,懲罰也終將到來,但是“如果必須有懲罰,他們想要一個判罰者,他們不喜歡毫無理由的災難”(阿特伍德,《洪水之年》 241)[5]。由此說來,秧雞和亞當都試圖找到一種阻止人類的方式,秧雞選擇用專制的獨裁的手段,而亞當選擇宗教的共情的。不論是哪種方式——泯滅人類或把人類交還于上帝手中,都徹底顛覆了人類中心主義,消解了人類于自然中的中心位。在亞當眼中,人類甚至不得不將自己算為蛋白質,維持食物鏈的循環。盡管“如果我們更喜歡當盤中餐而不是食客的話,我們就不是人類了”(355)[5]。然而當人類構建起的“秩序”的堡壘已經轟然倒塌,那么便沒有什么能夠再保護我們永遠做個食客。
多數情況下,“人文精神”被看作人類尊嚴和希望的象征。但在《羚羊與秧雞》中,關于人文精神的信陽市已然崩塌,藝術與科學借吉米和秧雞之口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科學毫不留情地始終占據高位。正如Northover所說,秧雞和吉米的對話,更像是秧雞本人高談闊論的獨角戲(85)[13]。而在《洪水之年》中,雖然上帝園丁不再自視為世界的中心,但人文精神卻是高舉于世界廢墟之上的火炬。在書的結尾,當重病的吉米與上帝園丁相遇,他口中反復說著的詞是“音樂”。吉米聽到有人在唱歌,他露出狂喜的神情,并動情高呼“你不能消滅音樂”“辦不到!”(阿特伍德 443)[5]。而隨后故事定格的尾聲,就是人們看到“火把搖曳的光芒,曲曲折折地穿過幽暗的樹林,向我們走來”(444)[5]。如果說音樂代表人文的光輝,那么此時的火把則寓意著人文精神始終是人類的希望。文明已成廢墟,但人文精神永存。
文藝復興以來,人類幾乎被賦予神性,被看作萬物之首的存在。人文主義打開人類自我認識的大門,之后改變世界的是一場科學精神的洗禮。人類被鼓勵探索宇宙,發現關于萬物的真理,自然世界逐漸被科學和技術的世界所取代。在這樣的世界里,自然成為實驗室研究的對象和工廠生產的原材料。隨著科技獲得越來越大的力量,它對自然的攫取愈發猖獗,毀壞環境、改變物種。人們開始關心環保和倫理問題,這種擔憂也體現在文學領域。多少是太多,多遠是太遠,這不僅是阿特伍德這兩部作品的核心問題,也是全人類所應共同思考的問題。文學想象或許不能提供最終的答案,但它迫使讀者直面末日的荒誕和可怖,擺脫現實世界的定勢,重新審視習以為常的或尚未留意的一切,從而思考科技、自然與人類之間龐雜而幽微的關系。
注釋:
①英國作家瑪麗·雪萊于1818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如今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的解釋為“失控的受造物(常毀滅創造者)”(used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sb.creates or invents that goes out of control and becomes dangerous,often destroying the person who created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