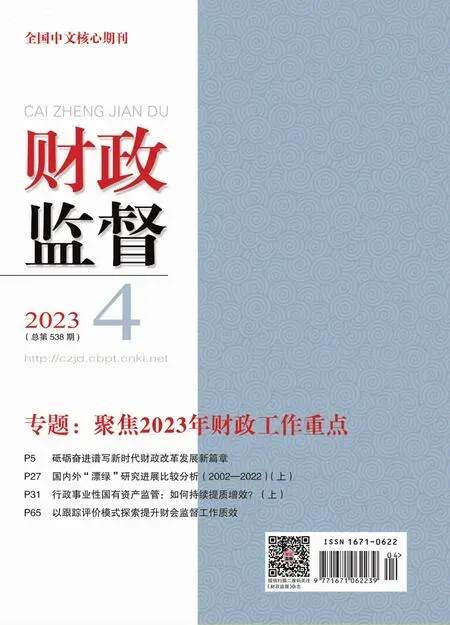“資產減值準備”成為企業利潤的“調節器”
●羅 薇
一、案例背景
甲公司是一家具有金融控股性質的地方國有獨資企業,其主管部門負責對公司發展和治理、業績和利潤等進行指導和考核。根據甲公司年報反映,2018年及2019年,分別實現利潤3.53億元及4.96億元。
2020年9月,財政部派出檢查組對甲公司會計信息質量開展檢查,就賬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相關問題進行追溯和延伸時發現:
2017年,根據劃轉協議安排,甲公司擬持有A信托公司20.44%的股權。甲公司在轉讓程序未獲得審批之前,即投資股權未實質辦理變更、不享有股東權益時,提前確認對A信托公司的長期股權投資,隨后審計調整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并以享有A信托公司2016年末凈資產份額作為初始投資成本,導致甲公司2017年年報虛增資產17.88億元。
2018年和2019年,A信托公司財務狀況持續惡化,經審計凈資產分別下降為32.55億元及20.49億元,同時因違反業績承諾,被第三人起訴追償38億元。甲公司本應根據其持股比例和A信托公司年報凈資產的變化及時確認資產價值、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并披露重大追償事項。但甲公司對此選擇性的“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反而將其作為利潤的“調節器”,既不披露重大事項,也不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分別導致甲公司2018年及2019年年報虛增利潤11.12億元及2.5億元。
綜上,甲公司連續三年年報中反映的重要會計信息指標 (資產和利潤)嚴重失真。
二、違規事實
(一)虛增資產
事實上,2018年1月,A信托公司修訂本公司章程并經當地銀監局批復同意,甲公司才正式成為其股東并享有股東權益。因此,甲公司應于2018年確認對A信托公司的投資。2017年3月,甲公司未按照 《信托公司管理辦法》等有關法律法規規定辦妥相關手續即將劃轉入的A信托公司股份計入長期股權投資17.88億元,并在當年年終審計時調整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直接導致甲公司2017年虛增資產17.88億元,甲公司經審計的2017年合并凈資產總額為87.05億元,虛增比例高達25.85%。
(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存在減值跡象,未計提減值
2018年,A信托公司年報凈資產32.55億元,甲公司按股權比例享有凈資產6.75億元,應確認減值準備11.12億元,確認后甲公司2018年利潤應從3.53億元調整成-7.59億元。2019年,A信托公司年報凈資產20.49億元,甲公司按股權比例享有凈資產4.25億元,應確認減值準備2.5億元,確認后甲公司2019年利潤應從4.96億元調整成2.46億元。
(三)利用虛假財務信息發行中期票據
2019年11月,甲公司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成功發行“201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據”9億元。根據《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第十八條 “資信狀況符合以下標準的公司債券可以向公眾投資者公開發行,也可以自主選擇僅面向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發行人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不少于債券一年利息的1.5倍”的規定,甲公司2018年利潤實際為-7.59億元,即甲公司2016—2018年未能實現連續三年盈利,不符合發行公司債券條件。
(四)未披露金融工具信息及或有事項
2019年,A信托公司與其他公司存在重大涉訴糾紛,其他公司主張A信托公司的補償金額高達38億元,且該重大涉訴糾紛在裁判文書網、公開媒體渠道均可獲知。甲公司在明知前述事實的情況下,未按準則規定在其2019年審計年報中披露金融工具信息及或有事項,也未計提預計負債。
三、違規動機及原因分析
(一)粉飾企業利潤,滿足主管部門業績考核指標是其主要動機
在提高市場經濟活力、推動企業實現保值增值的新形勢下,各地為提高所屬國有企業的競爭力,主管部門對國有企業負責人及整個管理團隊設置相應的績效考核辦法,一般形式就是雙方簽訂經營業績責任書,責任書中設定了年度實現利潤目標、薪酬分配方案等指標。在獲利驅動和經營不善的壓力下,國有企業負責人及管理團隊不得不通過調控經營業績來應付績效指標考核。
(二)美化企業財務報表,以便達到獲取銀行信貸、發行企業債券等目的
企業本可以通過資產減值計提消化長期積累的不良資產泡沫,優化資產質量,使財務報表能夠更加客觀和真實地反映企業未來獲取經濟利益的能力。但是在實務中,資產減值準備的會計政策可選擇性較大,其確認和計量對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和經驗積累要求較高,這就給企業在操縱可自由控制損益確認的項目時,隨意在不同會計期間轉移利潤的空間,即企業具備利用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和轉回來平滑利潤、裝飾報表的條件。如本案例中,甲公司在利潤較低時,不計提減值準備,避免虧損,通過“好看”的會計報表達到銀行信貸、企業發債等的條件并獲取相應融資。
(三)企業會計報表在銀行信貸管理和企業債券發行中的作用被弱化
企業會計報表本應是判斷企業盈利能力、償債能力及投資回報率等的重要依據。但從實際情況看,銀行機構在擴大貸款規模、債券發行機構為完成業績任務的利益驅動下,對企業會計報表真實性的重視程度降低,不愿且不會投入必要的時間和精力去辨別和核實企業提供會計報表的真實性和有效性,極大地影響了其他需要通過銀行機構或債券發行機構去了解對應企業的關聯者,對該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影響的重要程度作出客觀、合理的評估。
四、案例涉及知識點
本案例主要涉及 《企業會計準則第13號——或有事項》第十四條,《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第四十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企業會計準則第2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更正》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以及《企業會計準則第37號——金融工具列報》第十四條等有關知識點。
五、啟示與思考
(一)提前介入全程監管,提升法治權威性
當前,我國主要通過年報事后審查對企業資產減值計提事項展開監管,監管反饋滯后,這就為企業利用計提大額資產減值準備達到粉飾業績或突擊創利等動機埋下伏筆,如近年來不斷出現上市公司商譽減值的“暴雷”現象。監管部門如能提前介入,充分發揮出警示糾偏功能,對企業形成商譽的整個過程開展閉環監管,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利用計提大額資產減值準備操作利潤的風險。此外,隨著我國經濟迅猛發展,對企業違規操作的處罰措施和懲處力度已不適用,監管震懾威力不夠,應從制度上堵住企業可隨意操作的空間,充分發揮財會監督的權威性和威懾力:一是結合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形勢,進一步修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從制度層面加大對企業會計選擇權的監管力度;二是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加大對企業信披違規、利潤操控等行為的處罰力度,從行為層面明確堅守對企業會計信息質量造假行為的零容忍底線,更好地維護法治監管的權威。
(二)完善準則確定性,提高操作可行性
企業判斷資產是否減值、是否需要計提減值準備時,主要從資產可收回金額是否低于賬面價值來加以判定。但實務中,資產可收回金額的確定無論采用公允價值還是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主觀性都較強,完全依靠企業財務人員的執業經驗和個人判斷。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況,公司治理也因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導致管理層和股東之間利益沖突等結構性缺陷,監管部門應更加謹慎地賦予企業自主選擇和變更會計政策的權限,比如增加企業對計提減值準備的金額、比例方面的審批控制,進一步明確相關會計處理,提高準則的可操作性。
(三)加強職業素質培訓,提升判斷客觀性
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對財務人員是否能夠充分估計經濟環境和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而作出判斷要求很高,需要具備較完善的職業素養和行業經驗。因此,如何培養財務人員良好的職業道德以及提高財務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和專業技能,使其在對不確定性的事項進行恰當估計和判斷時,能夠作出謹慎、科學、客觀的判斷是亟待解決的一項既基礎而又重要的課題。需要從強化法治觀念、加強理論知識、提高業務素質、拓展知識結構以及增強風險防范意識等多方面入手,不斷營造財務人員良好的從業環境和提升其客觀公正的執業能力,確保企業會計報表可以如實反映資產的狀況和真實的盈利水平。